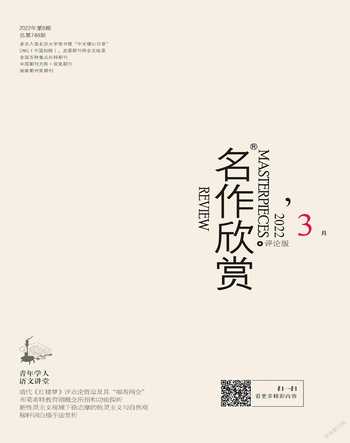从文本到舞台
董佳慧
摘要: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普通人隐秘的心理与情结,展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西方文化交汇时人们的情感、婚姻生活,揭示了传统与现代融合下的社会中女性仍然无法摆脱男权压迫从而引发的悲剧人生。田沁鑫导演将此小说改编为同名话剧,从话剧的角度将其情节重新解构,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本文将从舞台、时空、人物三个方面来对《红玫瑰与白玫瑰》的叙事艺术进行分析。
关键词:舞台 人物形象 时间空间 话剧改编 田沁鑫
《红玫瑰与白玫瑰》是张爱玲为数不多的一部中篇小说,写出了普通夫妻生活间的种种难言之隐,也反映了男女不平等的地位给女性带来的悲惨命运。不论是红玫瑰还是白玫瑰,最终的结局都令人叹息。小说改编为话剧,关键在于如何用舞台调度来表现冲突,也就是如何表现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以及人物内心矛盾。田沁鑫导演巧妙地借助戏剧舞台,将人物一分为二,分别由两个演员来饰演,更加鲜明准确地揭示出张爱玲小说的那些隐晦的心理活动。话剧用极简写意的方式将舞台划分为三个部分,打破了原本的叙事结构,增强了人物之间的戏剧冲突,摆脱了原文沉闷、难嚼的压抑气息。本文将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进行分析。
一、舞台效果处理——对于爱情、家庭的选择
剧本基于文学,再加上剧本语言,方可登上舞台。读过张爱玲小说的人都知道,她的小说一般都很难改编成戏剧登上舞台,因为太过于真实,也过于隐晦。正如张爱玲小说中所讲:“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原文本中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繁华布景下的旧上海时代展现得淋漓尽致,读起来令人压抑、叹息。
田沁鑫导演将舞台分为三个部分,左边是佟振保的家,里面是笼统的白的孟烟鹏,右边是王士洪的家,里面住着如火般热情的王娇蕊,中间是一条通道,男人可以在中间的通道中随意地窥探红白玫瑰中任何一人的活动,而女人则只可以在固定的房间内徘徊,仿佛是禁锢在玻璃展台下的两朵玫瑰花,任由男人观赏和定夺。田沁鑫导演的这种舞台艺术充分展示了当时年代女性的地位以及女性在当时环境中的符号性特征。这种布置舞台的方法,使原本难懂的文本更直接、自然地展现在人们眼前,艺术形象最基本的特征就是直接性,而田沁鑫导演运用戏剧语言对于原文本的重新解构使得更多人读懂了张爱玲心中的那份无奈和感慨。对爱情充满期待的永远都是女性,无论是勇敢追爱,还是安分守己,都不得善终。在这个舞台上不论是受丈夫深爱的情人还是讨嫌的妻子,都一直处在被动的局面,受男人思想的动摇。而饰演佟振保的两个演员来回穿梭在四个“玫瑰”之间,虽然直观地看起来佟振保一直处于支配、主导的地位,但不论是在情人那里还是妻子那里,他都逐渐被折腾得有气无力,社会以及世俗的眼光也使他身上的负担越来越重。在一个男权至上的社会中,女性深受着有形的压力,而男性则深受于无形的压力,同样也身处于水深火热当中。
在这个舞台布局中,左右两边的红白玫瑰可以比作是男人的左右心房,左边心房藏着妻子,家世清白、内心干净,但又不会保守没有趣味,右边心房藏着情人,热情似火,婴儿般的头脑以及成熟魅惑的身体,却又经受不住世俗的眼光。这样巧妙的布局正是田沁鑫导演对张爱玲小说那部分隐晦内容直观反映出来,形成了一部带有喜剧色彩的悲剧。这种舞台布局将同时上演男主人公与红白玫瑰之间的感情故事,一边是喜一边是悲,使观众不用阅读原文本,也能设身处地地感受到这一场荒诞的爱情故事。
二、时间与空间——电影符号化及戏曲的舞台艺术应用
张爱玲的这篇小说用西式的手法来写中国普通人的家庭故事,结构自由新颖。田沁鑫导演也看到了这一特点,采用西方舞台戏剧艺术来改编原文本,打破了原有话剧“三一律”的特点以及线性的叙事方法。将男主角与两位玫瑰的感情状态发展同时展现在观众眼前,这种表演手法打破了时空的局限。剧中一开始饰演红白玫瑰的四位演员便讲述自己的故事,经历过几段感情的波折,可以直接地反映出红白玫瑰在对待感情时内心的挣扎、徘徊以及到最后对爱情的希望彻底磨灭。男主人公佟振保随着时间的推移,感情由兴奋变得默然和痛苦。舞台上将处于过去式的红玫瑰和被家庭事物繁琐的白玫瑰,置于同一空间,开始同时叙述佟振保与烟鹏和娇蕊之间的故事,这种手法更直观地表现出舞台上每个人物对于感情在灵魂深处的挣扎,这样的布局一直到话剧结尾,让观众从一开始的迷惑到最后的豁然开朗,开启了一场另类的叙事空间。舞台上不同时空的红白玫瑰向观众叙述着自己的生活习惯与感情过往。而剧中的男主人公注定也终将在红白玫瑰之间纠缠,这种设置完全打破了时空的界限,将剧中三位主人公的关系直观明确地展现在观众眼前。
(一)电影符号化剪辑艺术在戏剧舞台的灵活应用
田沁鑫导演在与戴锦华老师的一次访谈中谈到:是中国传统艺术滋养了她,使她在舞台上变得写意性强,游戏感强,时空的流变非常自如。她直言到现在为止她的戏剧结构文本也很像电影的结构方式,是受到戴锦华老师课程的影响。《黑色追缉令》和《罗拉快跑》两部电影都对她受益匪浅,所以舞台上会有插叙、倒叙、平行蒙太奇出现。田沁鑫导演的神奇之处就在于把电影中符号化的剪辑方式灵活地运用在了戏剧当中,电影的剪辑艺术为自己戏剧的叙事来服务,从而有了自己独特的叙事风格。在左右房間固定的红白玫瑰使男主人公振保在过去和现实中来回穿梭,过去与现实融为一体,而男人的不同态度也跃然眼前,不用过分解读就能读懂张爱玲原文中的内涵。譬如舞台上的白玫瑰穿上圣洁的婚纱走进婚姻的殿堂,而一旁的红玫瑰却因为被抛弃伤心欲绝,最后披上了盔甲。两种鲜明的对比形成强烈的反差,成了一部女性命运的“二重奏”,不停地撞击着观众的心灵。男人在面对热情如火的情欲终究选择了平淡。也正如张爱玲所说:“如果爱情是一场劫,那么每个人都要历经劫数才能重生。”这种时空的重新编排使剧中人物的遭遇更加扣人心弦,也让张爱玲原文中那种沉闷的心理活动更加直观地展现到舞台上。
(二)中国戏曲表演艺术在话剧中的应用
田沁鑫导演对于戏剧舞台的表演杂糅着对中国传统戏曲文化的继承,对于舞台布景的极简式以及表演动作的程式化、假定性,她在与戴锦华老师的访谈中谈道:自己戏剧的形式感首先有中国戏曲的滋养,小时候就开始学戏的她,受到戏曲潜移默化的影响,譬如它的中和之美,还有“超脱之虚,夸饰之奇”以及生旦净末丑的角色分配,还有身体表达、造型意识,这对她后来的创作都是有巨大影响的。
戏曲的假定性是戏曲特有的表现形式。例如,梁山伯与祝英台走了七八里路,时间地点不断变化。中国戏曲艺术承认演戏的作用,才使得这场戏不需要那么长时间,不需要任何布景,凭借演员的唱词和舞蹈身段造成移步换形,舞台上以来回不同的方式走走停停、翻山越岭、涉水过桥等,所需要的各种意境就表现出来,从而取得良好的演出效果。田沁鑫的个人经历使她的戏剧受到了中国戏曲写意式与假定性的影响,中西方文化融会贯通,构成了自己戏剧独特的艺术魅力。例如剧中佟振保与王娇蕊的钢琴合奏,很直观地反映出二人琴瑟和鸣和当时的感情正在升温;而当佟振保与红玫瑰即将分离时,同样的用奔跑的反方向来象征。在极简的舞台背景下,通过几位演员富有激情的肢体语言动作表演将原文中隐晦的心理活动直观地展现在观众眼前。观众也见证了爱情从萌芽到枯萎的全过程,剧中家务的琐碎以及丈夫的冷漠也使观众感同身受,反映出当代普通家庭中的现实生活。再如话剧中用一件衣物直接代表了振保母亲,将原文中不重要的关系淡化或者抹去也是独特的艺术魅力,但并没有使整个戏剧出现断层。田沁鑫导演对于舞台的设计也是她内心对于张爱玲故事的另一张脸谱的形成,这种写意性的舞台设计,也脱离不了她本身对于中国戏曲的理解,所以形成了这场中西方文化融会贯通的视觉盛宴。
三、人物形象的设计——理智与欲望的斗争张爱玲用小说的题材来叙述这个故事,通过环境的烘托和细腻的心理描写来刻画每个人物灵魂深处的感情世界,但是这种文字的表达在戏剧舞台上是难以实现的。戏剧体裁的关键就是体现冲突,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田沁鑫导演突破常规,用两个演员去饰演一个人物的两个不同的心理,一个本我,一个自我,一个是欲望,另一个是理智。通过欲望和理智之间的对话、动作以及他们之间不同的立场来体现人物内心的挣扎、彷徨和痛苦,从而使整个人物更加丰满。观众更直观地看到爱情从萌芽到凋零的整个过程。此外,这种设计手法增强了原文本与话剧的差异性,台上演员甚至隔空与张爱玲喊话,对原人物进行批判,增加了舞台的幽默性与诙谐性,使观众有不一样的观赏体验。张爱玲的原文是沉闷的、苦涩的,笔触却是锋利的。田沁鑫导演在舞台上塑造的故事是带着喜剧色彩的悲剧,使舞台气氛更加活跃,剧中人物可笑而不自知,增强了反讽意味。舞台上两位女性的人物形象都是在男性的视角下包装过的,所以和原文本中的人物形象有所不同。演员也通过夸张的肢体语言和表演来展示人物细腻的心理活动。
每个人物的性格不同,人物的本我和自我出现的比重则不同。红玫瑰王娇蕊拥有着成熟女人般的身体,婴儿式的头脑,她热情似火,所以她自我出现的部分远超于本我,欲望盖过了理智,这也体现了她冲动做事、不计后果的性格。“红玫瑰”的本我一直躲在舞台背后,沉默寡言,她的“理智”在遇到男主人公佟振保之后就被抛到了脑后,“欲望”驱使着她相信这就是“爱情”,而后来的“欲望”开始逐渐凋零,披上盔甲的她最终成长起来,屈服了“理智”。嫁为人妻的“红玫瑰”以“本我”的形象出现,虽然依旧浓妆淡抹,但已经成熟。让观众不由得心生凄凉,感叹当时时代下勇敢追求爱情的女性的悲惨命运。
白玫瑰则与红玫瑰完全相反,她的“理智”压制着“欲望”,本我与自我还经常对话,宛如一对“挛生姐妹”,互相质问对方,使人不經意间捧腹大笑。原文中的孟烟鹏,是“白月光”,她勤俭顾家,处处为丈夫着想,家世清白,规矩守旧。而戏剧舞台上的白玫瑰被塑造成一个大声说话,不会为人处世,不管做任何事都会让丈夫难堪的“粗鲁”角色。这个人物形象是男性心目中的“白玫瑰”形象,当遇到小裁缝的夸奖时,一直不受重视的她,内心突然照进了一束阳光,所以即便她不爱小裁缝,还是在一个雨天出轨了。但她的“理智”最终还是打败了“欲望”,与小裁缝断了联系,丈夫对自己也愈加过分。白玫瑰的结局是穿着带有白色绣花的黑色旗袍,目光呆滞,一举一动都很呆板,这也体现出她的“欲望”和“理智”都已经被毁灭,自我意识崩塌。
佟振保作为剧中的男主角,他的本我经常与自我产生对话和互动,他从头到尾都一直是“理智”与“欲望”的共存。留洋归来的佟振保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是众朋友眼中的“正人君子”,他在“本我”“自我”中挣扎、徘徊,最终屈于社会批判的眼光,选择了平淡的“白玫瑰”。“一个任性的有夫之妇是最自由的妇人,不用对她负任何责任”。他的“欲望”和“理智”终究是相似的,可以说佟振保这个人物一开始就是打着“柳下惠”的名号去开始这段爱情的。一开始他便知道与红玫瑰的这场爱情是不被社会所认可的,但“欲望”驱使着他,“不用负责任”驱使着他。面对欲望和躯体他扑向了王娇蕊,但当发现王娇蕊因为她要放弃婚姻时,他在“本我”与“自我”中挣扎,最终抛弃了她,娶了“白玫瑰”。
四、结语
张爱玲的这部小说主要是通过细腻的心理活动和环境的烘托来展示男女之间复杂的感情故事,将其故事文本完全不做改动地搬上戏剧舞台是很难表现出其中错综复杂的感情线的。田沁鑫导演推陈出新,通过新颖的舞台设计以及一分为二的人物形象表达给观众不论身心还是视觉都带来了巨大的震撼。时空的自由并行,演员激情的动作语言,改变了观众对原文沉闷的印象,开启了一场新颖的舞台表演。田沁鑫导演在原著的基础上对作品重新进行解构,赋予了其新的生命,百年一遇,让人不禁油然发出感叹。田沁鑫导演打破了传统第三人称叙述的方式,而采用回忆追溯的方式来讲故事,更加直观地让观众了解到每个灵魂深处的内心世界。而潜藏在人物内心深处的感情世界通过特定的情况激发出来,这部话剧的时空并行,一角分两人的设置将其完全展示了出来。从这种意义上讲,田沁鑫导演在原著的基础上,运用多种丰富的舞台设计效果将原文本展现得淋漓尽致,最大限度的赋予作品新的生命和时代特色。挖掘人性深层的渴望与诉求,这也是田沁鑫导演所追求的终极表达,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倍感亲切的张爱玲。
参考文献:
[1]彭吉象.艺术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宋文植,许玉.从戏剧到小说——论田沁鑫话剧《红玫瑰与白玫瑰》的艺术魅力[J].戏剧之家,2019(18).
[3]王艺璇.当田沁鑫遇到张爱玲——浅析《红玫瑰与白玫瑰》[J].戏剧之家,2017(6).
[4]田沁鑫.田沁鑫的戏剧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5]高淑敏,林婷.田沁鑫戏剧时空艺术探索——以话剧《红玫瑰与白玫瑰》为例[J].吉林艺术学院学报,20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