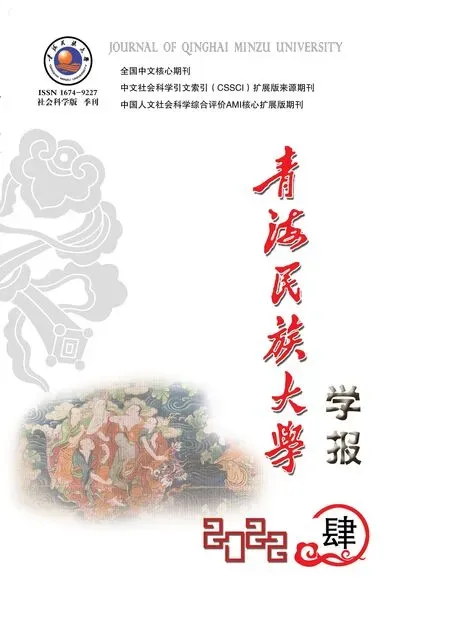富美宫传统的送王船与厦门等地的送王船仪式异同研究
石奕龙
(厦门大学,福建 厦门 361005)
引 言
中国厦门和马来西亚马六甲能联合起来,共同建构“送王船(WangChuan Ceremony)——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的项目,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申报, 并在2020年12月该组织的评审会上顺利通过审议, 获准列入该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Representative List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Humanity)而成为世界级的非遗项目,其主要的合作基础,就是两地的送王船仪式实践有着重要的共性, 即两地的仪式实践都有迎王、送王的过程,而且其中多种因素所体现的意义与象征也趋于一致。 尽管两地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名称不同,如中国为“闽台送王船”,马来西亚为“王舡大游行”,其他方面也有些差异,但由于有着这重要的共性,两地才可能合作建构文本, 联合申报, 并申报成功。 然而,在申报之前,甚至是已获得世界级非遗项目的今天, 民间一些不明真相又不做认真仔细研究的人, 仍存在着一些不符合历史事实与社会事实的言论, 硬是要将一些名称上类似但事实是“送瘟”的仪式与之合并或混为一谈,这将不利于该项目的保护与发展, 也不利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遗产委员会事后定期对遗产项目保护的核实与检查,故很有必要公开辩之、区别之,以辨明事实真相,以利于未来的实践与保护。
一、世界级非遗项目“送王船”的基本共性是都具有迎王、送王仪式
2020年12月17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批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 的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福建南部、台湾南部和马来西亚马六甲等地区的民间,有着各种不同的称呼或俗称,如“送王船”“送王”“做好事”“烧王船”“闽台送王船”(国家级非遗项目的名称)、“王舡大游行”(马来西亚国家级遗产项目的名称)等。 尽管如此,但他们所从事的仪式实践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所从事的“送王船”实践都有迎王、送王的过程或仪式。 简单说,这类仪式是一个具有迎王、送王过程的仪式,也就是说,这类仪式首先有迎请王爷到任的仪式,然后才有送王爷乘王船离去或烧王船仪式,而且定期举行;与只送不迎与非定期举行的“送瘟”“送瘟神”或“送瘟船”的仪式决然不同。
下面我们先多了解一下其仪式的内容与特点,再来辨识与实质为“送瘟”而又表面称之为“送王船”仪式的差别。
首先, 现为世界级非遗项目的送王船仪式都是定期举行的, 不同的只是有的社区一年举行一次,有的社区三年或四年举行一次,有的甚至间隔的时间更长些。如厦门市翔安区新店镇后村村、漳州市九龙江水居社进发宫等每年都举办一次,厦门市思明区厦港街道沙坡尾社区龙珠殿每逢闰年举办一次, 厦门市海沧区海沧街道钟山社区水美宫每三年(虎、蛇、猴、猪年)举行一次,海沧区海沧街道石塘社区每三年(牛、龙、羊、狗年)举办一次,厦门市同安区西柯镇吕厝村、 湖里区禾山街道钟宅社区、思明区前埔街道何厝社区等每四年(鼠、龙、猴年)举行一次,厦门市湖里区金山街道浦口社区六年(虎、猴年)举行一次。
其次,举行仪式的宫庙并非都是“王爷庙”,有的以宫庙为单位,有的以宗祠为单位,有的以村落为单位, 如台湾台南西港的迎王送王仪式由主祀天上圣母妈祖的庆安宫主办, 厦门同安区西柯镇吕厝社区由以供奉水仙尊王、吕祖、姜太公、王爷为主神的华藏庵主办, 厦门湖里区钟宅社区由以主祀观音菩萨的澜海宫与钟姓宗祠主办。
再次,这类仪式都先有“迎王”的仪式,也即这类仪式都事先有在水边、海边举行“迎王”仪式,迎来一尊或几尊王爷后,才有后续的“送王”或“送王船”仪式。尽管迎来、送走的时间并非一致。有的几天,有的几个月,有的几年,有的甚至十几年或几十年。
最后,所迎、送的王爷称“代天巡狩”王爷,人们认为他们是类似传统封建社会的钦差大臣,是到某地来巡狩或镇守的神明,如2018年(狗年)厦门市海沧区海沧街道石塘社区举办迎王送王仪式时的告示云:
禄位高升
玉敕代天巡狩府朱为荣任事照得
本爵钦遵
玉旨巡查胜境,默佑人间介甭景福,兹于十月廿三至廿五
吉时到境视事,凡诸一切行袁(辕)人等,须当洁净斋戒,至期忝谒行礼,毋致混杂参差,合就出示 所仰众善信人等知悉毋遗,特示
右仰各宜知悉
天运戊戌年十月廿三日给
示
主行科事王罗祥承诰奉行
发府前挂谕
玉敕代天府朱氏 为晓谕事照得
皇天眷顾,惟德是依,人心举善,正诚可感,本爵分符
派灵箓,护国庇民,驱妖氛,由水陆自北而南,理
枉伸冤,祸福因其素行赏罚,皆出自公,阴纪可助
阳纲,宜念监察不真,幽条严于明律,勿谓报应
有差,汝等士农工商,各宜守分,官吏胥使,更
当尽心,务使草野之士女皆宁,乡间之鸡犬不
动,植兹冥福,表我神灵,为此晓谕,各宜知悉。
右仰各宜知悉
天运戊戌年十月廿三日给
示 主行科事王罗祥承诰奉行
发府前挂谕
当朝一品
玉敕代天府朱氏为访察民间善恶, 以安民生事,照得
合境众善信等, 今月廿三至廿五日建设禳灾祈安醮科五朝
本爵钦遵
玉旨,代行巡视,择于廿三日吉时到任,体
上天爱民至意,要百姓安乐为心,务须斋戒,诚心祷告
天恩,自求多福,据此,合行示饬该属神将随行,士卒遵
守营卫,不许喧哗,扰害生灵,致干未便,各宜凛
遵慎之,特示。
右仰各宜知悉
天运戊戌年十月廿三日给
示 圭行科事王罗祥承诰奉行

图1 厦门市海沧区石塘社区举行请王送王仪式时的告示
发府前挂谕
即代天巡狩的朱王爷遵上天的玉旨于戊戌年(狗年) 农历十月廿三到廿五到石塘村巡狩“视事”, 故石塘人需在十月廿三日举行迎王仪式,从事一系列祭祀活动后,在十月廿五日举行“送王”仪式,将王爷送走。 又如同安区吕厝村通常在鼠、龙、猴年举行迎王送王仪式,不过在这些民间俗称的“王爷年”中,正月初四在海边(现在海边建有迎王广场)的迎王是迎接新一任王爷的到来,然后此新一任王爷需在吕厝等地镇守四年后才被送走,如鼠年正月迎来的代天巡狩王爷, 要到龙年十月才送走,所以每个“王爷年”正月迎的是这一任的新王爷,十月送走的是上一任旧王。 因此,在举行这类实质上有着迎王、 送王仪式而表称为“送王船”的仪式时,人们多认为这类迎来、送走的“代天巡狩” 的王爷是类似于封建社会中钦差大臣一样的神明,即他们为上天(以玉皇大帝为表征)的“钦差”来地方上代天巡狩,而非“瘟部”的“瘟神”或瘟神中的“瘟王”。
换言之,被列入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送王船”,或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闽台送王船”的迎王、送王仪式是根植于闽南人滨海社区的民俗文化传统中的一种重要的禳灾祈安仪式,其过程通常如下:某个水边的村落或城镇,在定期的某个时间点里,在海边请一尊或几尊“客王”(其称之为“代天巡狩”或“代天巡狩王爷”或“大总巡”“代巡”“千岁”“王爷”等)到该地巡狩、镇守几天或几年后,才会举行送王爷的仪式。 送王时,先准备好一艘用木架纸糊的、模仿官船的王船(即王爷船)或纯粹木制的王船作为搭乘工具以便送王。 送王期间,会竖灯篙,召唤神鬼来赴会, 用丰盛的供品祭祀将要离任的代天巡狩王爷,普施俗称“好兄弟”的水陆孤魂野鬼,也会举行代天巡狩王爷或包括王船在内的巡境驱邪赐福的仪式。民众簇拥着王船巡查本社区的四境,同时接受王船上洒出的平安金纸,带回家保平安,万人空巷,热闹非常。 巡境的王船也一路召请“好兄弟”随王爷登上王船,转化为王爷的兵将。 之后才将木制的王船迁船至水边,放于水中,让王爷等上船后,再让载着王爷的王船顺水漂走离去;或将木骨纸制的王船或木制王船迁船至水边的“王船地”,待王爷等上船后,在择定的时辰中将其化吉而离去。 前者称“游地河”,后者称“游天河”,现在则多以“游天河”的烧王船形式送王爷等离去,而且不论是木骨纸糊的王船与木制的王船均如此。以此仪式实践来表达洁净地方、禳灾祈安、祭海祈福的意义,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百业繁荣,同时也在此送王的过程中带走本社区的邪煞、 晦气等,俗称“好兄弟”的无主阴灵则转化为代天巡狩王爷的兵将,随王爷去他处代天巡狩或回归天庭。
二、泉州富美宫的传统送王船仪式实质是“送瘟”,而非“送王”
在有着迎王送王过程的送王船实践的地区,也存在着一些表面上称之为送王船, 但其实质却是“送瘟”的仪式实践,其中泉州富美宫历史上从事的所谓“送王船”即为一个典型代表。 泉州文人陈垂成撰写的《泉州习俗》说:
“泉州凡遇灾患之年,均举办水醮、‘送王船’及群众性的‘水普’等,泉属各县闻讯也来参加。 ”“富美(境或宫)还有一种意在消灾、解厄、保境安民的送真‘王船’之俗。其船用木造的帆船,长三丈有余,载重约在二三百担之间,形体似官船,装饰华丽、威严、庄重、大方。 船上供祀王爷神位,仪仗罗列,并放置生活用品实物及活鸡活羊等。选择吉日下水,人们备办供品“赞筵”,道士行祭礼,仪式庄严、肃穆、热烈。挑选富于航海经验、驾驶技术高超的艄公数名,佩带符箓登船,在鼓乐、鞭炮声中,起锚开船沿晋江而下驶出海口,择定海滩停泊,继而择定航向,再举行“交班”仪式,包括祷告、焚烧符箓、把船移交给神明,然后张帆起锚,人员上岸,王船随风逐浪漂流而去。 据载有的王船漂抵台湾,台胞便将船上神像奉祀于泊处本乡,并视之为幸事。 ”①
换言之,泉州富美宫在“灾患之年”才会请道士举办“水醮”“送王船”和“水普”等仪式,故其是“遇灾患之年”才举办的,由于“灾患”不可能定期产生, 故这种送王船不可能定期, 与厦门湾和台湾、海外等地定期举办的送王船完全不同。 其次,富美宫送王船现象的功能纯粹在于“消灾、解厄、保境安民”。 其三,这种表面上称为“送王船”的富美宫传统送王船仪式,实际上是泉州的道士在“灾患”发生时所从事的驱瘟科仪。其程序有道士驱瘟的“水醮”,然后制作一王船,派遣王爷押送瘟神速速离去,故它只有送瘟或泉州人所说的“送王船”,而没有迎王的仪节。因为对瘟神来说,人们的观念是驱尽而后快,而不可能去碰他,更不用说去迎接他了。所以这种驱瘟的仪式只有“送”的仪式,而没有“迎”的仪式,而且送的是瘟神,而不是王爷。 其四,由于是驱瘟的科仪,故除了相关的处理仪式的人员外, 一般的信众多不会参与, 而且还会趋避之,主要是怕被瘟神污染。
富美宫当代的董事、理事们甚至自己认为“王船”古称“瘟船”,王爷是“瘟神”,如富美宫董事会与泉州市区民间信仰研究会编撰的《泉郡富美宫志》云:“王船,古称瘟船,是用来祭献王爷(瘟神)的重要民俗活动之一。 泉郡富美宫因是泉州王爷行宫,历史上送王船甚为频繁,且仪礼隆重。相传,送王船之举因非同一般祭祀习俗, 只在灾年或接送过往王爷时举办。 ”“由于泉州地处亚热带潮湿地区,历史上自然灾害时常发生,尤以瘟疫危害更甚,为保境安民,把‘送王船’视为驱瘟逐疫、消灾解厄的重要举措, 借以增强人们抗御自然灾害的精神力量。”②“王船系仿民用船制作,因装饰华丽,民间又称彩船。”“送王船,先期须举办醮会,祭毕,由事先挑选好的几名水手各背带符箓, 王船在富美渡头旁下水,这时,江畔彩旗招展,鼓乐、鞭炮齐鸣, 数以千计信众焚香叩拜, 王船按指定时间起锚,由水手徐徐从晋江下游驶出泉州湾,而后停泊于海滩,举行人神交接仪式,在简短祭献后,由水手按预定方向,张航起锚,然后焚化背带的符箓,人员离船上岸,交接告毕,王船顺风漂向远方。 ”③此外,在同书中又对“王爷”有自己特别的、自相矛盾的阐释,如“王爷崇拜则是泉州民间信仰中的一大类别,是古代瘟神崇拜的发展,也是泉州人民为抗御灾害,战胜瘟疫所创立的一类神的体系。为此赋予了王爷既能司瘟又能驱瘟,能降灾又能赐福,具有赏善罚恶为特征之神。 而同瘟神在性质上有所区别。 ”④换言之,即把王爷先认定为“瘟神”,然后又说王爷与中国文化中的瘟神又有所区别,“王爷既能司瘟又能驱瘟,能降灾又能赐福”,是“具有赏善罚恶为特征之神”,非常矛盾。
其实,这些现代表述的混乱与矛盾,显示当代富美宫董理事们对他们的前辈的所思所为的误解和误读。因为1903年(清光绪廿九年、日本明治三十六年)8月一艘富美宫驱逐瘟疫的“彩船”(文本中的表述,俗称王爷船,简称王船)漂至台湾苗栗县后龙镇外埔村海边,被当地村民搬回村里。当时为日据台湾的时代,日本警察去“临检”,记录了这一事件与船上的物件等,船中有一些文书,表明该王船来自哪里?为什么送王船等?也说明了王爷与瘟神的关系与区别, 和当时的富美宫的理事们是如何界定王爷与瘟神的。 如:
一、 船名:金(庆)顺号
船头左右有如下文字:
福建泉州府晋江县聚洋铺富美境新任大总巡池金形(邢的别字)雷荻(狄的别字)韩章七王府彩船 安字第二十八号 牌名金庆顺号
一、 船种:中国型戎克船(三支樯)
一、 船籍:中国(港名不详)

图2 漂至台湾苗栗县后龙镇外埔村的“金庆顺”号
一、载重:二百担⑤
换言之, 这艘泉州富美宫送出的彩船的船名为“金庆顺号”,其船的执照为“安字第二十八号”,为“福建泉州府晋江县聚洋铺富美境新任大总巡池、金、形(邢的别字)、雷、荻(狄之别字)、韩、章七王府彩船”, 三桅的“中国型戎克船”,“载重二百担”为民用的商船形制。 也就是说,这是泉州富美宫送出的“新任大总巡池、金、形(邢的别字)、雷、荻(狄的别字)、韩、章七王府”,即7 位代天巡狩王爷的“彩船”“神船”(亦文本中提及的,即俗称的王爷船,简称王船)。根据图3 的照片看,船上供奉的神明除了有池王、金王、邢王、雷王、狄王、韩王、章王等七位王爷的软身神像外, 还供奉有天上圣母妈祖、郭圣王与郭太子三尊硬身神像。船号与执照表明其为“三桅”的民用商船体(非官船形制,因为从照片看, 该船的船头并没有官船特有的“吞口像”或“狮面”),有清政府准许出港或出外海的执照(尽管它可能是假的)。 以此来极力表明其非私自偷渡出外的船只, 因为当时清政府对三桅以上的船只的出海都有限制, 所以此项送王船行动需得到清政府泉州官方的核准后才能进行。

图3 金庆顺号上的七府王爷与其他神明
又如彩船金庆顺号中贴附的日人称之为“第一号证件”的文书云:
(第一号证件)
谨启者: 兹奉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南门外富美乡福神
萧太傅大人 建造新任大总巡
池、金、邢、雷、荻(狄)、韩、章 七位王府彩船于此六月十三日诣祥芝澳
扬帆驾放出洋,巡游四方。 该船如到贵处,希恳贵乡诸善信,即将该船游泊何埠并何时日,仰乞代復一缄,以慰敝乡绅董之遥盼也。 并付笔
资银四角到所收人顺挥来慰,则获福无穷,而诸善信均沾神庇也。 此托
贵乡诸绅董老爷 钧鉴!
泉州晋江县南门外富美宫绅董公启
这是当时富美宫的董事会(其成员亦是富美乡或境的乡绅)写给捡到该彩船者的一封信。大体告之对方,这是富美宫福神(主神)萧太傅大人“派出”的“新任大总巡池、金、邢、雷、狄、韩、章七位王府彩船”,1903年(光绪廿九年)农历六月十三日从泉州湾口的晋江县祥芝澳“扬帆驾放出洋,巡游四方”,希望接到彩船者能回信告诉他们,彩船何时到了什么地方。 富美宫的“绅董”怕接到彩船者不回信或没钱回信,故还附了“笔资银四角”为回资与报酬,并祝愿接到彩船者“获福无穷,诸善信均沾神庇”,也就是均沾“萧太傅大人”以及他派出的“新任大总巡池、金、邢、雷、狄、韩、章七位王府”神明的“神庇”,而且回信者能“获福无穷”。由此看来,当时泉州府晋江县南门外的富美乡(境)或富美宫的绅董绝不可能将这几位“新任大总巡”王爷视为“瘟神”或“瘟部诸神”,而是将其视为可以驱逐瘟神、 押送瘟神出境、 出海的正能量的强力大神。 否则,怎么敢祝接彩船者“均沾神庇”和“获福无穷”。遗憾的是,这份文件(信件)没有明说“送王船”的原由,但同样是这艘彩船上附带的第二号证件“船牌”对其原因则略有透露,如:
(第二号证件)船牌
灵宝大法司 为护船照事照得
大清国福建省属下, 泉州府晋江县南门外三十五都聚津铺鳌旋富美境合信众等,遵奉
富美萧王府新任大总巡勅喻, 择于伍月十七修设平安清醮,构造彩船一只,梁头一丈五尺,龙骨
二丈一尺四寸,及杉板一只,装载冥银、金帛、代人,奉送
瘟部及值年行灾使者绅(神)祇,保护閤郡老少平安。 合要牌示,仰
本船官员舵舡水手夥长目哨人等知悉, 务要小心远送诸项鬼祟及疾疠、疫疠等,速归东海,勿致
疏忽毋违。凡过关津隘口,到放,不得阻滞,取咎,须至牌者
右仰押船官员等众 准此
天运癸卯年(1903年)伍月十七日 坛司给
牌
限即日销⑥
这大概是富美宫举办“平安清醮”请来的道士做“驱瘟”科仪所出的“告示”。它说“泉州府晋江县南门外三十五都聚津铺鳌旋富美境合信众等”,也就是富美宫或富美境的信众等,“遵奉富美萧王府新任大总巡勅喻”,这里虽没有直接讲明“大总巡”是谁,但根据上述的“第一号证件”,我们可以知道,这“新任大总巡”为“池、金、邢、雷、狄、韩、章七位王府”或七位王爷。他们发出“敕谕”,在1903年(清光绪廿九年)农历五月十七日请道士举办“平安清醮”(即前述泉州人陈垂成《泉州习俗》中提到的“水醮”),造彩船一艘,押送“瘟部及值年行灾使者神衹”及“诸项鬼祟及疾疠、疫疠等”(即“诸瘟神”)“速归东海”,以“保护閤郡老少平安”,也就是保护当时泉州府城、晋江县城,即现在整个泉州市区男女老少的平安。换言之,即现泉州市区地方发生瘟疫等“灾患”,所以富美宫的萧王府举办驱瘟科仪,派出池、金、邢、雷、狄、韩、章七位王爷,造了一艘彩船, 押送瘟部及值年行灾使者诸神祇(即“瘟神”)出海,使其“速归东海”,来保证与庇佑整个泉州市区人们的平安。因此,这些被萧王爷派出的、称为“大总巡”的“池金邢雷狄韩章王爷”并非“瘟神”已明。 由于他们不属于“瘟部”,不是“瘟神”,因此也不能称其为“瘟王”了。所以,在当时的富美宫绅董眼里,他们是“代天巡狩”的钦差神明,其功能是押送“瘟部”诸神祇(瘟神:瘟部、值年行灾使者、鬼祟、疾疠、疫疠等)出境,回归东海(泉州人认为他们的来处)。 文本中提到的那些“瘟部及值年行灾使者”及“诸项鬼祟及疾疠疫疠等”才是所谓的“瘟神”。也就是说,清代末年的富美宫绅董们是把“王爷”与“瘟部诸神衹”区别对待的,王爷是正能量的“正神”,而非司瘟的瘟神,彩船是“王爷”的,也可以称之为神船或“王爷船”或简称为“王船”,但此彩船的功能并非“送王”,即将“王爷”送走,而是萧王爷派出的王爷乘坐着“彩船”押送危害泉郡的“瘟神”出境,“速归东海”。
而关于因瘟疫或“恶疫”等灾难而派出“大总巡王爷”用彩船押送“瘟部诸神衹”(诸瘟神)回归大海的意义,其实,接到“金庆顺号”彩船的台湾苗栗后龙外埔人也是清楚的, 并认为接到彩船是件“吉事”。如日本警察曾对当地人进行了调查,外埔庄65 号的老人洪晋来(当年65 岁)、162 号的吕芮(当年62 岁)就告诉日本人这是怎么回事,如他们告诉日本人说:
在中国泉州府晋江县聚洋铺及石头港, 于恶疫流行之际,有如下之习惯,即以地方善男善女之施舍,购买一艘船,加以彩饰,祭祀各种神明,且放置许多供物,然后放行出海,以消除该恶疫,称之为神船。 现漂抵者即是该神船,绝非载乘人们者。
神船漂抵之地将之当作吉事, 建立庙宇以奉祀该神像,并且举行盛大的祭典以纳福。拒今三十年前,外埔庄曾有神船漂抵,当时乃新建庙宇加以奉祀,即今之王爷宫。⑦
换言之, 也就是外埔庄的洪晋来和吕芮老人告诉日本警察, 这是大清国福建省泉州府晋江沿岸的富美宫、文兴宫(石头港的)等,因“恶疫流行之际”,为了“消除该恶疫”,富美宫的执事用信众施舍的钱“购买”建造了“神船”,将其“放行出海”,为的是“消除该恶疫”,也就是送王船是为了除疫驱瘟。而且他们也认为,“大总巡王爷”等和“瘟神”不同,因为在这艘彩船上,“瘟神”是没有具体神像的,有神像的(不管是硬身的还是软身的)都是正能量的神明——正神。所以他们告诉日本人,台湾这里的“神船漂抵之地将之当作吉事,建立庙宇以奉祀(神船带来的)该神像。 ”同时也告诉日本人“距今三十年前,外埔庄曾有神船漂抵,当时乃新建庙宇加以奉祀,即今之王爷宫。 ”这座王爷宫就是外埔庄的“合兴宫”。根据该宫的宫志记载,在光绪廿九年(1903年)前30 多年的清同治八年(己巳年,1869年)农历六月初四,外埔庄也接到一艘从泉州石头港“文兴宫”派出的驱瘟神船,其上有龙、天、张、沈、林、刘、苏七位王爷和潘、苏、文、范、玉、李、王等七位王爷夫人和妈祖、千里眼与顺风耳等军将与五营头⑧押送瘟神出境。 外埔人“不但不把神船漂来当作不吉祥,反而当作最大吉利,以致予以盛大的参拜奉祭”“当作吉事”。“依照耆老所说,当地三十年前,居民还不满百户,是一个道地的贫寒村落,自从三十年前,神船漂流之后,五谷丰收,渔猎亦多,于是渐渐繁荣,到目前已有二百五十户以上,一般住民甚至要比附近村落富裕。另外,界于新竹与中港之间的香山,在十四、五年前,漂来一艘神船,香山也因此顿然繁荣。 外埔庄民此次眼见神船漂来,喜出望外之余,更乐意见到整个村落的繁荣。 ”⑨因此外埔人在第一次接到王船后, 通过祭祀就在海边修建了庙宇——“王爷宫”(即后来的“合兴宫”)来祭祀第一艘神船中的七府王爷及夫人等的神像。也因此,这30 多年来,外埔庄有了很大的发展,丁财兴旺。 自然,当1903年接到富美宫的神船后,也是“喜出望外”,也自然要供奉“金庆顺号”彩船带来的七府王爷等的神像。
因此,由以上的一些记述看,台湾人对大陆漂来的“送瘟”神船(彩船或王船)并没有认为是瘟神上门,而是认为送瘟后的神明的到来,所以会将船上的神明王爷等的神像请回去供奉, 或者建庙供奉,而这种行为是会使村落丁财繁荣的“吉事”,所以有时也会出现几个村落相争的局面, 然后协商分请王爷回各自的村落奉祀。通过这些,我们也可以看到, 即便是以王爷押送瘟神出境出海的“送瘟”船,也会造成台湾等地的王船漂抵地产生新的王爷庙的现象。这不是对瘟神的崇拜,而是对王爷的崇拜导致的。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现代富美宫的董理事们在《宫志》中用括号来说明王爷即是瘟神的表述, 是一种对前辈思想的误读或错误的理解。这也表明《泉郡富美宫志》中认为的“王爷既能司瘟又能驱瘟,能降灾又能赐福,具有赏善罚恶为特征之神”⑩的界定,是不符合富美宫自己的历代实践,因此是错误的。
当然,误解的还有日本人,他们也没有理解当时富美宫绅董的意思, 也没有理解外埔庄耆老对神船(彩船、王爷船)、大总巡王爷的认识,而是根据嘉庆十二年编撰的《台湾县志》中的记载,将这种代天巡狩的大总巡王爷称之为“瘟王”,如金庆顺号王船船附的第二号证件的文书说, 彩船送的是“瘟部及值年行灾使者神衹”和“诸项鬼祟及疾疠疫疠等”瘟神,但到了日本警察的口中,却成了“前段表示本船系建醮以奉送瘟王者,中段命令船员等宜注意速将瘟王送还东海”。⑪虽然在该文后面的叙述中表达还算准确,如“要之,该船系中国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南门外富美乡之信徒, 为祈求平安而建醮造彩船,将瘟神送出远洋”,⑫但由于在一篇文章中,前后的提法不一致,其造成的混乱可想而知。实际上,有许多学者在使用这篇调查文章后,由于没有去细查和分辨日本人的误读之处,直接引用, 所以也患了与日本人同样的错误。 其实,嘉庆十二年编撰的《台湾县志》中提到的“瘟王”,实际上是受到道士送瘟科仪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再另文讨论。
通过上述的白纸黑字的记载以及我们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富美宫清末传统的送王船仪式,是在有恶疫时,由富美宫萧太傅派出几位王爷,用彩船(王爷船)押送瘟部诸神衹(瘟神)出境出海,以保证泉州市区“閤郡”男女老少平安的“平安清醮”仪式,而非只是富美境这一泉州南门外的一小块地方的事。而且,也没有像当下富美宫董理事们用括号表达的形式将王爷与瘟神划等号。 这就使我想起,十多年或20 多年前曾听泉州市已故的黄炳元先生说过, 过去当泉州市区的范围中出现瘟疫之事时, 泉州地方力量就会在通淮关帝庙中举行“三堂会审”的仪式,即请南门天后宫的天上圣母、 花桥慈济宫的保生大帝与通淮关帝庙的关圣大帝一起“三堂会审”,驱逐瘟神。 之后,则请南门外后母尾的主祀萧阿爷(萧王爷)的富美宫举行醮事,监造王船,然后择日派富美宫萧太傅手下的王爷,乘王船押送“瘟部诸神衹”(瘟神)放之大海出境。所以富美宫虽是一个乡或境的小庙,但其“送王船”(送瘟)的仪式却是关系到泉州市区中所有人的安危, 故富美宫的此仪式对泉州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这是我听到的民间传说,没见可靠的白字黑纸记载,也没有民间碑刻类的记述,所以此传说的可靠性还有待进一步证实。 不过从上述金庆顺彩船上的文书中提到富美宫的送王船“送瘟”是关系到“閤郡老少平安”的记载,我觉得已故黄炳元先生的故事极可能是真实可靠的。
尽管清末富美宫的绅董、 信众把代天巡狩王爷与瘟神区别开来, 但毕竟富美宫的这种实质为“送瘟”的送王船仪式是在有瘟疫的情况下才请道士举办自称为“平安清醮”的“水醮”后的“送瘟”行为,故其仪式展开时,除相关人员外,一般的民众是不会积极参与的,而且还需要尽量避开,以避免被“瘟神”所侵扰,自己触霉头。故清末民初的泉州文人吴增在其《泉俗刺激篇》中对泉州的地方这种实质为“送瘟”的送王活动有所批评,但也暴露当时泉州人对王爷与瘟神的区别已开始模糊, 如他在《贡王》中云:
(泉州人)有病药不尝,用钱去贡王,生鸡鸭,生猪羊,请神姐,请跳童,目莲傀儡演七场,资财破了病人亡。 此时跳童又跳起,说是王爷怒未已,托神姐再求情,派刀梯,派火城,五牲十六盘,纸船送王行。送王流水去,锣鼓声动天,吓得乡人惊半死,恐被王爷带上船。
泉州人陈盛明辑注该书时,做了一些按与注,其云:按,旧时认为“王爷公”是位高而凶恶的神,怠慢不得,要用丰盛的供品和隆重的仪式敬奉,向它进贡,叫做“贡王”。 得了病是得罪王爷所致,更要加倍买好它:托神姐、跳童这些“力能通神”的人,向它求情,请跳童表演登刀山(用刀扎成梯子爬上去)、跳火城(用柴草堆成圆圈,烧着跳进去),让神息怒。 然后用纸(或木片)糊扎的船放在溪流送它远去,以免再在当地肆虐。 送“王爷船”时,要大锣大鼓, 严禁小孩观看, 怕魂魄被王爷带上船去。 这种闹剧,清末民初还常看到。⑬
换言之,在清代和民国时期,泉州人认为,“王爷公”虽不是“瘟神”,但却“是位高而凶恶的神”,因此“怠慢不得”,送“王爷船”时,不仅“严禁小孩观看,怕魂魄被王爷带上船去”,而且也“吓得乡人惊半死,恐被王爷带上船。 ”因为这种王爷船也被视为是“瘟船”。⑭久而久之,使泉州人多将王爷视为“是位高而凶恶的神”或类似“瘟神”一样的神明,对其产生一种普遍恐惧的心理和氛围。对表面上称其为“送王船”这类实质上的“送瘟”举动,并不认为是大众可普遍参与欢庆的“地方的狂欢”,而是将其视为这是一种通向或走向死亡的道路或者威摄或“闹剧”。 故过去泉州民间对不听话的小孩,常常用“你要是不听话,就会被王爷抓走”或“你搁七说八说,不怕让王爷掠去”的言语去恐吓他/她,而这种心态与氛围也延续至今日。 所以,才会导致20 世纪90年代富美宫的乡绅与董理事们邀请泉州地方文人撰写《泉郡富美宫志》时,以在王爷后面加括号的形式将王爷直接称为“瘟神”,同时也将王爷乘坐押送瘟神出境的王船称为“瘟船”。⑮
结 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现纳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送王船”仪式实践,或纳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闽台送王船”仪式实践的共性,为它们都有迎王与送王环节,而且是定期举办的,所迎、送的都是民众称之为“代天巡狩”的王爷,也就是说,这类仪式实践是有迎请王爷来,才有后续的送走王爷。而且都认为王爷不是瘟神,而是代表上天来到某地巡狩或镇守的钦差神明。 王爷到某地是“上任”,送走是“卸任”或“卸职”,也顺便带有“洁净”地方和带走和转化可能影响地方不靖因素(如邪、煞、晦气、俗称“好兄弟”的孤魂野鬼等)的功能。 由于代天巡狩王爷的“到任”是为民众“做好事”来的,民众对其“感恩戴德”,而且,王爷离任需乘“王船”(官船体的船只)离去,所以,当王爷离任要走时,感恩的男女老少民众都争相来相送,故相关的送王仪式参与者众多,热闹非常,因此民众多用“送王船”来指称这一仪式实践的全部,而忽略了“迎王”的环节,所以,如果此仪式实践用“迎送王”来界定或命名,可能会更准确地把握和反映该仪式实践的特性。
泉州晋江边上的富美宫历史上所从事的送王船仪式,虽然表面上也俗称“送王船”或“送王”,与上述仪式实践相类, 但其实质则是遇见灾患时所做的“送瘟”仪式实践,其所驱离与送走的重点是“瘟神”,所以该仪式应称之为“送瘟”仪式才能较准确地反映该仪式的意义与性质。至于船上的“王爷”,他们并非“瘟神”,而是执行“押送”任务的正神,所以当他们漂抵某地时,就会有漂抵地的民众接手祀奉,而成为漂抵地民众的守护神。由于灾患并非定期出现,因此,富美宫表称“送王船”实质为“送瘟”的科仪也不可能定期举行。由于涉及瘟神,故仪式从事时,除了相应的执事外,没有很多人积极参与的境况,民间也形成认为此“送瘟”仪式,需要规避气氛, 而且怕像瘟神那样被王爷抓走、送走。所以,富美宫传统所做的不定期“送王船”仪式应该界定为“送瘟”仪式才能准确地表达其实质。其与有着定期从事迎王、送王仪式的“送王船”仪式实践在许多形式、内容、象征、意义、性质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差异,因此它们并非同一类仪式实践。
最后再狗尾续貂地加上一句,即2019年富美宫重新按照前述的迎王、 送王的程序而举办那场新建构的“送王船”仪式,这才与现已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闽台送王船”仪式,或2020年12月17日正式获准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送王船”仪式实践一致。
注释:
①陈垂成:《泉州习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00 页。
②
《泉郡富美宫志》,泉郡富美宫董事会、泉州市民间信仰研究会合编,1997年,第61-62 页。
③《泉郡富美宫志》,泉郡富美宫董事会、泉州市民间信仰研究会合编,1997年,第63 页。
④《泉郡富美宫志》,泉郡富美宫董事会、泉州市民间信仰研究会合编,1997年,第1 页。
⑤《泉州地区的神船》,《台湾惯习记事》(中译本)第三卷第九号,台湾省文献委员会译编,第142 页。
⑥《泉州地区的神船》,《台湾惯习记事》(中译本)第三卷第九号,台湾省文献委员会译编,第146 页。
⑦《泉州地区的神船》,《台湾惯习记事》(中译本)第三卷第九号,台湾省文献委员会译编,第143-144 页。
⑧合兴宫管理委员会编:《外埔合兴宫》, 合兴宫管理委员会印,2009年,第32 页。
⑨《神船之解》,《台湾惯习记事》(中译本)第三卷第十号,台湾省文献委员会译编,第149 页。
⑩《泉郡富美宫志》,泉郡富美宫董事会、泉州市民间信仰研究会合编,1997年,第1 页。
⑪《泉州地区的神船》,《台湾惯习记事》(中译本)第三卷第九号,台湾省文献委员会译编,第146 页。
⑫《泉州地区的神船》,《台湾惯习记事》(中译本)第三卷第九号,台湾省文献委员会译编,第148 页。
⑬吴增《泉俗刺激篇》,泉州市民政局、泉州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泉州旧风俗资料汇编》,1985年,第123 页。
⑭《泉郡富美宫志》,泉郡富美宫董事会、泉州市民间信仰研究会合编,1997年,第61 页。
⑮《泉郡富美宫志》,泉郡富美宫董事会、泉州市民间信仰研究会合编,1997年,第61 页。
——泉州宋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