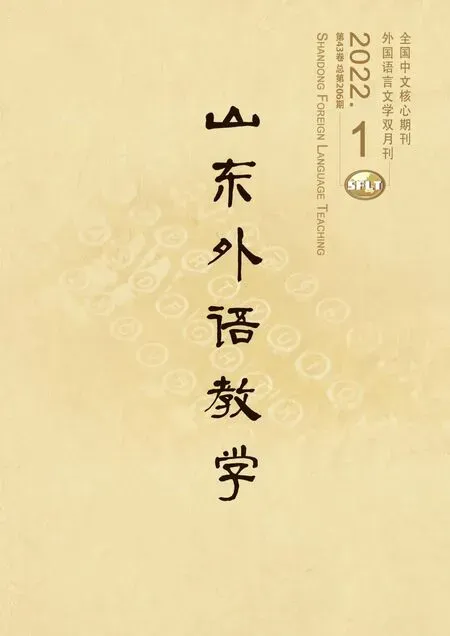基于语言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跨境语言规划:框架与意义
阎莉 文旭
(1.北京中医药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2488;2.西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0715)
1.引言
2013年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对国家间交往的语言需求有了明确的指向。“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官方语言和通用语言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我国的边疆民族语言,也是跨境语言。这些跨境语言与外语多有交叉和融汇之处(文秋芳、张天伟,2018),具有多重资源价值,其开发利用有助于国家多语能力建设、国家边疆安全维护等。但由于当前对跨境语言资源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导致它们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尚无法较为理想地发挥服务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的作用。本文针对本土跨境语言资源,以语言生态学范式为指导思想,从地位规划、本体规划、教育规划、服务规划等维度构拟我国跨境语言规划框架,并阐述其现实意义。
2.跨境语言及其规划研究的背景
2.1跨境语言的界定
我国跨境语言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经过30年的发展逐步成为当今语言学界关注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跨境语言概念由马学良和戴庆厦首次提出并被定义为“分布在不同国度的同一语言”(马学良、戴庆厦,1983:13)。随着研究的逐步推进,其概念内涵进一步扩大。戴庆厦后来对其进行了重新界定,认为“跨境语言是一种因国界因素而形成的语言模式,是分布在不同国家中的同一语言的不同变体”(戴庆厦,2016:159),并根据跨境两国的地理特征将其区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国界接壤或部分接壤的国家存在狭义的跨境语言,如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国界相连,其国语哈萨克语也是我国境内哈萨克族使用的民族语言。国界不接壤甚至地理位置相隔较远的国家存在广义的跨境语言,如中国与泰国国界并不相连,我国境内的傣族所使用的傣语和泰国的泰语可归属于广义的跨境语言。本文采纳戴庆厦的狭义跨境语言观,指其所属国家在地理位置上接壤、部分接壤或者邻近,由具有不同国籍的同一民族的居民所操的同一语言的不同变体。
2.2跨境语言规划研究的背景
根据语言的不同系属,我国的跨境语言可分为跨境少数民族语言和跨境汉语方言,其中前者占绝大多数。就我国跨境语言的数量而言,学界尚未达成共识。有学者认为,这主要与国内外采取的统计方法差异有关(黄行、许峰,2014;黄行,2015)。本文根据前文对跨境语言的界定,以国内语言身份识别统计方法认定的语言数量为基础(周庆生,2014),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境语言数量重新梳理后认定为34种,约占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总数的近三分之一。

表1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语言概览①
已有研究显示,与“一带一路”8个核心区国家共有的跨境语言在我国的语言地位及语言活力度差异较大,如哈萨克语是哈萨克族的广泛交际语言,而京族使用的京语(越南国语越南语的变体)却属已受到威胁的语言,语言转用现象严重,语言活力堪忧(黄行,2015)。虽然我国当前的语言政策一直致力于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并推动语言文字多样化发展,但“对跨境语言却缺少特别的关注,笼统地将其作为少数民族语言来对待”(朱艳华,2016:205)。戴庆厦(2013)指出,我国跨境语言的研究正进入一个关键期,但已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语言本体的探讨上,缺少对其使用功能的研究。因此,一方面,学科发展需要跨境语言维护、语言功能、语言政策、语言教育等语言规划领域的应用研究;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不仅为我国跨境语言的功能研究提供了契机,而且使得国内的语言政策和规划面临新的任务。
3.基于语言生态观的跨境语言规划框架
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引发了语言生态危机,造成少数民族语言的转用乃至消亡。面对这一语言生态变化,语言政策和规划领域的学者纷纷借鉴语言生态学研讨多语环境下少数民族语言的语言规划问题。虽然“语言生态”这一术语的使用由来已久(Spolsky,2004;Eliasson,2015),但将语言生态学概念用以研究所有可能增强或者削弱语言功能的环境因素则始于Haugen(1972)。语言生态学作为一种新的语言学研究范式(Couto,2014),抑或新兴学科(黄国文、陈旸,2017),“为研究全球化对全世界语言文化多样性造成的冲击及语言政策和规划等政府对语言问题的应对措施提供了理论支撑,紧系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宏观关系”(蔡永良,2012:212)。因此,语言生态观成为当前语言政策制定和语言规划的指导思想之一。
3.1目标和宗旨
基于语言生态观的我国跨境语言规划的核心是秉承生态价值取向,构建具有多样性、包容性、和谐性和可持续性的中华民族语言命运共同体。但其内涵不仅包含跨境语言本身,还涉及对影响语言的社会生态环境因素的考量,如政治、经济、安全等,是通过对语言的干预,来解决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的一种方法(Weinstein,1980)。因此,我国跨境语言规划的目标可分为语言学和非语言学两个层面。
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构成了人类社会的一种生态系统,但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深化对各国语言生态尤其是少数民族语言的生存造成了一定的威胁。就我国境内的跨境语言而言,有学者指出,它们在跨境语言身份认同、语言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等方面与境外相同的民族语言相比基本没有优势可言(黄行,2015)。因此,就语言学层面而言,跨境语言生态规划肩负着抵制濒危语言现象、保护语言多样性的重任,其总目标是通过建设中华民族语言命运共同体,构筑国家语言生态平衡,发展国家多语能力;而非语言学层面上的总目标则是助力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五通”,拓展国家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全球利益,促进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这也是该规划的整体宗旨。
3.2框架设想
语言规划旨在影响人们对语言及与其相关的选择,让语言更好地为人类服务。根据语言规划的生态观,我国跨境语言规划是中华民族语言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组成部分,要保护跨境语言的多样性并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与文化建设、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关系愈发密切,其社会功能也愈发多元。而跨境语言作为我国特殊的本土资源,其工具性功能、人文建构功能、经济支撑功能、安全维护功能等已被学界关注并探讨(张日培,2015;赵世举,2016)。具体而言,基于语言生态观的跨境语言规划的内容主要分四个方面:地位规划、本体规划、教育规划和服务规划,聚焦跨境语言社会功能的定位、保持、提升和发挥,如图1所示。

图1 我国跨境语言规划的内容
3.2.1语言地位规划助力跨境语言社会功能的定位
语言的地位规划指为明确或改变某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社会功能和地位所进行的种种努力,一般需要借助于政治的力量来进行(Kaplan & Baldauf,2003)。李宇明在地位规划的总体框架内进一步细分出功能规划的内容,即构建多种语言互补共生的多言多语生活需要更加仔细地确定各种语言及其变体的社会功能,使其各安其位,各展所长(李宇明,2008)。根据语言生态学中的生态位法则,各种语言都在语言系统中占据一定的地位,应该发挥各自不同的功能。当前,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核心区国家跨境语言的语种数量、地位等级、社会活力、文字体系等进行的调查和分析结果显示(周庆生,2014;黄行、许峰,2014;黄行,2015),有相当数量的跨境语言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据着国语、官方语言或者广泛交际语言的地位,如俄语、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等,但在我国语言秩序中并没有明确的地位和在国家利益中的功能定位,而且不少跨境语言已经濒临灭绝,语言保持形势堪忧,语言拯救迫在眉睫,语言传播亟待规划。而基于语言生态观的跨境语言地位规划的实质是对各跨境语言在言语社区中的用途或功能的分配,对各跨境语言使用的场合做出规定,最终体现在对不同跨境语言社会功能的定位上。
基于此,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在国家层面制定相关语言政策,重新定位跨境语言在我国语言生态系统中的社会地位和功能。上述四大功能体现了跨境语言作为国家资源在满足社会需求、服务国家战略方面的价值,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可使其得以有效发挥。根据Kaplan & Baldauf(2003),地位规划的首要步骤是地位政策规划,即通过明文规定语言地位的规范化,包括官方化、国家化等。因此,国家语言政策可视为地位规划的重要实现手段。跨境语言相关政策的制定事关国家语言规划的顶层设计,包括国家和各级行政机构对跨境语言的认知,以及由此而制定的相关条例、规定、措施等。因此,有必要高屋建瓴地先行制定区域性跨境语言政策。例如,可根据我国与周边不同国家的发展战略,对地域性跨境语言的需求和现状进行分析,区分出关键语种、次关键语种、迫切语种、濒危语种等;通过开发跨境语言资源和发展语言产业,培养“非通用语”外语人才等细分领域的政策予以落实,以增强跨境语言的使用活力、传播力和影响力。在语言地位规划中给予跨境语言发挥其多样化社会功能的区域和领域空间,可为其服务社会和国家提供发展平台。
3.2.2语言本体规划助力跨境语言社会功能的保持
语言的本体规划是关注语言本身或语言内部结构的规划(Kaplan & Baldauf,2003)。跨境语言的本体规划是在地位规划的前提下进行的,目标是促进跨境语言内部结构的不断规范、完善,通过语言本体自身的与时俱进与国际接轨,从而使其能够有效发挥地位规划赋予的社会功能。根据语言生态学,语言本体的生存、发展和演化对社会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的作用,反过来也受社会生态环境中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安全等因素的影响。因使用跨境语言的边民的语言习得和语言使用的社会环境有别,跨境语言本身在语音、语法、词汇等方面必然存在不同程度的演化差异,由语言文字的规范、拼写和拼读等方面的不同导致的语言应用冲突也会在境内外沟通中彰显出来。因此,从语言生态学视角进行跨境语言本体规划需要充分考虑不同区域跨境语言的内外生态环境和语言使用者语言态度的影响作用,既要服务国家战略,又要维护国家语言生态健康。
基于此,首先,本体规划必须保证跨境语言能够满足境内外的沟通交流,即保持并发挥其工具性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助力国家拓展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全球利益。因此,应根据国情差异、结构特点、演变规律等对跨境语言文字进行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化,以提高其活力。对于“一带一路”沿线跨境语言中国内外本体差异较小的语种可尽快借助于技术手段,实现语言信息化,提高语言现代化的水平;而彼此本体差异较大的跨境语种,应根据语言自身的特点和发展演变规律,在文字的创制与改革、拼音或注音方案的制定与推行、词汇和语体的现代化等方面扬弃与借鉴并举,力求与国际接轨,实现最大程度的国际化。囿于各国语言政策的差异,可在以上领域求大同存小异。其次,为维护国家语言生态健康,扭转语言濒危现状,跨境语言的本体规划要以尊重语言变异为基础,以增强境内跨境语言活力、保持我国语言多样性为准则。
3.2.3语言教育规划助力跨境语言社会功能的提升
语言教育规划是Kaplan和Baldauf于2003年在Cooper(1989)提出的习得规划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指对与某种语言学习相关联的一切教育活动的系统组织。语言生态学范式基于世界范围内的语言多样性,主张语言维护和外语或多语教育。因此,跨境语言教育规划要就当前我国边疆地区民族语言保护、外语教育政策以及“非通用语”外语人才需求的现状予以分析。例如,在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区域性基础外语教育中可考虑赋予部分跨境语言与英语等语种相当的外语语言地位,提升其整体社会功能。基于语言生态观的跨境语言教育规划顺应了当前国际语言教育战略发展的趋向——倡导语言生态发展和平衡以及维护语言文化多样性,提倡国民多语能力培养。因此,有必要通过国家和地方层面的语言教育规划,培养谙熟跨境语言及其文化,同时又掌握国家官方语言或国际通用语言的高端双语或多语人才,建设国家多语人才资源库。
基于此,首先,跨境语言教育规划在官方语言教育系统中的教学对象、教育制度设计与实施路径、人财力投入、教育成效评估等方面应有别于一般的外语教育。一般而言,跨境语言学习大致分为先天家庭习得和后天学校学习。据Spolsky(2009)的研究,前者使得语言使用者的语言能力具有后天学习者所无法比拟的优势,也使得他们更容易在家庭母语习得和后天外语教育中通过语言再习得的方式成长为优质双语或多语人才。因此,要重视以家庭语言习得的方式实现边疆少数民族母语的自然代际传承。Spolsky(2009)还指出,要实现语言的自然代际传承,家长对家庭语言域中语言环境的掌控至关重要。其次,“一带一路”沿线跨境语言大都为我国的区域性少数民族语言,进入教育体系的语种相对较少,而传统外语教育模式培养人才周期较长,因此为保质保量加快人才培养速度,可在后天语言教育规划中将其从传统外语教育模式中剥离出来,依据语言习得规律进行合理规划。例如,依靠家庭和社区的力量实现民族语言代际传承;在高端双语或多语人才培养方面选取具有跨境语言和汉语双语家庭习得背景的使用者尝试进行双语培养、中外联合培养等。
3.2.4语言服务规划助力跨境语言社会功能的发挥
基于国家构建和谐语言生活的整体规划目标,一个新的语言规划类型——服务规划应运而生。语言服务规划跟语言需求密切相关,是从语言需求者视角进行的语言规划。十三五以来,“语言服务”被确定为国家语言政策的重要方面。“语言服务作为语言生活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并不是‘舶来品’,而是依托中国本土的语言生活而不断丰富与发展的”(屈哨兵,2011:31)。2020年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也为我国提供了审视国家应急语言服务建设成果的契机(滕延江,2020)。语言政策是语言规划的表现形式,因而语言服务规划理应成为我国语言规划的新增维度,与传统的地位规划、本体规划和教育规划并行,这不仅是对原有语言规划类型的拓展,也是由“一带一路”语言生活管理的现实需求所决定的。因此,基于语言生态观的跨境语言服务规划有着时代所赋予的崭新内涵和现实要求:它以跨境语言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为宗旨,以促进跨境语言社会功能的发挥为导向,意在生态和经济两手抓,将跨境语言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打造区域语言经济的业态新格局。
基于此,跨境语言服务规划不仅要从语言生态平衡的视角保护跨境语言资源,更要树立少数民族语言规划的经济学意识,重点研究将边疆少数民族的母语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本的可行途径,以重点发挥其经济支撑功能。即语言保护应该重点探讨将少数民族母语资源转换为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及其与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关性,研究如何形成“一带一路”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产业体系和语言经济形态(方小兵,2014)。而跨境语言使用人口的减少、使用域的缩小及社会声望的优劣与政治、经济等环境因素息息相关,归根到底源于经济因素。当前,在产业发展方面,以语言科技和语言信息为代表的新兴语言产业已崛起,如机器翻译产业、搜索引擎产业、人工智能产业等发展迅速,多语言服务业也细分出语言培训、语言翻译、语言出版、语言测试等领域。“一带一路”旨在打造一个巨大的亚欧非大陆经济活跃带,因此以机构和利益集团为参与主体,即依靠市场力量的拉动促进跨境语言产业化发展,是语言服务规划实施的抓手。全球化和信息化为语言产业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新型语言服务产业的应运而生催生了“语言经济”这种新的经济形式(赵世举,2015),因此需要抓住少数民族语言经济的市场时机,为跨境语言的知识化创造空间和条件。最终,发展母语经济也将成为在可操作层面探讨解决民族语言保护困境问题的可行方略。
根据语言生态学,语言系统具有动态性特征,相关语言政策也并非一成不变,需要进行动态调整。因此,可依据实际情况对跨境语言规划的内容进行取舍。语言规划旨在通过制定和评价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寻求最有效的决策。所以,在实施过程中应适时对规划所涉内容进行评估,包括规划的执行力度、规划产生的经济效益数据、社会认可度及与“五通”的融合度等,并根据调研结果进行调整和优化。
4.跨境语言规划的现实意义
跨境语言资源应服务国家战略、拓展国家利益,其规划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1建设国家多语能力
我国“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问题从本质上讲乃是国家多语能力问题,而跨境语言规划可视为国家多语能力建设的内生捷径。本文基于语言生态学范式,结合我国“一带一路”语言互通的需求,在语言政策和规划领域中提出国家多语能力这一概念。国家多语能力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秉承战略发展理念规划和处理国内和国际事务所需的多种语言的能力。在内涵意义上,国家多语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相比更为具体,是国家层面对多种特定语言需求如民族语言、外国语言等的一种反应和应对能力。境内外同一民族的跨境语言具有高相似度与互懂度,在培养“非通用”外语人才和建设国家多语能力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因此,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族语种特点和我国面临的语言互通需求,独辟蹊径建设国家多语能力,如国家民族语言能力、国家周边外语能力等,理应将跨境语言规划纳入其中。
4.2构建我国国家认同
当前,我国迫切需要通过实施国家语言规划为“一带一路”提供人文保障,特别是通过充分发挥跨境语言的情感沟通功能协助“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构建国家认同。由于族群认同与语言在特定语言使用语境中相互包含与构建(Trofimovich & Turuševa,2015),因此当跨国界而居的同一民族因语言互懂度较高而成就有效沟通时,族群认同感会非常强烈。显然,跨境语言所承载的民族文化将在“一带一路”民族认同和民心相通方面发挥独特的优势,从而促进民族间文化互鉴和彼此认同,打造“人文之路”,为国家间政治对话、经济合作、外交融通等创造有利条件。此外,在多民族国家内部,发展边疆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维护边疆少数民族在各自所在国的群体利益,关系到彼此国家认同的建构。跨境语言规划有助于增强我国跨境语言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掌握跨境语言国家传播的话语权,可为构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众对我国的国家形象认同提供人文支持。
4.3促进国家语言生态平衡
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跨境语言规划为跨境语言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保障,既有助于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传承,亦有助于国家多语生态系统的平衡,同时对濒危语言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有重要作用。语言生态学聚焦语言保护,认为语言多样性是维护语言生态系统平衡的动力之一。“在语言保护工程中,对跨境语言的保护是一个薄弱环节,至今未能引起全社会足够的重视”(朱艳华,2016:208)。因此,对我国跨境语言进行规划既有助于语言知识化与标准化、语言保持、语言传播等,也有利于我国语言平等、语言共荣、语言互补等语言生态系统的内部和谐。
4.4助力国家安全维护
跨境语言管理有助于促进族际和谐与地区和平稳定(何山华,2018),不仅关涉国家非传统领域安全,还事关国家传统安全。一方面,境外反华势力可利用边疆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跨境语言传播与我国意识形态相悖的文化,给中华文化带来侵蚀,破坏我国的文化安全。另一方面,以文化安全隐忧为典型代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文化上的“离心”特征,通过宗教渗透达到政治目的,经敌对势力的演化和利用,往往还会影响国家的传统安全。相关调查显示,近年来我国的跨境冲突使得边疆民族团结、社会安定、国家周边安全等存在一定隐患。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传统安全的风险因素往往与语言紧密相连,语言问题也逐步“被安全化”(王建勤,2011)。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政治、经济、商务等领域的深入合作将为我国边境的传统安全带来新的挑战。面对新的形势,我国亟待构筑安全的国家语言保障体系。而跨境语言规划在维护国家安全、拓展国家利益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5.结语
从全球视野来看,跨境语言在世界绝大部分地区都存在(张四红、刘一凡,2021),是现代多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独特研究领域。当前,“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了我国与沿线国家尤其是跨境国家间新的语言生活,中华民族语言命运共同体建设要求我国增强对跨境语言及其规划的学术研究。而中国区域性语言政策的制定也应与时俱进,重点考虑如何利用跨境语言等本土特殊语言资源。随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关系的推进,跨境语言规划不仅有助于促进国家语言生活多元、和谐、可持续发展,而且可提升中国语言学研究,推动中国周边跨境语言研究和国际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张四红,2020),为世界范围内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提供重要学术借鉴。
注释:
① 该表主要根据戴庆厦、成燕燕和傅爱兰等(1999)、周庆生(2014)及其他相关文献资料整理而得。“■”表示境内外的语言名称完全相同。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我国境内的回族已完全丧失自己的本民族语言,现通用汉语,只是在不同地区持不同方言。因此,回族虽然属于跨境民族,但在我国境内已无本民族语言,故在本表内不做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