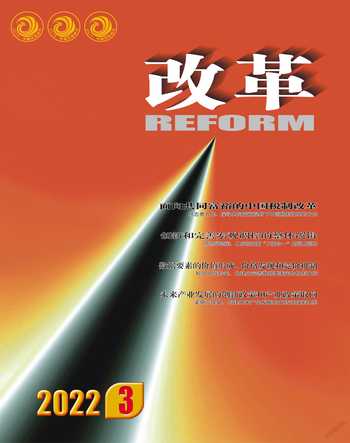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理论分析、事实依据与实践路径
李标 孙琨 孙根紧
摘 要:数据要素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战略资源。依循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分配理论,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是数据要素所有权的经济实现。数据要素融入社会再生产之后,在生产力促进机制、流通效率改善机制、消费扩容提质机制、分配结构优化机制的作用下,内生了财富增进效应。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的有机融合塑造了数字增长动能,推动了经济“数智化”转型,改善了宏观调控效率。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实践,应以清晰界定不同类型数据的权属范围为逻辑起点,从法理上避免违法违规使用或交易数据对其要素化、资源化的制约;建立健全由均衡价格参照机制、询价竞价机制与公允估价机制构成的数据要素价格生成机制,使数据要素市场交易定价更加科学;在以市场交易为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主要方式的基础上,培育鼓励“估价作股、数字租金、以数易数或以数易商(服)”等新形式参与收入分配,促进数据要素沿着资源化、资本化、资产化的价值链拓展收益;加强数据流通监管,加快涉及数据确权、隐私保护、数据寡头垄断等相关法律的立法、修法与释法工作,促进确保数据要素收益公平分配的制度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关键词:数字经济;数据要素;收入分配;财富创造;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2)03-0066-11
数字技术发展与运用之基在于数据。数据是生产生活与经济社会发展“足迹”的数字记录,是数字经济时代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和战略资源。为更好地推动数据要素服务于发展,国家将数据纳入参与收入分配的生产要素范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推动数据要素更好地参与收入分配要回答如下问题: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理论逻辑是什么?是否有牢固的经济事实支撑?实践路径又有哪些?回答好这些问题,可为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制度完善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加速数字经济提质扩容,加快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
一、相关文献综述
伴随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数据成为日益重要的生产要素。市场经济条件下,明确权利归属、科学制定价格、建立有序的交易机制等是推进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重要内容。相关研究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是关于數据权属的界定。按照生产主体的不同,可将数据划分为政府数据、企业数据和个人数据[1],依据数据类型差异化配置权属是可行之举。个人数据的生产主体是个人,个人数据应完全归个人所有;企业对基于原始数据匿名、清洗等处理后的数据集享有限制性所有权,即不完整的所有权[2];政府具有公权力属性,政府收集数据的花费主要由税费支付,政府数据应属于全社会共同所有[3]。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等并没有规定数据的具体权属,主要原因在于数据载体多样,价值有差异且不稳定,外部性等使数据产权难以照搬或参照物权予以界定。由此,对于数据要素产权的归属仍需加强司法解释,探索数据生产链条各环节的数据确权问题。
二是关注数据及其衍生品定价。市场主体针对数据及其产品定价展开了探索。有研究指出,为确保成本回收和利润最大化,规模经济与共用品特征突出的网络信息产品适合差别定价法[4];Liang Fan等归纳整理了大数据市场基于卖方视角的两大类定价策略[5];左文进和刘丽君分析了基于大数据资产属性与买方视角的数据资产公允估价方法[6]。目前,数据市场上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价机制与技术,这使得数据市场分割、定价不客观、垄断等市场失灵问题突出,导致了数据要素收益分配扭曲。因此,仍需研究设计有层次、适用差异化场景的数据要素价格生成机制,以更好地匹配数据的资源化、资本比和资产化。
三是关注数据市场交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让渡所有权或部分权能是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基本方式,交易机制对要素收益分配结果有重要影响。一些研究认为,数据交易应通过法律法规明确流转范围与内容[7],合理规范数据要素使用权[8],以确保数据交易安全有序;数据交易机制应简洁、程序化,减少人为因素[9],以提升数据交易效率;还应加强个人隐私保护[10],利益相关者就个人数据使用协商补偿[11],将必要设施原则用于数据垄断规制[12],以确保交易公平。
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三方面的拓展:第一,加强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理论分析。与西方经济学或法学视角不同,本文侧重论述这一制度内蕴的政治经济学逻辑。第二,细化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事实依据。在前期研究基础上,本文梳理了数据在动能塑造、转型升级和宏观调控方面的经济表现,并将之作为此制度安排的现实依凭。第三,探讨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实现路径。现有文献尚未系统回应如何实践此激励制度,本文从产权界定、价格制定、方式创新、制度保障四个方面加以分析。
二、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理论分析
这里着重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找寻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理论渊源,阐释其内涵,论述数据要素增进财富的作用机制。
(一)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理论基础
直观地看,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以“斯密教条”(即“三要素价值理论”)为理论依据,是生产过程中数据要素创造价值在分配领域的具体表现。实际上,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生产环节创造价值的要素只有“活劳动”,而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数据仅是通过提供相关信息等方式协助价值创造,其参与收入分配的理论基础并不是“三要素理论”,而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分配理论。
亚当·斯密的“三要素价值理论”的核心要义是:劳动、资本和土地三种要素协同生产商品,提供了商品效用,所有的生产要素共同创造了价值,进而劳动要素获得工资、资本要素获得利润、土地要素获得地租,即“三位一体”公式。相对地,马克思则认为,亚当·斯密混淆了价值与使用价值的来源,并明确指出:“工资、利息、地租等作为社会生产过程的各种特殊因素所分得的收入的不同形式,源泉仍然是劳动创造的价值。”[13]931实际上,按生产要素分配与“三位一体”公式有着显著的区别:一方面,“三位一体”公式过于表面,其庸俗性在于将资本、劳动、土地都同等地看作价值的源泉;另一方面,“三位一体”公式混淆了收入分配与价值创造,二者不是同一层面的问题,价值创造与劳动相关,分配则与要素所有权相关,分配过程就是要素所有权的实现过程[14]。
依循马克思的逻辑进路,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是各种生产要素所有权的经济实现,也即新价值在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分配。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这个价值的一部分属于劳动力的所有者,另一部分属于或归于资本的所有者,第三部分属于或归于地产的所有者。因此,这就是分配的关系或形式,因为它们表示出新生产的总价值在不同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的关系。”[13]993总的来说,“各要素所有者参与收入分配是实现要素所有权的诉求,有着合理性与客观必然性。”[15]数据要素与其他生产力要素共同参与财富形式的收入分配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分配理论相容。
(二)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内涵释义
1.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含义
数据有着生产成本低、大规模获取的特性,且具备非竞争性、非排他性或部分排他性、低复制成本、外部性、即时性等独有的技术—经济特征[16],这使得数据能够独立作为一种新生产要素。基于前述分析,本文将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界定为数据要素资源所有权的经济实现,即市场主体通过数据要素及其相关产品所有权或使用权转移而获取收益的经济行为。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原因在于其渗透融入社会再生产各环节而衍生的经济益处。数据要素与劳动相结合能提高劳动技能与综合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数据要素与劳动资料相结合能革新劳动工具、提升劳动资料质量与效率;数据要素与劳动对象相结合能形成新型劳动对象、扩大劳动对象范围、提升附加值;数据要素与科技相结合能推动科技发展、加速科技与生产融合[17];数据要素与管理要素相结合能够减少不确定性冲击,赋能市场和政府主体优化决策,实现经济活动效率化、经济管理精细化和经济决策科学化:微观上,赋能企业更准确掌握市场供需、科学决策、安排生产与优化资本流向;宏观上,赋能政府做好国民经济预测与发展规划工作,合理配置生产要素,实现结构优化,促进经济循环畅通。总之,数据要素与其他要素融合能有效促进生产力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贡献。
2.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内容
在现代经济中,价值表现为货币化的财富,从而收入分配与财富分配具有了内在一致性。在马克思那里,财富的创造与增进(主要指货币化的使用价值数量增长)是各种生产要素的共同作用,非劳动要素所有者凭借要素所有权而分配价值或财富符合调动全部主体、全部要素参与生产积极性的制度安排出发点。在分配内容上,价值分配与财富分配的内容与数量上完全一致,是社会总产品价值扣除三大部分(简单再生产消耗的生产资料价值、扩大再生产追加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价值以及应对不确定性的后备基金或社会保险基金)之后的净剩余。理论上,用于分配的部分在价值量上通常是可变资本价值与剩余价值之和,也即社会净价值、净财富或净收入。这也成为数据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共同分配的对象。
3.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原则
允许非劳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一方面是出于发展生产力的需要,调动生产要素及其所有者服务生产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促进物质财富增长;另一方面,既然非劳动要素及其所有者在国民经济财富增长过程中有较大贡献,那么,从公平角度出发,其参与收入分配合乎客观逻辑。因此,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首先应遵循“效率与公平兼顾”的指导原则,既要激励数据要素融入社会再生产过程,又要确保其所有者凭借所有权获取应得收益。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数据要素收益权的实现离不开市场,需要通过市场交换价值或价格来体现。由此来看,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应遵循“供需匹配”的实践原则,由数据要素相关市场主体按照统一、规范的标准,评价数据要素贡献大小,由市场供给与需求决定数据要素的价格。这一原则适用于整个数据价值链条,包括数据衍生产品和深入挖掘的价值模型与定价模型等。
(三)数据要素增进财富的机制
1.生产力促进机制
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表明,财富增长与生产力成正比,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形下,劳动生产率越高,生产体系创造的使用价值规模越大。与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和管理一样,当数据与生产资料分离时,它们只是可能的生产要素[18]。数据要素作用于财富增长的逻辑进路是“数据要素→生产环节→生产力(劳动生产率)→财富”。在生产环节,数据借助工业互联网,有助于组织要素投入,实现机器间数据共享、协同生产,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19],还能“促进技术模块化变革,使技术更加通用和易操作,释放溢出效应和赋能效应”[20],從而提高生产力水平,财富增进得以实现。
2.流通效率改善机制
一般地,交换效率越高,社会再生产循环便越快,财富增进效果越好。数据要素通过影响流通而促进财富增进的路径是“数据要素→流通(交换)环节→流通效率提升→财富增进”。一方面,数据要素的运用不仅促使传统的“线下”面对面交换模式转向依托虚拟数字平台市场的“线上”交换模式,而且通过精准预测与推送等智能方式深度优化了“线上”交易模式,降低了搜寻匹配成本,缩短了交易流程;另一方面,高效流通体系能够在更大范围把生产和消费联系起来,扩大交易范围,大数据技术能够实现商品的高效集中与分散,大幅节约商品到达消费者手中的流通时间。因此,数据要素及其隐藏的信息被运用于交换环节可有效改善交换效率,加速经济循环,促进财富增进。
3.消费扩容提质机制
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表明,消费为生产提供了动机,且只有建立在消费增加基础上的扩大再生产才具备增长效应。深度挖掘运用消费数据,能精准捕获需求信息,提高供需匹配效率,扩大消费规模,促进经济循环量能与效能提升,此即数据要素借助消费渠道发挥牵引财富增长的机制。具体地,“运用大数据技术匹配历史消费数据与即时消费数据、刻画消费真实情景与消费者行为规律,使得精准预测需求偏好、识别消费需求成为可能”[21],供需匹配效果与消费效率明显改善,社会再生产循环加速,财富随之增加。基于平台的商品供需集合较大,辅以显性化的质量评价数据,选择“物美价廉”的商品成为可能,消费数量、频次提升概率大,从而带动财富增进。此外,数据要素的渗透能促进数字教育、数字医疗等新消费发展,塑造新增长着力点。
4.分配结构优化机制
分配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分配不合理会损害要素主体生产积极性,抑制财富增长。在数字经济时代,各行业、各环节、各场景普遍存在数据因子融入的形式,由此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原本就是优化分配结构的体现。数据要素还能改善分配效率,促进财富增长。一方面,大数据技术在征税方面的运用,有利于规制偷税、漏税与取缔非法收入,由此增加的财政收入可用于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促进财富增长。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对表面不具有相关性的海量数据展开机器学习,能解決传统分配方式中存在的信息黑箱问题,科学甄别要素边际产出,合理确定要素收入份额,激发要素生产积极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22],推动财富规模扩张。
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基于劳动价值论与分配理论在分析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时,内生规定了生产要素在高利润率与低利润率部门之间自由流动,这说明形成平均利润率与生产价格时隐含了完全竞争或近似完全竞争的假设。因此,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要充分发挥效率与公平兼顾以及供需匹配两大原则的作用,高效实践“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机制”,清晰界定数据产权,并尽可能确保数据市场竞争生态良好。实际上,我国的数据要素市场正处于探索阶段,由数据要素交易主体、交易手段、交易中介和交易监管构成的市场体系逐步成型。该阶段下,囿于数据收集成本高、数据标准不一、数据及其衍生品定价机制迥异等,出现了类似“算法共谋”“大数据杀熟”“二选一”等互联网平台垄断市场结构,倘若不进行制度规制,数据要素收益很难公平分配,因为数据垄断主体能够借助垄断低价与垄断高价获取高额不正当收益。这意味着,推动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有必要按照数据的经济属性,综合考虑法律、文化等因素,依法开展“数据分类确权”,进而对垄断等市场失灵现象进行规制,以更好地发挥效率与公平兼顾、供需匹配的作用。
三、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事实依据
从国民经济运用数据要素的最终输出结果来看,我国经济发展深度使用数据要素以后出现了诸多显著改善。例如,塑造了增长的新动能,推动了经济转型升级,改善了宏观调控绩效。这些实际经济益处,既体现了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内蕴的现实逻辑,又为其提供了牢固的事实依据。
(一)塑造了数字增长动能
从要素投入角度来看,要素总量扩张的发展模式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规模迅速增大。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数量扩张型增长模式掩盖的结构性问题显化,重塑经济增长动能成为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规律、新格局的客观需要。国际数据公司(IDC)发布的《数据时代2025》显示,2025年全球每年产生的数据量将从2018年的33ZB(1ZB=10万亿亿字节)增长到175ZB。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被广泛运用的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与经济融合的程度日益加深,经济增长的数字动力显著。《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年)》表明,我国数字经济规模由2005年的2.6万亿元扩张到2020年的39.2万亿元,占GDP比重由2005年的14.2%提升至2020年的38.6%;2015—2020年,数字经济增速显著高于同期GDP增速,且2020年数字经济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世界经济下行影响下仍保持9.7%的增速,远超同期GDP名义增速。
在现代经济增长分析框架下,经济增长数字动能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数据要素的运用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有学者发现,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互联网电子商务及其应用显著促进了我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23]。理论上,全要素生产率涵盖了劳动生产率、要素配置效率、供需匹配效率等,生产环节将数据与其他要素高效融合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年)》显示,产品全生命周期数据管控助力企业新产品研发周期降低16.9%,产能利用率提升15.7%,设备综合利用率提升9.5%。充分运用大数据有利于降低交易发生的信息门槛与搜寻成本,促成大量新交易,加快资源流通速度,改进资源配置效率[24]。此外,与数据要素运用紧密相关的新技术大幅提高了供需匹配效率。
简言之,不论是理论视角还是实证视角,数据要素不仅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改善,而且生成的数字经济这一新经济形态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也较为显著。《2020—2026年中国数字经济行业市场前景规划及市场前景趋势分析报告》显示,2019年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7.7%。可见,数字经济正逐步成为结构性减速背景下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数据要素有较大可能成为引领新一轮经济周期的关键变量。国家适时给出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制度设计,既是对数据要素驱动经济增长能力的回应,又是确保数据要素能够持续释放生产力的科学激励机制。
(二)推动了经济转型升级
经济转型升级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抓手之一,也是新时代下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要目标。立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在于产业调整及其结构优化。历史地看,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对应的支柱产业与主导产业明显不同,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因素也有所差异。新一代数字技术的突破性发展,使得数据日益成为产业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三次产业的边界日趋模糊,推动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促进从研发设计、生产加工、经营管理到销售服务全流程数字化,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和供需精准对接,从而为转型升级开辟新路径[25]。《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0年)》显示,工业互联网已在我国40个国民经济大类行业落地应用,涌现出100余个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平台链接工业设备总数突破7 300万台(套),形成数字化研发、智能化制造、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化延伸、精益化管理等模式。
随着我国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日益重视,数据要素正不断与传统产业渗透融合,加速了不同产业、不同行业的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有效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数智化”转型升级。来自《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年)》的数据表明,2020年我国的产业数字化依然保持快速发展趋势,产业数字化规模达31.7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1.2%,同比名义增长10.3%;占数字经济比重由2015年的74.3%提升至2020年底的80.9%,农业、工业、服务业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为8.9%、21.0%和40.7%。我国经济正沿着“数智化”方向快速转型,已取得突出效果。当前,数据要素已成为经济“数智化”转型的关键因子。确立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制度,并将之付诸实践,有利于促进数据要素稳定释放结构调整红利。2021年3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专门设置了一篇“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强调了要激活数据要素潜能,以数字化转型为驱动力,深度推动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和治理方式的数字化变革。
(三)改善了宏观调控效率
在完全信息条件难以得到满足时,为避免可能的市场失灵导致经济福利损失,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履行一定的经济职能,具备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必要性。
理论上,宏观调控是否有效主要取决于政府职能部门能否搜集、整合、分类和处理海量数据,获取完备、充足的有效信息。在工业化时代,科技水平和技术手段只能搜集和提供不完全的信息。由于作为决策依据的信息不完全和不准确,政府在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财政政策、投融资政策时不可避免地有不科学的成分。在大数据时代,经由大数据智能平台获得完全信息和准确信息成为可能[26]。新一轮科技革命为数据服务于宏观调控提供了良好技术条件和设施条件,以数据为基础、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宏观调控模式正逐步成为现实。《数字时代治理现代化研究报告——数字政府的实践与创新(2021年)》显示,在经历2000—2014年的电子政务、2015—2018年的“互联网+政府服务”后,2019年我国各地开始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将数据的驱动作用从政务服务拓展至社会管理。截至2020年底,已有至少19个省份设立大数据管理机构。
政府将数据要素融合于经济管理领域,实现了宏观调控绩效的优化。首先,数据要素的充分运用能够更好地发挥政府调节市场经济的作用。大数据特有的海量挖掘、实时获取、高速处理和即时分享市场信息的技术属性使得市场更有效、政府更有为[27],能真正实现以市场发挥决定资源配置作用为基础的宏观调控,明确政府宏观调控的界限。其次,数据要素的运用使得宏观调控更趋精准。得益于大数据相关技术的发展与广泛运用,我国的宏观调控已由过去的“总量调控”转向“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精准调控、适时预调和微调控”。国家相关管理部门采取多种方式开发利用形式多样的大数据,并与政府信息整合,构建大数据经济分析模型,对国民经济各领域的运行状况及时监测,提高了宏观调控的精准性[28]。最后,数据要素的运用使得宏观调控政策更加及时有效。运用大数据分析有效刷新了政府的认知能力,缩短了调控时滞,提升了宏观经济政策时效。
数据要素进入生产函数并获得相应的经济回报,不仅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分配理论核心要义的具体体现,而且是经济实践的客观要求。伴随数据要素利用广度与深度的提升,供需的快速匹配加速了价值的循环与周转,使得数字经济成为增长新动力。数据要素向传统产业的渗透催生了产业数字化的新业态,加速了经济转型升级。生产、交换与消费环节充分挖掘使用数据,有效优化了生产效率。大数据技术的充分运用提高了获取更多数据以及更精准地甄别数据映射信息的能力,使得政府决策的依据更加牢靠、更加科学,改善了宏观调控绩效。在数据要素渗透融合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新发展时代,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以数据作出重大经济发展贡献的事实为依据。因此,有必要加快推动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这一制度安排的落实,以更好地发挥数据要素优化经济发展质量的作用。
四、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实践路径
(一)加快完善数据要素产权的细化分类界定
数据要素“具有载体多栖性、价值差异性、使用高盈利性以及外部性,使现有法律制度难以解决数据的产权安排”[29]。综合考虑我国实际以及《民法典》明确了数据与网络虚拟财产可视为“物”,突破了“数据由于无形、无独立经济价值而不能独立被视为民事权利客体与财产”[30]的制约,因而应遵循“分类确权”原则,明确数据权属配置。
数据收益分配的主体包括数据来源用户、数字企业、非数字企业、政府。与之相适应,数据要素的产权应区别进行界定。个人是数据最初的生产者,考虑到姓名、性别、交易信息等数据能形成“人格画像”,属于隐私范畴,因而应遵循人格保护原则,将原始或底层数据的绝对所有权界定给个人,以体现个人对自身信息的安全把控。基于个人数据“衍生的所有权归政府和企业等数据二次开发利用主体所有”[31]。相关主体共享或交易数据时,应始终坚持“不穿透底层”的安全红线,确保隐私保护与数据价值挖掘相容。实践中,华东江苏大数据交易中心在数据交易“四不准则”中,专列一条强调“绝不交易底层数据,而是交易经过分析、清洗、脱敏、脱密后的数据产品”;2022年1月1日起施行的《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也体现了上述原则。
企业数据主要有自身数据、用户数据以及脱敏建模数据三类。对于为改善劳动生产率而自行搜集的用于提供最终产品或服务的生产数据,企业拥有全部的所有权。企业也可能会搜集具体交易发生前后生成的用户数据,进行“精准营销”与“大数据杀熟”行为,这会侵犯用户隐私权与知情权。企业对用户数据仅享有不完全所有权,即在用户授权下享有使用权,应承诺与用户分享收益,如派现(券)、服务折扣、数据衍生品优先、免费或优惠使用等,对此司法解释应予以明确(深圳就确立了以“告知——同意”为前提的个人数据处理规则)。如果企业(包括数字企业与网络平台企业)在经过用户同意而搜集原始底层数据之后,运用算法建模脱敏清洗,可遵循“额头出汗(谁付出劳动,谁享有所有权)”原则或“算法规制反向确权”[32]原则,将此类开发数据及其衍生品的产权赋予算法技术劳动付出企业。特别地,公共事业经营企业的数据属于依法从事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而产生和获取的,根本目的是公共利益最大化,公共属性明显,其产权是不完全的,收益权不应由企业独享。在为更好地提供诸如疫情防控、交通管理、公共资源配置以及国家安全等公共服务的特定条件下,企业应配合政府调取相关数据。
政府数据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使用价值不可分割的特征,同时考虑政府与生俱来的公共属性,本文认为政府数据属于公共产品或公共資源。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没有产权主体,因为政府依法在数据搜集、整理、存储、挖掘、确权等方面付出了大量劳动,为数据资源化、资产化与价值化提供了可能,政府使用数据也是以公共利益为基本导向的,且通过稳妥开放共享数据,推动“数据孤岛”问题破解。从最大化政府数据效益与安全发展的角度考量,政府数据的所有权应由国家代表全体人民享有(即国家所有权),其产权应界定给政府,并授权相应职能部门或特定法人机构运营。
(二)建立健全数据要素科学的价格生成机制
沿着要素配置市场化变革的逻辑进路,数据要素合理价格的制定应充分体现市场决定要素价格的基本经济原则,建立由均衡价格参照机制、询价竞价机制、公允估价机制构成的数据要素科学价格生成机制。
数据要素的均衡价格参照机制是基于国民经济部门的投入产出均衡而形成数据理论价格的定价机制。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价值转型理论,商品的价值分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三部分,依循完全竞争假设与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原则,经过要素在部门内部与部门之间自由流动直至达到相对稳定状态,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即生产成本(预付资本,即不变资本加上可变资本)与平均利润(预付资本与平均利润率的乘积)之和。借助大数据技术,依据特定“算法”能模拟出数据要素在不同部门达到相对均衡状态时的理论价格,可将之用于数据要素定价或市场交易参考基准。
数据要素的询价竞价机制是由供需双方共同作用而生成交易价格的定价机制,是市场机制实现其价值的直接表现。数据市场交易价格与供需状况、市场结构等紧密相关。当供需不匹配时,数据市场交易价格将偏离理论基准价格。如果供需的数量都很大,数据市场接近完全竞争状态,可让买卖双方基于初始基准价格在依法建设运行的平台上询价与竞价,由市场自行探索生成体现遵循价值规律的价格。当供给方较少时,应允许卖方采取成本加成策略,获取适度垄断利润,引导卖方主动出售数据,增加数据供给量。此外,倘若数据要素供给与需求的市场主体都存在较强的垄断力量,这时可遵循福祉最大化原则,通过竞价拍卖的模式形成市场交易价格。
数据要素的公允估价机制是在數据要素资源化基础上,经由可信第三方对数据资源进行评估的定价机制。数据在搜集与建模脱敏等处理形成要素资源后的价值较低,而且受高频性、外部性等因素影响,数据价值不够稳定。通过数据要素与具体业务融合以及交易、流通等社会化配置等方式实现资产化与资本化,能够提升拓展数据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由于数据集可分割、需求方技术能力和使用目的差异以及诸如并购、诉讼等非交易场景的存在,基于卖方视角的询价竞价机制不适用,需要立足买方视角依托持有数据资产评估许可证的第三方对数据资产进行估价,形成公允价格。2021年10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信息技术服务 数据资产 管理要求》(GB/T 40685-2021)为数据资产管理和价值评估提供了借鉴参考。
(三)创新拓宽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方式
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直接方式是通过市场出售脱敏的数据原材料、交易标准化与定制化数据产品、提供数据接口(API)服务、为B端行业客户与G端政府客户提供数据咨询服务、为C端客户提供消费“画像”与营销触达服务,从而获取经济回报。这与数据要素资源化相适应,但难以支撑数据的资产化与资本化。因此,可尝试“估价作股、数字租金、以数易数或以数易商(服)”等方法以适应数据价值链的延展。
估价作股是通过数据资产估价参股企业,并凭借股份从数据资产收入中获取股息、股利或者通过出让股份获取收益的分配方式。此种分配方式适用于组合海量数据、构建数据集合、深度挖掘数据价值的情景,有利于促进数据由要素资源升级为资产与资本。数字租金是数据平台等相关企业向租户提供经过封装和脱敏的价值数据和开发环境,合作开发大数据产品与服务,租户则向平台商缴纳平台资源使用费用、数据调用费、技术服务费等,这是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另一方式。在数据要素产业链分工严格、技术门槛高、成本较大的背景下,数字租金模式一定程度上能够消除数据及其衍生品需求方资金不足、技术不足、使用目的差异等制约,加速数据要素价值实现速度,使数据要素价值成倍增加。此外,数据生产经营主体亦可尝试以数易数或以数易商(服)模式实现数据收益分配。与前述不同,该分配模式并未通过货币中介体现价值,数据供给主体之间或数据供给主体与需求主体之间(平台与平台、个人与平台等)遵循商品交换的等价交换原则,在签署共享服务等协议条件下直接进行数据与数据的交换或数据与服务使用权限的交换(如京东万象、阿里等数据平台进行的API交换;数据宝平台上国有数据、政府数据之间的交换),这有利于引导各方共享数据,降低搜集成本,壮大数据集合,加速数据要素市场形成。
(四)建立健全数据收益公平分配的制度保障
数据要素产权不清、商业机密和个人隐私泄露、市场垄断、监管缺位等问题容易导致人民福祉受损,致使分配结果不公。因此,有必要基于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内在的公平导向,健全完善数据要素收益公平分配的制度安排。
健全有关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法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就数据安全作出了相对完备的规定,但其中与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条款较为笼统。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对个人数据搜集、处理、传输与使用等予以了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也强调保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个人、组织利益,但其对个人信息等涉及安全与隐私保护的问题未给出充分的司法解释。在发达的数据交叉识别技术下,数据占有主体完全能通过看似碎片化的行为、习惯、偏好等数据识别个人身份或窥探隐私,并将之运用于经营,获取不正当经济利益,而作为数据提供者的个人没有获得应有的收益补偿。为解决数据使用可能导致社会福利受损的外部性,需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自然人信息受法律保护及相关细则的基础上,加快界定不同数据产权,完善数据财产权制度,促进数据人格权与财产权两大权利属性特征兼容;鼓励深圳、上海、广州等有条件的地区积极探索完善出台地方性的数据交易条例(规范),对数据运营企业进行技术、安全审查等准入审查,确保其具备深度脱敏、安全运营微观主体数据的能力;在数据人格权适度商业化的前提下,尝试探索个人在数据市场上交易私人信息的司法实践,确保个体获取隐私数据交易收益,促进个人分享数据,降低隐私保护及维权成本。
健全数据要素流通的治理制度。确保数据要素收益公平分配,需加强数据要素市场的监督管理制度建设,着力消除市场失灵,形成全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数据要素市场体系。首先,应在地方设定的数据交易规范或标准基础上,建立全国适用的数据交易法律或法规,统一数据交易市场规则,提升数据流通效率。其次,国家应坚持福祉提升和公平竞争导向,发布数据要素交易与使用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指南;适时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统一执法标准,以限制竞争与否和支配地位滥用与否为监管重点,明确对数据垄断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处罚力度。此外,应加强监管队伍建设,设立专门监管数据流通的政府职能部门;建立监管信息共享机制,形成全面监管的制度环境。最后,应探索征收“数字税”,实施强制许可制度。
参考文献
[1]李政,周希禛.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学习与探索,2020(1):109-115.
[2]王融.关于大数据交易核心法律问题——数据所有权的探讨[J].大数据,2015(2):49-55.
[3]刘朝阳.大数据定价问题分析[J].图书情报知识,2016(1):57-64.
[4]干春晖,钮继新.网络信息产品市场的定价模式[J].中国工业经济,2003(5):34-41.
[5]LIANG F, YU W, AN D, et al. A survey on big data market: pricing, trading and protection[J]. IEEE Access, 2018, 6(4): 15132-15154.
[6]左文进,刘丽君.大数据资产估价方法研究——基于资产评估方法比较选择的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9(8):116-119.
[7]朱新力,周许阳.大数据时代个人数据利用与保护的均衡——“资源准入模式”之提出[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1):18-34.
[8]陈琳琳,夏杰长,刘诚.数字经济市场化监管与公平竞争秩序的构建[J].改革,2021(7):44-53.
[9]吴江.数据交易机制初探——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J].天津商业大学学报,2015(3):3-8.
[10]KERBER W. Digital markets, data, and privacy: competition law, consumer law, and data protection[J].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 Practice, 2016, 11(11): 856-866.
[11]SAMUELSON P. Privacy as intellectual property?[J]. Stanford Law Review, 2000, 52(5): 1125-1173.
[12]曾彩霞,朱雪忠.必要設施原则在大数据垄断规制中的适用[J].中国软科学,2019(11):55-63.
[1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4]洪银兴.先进社会生产力与科学的劳动价值论[J].学术月刊,2001(10):38-43.
[15]洪银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财富理论的探讨——基于马克思的财富理论的延展性思考[J].经济研究,2020(5):21-30.
[16]蔡跃洲,马文君.数据要素对高质量发展影响与数据流动制约[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1(3):64-83.
[17]蒋永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现实路径[J].国家治理,2020(31):43-45.
[18]谢康,夏正豪,肖静华.大数据成为现实生产要素的企业实现机制:产品创新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20(5):42-60.
[19]宋冬林,孙尚斌,范欣.数据成为现代生产要素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经济学家,2021(7):35-44.
[20]王梦菲,张昕蔚.数字经济时代技术变革对生产过程的影响机制研究[J].经济学家,2020(1):52-58.
[21]MCKINSEY & COMPOANY. Big data: the next frontier for innovation, competition and productivity[R/OL].(2011-05-01)[2022-03-13]https://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mckinsey-digital/our-insights/big-data-the-next-frontier-for-innovation.
[22]师博.人工智能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理诠释[J].改革,2020(1):30-38.
[23]陈维涛,韩峰,张国峰.互联网电子商务、企业研发与全要素生产率[J].南开经济研究, 2019(5):41-59.
[24]杨汝岱.大数据与经济增长[J].财经问题研究,2018(2):10-13.
[25]王一鸣.数字经济启动发展新引擎——激发数字经济新动能[N].人民日报,2020-07-28(005).
[26]何大安,杨益均.大数据时代政府宏观调控的思维模式[J].学术月刊,2018(5):68-77.
[27]朱建田,何艳霞.大数据:重塑“新计划经济”还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J].西部论坛,2020(5):13-21.
[28]马建堂.新常态下我国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的重大创新[J].行政管理改革,2015(11):4-9.
[29]丁文联.数据竞争的法律制度基础[J].财经问题研究,2018(2):13-17.
[30]梅夏英.数据的法律属性及其民法定位[J].中国社会科学,2016(9):164-183.
[31]戴双兴.数据要素:主要特征、推动效应及发展路径[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6):171-177.
[32]韩旭至.数据确权的困境及破解之道[J].东方法学,2020(1):97-107.
The Participation of Data Elements in Income Distribution: Theoretical Analysis, Factual Basis and Practical Path
LI Biao SUN Kun SUN Gen-jin
Abstract: Data elements have become strategic resources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According to Marx's labor value theory and distribution theory, the participation of data elements in income distribution is the economic realization of data element ownership. After the data elements are integrated into social reproduction, the wealth enhancement effect is endogenous under the role of productivity promotion mechanism, circulation efficiency improvement mechanism, consumption expansion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mechanism and distribution structure optimization mechanism.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data elements has shaped the driving force of digital growth,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igital intelligence" and improved the efficiency of macro-control. The practice of data elements participating in income distribution should take clearly defining the ownership scope of different types of data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legally avoid the restriction of illegal use or transaction data on its elementalization and resource;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data element price generation mechanism composed of balanced price reference mechanism, inquiry and bidding mechanism and fair valuation mechanism, so as to make the transaction pricing of data element market more scientific. On the basis of taking market transactions as the main way for data elements to participate in income distribution, we should cultivate and encourage new forms of participation in income distribution, such as "valuation for shares, digital rent, trading by numbers or trading by numbers(services)", and promote data elements to expand income along the value chain of resource, capitalization and asset.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f data circulation, accelerate the legislation, amendment and interpretation of relevant laws related to data right confirmation, privacy protection and data oligopoly,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system to ensure the fair distribution of data element income.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data elements; income distribution; wealth cre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基金項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理论框架与推进路径研究”(JBK220201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创新与路径选择研究”(JBK2004015)。
作者简介:李标,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四川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孙琨,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孙根紧,四川农业大学商旅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