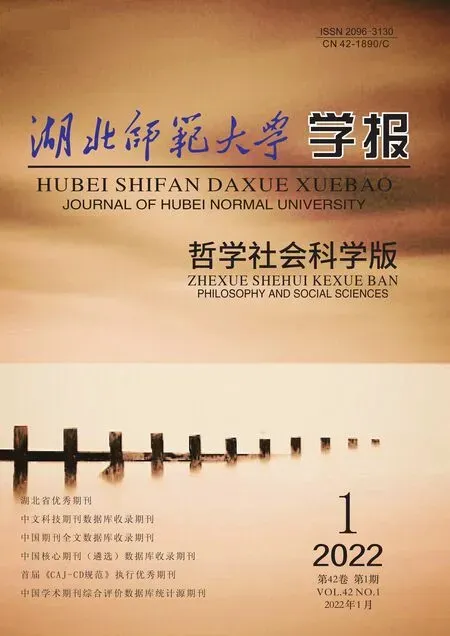明代寺院捐赠与地方社会的互动
——以泽州县为中心的考察
王 后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引言
佛教在元代经历了短暂的辉煌复兴后,进入明代以后不得不减缓发展势头。明代统治者一方面利用佛教劝导百姓向善的积极因素来稳定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又严格管理佛教组织,控制寺院经济的发展,防止佛教威胁政治统治。国家将佛教置于严格的控制之下所带来的后果是中下层僧尼进一步丧失思想、经济方面的独立性,被压缩的生存空间使得他们不得不面向社会获取有效的资源来维持寺庙的正常运转。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僧侣面向社会不同群体募资来维修颓圮坍塌的寺庙,并借助社会力量宣扬佛教的教义。作为回报,寺庙会将捐赠的功德主的姓名刻录在石碑上存留纪念。捐赠者希冀通过这种方式彰显自身的财富和权力,并在地方社会中巩固自身的地位。研究这些记录碑刻可以为我们展开明代地方社会关系网络的动态变化,并清楚了解到佛寺捐赠怎样推动了地方社会的整合。本文以三晋出版社出版的《三晋石刻大全》(晋州市泽州县)为主要史料,选取佛教文化悠久的泽州县作为研究区域,分析泽州县的佛寺分布和佛寺捐赠群体,并将佛寺置身于地方社会中考察其动态演变。
一、泽州县佛寺分布情况
今天的泽州县位于山西的东南部,太行山的北部,且处于山西与河北两省的交界处,自古为三晋通向中原的要冲,境内有丹河和沁河流经。宋代泽州属河东路泽州高平郡,元代属晋宁路,以泽州领五县:晋城、高平、阳城、沁水、陵川。明代洪武元年,以晋城省入泽州,隶平阳府。九年,改直隶州,属冀南道,隶山西布政使司领高平、阳城、陵川、沁水四县。清朝雍正六年,奉旨升泽州府,州治改为凤台县,府下辖凤台、高平、阳城、陵川、沁水五县。
对于泽州地区而言,佛像崇拜是乡村社会中信仰最为普遍的神祇之一。早在北魏时期佛教就对泽州地区产生过一定影响。现存泽州县巴公镇崇寿寺的一块造像碑显示该碑勒石年代为北魏,碑身四面都雕刻了大大小小的佛像,说明这一时期的佛教在泽州地区是有一定的信仰受众。唐宋以后,佛教发展进入鼎盛时期,统治者大力崇佛,下令在全国各地修建多所佛寺,并经常性地出资印刷佛经,举行盛大的迎佛骨活动。这些都为民间信仰佛教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唐宋年间泽州地区兴建了数目众多的佛寺,佛教深刻地影响着当地百姓的信仰,具体表现在信徒自发组织念佛。“城隍信士,共结法华。邑都有二十八人,各持念《法华经》一品,至一二年后,伦散出邑。”[1]王公贵族甚至会出资代替佛寺捐纳赋税,来表明自己的乐善好施,以求积累功德获得福报。“泽州东南卅里,敕赐寺额号曰:“青莲”。“其寺北齐初首禅师口奏藏阴,所管三庄田地计余顷,两税计钱七千五百。至大和元年,僧惠愔词说郡主王中丞摊却六千五百余,有一千寺家输纳。”[2]佛教植根于泽州乡土社会,历经几个世纪的朝代更替,依然拥有广泛的信徒且借助佛寺维持自身的延续,这与僧尼的不懈努力分不开。寺庙僧侣除了注重自身钻研佛法以外,还会在举办法会时延请其他高僧进行宣讲,从而增加寺庙的神圣感和权威性。北宋青莲寺碑刻中便记载“时大宋崇宁四年岁次乙酉三月一日,因下院净影寺斋会,有住持福润预日赴上寺,请峦禅师说法。”[3]
明代以后,王朝统治者确立的宗教基本政策是以儒教为中心,佛道二教作为辅助稳定社会秩序,并实现对佛教的全面管控。明太祖朱元璋规定把佛教重新划分为佛、讲、教三类,其中教僧主要负责举办经忏仪式,为百姓进行消灾超度。另外,洪武十五年,朱元璋置僧道二司:
在京曰僧录司,道录司掌天下僧道。在外府州县设僧纲道纪等司,分掌其事,俱选精通经典戒行端洁者为之。僧录司左右善世二人,正六品、左右阐教二人,从六品、左右讲经二人,正八品、左右觉义二人,从八品;道录司左右正一二人,正六品、左右演法二人,从六品、左右至灵二人,正八品、左右玄义二人,从八品。府曰僧纲司,掌本府僧教,都纲一人,从九品、副纲一人,未入流。道纪司掌本府道教,都纪一人,从九品、副纪一人,未入流。州曰僧正司,僧正一人,道正司道正一人。县曰僧会司,僧会一人;道会司,道会一人,俱未入流。凡天下府州县寺观僧道名数,从僧录道录二司核实而书于册,其官一依宋制不支俸给吏牍以僧道为之,仍以佃户充从者,凡各寺观住持有缺,从僧道官举有戒行通经典者送僧录道录司,考中具申礼部奏闻,方许州县。僧道未有度牒者,亦从本司官申送如前,考试礼部类奏出给。凡内外僧道二司专一检束天下僧道恪守戒律清规,违者从本司理之,有司不得与焉。若犯与军民相干者,方许有司惩治。[4]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僧尼的管控,使寺院组织纳入到国家政治规范当中。除了以上措施之外,朱元璋还下令合并裁汰全国寺院,减少僧尼数量。通过碑刻内容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一举措的成效。现存明代时期的碑刻几乎很少看到创建寺庙的内容,大部分是记录对明代以前的寺庙进行重修的捐赠。但是,并不能因此认为佛寺的发展大受打击,实际上,明代的泽州府仍然是佛教重镇,与其他民间信仰所供奉神灵寺庙相比佛教仍然占据主要位置。地方志记载的佛寺数目多达三十余所,其分布和修建情况见表一。

泽州府附郭佛寺分布表[5]
通过上表我们可以知道泽州府治地区保存的寺庙数目是相当多的,而且其分布不仅是在山林之中,很多是作为村庙被加以供奉的。但由于国家对佛寺的裁并,可以看出明代甚少新修的佛寺。
二、佛寺捐赠的动因探析
如何维持佛寺的物质建筑并使其能够得到良好的修缮成为寺院僧侣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因为这既关系到他们是否能够生存下去,又关系到佛教在当地发展的兴衰。并不是所有的寺庙都能够有大片土地作为稳定的收入来源支持庞大的修缮费用,向社会不同群体募捐成为了他们的首要选择。一般而言,社会阶层向佛寺布施的直接动因就是积累功德,但是当佛寺深入民间社会,成为区域内部的神圣空间时,它成为了区域内各种力量施展的舞台。本文认为社会不同群体捐赠动因还存在以下几点。
(一)形成身份认同感
隐藏在泽州硖石山深处的空幽古寺青莲寺凭借着其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人文景观成为了不少文人官员流连忘返之地。青莲寺实际是由上下二寺组成,两寺相距约500米。寺庙初创于北齐,现存青莲寺一则名为《大金泽州硖石山福严禅院记》记载道:“‘古青莲寺’寺额,咸通八年所赐也。寺之东五里古藏阴寺,即北齐昙始禅师之所建也。”[6]随后昙始的弟子慧远在寺内修行弘演大乘佛教,得道后掷笔腾空而化,形成了该寺著名的人文景观掷笔台。北宋太平兴国三年青莲寺上院赐额“福严之院”牒,随后的历代都对该寺加以修葺,寺庙本身悠久的历史再加上各地名僧来此修行主持使青莲寺成为泽州的名寺。因此,明代许多文人墨客都到此拜访抒发胸臆。卜正民教授认为士绅在佛寺留下诗文属于文化捐赠的方式,“文学的赞辅像经济的捐赠一样,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但都有助于建立一个在他人看来有威望的公共宗教机构。它明白地显示出寺院是值得士绅发生兴趣的,其间蕴涵着一种保护。文学作者越著名,寺院的声誉就越辉煌。”[7]如果只从佛寺角度来对待士绅留下的赞赏性诗文,那么人们很轻易地就得出结论这类诗文实际上的作用是为了增加寺院的价值从而使其更具吸引力,并且往往会认为这类诗文是士绅出于交往密切的僧侣的请求而作。换一种角度出发从士绅本身的视野来看,留下诗文隐藏着他们内心深处的诉求,因为文字作为一种记录向前人致敬的同时也起到了一种区隔于他人的身份象征的作用。
现有的碑刻记录显示历经整个明代共有约十一位士绅留下了关于青莲寺的诗文碑刻,除了有着同一籍贯之外,他们相似的仕途经历不禁使人猜想这些士绅本身之间是否存在更为密切的联系以及诗文创作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下表是笔者记录的参观青莲寺并留下诗文作纪念的明代士人。

青莲寺文化捐赠身份表[8]
不难看出这些士绅的地位在当地都是相当有名望的,且都出身正途。那么他们如此热衷于造访青莲寺是出于对佛教的信仰吗?尽管明代出现三教合一的思想发展潮流,不少儒人文士将佛教与儒学融会贯通,本身也表现出强烈的宗教信仰,甚至大力支持佛教在民间的发展,比如黄宗羲所撰的《明儒学案》中便如此记载儒学者邓豁渠:“己亥,礼师,闻良知之学,不解。入青城山参禅十年。至戊申,入鸡足山,悟人情事变外,有个拟议不得妙理。当时不遇明师指点,不能豁然通晓。癸丑,抵天池,礼月泉,陈鸡足所悟,泉曰:‘第二机即第一机。’渠遂认现前昭昭灵灵的,百姓日用不知,渠知之也。”[9]但是,查阅泽州籍进士的生平,似乎并未能明显看到他们是否有对佛教具有虔诚的信仰,甚至很少涉足对于其他佛寺的捐赠。这大概是由于青莲寺是著名的名胜古迹,被关注程度远远多于其他佛寺,因而士绅们的选择具有针对性。然而长期接受儒家伦理体系价值观并尊奉其为正统思想的士绅们对于佛教的态度是暧昧的,诗文当中对于佛寺的赞美固然证明了他们并不反对佛教的存在,但是否对佛教有着更深一步的认同则难以捉摸。在一则记述青莲寺福严禅院经文历史的碑刻当中,撰文者都察院右都御史周盘则提到:
夫毘蓝托荫,盘陀证果,雨花吐露,尔辈所知也。鹫岭法华、逝林华严、三乘五教,尔辈所知也。金人兆梦,白马归东,利生广大,调物供生,亦尔辈所知也。至于无人无我,无染无净,不生不灭,非明非暗,不有之有,成于有有之宗,不空之空,而现于空空之境。吾儒之道,真常湛然,弗随物化,脱声尘杂,文字白醭。出口,青草生舌,身心混融,虚己冥真,有绝不可思议者在,尔知之乎?吾儒之道惟天,不可得闻。[10]
作者实际上认为儒家伦理所蕴含的价值和意义并没有真的被世人所清楚的知道和了解,甚至暗含人们过分关注佛教而忽视对儒教的钻研的谴责之意。那么,这些士绅创作的诗文是否暗含着其他的表达呢?这里我们需要首先梳理这些士绅的仕途经历来一窥究竟。弘治进士出身的孟春,地方志记载:
守严州,以清官第一称。擢囧寺,力拒阉瑾及守档勒贿。巡抚宣镇,威惠并著。时于经、钱宁、江彬等阉势甚张,来索粮价数万缗,坚持不与。大瑣张永行边,过宣大,群僚匍伏,春长揖而已。群小衔之,卒为所中。落职。嘉靖初荐起,巡抚顺天。时大旱,奏辩许铭冤,并乞斩贪弁暨宸濠逆党,以答天谴。设豫备仓,经画部内,得粮二十万石。诏嘉予,晋吏部侍郎。上言大同反侧,惟无控制大臣,故及此,乞添宣大及陕西三边总制各一员,报可。佐铨望重,世庙赐“行不自欺”四字旌之。未几,十大狱起,复以直言忤时宰。遂与颜颐寿、马录同时削籍。疾革,嘱殓以青袍角带。赠工部尚书。[11]
可见孟春是明代官场的一股清流,敢于直言进谏且不与阉党同流合污。而与孟春同为好友的李瀚在明正德十一年一同游览青莲寺,留下了感慨年华易逝的诗句。李瀚也是以为人正直、不畏权势而著称,“瀚以风裁自持,不畏强御,所至以严正见惮,然持法平恕,人亦无怨言。”[12]在李瀚担任乐亭知县时致力于地方建设,加固城墙保护城内百姓安全,又大力改善当地教育环境,兴文教,地方志赞扬“他惠政种种不能悉,大都洁已爱民,寛而有制,严而不苟,故公去逾百年,而士民思慕无赞。”[13]青莲寺仅仅是因为它独特的景观就能吸引如此多的士绅前来赏景作诗吗?实际上青莲寺已经成为一种精神象征,悠久的历史和无数名人留下的诗文使后人争相模仿,企图表达自身与前人也一样具有高尚的品行从而区隔于其他士绅。再比如任泽州知州的陈棐于嘉靖二十九年同样来到了青莲寺,留下其赞叹景观的诗作。有趣的是陈棐同样也是以做官刚正不阿,居官清正而著称。嘉靖二十二年,他向明世宗进言,力陈京闱之弊,指出科举考试中存在着冒籍、寄籍参加考试,甚至有人勾结考官等弊端,随后提出了改善的建议得皇帝认可,并在之后频繁上奏关于民政的奏折,请求治理水患和边疆防御。
这些具有相同做官经历和为官风格大体一致的士绅来到同一寺庙留下诗作,笔者认为并不是一种偶然,被镌刻的诗文成为一种记录被存放在地方社区的中心被众人观摩,这增添了寺庙的名望的同时也强化了士绅群体的身份认同感,这种文化捐赠的方式暗含了一种期冀,那就是能够与在此留下诗作的前人一样被纪念。他们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区隔于一般的士绅群体。
(二)建构地方话语权
明代统治者为了加强各地的防御,将宗亲派往全国各地镇守,尽管作为藩王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他们仍然面临着如何在地方上更进一步的渗透自身势力范围的问题。以明代宣宁王为例,“明宣宁王、隰川王皆代王支子也。代王桂初封豫,洪武二十四年改封代王大同。建文时,废为庶人。永乐靖难后,复之。稍不自检,与其子逊炓、逊烠亵衣冠行市,袖钟斧伤人。上闻之,遗书戒谕。王亦悔,逊炓王第七子,正统二年册封宣宁郡王,初建大同府城,天顺四年徙泽,成化六年卒。谥靖庄。”[14]明英宗考虑到山西大同城中狭隘,郡王数多,故令各州造府以备迁徙。要离开故土重迁,朱逊炓自然是万般不愿,于是以泽州居住环境恶劣水土不服为由请旨改迁。皇帝回复到:
夫泽州去大同不远,气候水土未必不同,疾病未必因此而生,往者因王兄弟欲同迁一处,以便养母,故定居于此。今居之未久,辄因疾病,多生疑虑,又欲改迁,何纷更如此。近灵丘王奏云:绛州不如泽州,水土肥饶,人民丰富,心欲之而不可得,而王乃以为恶地,何所见不同如此。是皆溺于便安,心不专一之过也,所请难允。王宜慎自调摄,安心以居,毋自私以求便安,毋自惑以生恐惧,毋再奏扰,以取祸愆。特书以复,王其知悉。[15]
皇帝下令使大同郡王迁徙不仅仅是因为如此多的郡王居住此地给大同造成了财政压力,更因为山西独特的地理位置需要派郡王担负守边的责任,故而英宗自是拒绝了宣宁王的请求。宣宁王逊炓和隰川王逊熮于天顺五年迁到泽州,但没过多久便去世。随后由其子朱仕嬴承袭封号,王府真正开始介入泽州地方事务是在弘治三年,位于泽州金村镇的显庆寺内住持明锐主张重修寺内大雄宝殿三楹,东老府宣宁王和西老府隰川王均参与了此次修寺的捐赠。作为外来群体,对佛寺的捐赠成为一种扩大自身影响力的方式,这是扭转地方民众对其看法的良好契机。因为仕嬴父逊炓以顽劣乖张而记载于史册,明史记录其以偏听纵杀而闻名,明英宗对这两位郡王深感头痛,于正统五年下令告诫:
近闻尔兄弟二人过失颇多,今畧举一二事重者,遇节进表,皆不行礼,是不有朝廷也;遇祭社稷未祭之,先骑马直入坛内,取猪胰鹿角鹿皮等物回宫中用,是不有神明也;世孙者,代府之宗嫡。尔二人专于父前离间,致父切怒世孙,尔兄弟二人又常随父及宫人,用砖石铁锤打破世孙府门,意欲害之,世孙躲避得免,是汝不有宗嫡也;先帝宣德五年,命世孙代祖裁决府事,王府文武官每清晨至府门候见,尔二人随父或步行或骑马出灵星门外,拦打本府官,不容入府见世孙,是陷父于不慈也;祖训离间亲亲,明有正条,尔二人自今宜存念至亲,洗心易虑,务隆敦睦,毋蹈前非。[16]
足以可见宣宁王逊炓和隰川王逊熮的行事作风顽劣。因此,在迁移到泽州后,面对一个全新的环境,群王们不得不考虑如何参与到地方事务上来,并获得一定的话语权。随后王府广泛参与佛寺的捐赠,于正德十四年再次捐赠崇寿寺修造地藏殿妆塑十王,此次的捐赠者为宣宁王府仪宾蔡玺。
佛寺作为一个具有开放性特点的地区中心,成为与世俗社会交流的公共空间。作为历史悠久的显庆寺和崇寿寺,在泽州区域拥有广泛的信徒受众。其金碧辉煌的庙宇自然吸引着络绎不绝的人们前来礼拜。因此,对寺庙的捐赠不仅会在碑刻上存下记录,供他人观瞻,还是树立形象的巧妙途径。对于宣宁王府和隰川王府而言,捐赠佛寺就是扩大自身在泽州区域的影响力的选择之一。
(三)延续精神信仰场域
并非所有的寺庙捐赠都出自社会群体的主动募捐,如果没有寺院僧侣的组织和筹募,很难完成大规模的寺院修葺。僧侣发起社会募缘主要是由于寺庙年久失修,难以维持,有碍观瞻。如二仙庙内的佛殿“弛弗治,历既久,基址颓圮。”后于天顺戊寅年间,在社内乡耆原文秀的发起下,重建佛殿三间。观音堂内“堂置盖亦有年。吾祖曾鲜僧万聆而就食者,讵堂鸣经浃旬弗之据。迨薄于今,剥落逾圮,吾兄周埙谋、叔周文魁检督尊行化诱,不忘先人而图惟修葺……”[17]因此,最渴望使寺庙能够焕然一新的首先是僧侣,碑记中所记载的重修佛寺的工程一般都是由寺院内僧人募缘集资兴修,明代兴修的显庆寺就是由僧人明路主持的,随后历任掌事僧侣都在继承前任的基础上孜孜不倦地对佛殿进行维修和加盖:
国朝成化八年壬辰,掌寺事僧明路发大头力,募缘兴修,首建千佛阁五间,次作两夹室以及东西廊庑,总若干楹。中供水陆大会。十年甲午,僧明彻继领寺事,重修天王殿三间,塑绘如式。十六年庚子,明路又修钟鼓二楼,左右对峙,晨昏叩击,以节焚诵。弘治三年庚戌,法堂将废,明鋭主法席,撤而新之,复还旧观。惟毗卢殿狭隘,瞻礼弗称。十一年戊午,明坚继主法席,慨然以改作为己任。于是倡率寺众募缘,裒积所施,庀材鸠工,增拓旧址。加三之一,乃作大殿三间,中塑毘卢佛像,面离;背塑观音大士像,面坎。轮焕庄严,灿然一新,芗镫旛盖。鲜洁华好。[18]
之所以要不断翻新和增修的目的依照僧侣们自述是为了光复法门。这背后隐藏的是佛教的生存危机,明代统治者对于佛教是一种暧昧的态度,既认可佛教的存在,又压制其过分扩张,嘉靖皇帝就施行严格的禁佛政策,“上曰:应祀神庙令有司修理,但近年以来,奸民阿奉,镇廵司府州县等官,不问贤否,暨立祠堂、去思碑亭。并私创庵院淫祠,其令廵按御史逐一查毁,即以所鬻价,为修理神庙之费。”[19]僧侣们所面临的窘迫处境使得他们寄希望于修寺来宣传佛法。
实际上,僧侣修寺的另一动机在于维持自身生存。明代万历年间,一块记载重修佛殿的石碑上记载到:
尝闻作善降之百祥,未闻作不善可以蒙余庆者也。州治东湖裹村,其乡多好善乐施者,西北隅古有二仙庙,祠稍涉损坏,即行修理。庙之东有佛殿一所、三官殿宇一所,非前人创盖不坚,但岁远日久,其庙宇墙壁不免被风雨所伤。本村耆老原朝夆、原显仁、原有本会诸一社人曰:“先人建立若此,我辈坐视塌毁,无论神不保佑,宁不衾影有余愧乎?”因此合社人等俱发善心,各输囊金,不啻佛殿墙壁周围,易土而为砖,即三官殿前墙,亦一时重修而更新。吾想庙之新则神将安矣,神之安则人有依矣。自是默运威灵,阴沾渥泽,乃理之一定而不移者也……[20]
只有庙宇辉煌壮丽,神灵才能够发挥更大的功效,若是颓废衰败,神灵则不会庇佑,因此人们不会相信祈祷一座破败的庙宇能够得到回应,而寺僧恰恰需要依靠施主们的捐资来维持基本生存,所以维持佛寺的辉煌与他们自身也息息相关。
除了僧侣之外,希望延续佛寺的群体就是普罗大众。如明万历六年位于泽州巴公镇西郜村的崇寿寺的佛像修建就是由本村人捐资。表三是其捐资数目和人数统计。
由表格可看出捐赠人数最多的为李姓,张姓和赵姓紧随其后,这些不同的家族是否出于扩大宗族力量而对同一个寺庙进行捐赠有待进一步的探究。普通百姓希望能够通过捐款修寺来积累功德,因为修寺是“是无量之功德,一里之托庇也。”[22]除此之外还有消除业报,保佑健康和财富的获取,解决自身在现实中的困境。“愿诸神之锡瑞兮,俾富寿而炽昌。”[23]有意思的是,僧侣正是利用人们畏惧神灵害怕因为不敬佛而遭到报复这一心理,鼓励大众只有通过行善事才能够抵消自己所犯下的业,利用神灵来威慑那些对于佛教信仰轻视的人们,这样的宣传对于文化层次并不高的百姓应该是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在修佛庙的捐款名单中,甚至列有妓女吕氏捐银二钱,还有常客光卅商人段繍衣“出赀财置颜料,积日累月,积月累年,越四载,造像三十三尊,记费于有余金……。”[24]这反映了佛寺并不会因为群体身份而对捐款人员进行限制。不同群体共同参与到修寺这一活动中,带着对佛像的尊敬和敬畏捐献自己的力量,从而解决了自身在现实生活中难以解决的精神诉求,以求得心灵慰藉。更何况能够将自己的姓名存留在碑刻中成为纪念也是一件值得称赞的事情。
三、佛寺捐赠的社会功用
从僧人的募缘再到组织工匠进行寺庙的修葺,最后是竣工后举行庆典重新见证寺庙的辉煌并将捐赠者刻入石碑中进行纪念。这一历时长久的工程需要多方力量的合作,从而使得陌生人们的交流成为可能。在佛寺捐赠这一过程中,官方力量的较少介入给予地方群体发挥管理慈善事业的空间。这一仪式打破了区域内不同人群的生活界限,使他们能够共同参与到重修佛寺的公共工程上面,区域的整合功能因此得到强化。
(一)增强地方社会的凝聚力
寺庙是一个地区的文化和宗教的象征,它属于传统社会符号体系中的一环。重修寺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耗费的人力和物力以及财力是必须要多方协作才能共同完成,首先是要有发起人,一般是为僧尼或者是具有声望或者财富地位的士绅,其次要募缘,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这意味着这项工程能否成功,最后是召集石匠和玉工等人进行兴修。当所有的事情完成后,便会立下碑记,上面镌刻所有参与者的姓名,这对于所有的人来说,既充满了成就感,又能使自己觉得所在做的是一件神圣和积累功德积福报的善事。其次,因为人们认为重修寺庙关系到一个社区的福祉,所以并不会有谁是被迫参与到这件事情当中,因为他们所生活的地区是否能够得到神灵的庇佑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乡民们认为庙宇兴废与风俗盛衰有关,“从来庙宇之废兴系风俗之盛衰,盖人贫则忧,忧则享祀废,人富则乐,乐则善心生。”[25]修寺的过程使得参与进来的地区民众能够更有地方认同感,从而增强了凝聚力。部分佛寺的兴修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们对于佛教做法的需要,如资圣寺重修水陆斋,“大阳镇资圣寺旧有是会,亦因循发旷。镇中寿官李时中同都合富本寺僧理季并会中二十余人重修是斋,每月朔望次第举行。遇元霄日尽夜里祀,数夕隆然,而坛口然,而祀群然,而僧其仪秩秩焉,其乐锵锵焉,其人情睦然而和,祗然而敬焉。”[26]所谓的水陆斋是汉传佛教的一种修持法,也是汉传佛教中最盛大且隆重的法会,起源于梁武帝,发展于唐代,成熟于明代。该法会以准备的斋食上供诸佛,下救拔于六道众生,通过设坛场,传经讲法,使参与法会的众生得到佛法熏陶。史料显示正是出于人们的诉求,佛寺重举斋会,而人们在参加这一法会的过程中拉进了彼此的距离。由此可见,重修佛寺为地方社会生活与组织发展与存在提供了一个基础,增强了不同群体之间的粘合力。
(二)改善地方社会的风俗教化
佛教能够植根于中国的根本在于它完成了本土化的过程,并为适应环境作出了自我改造,它选择隐蔽自身与儒教中相悖的理念,而加大宣传自身与儒教在教谕百姓方面的一致性的特点。它将自己的地位抬高到与儒教相等的地位,认为两者所发挥的作用是互相辅助的,从而获取士绅的广泛支持,赢得社会基础。如强调佛教劝人向善,认为修佛像的目的在于物化了精神层面的神灵形象,才能够“使恶者惧而善者劝,此亦劝善惩恶之意”,这如儒教所宣扬的伦理观念殊途同归,佛教除了能够劝导人心向善,还能够劝化凶恶之徒,这也是士绅积极参与的原因。修寺本身的目的就是为了弘扬佛法,而佛教兴盛,意味着社会秩序能够进一步得到稳定,由此可见,重修佛寺的过程也是寺僧再度弘扬佛法的过程,它对于一个地区的社会教化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结语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产物在汉代传入中国,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变化完成了中国本土化的适应和世俗转变,并扎根于中国的乡村社会。作为区域的一个神圣空间,它在保留了佛教这种制度性宗教原有的独立性神学体系、仪式过程以及组织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具有区域性的特点,因为它被当做地方社会秩序构建的一部分,成为当地社会百姓求神拜佛场所的同时,也被作为不同群体表达自我力图扩大自身影响力的公共领域。整个明代佛教始终在泽州地区宗教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固然与庞大的信徒支持有关,但也离不开寺院僧侣主动接触世俗社会并为寺院延续作出的不懈努力。
——以官绅道德职责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