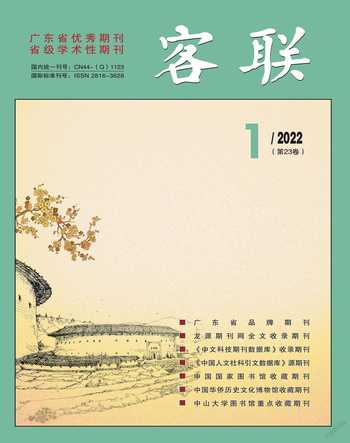反垄断法理论存在的冲突相关问题的研究
徐昕
摘 要:反垄断法主要是关于反对限制市场竞争、维护自由市场公平竞争和保持经济发展活力的一类国家法律行政规范的通称。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反垄断法已经开始有着很高的社会法律基础地位,被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已经变成是公平竞争市场经济的一项法律基本法,甚至被称为“经济宪法”“自由企业大宪章”等。随着反垄断法的发展,反垄断法保护的对象已从传统的主流法对法律关系主体关系两头的人的保护转向对主体间互动的关系状态的保护,也就是从主体到主体间的转向。这一转向说明了反垄断法是一种新的法律类型,其理论虽不是对主流理论的完全反动,但必将对主流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挑战。
关键词:反垄断;冲突;经济分析;局限性
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上,垄断通常被广泛认为仅仅是市场经济社会发展在达到一定经济高度以后必然就会产生的、与市场竞争直接对立的一种经济典型现象,是一种源自参与市场竞争但又反过来用以否定、限制、阻止参与市场竞争的"异化"经济力量,因而对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者和市场秩序来说无疑是极大的经济威胁。在经济法律学的意义上,垄断则可能是仅泛指特定的企业市场主体违法或者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状态或者竞争行为。同时,垄断又是所谓的"市场失灵"的一种经济典型现象表现,因而又被广泛视为政府对企业市场竞争进行适度行政干预和及时补救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反垄断法与其他反垄断保护政策其实是两个同义语,而其中反垄断法又主要指的是用于保护参与市场竞争的,因此也可以称为市场竞争法或者市场竞争保护政策。简单一点说来,但其实相对于一种反垄断不正当竞争的立法来说,反垄断法更多地还是体现了一种公法的法律性质。
一、反垄断法的既有理论认知及主要功能辨析
(一)反垄断法的发展
反垄断、维护竞争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奴隶社会和中国战国时期,这方面的法律规范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而后1890年的美国《谢尔曼法》一般被世界公认认为是我国现代传统意义上的反对和垄断法制度产生的重要标志。此后一百多年来,反垄断中的法律规范制度在当今世界其他各国已经得到了普遍的科学建立和研究发展。在早期,反垄断法主要应用集中在发达中和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成为这些发达国家政府保障和引导促进他们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法律政策性和法律制度工具。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已经制定和研究实施了许多反垄断法以用于保障和促进推动各自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美国特有的“反垄断”一词也是一种历史遗物,它源自于在后内战时期创建的控股公司(例如,标准石油信托或烟草信托)的法律形式。有时会用连字符“反托拉斯”拼写,来表示这是反对当时出现的大型托拉斯的立法i。
在立法之初,由于受传统社会观念和法律观念的影响,法律保护的重心是人,即法律关系两头的主体,因而反垄断法就以个体:竞争者与消费者作为保护重心。正如Sulivan及Fox在研究Sherman Act立法前的经济情况后所指出:在当时托拉斯风潮致使农民、劳工、小企业家受害甚深,民主共和两党皆提出反托拉斯政策,而终于通过了Sherman Act,其后立法通过的反托拉斯法案,也都一样着重于控制大企业的力量滥用,保护小商人有合理参与机会。1950年国会通过的Geller-Kefauver Amendment,严格控制企业结合,其价值考量也在于分散经济力量。法院严格执法的时期,促进机会平等、力量的分散、防止市场力量集中及剥削。Timothy J. Brennan(2018)认为反垄断应以稳定经济效率为指导的观点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发展。其实际表现可以追溯到1974年在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司(经济政策办公室,现为经济分析小组)成立了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家小组,1977年最高法院取消了非价格纵向限制本身的规则,1978年成立了联邦贸易委员会经济局,1982年,在反垄断部门的领导下,威廉·巴克斯特(William Baxter)頒布了第一版现代横向合并指南。至此这一趋势大体上持续了下去。
(二)反垄断法的目标
反垄断法虽是国家通称,但其在不同的发达国家中其名称各异。它们所需要规制的法律对象应该是大致相同的,即各种限制垄断或者各种限制垄断竞争者的行为。当然,在不同的法律称谓和不同立法法律体例下,它所需要包含的法律内容也很有可能不一定完全相同。刘永水教授(2010)认为现代反垄断法“保护的是竞争而不是竞争者”,已被世界各国反垄断法学者和实务工作者所接受。这一转向说明了反垄断法是一种新的法律类型,因而,其理论虽不是对主流法理论的完全反动,但必将对主流法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挑战。
反垄断法的根本目标都在于没有一个统一的执行模式,因为国家反垄断中的法律规定制度需要根据国家市场竞争的长期发展趋势变化实际情况而不断地对其进行改革完善。2007年,最高法院在非价格限制的基础上增加了纵向价格限制转售价格维持,因为这需要一个理性分析规则。2010年最新版本的《横向并购指南》拓宽了评估并购的价格效应和消费者损害的分析工具,从基于价格大幅非转换性上涨(SSNIP)的假设垄断测试下的市场定义,到通过包括但不包括在内的模型评估的单边效应仅限于向上定价压力和基于计量经济学的并购模拟。尽管如此,一段时间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反垄断的目的就是稳定的经济效率,其他因素应该是反垄断执法的动机。
也有众多学者提出了替代经济效率的方案作为反垄断执法和决策的目标:包括公平、不平等、劳动收入份额、工作、对竞争的影响(除了消费者福利)、消费者选择、促进民主、政治权力集中、全球化、国内对资源的控制、媒体准确性、环境保护、管理能力和减轻消费者错误。同时也有三个因素使人们普遍怀疑这样做的好处。其一,反垄断足够复杂,如果在平衡中加入额外的因素,可能会使公众更难理解。第二,可以采用其他政策来寻求这些替代品,这些替代品的设计要更好,而且不受某一特定公司或部门是否可能涉及反垄断违法行为的影响。第三,反垄断不应偏离其经济效率使命,因为没有其他促进经济效率的全经济工具。这些考虑和其他因素被用来评估将每一种选择纳入反垄断执法和裁决的潜在有效性。其中许多选择可能是反垄断执法的一个附带好处,但不是反垄断执法者和法院可以明智地权衡经济效率的一个因素。ii
因此,对替代品的调查得出的结论,反垄断的核心问题仍然是:追求消费者福利还是追求总体福利作为反垄断的目标。这是一个持续存在争议的问题。我只注意到,那些反对以静态总体经济效率为反垄断执法重点的人,除了在辩论的消费者福利方面的论点之外增加一些备选方案,并没有获得显著的额外吸引力,因此保障总体经济效率这一目标似乎还是占了上风。
二、反垄断法存在冲突的经济分析及其限制
任何一篇反垄断文章,如果对经济学的解释和分析表示了怀疑,都容易招致一些批评。例如波斯纳(R.A.Posner),就非常干脆且坚定的认为反垄断政策的唯一基础就是经济学。他们认为,任何质疑经济学作为进行反托拉斯分析的最佳手段都是对经济分析的一种的诽谤。确实,经济学分析这座大厦在过去三十年中建造的越发雄伟壮观,并且能够回答竞争法中出现的许多最重要的问题。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经济分析根本无法回答所有问题,有几个重要问题都超出了经济学的能力范围,至少也应当考虑到现代的经验技术。为了能够解决经济分析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必然会借鉴历史、政治和文化来制定答案,与此同时这也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相对性。但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没有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一)美国与欧盟对反垄断法的态度异同点
欧盟和美国对反垄断政策的态度就仍存在冲突。特别是对主导企业单方面行为的适当处理尚未得到一致。因此欧盟(EU)法仍在继续谴责那些在美国被视为无害的行为,最具争议性的是,要求经营成功的公司与竞争对手分享投资成果,结果是大西洋两岸的鸿沟阻碍了实现国际统一的努力。这一分歧引起了关于每个法域实体法相对优越性的激烈辩论,美国和欧盟都鼓吹各自的优势方法。美国指责欧洲抛弃了反垄断法的基本原则,实施保护主义、过度干预和破坏性政策。反过来,欧盟对于美国认为的其专属权限范围内所实施的措施发表的不受欢迎的评论表示不满,并坚定地捍卫其做法的合法性。尽管鸿沟有时看起来是不可逾越,但是相互之间的辩论仍可以带给人们许多启示。iii
事实上这场争论的基本原则惊人地一致。美国和欧盟都把相关的政策问题视为不包括经济方面的问题,并且都把消费者福利放在首位,拒绝承认反垄断法保护的是竞争而不是保护消费者。大西洋两岸的反垄断执法机构聘请经济学家分析商业行为的正当性,利用微观经济学、博弈论和计量经济学的工具,审查可以的合并行为且认为只有那些发现价格上涨超过竞争水平从而以配置效率低下的形式造成市场扭曲的行为才值得关注。仅从价格理论的角度就表明,经济推理和统计分析的进步最终将揭示最优政策。一旦确定了这些最优政策,全球协调应该是不可避免的。iv因此解决竞争问题的非对称方法的争论应该被认为是值得称赞的。只有通过相互参与智慧和有针对性的讨论,才能揭示监管干预的正确经济学。
占主导地位的公司的掠夺性定价为消费者带来了非凡的即时收益,但有可能在未来造成效率低下。一旦捕食者消灭了它的竞争对手,它可能就能够将市场价格提高到超竞争水平,从而牺牲消费者的利益。在判断这种行为的合法性时,必须在信息有限的情况下,权衡明确的短期利益和不确定的负面未来影响。在这方面,美国和欧盟从拒绝提供的情况中扭转了它们的偏好:美国注重于眼下低于成本的定价案例,对未来的影响并没有过多关注;而欧盟认为未来的损害起决定性的作用,对未来损害的可能性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并相应地将目前的利益减至最低。例如,产品捆绑和独家交易案例可能会立即为消费者带来效率收益,但有时可能会阻碍竞争对手未来进入市场。与拒绝交易不同的是,欧洲对其所认为的由提高效率的短期现象造成的潜在有害的长期影响给予了决定性的重视。
(二)反垄断法经济分析的局限性
严重的认识局限性必然会挫败任何试图解决短期和长期竞争效应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尝试。这种紧张关系贯穿于反垄断理论的某些方面,损害了经济学产生国际协调的能力。长期和短期权衡的不确定性是单靠经济学不能使得思想的完全融合。毫无疑问,欧盟对拒绝的短期效应给予了更大的重视,而美国一直非常不愿意要求私人当事方甚至垄断者分享其创新成功的成果。
尽管经济分析和消费者福利的有广泛的支持,还是有学者王先林(2017)观察到了实质性国际分歧的悖论,并试图赋予这一悖论意义解释长期影响的商业实践的经济分析相关的弱点。由于不同的管辖区各有不同,因此也有政治偏见。应该清楚的是,国际反垄断政策的协调将仍然难以实现法律和统计缺乏提供明确政策结论的能力。与这一结论相一致的是,作为一个历史问题,竞争法已被证明是为了促进实施竞争法者的政治意识形态而形成的。并且发现经济分析为大多数反垄断问题提供了最佳解决方案。但是即使是在竞争法这样一个受到学科严重和有益影响的领域经济学还是有局限性的。即使在其影响力不断增强的三十年中,经济学对竞争法进行了重塑和完善,但该法的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仍然难以进行经济分析。对于这些问题,政治和历史的混乱、个性化、特殊性和不科学性是万不得已的答案。但这些答案也有局限性:没有一个解决方案适合所有国家;不同的法律制度不能完全围绕着本质上是政治性的选择;旧制度和新制度各自的价值观很可能发生冲突。
竞争执法者倾向于得出最符合其政治倾向的结论,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反垄断法中的这种国际分歧。它解释了尽管双方一致认为竞争政策应主要为消费者福利服务,但持续分歧的积极悖论,揭示了未来危害的前景化,并就框架建设性辩论的适当术语提供规范指导。考虑到现代商业的全球范围,一个法域决定禁止一种被其他人视为无害的做法,这会产生强大的负面外部性。一家国际公司可能必须遵守最具限制性的监管机构的规则这一事实应该引起决策者的极大关注。鉴于反托拉斯法的可塑性和其行为的政治敏感性,竞争法只不过是当代公共政策的一种表现。然而,过去寻求实现的无数往往相互冲突的目标现在已经让位于普遍存在的关于共同标准的现代协议:消费者福利。经济学已成为赋予这一概念意义的唯一分析工具,并被用来相應地为反垄断调查提供信息。更具体地说,价格理论在商业实践方面得出客观可验证的结论的能力有限。
三、总结
反垄断法是生产社会化高度发展的现代市场经济的产物,它所解决的是市场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的动力机制。其保护的重心是所有市场主体共处的竞争秩序,而非单个市场主体经营者或消费者的权利。各国反垄断法主要还是集中在对垄断行为即各种实质性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制上,既包括已经具备某种垄断地位的经营者滥用其地位的行为,如垄断高价、搭售及附加其他不合理交易条件、强制交易以及差别待遇、掠夺性定价等,也包括尚不具备垄断地位的企业谋求垄断利益的行为,如达成固定价格、限制产量、划分市场等垄断协议,实施排除、限制竞争的经营者集中行为等。v
可以这样说,反垄断法对整合垄断的具体规制仍然是通过区分不同市场情形分别对待的,它本身并非一概地限于反对所有的垄断,而只限于反对那些特定的违反垄断市场行为。因而与国家规定发展产业规模市场经济的国家产业经营组织发展政策并不必然矛盾,两者仍然可以充分相互配合、相互制约,既可以有效防止因过分片面强调国家产业经济组织发展政策而严重影响限制产业市场竞争,又可以有效防止过分强调反垄断而严重牺牲国家应有的产业规模市场经济效益。因此,笼统地全盘批评国家反垄断法或者全盘否定地方政府的这些反整合垄断政策举措既在法律逻辑上难以完全成立,也与实际的市场情况明显完全不符。对于违反整合垄断法的问题在国家经济法律理论上的深入争论不但肯定还有机会得以继续,而且这种新的争论本身仍然是一件好事,有利于经济理论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也同样有利于国家相关法律制度的更加合理完善。
注释:
i Albert Allen Foer. Culture, Economics, and Antitrust : The Example of Trust,The Antitrust Bulletin,2018.
ii Eric A. Posner; "Antitrust Remedies for Labor Market Power," Harvard Law Review 132, no.2 ,2018.
iii Eric A. Posner; "Antitrust Remedies for Labor Market Power," Harvard Law Review 132, no. 2 ,2018,536-601.
iv Lina M. Khan, "The End of Antitrust History Revisited," Harvard Law Review 133, no. 5,2020,1655-1683.
v 林张萌. 跨国并购中的美国国家安全及反垄断审查制度[D].华东政法大学,2018.
参考文献:
[1]刘水林.反垄断法的挑战——对反垄断法的整体主义解释,法学家,2010(01):85-97.
[2]Timothy J. Brennan. Should Antitrust Go Beyond “Antitrust”?,The Antitrust Bulletin 2018, 49-64.
[3]Kenneth G. Elzinga, "Antitrust Predation and the Antitrust Paradox,"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57, 2014.
[4]黄潋.《反壟断法》域外适用标准与冲突解决问题研究.华东政法大学,2019.
[5]伍富坤.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的《反垄断法》调整,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1(03):132-141.
[6]Gilbert B. Becker. The U.S.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After One Half Century : Three Steps Forward and One Step Back,SAGE Publications,2018,63(1).
[7]王先林.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订与竞争法体系的协调与衔接,中国市场监管研究,2017,(12) :2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