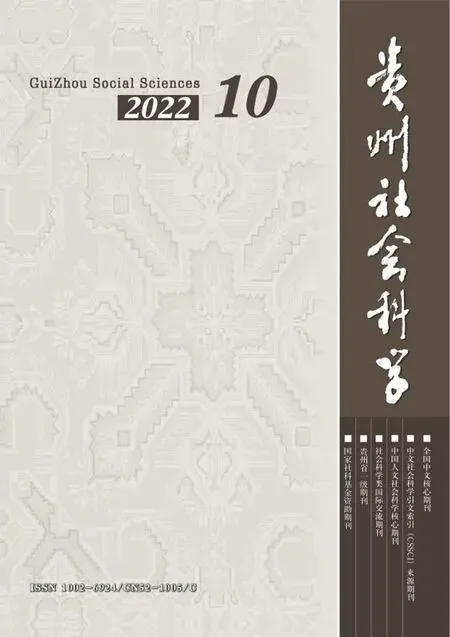《穆天子传》与汉武故事
——兼论古史材料审查与中国古典学重建问题
周书灿
(苏州大学,江苏 苏州 215123)
杨宪益先生是驰名中外的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文化史学者和诗人。自1983年以后,杨氏《译余偶拾》一书陆续由国内多家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20世纪40年代杨氏所写的一系列文史考证文章,特别是中西交通史方面的文章和笔记。《译余偶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山东书画出版社2006年版两种版本均收录有杨氏《〈穆天子传〉的作成时代及其作者》一文。在该文中,杨氏对《穆天子传》成书年代及其作者,提出了近乎独一无二的一家之论,长期以来,杨氏的以上说法,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如有的学者一方面断言,杨氏提出的五点证据“都不能成立”,①却同时又实事求是地指出:“今日信从此说者虽然已甚寡,但由于他们提出的一些疑问始终没有得到妥善的解答,其影响也就远非人数所限”。②显然,对杨氏的以上观点简单地予以彻底的否定,似乎不仅未能很好地将《穆天子传》的成书年代与相关争讼未止的繁难问题彻底解决,反而会继续给当代学术界增加诸多难以破解的新的疑问。
一、《穆天子传》成书于西汉说及主要证据
杨氏一文开篇即断言:“《穆天子传》不会是秦汉以前的作品”,③判定《穆天子传》成书于“汉武帝时到西汉末年之间”,④并推测《穆天子传》“是虞初的作品”⑤。为支持以上论点,杨氏旁征博引,列举了大量重要的证据材料。兹略作分类归纳,述之如下:
(一)《穆天子传》里关于西域的知识,不是秦汉以前的人所能有的
杨氏将《穆天子传》的内容与学术界通常所认为的先秦时期的文献记载进行比较,以证《穆天子传》“晚出”:1.《国语》里只有“穆王将伐犬戎”几句,与《穆天子传》里夸大的记载不同。2.《左传》里只有“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有车辙马迹焉”几句,况《左传》本身是否完全是汉代以前的作品,尚有问题。3.今本《竹书纪年》里的记载大致与《穆天子传》相符,然而今本《竹书纪年》的不可靠,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也许这些都是后来根据《穆天子传》加进去的,况且《竹书纪年》是在晋代与《穆天子传》(疑脱“同”)时代被发现的,根本不能作为考据《穆天子传》时代的证据。4.与《穆天子传》同时被发现的《逸周书》里所纪大夏、莎车、匈奴、楼烦、月氏、东胡等地名,更反而足以证明晋代发现的这一些古书,都不是汉代以前的作品。5.《山海经》中说,西王母是一种怪物,到了《穆天子传》里,西王母就人格化了。⑥
(二) 一般人所认为《穆天子传》是战国时书,存在许多问题
杨氏并不否认晋代汲冢书被发现的事实,认为相当可靠,但提出了以下几点疑问:1.《晋书·武帝纪》和荀勖《穆天子传序》所记汲冢盗掘年月不符,可以看出关于发掘的情形,当时业已不甚清楚。2.荀勖以汲冢为魏襄王坟,并没有证据,《西京杂记》里说过魏襄王冢在汉代已被广川王去疾发掘过,其中并没有大量竹简。3.竹简上所书字是小篆,而小篆是秦李斯等在消灭六国后所创造的。4.荀勖说竹简用素丝编,可见简上丝还未朽,丝麻等物在地下是不能保留五百多年的,至少素丝的颜色也应该变得不容易辨认了。5.汉武帝时始有长二尺四分的官书,就简长来看,《穆天子传》应该是汉武帝以后的官书。⑦
(三)汉武帝见西王母的故事起源于武帝时期,迄西汉末成为一种普遍的民间信仰
杨氏指出,汉武帝见西王母的故事,见于《洞冥记》《拾遗记》《汉武帝内传》《汉武故事》《海内十洲记》等著述。1.从这些故事的内容看,显然是因了武帝通西域,民间闻见远方异物,附会而成。神话里的西王母相当于历史上的大宛,《神异经》所谓“东王公”,大概指的就是汉武帝。2.汉武帝时人确信西面有西王母国,希腊在东方的名称Yunani、Yavana译为西王母,汉武帝寻求西王母国,也就是寻求西方的希腊。3.汉武帝封禅前后的事与《穆天子传》的记载比较一致。汉武帝见西王母的故事是由泰山封禅等事实演化出来的。⑧
(四)《穆天子传》是根据一部分周代史书材料写成的作品,近于小说家言,《汉书·艺文志》载有《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史记》言虞初曾以方祠诅匈奴大宛,汲郡所发现这一批书,很可能就是虞初的《周说》
和以往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以《穆天子传》为战国时期作品的见解不同,杨氏关于《穆天子传》作成时代及作者的看法,颇为独到。⑨值得注意的,在材料并不具备、信息并不完整、证据并不充分的背景下,出土《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的汲冢几乎被学者异口同声地“公认”为战国时期魏墓,《穆天子传》成书于西汉说也因而基本上长期不被学术界所认可。笔者并无丝毫为杨氏观点翻案的动机,而仅仅期望在对汲冢、汲冢书及一系列相关问题的复杂性申论的基础上,对古史材料审查与中国古典学重建问题,略陈管见。
二、西汉说“证据”与观点的分析与思考
随着先秦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杨氏“西汉说”的以上证据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则越来越清晰可见。
诸如第一点,“《穆天子传》里关于西域的知识,不是秦汉以前的人所能有的”的论断,未免过于绝对和武断。杨氏以《国语》、《左传》中只有有关周穆王史迹的若干简略记载,以证《穆天子传》“晚出”,显然疑问很多。先秦时期大量历史传说的流传,除了有诸如《左传》《国语》等传世文献的简略记载外,还有大量珍贵的文献,通过瞽矇口耳相传,以口头文献的方式保存流传下来。《国语·周语上》记载:“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行事而不悖。”⑩从以上记载可知,在信息不畅,在文献缺乏的先秦时期,瞽、矇、耆、艾对古史传说的传诵整理,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不考虑文献流传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大量典籍散佚失传,以及古代文献流传过程中通过瞽、矇口耳相传流传保存下来大量有价值的口头文献等情形,仅仅以《左传》《国语》所记周穆王史迹简略,就断定《穆天子传》“晚出”,显然很难完全令人信服。此外,随着刘歆伪造《左传》说的大体终结,杨氏关于“《左传》本身是否完全是汉代以前的作品,尚有问题”的担心和顾虑,今日也完全可以打消。至于《逸周书》《山海经》的著述时代,目前仍处于争讼中,以《逸周书》所纪族名、地名及《山海经》中西王母形象,与《穆天子传》中相关地名和西王母人格化演变,不加分析地相互进行比较,所作出的结论就必然难以百分百牢靠。
又如第二点,笔者并不赞同前举部分学者断言,杨氏提出的五点证据“都不能成立”。迄今为止,出土《穆天子传》《竹书纪年》的汲冢的年代、汲冢墓主及位置等若干关键性问题,仍存在着诸多无法破解的谜团,尽管学术界对相关问题作过长期探讨,然由于随着时间流失,信息日渐模糊纷乱,诸多关键性问题,或将成为永久之谜。然在今天看来,上举杨氏所列“一般人所认为《穆天子传》是战国时书,存在许多问题”的五条证据,存在的疑问还是颇多的。如《西京杂记》中的确有与传统记载不同的广川王盗发魏襄王冢的记载,但《西京杂记》相传为汉人所作的笔记小说,迄今作者尚无定论,有的学者称其“是一部充满神秘和疑点而又极具诱惑力的古代著作”,“一直处于学者的讽诵借鉴和抨击蔑视的矛盾旋流中”。有学者即曾指出:“《汉书》载其掘墓出尸,但不载发古冢之事。”因此,以充满着种种疑点的《西京杂记》的记载,否定有关汲冢的传统说法,证据同样未必可靠。又如,竹简上所书字是小篆,只是多种文献记载中的一种说法。除小篆外,汲冢竹书的字体,还另有科斗文、古文两种说法。既然如此,从汲冢竹书文字书体,以证《穆天子传》为战国时书,存在很多问题,显得证据乏力。杨氏怀疑丝麻等物在地下不可能保留五百年,似也大可不必。如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M2009虢仲墓即出土过一套比较完整的麻布服饰,是保存较好为数不多的西周时期纺织品。又如1957年湖南省博物馆在长沙左家塘发掘的一座战国中期楚墓中出土的一叠丝织物,重新进行了清理,发现了一批质地保存较好,颜色仍鲜艳的丝织物。还有,湖北江陵马山砖厂一号墓出土的战国丝织品,数量和种类比较多,保存得比较好。杨氏怀疑汉武帝时始有长二尺四分的官书,就简长来看,《穆天子传》应该是汉武帝以后的官书。荀勖所定晋代律尺,1尺合23.10厘米,有的学者则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厘定两晋一尺之长为24.2厘米。据此推算,荀勖《穆天子传序》所言汲冢所出竹简“长二尺四分”,则大体相当于今天55.44—58.08厘米之间。然而今天可以确知的,曾侯乙墓共出土竹简计二百多枚,整简长度多为72—75厘米,宽1厘米左右。包山楚墓所出部分遣策,一般在72.3—72.6厘米之间。卜筮祭祷记录简的长度大致有三种:一种长度在69.1—69.5厘米之间,一种长度在68.1—68.5厘米之间,一种长度在67.1—67.8厘米之间。大部分文书简的长度没有超出62—69.5厘米的范围。以上考古资料则为杨氏的推论提供了有力的反证。
再如第三点,杨氏在材料使用、论证方法等方面同样存在不少问题。诸如,杨氏所举记录汉武帝见西王母故事的《洞冥记》《拾遗记》《汉武帝内传》《汉武故事》《海内十洲记》等著作,和《西京杂记》性质类似,分别为时代和作者并不完全明确的志人小说或地理博物类志怪小说,史料价值大值得怀疑。以上文献所记经过后人改编过的汉武见西王母故事,和今本《穆天子传》所记周穆王至西王母之邦的传说,或各有各的源头、素地和发生、流传背景,不加分析,牵强附会,未免给人以先入为主,削足适履之感。同样,将汉武帝封禅前后史事与《穆天子传》记载,强为比附,将历史事实与各类移花接木后编排拼凑的故事,混为一谈,则只能治丝益棼。乾嘉学派以来,中国学术界普遍赞同的,语言学材料只能作为历史研究的辅助材料来使用。杨氏却以突厥语乃至西语中的语言学材料,作为立论的重要乃至唯一证据,以证神话里的西王母相当于历史上的大宛,《神异经》所谓“东王公”,大概指的就是汉武帝,希腊在东方的名称Yunani、Yavana译为西王母。又如杨氏引用日本学者小川琢治八骏的名称都源于突厥语的观点,推测“穆王八骏的故事更显然与汉武帝的天马有关”,推论多于考证,证据单薄无力。
综上可知,既然杨氏《穆天子传》成书于“汉武帝时到西汉末年之间”说,在材料审查与运用及证据的可靠性、方法的健全性等方面均存在一系列突出的问题,其所作《穆天子传》“是虞初的作品”之大胆推测,自然就没有进一步讨论之必要了。
三、“西汉说”无法得到确认,又无法被彻底否定
综前所论,由于杨氏“西汉说”据以立论的诸条证据,明显存在着一系列问题与疑点,因而,《穆天子传》成书于西汉说,就无法得到确认。然而“西汉说”无法得到确认是一回事,该说是否存在可能性,则显然又是一回事。其中,杨氏据以立说的以下几点论述,颇值得进一步进行深入的思考。
首先,杨氏说:“古代关于穆天子西征的记载很少”。迄今为止,笔者以为,杨氏这一说法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事实上,今天确知的先秦文献中,不仅“关于穆天子西征的记载很少”,即使有关《穆天子传》中两个最重要的主人公,穆天子,特别是西王母的史事和传说的记载,也少得极其可怜。
周穆王的史迹,于较为确信的先秦文献中,只有《国语·周语上》祭公谏穆王征犬戎,及《左传》昭公四年“穆有涂山之会”,《左传》昭公十二年“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等寥寥数条记载。至于《山海经·大荒北经》注、《文选·江赋》注等引《竹书纪年》所记“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积羽行千里”;《艺文类聚》卷九一鸟部、《太平御览》卷九二七羽族部引《纪年》所记,穆王十三年,西征,“至于青鸟之所憩”,或“至于青鸟之所解”;《艺文类聚》卷七山部、《太平御览》卷三八地部等引《纪年》所记“周穆王十七年,西征,至昆仑丘,见西王母”;《北堂书钞》卷一一四《武功部》等引《纪年》所记“周穆王伐大越,起九师,东至九江”;唐写本《修文殿御览》残卷引《纪年》所记“穆王南征,君子为鹤,小人为飞鸮”;《开元占经》卷四引《纪年》说“穆王东征天下二亿二千五百里,西征亿有九万里,南征亿有七百三里,北征二亿七里”等各种真伪难辨的记载,则正如前举杨宪益所言:“《竹书纪年》是在晋代与《穆天子传》(疑脱“同”)时代被发现的,根本不能作为考据《穆天子传》时代的证据”。
《国语·周语上》仅仅提到周穆王拒绝祭公谋父的劝阻,征伐犬戎,获四白狼、白鹿以归,导致荒服不至,至于周穆王“周行天下”,《左传》并未说得更清楚。即使到了西汉时期,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关于周穆王史事,除了照录《国语·周语上》祭公谏穆王征犬戎的记载外,只是增加了“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于王,作修刑辟”的内容。《史记·秦本纪》始有“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的简略记载。再往后,范晔在《后汉书·东夷列传》中进一步丰富了周穆王伐徐传说的若干细节。
《左传》昭公四年所记周穆王涂山之会的传说,出自椒举对楚子所讲的一段话,除了“穆有涂山之会”,椒举还提到“夏启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阳之蒐,康有酆宫之朝”以及“齐桓有召陵之师,晋文有践土之盟”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以上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均信而有征,凿凿可信。然“穆有涂山之会”的记载,则似乎在古代文献记载中,独此一见。王玉哲曾推测,周穆王涂山之会“似乎是破徐以后,威服东南夷的盟会”。笔者则以为,《左传》哀公七年景伯提到“禹合诸侯于涂山”和《左传》昭公四年椒举所言“穆有涂山之会”,两次会盟均在同一地点举行,“是历史的真实记载,还是后人‘识记’的错位,值得很好研究”。由于材料的极度匮乏,显然该传说目前只能处于既无法得到确认也无法被轻易否定的两难状态。
周穆王伐徐的传说,见于记载较晚,且部分文字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充满着诸多难以破解的谜团。其中最容易发现的,即《史记·秦本纪》《后汉书·东夷列传》所记周穆王伐徐故事中,人物年代错乱。尤其如《后汉书·东夷列传》,将周穆王、徐偃王、楚文王不同时代的人物,编排在同一则故事中,只要稍有点历史知识的人们,一眼就能看出其中的破绽。早在唐代,张守节在为《史记》作《正义》时,即曾引谯周《古史考》云:“徐偃王与楚文王同时,去周穆王远矣。且王者行有周卫,岂得救乱而独长驱日行千里乎?”张氏由此判定:“此事非实”,并作按语:“《年表》穆王元年去楚文王元年三百一十八年矣”。清代学者崔述亦曾指出:“且楚文王立于周庄王之八年,上距共和之初已一百五十余年,自穆王至是不下三百年,而安能与之共伐徐乎!”梁玉绳在《正义》基础上进一步论及:“此事详载《后汉书·东夷传》,真伪莫考,诚如谯周所疑。而以为徐偃与楚文同时,则仍《韩子》之误也。三百十八年之数亦未确,厉王已上,《年表》无年,不识守节从何案譣。据《世表》,穆王时之楚子是熊胜。”无独有偶,沈钦韩也发现以上记载的破绽,并辨之曰:“偃王既当穆王时,不得以武王熊通之子文王连文也,传记之谬,洪兴祖《楚词补注》亦言之”。此后,王先谦则曰:“《竹书纪年》云,穆王十三年冬十月,造父御王入于宗周,十四年,王帅楚子伐徐戎,克之。《竹书》出皇甫谧伪撰,不足据信。穆王克徐、楚文灭徐,盖是二事合之,遂不可通”。王氏评论谯周之“献疑,固当,然尚以灭徐混而为一,终莫能明也”。
综合以上材料可知,虽然诸家对《后汉书·东夷列传》穆王伐徐故事中人物年代解释,各有偏差,王先谦所言“《竹书》出皇甫谧伪撰”,并无什么可靠的证据,但诸家都认识到,《史记·秦本纪》《后汉书·东夷列传》所记周穆王伐徐故事中,人物年代错乱,则可谓异口同声,不期而同。这一点,显然也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迄今为止,极少数学者认为,周穆王伐徐这个故事,“不像无中生有,纵然其中夹杂了不少矛盾和错误,但其大枝大节必有史实存在”。但总的来看,周穆王伐徐的故事,则大体上和前举周穆王涂山之会的传说的性质类似,信者信之,疑者疑之。以上两则有关周穆王传说的复杂性,有力地印证了王国维“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论断的科学性。
和周穆王的史事与传说相比较,中国早期文献对西王母的传说的记载,则更为罕见。除去和周穆王史事与传说连在一起,不能作为《穆天子传》时代证据的《竹书纪年》外,惟见于时代尚不明确,至今仍争讼很大的《山海经》和《列子》两书。
西王母于《山海经》中凡三见。《山海经·西山经》云:“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山海经·海内北经》说:“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虚北。”《山海经·大荒西经》:“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在《山海经》不同篇章,西王母的形象,颇有差异。袁珂先生说,《大荒西经》中的西王母“为穴居蛮人酋长之状”,《西次三经》中的西王母“乃益增其狞猛之气,升天而为神矣”,《海内北经》中的西王母“实又俨然具有王者之风,可以与《穆天子传》所写相通矣”。既然如此,杨宪益以“到了《穆天子传》里,西王母就人格化了”作为“《穆天子传》晚出的证据”,显然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列子》卷三《周穆王》提到周穆王“不恤国事,不乐臣妾,肆意远游”的传说,其中,周穆王“遂宾于西王母,觞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之谣,王和之,其辞哀焉”等文字,和《穆天子传》的故事颇相关联。此外,《列子》卷五《汤问》还提到“周穆王北游”及“周穆王西巡狩,越昆仑”等传说。《列子》八篇的真伪,是学术史上极其复杂,迄今仍争讼未止的繁难问题。季羡林先生曾将《列子·汤问》“周穆王西巡狩,越昆仑”的故事和西晋竺法护译的《生经》卷三《佛说国王五人经》二十四里的一个故事,相互比较后发现,“这两个故事,内容几乎完全相同。甚至在极细微的地方都可以看出两者间密切的关系”,并断言“《列子》这部书是彻头彻尾一部伪书”。既然如此,杨宪益所作“《列子》里的周穆王一段显然以《穆天子传》为蓝本”之推论,自然也就无法轻易否定。
综上可知,《穆天子传》的基本素材,应分别采自不同时期的不同文献。如《穆天子传》卷一“天子北征于犬戎”下,郭璞注曰:“《国语》曰:‘穆王将征犬戎, 公谋父谏,不从,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不至’”。在郭璞看来,《穆天子传》卷一“天子北征于犬戎”,指的就是《国语·周语上》所说周穆王拒绝祭公谋父的劝阻,征伐犬戎,获四白狼、白鹿以归,导致荒服不至之事。《国语·周语上》所记穆王伐犬戎之事,或即《穆天子传》创作中的最基本素材。然《穆天子传》前四卷所记周穆王驾八骏西巡天下,行程三万五千里,会见西王母之事,和《国语·周语上》所记周穆王拒绝祭公谋父的劝阻,征伐犬戎,获四白狼、白鹿以归,导致荒服不至之事,则又似毫不相干。显然,《穆天子传》是在《国语·周语上》周穆王征犬戎和《左传》昭公十二年周穆王“周行天下”的历史和传说的基础上加以综合并进行大胆地发挥想象创作出来的。仅仅从《穆天子传》前四卷的所记周穆王西行详细行程及会见西王母的传说可以断言,《穆天子传》的写定年代一定在《左传》《国语》成书之后,且西王母的传说已经在民间逐步广泛流传。然根据前面分析可知,除了写定时代并不明确,甚至真伪难辨,充满着重大争议的《山海经》和《列子》中方有与《穆天子传》相关且素材各不相同的西王母传说,则完全可以肯定地说,战国时期,西王母的传说或已发生,但尚未流行,更未定型。杨宪益所作“西王母的传说似乎始于汉武帝”之观点,虽非学术界的最后定论,但的确有一定的合理性,当为颇为值得重视的具有一定科学性的大胆推测。同时,迄今为止,无论文献记载,还是考古资料,都无法为出土《穆天子传》《竹书纪年》等文献的汲冢的位置、墓主等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按照最严格的逻辑推理,《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和《史记·魏世家》索隐分别说,《纪年》“下至魏哀王二十年”,“终于哀王二十年”,也只能证明《竹书纪年》写定和出土《穆天子传》《竹书纪年》等文献的汲冢的年代上限,绝不可能早于魏哀王二十年,而其年代下限,迄今为止,谁也说不清楚。既然如此,《穆天子传》成书于西汉说,目前很显然仍处于无法得到确认且也无法被彻底否定的两难状态。
四、古史材料审查与中国古典学重建问题
早在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曾论及:“许多好古深思之士,往往为伪书所误,研究的基础先不稳固,往后的推论、结论更不用说了。即如研究历史,当然凭藉事实,考求它的原因、结果。假使根本没有这回事实,考求的工夫岂非枉用!或者事实是有的,而真相则不然,考求的工夫亦属枉用。几千年来,许多学问都在模糊影响之中,不能得到忠实的科学根据,固然旁的另有关系,而为伪书所误,实为最大原因”。
梁氏把“许多学问都在模糊影响之中,不能得到忠实的科学根据”的最大原因归咎于“为伪书所误”。随着现代学术的进展,学术史上曾经普遍使用的“伪书”一词,曾经有过一些概念上的争议。如李学勤曾将新发现的简帛古书与现存古书进行对比,举证古书产生和流传过程中佚失无存,名亡实存,后人增广、修改、重编、合编,篇章单行,异本并存,改换文字等情况后认为:“大多数我国古代典籍是很难用‘真’、‘伪’二字来判断的”。早在20世纪20年代,梁氏即曾把伪书区分为全部伪、一部伪、本无其书而伪、曾有其书因佚而伪、内容不尽伪而书名伪、内容不尽伪而书名人名皆伪、内容及书名皆不伪而人名伪、盗袭割裂旧书而伪、伪后出伪、伪中益伪十种类型。显然,古书产生和流传过程中呈现出的复杂性特点,梁氏亦早已注意到。梁氏主张对于真赝错出的史料,进行“严格之抉择”,“甄别适当”,“先辨伪书,次辨伪事”。李学勤则在新的学术背景下,积极主张“由个别古书真伪的重新考订,逐渐走向对辨伪方法本身的再认识”的所谓“对古书的新的、第二次的反思”。在今天看来,无论是梁氏所说对古书的“甄别”,还是李氏所说的对古书的“反思”,似乎都具有对古书进行严格的审查,为中国古典学建立合格的史料学基础的共同旨趣。
应该认识到,梁氏对古书的“甄别”并非是怀疑一切,相反其在论及伪书的鉴别方法时,则强调说:“无极强之反证足以判定某书为伪者,吾侪只得暂认为真”。同样,李氏对古书的“反思”也并非对传统疑古辨伪的全盘否定,其明确地表示:“用新的眼光重新审查古籍,会使我们对古代学术史研究的凭借更为丰富和广泛。……‘重写学术史’不是要把过去认为是假的都变成真的,也绝对不会后退到‘信古’的阶段上去”。显然,梁、李二氏在如何看待古书的文献和史料价值问题上,大体上可以认为是并行不悖。梁氏以《山海经》《穆天子传》两书为例论及:“其书虽诡异,不宜武断以吐弃之,或反为极可宝贵之史料亦未可知也。”李氏则从另一个角度举证说:“东晋时开始出现的伪古文《尚书》,经过宋、明、清几朝学者的考证,证明它是一部伪书。可是一直到近些年,仍有人在为其翻案。现在的清华简中出现了真正的古文《尚书》,进一步证明伪古文《尚书》是伪书。”显而易见,梁、李二氏对古书的“甄别”与“反思”,暗含了对复杂的古史材料,当信则信,当疑则疑的共同倾向。
20世纪20年代以后,轰轰烈烈的古史辨运动曾经对中国古典学路向产生过极其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自古史辨兴起直至今日,伴随着中国古典学的前进和发展,中外学术界对古史辨质疑和批判浪潮,风起云涌。从徐旭生对极端疑古不良学术倾向的纠偏,“为中国的古史传说时代的研究,创立了一个新体系”,到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论点体系的形成,中国古典学的路向一度被学者称为“去向堪忧”。2017年8月,笔者曾以列子时代考订和《列子》八篇真伪之辨为例,再度论及到中国古典学的重建问题。笔者的基本观点可以简单概括为,从中国学术史上有关列子时代考订和《列子》八篇的真伪之辨,可以清晰地看出,除了明清民国时期,存在极端疑古的不良倾向外,总体而论,从信中有疑到考而后疑与考而后信两种倾向并存,“信”与“疑”始终没有呈现出绝对的分离状态。简单地将“信”和“疑”对立起来,注定很难准确揭示出纷繁复杂的古史、古书的历史实际,自然也很难谈到在真实可信的史料基础上进行古典学重建问题。前不久,笔者又专门就汲冢争讼与流失简真伪之辨问题,继续论及。迄今为止,汲冢书出土的年代、汲冢墓主及位置等若干关键性问题,仍存在着诸多无法破解的谜团。在材料并不具备、信息并不完整、证据并不充分的情况下,总体上先入为主地判定汲冢为战国晚期墓葬,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包括《穆天子传》《竹书纪年》在内的汲冢书的写定年代,则未免显得过于绝对和武断。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来历不明,出土背景不清的各种流失简陆续整理出版。各种流失简的整理出版为中国古典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新材料,同时引发了关于上博简、浙大简、清华简、北大简等流失简真伪的质疑、辨伪及若干答辩和反击。从学术史视角观察,以上论辩基本上是在学术层面展开的,但论辩的性质却颇为复杂。新时期学术界关于上博简、浙大简、清华简、北大简等流失简真伪的激烈论辩,为新时期中国古典学的重建问题提出一极有价值的启示:对古史古书的审查,是重建古典学的基础,不对新旧史料进行科学的“澄滤”,曲解与割裂信古、疑古、释古之间的关系,必会将中国古典学重建引向新的误区。总之,无论是“走出疑古”,抑或是“终结‘疑古’”,都无法构成一个合格的学术命题。
注 释:
①② (晋)郭璞注,王贻梁、陈建敏校释:《〈穆天子传〉汇校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整理前言》,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