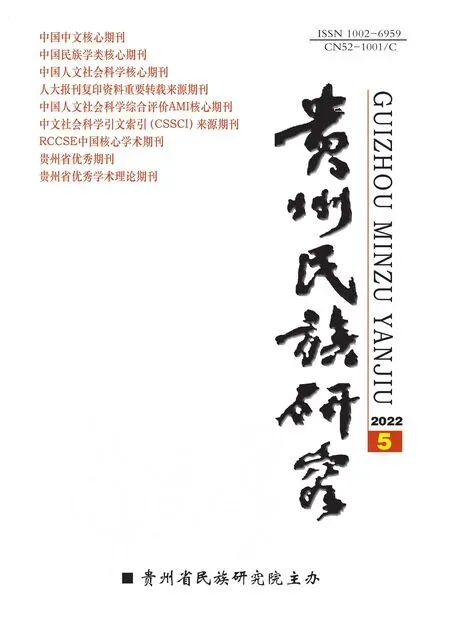抗战时期云南籍高官赞同“中华民族是一个”主张的原因及意义
娄贵品
(云南大学 历史与档案学院,云南·昆明 650091)
1939 年7月7日,“中华民族是一个”讨论背后的主角傅斯年[1],在给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理事杭立武的信中,提到龙云、周钟岳等云南籍高官的中华民族观,称“龙主席对此事(指‘中华民族是一个’讨论) 甚注意,这些文章都去看,大佩服颉刚之论点,对这些高谈这民族、那民族者大不高兴。他说,我们都是中国人,为甚么要这样分我们……此消息系弟闻之于一位此间很重要的人,龙之二等亲信左右,弟之朋友也,千真万确。”“此会(即云南省民族学研究会) 初成立时,请龙公为会长,龙不理焉。吴某去请教周钟岳,周云诸公不可好奇心太盛,去量人的鼻子。”[2](P768,769)那么,傅斯年所言是否属实呢?学术界目前都视其为可信资料,加以引用。然而,傅斯年在同一封信中对吴文藻的指责就多不“千真万确”[1]。所以,其关于龙云、周钟岳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态度的说法,真实性是需要论证的。
目前,无论是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讨论的研究,还是关于龙云、周钟岳的研究,都没有涉及这一问题。面对民族工作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命题,黄兴涛教授指出,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来说,应该格外重视和深化近世以来中华民族自觉史的研究。因为这一研究的拓展和深化,可以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更为切近的历史借鉴和基础性的认知支撑。其中少数民族人士对“中华民族”概念的使用和认同,是现代中华民族自觉史的核心内容[3](P9,11)。因此,本文在论证傅斯年所述属实的基础上,从主位研究的角度,分析龙云、周钟岳等云南籍高官赞同“中华民族是一个”主张的原因及意义。
一、龙云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态度
顾颉刚先生回忆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发表后,“听说云南省主席龙云看了大以为然,因为他是夷族人,心理上总有‘非汉族’的感觉,现在我说汉人本无此族,汉人里不少夷族的成分,解去了这一症结,就觉得舒畅得多了”[4](P176-177)。这很可能是顾先生当年从傅斯年处听说的,所以不能与傅斯年的说法形成互证。比较直接的办法,还是从龙云当时的民族观念与行事入手。
潘先林教授最早注意到,1936年龙云为其妹龙志桢去世编辑的《贞孝褒扬录》,收有赵式铭作《龙贞孝传》。其中说:“龙氏受姓最古,至西汉龙德,以雅琴闻。其子孙散处国中,多著名迹。而滇之龙氏,则至今云南主席龙上将而始大。”此外,署名周钟岳、袁嘉谷、由云龙、龚自知、陆崇仁等发起的《征题贞孝龙女士事略启》 说:“繄夫龙氏,肇自龙师,比于凤纪。轩后之所置,太皞之所启。厥惟远哉,由来旧矣。逮及明末,迁于滇中。乌蒙望族,芒部遗封。皓溔所衍,嶻嶪所钟。载育有德,以昌其宗。男唯女俞,兄友弟恭。”[5](P111)两种家族叙事都无详细谱系,从血统来说,肯定是不可靠的。但如果转化一下视角,从主位研究的角度出发,结合龙云的言行,则不难发现,龙云的家族记忆正是离我们不太久远的“四裔”融入中华的一个客观事实和典型案例。
钱穆先生指出,中国古人并无鲜明的民族观。华夏则称为“中国”,蛮、夷、戎、狄则称为“四裔”。但此等分别,实不从“血统”分,而只从“文化”分别来。文化深演,则目为诸华与诸夏,即所谓之中国人。文化浅演,则称为蛮夷与戎狄,即所谓之四裔[6](P2,3-4)。龙云对此是接受且践行的。
马子华说:“龙云自幼受到了儒家思想教育,非一日一时,青年时代的龙云,耳提面命,朝诵夕读,四书五经对他的思想影响极大。他熟知‘忠君报国’及忠、孝、仁、爱、信、义、德、耻、礼、节……一系列儒家的教条,对他的影响很深远,所以,我常说:‘龙云是一个典型的儒家思想信奉者。’儒家思想,常表现在他的某些言行当中。”龙云平时不穿军服,也不穿西装,多半穿长衫马褂,头戴洋毡帽,显得十分端庄和斯文。这种穿着和爱好,和他从小所受教育和文化熏陶具有直接关系[7](P31,25)。龙云的公子龙绳武后来在台湾接受采访,被问到“龙家有一个光荣的过去,龙主席用什么当治家格言?”龙绳武回答:“我老太爷对人、事的批评总不离四维八德的看法。现在大家都不谈这些德性修养了,这是中国文化复兴不起来的原因。”[8](P116-117)显然,龙云通过学习并践行儒家文化,已“进于中国而中国之”。表现在政策方面,并不区分汉与非汉,“各个民族因风俗习惯的不同而各自形成其特殊的社会,但是在政治上却没有什么分别”[8](P102)。
关于龙云在统治云南时期回避或淡化彝族身份的行为,解放后大家一般从工具论的角度来分析。如云南省民委主任、民族学家王连芳先生回忆说,解放前彝族军阀龙云为了统治需要,往往回避自己的彝族身份[9](P77)。民国时期与龙云接触过的彝族土司岭光电回忆说:“龙云当了云南省主席,却不敢直接暴露族籍,原因是彝族文化较低,作不了他后盾的关系。”[10](P119)
问题是,解放后,龙云既无统治的需要,也无回避的必要,公开认同彝族身份对其更加有利,然而龙云却无意于此。本来,我们具有多重的集体归属认同,选择哪一种认同可以根据目的或视环境而定[11](P20)。因此,龙云的表现,恰好说明他是真的反对民族区分与识别,反感突出民族身份与符号,而不是出于工具性的考虑。解放初期龙云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的表述尤其能说明这一点。在1957 年5月30日中共统战部民主人士座谈会和6月24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云南小组会上,龙云都谈到了少数民族问题。他认为“少数民族,自古以来没有那么复杂,大家都是一个祖先”“同系一族,因地异名”[12]。它们只是名称不同,来源则一,没有区别,住在昆明的人可以叫“昆明族”,住在北京的人可以叫“北京族”。在龙云看来,族别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和客观存在,而是人为的[13]。显然,龙云不仅主张中华民族同源,而且坚持如要在中华民族内部再区分族类的话,要采地域主义原则。其对“族别”的认识,更是具有明显的建构论倾向。考虑到当时的背景,这无疑才是龙云最真实的看法。
二、周钟岳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态度
周钟岳,云南剑川人。1903年中乡试解元,后从日本弘文馆及早稻田大学肄业。归国后任两级师范学堂教员、教务长。辛亥革命时参加昆明重九起义,1912年任云南省教育司司长,1914年任全国经界局秘书长。1917年回滇任靖国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1919年后任省长、民政厅厅长、通志馆馆长等职。1939年5月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部长,1944 年11月任考试院副院长。
“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提出及讨论均与大泰族主义有关。在1939年8月完成的《云南各夷族及其语言研究序》中,周钟岳先生“虑世俗或为所蒙,略举史事以明其妄。”不仅赞成“中华民族是一个”,而且认为中华民族同源。周先生以云南省为例指出:“予以为滇省种族,旧志所称,无虑数十百种。然深籀其语系变迁之迹,则今所称为异种殊俗者,其始或出于一源。盖因滇境崇山大川,道路险阻,初民移殖,适应其环境之异,而演变之文化亦渐歧。予前序吾友赵弢甫白文考证,曾持此论。”“滇中夷民,溯其本源,皆汉族之支与流裔,特因迁徙流传,屏居荒裔,文化久湮,遂睢盱如徼外耳……如近时暹罗改称泰国,并依附掸族,妄谓欲收复故土,建立掸族国家,恐欧洲民族之争,将重演于东亚。”[14]此文在重庆《中央日报》刊载后,周先生又寄《新动向》 《时代精神》发表,可见对此极为重视,希望其得到广泛传播。
所谓“序吾友赵弢甫所著白文考证”,周先生曾为同学赵式铭《剑川白文考》 作《序》。其中说:“剑川方言,往往与雅记故书相合,即其音稍有舛异,然以双声叠韵求之,则可以尽通其阂。近顷吾同门友赵君弢甫,著《剑川白文考》,予得悉心读之,乃知剑川方言,多本故训,苟能察其声音条贯,几无一字无来历者。弢甫淹通典籍,博综群言,其所诠释,皆有依据”“予既服弢甫是书之精审,因以思古来文字之变,约有两途。一则同一语系,而字音递变者。此中复分为二,其因地殊时异,言语分歧者,则更造一字,以通其变……其有常言谚语,沿用古音,因展转溷讹,茫然不识其意,及审其音变,稽诸古书,为之疏通证明,遂敫焉如析符之复合……一则非同一语系,而因乙种人民濡染甲种文化,名物之语,强半相同,如朝鲜、日本、缅甸、越南采用汉文汉语是也。剑川方言,乃介乎二者之间,盖其承用汉语名词与后者无异,而其词多依古训,则又与前者相同也。尝考剑川口语,称为白文,迤西各县方言,大都相近。至其与汉文古语相通之故,疑莫能明。予意商周之时,产里、百濮列于王会,或习汉语以归,教其乡人,或自汉通西南夷,中原士夫,渐入荒裔,边民亦遂习其言辞。此虽于载籍无征,然其理固可推想而得。今剑川居民,考其籍贯,类自腹省移徙而来,土著之人,百无一二,而居常言语,悉操土音,旧俗相仍,习焉不察。弢甫乃于街谈俚语,一字一句,皆证之经史诸书,以参其离合,使人知远徼方言,皆通雅训,未可以侏离夷语同类而共视之。”[15]
在周先生主持编纂、1944年3月全部结束审定工作后又经其详细校阅的《新纂云南通志》 中,方国瑜先生撰写的“族姓考”云:“中国所谓华夷之分,纯以其文化之发达与否为断”,中华民族为整个民族,汉满蒙回藏苗及其他各族“皆华族中分支之氏族”[16]。
由上观之,对汉夷关系及其文化异同,周先生大体认为汉夷同源,汉夷文化差别是汉人移民边地后适应边地环境所致,因文化的差别遂有汉夷之分。所谓“皆华族中分支之氏族”,表面上看似乎源于1943年蒋介石中华民族“有宗族之分支,无种族之区别”的训示[17],但其实还是“滇中夷民,溯其本原,皆汉族之支与流裔”的升级版。
三、龙云与周钟岳坚持中华认同的原因及其意义
就历史时期而言,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共同体。“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则中华之名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其称中华如故。”[18](P182-183)这里的文化是以周礼为核心的文化,所以这一原则亦被称为“礼别华夷”[19](P94-101)。民族创造了文化,但民族亦由文化而融成[6](P1)。“四裔”融入中华正是通过学习和认同儒家文化完成的,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得以凝聚并能够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因为建立在文化基础上的认同最为强烈[11](P21)。
随着各族融入中华,华夷之间也逐渐有了共同的祖源记忆。族群的本质由“共同的祖源记忆”来界定及维系[20](P5)。对族裔认同来说,重要的是虚构的血统与想象的祖先。起决定作用的,是关于共同祖先的神话,而非事实[21](P31)。
正是看到了这一点,费孝通先生非常看重华夷共祖的记忆与认同在中华民族凝聚与发展中的意义。1993年费先生坦陈其学生时代对顾先生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点“完全折服”,半个多世纪后,却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认同的汇合是族类融合发展的需要,虚构三皇五帝系统的,不是哪一个人而是各族的群众[22](P5,7-8)。
就云南而言,“礼别华夷”的族类观念得到广泛传播和普遍接受,与儒学在云南的发展有关。儒学在云南的传播,在明代以前是“学”的传播,不带宗教的色彩,也就是说此时儒学不带宗教的品格,而后随着中原移民的大量涌入,儒学在云南落地生根,此时儒学有了宗教的意味,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文化才在云南成为主流。经元明清的蓬勃发展,《春秋》大一统之义和《礼》教被广泛接受。以清代为例,据不完全统计,滇人著述已过2000余种,有关经学著述共89种。属于教材的有如《易经讲义》 《四书讲义》等;具有导读性的有如《尚书要旨》 《四书扼要》;属通俗读物的有如《四书七律诗》 《四书歌诗》等;属于类编的有如《十三经绘说类编》;属于专著的有如《易经通解》等[23](P326,263-265)。
从《新纂云南通志》“族姓考”,可以判断周先生、方先生都是接受“礼别华夷”的族类观念的。就本文而言,在民族识别后被赋予少数民族身份的龙云(彝族)、周钟岳(白族)、方国瑜(纳西族)、赵式铭(白族) 等等,均大体如此。如方先生在1944年发表的《么些民族考》 中说,“民族名号之立与失,即为其文化关系,以中原江南言之,古代众族之名号,今已不存,因众民族之文化已融合于汉族文化……今西南民族,每有讳称其种族之名,盖以为文化已同于汉人,无须存在其初有之名号,正由一名号代表一文化集团,既无独立之文化,则特有之名号亦无存在之必要,想必有一日西南民族之众名尽归于消灭也。”“今之naci 族受汉文化陶镕已深,则不惟不用么些之名,即naci之名亦可废”[24]。这段话无疑是傅斯年所述龙云“对这些高谈这民族、那民族者大不高兴”的最好注脚。
抗战时期,云南是西南大后方的重要省份,龙云的政治向背攸关抗战全局与前途。因龙云与汪精卫的关系,杨天石先生称“龙云是汪精卫反蒋降日计划的领头羊”[25]“抗战阵营内部的一颗未爆炸弹”[26]。而龙云之所以未“爆炸”,在中华民族存亡续绝的关键时刻坚决反对外来侵略与国家分裂,根本原因在于其具有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坚持正确的民族观和国家观。云南因此完成了对外联通同盟国家,对内屏障国家中枢的历史任务。
当年傅斯年在私人信函中称赞龙云、周钟岳等人曾说:“彼等皆以‘中国人’自居,而不以其部落自居,此自是国家之福。”“他(即龙云)的这个态度,是好事,是一可佩者,是与国家有利者”[2](P768)。后来潘先林教授也指出,龙云在更多的时候认同了汉文化,同时也认同了汉文化的承担者——汉民族,这在近代面临严重的国家民族危机和中华民族的“自觉”历程中是有其积极意义的[5](P112)。儒家文化不仅是汉族文化,更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所以认同和践行儒家文化,正是认同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重要表现。
马大正先生在谈到我国现实中面临分裂势力的挑战时指出,每个地区分裂势力发展的脉络不完全一样,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之所以能够成气候,关键还是当地民众的文化认同与中华文化的认同距离很大[27](P52)。新时代要求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增强“五个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龙云、周钟岳等主动融入中华,自觉学习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自觉树立和坚持正确的民族观和国家观,明辨是非,正视历史大势,选择正确的政治道路等,尤其值得肯定和学习。
四、结语
抗战时期傅斯年所述龙云、周钟岳等云南籍高官反感在云南和中华民族内部进行民族区分是事实。龙云、周钟岳等赞成“中华民族是一个”主张,并不是出于工具性的考虑,而是他们在民族观方面的真实体现。尽管工具论把“民族”解释成社会利益集团中的一个[28](P45),在现实中,完全工具性的例子也比比皆是。作为儒家思想的信奉者和践行者,龙云关于龙氏的家族记忆,实际上反映了龙云认同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客观事实。在当时,不管是主张中华民族同源论者,还是坚持中华民族起源多元论者,都认为中国已形成一个中华民族[29](P1-2)。这些离我们不太远的“四裔”融入中华的具体个案,也是近代中华民族自觉史上的典型案例,能让我们看到“礼别华夷”的族类观在晚清民国时期的持续和影响,加深我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发展史、中华民族自觉史的认识。
2014 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进一步推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而云南省的目标是要建设成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30]。这是因为云南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的建立,在明清时期即已大体完成。清代推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及汛塘制度,越来越多的汉族移民不断进入云南,并进一步渗透到坝区边缘与山区腹地。在推进移民实边的过程中,伴随着实施改土归流、开科取士等一系列政策,汉文化在云南得到更加广泛和深入的传播[31](P106)。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云南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构筑了共有精神家园和共同的历史记忆,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它们牢固树立了正确的中华民族观和国家观,自觉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坚决反对一切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