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闻约取
张之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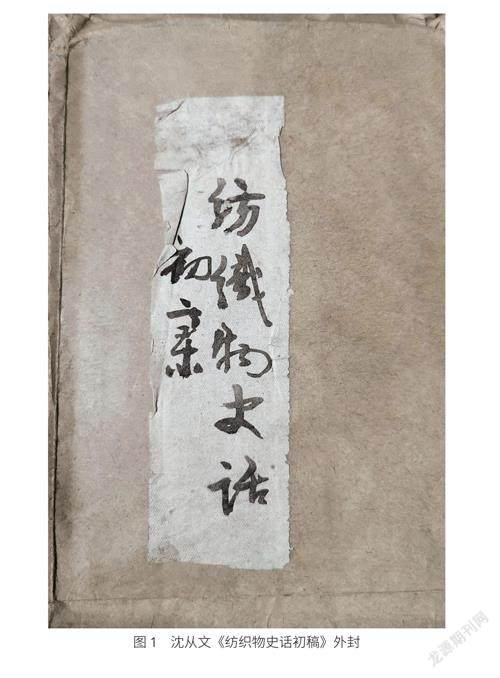

沈红** 在“纪念沈从文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学术论坛”代其母宣读文稿,并发言:“作为家人,感谢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的研讨会,感谢老师们的学术分享。二十年前我也来到过这里,参加国家博物馆为纪念沈先生诞辰100 周年举办的座谈会,很亲切。是你们把我带到老人家生前工作了半生的地方,是你们用学术的方式把他呼唤到这里。我觉得他在这里聆听,和我们隔着时空团聚。我母亲托我带来她写的一篇文章,摘录几段和老师们分享。”
这篇短文是为关心沈先生的人们对他的文物研究多一层了解。我谈三个内容:文学与文物相通;从博物馆说明员做起;艰难岁月的文物缘。
一、文学与文物相通
从文学创作到文物考古,在别人看来隔行如隔山,对沈先生来说却是一脉相通。
对音乐和美术的特殊感受和独特体察,是他文学创作的动力。他说:
认识我自己生命,是从音乐而来。认识其他生命,实由美术而起。看到小银匠锤制银锁银鱼,看到小木匠和小媳妇作手艺。明白一件艺术品的制作,除劳动外还有更多方面的相互依存关系。
一切美术品都含了那个作者生活挣扎形式,以及心智的尺衡,我理解的(艺术知识)也就细而深。
为扩大知识范围……北平图书馆的美术考古图录,故宫三殿所有陈列品,都成为我真正的教科书。读诵的方法也与人不同,还完全是读那本大书的方式,看形态,看发展,并比较看它的常和变,从这三者取得形象,取得知识。
于是他发现:
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
二、从博物馆说明员做起
沈先生来到历史博物馆,从说明员到副研究员工作三十年。当时流行语是“全心全意为教学、科研、生产服务”,他做到了,并且一直是在文物保护第一线探路打前站。
他曾为千千万万人讲解。为了做一名合格“说明员”,他向观众学习,了解观众的需要,针对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观众耐心讲解,不折不扣地在陈列馆转了十年,前后参加了多种专题陈列,和大约三十万观众接触过。
他清点文物,推行文物下乡下厂,为全国各地工艺生产一线服务,在几个工厂办专题展览。指导中央美术学院制作“建国瓷”。
在进入历博之前老先生就与博物馆有缘,北京大学1947 年筹建博物馆系,筹建一所配合教学研究用的历史和民俗性质的小博物馆, 为了支持北大,他把家中的收藏品送过去,摆进了他们的陈列橱。
为高校授课编写教材,是另一项花费大量心力的事。
他曾为北京大学博物馆系讲授《工艺美术史》课程,为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讲授《中国染织美术史》,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讲授《清代瓷器》课程,出版总署编辑《中国历史文物图谱》,沈先生任编委。同时,他帮助故宫培养织绣文物专业队伍。
沈先生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期间,就物质文化史专业工作多次提交提案。1956 年至1982 年曾先后提交二十多件提案,除建立“中国丝绸博物馆”尚未落实外,其他提案均一一得到落实。
他认为提案中执行较好的是高等艺术院校编写的统一教材。1960 年中宣部和文化部成立高等艺术院校统一教材编选组,聘他为顾问。他对每种专业教材的编写,都拟出了提纲和参考书目,亲自分批带编写人员到故宫、历博看文物。等编选写出初稿后,又耐心审校批改。
老先生帮助很多高校教师编写教材,如重庆工艺美院教材《中国漆工艺史》、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中国染织纹样简史》、南京工艺美院《中国工艺美术史》。据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回忆,出版社拿到的是沈先生第四次校阅,历经“文化大革命”保存下来的书稿,此稿沈先生补充了三分之一内容,而出版时老先生并不要署名(图1)。
三、艰难岁月的文物缘
回想老先生一生中两段远离北京的困难岁月,一段在云南,一段在湖北。
1937 年抗战爆发,沈先生和清华、北大师生同车南下,辗转几个月前往昆明。由公路沿湘黔国道入滇时,因汽车常在半道停顿,他有机会观察民俗民情。从煮烤茶的白瓷罐、公用井旁的取水罐到殷朱素漆奁,得到启发,“仅此小小事物,即可见出古典传统与区域性风格的混合”。他推测这个区域会有些不为文献记载的文化,可寻觅,可发现。
“民间丰富深邃异常”,他极力鼓励习美术的青年朋友向滇西深入旅行,作现代徐霞客。过一年后,李霖灿与李晨岚的大雪山游记和“麽些文” 初步研究报告寄回昆明。沈先生深表赞赏,支持他们发表研究成果。这两位学者成为纳西民族文化研究的拓荒者,他对此感到欣慰。
抗战期间,他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书,对西南漆器倾注极大热情。考察器物图纹彩饰,分出四种不同设计。“……引起我对西南漆器更深的爱以及更多关心,几乎把陈列市上能买到的全买到。本意以为如为搜罗到三百种时,必可就手边所有写出个比较报告。”不料战事转紧,昆明成为大轰炸目标。此项工作不能继续,他不得已把多年来收集的大小百十件漆器疏散,分送给亲朋好友。
另一段离开北京的艰难岁月,是1969 年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老先生辛苦汇集起来的藏书和文物资料,毁于一旦。在养猪、种菜期间他念念不忘文物研究。他试用长诗《文字书法发展史》叙述历史。“在极端孤寂简单乡居中,用默记方式,试写文物常识小文。”凭记忆写下20篇《 文物识小录》 ,搭起 20多个专题的研究框架。
沈先生记忆力出奇得好。虎雏在整理涉及书法的十封信时,惊奇发现,老先生在血压高达200mmHg,手头无工具书的情况下,书信中提到书画、碑帖95 种,人物157 位,引用的字词、术语、器物,竟无差错。
他在家书中说:
一切得用工具书虽已散失无余,满脑子丝、漆、铜、玉、竹、木、牙、角,花花朵朵,坛坛罐罐……凡是经手过眼的,常以万千计,多还重叠积累保留在印象中。于是反复回忆温习……一一写出草目。
抗战中寻觅西南文物,干校时默写大书小录。无论在云南在湖北,都有文物研究在手、在心,不离不弃。
按老先生意愿,《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第一本“大书”,计划还要编纂九本书。这个计划后来因他病倒而停止。在我们登记老先生物质文化史研究的未刊遗稿时,发现老先生尚有正在钻研的十余个专题研究的论文90 余篇(图2)。
我们从未听他说自己是大学者,他也反对被不恰当地拔高,警惕过多名望。
他稱自己为“普通一兵”,他称自己为“公民”。这段话是老先生对自己文物研究的最好说明:
作为公民,处境即或再困难,人只要还活着,就有责任待尽。
尽可能把工作继续下去,这是我热爱国家的唯一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