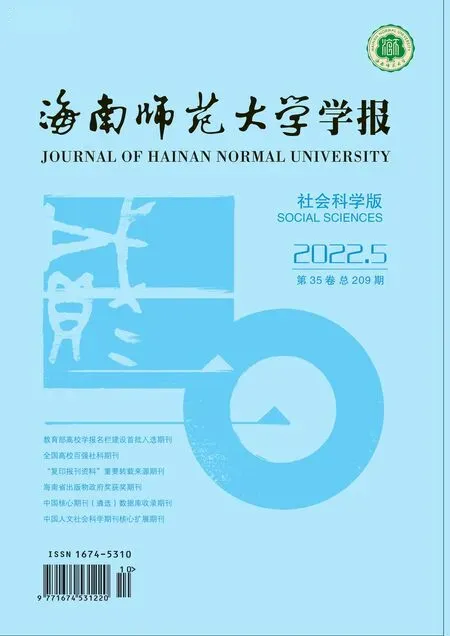苏轼“辞达”说再论
甘生统
(海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海南 海口 571158)
作为产生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背景下的一个重要文论命题,苏轼的“辞达”说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话题,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解读,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意义的观点主张,但因为该命题为苏轼文学思想之基础,意蕴丰富、影响较广,加之目前研究尚存较大探讨空间,因此,很有继续探讨之必要。
一
概括来说,苏轼关于“辞达”的论述是一个逐渐成熟起来的文学创作理论。
该理论的形成是动态的,经历了一个师从孔子旧说到赋予其新意的发展过程。苏轼首次提出“辞达”问题,是在作于绍圣元年(1094)的《答虔倅俞括一首》:“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所谓文者,能达是而已。”①[宋]苏轼撰,张志烈等校注:《苏轼全集校注·文集》卷五十九,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493页。重述这一命题是在作于绍圣三年(1096)的《与王庠书》:“前后所示著述文字,皆有古作者风力,大略能道意所欲言者。孔子曰:‘辞达而已矣。’辞至于达,止矣,不可以有加矣。”②[宋]苏轼撰,张志烈等校注:《苏轼全集校注·文集》卷五十九,第5306页。最后一次论及该话题是在元符三年(1100)的《与谢民师推官书》: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③[宋]苏轼撰,张志烈等校注:《苏轼全集校注·文集》卷五十九,第5292页。
第一次提出时,苏轼只是借孔子之语指出文学创作的必要步骤是要感之于“物之理”,然后将这种感悟诉诸笔端。从句意看,实际上只是对孔子观点的简单借用。第二次提出时,其说已具有一些新义:在内容上,认为辞所“达”者,不仅仅是“物之理”,而是比“物之理”范围更广的“所欲言者”;在表达效果上,认为“辞止于达”就足够了,“不可以有加矣”,这在一定程度上已将“辞达”与艺术境界联系起来。第三次论述最为详尽,是其“辞达”说最为核心的部分。这里他将“物”“意”“言”三者统一起来,认为语言的使命就是“求物之妙”,“辞达”既能将“物之妙”“了然于心”又能“了然于口与手”,表达时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从而具有无以复加的艺术境界。具体而言,这一理论包含如下一些内涵。
首先,“辞达”的主要内容是“物之妙”。上引三则材料在表述上尽管有繁简之别和深浅之异,但都提到了“辞”所要“达”的内容,只不过用语各不相同。第一则说“物固有是理”,“所谓文者,能达是而已。”第二则说“辞达”就是“能道意所欲言者”;第三则说“辞达”就是“求物之妙”。从“理”到“意所言者”,再到“求物之妙”,看起来只是表述上的不同,但从言意关系的角度看,实际上体现了东坡对这一问题在认识上的不断深化。《周易》和《庄子》中提出的言意问题经魏晋玄学家的不断阐发进而影响到文学以后,如何最大程度地解决言不尽意的矛盾,成为文论家始终关注的问题,陆机《文赋》中提出的“意不称物,文不逮意”困境,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提出的“方其搦笔,气倍辞前,及乎篇成,半折心始”的现象,始终是困扰作者和文论家的难题。造成此难题的一大原因就是“言”所要表现的对象“意”或“物”有着复杂性,它既具有相对容易表现的“物之粗”的一面,也有不可言传的“物之精”的一面,前者可用语言文字表现,后者则因“意翻空而益奇,言征实而难巧”而很难捕捉。苏轼在第一则材料中提出的“理”是“物固有”的,相对容易认识,属于“物之粗”者,也容易“辞达”;第二次提出的“意所欲言者”,其范围明显比“理”要宽广丰富;而第三次提到的“物之妙”的内涵又较“所欲言者”更为广博,不仅含有“物之粗”者和“物之精”者,同时还有创作主体因其独特的禀赋所感受到的审美对象的艺术魅力。苏轼诗文有多处言及这一问题。其《书子厚梦得造语》云:
子厚《记》云:“每风自四山而下,震动大木,掩冉众草,纷红骇绿,蓊勃芗气。”柳子厚、刘梦得皆善造语,若此句,殆入妙矣。梦得云:“水禽嬉戏,引吭伸翮,纷惊鸣而決起,拾彩翠于沙砾。”亦妙语也。①[宋]苏轼撰,张志烈等校注:《苏轼全集校注》卷六七,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548页。
又,《评诗人写物》云:
诗人有写物之功。“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他木殆不可以当此。林逋《梅花》诗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绝非桃、李诗。皮日休《白莲》诗云:“无情有恨何人见,月晓风清欲堕时。”绝非红莲诗。此乃写物之功。若石曼卿《红梅》诗云:“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语,盖村学中体也。②[宋]苏轼撰,张志烈等校注:《苏诗全集校注》卷六八,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663页。
他认为柳子厚、刘梦得、林逋、皮日休等人诗作中描绘的艺术形象所具有的传神之美、动态之美、意蕴之美,既不是“物固有”之“理”,也似乎不是“意所欲言者”,而是诗人用其特有的“写物之功”表现出来的“物之妙”者。“辞达”就是将这些“物之妙”完美地呈现出来,而能完美地呈现出来,则“文不可胜用矣”。郭绍虞将“辞达”说,分为“质言之的达”和“文言之的达”:“质言之的达,只能达其表面,达其糟粕而不能达其精微。至古文家则异于此者,必须先能体物之妙,了然于心,攫住其要点,捉到其灵魂,然后随笔抒写,自然姿态横生,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而道也亦自然莫之求而自至的以寓于其间。这才尽文家之能事,这才是文言之达。”③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76页。东坡所“达”的“物之妙”者就是这种“文言之的达”。
其次,“辞达”的标准是“行云流水”“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苏轼对谢民师的作品极为称赞,认为“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其“辞达”说就是在对谢民师诗赋杂文的评价中引发出来的。谢民师,名举廉,元符三年(1100)苏轼遇赦北归时任广州推官,曾以所著诗文求教于苏轼,苏轼途径临江(今广东清远县)时在其复信中作了上述评价。苏轼集中有关谢民师的作品有四篇,除此文外,尚有短信两封和题为《往年宿瓜步,梦中得小绝,录示谢民师》的七绝一首。苏轼高度评价谢民师主要有三个因素,一是与谢民师作品本身的成就有关;二是与遇赦北归时的心情有关,苏轼结束了三年的儋州流放生涯回到广州,心情舒畅,加之素不相识的谢民师慕名前来并很谦虚地向他请教,这种倾盖如故的热情令他感动;三是因为谢民师的创作风格与他的文学主张完全吻合。谢民师的作品目前文献记载不多,其作品风格之全貌很难管窥,因此,在一种略带感激的心情之下借对与自己的旨趣相近的作者诗文的评价阐述已成竹于胸的文学主张,应该是苏轼当时复信时的主要心态。苏轼以为行文的最佳状态是“行云流水”、“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是他的一贯认识,其《自评文》评价己作的著名评语,“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随物赋形”“行于所当行”等,用略带自得的语气所表述的就是他的这种为文主张。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两段旨意相同的文字中描述创作理想时的用语“行云流水”和“随物赋形”等都采用了“水”这一意象。在之前的文论中,以水为喻说明创作问题的现象较为普遍,如陆机用“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形容作家活跃的文思,钟嵘用“芙蓉出水”比喻谢诗的自然清新,韩愈以物浮水上喻“气盛言宜”,皇甫湜、苏洵论韩愈之文如长江大河等。苏轼用水喻也是这一传统的延续,所不同的是苏轼并非着眼于上述特征,而是水的其它质素,具体而言就是其流动自如的自由状态和行于当行止于当止的舒展形态,在苏轼看来,这种状态及其隐含的规律与创作中的文质妙合、辞意畅达的境界合若符契,是“辞达”的最佳形态。
最后,实现“辞达”的途径是既要“了然于心”还要“了然于口与手”。在苏轼看来,在“求物之妙”的过程中实现“行云流水”“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辞达”状态,是极不容易的事,其难度如“系风捕影”,不仅要“了然于心”,还要“了然于口与手”。对此中意涵,学者们的表述不同但意指大体相近,如吕叔湘以为就是“所达”和“能达”,也就是要能对所要表达的事物有深入的认识,还要能够用恰当的言语把这个认识表达出来。①吕叔湘:《说“达”》,《语文战线》1981年第8期。张少康以为:“苏轼所谓‘了然于心’,是指对‘道’的深刻领会;而所谓‘了然于口与手’,是指‘艺’或‘技’的精到纯熟。只有既‘了然于心’,又‘了然于口与手’,才能艺术地再现‘物之妙’。”②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22页。詹杭伦以为这里包含了两个层次:“第一是观察层次,作家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和理解,要做到求物之妙,明物之理,了然于心;第二是表现层次,作家在写作时要做到能道意所欲言,了然于口与手,文理自然,姿态横生。”③詹杭伦:《苏轼文艺审美理论六题》,《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这些解释虽因视角不同,其着眼点有所区别,但不论哪种解释都在强调“辞达”过程中创作主体的“知”与“能”的重要性,所谓“知”就是“了然于心”,就是“所达”和“道”,属于“观察层次”;所谓“能”就是“了然于口与手”,就是“所达”和“艺”,属于“表现层次”。在这一点上,研究者们的看法可谓不约而同。需要注意的是,在苏轼看来,“辞达”过程中的“知”固然重要,但“能”的作用似乎更为突出,做到“了然于心”,对于一个作家是重要的,但还是远远不够的,同时还必须具有高度的表现能力和艺术技巧,将它表现出来,不只是达到形似,而且要达到神似,表现出事物的真髓来,做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正如他对于王维诗的评价那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书王维蓝田烟雨图》)。④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08页。而要做到“能”,在苏轼看来,就要做到胸有成竹和不断实践,其《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云: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⑤[宋]苏轼撰,张志烈等校注:《苏轼全集校注·文集》卷一一,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54页。
其《日喻》云:
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⑥[宋]苏轼撰,张志烈等校注:《苏轼全集校注·文集》卷六四,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120页。
前则材料以画竹为例,强调通过观察和体悟,在把握竹之形的基础上进而捕捉竹之神,由表及里,由粗至精,由知而能。后则材料所阐述的就是实践在“能”中的重要性,要识得“水之道”不是件一蹴而就的事,须不断进行“日与水居”的实践,从“能涉”到“能浮”再到“能没”,就是“没人”在不同的实践阶段取得的不同成效。
除以上外,在苏轼看来,要做到“辞达”还需要个性与人格的自由张扬。其《送水丘秀才序》说:“今之读书取官者,皆屈折拳曲,以合规绳,曾不得自伸其喙。”⑦[宋]苏轼撰,张志烈等校注:《苏轼全集校注·文集》卷一〇,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025页。《策总叙》云:“自汉以来,世之儒者,忘己以徇人。”①[宋]苏轼撰,张志烈等校注:《苏轼全集校注·文集》卷八,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71页。认为在屈服于功利目的而丧失个性的情况下是无法做到“辞达”的。“辞达”需要自由表达自己思想的勇气,“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予,以谓宁逆人也,故卒吐之。”②[宋]苏轼撰,张志烈等校注:《苏轼全集校注·文集》卷一一,《思堂记》,第1146页。同时要有对写作的由衷热爱,“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自谓世间乐事,无逾于此”③[宋]何薳:《春渚纪闻》卷六引苏轼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4页。。不屈己不迎合不吐不快的爽直性情,加上以文章为快意事的特殊爱好,才能在写作中随意驱遣笔墨,在行云流水般的创作成果中享受到创作特有的乐趣。
二
东坡“辞达”说是对传统“辞达”理论的突破。“辞达”说源于孔子。《论语·卫灵公》曰:“辞,达而已矣。”这一论断,因缺乏具体语境,加之文献记载孔子尚有“情欲信,辞欲巧”等肯定文饰的论述,因此历代对这句话的的解释争议颇大。但是绝大多数学者所理解和接受的就是以为孔子反对过度文饰的说法。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语云:“凡事莫过于实足也,辞达则足矣,不烦文艳之辞也。”皇侃《论语义疏》云:“言语之法,使辞足宜达其事而已,不须美奇其言,以过事实也。”④[魏]何晏集解,[梁]皇侃义疏:《论语集解义疏》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宋代《论语》注家对“辞达”的解释与唐以前虽略有不同,但其理论向度基本相同,如司马光以为:“孔子曰:‘辞,达而已矣。’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无事于华藻宏辩也。”⑤[宋]司马光:《答孔文仲司户书》,司马光撰,李文泽,霞绍晖校点:《司马光集》卷六〇,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54页。王安石也说:“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⑥[宋]王安石:《上人书》,《临川先生文集》卷七七,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11页。陈祥道《论语全解》:“君子之辞,达其意而已,夫岂多聘旁枝为哉?”⑦陈祥道:《论语全解》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朱熹亦云:“辞,取达意而止,不以富丽为工。”⑧[明]胡广等:《四书大全·论语集注大全》卷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即便是苏轼本人,在引孔子“辞达而意”句阐述他的为文主张时,实际上也是认定孔子这句话是反对文饰的,《答谢民师书》中所谓“夫言止于达意,则疑若不文,是大不然”的话,隐含的就是这样的理解。因此,从上文分析“辞达”说的独特内涵看,苏轼的“辞达”说极具创新意味,在北宋中期诗文革新运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他在总结自己创作体验的基础上为这一古老命题注入的一股鲜活思想。
需要注意的是,苏轼“辞达”说虽有鲜明的创新色彩,但其学说并非完全是天才的发明,而是在吸收前人基础上的创造和新变。汉代的扬雄在其《太玄》中早就提出了“宏文无范,恣意往也”的行文主张,这当是苏轼“当行”“当止”思想的最早源头,但扬雄的创作与理论有所脱节,因此这一主张并未引起后世重视,他本人还遭到了苏轼的严厉批评,以为其文“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魏晋时,对苏轼“辞达”说有一定启发意义的论述就逐渐增多,如关于“达物之妙”亦即惟妙惟肖地表达出所写对象的状貌问题,陆机、刘勰等人屡有言及,陆机《文赋》说:“虽离方而遁圆,期穷形而尽相。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认为事物经常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要表现其状貌确实很困难。而文章写作,不仅要形其状貌,还要“辞达而理举”,要把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表现出来。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也说:“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以为描写神气,图摹状貌,比附声响,既依随风物之变迁以委曲尽妙,又要配合内心之感应以斟酌至当,做到心物交融。写作中要做到“拟容取心”(《比兴》),不仅要描绘物象,还要表现出物象蕴含的内在精神。刘勰的势论对苏轼“辞达”说应有一定影响。刘勰认为文章写作就是认识和表现事物之势的过程,“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文章体势,如斯而已。”⑨[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定势》,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113-1115页。苏轼强调写作中要“随物赋形”,“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实际上就是强调要尊重事物自身特点,顺应其发展规律,依从其特有之势进行写作,从中不难看出两者间之关联。而刘勰从文章创作原则的高度对文、辞、情三者关系的评价,“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几乎就是苏轼“辞达”说所秉持的基本原则。
苏轼的“辞达”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唐以来古文家“辞达”理论的发扬。韩愈《答刘正夫书》提出文“无难易,惟其是”的主张①[唐]韩愈:《韩昌黎全集》卷十八,北京:中国书店,1991年,第264页。;柳宗元《复杜温夫书》自述为文“意尽便止。”②[唐]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三四,北京:中国书店,1991年,第365页。李德裕《文章论》主张“言妙而适情。”③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63页。裴度《寄李翱书》说:“且文者,圣人假以达其心,达则已,理穷则已,非故高之、下之、详之、略之也。”④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第159页。皇甫湜《答李生第二书》云:“夫文者非他,言之华者也,……文则远,无文即不远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⑤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第175页。欧阳修也提出了“事信言文”的主张。其《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说:“某闻《传》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⑥[宋]欧阳修著:《欧阳修全集》卷十七,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第486页。其《答吴充秀才书》认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⑦[宋]欧阳修著:《欧阳修全集》卷十七,第222页。其《六一诗话》在评价韩文时也提到:“退之笔力,无试不可……余尝与圣俞论此,以谓譬如善驭良马者,通衢广陌,纵横驰逐,惟意所之。”从这些论述中不难发现苏轼“辞达”说的理论所本。
值得一提的是苏洵对苏轼“辞达”说的影响。苏洵《仲兄字文甫说》说:
故曰:“风行水上涣。”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岂有求乎文哉?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风之文也;二物者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⑧[宋]苏洵著,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佑集笺注》卷十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12-413页。
这是苏洵为其兄苏涣改字所作的一段议论,苏洵结合《易经·涣卦》提出将苏涣之字“公群”改为“文甫”并借题发挥提出一系列理由,其中就提出了文采生于“不能不为文”的观点。苏轼《南行前集叙》云:“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⑨[宋]苏轼撰,张志烈等校注:《苏轼全集校注》卷一〇,第1009页。他自言“少闻家君之论文”,所说的当就是上引苏洵的主张,苏洵所言“不能不为”发展到后来就是苏轼的“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这应是苏洵对苏轼文学思想的诸多影响中较为重要的一种。
三
苏轼“辞达”说对后世“辞达”理论有深远影响。这种影响根据其大小可分为间接影响和直接影响。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对“辞达”说提出新解的理论上,直接影响则体现在以弘扬苏轼学说为主的理论上。
苏轼以后,对“辞达”理论有较大发展的是宋濂、杨慎、金圣叹、恽敬等人。宋濂以为,“辞达”首先要做到修身、明道:“大抵为文者,欲其辞达而道明耳。⑩[明]宋濂:《文原》,宋濂著,黄灵庚校点:《宋濂全集》卷八十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2004页。文者果何繇而发乎?发乎心也?心乌在?主乎身也,身之不修而欲修其辞,心之不和而欲和其声,是犹击缶而求合乎宫商,吹折苇而冀同乎有虞氏之《箾》《韶》也,绝不可致矣。”⑪[明]宋濂:《文说赠王生黼》,宋濂著,黄灵庚校点:《宋濂全集》卷八十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1962页。他从这一认识出发对当时文坛上的“佶屈聱牙”和“浅易轻顺”的倾向进行了批评。杨慎从反对冗长之文的观点出发,提出:“孔子曰:‘辞达而已矣’,恐人之溺于修辞而忘躬行也,故云尔。今世浅陋者往往借此以为说,非也”。⑫[明]杨慎:《辞达》,《丹铅续录》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80页。以为孔子的“辞达而已矣”与老子的“美言不信”之间有着同工之妙,告诫人们理解时不要“专美言而忘信”。金圣叹进一步拓宽“辞达”说的范围,将其作为一种结构理论加以阐释:“孔子曰:‘辞达而已矣。’此句为作诗文总诀。然夫达者,非明白晓畅之谓,如衢之诸路悉通者曰达,水道之彼此引注者亦曰达。故古人用笔,一笔必作十笔用。”①林乾主编:《金圣叹评点才子全集》(第一卷),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年,第872页。恽敬则将其与作者心性联系起来,赋予“辞达”说以新的内涵,其《与纫之论文书》云:“孔子曰:‘辞达而已矣。’……圣人所谓达者何哉?其心严而慎者,其辞端;其神暇而愉者,其辞和;其气灏然而行者,其辞大;其知通于微者,其辞无不至。言理之辞,如火之明,上下无不灼然,而迹不可求也;言情之辞,如水之曲行旁至,灌渠入穴,远来而不知所往也;言事之辞,如土之坟壤咸泻,而无不可用也。”②[清]恽敬著,万陆、林振岳标校,林振岳集评:《恽敬集》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29页。
这些观点与苏轼“辞达”说有很大差异,但细绎其辞,不难看出其间的相似之处,即这些观点中显示出的不因袭旧说的创新意识和敢于批评不良文风的批评锋芒,从苏轼在宋元以后的接受和传播看,这些观点的提出不能说没有受到苏轼学说的启发和影响。
受苏轼“辞达”说直接影响的学者似乎更多。苏轼对这一群体的影响较为复杂,有些是直接祖述其观点,如南宋汪藻《鲍吏部集序》:“古之作者无意于文也,理至而文则随之,如印印泥,如风行水上。灿然而成者,夫岂待绳削而后合哉!”③[宋]汪藻:《鲍吏部集序》,见《浮溪集》卷十七,《四库全书》本。赵秉文《〈竹溪先生文集〉引》云:“文以意为主,辞以达意而已。古之人不尚虚饰,因事遣词,形吾心之所欲言者耳。间有心之所不能言者,而能形之于文,斯亦文之至乎?譬之水不动则平,及其石激渊洄,纷然而龙翔,宛然而凤蹙,千变万化,不可殚穷,此天下之至文也。”④[金]赵秉文著,孙德华点校:《闲闲老人滏水集》卷十五,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319页。推崇行云流水般自然而然的写作,反对“务奇”“夸多斗靡。”他们不惟观点相同,连表述都相似或相近;有些则是对其观点进行辩护,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以阐发,如王若虚“辞达理顺”说就是对东坡观点的直接继承,其《文辨》云:“东坡自言其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滔滔汩汩,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自知。所知者,常行于所当行,而止于不可不止。论者或讥其太夸,予谓唯坡可以当之。夫以一日千里之势,随物赋形之能,而理尽辄止,未尝以驰骋自喜,此其横放超迈而不失为精纯也邪?”⑤[金]王若虚著,马振君点校:《王若虚集》卷三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443页。方孝孺对宋濂的学说多有继承,但其理论和创作沾溉苏轼者似更多,其《与舒君书》云:“文者,辞达而已矣。然辞岂易达哉!……夫所谓达者,如决江河而注之海,不劳余力,顺流直趋,终焉万里。势之所触,裂山转石,襄陵荡壑,鼓之如雷霆,蒸之如烟云,登之如太空,攒之如绮縠。回旋曲折,抑扬喷伏,而不见艰难辛苦之态,必至于极而后止。”⑥[明]方孝孺著,徐光大校点:《逊志斋集》卷十一,宁波:宁波出版社,1996年,第378页。从观点到表述无不留有东坡的印记。朱彝尊《逊志斋文钞序》评价方孝孺:“宣德以还,文字之禁渐驰,公文始显行于世。其闳深博大,骎骎乎驰逐昌黎、眉山之间。”⑦[清]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18册,第65页。俞化鹏亦云其文“如万斛源泉,随地奔涌,博综经济,穿贯天人,其中无所不有,而大旨一归于明道。”⑧[清]俞化鹏:《重辑方正学先生文集序》,张常明编注:《逊志斋外集》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5页。这些评述正是看到了苏轼对他的深刻影响。
受苏轼影响较深的理论中值得注意的是晚明以后的几家学说。一是晚明时期心性派文论家。他们对苏轼极为推崇,李卓吾、焦竑、公安三袁,甚至稍后的钟惺、谭元春皆对其有赞述,其中尤以焦竑和袁宗道最值得称道。袁宗道曾以“白苏斋”为其书斋名和文集名,可见其对东坡敬仰之深,焦竑集中有《刻苏长公集序》《刻苏长公外集序》《刻两苏经解序》等文章,对东坡为人、为文及治学极尽揄扬,李贽《书苏文忠公外纪后》将焦竑比作当代苏轼,以为“焦弱候,今之长公也”。对苏轼“辞达”说,两人基本上完全接受,焦竑《刻苏长公外集序》:“世有心知之而不能传之以言,口言之而不能应之以手。心能知之,口能传之,而手又能应之,夫是之谓辞达。”⑨[明]焦竑撰,李剑雄点校:《澹园集》,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751页。袁宗道《论文(上)》曰:“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辗转隔碍,虽写得畅显,已恐不如口舌矣,况能如心之所存乎?故孔子论文曰:‘辞达而已。’达不达,文不文之辨也。”⑩[明]袁宗道著,钱伯成标点:《白苏斋类集》卷二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83页。在“辞达”问题上他们大多在祖述苏轼旧说,但他们的那些石破天惊的学说如“童心说”“性灵说”等,从理论根源上说,应该与苏轼“辞达”说关系至密。二是明清之际的叶夑。叶夑在文学思想方面最主要贡献,在于在承续南宋思想家叶适关于“情”与“理”规定“物”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理、事、情”说,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由理、事、情三个相互联系的因素构成,所谓“辞达”就是三者的相互贯通,其《原诗》说:
自开辟以来,天地之大,古今之变,万汇之赜,日星河岳,赋物象形,兵刑礼乐,饮食男女,于以发为文章,形为诗赋,其道万千。余得以三语蔽之,曰理,曰事,曰情,不出乎此而已。①[清]叶夑著,蒋寅笺注:《原诗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18页。惟理、事、情三语,无处不然。三者得则胸中通达无阻,出而敷为辞,则夫子所云“辞达”。达者,通也,通乎理、通乎事、通乎情之谓。②[清]叶夑著,蒋寅笺注:《原诗笺注》,第125页。
他的“理、事、情”说,实际上就是对苏轼“辞达”说中“物之妙”问题的深化和细化,尽管意蕴丰富的“物之妙”具体化为这三个要素,还是有不尽全面之嫌,但不能不说这三个要素应是文辞所表达的内容中最为核心的部分。三是被称为“嘉、道间一作手”的潘德舆。潘德舆继承了儒家以教化为核心的诗文创作理论,对在他看来与儒家传统观点不符的学说加以批评,对苏轼“辞达”说就是如此,其《养一斋诗话》云:
“辞达而已矣”,千古文章之大法也。东坡尝拈此示人,然以东坡诗文观之,其所谓达,第取气之滔滔流行,能畅其意而已。孔子之所谓“达”,不止如是也。盖“达”者,理义心术,人事物状,深微难见,而能阐之,斯谓之达。达则天地万物之性情可见矣,此岂易易事,而徒以滔滔流行之气当之乎?以其细者论之,“杨柳依依”,能达杨柳之性情者也;“蒹葭苍苍”能达蒹葭之性情者也。任举一境一物,皆能曲肖神理,托出豪素,百世之下,如在目前,此达物之妙也。《三百篇》以后之诗到此境者,陶乎?杜乎?坡未尽逮也。③[清]潘德舆撰,朱德慈辑校:《养一斋诗话》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8页。
潘德舆通过对孔子“辞达”和苏轼“辞达”说之比较分析,认为孔子所谓“达”中“天地万物之性情可见矣”,而苏轼所谓“达”“第取气之滔滔流行,能畅其意而已”,这种分析明显是一种张冠李戴,因为他高度揄扬的孔子“辞达”说的特点恰是苏轼“辞达”说的精髓。潘德舆强调创作主体的性情、学问、修养对创作的影响,很多学说明显是吸收苏轼而有所发展,他在尊圣背景下对苏轼“辞达”说的批评,一方面说明了苏轼学说在传播中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既表现在反对者对其合理性的肯定中,也表现在追随者对其学说的误解中,潘德舆带有同室操戈性质的批评就属于后者;另一方面也说明苏轼的学说具有巨大创新意义,他在“辞达”问题上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在潘氏看来,似乎只有孔子与之相配,他这种有意识的“误读”反映出的恰是苏轼“辞达”说的高明所在。
综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苏轼“辞达”说是一个意蕴极为丰富的文学创作理论,这一学说是对传统“辞达”理论的突破,对后世相关理论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