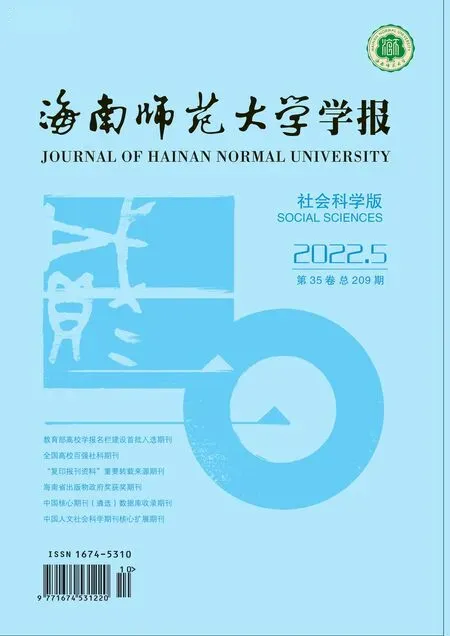新变与重构:现代中国“文学话”界说与辨析
杨瑞峰
(1.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2.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晚清民国以来,在西学东渐与自我变革的合力推动之下,源自西方,统合诗、词、文(文章、散文)、曲、小说等不同文类的西式“文学”(Literature)概念被引进国门。“一时间,‘文学’成了汉语社会频繁使用的概念和术语,与之相关的各种实践也四方呼应,遍及朝野。”①徐新建:《“文学”词变:现代中国的新文学创建》,《文艺理论研究》2019年第3期。“文学”新变引发了一场极具历史绵延性的思想震荡,反映在文学批评领域,不再延续古代中国分体批评的思维模式,对“文学”进行整体性探讨的热情空前高涨。在此情境中,“文学话”这一借助传统话体文学批评体例阐发全新“文学”观念的批评文体得以创构。作为一个“有实无名”的现代批评文体范畴,“文学话”文体的构拟,虽受西方新潮观念影响,但同时也是传统话体文学批评适应新的文化语境、不断进行自我调试的必然产物。因此,对“文学话”概念的界说与阐述,必须在“古今中西”思维的宏观框架中展开,在深入洞察传统话体文学批评现代转型与文类裂变历史迹脉的同时,兼顾“西方影响”并着重辨析其与西式述学文体之间的异质性。
一、“文学话”的概念界说
传统话体文学批评的命名与分类,总体上以“名实对位,兼顾文体”为基本原则。申言之,凡是以“话”“谈”“漫谈”等具有鲜明的“谈话体”①参见梁启超:《小说丛话》(原载《新小说》1903年第7期),《梁启超全集》第17集,汤志钧、汤仁泽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05页。意味的语词标目的文章,若其批评内容多为记录文人逸事、文坛琐事,文体形态上分则论述且各则均体例短小,论述内容彼此独立,即为话体文学批评。晚清民初以来的很多文学批评文章、著作在命名、文体方面依然延续着这一批评规范,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传统话体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与文类裂变,这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旧有的诗话、词话、文话、曲话、赋话等仍在不断发展;其次,利用话体文学批评的体式进行小说、戏曲、话剧、电影、音乐批评的文章著作开始涌现,并渐成规模;最后,不分文体,综论“文学”的“文学话”文体得以构型,且作为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向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述学规范转化的过渡性文体形态发挥了重要的功用。
所谓“文学话”,是借用传统诗话、词话、文话、曲话、赋话等话体文学批评的文体形式,综论现代新生的“文学”(Literature)观念的文学批评文体。题名方面,“文学话”除了延续传统话体文学批评大多直接缀以“话”字的惯例之外,又往往以“谈”“谈丛”“闲谈”“谈座”“谈屑”“琐谈”“枝谈”“笔谈”“漫笔”“随笔”“漫话”“杂话”“卮言”“闲评”“管见”“讲话”“讲座”等标目,文体命名更为多样,但整体上不脱离话体批评漫谈散议的基本意趣;文体形态方面,“文学话”主要表现为分则论述,且各则之间无严丝合缝之逻辑关联的随笔型、漫谈式、笔记体,在此前提下,凡论理、品人、录事、志传、集句、考索等文体构型策略均或用之;宏观特征层面,“文学话”既有别于传统文学批评中常见的诸如评点、序跋、论说等其他文体,也有别于现代以来借镜西方述学规范而成的重逻辑、成体系、有系统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论著;微观层面而言,“文学话”与诗话、词话、曲话、赋话等专论某一文体不同,带有鲜明的综论特征。
“文学话”文章著述、命名方式与文体形态均与传统话体批评近乎一致。如范烟桥曾先后于1926年、1928年在《民众文学》杂志发表《文艺谈屑》(全文3390余字,共25则,分两次发表)。这里的“谈屑”显然仿古代话体批评“谈尘”一类命名方式而来(宋代谢伋撰有《四六谈尘》,是“四六话”代表之作),而其分则论述,不求逻辑谨严与结构完备的撰述方式,显然也是话体批评理论言说方式的现代投影。现例举几则以资直观比较:
野鹤零墨云。过墟书一书。述刘三秀事。文笔綦详密。绘声绘影。实与近日说部相近。青浦钱君便便衍其事。成鹣鲽因缘一书。亦简静可玩。按刘三秀相传为摄政王多尔衮组室。无可考。
封神演义虽荒诞。亦不有所本。琐记云“考周书克殷篇。武王途征四方。凡愗国九十有九。馘魔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魔与人分别言之。虽不知所谓魔者何谓。然足证小说之依托。广成子见庄子。赤精子见汉书李寻传。托塔天王见元史与服志,哪吒见夷坚志。灌口二郎即杨戬。其说皆不为无据。”
小说绘画图。元时已有之。观于元曲选可知。永乐大典忠传亦有图。清季如任渭长吴友如周慕桥。画像极工美。亦有揣摩既久。因以成绝技者。昔柳摭谈云。石门劳笙和。九岁阅西游记。翻得牛魔王与玉面公主宴饮图像。戏仿之。膨朜腹胀。狐媚鸨淫之况。弈弈有神。比长以传神名。吾乡陆廉夫先生为挽近国粹画领袖。闻其少时。亦喜涂抹。即以小说绘像为蓝本云。②范烟桥:《文艺谈屑》,《民众文学》1928年第17卷第13期。
除此之外,陈光尧的《文艺集话》、槐青的《文学谈屑》、蓬生的《文学漫话一打》等,也都采用了与传统话体文学批评近乎一致的言说方式,现分别例举部分片段如下:
近年来中国又很盛行新式的“八股时文”了,一般站在政治方面的人们,大致个个都会做,而且做得很精。
文豪是由种种出版物造成的,要是世间没有出版物,则一般著作者虽有“文”亦必不能“豪”。
一般大学问家死了之后,最可惜的事,是听不到后世人对于他的批评,虽然这批评里包含的有同情有攻击。
苦闷,胃病,失眠,失恋,……等等,为文人们最易犯之通病。……①陈光尧:《文艺集话》,《良友》1931年第63期。
《水浒》中有“无巧不成话”一语,我觉得很有趣,这里就是小说和戏剧情节(Plot)之所在。自然,这“巧”不能太过离奇,至少要合乎伦理和人情,“祸不单行”是悲剧内容的问题,“无巧不成话”却是文学技巧上的问题。
多动作的小说,剧本和诗歌必多动词,诗词歌赋和美丽的文章必多形容词,中国的形容词为数最多,且有特殊的美点,譬如簌簌,葱葱,昵昵,惺惺,岧峣,霭霭,之类,实有外国文中形容词所不及的美处。
元曲:“若是寝正浓,梦乍醒;且休问斜月残灯,直睡到东窗日影”。是难能佳句。这是用空间观念代替时间观念的写法。爱尔兰诗人夏芝(yeats)的诗《The Lake Isle of Innisfree》也有同样的写法:“And I shall have peace there,for peace comes dropping slow,Dropping from the veils of the morning,to where the cricket sings.”……②槐青:《文学谈屑》,《平潮》1933年2月刊。
(一)文学是社会的产物,也是个人的产物;同时,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也是个人意识形态的反映,所以没有个人与个人的——读者和作者——关系,文学是不会产生的;没有社会的关系,文学也是不会存在的。
(二)中国文学里面,以殉情主义为最多;像古代词臣的《黍离》《麦秀》之歌,三闾大夫的香草美人之作,无非是追怀往事,哀感今朝。
(三)每一种文艺思潮的存在,都是在它自己的内部形成一种相反的东西,而终于否定了它自己而存在的;而它自身的生长呢,也是从一时代的文艺思潮的内部中形成的。
……③蓬生:《文学漫话一打》,《亚光》1936年第2卷第3期。
以上所论,皆就发行于报刊杂志的单篇(或系列)“文学话”言之。就刊行方式的角度而言,现代中国的大量文学批评、文学理论著作实际也属于“文学话”。如巴人的《扪虱谈》(1939)、黄道明的《文学丛话》(1942)、胡风的《文艺笔谈》(1943)、朱光潜的《谈文学》(1946)、何典的《文艺漫谈》(1947)、洪为法的《谈文人》(1947)、李广田的《文学枝叶》(1948)等,虽以“著作”体例传世,但行文林林总总、结构涣散、意至笔随,带有鲜明的话体批评遗风,实际与当时通行的文学理论类著作迥然不同。
通过上述引用与论述,“文学话”的文体特质,基本可见一斑,其与诗话、词话等话体文学批评之间的文体源流关系也基本确立。除此之外,要对“文学话”概念有一个明晰的界说,还需要对其与传统话体文学批评之间的差异性,其“综论”特征的具体面相和其自身在现代这一特定时段所经历的批评言说方式的历史演变进行追问。
使用“文学话”这一命名,实际隐含了对现代中国文学批评发展进程中“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命题的默认和进一步探索。鉴于此,除了对概念本身的内涵进行界说之外,还必然包含另一种更为精微的思考,即“文学话”与诗话、词话、文话等既有话体批评范畴有何区别,反过来,这种思考的结果又会催生或曰强化理解“文学话”内涵的基本原则。“文学话”与既有话体文学批评星丛概念之间的区别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除了与诗话、词话、文话等范畴约定俗成、人尽皆知的潜在优势相比,“文学话”显得陌生因而容易给人指向不明之感之外,更重要的是,随着“文学话”篇幅的不断扩大与现代报刊连载机制的普及,很多长篇“文学话”往往分专则论述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等单一文类,若不以整体之眼观之,极易与传统话体批评相混淆。如钱杏邨的《文艺随笔》,全文共三则,除第一则“周作人与阶级文艺”不分文体的综论文学,第二则“读单贤林的《新的露西》”与第三则“小说的起结和翻译的取材”均主要探讨小说问题。①钱杏邨:《文艺随笔》,《海蜃半月刊》1929年第1卷第1期。李广田的《文艺书简》由十来则短文组成,其中,“谈写诗”一则专论诗歌写作②李广田:《文艺书简·谈写诗》,《中学生》1947年第188期。,“谈小说”一节专论小说写作③李广田:《文艺书简·谈小说》,《中学生》1947年第196期。,另有“谈散文”一则专论散文写作问题④李广田:《文艺书简·谈散文》,《中学生》1947年第197期。。在这种情况下,若将钱杏邨《文艺随笔》之二三则视为“小说话”,将《文艺书简》中专论诗歌、小说、散文的各则归入“诗话”“小说话”“文话”似乎也无不妥。
为避免“乱体”,需要运用语境化的思维去理解何为“文学话”。“文学话”的兴起以现代“文学”概念的诞生为基本语境,在此之前,若以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思维观照中国古代批评实践,文学批评的整体框架只能由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等不同文类批评的残篇断简拼贴出大致轮廓。换言之,在中国古代,整体性的文学批评观念零散分布于各体文学批评实践之中,因此,中国多诗话、词话、文话、赋话、曲话、小说评点等“专门之学”,而少成体系的、精心结撰的文学批评专著。晚清民国以来,随着西方新式文学观念的输入,这种情况逐渐发生了根本变化。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等被统一整合在了“文学”序列之中,“探讨文学整体问题的热情远远超过了研究各种文体的兴趣”⑤刘纳认为,中国“文学”整体观念确立于五四时期,其基本标志是陈独秀对“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的区分,刘半农对“文学”与“文字”的区分等,正是这些倚仗西方理论,以整体性“文学”问题的探讨取代以往对各种个别文体的研究兴趣的举措,逐步确立了完整的“文学”观念。参见刘纳:《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13-314页。。在这个意义上,“文学话”(尤其是规模较大者)中包含谈诗论文之专门部分就容易理解了。
需要指出的是,“文学话”中有论诗、论小说、论散文之专门内容,并不意味着它与诗话、文话、小说话等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实际上,“文学话”与诗话等应为同类平行概念,“文学话”之所以为话体文学批评之一种,主要源于它与诗话、词话思绪跳荡,不重逻辑的文体规范高度一致。同时,又明显区别于同时兴起的重视逻辑推理的文学批评类著作,而需要于既有概念之外,增设“文学话”这一陌生概念,则源于其与诗话之专论诗歌、词话之专论词、文话之专论“文章”不同,在批评对象上要么直接宏观论述文学问题,要么单则论述不同文体,但整篇文章则往往论及两种文体以上,具有综合性。即使钱杏邨的《文艺随笔》二、三则专论小说,但尚有第一则宏观论述“文艺”问题,若将整篇文章视为一个整体,自然属于综论“文学”之作,只是其中论述小说的内容占据主导地位。同理,李广田的《文艺书简》纵然有专则谈论诗歌、小说、散文,但文章整体上以“文艺”(实即文学)统摄,且尚有其他部分综论“文学”,因此,也不能简单将其视为诗话、文话或小说话。因此,唯有以“题文统一”为基本前提,采用整体性考察的视野,才能明确何为“文学话”。
二、由“文话”到“文学话”:背离与归趋
在既有的话体文学批评文类谱系中,“文话”与“文学话”的关系最为密切,一方面,“文话”批评对象(文章)的现代转型(文学),是“文学话”得以确立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受晚清民国以来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在向现代“文学”观念转型进程中所造成的新旧杂糅的历史情境影响,致使后人对“文话”在实践与理论认知两个层面均产生了偏差,由是造成了“文学话”的被遮蔽。因此,对“文学话”的理解,绕不开对其与“文话”关系的历史性盘查和共时性辨析。
与诗话、词话等发端既早,体量亦大的话体文学批评相比,“文话”在其发端期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个重要的体现是,清代学人在着手整理文话资料时,均以“古有诗话而无文话”⑥阮元:《研经室续集》(卷三),《四部丛刊》本。一类话语为其学术实践的必要性张目。究其根源,文话的湮没无闻与“文”字内涵的多义性密切相关,而“文”字内涵的含混又必然地导致了古代“文”学内涵的多元指向:秦汉之际,“文”与“学”各有丰富且各自独立的内涵,故此时期“文学”意涵要么偏重“文”的一面,要么偏重“学”的一面,缺乏稳定性。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文的自觉”意识的高涨,“文学”内涵呈现重“文”抑“学”的基本情势。隋唐之后,尽管“文学”词义继续增殖,内涵指向更为驳杂,但整体上已偏重于“文章”之义,从而为清末民初新式“文学”范畴进入国门之前中国学人的“文学”界说确立了主要参照系。①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具体的字义演变及其对中国古代“文学”内涵演变的影响,笔者在《报刊体“文学话”与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普及》(载于《云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一文中已有详细论述,此处为避免重复,不再具体展开,只做结论性简述。
故此,产生于隋唐之后的“文话”也就自然是一种文章学意义上的话体文学批评。而清末民初之后产生并为今人随意支取的“文学/literature”概念,“在中西文化的历史进程中也并非古已有之”,而是“历史古今演绎的结果”,在思想史、文化史的意义上来看,它“包含了中西对接的历史面相”②余来明:《“文学”概念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1页。;在具体内涵方面讲,一方面褪却了传统文章学意义上以道统为核心、以伦理为主导的“道之文”色彩,另一方面又因将戏曲、小说等“君子弗为”的“小道”纳入其文体范围,并因重视个人情感的生发与表达从而走向了“心之文”的轨道。所以,现代新兴的“文学话”是顺应“文学”新变而新生的一种话体文学批评体式,尽管对传统“文话”的体式特征有所延续,却并非同一事物的不同称谓。
由于现代中国文学是在“古今中西”多重视野彼此杂糅的历史语境中逐步建构起来的,因此,对相关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的理解,必须将着眼点置于一个由一系列的承传、断裂、重构拼贴出来的宏观框架之中,换言之,在一个重大转型期诞生的新型范畴面前,以探求绝对差异为逻辑预设的比较方式是失效的,忽视了这一点,相关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就只能是人为地、事后追溯的结果,而非一种关于历史事实的客观叙述。因此,对“文学话”与“文话”异质性的探索,现今已为常识的“文”与“文学”的区别虽是理论根基和基本落脚点,但更重要的是回到历史现场,盘查二者之间差异性的显现或曰“断裂”的发生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历史过程。
事实上,在现代中国“文学”观念建构过程中,受“文”与“文学”之间“不彻底的断代性”影响,也有部分文话作品挣脱了传统文话作为“文章批评”的历史界域,批评眼界拓展到了其他文类。比如,章庭华的《论文琐言》,就其主体内容而言,毫无疑问当属“文话”,但突破文话批评边界的倾向也已经显露无遗。例如,“史体与小说之距离,不能以寸语语,严重则为史,一涉纤佻则近小说矣。”“屈子开辞赋一派,扬马更推衍之。”“叙琐碎事须有光气以盖之,无光气则易涉小说。”③章庭华:《论文琐言》,《双星》1915年第4期。“《阿房宫赋》体格调法异于《上林》。”“《两都》《西京》如古法古乐杂陈一室,读之令人肃然起敬。”“行文有添字法,有沉字诀,史家所以能驾乎小说家之上者,知添字法也。”④章庭华:《论文琐言》,《文星杂志》1915年第1期。“诗文贵能体物……”“小说与正史之别,几不能言……”⑤章庭华:《论文琐言》,《文星杂志》1915年第2期。等句,兼论“史传”“辞赋”“诗歌”“小说”等文体,从而呈现出通于赋话、诗话、小说话的文体姿态。而且,此文有大量篇幅是对《论语》《孟子》《庄子》《汉书·艺文志》《论衡》进行评述的“书评”之言,实际已开“书话”先河。
众所周知,在话体文学批评发展史中,各文类之间互相寄生的状态古已有之。因此,确定某一话体著述到底属于诗话还是词话,主要看其主体批评内容。易言之,诗话中有论词、谈赋、说文之语属惯见情况,但其所占比例一般较少。但《论文琐言》中“书话”“赋话”“小说话”所占比例已远较文话为多,因此,该作的问世,从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文话向“文学话”的过渡,或者说二者之间体际会通的道路已经铺就。当然,诸如《论文琐言》一类文话通于其他话体批评的倾向过于鲜明,或许也与“文”在传统语境中所指复杂有关。⑥古代的“文”在不同的理论家那里,其所指也往往不同,在有些语境中它可以用来指代“诗”(如在宋代真德秀的《文章正宗》中),在其他语境中也可以指代小说、戏曲等(如金圣叹)。而《论文琐言》发表的1915年前后所产生的“文学话”,实际上也存在“名不符实”的情况。1914年,周作人发表《艺文杂话》⑦周作人:《艺文杂话》,《中华小说界》1914年第2期。,该文是继王国维《文学小言》之后出现较早的“文学话”,全文以“艺文”(“文学”别称)⑧结合《艺文杂话》的内容来看,周氏所谓“艺文”,乃是“文章”之意,也就是“文学”之意。在现代中国“文学”概念建构的初期,周氏虽积极吸纳并在理智上认同西方新潮文学观念,但其早期论述更倾向于以中国传统的“文章”一词代替经由日本中介而来的西方“文学”一词。比如,他在阐释西方“文学”概念的演变时就曾说道:“原泰西文章一语,系出拉丁体诺文liter及literatura二字,其义至杂糅,即罗马当时亦鲜确解。”参见独应(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河南》1908年第4-5期。标目,文体形态与传统话体批评完全一致,但全篇基本均在谈诗,实际应当划归“诗话”。此外,前文例举的范烟桥的《文艺谈屑》虽不限于专谈某一种文体,但其主体内容仍在谈论小说、戏曲。由此可知,一种新式文学观念的建构往往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期间,被替代的观念虽然日渐衰落,但其能量与刺激却往往并不会迅速消散。因此,“文学话”由“文话”裂变而来,进而独立为一种文体形态,其间情形,并非一种直线替进的历史假想可以解说,这种蜕变的迹象,既反应于“文话”对自身批评界域的不断突破,也体现在“文学话”自身趋于“纯粹”的演变历程。
三、“文学话”的“独立性”与“过渡性”辨析
诞生于话体文学批评自身完成了“理论化转向”、西式文学理论述学规范逐渐成型之时,决定了“文学话”主要是一种理论批评文体。与其他话体文学批评一致,“文学话”在主体内容上也分“论理”与“纪事”两部分,但通观大量以《文坛随话》《文坛琐话》《文坛逸话》等命名的纪事类“文学话”,大多已背离传统纪事类话体批评所纪之事“谆谆示戒”“足资考证”的伦理、史料价值,要么沦为对文坛、文人八卦的记述,要么借话体批评之名,讲述一些与文学并无关联的事迹。譬如《现代文学评论》杂志于1931年第1卷第1期刊载的“文坛逸话”中,署名“洁”的《焦菊隐燕尔新婚》、杨昌溪的《爱罗先珂摸小脚》、德娟的《张资平怕走四川路》,后来《大众画报》“文坛逸话”刊载的《周作人口袋充实》《郁达夫飞黄腾达》(1933年第2期),《青年战线》“文坛逸话”栏目刊载的《张若谷闯祸》(1933年第6期)、《丁玲新爱人》(1933年第8期),直至《文饭》杂志1946年第20期刊载的《戴望舒毒打老婆》《穆时英跪求太太》,1947年朱实发表于《一四七画报》的系列《文坛逸话》,如《林琴南作小说骂人》(1947年第14卷第3期)、《林语堂叩头讲卫生》(1947年第14卷第5期)等等,均已偏离了话体批评以事实充实、完善文学思想,辅证理论批评的基本意图,沦落为纯粹意义上的“饭后谈资”。
纪事性的衰微固然可憾,但也为“文学话”提纯为一种理论批评文体提供了便捷。作为一种批评文体的“文学话”,既不遵循传统话体批评分体而论的基本程序,也不同于以系统性、逻辑性为基本特质的西式述学文体,自有其文体“独立性”。因此,对于“文学话”的全面理解,还应该建立在将其与同时期性质相近的“理论文”进行比较的基础之上。
(一)“文学话”与“新文体”“理论文体”之比较
从传统的诗文评到现代“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规范的确立,中国文论通过借镜西方实用主义、历史进化论等思维方式,以大兴报刊媒介、创办学校,进行文教制度改革与学科建制等一系列举措实现了全面转型。在这场文化变局中,有识之士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出发,征用各方资源以获取文化发展、变革的动力、手段和策略,并形成了诸种“新兴文化模态”,而文体无疑构成了这些不同文化立场与文化模态最直观的体现形式。因此,“文体革命”曾一度与“国字革命”“教育革命”并置,被视作“新文化的桥梁”①李一之:《新文化的桥梁——“国字革命”“文体革命”“教育革命”》,《众志月刊》1934年第1卷第4期。。由是,不仅传统中国文学创作文体秩序为之一变,也带动了说理文文体的系列变革。这其中,与“文学话”在文体特质、内涵指向等不同方面容易产生混淆的主要有梁启超创制的“新文体”和当时正在逐渐走向成熟的“理论文”②“理论文”包括学术性论文、学术性专著,在文学研究领域,即有别于传统文学批评文体特质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一类论文与著作的统称,为契合当时学界的普遍称谓,突出“理论性”(科学性、逻辑性)特质,与“新文体”在使用语境上达成一致,此处以“理论文”统称上述论著。。故此,将“文学话”与此两者进行比较,也就构成了厘清“文学话”内涵与边界的题中之意。
梁启超“三界”革命口号的提出,将晚清以降的经世文潮推向了高潮,亦奠定了现代文学与文学批评时常嵌入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政治功利化走向。作为“文界革命”的具体实践和卓越成果,“新文体”的创制无疑在中国现代说理文的发展历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关于“新文体”的文体特质,梁启超曾自述:
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按:指创办《新民丛报》《新小说》时)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例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①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全集》第10集,汤志钧、汤仁泽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78页。
严格来讲,“新文体”与“文学话”之间的差异较为鲜明,即两者在主体内容指向上并不相同。“新文体”主要是一种政论文,对此,梁启超在自述其早年求学经历时就已间接说明:“其后(按:指‘屡游京师’,与夏曾佑、谭嗣同结交并深受其影响)启超等之运动,益带政治色彩。”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全集》第10集,汤志钧、汤仁泽编,第277页。而“文学话”主要探讨“文学”问题。虽然“文学话”之“综论性”本身由多元指向聚合而成,加之政治救亡又是彼时时代思潮之底色,因此,“文学话”也或多或少会涉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但两者在论述策略上又截然不同。话体批评多呈“语录结集”之态,作者观点的表达常以“下断语”的方式进行。例如,沈雁冰在《杂感》一文中谈“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时说道:“世界各民族的文学全盛时代大都在治世,衰落时代大都在乱世;由乱而入治,必先文学界发出蓬勃的朝气。我们于此觑得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③沈雁冰:《杂感》,《文学》1931年第90期。。仅此数语,不多作说明。而梁氏“新文体”追求“条理明晰”,夏晓虹认为,这里的“条例明晰”主要体现在两点上:“一是梁启超很注重归纳、演绎的推理方法,也长于此道,因此他的行文逻辑性很强,论说层次清楚;二是梁启超善于条分缕析,从各方面周密地阐述一个问题,行文每取‘最数法’,即以数目字为标记,分段梳理”④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14页。。两者差异,由此可见。但两者亦有相近之处,这种相似性在语体方面得到了最为直接的体现,两者均呈现出“平易畅达”“杂以俚语”的特性。“新文体”之“平易畅达”主要体现在作者鼎革桐城派古文余风,以浅近的文言行文,追求平易浅显的文风,向“俗语文学”靠拢;而话体文学批评起初本就以口头形态面世,后来由社交场合的话语形式转变为书面形式,“文学话”作为话体批评之一种,其语体形态上的“俗文体”属性自不待言。
正如王一川所言,晚清民初出现的各种新兴文化,“它们之间的竞争和博弈其实既是晚清以来文化格局的基本动力所在,也是中国文化近现代转型的根本体现。此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西来文化的刺激和模范是一个基本的因素,但却不是根本的因素”⑤王一川:《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建设》,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8页。。当然,传统的转化大体上也是遵循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淡化的规律的。如果说产生于20世纪初期的“新文体”与“文学话”整体而言尚带有强烈的传统色彩⑥夏晓虹曾细致论述了梁启超的“新文体”如何批判性地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各种文体特质。参见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15-118页。,那么随着西学东渐进程的深入发展,当西方文化观念在中国社会全方位的改良、革命活动中的优越性得到一次次验证之后,传统的影响较之早期还是呈现出逐渐“褪色”的趋势。其中,“理论”意识的觉醒便是典型症象。据陈雪虎考证,中国现代性“理论”用义的产生,从历史时段的角度来看,大抵是从“咸同洋务”开始,经由“维新变法”“晚清新政”等节点性事件到民国初期这一阶段。在学科的意义上,它经历了一个由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最后进入人文科学的历程。⑦陈雪虎:《由过渡而树立:中国现代文论的发生》,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5-6页。文学领域“理论”意识的觉醒,催生了大量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教材和相关论文,这些论著,在文体特质上与传统话体批评的差异十分明显,因此,将其与“文学话”进行对比,也是理解“文学话”内涵与边界的重要途径。
夏济安在《两首坏诗》一文中曾对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整体特性作过总体性界说。在夏氏看来,中国人的批评文章追求“一点即悟”“毋庸辞费”。因此,它具有鲜明的阅读指向性,“是写给利根人读的”。与之相比,西方人的批评文章则是“写给顿根人读的”,所以强调一定要把道理讲清楚。⑧夏济安:《两首坏诗》,《夏济安选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98页。这种思维倾向落实于具体的批评实践,致使中国人的文学批评时常借助象征、类比、假借、引申等方式进行,强调通过瞬息即逝的直觉体验把握不同意象之间建立起来的“瞬间联系”,继而借助意象之间、符码之间的相互碰撞,生发出新的韵味来。⑨黄念然:《论中国文学批评文体的现代转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这种以“隐喻性”为主导特质的批评话语言说方式,使得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具有鲜明的“文学性”,从而与西方以逻辑性、体系性为根本追求,崇尚透辟的理性解析、追求在文学的本体性问题方面有所建树的批评方式存在巨大差异。而这一根本差异实际也是考察“文学话”文体独立性的重要依据。
(二)“文学话”的“过渡性”诠解
在“文学话”的宏观特质中,除了别于其他理论批评文体的文体“独立性”之外,“过渡性”也需要给予重点关注。“文学话”的形成,与中国现代文学观念、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建构特性密不可分。换言之,现代中国文学观念逐渐由混沌走向清晰,现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建构由探索逐渐走向成熟是“文学话”赖以构型的知识语境。反过来,正是出于建构期的现代文学及其理论批评相关观念的朦胧性和不确定性,促成了“文学话”这种以传统体式阐发新生观念的批评形态或曰理论形态的盛行。由此可见,“文学话”的面世,不仅与传统话体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有关,而且也与现代中国整体性文学生态的探索性和建构性具有直接的关联。
正是基于上述情形,中国现代文论的“现代性”无法简单粗暴地与“西方性”划上等号,而应该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双重质素所造就的张力结构中进行盘查。对此,王一川曾发表过精到的见解。他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独特性品格中,至少蕴蓄了两方面的元素:一为受西方影响而滋长起来的那种区别于中国传统文论的“世界性元素”,它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品格”;二是那些通过寝馈传统,即回溯中国古典文化及文学理论资源而来的“本土性元素”,它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传统性品格”。①王一川:《中国现代文论传统》,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84-185页。于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生成与建构,便始终在一个以“现代性”为原点而建立起来的横纵坐标图中进行。其中,一条轴线以“告别传统”为精神旨归,另一条则标志着以恪守传统为职志,捍卫民族文化的精神立场,但两者的相交却又无法回避地解构或曰消解着各自精神立场的纯粹性。古典与现代交替之际,这一坐标系为我们呈现出了无数个精确的“读数”,“文学话”即为其中之一。
作为现代中国文学批评文体之一种,“文学话”之“过渡性”质地的呈现,其思想根源在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观念的开放性。正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那种容纳古今、涵括中西的殊异性,为“文学话”受传统话体文学批评滋养而来,向西方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专著体式而去的“过渡性”特质奠定了思想观念基础。这一点,在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称名中就体现得颇为明显。一个饶有兴味但又鲜少被提及的研究现象是,在中国早期文学批评观念的建构中,“文学批评”概念除了与“文学鉴赏”“文学评论”“文学赏析”等范畴彼此纠葛之外,还与“批评文学”时常互替,甚至由此引发了关于“文学的”批评和“文学”的批评之间差异性的探讨。董秋芳的《批评文学与文学原理》(《京报副刊》1925年第57期)、龚翊明的《批评文学应有的修养》(《浙东》杂志1936年第1卷第4期)、李长之的《产生批评文学的条件》(《新民族》杂志1939年第4卷第1期)等,便是其中典型例证。就这些文章的具体内容来看,直接以“文学批评”名之亦无不可,但作者却以“批评文学”替代“文学批评”,这实际上是作者在接纳新知的过程中深受本土文化传统影响的重要表征。这些文章体现了鲜明的西方理论批评思维导向印迹,但同时,他们还未完全脱离中国传统批评理论寄生于文学创作的历史积习施诸其思想认知方面的影响。这一点,在曹聚仁关于“文学的”批评和“文学”的批评两者之间区别的论述中体现得最为直接。他说:“‘文学的’批评,是说某种批评,他的本身有文学的意味。如《文心雕龙》不但是批评文学的,他的文词,也有文学意味。‘文学’的批评,则谓他所批评的是文学,如魏文帝《典论·论文》是在批评文学的。”②聚仁(曹聚仁):《“文学的”批评和“文学”的批评》,《暨南周刊》1925年第11期。暂不论其比较对象是否合理(若与西方文学批评相比,《文心雕龙》与《典论·论文》都属“文学的”批评),以本土思维化育西方理论文体的努力已可见一斑。
正是建构期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在知识来源、思想内容,称名等方面所呈现出的艰难的抉择与探索情境,鲜明的矛盾与冲突特质,为“文学话”“过渡性”特征的培植提供了土壤。但是需要进一步指出并强调的是,此处所谓“文学话”的“过渡性”,并不与现代中国单纯时间意义上的线性历史演进逻辑完全吻合,而是呈现出波状交合的态势:在不同的“文学话”作者那里,其作品时而领先于历史时序,时而滞后于历史时序,但总体上与整体历史文化状况的发展趋势保持一致。这一点,通过对不同时段产生的“文学话”文本特性的比较就能发现。
整体上看来,自王国维1906年发表《文学小言》,到周作人于1914年发表《艺文杂话》,再到20世纪20年代沈雁冰《“文学批评”管见一》(1922)、钱杏邨《文艺随笔》(1929)等作品问世,30年代陈光尧《文艺集话》(1931)、朱湘《文艺闲谈》(1933)、许钦文《文学细话》(1933)等先后出现,再到40年代赵天人《文坛随话》(1940)、王希张《漫话文艺与人生》(1940)、李广田《谈文艺批评》(1941)、向培良《文艺纵横谈》(1947)、李广田《文艺书简》(1947—1948)等创作完成,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应作品呈现出与西方文学批评论文、著作越来越接近的特质。在文章的篇幅长短上,总体呈现出不断拓展的趋势,而且各部分、各段落之间的逻辑关联也越来越紧密。譬如,周作人的《艺文杂话》全文仅两千余字,分12个段落,各段之间毫无关联,时而谈古,时而论今;时而述中,时而言西;时而批评作品,时而介绍作家,纵情任性,毫不拘束。①周作人:《艺文杂话》,《中华小说界》1914年,第2期。而许钦文的《文学细话》,不仅篇幅大大增长,已达14,000余字,45则的体量,且各则之间、每则内部各段落之间的逻辑性也大大增强。文章先从广义的“文学”范畴切入,讨论了文学与图画、雕塑、建筑、音乐等艺术门类的区别,继而对时兴的诸如“文学的文学”“人生文学”“革命文学”“普罗文学”等文学主张做了简要介绍,既涉及纵向的、历史生成方面的考索,也偶尔对各种有所关联的不同主张之间的区别作简要论述。此外,文章也涉及写作修辞方面的内容和对国外各大民族文学概貌的介绍,体现了作者对文学问题较为系统、全面的思考和广阔的文学视野。②《文学细话》共45则,连载于1933年《读书生活》杂志第1至3期,其中,第1则至第15则载于该刊第1卷第1期;第16则至第30则载于该刊第1卷第2期;第31则至第45则载于该刊第1卷第3期。至于20世纪40年代的“文学话”,逻辑性更是进一步强化,已大体趋同于西方理论著作,只是由于前文所说,话体文学批评的确定,要从“名实对位、兼顾文体”的立场出发,所以这些作品才能划归“文学话”之中。
但也有与总体历史趋势并不一致的作品存在。比如,同样发表于1914年,周作人的《艺文杂话》就与许指严《文学卮言》体性差异明显。《文学卮言》虽篇幅不长,且以文言写就,但却颇具现代文思,且逻辑也较为谨严。作者认为,“论理”“叙事”“审美”可囊括“汉秦以下一切文格而范围之”。同时,作者指出才识与兴趣是“窥此三者之奥窔而擅其胜场”的要义,并主要对“兴趣”做了阐述。在对“兴趣”进行阐释时,又细分出“高尚之兴趣”“精密之兴趣”“疏朗之兴趣”“闲适之兴趣”“豪放之兴趣”“沉郁之兴趣”“悲壮之兴趣”“陶写之兴趣”“婉曲之兴趣”“藻丽之兴趣”等十种类型,并分别进行了进一步的细致阐述。如作者解释“高尚之兴趣”:“古人虚拟其状,所谓‘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又‘天半朱霞,云中白鹤是也’。施于论理文,不可无此识度,即叙事审美等文,尤不可无此胸襟。学者能于平日涵养之则,临文自有岩岩岳岳之概。”除却语言差异,命名差异,此文的“论文化”取向已经显露无遗。③许指严:《文学卮言》,《学生》1914年第1卷第2期。而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的《文学漫话一打》则又体现出逆历史潮流的趋势,在西方意义上的文学批评规范相对成熟的语境中,反而与传统诗话一类在文体形态上高度一致。④蓬生:《文学漫话一打》,《亚光》1936年第2卷第3期。由此可见,所谓“过渡性”,只在整体描述的意义上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