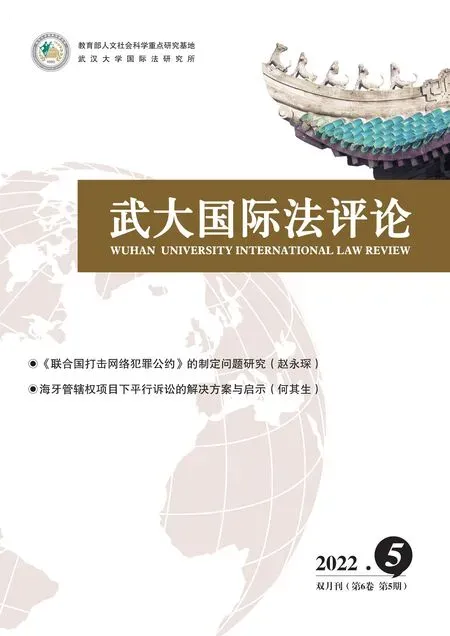国际投资仲裁中的“法庭之友”资格认定
——基于法益衡量视角
单菊铭
引言
近期,密苏里州诉中国案再次引发大众对于“法庭之友”这一古老制度的关注。①在密苏里州诉中国案中,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以独立学术机构的名义向法院提交了“法庭之友”意见,主要针对国际法上的国家豁免问题。白衣骑士“维护国际法”(Upholding International Law,一家主要律师在荷兰的不知名机构)也先后两次提交了两次“法庭之友”意见(2020 年9 月25 日、2021 年1月4日)。“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制度源自古罗马法,早先在英美法系的司法体系中得到广泛运用,晚近方适用于国际争端解决场所。②See Astrid Wiik,Amicus Curiae before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73-123 (Hart Publishing 2018).“法庭之友”制度通常是指,无权作为当事方参与案件但与案件处理结果有着重大利害关系的非争端方(non-disputing parties),作为代表参与诉讼程序并提交意见的过程。①参见张泽涛:《美国“法庭之友”制度研究》,《中国法学》2004年第1期,第173页。相对于其他法律制度而言,“法庭之友”制度不仅具有参与成本低、法律风险小的优势,而且还将公共价值观引入争端解决程序,极大地提高了机制合法性。
“法庭之友”参与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程序较晚,但与国际法院、WTO 上诉机构以及国际海洋法法庭等其他国际争端解决场所中的“法庭之友”参与情况相比,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中的“法庭之友”参与不仅形成较为完善的规则,②《ICSID仲裁规则》(2022年版)对“法庭之友”参与规则进行了修订和完善。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据统计,截至2021 年底,ICSID 中“法庭之友”参与案件就有86 个,且近年来“法庭之友”参与投资仲裁的积极性还在不断提高。③See https://icsid.worldbank.org/cases/content/tables-of-decisions/ndp,visited on 5 August 2022.
“法庭之友”资格认定是对作为非争端当事方的个人或实体享有以“法庭之友”身份参与诉讼或仲裁程序的适格性的判断。“法庭之友”参与国际投资仲裁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程序性的参与,例如,参加听证会和查阅文件;另一种是实质性的参与,例如,提交书面意见。本文对“法庭之友”参与资格的认定限定于提交意见资格的认定,主要基于三点考量:其一,“法庭之友”提交意见资格的认定是国际投资仲裁“法庭之友”参与规则设计与仲裁裁判实践中最重要的一环。其二,国际投资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以及投资协定中的规则为认定“法庭之友”是否享有提交意见的资格提供了规范依据和客观的认定标准。其三,“法庭之友”提交的意见可能实质性地影响仲裁裁决。④See Nicolette Butler, Non-Disputing Party Participation in ICSID Disputes: Faux Amici? 66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143(2019).
从资格认定实践看,“法庭之友”案件的激增、国际投资仲裁无“遵循先例”的传统以及“法庭之友”身份多样性的叠加作用,导致了投资仲裁中“法庭之友”参与裁判实践的混乱与矛盾现象。在面对不同身份的“法庭之友”参与时,如何根据“法庭之友”的具体情况进行个案认定,成为“法庭之友”资格认定中的现实难题。仲裁庭应当依循何种标准进行资格认定?如何根据个案进行灵活解释?如何确定仲裁庭合理解释的边界?最新修订的《ICSID 仲裁规则》(2022 年版)对“法庭之友”资格认定进行了统一规定,但立法也难解实践之困顿。⑤国际投资法中的“法庭之友”参与制度呈现的“实践—规则—实践”演进特点,使得“法庭之友”参与资格认定规则的发展总是滞后于实践,法律沉默和法律漏洞现象也仍旧存在。近年来,国际投资仲裁中的“法庭之友”资格认定问题也受到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关注。但现有研究或关注于不同机构、不同条约中“法庭之友”资格认定规则的梳理、对比⑥See e.g., Crina Baltag,The Role of Amicus Curiae in Light of Recent Developments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Legitimizing the System? 35 ICSID Review (2020);Gary Born & Stephanie Forrest,Amicus Curiae Participation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34 ICSID Review (2019); Sophie Lamb, et al.,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Amicus Briefs in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5 Indian Journal of Arbitration Law(2017).,或聚焦于“法庭之友”参与的典型个案分析①See Christian Schliemann, Requirements for Amicus Curiae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A Deconstruction of the Procedural Wall Erected in Joint ICSID Cases ARB/10/25 and ARB/10/15,12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2013).,缺乏对“法庭之友”资格认定理论与实践的系统研究。
近年来,国际性或跨国性争端中开始出现“法庭之友”的参与身影。②例如,南海仲裁案、密苏里州诉中国案、美国对华维生素C反垄断案等。虽然目前涉华国际投资仲裁案件中尚无“法庭之友”的参与,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国际投资仲裁中“法庭之友”提交的意见可能实质性地影响投资仲裁裁决③See Nicolette Butler,Non-Disputing Party Participation in ICSID Disputes:Faux Amici? 66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143(2019).。据统计,在中国作为被诉方的9 起案件以及中国投资者提起的13 起投资仲裁案件中④See Investment Policy Hub,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vestment-dispute-settlement/country/42/china,visited on 5 August 2022.,不少案件争端都与环境等公共利益有关。因此,一方面,不能排除“法庭之友”参与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法庭之友”实质上影响仲裁裁决的情况。考虑到我国国内法中并未引入“法庭之友”制度,并且无论是我国海外投资者、我国政府机构,还是国内非政府组织或个人,都尚无参与国际投资仲裁“法庭之友”案件的经验,对投资仲裁中“法庭之友”资格认定问题的本质分析与裁判实践总结,对于投资者关注“法庭之友”参与对案件的影响、促进我国公共利益的维护与国家利益的表达以及提高国内潜在“法庭之友”参与主体的参与质量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从法益衡量视角透视国际投资仲裁中“法庭之友”的资格认定问题,通过对“法庭之友”资格认定本质、规范依据与仲裁认定实践的梳理和分析,发现国际投资仲裁中“法庭之友”资格认定的规律与难题,进而提出实现法益保护与化解认定难题的解决方案。
一、“法庭之友”资格认定的法益衡量本质
国际投资仲裁中“法庭之友”资格认定的表象是关于“法庭之友”参与权利的判断,但实质上公私法益间的利益衡量才是其资格认定的内生逻辑。国际投资仲裁中“法庭之友”的资格认定是在投资者、东道国以及非争端方“三元主体”的法益结构中进行的法益评价。
(一)“三元主体”结构中的法益衡量
法益衡量又称“利益衡量”,是法官在案件涉及多个法益冲突的场合下进行利益权衡的判案工具,是一种法律实质解释方法。作为一种具有普适意义的法律解释方法或司法裁判方法,法益衡量适用的前提是存在多个法益间的冲突现象。⑤参见胡玉虹:《关于“利益衡量”的几个法理问题》,《现代法学》2001年第4期,第33页。日本学者加藤一郎揭示了司法裁判中的法益衡量过程——如果关于某个法律问题存在两种及以上的解释情形,选择哪一种解释以及如何选择都只能通过法益衡量来决定。①参见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16页。法益衡量具有运用的必要性:一方面,法益衡量可以弥补实定法的缺陷。由于立法的固化或模糊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局限性,如果法律解释严格依循立法规范,仅仅停留在法条的字面含义上,裁判结果就可能面临着“合法却不合理”的境况,而作为法律解释方法的法益衡量可以有效填补法律漏洞。另一方面,法益衡量具有促进解释结果正义的功能。通过法益衡量,能够使法律解释结果更加接近正义。
国际投资仲裁中的公私法益冲突结构经历了由二元到三元的转变。国际投资仲裁中的“法庭之友”资格认定程序为公私法益的表达、法益竞争以及仲裁庭的法益权衡提供了专门场所。不同于只涉及私益间冲突的国际商事仲裁案件,投资仲裁案件往往存在公私两大法益的冲突。在传统的国际投资仲裁中,由于国家充当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因此法益冲突主要发生在东道国与私人投资者之间,法益衡量处理的是二元主体间公私利益冲突的简单结构。自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国际投资争端解决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投资仲裁的法益冲突结构略显复杂。国际投资争端的互动主体从国家和外国投资者扩展到以“法庭之友”身份参与案件的非争端当事方。②See Ibironke T.Odumosu,The Law and Politics of Engaging Resistance in Investment Dispute Settlement,26 Penn State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255-256(2007).因此,国际投资仲裁“法庭之友”资格认定中的法益衡量需要置于投资者、东道国以及“法庭之友”三元主体的公私法益冲突结构中。
(二)“法庭之友”资格认定中的法益评价
法益衡量的本质是选择优势利益并予以优先保护的过程。事实上,冲突法益往往不能同时得到满足,因此需要通过评价冲突法益间的“相对”重要性来确定它们的先后位序,也即法益评价。在国际投资仲裁的“法庭之友”资格认定中,何种法益应得到优先保护?在维护公共利益的基本共识下,国际投资法通过立法技术为“法庭之友”参与预设了“公益保护不得侵害合法私益”的评价尺度。
社会基本共识认为,生命健康利益的保护优于财产利益,弱势利益受到特别保护,且私人权利的行使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③参见梁上上:《异质利益衡量的公度性难题及其求解——以法律适用为场域展开》,《政法论坛》2014年第4期,第9-11页。一般认为,“法庭之友”所代表的利益与人权或环境等公共利益有关,这些公共利益往往关涉生命与健康等利益,并且相较于经济实力雄厚的外国投资者而言,这种利益也是一种弱势利益。而对于外国投资者而言,其在国际投资活动中的利益通常仅与财产利益有关。因此,理论上,“法庭之友”参与案件的公共利益应当受到优先保护。
然而,从国际投资仲裁中的“法庭之友”参与规则看,“公益保护不得侵害合法私益”是规则制定的底层逻辑。法律与法益是一对紧密联系的范畴,法律条文不是孤立制定的,是法律制定者对各种法益综合平衡的结果。对冲突法益的调整及对先后顺序的安排,往往需要依赖立法手段实现。①参见[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414-419页。尽管“法庭之友”的参与为投资仲裁注入了对公众利益的关注,但国际投资法本身固有的投资者保护基因使“法庭之友”资格认定成为“法庭之友”参与的门槛制度。因此“法庭之友”资格认定的实质就是在保障投资者私益的框架下对“法庭之友”必要参与之有限权利的赋予;不得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是仲裁庭批准“法庭之友”参与的基本要求。
此外,虽然国际投资法为“法庭之友”资格的认定提供了一般性条款,但由于资格认定问题极其复杂,一般性条款在作为认定标准或解释框架运用时略显不足。因此,在“法庭之友”资格认定过程中,仲裁庭需要往返于条文的客观标准与个案事实之间进行冲突法益间的自由衡量。
二、“法庭之友”资格认定的规范依据
法律事实的存在为法益衡量提供了一个可依循的客观标准。国际投资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以及国际投资协定中的规则为如何认定“法庭之友”资格提供了规范依据和客观的认定标准。
(一)依据非争端方自我披露的信息进行个案认定
“法庭之友”参与规则为申请参与投资仲裁的非争端方施加了一项“披露义务”。非争端方披露的自身信息是仲裁庭进行“法庭之友”资格认定的事实基础。为了做出正确的判断,仲裁庭往往需要依据“法庭之友”提交的身份、性质以及关联关系等具体材料进行资格认定。在Suez 等诉阿根廷案(以下称“Suez 案”)中,由于四名申请人未向仲裁庭提供有关其自身情况的充分且具体的信息,因此仲裁庭以“无法判断他们是否有成为法庭之友的资格”为由拒绝其参与请求。②See Suez, Sociedad General de Aguas de Barcelona S.A. and Interagua Servicios Integrales de Agua S.A. v.Argentine Republic (Suez and Others v.Argentina), ICSID Case No.ARB/03/17, Order in Response to a Petition for Participation as Amicus Curiae,17 March 2006,para.34.也就是说,要想获得成功参与的机会,“法庭之友”必须履行自我披露义务,不充分履行披露义务的“法庭之友”,可能面临被仲裁庭认定不具有参与仲裁程序资格的风险。
2003 年NAFTA 自由贸易委员会发布的《FTC 声明》是最早规定“法庭之友”参与投资仲裁程序规范的文件。《FTC 声明》第B2 条规定,“法庭之友”提交意见的申请应当包括……(3)对申请人自身情况的描述,包括成员资格和法律地位(例如,公司、行业协会或其他非政府组织)以及目标、活动性质、上级组织机构(包括直接或间接控制申请人的组织机构);(4)披露申请人是否与任何争端当事方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5)指明任何政府、个人或组织在申请人准备提交文件时曾提供的任何财务或其他协助;(6)说明申请人在仲裁中的利益性质。《UNCITRAL 透明度规则》第4 条的内容与《FTC声明》的规定基本相同。
与上述规定有所不同的是,《ICSID 仲裁规则》(2022 年版)并未单列有关“法庭之友”自我披露义务的强制性条款,但“法庭之友”的身份情况、与当事方的联系以及资助披露等事项规定在仲裁庭应当考虑的情况中。①参见《ICSID仲裁规则》(2022年版)第67(2)(d)(e)条。此外,国际投资协定中也有关于“法庭之友”自我披露义务的规定。例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第9.23.3条规定,每一份“法庭之友”意见都应当指明作者,披露其与任何争端当事方之间直接或间接的从属关系,并确认在其准备该意见过程中已提供或将提供任何财政或其他援助的个人、政府或其他实体。②参见CPTPP第9.23.3条。《美墨加协定》中也有类似的规定。③参见《美墨加协定》第14.D.7.3条。
(二)资格认定的考量因素及其自由裁量
“法庭之友”资格认定的考量因素是仲裁庭审查认定的核心与重点。当“法庭之友”满足身份资格要求并履行披露义务后,仲裁庭便进入考量因素的审查认定阶段。在此阶段中,仲裁庭往往需要结合“法庭之友”披露的自身情况与具体案情对考量因素予以考察。
《FTC 声明》第B(6)条规定,仲裁庭在决定是否批准“法庭之友”提交书面意见时,除其他事项外,还应考量以下情况:(1)从协助仲裁庭裁判相关事实或法律问题的角度来看,“法庭之友”应当提交不同于当事方的特定知识或见解;(2)“法庭之友”提交的意见应当与争端主题有关;(3)“法庭之友”在仲裁中有重大利益;(4)争端事项涉及公共利益。④但是,与《FTC 声明》不同的是,《ICSID 仲裁规则》(2006 年版)删除了对公共利益审查的规定。2014 年《UNCITRAL 透明度规则》第4.3 条规定,仲裁庭酌定考量的审查因素只包括:重大利益、协助功能两种情形。投资协定中的规定较为粗略,但基本遵循投资仲裁中的规定。CPTPP第9.23.3条也有类似规定。
此外,投资仲裁中的“法庭之友”参与规则还赋予仲裁庭在考量因素认定上的自由裁量权。⑤See Chen Yu, Amicus Curiae Participation in ISDS: A Caution against Political Intervention in Treaty Interpretation,35 ICSID Review 228(2020).《FTC 声明》已列明的因素只是仲裁庭审查认定“法庭之友”资格时的考量因素之一。⑥See Apotex Holdings Inc.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potex v.US), ICSID Case No.ARB(AF)/12/1, Procedural Order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Applicant Mr. Barry Appleton as a Non-Disputing Party, 4 March 2013,para.26.除明文规定的考量因素外,《FTC 声明》还规定了仲裁庭对其他事项考虑的权利,而这些“其他事项”并无详尽清单。在当事方协商同意的前提下,甚至还可以附加对其他因素的考量。①See Lone Pine Resources Inc. v. Government of Canada (Lone Pine v. Canada), UNCITRAL, Procedural Order No.1,11 March 2015,para.57.在此案中,当事方要求“法庭之友”必须来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缔约方,或是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缔约方的领土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士。另一方面,仲裁庭在如何适用与解释相关的考量因素时,仍有自由裁量的空间。
(三)资格认定中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
“法庭之友”参与仲裁不得扰乱仲裁程序或给当事方造成不公平、不合理的负担,这既是对仲裁庭审查认定的基本要求,也是对“法庭之友”的基本要求。为了履行这一基本要求,仲裁庭必须评估“法庭之友”参与仲裁程序给争端各方带来的潜在影响,权衡当事方的额外负担与“法庭之友”参与仲裁之间的关系。②See Gary Born & Stephanie Forrest,Amicus Curiae Participation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34 ICSID Review 653(2019).
《FTC 声明》第B(7)条规定,仲裁庭应当确保:(1)避免任何非争端方提交的意见扰乱仲裁程序;(2)非争端方提交意见不会对任何争端方造成负担或造成不公正的损害。③《UNCITRAL 透明度规则》第4.4 条、《ICSID 仲裁规则》以及投资协定中的相关条款规定与《FTC声明》中的规定基本相同。在保留了“法庭之友”提交书面意见不会给当事方造成不合理负担或不公平损害的规定的同时,《ICSID 仲裁规则》(2022 年版)进一步规定了“法庭之友”提交书面意见的形式、日期以及费用等内容,其目的是通过给“法庭之友”设置各种限制或施加义务以确保当事方的合法权益不会受到损害。
三、国际投资仲裁庭对“法庭之友”资格认定的实践梳理
在对“法庭之友”资格的判断中,仲裁庭往往需要结合个案中“法庭之友”的自身情况和具体案情,进行主观裁量。本部分通过考察投资仲裁庭在“法庭之友”资格认定中常见的考量因素,发现投资仲裁庭在不同案件中适用不同的认定标准,对同一考量因素的解释也存在几种不同的释法思路。
(一)协助仲裁庭裁判相关事实或法律问题
是否具有协助仲裁庭裁判相关事实或法律问题的功能是仲裁庭判断“法庭之友”适格性的首要考量因素。在ICSID 投资仲裁实践中,仲裁庭在“法庭之友”能否提供不同于当事方的观点、特殊知识或见解以协助仲裁庭做出正确裁决的问题上,存在三种不同的认定思路。
1.考察“法庭之友”的身份是否具有特殊性
在Philip诉乌拉圭案(Philip and Others v. Uruguay,以下称“Philip案”)中,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秘书处(以下称“FCTC 秘书处”)以及泛美卫生组织(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 PAHO)申请作为“法庭之友”介入案件,仲裁庭在判断三个组织是否能发挥协助功能时,对其组织地位或身份的特殊性进行了审查。在对WHO 和FCTC 秘书处是否能发挥协助功能进行审查时,仲裁庭将两者身份地位的特殊性与当事方对比。该案仲裁庭认为,WHO 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它是世界上最重要、最权威的公共卫生机构,它监督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称《公约》)的起草和通过,在烟草的管控方面具有专业的知识,因此,它可为本案的审理提供有关全球烟草控制和国际卫生协调工作的相关信息。①See Philip Morris Brand Sàrl (Switzerland), Philip Morris Products S.A. (Switzerland) and Abal Hermanos S.A. (Uruguay) v. Oriental Republic of Uruguay (Philip and Others v. Uruguay),ICSID Case No.ARB/10/7,Procedural Order No.3,para.17.FCTC秘书处是根据《公约》建立的实体,其主要任务是协调并帮助缔约方履行《公约》义务,因此也可能会带来不同于当事方的观点、知识或见解。②See Philip and Others v.Uruguay,ICSID Case No.ARB/10/7,Procedural Order No.3,para.24.在审查PAHO 是否能发挥协助功能时,仲裁庭不仅审查了其相较于当事方的独特性,还将其与WHO 和FCTC 秘书处进行了比较。仲裁庭认为,PAHO 具有不同于WHO 与FCTC 秘书处的特殊地位。它致力于改善美洲区域人民的健康,可就整个拉丁美洲的烟草控制、烟草使用的影响以及烟草行业的营销等提供区域性的视角,因此可以提供既不同于当事方又不同于WHO 和FCTC 秘书处的观点、知识或见解。③See Philip and Others v.Uruguay,ICSID Case No.ARB/10/7,Procedural Order No.4,para.17.
此外,在Infinito 诉哥斯达黎加案(Infinito v. Costa Rica,以下称“Infinito 案”)以及Alicia 诉墨西哥案(Alicia v. Mexican,以下称“Alicia 案”)中,仲裁庭也通过审查身份或地位的特殊性进行了协助功能的判断。Infinito案仲裁庭认为,“法庭之友”是在国内程序中对仲裁申请人和被申请人都胜诉的原告,基于身份上的特殊性,它可能提供不同于当事人的观点。④See Infinito Gold Ltd. v. Republic of Costa Rica (Infinito v. Costa Rica), ICSID Case No.ARB/14/5,Procedural Order No.2,para.31.而在Alicia案中,尽管“法庭之友”申请人也具有特殊的身份属性,但由于仲裁庭已经知道破产程序的存在,并可在必要时要求当事方提供进一步的资料,因此,仲裁庭认为,本案的“法庭之友”不太可能就与仲裁有关的问题提供与当事方不同的特定见解。⑤See Alicia Grace and Others v.United Mexican States(Alicia v.Mexican),UNCT/18/4,Procedural Order No.4,para.50.
2.考察“法庭之友”相对于当事方是否具有能力优势
在审查“法庭之友”是否能够发挥协助功能时,还涉及对“法庭之友”能力的考察,即“法庭之友”是否具有超越当事方观点、经验或知识的能力优势。在Apotex诉美国案(Apotex v. US,以下称“Apotex 案”)中,律师Appleton 以个人身份申请作为“法庭之友”提交意见。仲裁庭认为,虽然Appleton 先生在理解投资条约的意义以及分析政府监管行为等方面具备经验和专门知识,但与当事方的几位律师所拥有的丰富经验和见解相比,他个人的知识和见解难以与当事方的几位律师相媲美。①See Apotex v.US,ICSID Case No.ARB(AF)/12/1,Procedural Order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Applicant Mr.Barry Appleton as a Non-Disputing Party,paras.32-33.
3.考察“法庭之友”能否提供与当事方实质上不同的视角或见解
从Apotex 案开始,仲裁庭开始采用实质性解释标准,审查“法庭之友”能否提供实质上不同于当事方的观点、知识或见解。在该案中仲裁庭认为,作为“法庭之友”的BNM 公司对美国食品药品法等法律、司法制度以及对NAFTA 均没有任何专门知识或相关经验,因而不具有提供“实质上不同的视角或见解”(a materially different perspective or insight)的能力。②See Apotex v. US, ICSID Case No.ARB(AF)12/1, Procedural Order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Applicant BNM as a Non-Disputing Party,paras.23-24.
(二)“法庭之友”意见与争端主题有关的认定
实践中,对于如何解读“法庭之友”意见是否在争端范围内,存在两种不同的认定思路。
1.将“法庭之友”意见限定在与争端主题有关的范围内
在Biwater 诉坦桑尼亚案(Biwater v. Tanzania,以下称“Biwater 案”)中,作为申诉方的投资者认为,本案“法庭之友”所关切的问题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法律上都与仲裁庭需要在本案中所裁决的问题无关。本案不涉及环境保护或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即使“法庭之友”在国际投资协定与国家发展政策等问题上有着公认的专门知识,这也与本案争议无关。③See Biwater Gauff (Tanzania) Limited v.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Biwater v. Tanzania), ICSID Case No.ARB/05/22,Procedural Order No.5,paras.31-35.虽然在“法庭之友”意见与争端主题是否有关的问题上,该案仲裁庭并未做出解释,但仲裁庭最终还是认定“法庭之友”的意见与争端主题有关。而在Bernhard 诉津巴布韦(Bernhard and Others v. Zimbabwe,以下称“Bernhard 案”)、Border 诉津巴布韦(Border and Others v. Zimbabwe,以下称“Border案”)以及Apotex案中,仲裁庭均认定“法庭之友”意见与争端主题无关。Bernhard案和Border案仲裁庭认为,“法庭之友”提出的关于土著居民人权问题的意见属于争端范围外的问题。④See Bernhard von Pezold and Others v. Republic of Zimbabwe (Bernhard and Others v. Zimbabwe),ICSID Case No.ARB/10/15,Procedural Order No.2,para.60.此外,在Apotex 案中,“法庭之友”依据NAFTA 第1139 条所提出的意见,也与本案争端主题无关。
2.以争端当事方的异议或主张为认定标准
Philip案与Infinito案仲裁庭均未对“法庭之友”的意见是否属于当事方的异议或主张表态。Apotex案仲裁庭首次对“法庭之友”意见是否属于当事方的异议或主张进行了正面回应。在该案中,作为“法庭之友”的BNM 公司提交的书面意见涉及NAFTA 第1139(g)条下“投资”的定义范围,即暂时核准的ANDA是否构成NAFTA第1139(g)条下的投资问题。①See Apotex v. US, ICSID Case No.ARB(AF)12/1, Procedural Order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Applicant BNM as a Non-Disputing Party,para.28.但随后申诉方不再就失去发布新产品机会而要求赔偿损失,所以本案不再涉及暂时批准的ANDA是否构成投资的问题。因此,仲裁庭裁定BNM公司提交的意见涉及的是双方争议范围之外的问题。
(三)“法庭之友”与争端具有重大利益关系的认定
“法庭之友”享有参与仲裁程序资格的实质性前提是“法庭之友”与争端具有重大利益关系。ICSID仲裁庭对“重大利益”的认定存在三种思路。
1.对重大利益的解释与公共利益混同
在早期的案件中,仲裁庭往往将重大利益的解释与公共利益混同,以公共利益解释重大利益。Vivendi 诉阿根廷案(Vivendi and Others v. Argentine,以下称“Vivendi 案”)仲裁庭在审查本案的利害关系时认为,这些案件涉及公共利益问题,而且这些案件的判决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案件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人。②See Suez, Sociedad General de Aguas de Barcelona, S.A. and Vivendi Universal, S.A. v.Argentine Republic (Vivendi and Others v.Argentina), ICSID Case No.ARB/03/19,Order in Response to a Petition for Transparency and Participation as Amicus Curiae,para.19.Biwater 案仲裁庭也借鉴了Vivendi案仲裁庭的解释方法,模糊重大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界限。③See Biwater v.Tanzania,ICSID Case No.ARB/05/22,Procedural Order No.5,para.52.
2.通过“组织宗旨是否与争端主题相关”进行认定
在多数案件中,仲裁庭经常通过“组织宗旨是否与争端主题相关”判断是否有重大利益关系。例如,在Philip 案中,仲裁庭对PAHO 是否与本案具有重大利益关系进行了宽泛的解释。仲裁庭认为,鉴于PAHO 最近还参与了癌症、心血管和呼吸系统疾病以及糖尿病等非传染性疾病问题,而引发这些疾病的一个常见风险因素就是烟草使用,因此PAHO与仲裁有重大利益关系。④See Biwater v.Tanzania,ICSID Case No.ARB/05/22,Procedural Order No.5,para.27.
在Infinito 案中,非争端方声称它有重大利益关系,因为它不仅是一个致力于保护哥斯达黎加自然资源的环保组织,而且是一个导致原告特许权取消的司法程序实体。申诉方认为,环境保护不是本次仲裁的争端内容,当非争端方对争端没有重大利益关系时,可以将它们排除在仲裁程序之外。⑤See Infinito Gold Ltd. v. Republic of Costa Rica (Infinito v. Costa Rica), ICSID Case No.ARB/14/5,Procedural Order No.2,paras.13-18.虽然该案仲裁庭未对申诉人的异议做出回应,但仲裁庭最终认定“法庭之友”与争端具有重大利益关系。
3.将“重大利益”解释为“超出一般的利益”
以Apotex 案与Alicia 案为例,部分仲裁庭则将重大利益解释为“超出一般的利益”。Apotex案中,作为“法庭之友”的BNM公司认为,由于BNM公司正在考虑设立一个诉讼风险投资基金,生物技术、电信、采矿和能源部门可能会从中受益,因此它与本案有重大利益关系。①See Apotex v. US, ICSID Case No.ARB(AF)12/1, Procedural Order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Applicant BNM as a Non-Disputing Party,para.27.仲裁庭认为,一方面,BNM 公司没有具体阐释它所代表的利益将会如何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本案所管辖的具体问题的影响;另一方面,BNM公司考虑设立风险投资基金的事实并不等于预期的具体利益。②See Apotex v. US, ICSID Case No.ARB(AF)12/1, Procedural Order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Applicant BNM as a Non-Disputing Party,para.28.虽然BNM 公司似乎对仲裁庭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部分内容有一般性利益(general interest),但BNM公司并未表现出重大利益(significant interest)。③See Apotex v. US, ICSID Case No.ARB(AF)12/1, Procedural Order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Applicant BNM as a Non-Disputing Party,para.33.在该案仲裁庭对于另一位“法庭之友”Appleton 先生申请的裁定中,仲裁庭重申重大利益是“超出一般的利益”(more than a general interest)的观点。④See Apotex v.US,ICSID Case No.ARB(AF)/12/1,Procedural Order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Applicant Mr.Barry Appleton as a Non-Disputing Party,paras.38-40.Alicia 案仲裁庭同样采用重大利益为“超出一般的利益”的解释思路,认为本案“法庭之友”与案件有重大利益关系。⑤See Alicia v.Mexican,UNCT/18/4,Procedural Order No.4,para.52.
(四)“公共利益”的认定争端涉及公共利益的认定
从“法庭之友”参与投资仲裁的规则看,公共利益并非仲裁庭适格性判断必须要考量的因素。但是在仲裁庭的裁判实践中,公共利益问题普遍存在于“法庭之友”资格的认定中。仲裁庭对公共利益的认定思路包括以下三种:
1.仲裁裁决可能影响争端当事方以外的个人或实体
如上文所言,早期的仲裁实践中,仲裁庭模糊重大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界限。Suez案确立一项裁判准则,即当仲裁裁决可能影响争端当事方以外的个人或实体时,仲裁的争端主题就可被视为与公共利益相关。⑥See Suez and Others v.Argentina, ICSID Case No.ARB/03/17, Order in Response to a Petition for Participation as Amicus Curiae,para.17.此后的案件基本都沿用此标准来界定争端是否具有公共利益。⑦See ICSID Case No.ARB/03/19; ICSID Case No.ARB/05/22; ICSID Case No.ARB(AF)12/1;UNCT18/4.由于投资争端的当事方之一是作为国家的实体,因此投资争端所涉及的实质性问题远远超出了一般商业当事人之间的跨国商事仲裁所涉及的问题范畴。Suez 案仲裁庭也认为,国家的国际责任与私法规定的公司责任不同,在IC-
SID管辖下的投资条约仲裁案件中多半会涉及公共利益问题。①See Suez and Others v.Argentina, ICSID Case No.ARB/03/17, Order in Response to a Petition for Participation as Amicus Curiae,para.17.2.对公共利益的证明要求
对公共利益的证明要求体现在Apotex 案的解释中。该案仲裁庭认为,根据BNM 公司提交的“法庭之友”申请,无法确定它是为了维护何种公共利益而申请介入案件。即使可以推断BNM 公司意图维护的公共利益是指对整个制药行业的影响,但无论如何也不满足公共利益的要求。②See Apotex v. US,ICSID Case No.ARB(AF)12/1, Procedural Order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Applicant BNM as a Non-Disputing Party,para.36.
3.明确特殊利益非公共利益
Apotex 案仲裁庭也首次明确特殊利益非公共利益。仲裁庭认为,作为“法庭之友”的Appleton 先生所声称的公共利益实质上是一种特殊利益,并非公共利益。③See Apotex v.US,ICSID Case No.ARB(AF)/12/1,Procedural Order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Applicant Mr.Barry Appleton as a Non-Disputing Party,paras.39,43.在Alicia案中,仲裁庭沿用Apotex案中对公共利益的解释思路,仲裁庭认为,虽然“法庭之友”主张,如果仲裁庭做出对投资者有利的裁决将对整个债券持有人群体产生负面影响,使他们的债券投资面临极大风险,但是“法庭之友”寻求维护的是在国内诉讼程序中作为债权人的特殊利益,而仲裁庭无法判断这种特殊利益是否构成真正的公共利益。④See Alicia v.Mexican,UNCT/18/4,Procedural Order No.4,paras.24,53.
(五)“法庭之友”参与不会扰乱仲裁程序、不会造成不合理负担的认定
由于“法庭之友”的参与可能会以一种不成比例的方式增加仲裁成本,因此仲裁庭应确保“法庭之友”参与不会扰乱仲裁程序、不会给当事方带来不必要的费用负担或损害。
1.申请介入案件的个人或实体的身份限制
作为非争端方的个人或实体以何种身份介入案件也会对当事方造成影响。Infinito 案仲裁庭认为,“法庭之友”申请人试图作为案件当事方介入案件,如果允许它参与将迫使投资者同时面临两个案件诉讼,这将对当事方造成不合理的负担或不公平的损害,因此,非争端方必须作为仲裁庭的“朋友”行事。⑤See Infinito v.Costa Rica,ICSID Case No.ARB/14/5,Procedural Order No.2,paras.19,38.与Infinito 案仲裁庭的释法思路一致,B.V.公司诉爱沙尼亚案(B.V. v. Estonia,以下称“B.V.公司案”)仲裁庭也对申请参与案件的非争端方的身份做出要求。⑥See United Utilities (Tallinn) B.V. and Aktsiaselts Tallinna Vesi v. Republic of Estonia (B.V. v. Estonia), ICSID Case No.ARB/14/24, Decision on the Application for Leave to Intervene as a Non-Disputing Party,para.14.
2.提交文件与争端主题的相关性
从仲裁庭的释法思路来看,扰乱仲裁程序或给当事方造成负担还体现在“法庭之友”提交与争端主题无关的文件上。在Philip 案中,“法庭之友”申请中涉及了很多与本案无关的资料,仲裁庭认为,接受申请将迫使案件当事方对大量与案件无关的内容进行分析与答复,这无疑会给当事方造成不合理的负担。①See Philip and Others v.Uruguay,ICSID Case No.ARB/10/7,Procedural Order No.4,para.15.Apotex 案仲裁庭则关注无关资料对程序的扰乱问题。该案仲裁庭认为,由于“法庭之友”的申请并没有提供与本案争议相关的事实和论点,接受其申请将扰乱仲裁程序。②See Apotex v.US,ICSID Case No.ARB(AF)/12/1,Procedural Order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Applicant Mr.Barry Appleton as a Non-Disputing Party,paras.14,37.
(六)“法庭之友”独立性的认定
独立性与公平公正原则密切相关,独立性问题日渐成为国际投资仲裁关注的热点问题,“法庭之友”的独立性问题同样受到关注。在“法庭之友”资格认定中,仲裁庭往往会对“法庭之友”与当事方之间的直接或间接联系进行审查。
1.申诉方异议
“法庭之友”的独立性问题在Philip 案中被提出,但该案仲裁庭并未对该问题做出解释。③See Philip and Others v.Uruguay,ICSID Case No.ARB/10/7,Procedural Order No.3,para.11.第一次对“法庭之友”的独立性问题做出直接回应的案件是Bernhard 案,在该案中,东道国当地的原住民社区和欧洲人权委员会申请作为“法庭之友”参与案件。申诉方从三个方面指出其不具备独立性:第一,原住民社区的利益与被告国的利益一致;第二,原住民社区实际上是被告国的国家机关,不能独立于被告国。④津巴布韦总统有权委任及罢免原住民社区首领。See Bernhard and Others v. Zimbabwe, ICSID Case No.ARB/10/15,Procedural Order No.2,para.34.第三,“法庭之友”与其他机构之间的联系破坏了其独立性。⑤See Bernhard and Others v. Zimbabwe, ICSID Case No.ARB/10/15,Procedural Order No.2, paras.35-36.该案仲裁庭基本上同意申诉方对“法庭之友”独立性的异议主张。⑥但是,鉴于第37(2)条调查的简短性质,这一结论可能产生的所有后果将是不成熟的。因此,对于原住民社区是否独立的问题,仲裁庭认为,任命和解雇领导人的权力不是绝对的。See Bernhard and Others v.Zimbabwe,ICSID Case No.ARB/10/15,paras.52-53.
2.被告国异议
在Apotex案中,基于被告国对“法庭之友”独立性的异议,仲裁庭审查了“法庭之友”与申诉方的间接联系。被告国指出,申请人以前曾代表Signa S.A.公司(申诉方Apotex Inc.的合资伙伴)提交了一份起诉书,因此“法庭之友”与申诉方之间曾存在间接的联系,但在该案中“法庭之友”未说明其是否继续与申诉方之间保持这种间接关系。①See Apotex v.US,ICSID Case No.ARB(AF)/12/1,Procedural Order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Applicant Mr.Barry Appleton as a Non-Disputing Party,para.20.针对这一问题,申诉方回应称,其与该案“法庭之友”没有任何联系,也没有提供过任何支持。②对Apotex的会计记录进行搜索后发现,Apotex之前没有雇佣过申请人。See Apotex v.US,ICSID Case No.ARB(AF)/12/1,para.21.仲裁庭在裁决中指出,鉴于申诉方对该问题做出的澄清,仲裁庭认定“法庭之友”具备独立性。③See Apotex v.US,ICSID Case No.ARB(AF)/12/1,Procedural Order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Applicant Mr.Barry Appleton as a Non-Disputing Party,para.45.
四、“法庭之友”资格认定的规律与难题
近20 年来,国际投资仲裁庭对“法庭之友”资格认定的态度发生了从宽松到严格的转变。这种转变可以从Philip 案、Von Pezold 诉津巴布韦案以及Apotex 案这三个典型的“异质性案件”的“法庭之友”资格认定中窥见一二。但是,无论认定标准如何转变,“法庭之友”资格认定中仍存在诸多难题。本文主要分析“法庭之友”资格认定中存在的非投资性问题、考量因素间潜在冲突的结构性问题以及费用负担这一新问题。
(一)投资仲裁中“法庭之友”资格认定的规律发现
投资仲裁庭对“法庭之友”参与态度的转变还可以从仲裁庭对“法庭之友”资格的认定规律中获知一二。通过对ICSID 案例的实证研究发现,虽然投资仲裁庭在“法庭之友”资格认定问题上,尚未形成确定且一致的标准,但却呈现出从宽松趋向严格的认定趋势。
第一,协助功能。在早期案件中,仲裁庭对协助功能的审查较为宽松,仅依靠“法庭之友”自我披露的自身资料进行资格审查。随着实践的发展,一方面,仲裁庭在“法庭之友”是否具有协助功能的审查上开始出现较多的认定标准;另一方面,以Apotex案为代表,仲裁庭对协助功能呈现严格解释的趋势。
第二,与争端主题有关。早期实践并未对该考量因素予以过多关注,以至于与争端主题有关并未对“法庭之友”的参与产生实质性影响。而从Apotex案开始,仲裁庭开始适用以争端当事方的异议或主张为审查思路的认定方法,即要求“法庭之友”意见限定在当事方的仲裁主张范围内。④See Apotex v. US, ICSID Case No.ARB(AF)12/1,Procedural Order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Applicant BNM as a Non-Disputing Party,para.28.事实上,这也代表了仲裁庭对与争端主题有关的限缩解释,具有严格解释的倾向。
第三,重大利益的认定。仲裁庭对重大利益的审查愈发严格,审查标准也愈发具体化、精细化。早期案件中,仲裁庭对公共利益与重大利益未做明确区分,因而导致只要涉及公共利益基本就可以认定有重大利益。从Philip 案开始,仲裁庭开始采用新的认定进路,即过对“法庭之友”宗旨、工作内容等的审查来判断其是否与争端有重大利益关系。①See Philip and Others v.Uruguay,ICSID Case No.ARB/10/7.对重大利益的最新解释进路是一种程度性的解释。在Apotex案中,仲裁庭要求“法庭之友”证明其利益超出一般性利益构成重大利益。“法庭之友”负有“重大”程度的证明责任。
第四,国际投资仲裁案件大多涉及公共利益问题。早期案件中,只要“法庭之友”证明其可能受到投资仲裁裁决的影响,“法庭之友”意见即可被视为与公共利益相关。但这种认定思路导致仲裁庭对公共利益的过度宽泛解读,“法庭之友”的参与门槛降低,当事方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充分保护。随着实践的发展,明确特殊利益的认定思路在公共利益的审查中被采用,“法庭之友”是否涉及公共利益的解释标准更加具体化与明确化。
第五,“法庭之友”提交意见是否会扰乱仲裁程序或给当事方造成不合理负担,被视为“法庭之友”参与的一个消极考量因素。在对该考量因素的审查中,仲裁庭享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不特定的各种因素都可能被纳入仲裁庭的考量范围。此外,以Philip 案和Apotex 案为例,近年来仲裁庭更是加大了对该考量因素的审查力度,以充分保障当事方的合法权益。
第六,独立性。在早期的案件中,仲裁庭并未对“法庭之友”的独立性问题予以过度关注或专门审查,第一次对“法庭之友”的独立性问题做出直接回应的案件是Berrhard案。以此案为起点,在独立性的判断中,出现了较多且相对混乱的独立性认定标准,资金、技术、法律、合作关系以及与当事方之间的联系等都可以用来判断独立性。这导致仲裁庭对独立性的审查范围不断扩大,几乎任何相关事由都可以被用于启动独立性的审查。此外,在独立性审查的启动主体上,仲裁庭不仅会依据“法庭之友”自我披露的资料主动审查,实践中的独立性审查还会因当事方的异议而启动,投资者与被诉东道国都有可能对“法庭之友”的独立性提出异议。
(二)“法庭之友”资格认定的难题
笔者认为,国际投资仲裁“法庭之友”资格认定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四种类型:第一,概念性问题,即因基本概念不明确导致的解释混乱。例如,何为重大利益?第二,根本性问题。它们是公私法益冲突的隐形表现。例如,如何处理投资法中的非投资性问题?对根本性问题的态度决定了案件的处理结果。第三,结构性问题,即制度或规则架构设计中存在的问题。第四,“法庭之友”资格认定实践中出现的、未被解决的新问题。概念性问题是“法庭之友”资格认定中的常见问题,由于要对概念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十分困难,如何认定往往由仲裁庭进行个案裁量。因此,本文不讨论概念性问题,重点关注“法庭之友”资格认定中的根本性问题、结构性问题以及新问题。
1.根本性问题:投资活动中的非投资性问题
“法庭之友”资格认定的根本性问题与“投资法如何处理非投资性问题”这一隐性问题密切相关。虽然这一根本性问题并非“法庭之友”资格认定案件所独有,但仲裁庭对根本性问题的态度决定了案件的处理结果。
“法庭之友”参与的投资仲裁案件中涉及众多与外国投资行为相伴而生的非投资性问题。国际投资、环境等内容自然整合于一个投资仲裁案件中已成为一种常态。①See Huiping Chen,The Role of Amicus curiae in Implementing the Human Right to Water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29 Comparative &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454-463(2020);黄世席:《国际投资争端中投资规则与人权规则适用的冲突与挑战》,《当代法学》2018 年第4期,第119-133页。例如,Biwater 案就涉及投资与水权问题,Bernhard 案关涉投资与土著居民人权。②See Bernhard and Others v.Zimbabwe,ICSID Case No.ARB/10/15.事实上,在一个关涉广泛公众利益的“法庭之友”案件中,对争端做准确且独立的定性并非易事。非投资内容与投资内容的交织与模糊状态给仲裁庭造成了争端范围界定上的释法难题。
国际投资法虽然是一个专门的制度,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根植于国际法律秩序中,投资法与国际法其他子领域之间有着密切联系。③See Freya Baetens et al. (eds.),Investment Law within International Law: Integrationist Perspectives 132(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非投资性问题与投资问题往往以一种相互交织的状态在一个案件中出现,难以分割厘清。例如,非投资性问题是否属于与争端主题有关的事项,就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非投资性问题可被视为外国投资活动的“孳息”。如果仲裁庭不将此类非投资性问题纳入争端范围内,但事实上这些问题的确与投资问题相伴而生;如果仲裁庭将与公共利益有关的非投资性问题纳入争端范围内,则可能导致投资仲裁对公共利益的扩大保护,投资者的私人利益可能受到侵害。事实上,即便仲裁庭根据不同案件的具体情形做出公私利益的权衡取舍,得到一个令各方都满意的解释也非属易事。
2.结构性问题:资格认定考量因素间的潜在冲突
结构性问题属于规则或制度设计中的隐含问题,典型表现就是规则间的潜在冲突。“法庭之友”资格认定中的结构性问题以独立性与重大利益关系之间的冲突最为典型。Bernhard 案仲裁庭就曾指出,独立性要求与重大利益关系要求制造了一种潜在的紧张气氛。④See Bernhard and Others v. Zimbabwe, ICSID Case No.ARB/10/15, Procedural Order No.2, para.62.
事实上,投资争端中“法庭之友”代表的往往是受到外国投资活动影响的东道国,其利益受到投资争端的影响也是必然的。但问题在于,“法庭之友”与社会之间必然发生的利益联系可能影响独立性的判断。位于东道国境内、受外国投资活动影响的当地社区或人口与东道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法庭之友”与其代表的社会之间的必然联系、与东道国之间的间接联系,都可能被解释为欠缺独立性。因此,如何理解“法庭之友”是否具有独立性,还涉及重大利益关系的考察。然而,要想做出明确区分绝非易事。
3.新问题:“法庭之友”参与仲裁产生额外费用的负担问题
“法庭之友”参与的费用负担问题是投资仲裁中“法庭之友”资格认定中出现的新问题。ICSID 仲裁规则新一轮修订也对该问题进行了讨论,但由于该问题牵涉利益复杂,最终并未达成一致。
从“法庭之友”参与的费用负担的仲裁实践来看,第一次提及费用负担的案件是Biwater 案,但该案仲裁庭并未对“法庭之友”做出收取费用的命令。仲裁庭认为,接受“法庭之友”的意见可能会增加仲裁程序的总费用,从而给争端的一方或双方产生额外的负担。①See Biwater v.Tanzania,ICSID Case No.ARB/05/22,Procedural Order No.5,para.62.Philip 案首次明确仲裁庭有权命令“法庭之友”支付因其参与产生的额外费用。②See Philip and Others v.Uruguay,ICSID Case No.ARB/10/7,Procedural Order No.3,para.31.此外,Infinito案等多个案件也涉及费用负担的问题。③See Infinito v.Costa Rica,ICSID Case No.ARB/14/5,Procedural Order No.2,para.19.
ICSID仲裁规则新一轮修订文件曾对“法庭之友”参与的费用负担问题进行过讨论。欧盟委员会在多个案件中因拒绝提交参与费用而未能顺利提交“法庭之友”意见。因此,欧盟委员会认为,ICSID仲裁规则第一份修订文件对“费用负担”问题的措辞不够精确,理论上会导致“法庭之友”除了要承担自己的费用外,还需要承担当事方的费用。这种结果将有悖于仲裁庭、普通法院以及其他国际法院和法庭的现行惯例,因此,应当遵循“法庭之友”只需要承担其自身费用的一般原则。另一方面,这种做法甚至可能会对“法庭之友”的参与产生“寒蝉效应”,对其参与投资争端解决程序构成障碍,从而导致与希望程序更加透明的意图相反的结果。④欧盟主张对第48(4)(c)条的措辞作相应调整。See ICSID, Rule Amendment Project-Member State & Public Comments on Working Paper # 1 of 3 August,2018, https://icsid.worldbank.org/sites/default/files/amendments/Compendium_Comments_Rule_Amendment_3.15.19.pdf,visited on 5 August 2022.此外,强制“法庭之友”支付费用将阻碍其参与,从而对仲裁庭全面了解争端的能力产生不利影响,最终影响仲裁庭做出适当和一致的裁决。⑤See ICSID, Rule Amendment Project-Member State & Public Comments on Working Paper # 1 of 3 August,2018,p.317.
笔者认为,“法庭之友”资格认定中的释法难题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投资仲裁中公私法益的冲突,而释法的根本目的也是为了通过衡量各方的利益冲突而得到和平的结果。
五、“法庭之友”资格认定中的法益保护方法
从“法庭之友”资格认定的实践与发展趋势看,仲裁庭对公私法益的衡量可能会产生两种后果:一是过度维护投资者私益而导致公共利益欠缺保护;二是仲裁庭无法在冲突法益间进行适度衡量,导致法益衡量工具的滥用。为此,一方面,笔者尝试引入比例原则与裁判结果取向方法,为实现法益保护提供宏观方法论上的指导;另一方面,针对“法庭之友”资格认定中的难题提出具体微观的解决方案。
(一)法益保护的方法论指导
比例原则和裁判结果取向方法对于“法庭之友”资格认定中的法益保护原则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比例原则为法益衡量设置了必要限度,是防止法益衡量工具滥用的有效方法。裁判结果取向方法可以弥补法益衡量的狭义法益结构,关注法益衡量的社会整体效果,增强法益衡量的社会正当性。
1.适用比例原则,防止法益衡量工具滥用
比例原则(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源于古老的分配正义思想,早期在宪法、行政法以及民法等领域的司法实践中都有适用,①参见钱福臣:《解析阿列克西宪法权利适用的比例原则》,《环球法律评论》2011 年第4 期,第47-58 页;黄学贤:《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法律科学》2001 年第1 期,第72-78 页;郑晓剑:《比例原则在民法上的适用及展开》,《中国法学》2016年第2期,第143-165页。晚近出现在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以及国际公法等领域的裁判实践中。比例原则通常由妥当性、必要性以及相称性原则构成,其中相称性原则是典型的法益衡量原则,因而也是法益保护的重要内容。②参见张明楷:《法益保护与比例原则》,《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第94-95页。
比例原则对于“法庭之友”资格认定中的公私法益保护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在国际投资法的语境下,比例原则往往被当做一种条约解释的辅助手段,发挥着平衡利益冲突的作用。③比例原则大多被适用于与征收有关的裁判中,比例原则在国际投资领域的首次适用可追溯到Tecmed诉墨西哥案。参见买木提明·热西提、沈伟:《间接征收语境下公共利益的多重维度及比例原则的解释路径》,《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第82-99页。由于比例原则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只要存在不同利益间的冲突且仲裁庭享有自由裁量权,它就有适用的空间。④参见韩秀丽:《论比例原则在有关征收的国际投资仲裁中的开创性适用》,《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第118-121页。
比例原则通过为“法庭之友”资格认定中的法益衡量运用设置必要的限度,约束仲裁庭自由裁量,避免仲裁释法中出现过度保护投资者私益或过度维护公共利益的倾向,促进法益保护。在运用比例原则指导“法庭之友”资格认定时,需要考虑妥当性、必要性以及相称性三个问题。第一,仲裁庭采取的解释方法或审查方式是否实现“公益保护不得侵害合法私益”目的的适当手段?第二,为了实现“公益保护不得侵害合法私益”的目的,对某些认定因素的审查以及解释是否有必要?第三,为了维护投资者合法私益而对“法庭之友”参与进行限制时,仲裁庭维护的私益是否大于所损害的公共利益?
2.采用裁判结果取向方法,关注裁决的社会整体效果
法益衡量过程采用裁判结果取向方法,一般先有结论后找法律条文根据,与从作为大前提的法律依据出发推导出结论的概念法学方法正好相反。①参见梁上上:《利益衡量论》,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46页。法益衡量方法的根本缺陷在于,它只关注当下的、现实的法益,将利益狭义地界定为当事方的具体法益,而缺少对利益结构的整体衡量。裁判结果取向方法可以弥补法益衡量结构的狭义性,关注法益衡量的社会整体效果,以增强法益衡量的社会正当性。
虽然裁判结果取向方法尚未在国际投资仲裁的背景中予以讨论,但国际投资仲裁裁决仍属于广义的司法决策范畴,出于对裁判合法性与机制正当性的考量,投资仲裁庭在裁判过程中仍可能需要关注案件裁判结果的影响。“法庭之友”参与的投资仲裁案件更是如此。由于“法庭之友”代表公共利益,“法庭之友”意见被视为公众意见的晴雨表。②See Joseph D. Kearney & Thomas W. Merrill, Influence of Amicus Curiae Brief on the Supreme Court,148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785(2000).在是否批准“法庭之友”参与投资仲裁程序、是否批准“法庭之友”提交意见以及是否采纳“法庭之友”意见等问题上,仲裁庭裁判释法需要兼顾裁判预期实现的社会效果。在“法庭之友”资格认定的过程中,裁判结果取向方法可以通过嵌入和调适的方式对法律条文解释方法产生补正效果,从而最大程度防止裁判结果损害法治权威。
然而,裁判结果取向方法并非可以无条件地适用。例如,它只能作为法律条文解释方法的补充与例外。即当法律条文解释可能有失偏颇或无法解决利益冲突时,裁判结果取向方法才有适用的空间。③参见陈辉:《后果主义在司法裁判中的价值和定位》,《法学家》2018年第4期,第44页。在“法庭之友”适格性问题的解释中,仲裁庭应当遵循法律条文为主的法律解释方法,当仲裁庭无法做出判断时,裁判结果取向方法方可适用。
(二)资格认定难题的具体解决方案
1.非投资性问题的“宽进”与“严出”
“宽进”思路以保障“法庭之友”的参与权益为目的,通过“法庭之友”参与规则的完善以及参与程序的便利化等方式,鼓励并吸引关注投资活动中的环境等非投资性问题的“法庭之友”提出参与案件的申请,增强投资仲裁机制的透明度与合法性。
“严出”思路以确保“法庭之友”的必要实质参与为目的,通过仲裁庭对争端范围的严格解释,提高非投资性问题进入案件实质审理程序的门槛。一方面,严格审查“法庭之友”意见能否协助仲裁庭解决争端范围内的事实或法律问题。而对于如何认定争端范围,可以实行从争端主题到争端具体内容“两步筛选”的审查方式。首先,将“法庭之友”意见限定在“与争端主题有关”的范围之内;在满足“与争端主题有关”的要求后,再对“法庭之友”意见是否与争端当事方的异议或主张相关进行认定。
2.独立性的披露与重大利益的明确界定
“法庭之友”资格认定要件的潜在冲突以独立性与重大利益关系之间的冲突最为典型。由于“法庭之友”与其所代表的社会之间必然发生的利益联系可能影响其独立性判断,因此,对“法庭之友”是否具有独立性的认定,还牵涉对“法庭之友”重大利益中利害关系的考察。笔者认为,独立性与重大利益关系之间潜在冲突的缓和,有赖于独立性的充分发现与重大利益标准的明确界定。一方面,对“法庭之友”信息披露义务的强化,可以有效增强仲裁庭对“法庭之友”独立性的判断。投资仲裁实践中,仲裁庭对“法庭之友”独立性的判断往往依据当事方的异议来实现,因此,如果当事方未提出对于“法庭之友”独立性的异议,仲裁庭只能依赖“法庭之友”披露的自身信息。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强化“法庭之友”的信息披露义务,要求其对身份信息、关联关系以及资助情况进行详细说明,必要时可要求第三方对“法庭之友”的独立性出具证明(但这一举措也会增加成本)。此外,对于不履行充分披露义务的“法庭之友”,仲裁庭可以拒绝其提交意见,以强化不充分履行披露义务的不利后果。
另一方面,对重大利益做出明确界定。笔者认为,对重大利益进行明确界定,可以解决对重大利益宽泛定义所导致的各考量因素间冲突的问题。对重大利益考量因素的界定需要明确三个问题:第一,何为“重大”?第二,何为“利益”?第三,“法庭之友”与其他主体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构成重大利益关系?投资仲裁实践为以上问题提供了部分解决思路。例如,Apotex 案将重大利益解释为超出一般的利益,要求“法庭之友”的组织宗旨要与争端主题有关等。虽然,这种解释方式使得含义宽泛的重大利益得以清晰,但在进行“重大”或“利益”的界定时可能陷入解释学循环,例如还需要对何为一般利益进行二次解释。为此,笔者认为,对重大利益的解释可以采取“含义界定”与“正负面清单列举”相结合的方式,或将某些容易存在争议的情况排除在重大利益范畴之外,或明确某些出现频率较高的情况属于重大利益。
3.费用负担的“预防”与“程度”认定
“法庭之友”参与的费用负担问题是仲裁庭进行“法庭之友”资格认定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法庭之友”的参与可能会以一种不成比例的方式增加仲裁成本,因此,仲裁庭负有确保“法庭之友”参与不会扰乱仲裁程序,且不会给当事方带来不必要的费用负担或损害的责任。欧盟委员会作为“法庭之友”参与的多个案件,都出现了因费用负担问题而最终未能提交“法庭之友”意见的情况。①See B.V. and Others v. Spain, ICSID Case No.ARB/13/31; Eiser and Others v. Spain, ICSID Case No.ARB/13/36; SolEs Badajoz GmbH v. Spain, ICSID Case No.ARB/15/38; Watkins Holdings S.àr.l. and Others v.Spain,ICSID Case No.ARB/15/44.
笔者认为,对于“法庭之友”参与的费用负担问题可以通过设置预防措施和程度认定相结合的方式予以解决。预防“法庭之友”参与可能产生的费用负担问题,已在参与规则中有所体现,例如,对“法庭之友”提交书面意见的页码等进行限制,仲裁实践中还存在通过“法庭之友”提交的文件与争端主题相关性的审查,确保当事方的合法权益不会受到损害。
即使可以采取间接的预防措施防止或减少费用负担问题的出现,但仍需要有直面回应费用负担这一问题的对策。笔者认为,对于费用负担问题的认定可以采用程度认定方法,即通过对案件影响程度和“法庭之友”意见对案件审理的贡献两个程度指标来处理费用负担问题。只有在案件可能产生较大社会影响或牵涉重大利益关系,且对仲裁裁决构成较大贡献的“法庭之友”才可以免予缴纳费用。“法庭之友”参与的费用可以由仲裁庭裁定由案件败诉一方承担或由当事方共同承担。但是,这一以程度为认定标准的处理方法也会给仲裁庭的自由裁量带来新的问题,例如如何界定“较大社会影响”以及如何认定“贡献程度”,这些问题都有待在实践中寻找答案。
六、结语
国际投资仲裁中“法庭之友”资格认定的本质是公私法益冲突的衡量过程,是在保障投资者合法私益下对“法庭之友”必要参与权利的有限赋予。法益衡量理论为投资仲裁中“法庭之友”资格认定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根本性的解释框架。法律事实的存在为法益衡量提供了一个可依循的客观标准。通过对案例研究可以发现:第一,由于仲裁庭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仲裁庭对不同案件适用不同的认定标准,对同一标准的解释也存在几种不同的释法思路;第二,仲裁庭通过扩大审查范围或严格解释等方式,对“法庭之友”资格的审查认定趋于严格;第三,存在隐含于“法庭之友”资格认定过程中且易被忽视的根本性问题、结构性问题以及费用负担问题。
笔者认为,“法庭之友”资格认定中的释法难题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投资仲裁中公私法益的冲突,而释法的根本目的也是为了通过衡量各方的利益冲突而得到公平的结果。在比例原则与裁判结果取向方法的指导下,对投资争端中的非投资性问题可采用“宽进”与“严出”的方法;对“法庭之友”资格认定考量因素间潜在冲突的缓和,有赖于独立性的充分发现与重大利益标准的明确界定;对于“法庭之友”参与的费用负担问题,可以通过设置预防措施与程度认定相结合的方法予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