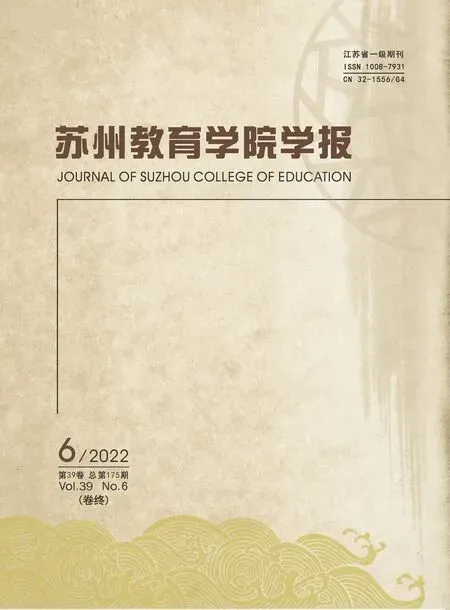未能化蝶的红蚕茧:朱鸳雏短篇小说论
吴 佳,孙 超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朱鸳雏(1894—1921),名玺,字尔玉,号孽儿,别号银箫旧主,上海松江人,近现代报人、小说家、文学家,南社社员。朱鸳雏自幼失怙,为松江孤儿院院长杨了公义子。聪颖好学,师从泗泾马漱予学韵语、从杨了公研文史。为诗清丽茂美,交游渐广,获当地文人推重。又好新剧,相貌娟好如女子,所扮旦角楚楚可人,与李子韩所饰生角珠联璧合,宣传新思想,耸动一时。喜作说部,以松江名小说家姚鹓雏为师,所作文言小说能得姚氏趣味。因鹓雏为林纾弟子,鸳雏亦成林纾辅翼。鸳雏小说作品为沪上报刊所青睐,渐露头角,曾由周瘦鹃汇辑其数十篇小说为《红蚕茧集》[1],列入大东书局出版的“紫罗兰庵小丛书”;又与姚鹓雏合著《二雏余墨》行世。鸳雏经杨了公、姚鹓雏介绍加入南社,不久因社内的唐宋诗之争而被南社领袖柳亚子公开开除出社,受此打击,一蹶不振,郁郁而终。多年后,柳亚子发表《我和朱鸳雏的公案》,颇悔年少意气,愧对友人。除《红蚕茧集》《二雏余墨》外,鸳雏还著有中长篇小说《峰屏泖镜录》、《玉楼蛛网》、《桃李因缘》(和铁冷同著)、《帘外桃花记》、《赭楼第一恨》;翻译小说《银纛记》(与季恂同译)、《这朋友娶过妻了》;杂文《上海闲话》;诗词散见于《二雏余墨》《红蚕茧集》《痴凤血》。后有时希圣拾阙补遗,整理出版《朱鸳雏遗著》。
目前,学界对朱鸳雏及其作品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专论仅有一篇,即芮和师的《“云间二雏”评说—江苏通俗文学作家姚鹓雏、朱鸳雏》。该文主要介绍姚鹓雏和朱鸳雏的生平经历及各自创作,将二人简单对比后,得出姚鹓雏比朱鸳雏的“心境似更为开阔,处世更为成熟,文学活动更为活跃,其诙谐幽默也为朱所不及”[2]的观点。毫无疑问,该篇论文首次将朱鸳雏纳入通俗文学研究领域,具有首创意义,但是对其作品研究大多停留在简介层面,有待进一步深入。另外,在南社研究相关论著中也有一些对朱鸳雏生平、创作的简单介绍,尤其关注他与柳亚子的笔战公案,如有《成舍我与南社“朱柳论诗”公案》[3]、《“南社内讧”新探》[4]等。这些论文都以笔战公案为研究视角展开对这段历史的溯源与分析,却没有涉及朱鸳雏的文学成就。基于以上研究现状,本文拟从文体与思想两个方面对朱鸳雏的短篇小说展开深入探讨,以期客观认识其创获与缺失,并尝试评估其推动传统短篇小说现代转型的独特贡献。
一、笔记小说的创新变体
朱鸳雏的短篇小说创作深受林纾、姚鹓雏的影响,在赓续文体互参传统的同时,借鉴域外小说技巧以寻求新变,因而,其文体呈现出一种有别于传统的变异形态。他的创作大多可视为传奇化的笔记小说,使用文言,假托实录,又颇具传奇性。
(一)文体互参:传奇化的笔记小说
周瘦鹃在《红蚕茧集·弁言》中称其为“旧作笔记”[5],实际上该小说集所收作品大量使用传奇笔法,富有一定的传奇性。“传奇”自唐人小说而来,强调情节的奇幻、人物的特异,追求叙事的“非常态”以及由此形成的浪漫风格。扎根于传统的朱鸳雏直接取法唐人小说,大量使用传奇笔法,以古求新,创作了一篇篇传奇化的笔记小说。
朱鸳雏的短篇小说或取材奇特,如《感逝记》,其自述“余欲造一有统系而叙述近古之小说,患无佳材,复苦模拟,盖读英国哈葛德氏所造,辄能摹及千年以上之人物,成为巨著,以震奋国人,知返古亦难矣哉。曩在故乡于旧家书觅得清道光人马晋之笔记,晋之参与洪杨之巨役,记出暮年,语多自悍,玩其词意,似牵涉女娲者,兹编其意而叙之”[1]59-60。再如《珰札记》,取材于邮差口述,小说中言明“职务之暇,常来问字,吾乃询彼职务上有无趣事,足助吾文者”[1]29。该篇时代感强烈,邮差作为当时的新兴职业,走街串巷,承担起传递信息的职责,而他们也成为诸多奇闻异事的发现者、见证者。《天刑记》则代文中主角记事,所谓“拜先生等赐也”[1]92,以获得小说的“似真”效果。或以神奇怪异之事入小说,想象丰富,给人以不可思议之感,如《炙骨记》,“余”在道观紫霞宫神遇已卒将士冯成材的魂魄,魂魄托“余”收其骨以归葬,这显然是唐传奇影响下的传统遇鬼题材。再如《汉水记》中的主人公为力证真情,跳水自尽,被人救上来后进入“鬼境”[1]51,营造出一种玄幻神秘的氛围。即便是平平无奇的爱情故事,也往往增添意外巧合作为情节之奇,使小说跌宕起伏,如《司书记》写的是徐子瑞意外收到一封寄错了的情书,按照常理,应该把信件退回邮局或作其他处理,最不可私拆他人信件。可徐子瑞夫妻俩却乘着兴致假托本尊代写回信,时而绞尽脑汁如何妥帖回复,时而揣度对方心意,乃至将对方寄来的食品一并收下自用,一来一往无不有趣。当然,最后这场闹剧随着收、寄件人本尊的相见而落下帷幕,偷取的乐趣也就戛然而止了。《生还记》光听名字便有引人之处,该篇小说写陆锐不顾家人反对,自愿当兵却又当了逃兵,怕妻子生气,便假借陆锐同乡身份报陆锐之丧来与家人重逢,没想到妻子早就看穿了他的伎俩,最终夫妻二人冰释前嫌。《拾遗记》写杨剑云女士游园时拾得钱包,本想私吞,但为了有所图而“好心”归还失主王子威,最后竟然凭借“美名”与王子威结为伉俪。
朱鸳雏的上述作品重在言情,充分诠释了近代小说题材从官场向情场的转变,作者在小说中玩转情场,描摹世间情态,为读者展现了一个五彩斑斓的至情世界。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朱氏短篇小说虽效唐传奇而首重言情,但所言之情已从男女之情扩大到广泛的世俗之情。如《干蝶记》《战瘢记》记叙友情;《碎牕记》《劳工记》《天刑记》《珰札记》描摹世态人情;《怨始记》《芳时记》展现三角恋情的矛盾;《散学记》表现师生之情。即便是写爱情的“至情之作”[6],也无不写尽情中的趣事、憾事、琐事、奇事、巧事等,真可谓极尽情事之描摹。
(二)借鉴西方:趋新求变的叙事技巧
晚清以降,国门洞开,翻译文学逐渐为国人重视,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一座桥梁,为正处于迷茫的中国文学界提供了不少可资借鉴的文学资源。作为当时的“后浪”,朱鸳雏颇喜林译小说,时常“仿效林译小说的体裁”[7]进行创作,有意借鉴域外小说,革新叙事技巧,因此,他的短篇小说呈现出一些迥异于传统的现代性特征。
首先,朱鸳雏的短篇小说在叙事视角上有别于传统。有些作品改第三人称叙事为使用第一人称进行叙事,变“他叙式”为“自叙式”,如《投荒记》《珰札记》《芳时记》《天刑记》中的“吾”,《画心记》《战瘢记》《感逝记》《卧雪记》中的“余”。使用第一人称“自叙”能最大程度地消除读者与文本之间的距离感,增强读者的情感体验。此外,朱鸳雏还大胆创新,将“他叙”与“自叙”相结合,颠覆传统的单一型叙事方式,《衾献记》的开头由“自叙”而起,表达“吾”对佳偶的看法,随即用“他叙”叙述主人公廖卿谋与夫人桐英享蜜月之“乐”的故事,中间又插入“自叙”,明确该故事的真实性,后又转入“他叙”作结。叙事视角的频繁转换,给读者上演了一出男人婚后坦白婚前不堪的滑稽戏码,使整个故事波澜起伏、真实有味。
其次,朱鸳雏还采用了书信体的叙事手法。书信体、日记体由来已久,属于一种比较私密化的文体,若是借助书信、日记来详细叙述故事无疑显得“太笨重而不自然”[8]。但是随着域外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冲击以及小说本身地位的不断提高,文学界开始尝试用书信体、日记体来翻译和创作小说。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开风气之先,随后包天笑的《冥鸿》、徐枕亚的《玉梨魂》等都尝试在小说中加入书信、日记元素以革新小说体例,呈现出不一样的观感。朱鸳雏在耳濡目染中也接受了前辈们的创作理念,以开放的姿态自觉进行实践。《战瘢记》开头便点明“此记以书信叙事”[1]41,随后便将书信内容以第一人称展示出来,表达对昔日战友今日教员的无奈之情,个人情感结合书信这种新颖的体例,使小说充满了强烈的主观色彩,也增添了不少真挚深沉的情感,更容易打动人心,也为后来的新文学作家将书信、日记与“个性”的结合提供借鉴。在《司书记》中,作者有意识地将书信往来作为小说线索,并巧妙地在叙事中运用书信补充相关情节,生发故事,演绎出一场闹剧。
最后,朱鸳雏在小说中有意加强环境描写,穿插对话,改变了传统短篇小说过密的情节化叙事模式。如《汉水记》开头写道:“风过处,一园林,色葱翠如溅也,垂晚阴重,森然不复辨林中之道,林背方亭,几如深藏壑底,受园外江光,自晦暗中生其幽致,余无所见,惟林溪四鸣而已。”[1]47-48这番描写既保留了古文的简练,又生动形象地呈现出傍晚园林景色的幽静深远。《感逝记》在点明该笔记由来后,便开门见山地进行环境描摹:“记云:今日小楼一角中鬓皓齿脱,偻背作书者,即余也。一楼以外,泖水汤汤,尽日东流,不减旧时之色,细林略矗矗,山翠峥嵘,亦如往日之容,片帆来去,斧声丁丁,景地依然,而航者樵者,均已易其人。前次经过之人,与岁时俱尽,倚牕而望,则枯鸦亵柳,点缀霜天。”[1]60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这样一段环境描写为下文“余”怀念亡妻奠定了感伤的基调。《怨始记》《碎牕记》《干蝶记》等则频繁穿插人物对话,使小说的叙事节奏放缓,从而更细致地刻画人物内心真实情感,这无疑体现了现代小说意识的觉醒。还有《投荒记》《司书记》《衾献记》等继承林译小说“特叙家常至琐至屑无奇之事迹”[9],关注平常人家柴米油盐的琐屑人生以及喜怒哀乐的个人情感体验,将笔触伸向夫妻之间,用平缓的语调娓娓道出闺房之乐,平凡却有味。
除此之外,朱鸳雏的短篇小说中还提到了不少外来词汇,如英格兰、望远镜、蜜月、香槟酒、KING、外国老鬼妇、牧师、教会、女皇等,甚至还直接引用了西方名人名言。这便在传奇、笔记的文体互参中点缀了异域风情,具有特别的时代意蕴,令人耳目一新。
二、思想旨趣的现代指向
清末民初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生急剧变化的现代转型期,作为上海报人、小说家的朱鸳雏自然也被裹挟着进入了这一时代洪流,其所作短篇小说在思想旨趣方面具有明确的现代指向。具体而言,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提倡婚姻自由,反对包办陋习。在中国古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能够把素未相识的无情男女捆绑在一起生活一辈子。为求得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历代有情人不断努力地抗争。杜丽娘和柳梦梅、崔莺莺和张生、贾宝玉和林黛玉等无不为了一个“情”字勇敢地与封建卫道者斗争,而这样的“传统”一直持续到近现代。在朱鸳雏的短篇小说中依稀可见相关描写,《汉水记》中主人公怀良在父母之命与自由恋爱之间痛苦矛盾,一面是“聊畹吾爱”[1]48,一面是父亲“先相契者”[1]49,不知该“如何了者”[1]49,最后投身汉水。此小说属于当时流行的哀情小说,作者将笔触伸向人物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刻画人物的矛盾纠葛,具有一定的现代性和深刻性。怀良对爱情的坚守,以死明志的决心,令人感动,悲剧结局也颠覆了传统才子佳人小说固有的大团圆结局,凸显了凄婉哀艳的悲剧美。《病因记》中的主人公为父母媒妁所迫,娶了“不识字,好金珠,为寻常中等女,于己幸福之前途,必无佳状”[1]71的沈红珠,不过,若是贸然解旧约,“于俗不容”[1]71,若是被医生判定有精神疾病,便可爽快解约。这种行为虽有违道德,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当事人不满包办婚姻,却又不敢公然与家庭作对,只好“智取”以摆脱窘境。这与《孽冤镜》《霣玉怨》《玉梨魂》等哀情小说在思想旨趣上颇为一致,有明显的时代烙印。朱鸳雏的《自媒记》还将批判矛头直指“以媒为业者”[1]105,揭露了他们反对婚姻自由乃是为谋生考虑,并非出于对传统规矩的守护。因此,这类人很容易妥协,只要满足其私利就会转变观念,正如《自媒记》结尾媒人老翁所为—“更不斥自由结婚之无耻,意谓世间但有吾受媒金之事,宁有吾女嫁人而亦授媒金于他人者?且我立业艰难,彼自由结婚去,不破吾资,吾女自媒,殆体亲意者欤”[1]107,其着眼点正是金钱利益。
第二,主张男女平等,反对妓女、奴婢制度,抨击卖女为妾等现象。正如《卧雪记》所言:“徒以所谓玉林女士者,其人足以代表吾国婢妾制度之一种事实,故契然不能邃忘,又不忍以为女流而阿之也。自来文人无以女士称及婢子者,有之,自吾之称玉林始。吾之意中,凡女子未有不齿于人之堕行者,皆可尊为女士,宁有谓贫父鬻身为婢,即为堕行耶?”[1]86自古以来婢妾地位低下,朱鸳雏有意改变此种等级差别观念,力图提高底层女性地位,因而在这篇小说中提出可尊称婢妾为女士的建议,这显然受到了西方男女平等观念的影响。在《天刑记》中,作者批判了将乡间女子卖于都市的卑劣行为,“始知农务之外,尚有卖人之生活”[1]96。公然鬻卖,最后报应在主人公父亲身上,作者认为这是“老天之施以刑也”[1]97。《返璞记》叙述了胡肃与妓女凌仙的感情故事,两人惺惺相惜,绻绻以待,但胡肃却因家室所系没法为凌仙脱去娼籍,后只能无奈分别。再见时,凌仙早已脱离娼籍,并在某村落中过着返璞归真的生活。胡肃见此,便不再打扰。这个故事让鸳雏有感而发:“环球之史……有提倡娼业者乎?乃此风之于吾国,于今为厉,盖吾见有无数执笔闻香之管仲也。吾记此文,自审幸非其类。”[1]84朱鸳雏在这里借题发挥,有力地批判了娼妓业,流露出对娼妓的同情,所谓“姹女无人欲”,“虽珠环粉染,实蠢蠢可怜者”。[1]84由此可见,朱鸳雏其实一直走在时代前列,他试图破除男尊女卑的观念,批判妓女、奴婢制度。他在《上海闲谈》中曾说:“余览遍在沪之人,有一轻视妇人之恶习惯,是亦阻碍进化之物也。”[10]既然阻碍社会进步,自然要予以抨击,朱鸳雏的上述短篇小说正是其倡导男女平等新风尚在文学中的表现。
第三,描写上海都市生活,暴露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阴暗面。朱鸳雏的短篇小说除《画心记》《战瘢记》分别以杭州和南京为叙事背景外,其他小说聚焦的都市主要是上海。如果说《画心记》描绘的杭州充满诗情画意,是中国传统城市的代表,那么其笔下的上海则光怪陆离、富有现代性。如《劳工记》讲述“吾”的同学姚君健离开家乡、离开爱人真卿前往上海,却“堕落于沪之勾栏”[1]76,沾染了恶习,最后无奈做了一名拉车夫。作品深刻揭露了上海这朵“恶之花”让多少清白人士移了性情,变得肮脏至极。同时,小说也巧妙地讽刺了那些空喊“劳工神圣”口号的人,故事结尾当真卿发现拉她的车夫是姚君健时惊骇狂奔,而车夫不明所以故而问道:“适君非高唱劳工神圣者欤?吾即真实之劳工耳。夙为君好,奈何鄙之?”[1]78接着小说通过复调叙述加深这重讽刺,当真卿充耳不闻入室后,同室姊妹看她神情恍惚而安慰说:“真卿中雨矣!君为劳工神圣奔走,将来必得善果也。”[1]78-79这些叙述真实地反映了现代都市的复杂性,也艺术化地呈现了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城市居民特有的迷惘心态。再看《天刑记》,小说中的童养媳阿金从小在乡间长大,“以溪水为妆镜,趺座梳头,觅野花以簪其发”[1]94,她不知道上海在哪里,与未来的丈夫“吾”也相处甚好。可这样一个淳朴天真的少女去上海后却愿意做富人之妾,足见金钱与现代都市生活的魔力。不可否认,近代上海是一座经济较发达、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但也处处充满了人生陷阱,稍不留意即会堕入欲望深渊。“沪为五方杂处之地,自光绪末叶以迄宣统,社会之怪现状,不可殚述。曩以为文明之中心点者,渐易而为野蛮之中心点矣,姑举数端言之。奸淫也,拐骗也,卷逃也,盗劫也,私盐私烟也,暗杀明杀也,窃犯赌犯也,赖婚重婚也,无日而无之……而迁居于沪者,蜂屯蚁聚,纷至沓来,一若自沪以外,曾无一片干净土足安其身者。”[11]朱鸳雏的这些短篇小说宛如都市照妖镜,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现代生活启蒙的作用。再看《媪变》,小说写一乡村老婆子经人介绍到上海一富贵人家做帮工,却为那里的奢华所熏染,逐渐变得养尊处优、嫌贫爱富。后来这户人家破产,老婆子便另寻他处,接连寻了几个,都觉得不如原先雇主好,让她没处捞油水,只能被解雇回家养老。可惜她的女儿女婿早就被她养成好吃懒做的性格,连老婆子得了风寒也不愿给她医治。老婆子临死前忏悔道:“我是个乡间老嬷子,苦吃苦做惯的,不道看着没相干的奢华,养成了那爱富轻贫的脾气,女儿女婿也吃用惯了。懊悔负着无名气,断送了老命。我死之后,你们没了十块八块钱津贴,便去做乞丐我也顾不得哩。”[12]这篇小说的社会意义深刻,有一定的现实批判力度,让读者看到大城市如何一步步改变了乡间老妇的性情。古语云“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大都市的畸形繁华不断地勾起人们内心的物欲,那些意志力薄弱的人轻而易举地就受到恶的影响。读者观此,也许心中就警惕起来,这也正是朱鸳雏及其他民初小说家撰写同类型小说的意旨所在。
三、未能化蝶的红蚕茧
综合文体创新与思想进步两方面来看,朱鸳雏以复古又不完全拟古的方式创作了一篇篇似旧还新的传奇化笔记小说,成为林纾、姚鹓雏等人短篇小说创作的辅翼。他既继承传统,以传奇笔法写情,又能别开生面,在思想内涵、叙事手法上加入新元素,体现出一定的现代性,“为长期停滞的中国短篇小说输入了新鲜血液,打开了一条生路”[13]154,成为推动民初小说现代转型的一员。此外,朱鸳雏作为南社成员,其冶传统与现代为一炉的短篇小说创作响应了包天笑、王钟麒等一批南社小说家融中西、新旧于一体的文学实践。研究朱鸳雏及其创作,对推动南社小说研究也有一定的意义。遗憾的是,鸳雏才多命薄,英年早逝,在短篇小说创作上还未能形成自己成熟的特色,当时有人对此惋惜道:“实我国著作界之大不幸。”[14]
朱鸳雏的短篇小说生前主要发表于《新世界》《世界画报》《小说画报》等流行报刊上,鸳雏逝后周瘦鹃将其汇编为《红蚕茧集》,由大东书局于1923 年12 月出版发行。该集共收录短篇小说23 篇,并附录诗词60 首。据周瘦鹃所言,“篡其旧作笔记,汇为两卷,曰银箫集,曰红蚕茧集”[5],每篇均以某某记名,如《投荒记》《画心记》《坠玉记》等,“因复合两卷刊为单本,统名之曰红蚕茧集”[5]。单行本最终统名为《红蚕茧集》有特别的寓意:一是集中所收小说实是作者抽血丝而作成之“红蚕茧”;二是集中所收小说多描述男女主人公困于情的状况,类似于春蚕吐丝、作茧自缚;三是有感于朱氏早逝,遗憾其作品未臻成熟,终为红蚕茧而未能化为彩蝶。
综观朱鸳雏的生平,本文认为其创作短篇小说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其敏感多情的内心驱使他通过这些作品来构筑一个特别的至情世界,然而他过于沉迷其中,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作品题材之拓展,对比其师姚鹓雏的短篇小说“或写情场、或言官场、或谈江湖,才子佳人、侠客异士、王公幕僚充斥其间”[15],这一缺点尤其明显。加之早逝,鸳雏的短篇小说创作还未能脱尽摹仿的痕迹,在文体及艺术上尚未能融通古今中西,在思想方面有着其师法对象身上同样的“时代病”—只是揭露社会的黑暗和扭曲,不曾提供任何解决方案。但从朱鸳雏已然表露的天赋才华来看,假以时日定会成一大家。因此,无论是当时师友,还是了解他的读者,一览其短篇小说遗集便自然会生出红蚕茧未能化蝶之憾。如痴佛所说“鸳雏的可惜,比屈原还要深一层”[16],寂寞徐生亦哀惋道:“今闻朱鸳雏作李长吉之赴玉楼,小说界又弱一个,当不仅鹓雏闻之而哀恸靡已者也。”[17]
历史长河中有多少像朱鸳雏这样名不见经传而被淹没的文人,他们零星的作品却对艺术发展有着重大贡献,他们留下的文学遗产值得我们正视和重视。正如陈平原评价清末民初的小说家所言:“这一代作家没有留下特别值得夸耀的艺术珍品,其主要贡献是继往开来、衔接古今。值得庆慰的是,谁要是想探讨中国现代小说与古代小说的联系与区别、研究域外小说对中国小说的影响以及中国小说嬗变的内部机制,都很难绕开这一代人。”[1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