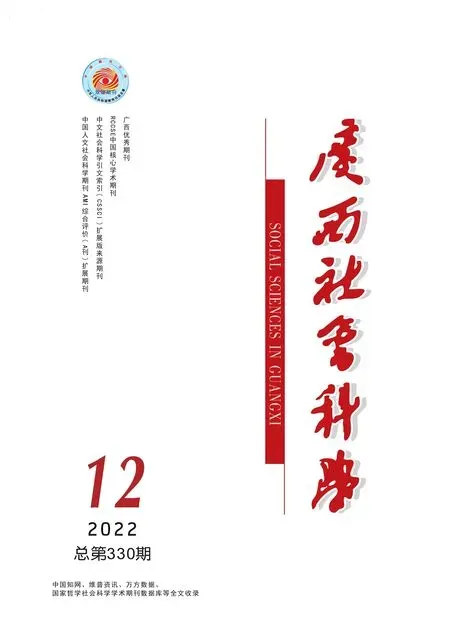中式博物学与生命共同体的价值维度
黄玲
(广西民族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21世纪,生态已然成为一个国际议题,“生态保护”与“生物多样性”的紧密关联日益凸显。联合国在2001年发表《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提出“希望在承认文化多样性、认识到人类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和发展文化间交流的基础上,开展更广泛的团结互助”,宣告了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物多样性是文化多样性在生物世界的映射,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是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关键。2021年10月1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中发出了“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倡议[1]。生态危机的出现源自人们在工业文明进程中对自然过度掠夺而造成“生态—生物—生命”的关联断裂。因生态危机是全球性的,人类需要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并建构生态文明,而建构生态文明不可脱离具有博物色彩的共生哲学[2]。博物学作为一种知识传统,涉及自然“生态—生物—文化”的整体,并以“生命共同体”为关照。因此,彭兆荣等学者认为,博物学理应成为“保护生物—文化多样性的知识范式与学科依据”[3]。
一、人文与科学:中西博物学的思想立场
博物学是人类与大自然打交道的一种古老的适应于环境的学问,也是自然科学的四大传统之一[4]。在传统理念中,人们往往倾向于将博物学归入自然科学的板块,但同时也认识到其广博性而难以归类:“博物学是对大千世界丰富多样的自然现象进行收集、分类、整理的知识,在早期,它实际差不多涵盖了除数理科学之外的所有自然科学。”[5]宇宙的广袤辽阔与自然的丰富复杂,使得在世界上不同地区生活的不同人群,都会基于地方的地理生态形成适合自我生存的知识。由此,不同地方会产生不同的博物实践、博物知识与博物传统。
西方将博物学传统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早期西方博物学的研究对象并非单纯的物种,而是关乎整体性或系统性的有机体。在《自然的观念》中,科林伍德提到古希腊自然科学含有一种把灵魂和理智理解为人与万物共有的看法[6]。在近代欧洲傲慢的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出现之后,西方博物学发生转向,18世纪出现以培根和林奈为代表的帝国进路,其核心理念是利用世界范围内的自然资源为人服务[7]。启蒙运动时期的帝国博物学家认为自然舞台只有通过移除其语言、神学、伦理等因素才能被解释。在牛顿力学支持下,植物学家视自然为无生命的,其中植物、动物包括人都可以还原为孤立的原子。这样一来,传统的博物学所强调的物种的地方性、价值性、文化性等特征就被剥离了[8]。
中国古代文明也有着深厚的博物学传统,吴冰心在《博物学杂志》中将中国博物学追溯到上古“博物之学,盖兴于上古”[9]。通过剖析《山海经》所建构的空间肌理,刘宗迪认为中国古代博物知识的产生是人类在先民狩猎、采集甚至巫师方士寻访草药等生产生活实践之“原始动机”的触发下,“对草木鸟兽的形态、习性和用途有了真切的认识”,在文字没有产生以及普及的情况下,多是在乡土社会中以方言土语口口相传的神话传说和歌谣谚语[10]。有学者将博物学定义为“关于物象(外部事物)以及人与物的关系的整体认知、研究范式与心智体验的集合”[11]。翻阅中国经典,俯拾皆可见博物知识,充盈着天地鬼神和自然万物的描述与想象,张华《博物志》是首部以博物命名的著作,既记载了山川地理、飞禽走兽、虫鱼草木、人物传记等,也收录了神话、古史、地志、名物等神奇怪诞之事物。可见,中国传统的博物集合了各种雅俗神怪,包罗万象、灵动多姿,并不具有刻板面目与森严等级。因此,古人给我们留下的博物志不仅是“经史子集”的正统学问与分类的异述和补充[12],更是我们的祖先与宇宙自然交流互动所积淀下来的生存智慧与文化遗产,应当加以挖掘和弘扬。
作为历史悠久、地大物博的东方文明古国,中国的博物学传统吸引了诸多西方博物学家的研究目光。袁剑在其译介《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中指出既有的博物学书写往往将民族国家作为单一整体,而忽视了如中国这样的大国内部的多样性,“关于边疆地区的博物知识及其历史生成恰恰是缺失或者零乱的”[13]。对我国文化传统的“人文价值”应持以自信,费孝通先生指出:“这个传统中不仅存在着滋养社会的重要价值观,而且也存在着有助于处理世界问题的智慧:‘和而不同’思想,对于克服‘世界性的战国时代’和‘文明冲突’的深层危机,造就‘美与共共’的局面,有着重要意义。”[14]有鉴于此,对中国多民族和边疆民族地区的博物传统进行搜集、整理、阐释和研究,尚有很大的空间。
彭兆荣认为,西方的博物学建立在“自然(nature)”的框架中,中式博物学则是建立在“天文—地文—人文”的完整形制中[15],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生活的密切协同、与传统农耕文明的结合[16]。由此可见,中式博物学包含着生命、生态、生物等多重维度,更显博大与包容。中式博物学的思想脉络与知识谱系中,更体现出人们对“地方知识”“民间传统”与“乡土智慧”的重视,成为植根生命深处的文化遗产。这些对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应对生态危机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化生”与“共生”:中式博物学的价值维度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类对宇宙自然的探究从未停止,对自我存在的思考孜孜以求,如太阳升降的亘古不变,如大地怀抱的生生不息,不断开启人类的生命感悟与思维认知,产生了人类生存与宇宙运行之关联性的诸多想象与实践,也由此产生了关于世界万物的认知与描述。钱穆对此做了系统梳理,他通过返回中国思想去寻找古人看待宇宙万物的方式,得出了“天人共生论”[17],指出中国的博物世界里,“万物不是被创造的,而是被造化的,所谓造化就是造与化,造意味着创造,化意味着转化,而造作即化育,即转化带来的‘生育’”[18]。因此,钱穆提出了“生生宇宙观”:“从宇宙与历史的整体上看,它们也都属于‘动’,是消融了物我死生之别的‘道’的一部分”,“天地之大德曰生。就大自然而言,有生命,无生命,全有性命,亦是同生。生生不已,便是道。这一个生,有时也称之曰仁。仁是说他的德,生是说他的性”[19]。可见,中式博物学蕴含着万物化生、“天人合一”的生命智慧,也涵括了多样共生、跨界共享的人文关怀,其价值维度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生命共同体的宇宙观:参赞化育、万物化生
在中国观念世界里,上下四方曰宇,往来古今曰宙,宇宙包容着绵络天地之大象。如《论语·阳货》有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认为人通过观察宇宙万物来掌握生存环境的规律,通过自然节律体悟生命成长的智慧。可以说,中国的博物学的关切点不在物自身,而是物象、人事与天道的参赞与化育所达至的“天地境界”。冯友兰认为“个人只有达到对宇宙的全体理解,才能真正达到知性尽性”[20],质言之,人只有将自我生命与富有生命力和创造性的宇宙自然加以联系与关照,通过理解人和宇宙全体的关系才能达成生命整体性。此种人类与宇宙交融共在的生命意识在人类古代文明中已有丰富的呈现,其对现代人而言,则是人类能够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本位经验。人类在自我生命中找到了宇宙的节奏,如日夜更替、四季变换,经过格物致知、触类旁通,便可以对自己的命运和存在的意义有更全面、深刻的认识与体悟。
(二)生命共同体的生命观:天地合德、万物共生
中式博物思想观念中,人的生命是与自然万物息息相关、与宇宙天地光光交彻的,而且不是独立的生命对应单一的物,而是天地相互交通方生万物,呈现为互联互补、交融共生的整体性。据《易经》所载,《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21]《礼记·月令》云:“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周易·否卦》之《彖》传曰:“否……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周易·泰卦》之《彖》传曰:“泰……天地交,而万物通也。”郭静云称之为“宇宙生机”:“神”来自天的恒星神光和神灵雨水,“明”则是出自地的日月火质的明形,二者皆是上下互不可缺的范畴。“神明”结合表达天地合德状态,天地合德才是万物之生机[22]。换言之,在古人的观念中,人生与社会皆取法于大自然,所以无论是在自然、人生还是在社会生活中,唯有天地之德相匹配,万物才由此化生。而人的生命深入宇宙的奥秘而显示其神性;同时又在宇宙博大精微中彰显出互动共生的生命观。《庄子·天下篇》曰:“古之真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在此,庄子的圣人生命观体现出通过对经验范畴的拓展、价值观念的加深获得身体与天道浑然合一的境界。而王铭铭则提出“人文生境”的概念,认为在现代社会中要更为重视人的创造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协调关系”,这是在调适中混合生成的有意义的整体[23]。由于人参于天地合德的化育过程,由此化生出与宇宙天道共享的生命。比起古代,当下社会的物质文明可谓高度发达,因此在人文精神上追求庄子所言之“圣人”境界并不为过,若每个生命个体都有参赞化育之意识,我们的社会也就可以具备生命共同体的生命观维度。
(三)生命共同体的道德观:通德类情、导达其仁
吴冰心提出:“上之以通德类情,下之以制器尚象,般般焉,首首焉。先民之业于斯为在矣。”[24]钱穆则认为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仅是“小言”,是“制器尚象”,真正的“大言”乃是“通德类情”,修身成仁:“若大言之,则俯仰之间,万物一体,鸢飞鱼跃,道无不在,可以渐跻于化境,而岂止多识其名而已哉。孔子教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乃所以广大其心,导达其仁。”[25]也就是说,最高境界是“万物一体”,掌握宇宙自然运行之道,把大自然万物万象的美好品质纳入人的心胸以拓其胸怀、成其仁德,是为君子,恰如“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易经》之《象传》)里的君子坦荡荡之境界。《中庸》有言:“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在此,圣人是以至诚至善的道德理想来创造生命共同体。
当今时代,人类的文明与科技已经远远高于一两千年前的古人,但古人留给我们的生命智慧依然生生不息:向宇宙自然参赞化育,在自我生命追求天地合德,与他者交往秉持民胞物与。我们从此三个价值维度来构建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以求获得生生不息的创生力量,从而激发“化生—共生—生生”这一循环互动的“文化生态系统”,以推进为工业文明所阻碍的“生态—生物—生命”之整体系统。而这些生命共同体之间亲近、和谐的共生状态,“亦有利于人类突破种族、国家以及人这个物种的狭隘观念,充分意识到在更大的命运共同体中人与人、人与自然协调演化的必要性”[26]。诚如方东美所言,“我们以平等的心情待人接物,自不难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共证创造生命的神奇”,“我们珍惜自己的生命。也当尊重别人的生命,同时更应维护万物的生存”[27]。
经济全球化正改变着人类的价值观念和思维表述,科学与文化、自然与社会本来是相互生成、紧密关联的,但在西方帝国的博物学中却形成了割裂和对立。这些引起了西方学者的自我质疑与反思。正如拉图尔(Latour)指出西方现代人基于帝国话语认为非西方人拥有的仅仅是对自然的表征,而西方人能够通过“科学知识的神启之门进入到事物本身”[28]。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把现代理性划分为工具理性(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人文理性),并把人们的行动相应地分为工具合理性行为和价值合理性行为[29]。为了规避只是通过技术和技术应用的共同性来发展文化所出现的无根的困境,一些研究后现代文化的学者指出:“只有当文化建立在规范的共同相关性、责任整体性基础上,即建立在既可分的又是共同的生活意义及基本信念基础上时,文化才可能永远有生命力……”[30]如果说,中式博物传统最初志在关心经由本土经验而产生的地方性知识,而随着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则变成批判工业文明反文化和反自然的思想资源。换言之,中国博物传统对经济全球化造成的文化同质与工业文明引发的生态危机呈现出反观、反思和反省的深刻意义,对保护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建设生态文明和生命共同体具有重要价值。
三、万物互联:信息时代的媒介生态与博物人文
信息化时代,电子作为媒介成为沟通信息的主要技术手段和交往载体,由此,文化群体的自我认知和符号象征遭受巨大的冲击和挑战。“数十年来电子传媒营造的全球化和一体化表象,世界各地的民间知识正在失传、地方语言的特色日益剥落,工业化与市场扩张令本土生活方向迅速消逝,甚至自然生态亦被破坏或改造而导致大量本土动植物品种的消失”[31]。在网络技术所构建的虚拟空间里,因具身性交往情境的消解,对抗技术理性所需的共同关联与责任整体是缺位的,更多的是个人原子式的存在与行动,个人成为网络世界里信息分布的一个节点。而要扭转这一被动局面的关键还是在人自身,“人文特质一定超越技性对人性的束缚,使得技术、文化和心性达到有机的统一”[32]。这就需要激发中式博物学传统中人的生命与宇宙自然的内在联系,帮助现代人厘清人与自然、人与宇宙的边界,重新连接被技术理性冲破的人的生命整体性。
在信息时代网络社会中,新技术和新媒介的出现造成了新的“物”,如何将这些技术的、机械的“物”与自然的、价值的“物”加以组合与运用,赋予人生命价值和可持续性发展,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新问题。媒介生态学就是用以探寻人类历史进程中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如何互动共生的尝试。马修·福勒认为,媒体生态是“一种指向情境脉络中的平行历史与能供性的描述符号”[33]。语言的多重性和描述符号是媒介生态学的关键词,这并非标新立异,而是“词与物”这一人类永恒的哲学命题在信息时代的新思考与新探求。卡西尔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34],本雅明也在《论原初语言与人的语言》一文中指出“人类精神生活的任何一种表达都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语言”,而由于传达自己的精神内容根源于万物的本性[35],因此语言存在与万物并存。换言之,对万物的言说来自人对自然宇宙的观察体验、人与万物的互动共生。“词”正是从“物”的自然属性中获得其最初的生命和灵气[36]。人类如果将世界理解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万物之间的联系沟通与信息传达就是可行的;反之,则难以达成理解与认同。诚如彭兆荣所言:“人类的文化表述和人文精神如果离开了对自然的认识、见解、启示和物化符号系统的文化表述,人文精神几乎无从生成和传达。”[37]
辩证地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科技的广泛运用所带来的“去中心化”深刻地改变了整个社会的深层结构,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注入新的内涵和特征。在媒介自觉的理念下,借助数字技术和多媒体的手段,激发词与物的深层关联与活的隐喻,激活、重建与创生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价值理性。而恢复传统博物学,彰显文化的地方性和空间性不失为一个有效路径。
人类历史上,科学的生成与博物学(自然史)是紧密相关的,二者并非泾渭分明,博物学的整体性和关照性可以突破技术理性的壁垒。在此,中式博物传统的“身体力行”能够发挥重要作用。“身体性”是由“身体由能够被复制的力,以及在它们之间内部运行的力(马克思所称其为‘价值’)所构成的过程”,是介于被归类为有机体的一方与被归类为技术体的另一方之间的一条通道[38]。因此,要达成二者的沟通,需要人们具备“参赞化育、万物化生”“天地合德、万物化生”“通德类情、导达其仁”等中式博物学思想和“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格物致知”的博物学方法论,是人们赋予其生命活动以价值与意义的知行合一。
在生物多样性这一整体视域下,稻米既是一个具有自我生命的植物种子,也是人类与自然发生交互的文化符号[39]。用中式博物学视野来考量,稻作文化凝结了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呈现为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交融的家园遗产,为世界诸多地区和人群所共享。我们尝试以中国南方壮族稻作文化的生态观念和道德伦理,来感受深蕴其中的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经验和生态智慧。
在岭南地区的左右江流域,充沛的水源、松软的土地和日晒降雨等适宜植物生长的因素,以及鸟类等动物的迁徙活动带来了物种流动迁移之后,壮族先民通过对野生稻种的发现与驯化,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创造出水田稻作的生产方式,随着与中原农耕技术的交流吸纳,逐渐实现了水稻连作。农业耕作的稳定促进聚落的定居,从而使人口增加、聚落扩大,形成了骆越族群。在古骆越人的集体记忆中,创造万物生命、教授人们耕作的人文始祖布洛陀和米洛甲,其名字中的“洛”字读音与壮语“鸟”(loeg)的读音相同,由此推知其神话原型与鸟有关,所蕴含的生殖和丰收的象征意义都显示出与上古鸟崇拜一脉相承[40]。在一些地方口头流传的神话传说中,还可以捕捉到以鸟作为始祖的信息,这些信息都集中在稻谷来历和稻作女神的母题上。例如,在广西隆安,传说在一次大水灾中水稻被淹死了,稻种也由此灭绝,只有“岜乜虽”(即西大明山)稻神娅王还存有稻种,于是人们委托麻雀去请求娅王赠送稻种,沿江一带才恢复了水稻生产[41]。另一则传说娅王是鸟王,为帮助壮族人民度过饥荒,亲自送来金灿灿的稻谷而献出了生命[42]。每年的农历六月初六,当地人都会祭拜稻神娅王,感念娅王恩情的同时也祈祷风调雨顺、稻谷满仓。据笔者调查,在滇黔桂交界的广西西林县,在农历的三月初三、五月初五、七月十九到二十五,百姓都会祭拜娅王祈祷稻作丰收。农历七月中旬,西林县许多壮族村屯民众都会聚焦在一起举行唱娅王的仪式,仪式唱述的经诗讲述了因娅王为人间劳累生病致死,于是人们悲痛而“哭娅王”,以示缅怀和感恩。在仪式过程中,仪式专家扮演娅王,其所唱的诗句出现山川、河流、树木、村落、风雷雨电等空间与自然景观,以及牛、马、猪、狗、羊、鸡、鸭、老虎、猴子、马蜂、鱼等动物和谷物、竹笋、瓜果、鲜花等植物,甚至还有锄头、锅铲等劳动工具和生活用具。笔者还观察到仪式现场的祭祀物中有一只用糯米粉捏制的鸟,其蒸熟后被点染上红色的眼睛和羽翅,栩栩如生。居住在右江流域上游、云贵高原边缘的云南壮族至今还保留着明显的鸟图腾,“云南西畴县上果村女性的成丁礼,是每年农历二月初一穿‘鸟衣’履行祭祀太阳鸟母的传统民俗活动”[43]。综合来看,唱娅王仪式及其唱诵经诗的内容,无疑是一部壮族村落社会的“博物志”。在流传于广西右江流域的娅王信仰中,娅王是万物之母,给人间送来稻种,并教会人们种植水稻,而鸟类作为上古鲜明鸟崇拜中的神灵能够为人间带来稻种和丰收的希望,因此,娅王女神(神鸟)创造生命与万物、传授耕作技艺的神话叙事已成为代代相传的文化记忆融入了壮族人民的生命意识。壮族民间活态传承的鸟崇拜与稻作文化,则与长江流域的玄鸟神话[44]和稻作文化呈现出交流共生的博物传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符号。而岭南地区左右江流域壮族娅王信仰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统与文旅融合、民族古籍的整理出版、民族歌剧的舞台演出等多媒体和数据化的表达演绎获得共享性,成为中国与东盟各国甚至人类跨界共享的家园遗产。
王铭铭认为,地方年度周期仪式作为包含着广泛的地理、经济、技术、社会内涵等一整套知识的宇宙观,将社区与其山、水、树、农田、牲畜、茶园等“环境”关联成有相互作用的生活世界整体[45]。在广西左右江流域的壮族村落,人们遵循天时节令开展稻作生产,稻谷生长需要山水林田协和守护,稻作一年的耕作与收成都在这一生态协同体系中运行及完成。因此,壮族人民形成了对田地、山川以及稻谷的敬畏与尊崇,也形塑出一套以稻作为表征的个体生命意识、家园生命根基和乡土伦理秩序等博物传统。
由此可见,信息时代受媒体技术的操控,但如果人类秉持一种文化整体性的理念思维,是可以经由符号编码和象征意义的生成与互动来建构一个丰富多样、生生不息的生命空间和博物世界的,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基本维度。在万物互联的网络社会中,一旦我们挣脱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桎梏,便可进入一个更广阔自由的生命世界,人类生活世界的整体就凝聚为人类共有的地球家园。
四、余论
在博物学家看来,博物学可以“作为一种教育力量”[46],从自身做起,“把自己放回到大自然中来理解,保持谦虚的态度,确认自己是普通物种中的一员,确认与其他物种与大地、河流、山脉、海洋共生是唯一的选择”[47]。在地球广袤的生活世界里,不断变化的生命形态和不同个体的生命感知,使得人们无法通过机械重复来获取知识,而要领悟生命世界与真正的价值内涵,必须时刻保有谦恭、敬畏之心,秉持热爱和同情,这才是博物学传统的智慧和精髓。汲取中式博物学的生命智慧,可以帮助我们摒除偏见、穿越时空,就像是太阳历经了地底的黑暗带来破晓的曙光一般获得新的开始。人们通过生命体验与自然万物“参赞化育”“天地合德”,通过万物的化生与共生,最后“导达其仁”,感受到生命的价值,在万物生命的关照与关联中形成生命共同体。因此,在博物人文的价值感召下,我们从自我身体和脚下土地开始,点点滴滴汇聚集体的力量,为生态文明和生命共同体的建设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