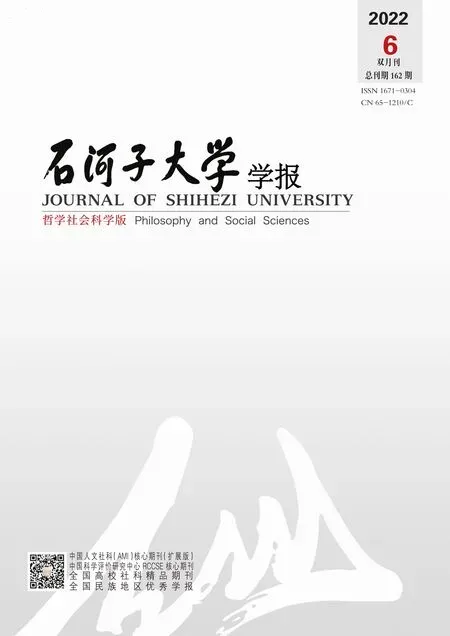莫高窟第464窟莲花冠上师为西夏国师鲜卑宝源考
孙伯君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北京 100081)
一
莫高窟第464窟位于莫高窟北区崖面北端,素有“小藏经洞”之称。该窟由前、后两室构成,前室南北壁和后室窟顶与壁面绘有精美的壁画,多幅壁画题有回鹘文榜题。窟内还存有西夏文题记,并绘有两方墨书“六字真言”,一方为梵文、藏文、回鹘文、汉文四体文字,一方为梵文、藏文、汉文、回鹘文、八思巴文五体文字,并有汉字偈“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己,寂灭为乐”和“禅”字。从20世纪初开始,伯希和、奥登堡、沙俄残余部队等先后对该窟进行了盗掘,后来,张大千、敦煌研究院等又对其进行了清理。据不完全统计,从该窟出土的西夏文、回鹘文、藏文、蒙古文、梵文等文献残片共有800余件,回鹘文木活字千余枚,主要分藏于敦煌研究院和法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吉美博物馆、瑞典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日本天理图书馆等处。
目前为止,学界对该窟的研究和讨论主要围绕壁画、题记、文献残片和回鹘文木活字等内容的考释,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于该窟的断代。壁画内容方面有梁尉英、王慧慧、张元林等的研究①梁尉英:《莫高窟第464窟善财五十三参变》,《敦煌研究》1996年第3期,第43-50+184页;王慧慧《莫高窟第464窟〈大乘庄严宝王经变〉考释——莫高窟第464窟研究之三》,《西夏学》2021年第1期,第317-331页;张元林《从“法华观音”到“华严观音”——莫高窟第464窟后室壁画定名及其与前室壁画之关系考论》,《敦煌研究》2022年第1期,第20-32页。,主要就前室与后室壁画的定名与所据佛经内容加以阐释;西夏文题记有史金波和白滨的释读②史金波、白滨:《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研究》,原刊《考古学报》1982年第3期,载白滨编《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16-451页。;西夏文文献残片有松泽博、戴忠沛、束锡红、黄延军、段玉泉、马万梅等的研究③松泽博:《敦煌出土西夏语佛典研究序说——天理图书馆所藏西夏语佛典について(2)-》,《龙谷史坛》,103/104:第152-80页;束锡红《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考论》,《敦煌研究》2006年第5期,第84-88页;戴忠沛:《法藏西夏文〈占察善恶业报经〉残片考》,《宁夏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第94-96页;黄延军:《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考补》,《西夏研究》2010年第2期,第112-114页;段玉泉、马万梅:《新见法藏敦煌出土西夏文献考释》,《敦煌研究》2021年第4期,第42-49页。;回鹘文题记有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杨富学、皮特·茨默、张铁山等的考释④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杨富学:《敦煌莫高窟464窟回鹘文榜题研究》,《民族语文》2012年第3期,第78-81页;皮特·茨默:《保罗·伯希和,突厥研究和莫高窟第464窟杂记》(Paul Pelliot,Lesétudes Turques et quelques notes sur la grotte B464 de Mogao),载《保罗·伯希和:从历史到传奇》(Paul Pelliot:de l” histoireàla légende),巴黎:2013年,第419-432页;张铁山、彭金章、皮特·茨默:《敦煌莫高窟北区B464窟回鹘文题记研究报告》,《敦煌研究》2018年第3期,第44-54页。;回鹘文木活字国内主要有雅森·吾守尔的研究⑤史金波、雅森·吾守尔著:《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关于该窟的断代,张大千、史苇湘、宿白和谢继胜等都主张“西夏说”⑥张大千:《莫高窟记》,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1985年,第628-629页。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70页;宿白:《敦煌莫高窟密教遗迹札记(下)》,《文物》1989年第10期,第71、82页;史苇湘:《关于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载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第184页。谢继胜:《莫高窟第465窟壁画绘于西夏考》,《中国藏学》2003年第2期,第69-79页。,最近沙武田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后室壁画绘制于西夏,前室为元代所重绘⑦沙武田:《礼佛窟·藏经窟·瘗窟——敦煌莫高窟第464窟营建史考论(上)》,《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年第7期,第24-38+139-140页;沙武田:《礼佛窟·藏经窟·瘗窟——敦煌莫高窟第464窟营建史考论(下)》,《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年第8期,第40-51+126页。。梁尉英认为该窟壁画绘制于元代早期⑧梁尉英:《莫高窟第464窟善财五十三参变》,《敦煌研究》1996年第3期,第43页。,杨富学则认为该窟后室壁画绘制于元代早期,而前室则为元代末期豳王家族所重绘⑨杨富学:《敦煌莫高窟第464窟的断代及其与回鹘之关系》,《敦煌研究》2012年第6期,第1-19页;杨富学:《文殊山万佛洞西夏说献疑》,《西夏研究》2015年第1期,第25-33页;杨富学:《裕固族与晚期敦煌石窟》,《敦煌研究》2017年第6期,第46-57页;杨富学:《裕固族初世史乃解开晚期敦煌石窟密码之要钥》,《敦煌研究》2019年第5期,第9-12页。,也有一定代表性。
关于第464窟壁画的内容,学界对前室南北壁39幅屏风式方格连环画内容的看法较为一致,同意梁尉英在《莫高窟第464窟善财五十三参变》一文中的判断,其表现的是《华严经·入法界品》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内容;而关于后室壁画,大家对其是一铺观音经变画,表现的是观音现身说法的内容没有异议,但对具体取自哪部佛经则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取自《法华经·入法界品》①张元林:《从“法华观音”到“华严观音”——莫高窟第464窟后室壁画定名及其与前室壁画之关系考论》,《西夏学》2021年第1期,第317-331页。,一种观点则认为取自《大乘庄严宝王经》②王慧慧:《莫高窟第464窟〈大乘庄严宝王经变〉考释——莫高窟第464窟研究之三》,《敦煌研究》2022年第1期,第20-32页。。
关于第464窟后室南面东起下排第一格所绘莲花冠上师像,谢继胜曾在《莫高窟第465窟壁画绘于西夏考》一文中通过对上师所戴冠帽样式与文殊山万佛洞,榆林窟第27窟、第29窟、东千佛洞第4窟、第5窟,黑水城唐卡、拜寺沟方塔等上师所戴冠帽的对比分析,确认上师所戴冠帽是西夏上师的典型冠帽,为藏传佛教宁玛派的莲花帽,从而确认了该壁画绘制于西夏前期③谢继胜:《莫高窟第465窟壁画绘于西夏考》,《中国藏学》2003年第2期,第69-79页。。
我们知道,西夏文献所记载的著名上师有的是西夏本土高僧,有的来自西藏。仔细考察464窟南面东起下排第一格壁画,其中人物的服饰除了冠帽与藏传佛教上师的莲花帽较为相像之外,整体的服饰风格基本还是汉地的,这让我们推测这位上师可能出自西夏本土。据藏文史籍和黑水城出土西夏文献记载,从西夏仁宗皇帝即位开始,藏传佛教始盛行于西夏境内,早期被封为国师的多为西夏本土僧人,后期被封为国师与帝师的多是来自西藏的喇嘛。而仁宗皇帝早期著名的僧人非鲜卑宝源莫属。
二
鲜卑宝源(?—1188),主要活跃于12世纪40—80年代西夏仁宗皇帝当政时期,是直接服务于西夏王室的高僧,曾在“番汉三学院”中担任管理佛教事务的官职,被皇帝任命为“番汉三学院兼偏袒提点”。他曾驻锡于皇家敕建的“大德台度民寺”(简称“大度民寺”),先后被授予诠教法师和国师,先被封授为“卧耶”,再升为“美则”,两种职务均见于西夏文《官阶封号表》,“美则”比“卧耶”要高一阶。他兼通汉语、西夏语,既是翻译家,又是文学家。
作为翻译家,鲜卑宝源最早翻译的佛经是汉文本《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两种经典合刻为蝴蝶装一册,俄藏有两个编号TK.164和TK.165④两个版本均刊布于《俄藏黑水城文献》第4册,1997年,第29-51页。。卷首款题“诠教法师番汉三学院兼偏袒提点卧耶沙门鲜卑宝源奉敕译,天竺大般弥怛五明显密国师在家功德司正乃将沙门口拶也阿难捺传”,末附御制“《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胜相顶尊总持依经录》后序发愿文”。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佛经中也有两部同名经典,编号инв.№6881,款题:
繝聻菞蝜睍冠氦苔繕祇緳萚緋箍省八粴簶蒷砓藹庆目危稟;身粄矖祇緳萚緋緈省紋打簶蒷成膳硾居瞭握⑤Е.И.Кычанов,Каталогтангутскихбуддийскихпамятников,Киото:УниверситетКиото,1999,стр.580-581.。[天竺大钵弥怛五明国师功德司正乃将沙门口拶也阿难捺传,显密法师功德司副挨黎沙门周慧海奉敕译]
该西夏文本经文后面的御制发愿文与宝源汉译本内容一致,并署“天盛己巳元年月日”“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谨施”,可推知汉、夏两种文本是同时于天盛元年(1149)之前自藏文本译出的,周慧海先自藏文译成西夏文,鲜卑宝源则据西夏文再译成汉文。
鲜卑宝源还曾与周慧海合作把藏文《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译成汉文。该经于西夏仁宗时期自藏文译出,重刊于明正统十二年(1447),保存于北京云居寺,卷首款题曰⑥罗炤:《藏汉合璧〈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考略》,《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4期,第14页。:
演义法师路赞讹赏则沙门遏啊难捺吃哩底梵译,
天竺大钵弥怛五明显密国师讲经律论功德司正乃将沙门口拶也阿难捺亲执梵本证义,
贤觉帝师讲经律论功德司正偏袒都大提点卧勒沙门波罗显胜、
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再详勘。
宝源自汉文译成西夏文的有《父母恩重经》,该经的俄藏本出现了一则译者款题,见于инв.№6570,原文作“矖粄泌蒷”,字面意思是“诠教沙门”②应作“簶蒷”。,段玉泉认为这一称呼是西夏文献中屡见的“矖粄繕祇簶蒷脖膰拓樊”(诠教国师沙门鲜卑宝源)的略写③段玉泉:《语言背后的文化流传:一组西夏藏传佛教文献解读》,兰州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45页。。另外一个本子инв.№759号卷尾署“猜泊己唆淮翆氦聚坚箎涸”(天盛壬申四年五月日智施),表明该本是1152年印施的。聂鸿音先生曾把俄藏TK.139号《父母恩重经》汉文本与存世诸多汉文本进行对照,认为它与敦煌藏经洞所出的P.3919号抄本最为接近,并进一步指出西夏本《父母恩重经》的出现是唐五代敦煌文献传统的延续④聂鸿音:《论西夏本〈佛说父母恩重经〉》,高国祥主编《文献研究》第一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第137-144页。。
宝源自汉文译成西夏文的还有《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是据唐代沙门宗密以《傅大士颂金刚经》为基础的注释本翻译出来的,俄藏黑水城出土инв.№5382号刻本的题记,用两行小字刻在卷首《发愿文》的“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后面⑤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2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2页。:
竤辊繕菞菞烁繫缾棍矖粄繕祇嘿臷菋锡瞲蜐涉弛蔎纝躬,距氟焦箍。蔲綀佬萝论煞城,较闽舉若癐紩蔓籃。省籱晾,窾闽若供籃蒜。
大白高国大度民伽蓝诠教国师与梵本及汉经注疏等重校,正其科判。人或欲闻解其理,可上下二节总观之。欲受持,则读下节可矣。
инв.№689卷尾存有西夏文译本的功德主和译者的职衔⑥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在圣彼得堡拍摄的照片。:
繝薭迈十糦箍苔蚔籍緳竝镁癏,脖膰矖祇磌迈嘿臷、锡紒蜐涉弛蔎纝纝息瞛躬,綈焦丸属,葾臷始怖。
西劝农御史正明辩罔德忠发愿,延请鲜卑法师与梵本、汉番注疏等反复雠校,去其舛杂,是为真经。
инв.№5382号卷尾的题记表明了刊印时间是天盛十六年(1164)⑦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2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93页。:
猜泊坪唆翙灯泪翆萰聚禋氦坚
螙藶超癏腞箙料窫傻涅萿
榜蚘矟惮薫寥
天盛甲申岁十六年八月十五日
发起刊印者前宫侍耿三哥
罗瑞领占讹书
鲜卑宝源不仅是翻译家,还是文学家。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有一部他撰的西夏文诗文总集《贤智集》,又称“鲜卑国师劝世集”,为乾祐十九年(1188)刻本。该文集共包括21篇,有9篇“辩”,1篇“赞”,3篇“颂”,1篇“文”,1篇“诗”,3种“惊奇”,4篇“意法”,1篇“杨柳枝”曲子辞。通过释读,我们曾判断这部劝人向佛行善的《贤智集》是鲜卑宝源生前在寺院做俗讲的讲稿。其中《贤智集》中所收“劝亲修善辩”等也是从敦煌变文“唱辩”继承发展而来⑧孙伯君:《西夏俗文学“辩”初探》,《西夏研究》2010年4期,第3-9页。。
《贤智集》卷首存序言,题“比丘和尚杨慧广谨序,皇城检视司承旨成嵬德进谨撰”,译文如下①聂鸿音:《西夏文〈贤智集序〉考释》,《固原师专学报》2003年第5期,第46-48页。:
夫上人敏锐,本性是佛先知;中下愚钝,闻法于人后觉。而已故鲜卑诠教国师者,为师与三世诸佛比肩,与十地菩萨不二。所为劝诫,非直接己意所出;察其意趣,有一切如来之旨。文词和美,他方名师闻之心服;偈诗善巧,本国智士见之拱手。智者阅读,立即能得智剑;愚蒙学习,终究可断愚网。文体疏要,计二十篇,意味广大,满三千界,名曰“劝世修善记”。慧广见如此功德,因夙夜萦怀,乃发愿事:折骨断髓,决心刊印者,非独因自身之微利,欲广为法界之大镜也。何哉?则欲追思先故国师之功业,实成其后有情之利益故也。是以德进亦不避惭怍,略为之序,语俗义乖,智者勿哂。
从序言可以看出,杨慧广刊行《贤智集》的乾祐十九年(1188),诠教国师鲜卑宝源已经去世。这让人联想到黑水城出土乾祐二十年(1189)御制《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发愿文》,其中谈及在西夏首都兴庆府附近的大度民寺所做的大法会,曾“延请宗律国师、净戒国师、大乘玄密国师、禅师、法师、僧众等,请就大度民寺内,具设求修往生兜率内宫弥勒广大法会,烧施道场作广大供养,奉无量施食,并念诵佛名咒语。读番、西番、汉藏经及大乘经典,说法作大乘忏悔。”②聂鸿音:《乾祐二十年〈弥勒上生经御制发愿文〉的夏汉对勘研究》,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4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45页。这次法会可能就是为了追荐这座著名的皇家寺院的前住持、国师鲜卑宝源而具设的。
据天盛二年(1150)夏仁宗敕准颁行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天盛革故鼎新律令》)卷十一“为僧道修寺庙门”记载③史金波、聂鸿音、白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404-405页。:
一等番、羌所诵经颂:
仁王护国、文殊真实名、普贤行愿品、三十五佛、圣佛母、守护国吉祥颂、观世音普门品、竭陀般若、佛顶尊胜总持、无垢净光、金刚般若与颂全。
一等汉僧所诵经颂:
仁王护国、普贤行愿品、三十五佛、守护国吉祥颂、佛顶尊胜总持、圣佛母、大随求、观世音普门品、孔雀经、广大行愿颂、释迦赞。
在这些西夏境内番、汉、藏族童行必诵的经典中,有《佛顶尊胜总持》《金刚般若与颂全》等多部鲜卑宝源翻译的经典,可见他在西夏仁宗时期作为宗教领袖的至尊地位。同时,无论是他翻译的《父母恩重经》,还是创作的《贤智集》,都与唐五代敦煌流行的文本与内容一脉相承,说明鲜卑宝源在接受后弘期传入西夏的藏传佛教影响以前,其佛教素养和传承基础多来自唐五代河西地区遗存下来的传统。
三
此前,学界认识到第464窟后室壁画是一铺观音经变画,表现的是观音现身说法的内容。不过,学者往往从汉传佛教观音信仰的角度对壁画内容加以阐释,或认为其内容取自《法华经·入法界品》④张元林:《从“法华观音”到“华严观音”——莫高窟第464窟后室壁画定名及其与前室壁画之关系考论》,《西夏学》2021年第1期,第317-331页。,或认为取自《大乘庄严宝王经》⑤王慧慧:《莫高窟第464窟〈大乘庄严宝王经变〉考释——莫高窟第464窟研究之三》,《敦煌研究》2022年第1期,第20-32页。。前者的依据是在中土与观音信仰相关的佛典中,《法华经·观世音普门品》详说此菩萨因缘、功能与神通,被视为观音信仰的根本经典,如鸠摩罗什奉诏译《妙法莲华经》卷7“御制观世音普门品经序”曰⑥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卷7,《大正藏》卷9,第56页下栏。:
观世音菩萨,以烁迦罗心,应变无穷,自在神通。遍游法界,入微尘国土,说法济度,具足妙相。弘誓如海,凡有因缘,发清净心,才举声称,即随声而应。所有欲愿,即获如意。妙法莲华经普门品者,为度脱苦恼之真诠也。人能常以是经作观,一念方萌,即见大悲胜相。能灭一切诸苦,其功德不可思议。
后者的依据则是汉传“六字真言”取自《大乘庄严宝王经》。
观音信仰在藏传佛教传译中分属两系:其一为弥扎·卓根班智达、绰普译师一系,其二为口拶也阿难口捺和巴日译师一系。前者又有绰普、夏鲁、格鲁等分支,后者被萨迦派所承续。两派最主要的特点均是以观想本尊、“六字”种子字和持诵六字真言为中心①王小蕾:《西夏元明清时期汉译密教观音经轨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20年,第1页。。
宝源译汉文本《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讲述观自在菩萨在波怛口辢山圣观自在宫向世尊宣陈大悲心总持、颂持仪轨及其功能,从内容看,是藏传佛教观音信仰的最重要的经典,且明确说为“天竺大钵弥怛五明国师功德司正乃将沙门口拶也阿难捺传”。口拶也阿难口捺,梵文名Jayānanda,义为“胜喜”,西夏称作“五明显密国师”或金刚座法师。范德康(Leonard·W.J.van der Kuijp)曾根据现存的藏文文献认为口拶也阿难口捺实际上是克什米尔人,曾是西藏非常知名的高僧,与西藏有名的思想家恰巴·却吉僧格(1109—1169)就中观题目所作的公开大辩论,最后以口拶也阿难捺失败而告终②范德康著,陈小强、乔天碧译《拶也阿难捺:12世纪唐古忒的克什米尔国师》,载《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14辑,1998年,第341-351页。。大概在西夏仁宗后期,他转到西夏传法,并被授予“功德司正”的官职,获封“五明显密国师”的称号。据黑水城出土汉文本《念一切如来百字忏悔剂门仪轨》和《求佛眼母仪轨》(俄藏A5)款题“西天金刚座大五明传,上师李法海译”③俄藏A5,刊布于《俄藏黑水城文献》第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34页。,他还曾把这两部经传到西夏。
在《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卷尾“后序发愿文”中,西夏仁宗皇帝曾陈述了颂持两部经典的功德④俄藏TK.165,刊布于《俄藏黑水城文献》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0-51页。:
切谓《自在大悲》,冠法门之密语;《顶尊胜相》,总佛印之真心。一存救世之至神,一尽利生之幽验。大矣,受持而必应;圣哉,敬信而无违。普周法界之中,细入微尘之内。广资含识,深益有情,闻音者大获胜因,触影者普蒙善利。点海为滴,亦可知其几何;碎刹为尘,亦可量其几许。唯有慈悲之大教,难穷福利之玄功,各有殊能,迥存异感。故《大悲心感应》云:“若有志心诵持《大悲咒》一遍或七遍者,即能超灭百千亿劫生死之罪,临命终时,十方诸佛皆来授手,随愿往生诸净土中。若入流水或大海中而沐浴者,其水族众生沾浴水者,皆灭重罪,往生佛国。”又《胜相顶尊感应》云:“至坚天子诵持章句,能消七趣畜生之厄。若寿终者,见获延寿,遇影沾尘,亦复不堕三恶道中,授菩提记,为佛嫡子。”若此之类,功效极多。……
除了《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黑水城出土西夏文献中还有《观自在菩萨六字大明心咒》、乾祐乙巳十六年(1185)智通施《六字大明王功德略》(TK136)、《圣六字大明王心咒》(TK137)、《亲集耳传观音供养赞叹》(Ф311)等,均为藏传佛教观音菩萨修习仪轨。
《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的“心咒”,即通常所说的“六字真言”。“六字真言”是“观自在菩萨六字大明心咒”或“圣六字大明王心咒”的简称,梵文作om mani padme hūm。鲜卑宝源这里所用对音汉字是:“唵麻祢钵嘻能铭吽”。
目前所知,见于西夏时期翻译、纂集和刊行的文献中的“六字真言”主要还有以下几种,均与西夏的观音信仰有关:
(1)西夏天庆二年(1195)皇太后罗氏发愿所施《佛说转女身经》,所用对音汉字曰:“唵麻祢钵嘻能铭吽”⑤俄藏编号TK.12,见《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91页。。
(2)俄藏黑水城出土TK.137汉文本《圣六字大明王心咒》,所用对音汉字曰:“唵麻祢钵嘻能铭吽”⑥俄藏编号TK.137,见《俄藏黑水城文献》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91页。。
(3)西夏智广于天庆七年(1200)编定的《密咒圆因往生集》中的“观自在菩萨六字大明心咒”,所用对音汉字曰:“唵麻祢缽嘻能铭吽”⑦通行本《密咒圆因往生集》,见《大正藏》卷46,第1007-1013页。。
(4)汉文本《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中“六字大明真言”,对音汉字曰:“唵么抳钵讷铭嘻能吽”①俄藏编号TK.271,见《俄藏黑水城文献》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58页。,与《大正藏》本《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一致。
(5)乾祐十六年(1185)智通所施汉文本《六字大明王功德略》,所用对音汉字:“唵麻祢钵捺銘嘻能吽”②俄藏编号TK.136,见《俄藏黑水城文献》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75页。。
其中前三种都是西夏时期翻译和纂集的,后两种是在唐宋时期流传下来的中原文献汉文本基础上修改的,这些对音汉字的读音反映了西夏人口语中的“番式”汉语。其中梵文padme对译作“钵铭嘻能”或“钵捺铭嘻能”,即梵文-d用“嘻能”“捺”对音、me用“铭”字对音,反映了西夏时期“番式”汉语的两大特点:(1)声母方面,鼻音字“能”“捺”读作带有同部位浊塞音的nd-;(2)韵尾方面,曾摄字“能”和梗摄字“铭”的韵尾-失落。同样的例子在西夏文献中比比皆是,如《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中梵文chedaa,对音汉字作“齐捺”,以“”译da;《番汉合时掌中珠》中宕摄的“皇”、“黄”、“凰”与果摄的“河”“和”“火”“祸”“荷”为同一个西夏字标音;梗摄的“庚”“更”“耕”“粳”与蟹摄的“皆”“介”“芥”“界”为同一个西夏字标音;通摄的“孔”与遇摄的“枯”“库”为同一个西夏字注音。
元代杭州飞来峰造像中,第33号龛观音菩萨造像右外侧上部题有“六字大明心咒”,对音汉字与西夏时期的对音用字颇为一致,曰:“唵麻祢巴铭吽”,说明元代西夏遗僧为重塑飞来峰造像的主体,且刻于夏末元初,当时这些西夏遗僧说的还是西夏时期流行的“番式”汉语。
莫高窟也存有于元至正八年(1348)刻就的梵文、汉文、藏文、回鹘文、八思巴文、西夏文六种文字的“六字真言”石刻,其中汉字对音作“唵麻尼(弥)把迷吽”,已经没有西夏河西方音的特点了。
莫高窟第464窟内前室东段两侧绘有两方墨书“六字真言”,一方为梵文、藏文、回鹘文、汉文四体文字,一方为梵文、藏文、汉文、回鹘文、八思巴文五体文字,其中对音汉字“唵 麻尼(弥)把密吽”,与元至正八年(1348)所刻“六字真言”用字基本一致,符合元代语音特点,而与西夏时期基于“番式”汉语的河西方音用字特征不合。
13世纪末,当马可波罗沿着“丝绸之路”行至沙州,抵达唐古忒境内时,他听到当地多数信奉佛教的居民讲着一种独特的语言,曰:“抵一城,名曰沙州。此城隶属大汗,全州名‘唐古忒’(Tangout)。居民多是偶像教徒,然亦稍有聂思脱里派之基督教徒若干,并有回教徒。其偶像教徒自有其语言。”③[意]马可波罗(Marco Polo)著,A.J.H.Charignon注,冯承钧译,党宝海新注《马可波罗行纪》,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2页。所谓“偶像教徒自有其语言”,当指马可波罗于13世纪末游历到敦煌时见证了“唐古忒”后裔仍然会讲西夏语。而随着元代党项人逐渐放弃自己的母语,他们所说汉语的“番式”特征也随之消失,从这个角度说,推测莫高窟第464窟前室壁画与东段两方墨书“六字真言”重绘于元代中后期是可以成立的。
四
鲜卑宝源撰《贤智集》卷首存有一幅木刻插图“鲜卑国师说法图”,图的正面是一位国师,交脚坐于宽大的靠背椅上,身着右衽交领衫,头戴山形冠,左手掌心向上,右手较为模糊,应是做说法的姿势,西夏文榜题“脖膰繕祇”(鲜卑国师);国师身后有一位头扎巾帙的长胡子老者打着伞盖;国师右手边站立一位双手合十、侧脸聆听的小僧人;左手边站立一位手捧沃盥的小沙弥;对面有六位身着不同服装、梳着各种发式、有着不同民族面孔的听众跪拜,榜题“矖萝缾”(听法众);国师前面有供桌,供桌上摆放着香炉、灯盏和净瓶等;说法图的侧面还绘有假山和芭蕉树一样的植物,树上飞翔着几只小鸟,显示着说法的地方是一处颇为清净之地。这幅说法图向我们展示了宝源在寺院做俗讲的生动画面④史金波:《西夏社会》(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彩图39。。从装束和构图看,这一画面与第464窟南面东起下排第一格所绘莲花冠上师、诸沙弥像与伞盖非常相像。
我们知道,藏密首重师承,无师则一切法不能安立,这或许是第464窟出现西夏国师鲜卑宝源说法图的原因。安西榆林窟第29窟题记上也出现了一个同姓的鲜卑国师,西夏文题记作“始佬经善瞪脖膰箎硾”(真义国师鲜卑智海),过去的汉文音译是“西毕”或者“昔璧”①史金波、白滨:《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研究》,载白滨编《西夏史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16-451页。,当译作“鲜卑”,这位国师的出身或许与鲜卑宝源有渊源关系。
元代西夏遗僧一行慧觉所撰《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遍礼忏仪》卷42有一大段文字,曾述及《华严经》从印度到中国的传承,在“西域流传华严诸师”“东土传译华严经诸师”之后谈到了“大夏国弘扬华严诸师”,其中第一位作“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中讲经律论重译诸经正趣净戒鲜卑真义国师”②《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遍礼忏仪》,全书42卷,为明末云南丽江土司木增携其子孙捐资,由常熟毛氏汲古阁雕刊的。。这位鲜卑真义国师即榆林窟第29窟题记上的真义国师鲜卑智海。他被列为“大夏国弘扬华严诸师”之初祖,似乎表明他对《华严经》在西夏的重译作了开创性的贡献。前述西夏乾祐二十年(1189)御制《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发愿文》,曾记述“延请宗律国师、净戒国师、大乘玄密国师、禅师、法师、僧众等,请就大度民寺内,具设求修往生兜率内宫弥勒广大法会,烧施道场作广大供养,奉无量施食,并念诵佛名咒语。读番、西番、汉藏经及大乘经典,说法作大乘忏悔。”③聂鸿音:《乾祐二十年〈弥勒上生经御制发愿文〉的夏汉对勘研究》,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4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45页。其中的“净戒国师”正可与“正趣净戒”勘同,这不由让我们推想这位真义国师是鲜卑宝源国师的继任者。而这次在大度民寺所做的“往生兜率内宫弥勒广大法会”就是由他主持,目的是追荐和超度前一年逝去的鲜卑宝源。
黑水城出土很多文献的款题提到“大度民寺”,特别是仁宗后期和桓宗时期出现的著名藏传佛教大师“中国觉照国师喇嘛蘖上师法狮子雅砻辛巴”,他来自西藏,与萨钦贡噶宁波(1092—1158)和祥仁波切(1123—1194)有师承关系,曾住持于大度民寺翻译了很多与金刚亥母修习有关的密法④孙伯君:《西夏国师法狮子考》,《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第25-29页。。
由此,我们似乎找到了莫高窟第464窟绘有鲜卑宝源国师说法图的理据,他就是该窟壁画所展现的西夏藏传佛教观音菩萨信仰的传译者、功德主。
五
如所周知,元代宗教上层多为西夏后裔,元代中原所传藏传佛教的汉文经本多是西夏时期翻译的。元代西夏遗僧还曾组织过大规模的写经活动,最著名的是李惠月发愿书写的金银字《大方广佛华严经》。这部金银字《华严经》在瓷青纸上用银字书写,经题及卷次、品名,以及“菩萨”“如来”“世尊”“天”“法”“佛”“皇”“僧”“毗 卢”“声 闻”“缘 觉”等字用金字书写。目前所知,该经存世共有13卷,每卷卷首都有精美的扉画。扉画笔法细腻,线描中施以金粉和银粉,美轮美奂,展现了杭州南宋宫廷画师的纯熟技法,同时具有藏传佛教的特征,所绘内容正是《华严经·入法界品》“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与莫高窟第464窟前室壁画内容一致。可见,这一主题在元代非常流行。这些金银字书写《华严经》卷尾大多存有李惠月抄经跋,曰:
长安终南山万寿禅寺住持光明禅师惠月,陇西人也。九岁落发披缁,一踞荷兰山寺,瞻礼道明大禅伯为出世之师,旦夕咨参,得发辉之印。先游塞北,后历江南;福建路曾秉于僧权,嘉兴府亦预为录首。忖念缁衣之滥汰,惟思佛法之难逢;舍梯己财,铺陈惠施。印造十二之大藏、剃度二八之僧伦;散五十三部之华严、舍一百八条之法服。书金银字八十一卷,《圆觉》《起信》相随;写《法华经》二十八篇,《梵网》《金刚》各部。集兹胜善,普结良缘。皇恩佛恩而愿报无穷,祖意教意而发明正性。师长父母,同乘般若之慈舟;法界众生,共泛毗庐之性海。
至元二十八年(1291)岁次辛卯四月八日,光明禅师惠月谨题。
从上述“抄经跋”可知,光明禅师李惠月为西夏遗僧,大概生于1221年。1227年西夏灭亡后,他于两年后出家,拜贺兰山佛祖院的道明大禅伯为师。他曾于元世祖忽必烈后期在江南做过“嘉兴府录首”,而从现存经他之手刊行的佛经多表现为《普宁藏》零本这一情况看,他所担任的“录首”实为组织刊行《普宁藏》的白云宗僧录,期间他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完成了12部《普宁藏》的印制。他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卸任僧录,转任长安终南山万寿禅寺住持,其间他发愿书写了汉文金银字《大方广佛华严经》共81卷,以及《圆觉经》《起信论》,同时,还抄写了泥金书西夏文《法华经》《梵网经》《金刚经》等。
值得注意的是,伯希和在第464窟携走的西夏译本《大智度论》卷87尾部的一张残片(Grotte 181:110),所盖戳记内容为:“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八施大藏经于沙洲文殊舍利塔寺,永远流通供养。”①伯希和:《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耿升、唐健宾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3页。同样有此施经戳记的残片还有张大千在该窟发现、现藏日本天理图书馆的《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以及敦煌研究院第六次洞窟清理中在莫高窟北区B159窟发现的《龙树菩萨为禅陀迦王说法要偈》②段玉泉:《管主八施印〈河西字大藏经〉初探》,《西夏学》第1辑,2006年,第99-104页。,这些经本均是西夏遗僧一行慧觉整理,白云宗僧录李惠月、管主八等刊行的《河西藏》零本。《华严经·入法界品》“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主题在元代流行,与元代白云宗尊奉华严教义不无关系。任宜敏《中国佛教史》(元代)曰:“聿兴于北宋末年的白云宗,以《华严经》为一代佛教的旨归,立‘十地三乘顿渐二教’之教相为教说”③任宜敏:《中国佛教史》(元代),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32页。。可见,不论是莫高窟第464窟前室壁画遗存,还是佛经遗存,均与元代大江南北的西夏遗僧的宗教活动与信仰相关,结合“六字真言”的对音汉字,推测前室壁画重绘于元代中后期是没有问题的。
俄藏TK.164《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与《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合刻本卷首有三幅版画,具有典型的西夏时期藏传佛教风格。
仔细对照莫高窟第464窟后室壁画与西夏时期刊行的《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卷首版画,其风格的区别还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元代在敦煌的藏传佛教僧人多为西夏遗僧,他们自然继承了西夏时期河西地区盛传的观音信仰。这一信仰是由克什米尔人口拶也阿难口捺从西藏传入西夏,并由西夏鲜卑宝源国师发扬光大的,因此,莫高窟第464窟后室在重绘观音经变画时,也把西夏观音信仰最重要经典《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的译传者、功德主绘于其中,以供信徒发愿观想。由此,我们推测莫高窟第464窟后室壁画也应是元代西夏遗僧所重绘,或许比前室壁画绘制的要早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