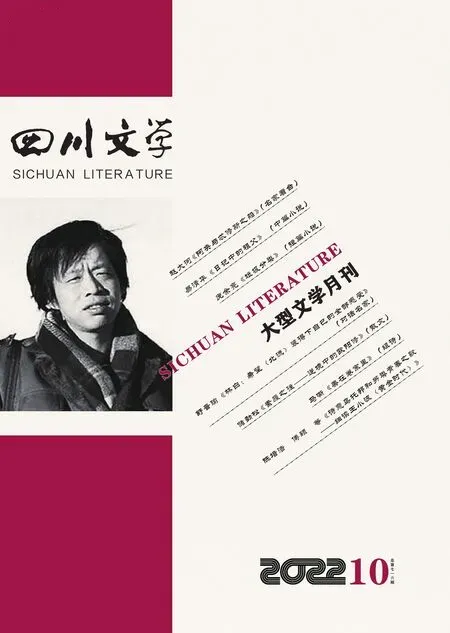记忆·日常·一瞬
——论葛亮小说中的香港书写
□文/许婉霓
一
“九七”之前,王安忆曾在小说《香港的情与爱》中开篇即道,“香港是一个大邂逅,是一个奇迹性的大相遇。”这一说法竟与葛亮在十几年后书写香港的首部小说集《浣熊》中“相遇”:“这城市并不缺乏相遇。”(《浣城记》)如果说,作家将生活中的相遇呈现于文字与故事,那么读者显然更为幸运:在生活的相遇之外,还可以透过与作品的相遇,去往另一重时空。
多年前的盛夏,因为实习,我在香港北角住过一段时间——这是我和香港真正落到实处的“相遇”之处。住处位于英皇道与七姊妹道中间一座人口稠密且复杂的老高层,几十户人家迷宫阵法般布于每一层,同层甚至还有一个公共佛堂。清晨,我便腾闪挪移过这烟雾缭绕与吟哦声声,赶去几站地铁外的金钟实习;傍晚,我又从绚丽高耸的办公楼一头扎回这座烟火升腾的老楼。总觉得此处唤起我阅读经验的,更像是西西在《书写的人》里描写的那个土瓜湾:“住在一层狭窄的楼房,开门/飘进对户的香炉烛火/开窗,面对邻家三餐茶饭”。不过近年来,我每每回忆这段经历,却总会不自觉被葛亮的香港书写覆盖——春秧街如线穿引过故事细处,新旧人事,一并扑面而来。其实住处不远就是春秧街,当年的我却毫无知觉。可见,香港的“相遇”稀松平常,但能精准描绘并留住这“相遇”,并非是人人都有的天赋。
土瓜湾隶属于大名鼎鼎的电影宠儿九龙区,土瓜湾自身也因为西西和《素叶文学》而进入香港文学视野,但事实上,隔海相望的北角在文学空间上也毫不逊色。位于港岛东北端的北角作为香港岛较早开发的区域,20世纪四五十年代承接了大量南来的江浙沪移民,一度有“小上海”之称;20世纪60年代之后,又有福建人进驻北角,接替外迁的上海人而使北角有了“小福建”之称。北角作为一个移民城市缩影的文化符号,早在1957年,香港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推手马朗,就写过影响很广的《北角之夜》:
最后一列的电车落寞地驶过后
远远交叉路口的小红灯熄了
但是一絮一絮濡湿了的凝固的霓虹
沾染了眼和眼之间朦胧的视觉
于是陷入一种紫水晶里的沉醉
仿佛满街飘荡着薄荷酒的溪流
而春野上一群小银驹似的
散开了,零落急遽的舞娘们的纤足
噔噔声踏破了那边卷舌的夜歌
……
20世纪50年代的北角之夜灯火灿烂,在上海开始踏上文学之路又南来的诗人马朗笔下,始终蒙着往昔沪上梦影,心在此地,思归彼处。“卷舌的夜歌”或是那中原之音,或是英文之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自不属于此地几无卷舌音的粤讴。香港本地诗人梁秉钧(也斯)在20世纪70年代便曾笑谈,将舞娘们的噔噔足音喻为“春野上一群小银驹”的奔跑之声,怕是他们这群战后在香港成长、当时并无北访经验的诗人所难以涉足的意象。因此,观梁秉钧在1974年写的《北角汽车渡海码头》,显然是另一番经济正在腾飞的香港景象:
寒意深入我们的骨骼
整天在多尘的路上
推开奔驰的窗
只见城市的万木无声
……
亲近海的肌肤
油污上有彩虹
高楼投影在上面
巍峨晃荡不定
……
梁秉钧十岁时开始生活于北角,他的经验全然是日常的,市声嘈杂,马路嬉闹,北角汽车渡海码头终日有“各方的车子”,充满“烟和焦胶”,蒸腾着属于香港20世纪70年代经济腾飞的现代化热气。这种兴旺的闹哄哄,同样由20世纪八九十年代频繁出入香港的黄灿然的那幅“活像旧时代的一截尾巴”的世纪末图景所定格:“闽南话是春秧街的普通话”“在晴朗的日子,看了就想下楼逛逛/在阴天的时候,看了就想关窗”(《家住春秧街》)。
沪上南来者马朗从外面的世界来看北角,梁秉钧这一代港地青年通过北角来认识身边的香港乃至世界,黄灿然这样出入香港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移民在北角生活之外开始关注并自觉尝试接续某种历史意识——北角在香港文学的各类书写中,从不落寞。作为后“九七”的香港新移民、“在千禧年的尾声”(《拾岁纪》)来到香港的葛亮,则延续并发展了他在过往南京书写中以时间拓宽城市空间的写作偏好,将文化驳杂的香港北角这一空间,转而成为其香港书写中“有关空间与时间的实验室”(《藏品》)。中篇《飞发》的半世故事就发生在北角:翟师傅家道中落,从半山搬到的正是“这福建人与上海人混居”的北角,母亲在百年春秧街开了南货店,翟师傅算是在这里扎下了根,先是开了风光无限、北角老辈人“集体回忆”的“孔雀理发公司”,再是开了和上海理发公司“温莎”对垒了余生的“乐群理发”。新作中篇《浮图》,更是将北角这条春秧街作为人物连粤名的人生起点与无数次返回的原点,也是家族追根索骥的地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北角这一文学空间为例,葛亮香港书写的一大特色,便是更为注重在这一文学地图上增加时间的维度,从而赋予这个城市“历史化”的向度。
二
葛亮的“匠人”系列小说之一《书匠》中,古籍修复师们或中或西,或许脉络有区别,但这一行业所讲求的“整旧如旧”与“不遇良工,宁存故物”两大原则,使修复师们殊途同归皆为帮助古籍能够最终超越时光,回到历史原来的位置上。葛亮近年的香港书写,也在为香港的人与事找寻历史的位置,他的写作,就如同“古籍修复师”,尽管路径各异,却使香港当下这一光滑平面下牵扯不断的旧时光,得以一批批浮出水面,由此组成香港文学地图的另一面向。
历史的呈现,关乎对时间的思考,落到小说的实处则是如何在故事行进中处理叙事时间。延展半世纪、以北角为空间的中篇《飞发》,正是可供观察的一部作品。《飞发》的结构颇有特色,以穿插的方式,在偶数章节中嵌入《楔子:“飞发”小考》《贰:“飞发”暗语》《肆:有关“三色灯柱”的典故》等非虚构的考据文字,介绍“飞发”的旧时知识。这是小说的第一重时间安排,既为“飞发”这一行当注入了时间维度,也从外在结构上以“格物”为方式引入跨度更大的历史时间,以提醒读者跳脱故事本身的叙事时间。奇数章节则是《飞发》故事的主体部分,通过内里脉络中一层又一层的时间追溯,牵引起香港旧时南来移民们如何在内地的习俗、“飞发”文化之根的影响下,见证香港北角这块土地的风物变迁和人物流逝的过往。葛亮写北角、写香港,自是贴近当下的市声民音,但他所关注的更是移民群体进入香港本土之后的生存状况,因此,他在呈现香港本土之外,很多时候离不开内地的根,常常通过时间因素的介入,让两地的根脉深潜于文本之中。
短篇《拆弹记》是另一个在时间上颇有心思的短篇。一枚上溯20世纪40年代太平洋战争时期的炸弹在某个平常日子,于启德地铁站旁的工地被发现。章节的倒数,隐喻着引爆炸弹的紧迫感,这种线性的时间倒数像葛亮设下的谜题,略有疏忽,读者便会滑入如上官喆一样的境地,一边隐隐质疑“七十多年前一颗炸弹的威力,距离这么远,真能波及自己吗”,一边又不由得随着这些倒数与紧急疏散通知,汇入当下的疏散人群,等到最后发现,自己才是整场“炸弹拆除”事件中被影响到的受害人——本来接近康复的臆想症,又再次爆发——而一切以上官喆为叙述视角展开的故事与过往,则因此陷入不确定性中。在小说表面的线性时间处理之下,葛亮悄悄植入了更为深远的时间内核。对于香港人而言,存续于1925-1998年的“启德机场”几乎见证了香港现代化至回归的整个过程,飞机轰鸣过九龙的千家万户正是几代香港人关于现代化的集体记忆,从启德机场到启德地铁站,时间横跨近一个世纪,“启德”这一地标本身便有其时间含义。而葛亮在此之外,又加入了另一重南来根脉的记忆:人类学博士上官喆和赵小凝参加的香港“考古团”好似过家家,却拉扯出一个南来香港、保持普通话交流的子虚乌有人士赵健行。与其说赵健行是葛亮为移民二代赵小凝安置的一个虚幻的西安根脉,不如说他更像是上官喆这样的新移民内心那份隐隐保有、不想忘记的来处之根。《拆弹记》的波澜之处正在于时间的层层包裹:炸弹搅乱了日常的时间,繁忙平静的港岛之下,是追及二战的香港“炸弹”存留、启德机场的兴废拆建的历史时间。这枚炸弹还在某种程度上带出了香港现代史中有关城与战争这并不日常的记忆,让我们看到了当年张爱玲《倾城之恋》浅水湾酒店里炮火撕裂日常的那份似曾相识。
中篇《浮图》的时间处理,同样值得考究。篇首知识分子连粤名在走进来的警员的注视下,吃着牛排;结尾是连粤名杀妻后,打通999,开始煎制牛排,并估算火候,想着“警察来到时,他刚好可以吃完”,由此时间接续篇首完成一个圆环,回到吃牛排的“当下”。然而这时间之环仅仅是一个切面,小说兜兜转转追忆的大半世时光溢出这一平面,撑起了一个饱满而立体的故事之球——北角春秧街“小福建”的背后,不仅由阿嬷相系福建仙潭老家的过往,也频频有着连粤名试图离开又轮回至此的宿命,连首尾吃的牛排,都是春秧街“鸿记”老板专门为老饕连粤名而留的。正是这种时间跨度的对比,恰使时间的厚度,以及由此带来的历史感得以呈现。同样是书写知识分子的题材,《浮图》与十七年前葛亮发表的短篇《无河之岸》在人物设置上有些相似:一个郁闷的男性知识分子,一个颇为强势的妻子,一个可能突破一地鸡毛家庭生活的第三者。但若将《浮图》与《无河之岸》这两个文本并置一处,则能看到故事空间这种表层差异之下,截然不同的时间厚度。《无河之岸》更多的是年轻学者初入社会的载浮载沉,《浮图》显然却是系于香港的一部个人乃至家族的历史:这历史先是牵系着长辈充满烟火祭祀、膶饼与芋粿的福建之根,而后与香港文化融于北角一地并成为北角人的集体记忆,与连粤名儿时成长、新婚甜蜜紧密咬合。可以说,连粤名的人生节点与北角、与香港、与福建都有牵连不断的关系,这和那些鱼系莲荷的绣鞋一起,既塑造了连粤名的审美情趣,也最后导致了连粤名杀妻的悲剧。
广为人知的李碧华小说《胭脂扣》(1984)中,袁永定曾做出一番自我认定:“我是一个升斗小民,对一切历史陌生。”这或从某种层面上说明,当时香港人在英国的长期殖民统治下,面对历史的某种生疏感与无所适从。如果观察葛亮近年小说中的香港书写,我们可以发现他对于时间的处理和看重,实际上与“记忆”是联系在一起的,他的香港书写中对于历史的强调是深入故事肌理的。
一方面,葛亮香港书写的重要标识,是将新移民们的内地记忆作为其文化之根与身份源头,置于故事的远景,不吝在倒叙与时间的交叉中,反复梳理这座城中属于个人记忆的部分。葛亮延续一以贯之的精致,脱胎于某种类似奥斯丁小说的叙事腔调中,又深深牵引着内地的来处。对于《飞发》,是佛山的岭南,是上海、南京的江浙沪;对于《浮图》,则是福建的闽地。另一方面,葛亮也抓住了香港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体认的重要转变——从对历史陌生,到对“集体记忆”的看重。在很多个场合,葛亮总是谈到某种“集体记忆”——这是香港在“九七”前后逐渐发烫的词汇,更是在新世纪后香港历次拆除地标(比如“天星码头”)中被反复掂量。说到底,当一个社会飞速发展,旧除新临时,“集体记忆”免不了频频登场。近年来,香港的“集体记忆”常被葛亮置于小说的近景,比如上述提及的《飞发》《浮图》的北角风物、《拆弹记》的炸弹遗留与启德机场兴衰。
经由叙事时间的处理,葛亮小说中的香港书写所欲达致的历史根脉呈现,与以往南来作家或本土作家的各有侧重皆有不同。在他的书写里,这两道时间线索被同时置于文本之中,得以融汇祖国根系与港岛土壤,并成为其笔下“集体记忆”的注解。因此,观察葛亮如何呈现“集体记忆”,成为切入并理解其小说中香港书写的重要一环。
三
从《谜鸦》开始,葛亮小说中的叙述便有着颇为冷静的状态。“我很喜欢一些前辈作家的小说中所体现的掌故感。”(《叙述的立场——葛亮、张悦然文学谈》)这种掌故感,并非带着自己强烈价值评判进入,而是与故事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在近年的小说中,葛亮常用平实且客观的文字,犹如戏剧中的旁白,在叙述的故事之外,介绍在上述跨度极大的时间中,某一空间的前世今生——北角如是,启德如是,推之香港亦如是。最极端的例子,便是《飞发》中,将考据式文字单辟为颇为规整的独立奇数章节。这一点,使得对读葛亮的小说和他的散文,成为一种非常有趣的阅读体验。《小山河》集中包含着香港十年生活的纠葛、快乐与困惑乃至游移、彷徨,语言典雅中,充沛着饱满欲溢的情绪;在这种对比之中,很容易便能在他书写香港的小说中,感受到其编织故事时试图保持始终的距离感。正是这种距离感,使葛亮在书写集体记忆时,拥有一种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的魔力。
香港书写在葛亮小说中的集中亮相,始于小说集《浣熊》。同名小说《浣熊》,以香港某次过境的热带风暴为名,枝蔓出一个从事诈骗行业的新移民与警察曲折又有点巧合的故事。如果从后见之明而言,这是其香港书写中较早涉及“集体记忆”的小说——像这种每年夏日司空见惯的热带风暴,确实是香港另类的“集体记忆”之一。不过,在小说开篇澳门悬挂“八号风球”时,本港只挂“三号”,或许因为“天上无端响过一声雷”便暗示了这一风暴难以真正成为大台风——毕竟在台风中心并不响雷,正如广东俗语有云,“一雷压九台”。若是葛亮有意设伏笔的话,或许可以视为《浣熊》中这一骗局的注脚。恰得益于叙述时有意保持的冷静状态,我们在阅读时,同样可以较为冷静地进出小说的故事内外看待小说中的细节。《浣熊》集中,多是以“新移民”为人物连接香港本地,但观乎各篇,发端于该集中从传统文化切入的香港书写,于后来重视书写香港的“集体记忆”而言,显然是有准备意义的。这种准备意义,不仅在于将具有距离且冷静的叙述作为一种讲述香港故事的基本方式加以延续,更在于这番叙事自觉背后所逐渐凝聚起的观察香港的目光与态度。
如果说,葛亮的长篇《朱雀》和《北鸢》有着某种家族故事的传奇色彩,他的香港书写恰恰相反。不像王安忆们书写香港那样关注“奇迹性的大相遇”——王安忆所言的“相遇”既大,更带有“奇迹性”;葛亮的“相遇”则渐渐褪去了那种传奇色彩,更多是诞生于日常,笔下的香港因此渐次曲径通往“寻常百姓家”,这是区别于诸多内地或南来作者的香港书写的另一关键之处。而葛亮小说中的日常书写,即便与港台作家的小说相比,也有自己的特色。20世纪90年代末,陈冠中的小说《什么都没有发生》同样书写一代香港人的日常,在看似“什么都没有发生”中,着重展现一种对香港历史的无感与无动于衷的香港“日常”。葛亮则不同,他在小说中展示的香港日常往往是一个深深扎根的故事,新移民们既有着属于个体、属于家族的内地之根,也有着和香港这个地方牵扯不清的在地经验,而这些为香港的日常所吞并,一同构成了香港的“集体记忆”,反过来又影响了香港此地斯民。“每次说香港的故事,结果总变成关于别的地方的故事;每次说别的地方的故事,结果又总变成香港的故事。”借也斯谈香港人在书写香港故事时的困惑、犹疑的这番话,来形容葛亮的香港书写特色,反而有说不出的恰切。
由此,从“日常”这一逻辑出发,葛亮关照的便不仅仅是局限于香港土生土长或新移民的市民,他同样善于看到香港内部的少数族裔与边缘人群。作为华洋混居之城,香港书写之所以复杂,正在于其不仅融于中国,更有面向世界的文化品格。中西的交融同样是葛亮香港书写的重要一环,《浣熊》中的警察便是一个与本港青年相比,“有一种独特的气质。就是,国际化”的“异族”。这样一部分少数族裔,常常在有关香港的作品中以非我族类的面目出现,但在葛亮的笔下,却构成香港日常的一部分,是香港人的面貌之一,共享着属于香港的“集体记忆”。《书匠》中的修复师,所承中西两种修复脉络,却殊途同归于书的修复,同样得见香港此地的日常所拥有的张力。葛亮关注香港社会中并不占多数的边缘人群,与他在非书写香港的小说中的写作逻辑其实是一致的。像小说集《七声》中,便已透露其聚焦边缘人物,以观照历史与社会中心的写作偏好:“‘一均之中,间有七声。’正是这些零落的声响,凝聚为大的和音。”因此,在香港书写中,他确乎更关注香港社会的一些边缘行业,像匠人系列与香港书写结合的《飞发》和《书匠》等,便是二者融合的新面向。
以冷静的叙述笔调,从边缘审视香港的新旧与中西交织,日常、平凡但有力,正是葛亮小说中香港书写的魅力所在。或者说,正是这些不同的面向,展现了葛亮对于“集体记忆”落于香港本地的一种理解。香港的“集体记忆”从来不是单色的,葛亮就像三棱镜,将这一缕缕暧昧不明的光线,分解出了五光十色,由此沿着不同光带,延展出不同的香港故事,呈现出多彩的香港面目。
四
著名的摄影家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 Bresson)为人所熟知的是“决定性瞬间”的摄影理论。按下快门,这充满创造力的一瞬间,正是将时空锁住并固定的一瞬间。小说的创作同样如此,如何在时空的容器中攫取决定性的一瞬,或许是每个小说家用文字对抗时间的关键所在。
充满混杂特质的集体记忆与文化构成,组成了葛亮香港书写中不同故事的底色,由此凝聚起了一个多情且多面的香港。叙述的距离感使葛亮在小说的行进中既能贴地,又有漂浮的部分。器物、匠人、风物、街景乃至气象,这些存在于香港此城的独特之处,以民间且日常的方式,为葛亮所摄获。“我更感兴趣去写的,是民间那些以一己之力仍然野生的匠人。他们在处理个体与时代的关系上,从不长袖善舞,甚而有些笨拙……但是,一旦谈及了技艺,他们立刻恢复了活气,像打通了任督二脉。”(《一封信》)若以布列松的理论观之,葛亮恰恰能够敏锐抓住这其中的从“笨拙”到“活气”一瞬。在香港这一空间之中,他不仅摄取香港之中西新旧,同时也力图使香港脱离“传奇”这一被凝视的位置,而以“日常”去展现这种香港内部的斑斓。“这城市的底里,已传而不奇。”(《浣城记》)无论这种日常如何整饬,也无论有多少可能打破这些平静日常的暗流,葛亮小说中的香港书写都更愿意去观照到这些平凡人生中可能的变数与掀起的波澜,抓住时间之上,落于笔尖的一瞬。
我总觉得,葛亮对于旧时光有着莫名的执着,在他的香港书写里,能够不时读到某种历史斑驳的灰尘。他的书写是扎入现实的,而现实里又伸着根须,对新陈代谢有着天生的悲悯与不舍,于是,在那种保持颇为冷静的叙事态度之下,又总能读到一种往日不复的隐约怅然。昆德拉曾说过,“每部作品都是对它之前作品的回应,每部作品都包含着小说以往的一切经验。”(《小说的精神》),这可以用来对照葛亮的香港书写。或许每一篇小说读来细碎繁密,各有千秋,但林总读之,却总能感到环环相扣,一脉相承——不仅是他笔下的香港历史绵延,市声在耳;他的香港系列小说本身,也能窥见这位从千禧年左右便来港的年轻人,这二十年间与这座城从“他乡”到“我城”的缘起与情深。从新移民到在地学者,香港愈加具体而清晰,记忆愈加将根与城缠绕在一起,并渐次由“此刻”生发出对“此地”从“过去”至“未来”的孜孜求索。
“决定性瞬间”固定了这无数排列组合时空中永远的一瞬,或许说来吊诡,正是这决定性的瞬间制造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三维空间里的永恒,从而达到了与线性时间的对抗。在线性时间的行进中,新旧难免带来大量的遗忘,隔阂因此产生,但怀念也因之诞生。尼采的“瞬间即永恒”从哲学角度重新衡量时间与价值,布列松的摄影理论则依托于摄影来达到作品固定时空瞬间的愿景,而葛亮正是用他的香港书写去摄录这些决定性的瞬间,以对抗遗忘,从而对抗时间。香港的确是一座不乏相遇的城市,而葛亮是一个捕捉相遇一瞬的好手。这些本是时间边缘角落的一瞬,自捕捉的固定时起便从现在变成历史,而历史也能在读者的一次次阅读和阐释中获得重生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葛亮小说中的香港书写,本身也是创造记忆、制造相遇,并且留存住香港“集体记忆”的重要方式之一。
我常常在葛亮的小说中寻找我所热爱的香港——这个香港当然和我的记忆似又非似,它充满着一种褐色的老电影基调,更有厚度,更有来路,也更有一种区别于灯红酒绿的文化积淀和相似于人生营营的感同身受。在北角街头,我曾随手拍过一张照片——红色的叮叮车晃晃悠悠穿街而过,车窗与反光于其上的麦当劳招牌的光影模糊中,是若隐若现的新光戏院。这是一个过客眼中的北角一瞬,却在阅读拉扯着原乡的中国血脉、见证着香港集体记忆的葛亮小说时,一同组成了愈加丰满的香港想象。那辆叮叮车的叮叮当当时常回响在耳际,哼着没有再走几步扎进葛亮小说里的那条春秧街的遗憾。叮叮车前的人流徐徐,车来让道,车走占道,浮城熙攘,万千气象或柴米油盐,皆汇入此番市声鼎沸中。
——关于葛亮研究的总结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