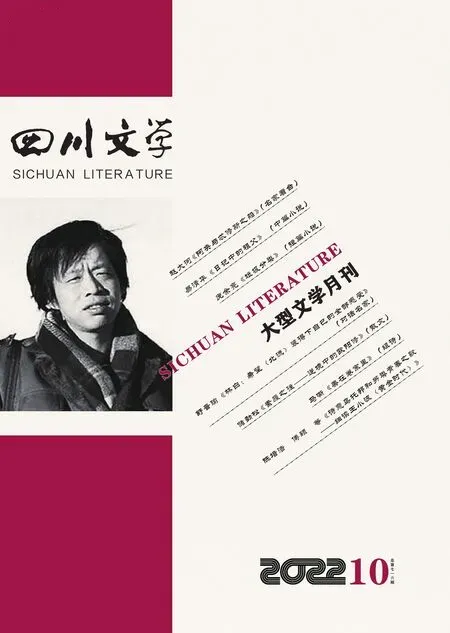一九七五年的老虎沟
□ 文/王倩茜
外 公
一九七四年,黑龙江虎林县的冬天过去了,街面的雪色还有些斑驳,枝叶晃动,藤蔓和花朵纠缠着爬进了一楼的小窗。外婆双手颤抖,从厨房端进来一盆白米稀饭。“胃又疼了?”外公弓在床上,腿也蜷缩起来,听到外婆问话,痛苦地嗯了一声。他攥紧的拳头顶在胃的位置,皱着眉头,眼睛还在盯着贴在墙上的报纸看。一条条过期的新闻在他的眼前飘荡。此时,一只飞虫慢慢爬过他的脸庞。他的脸枯槁得厉害,早已没有初来东北时的英姿。
东北的春天虽然干爽,但也留不住外公南归的心思。他有十几年没见在武汉的大女儿了,比他更衰老的父母也在武汉盼他回家。为了早点回到武汉,外公和外婆前前后后打了好多电话,跟认识的甚至陌生的人,诉说自己的命运。但结果不怎么理想,日子还是无关痛痒地熬着。
早就知道会是这样。外公说。他的眼睛都快要熬肿了,什么药都帮不了他。
外公是有预感的,命运卡在了时代的缝隙里,身不由己就成了一个预兆。早年间,他的父亲被错划“成分”,所以外公自己也成了有“问题”的人。想当年,激情燃烧,他和外婆从北京部队直奔北大荒,在一望无际的荒地上搭工棚,豪气万丈。刚过而立之年,外公便从部队转业了,到虎林农机厂任工程师。尽管是新晋青年,可外公慢慢察觉自己是有“问题”的人,所以开始低着头活着,变成一只绵羊。就这样一年又一年。后来,老绵羊又心甘情愿地到更艰苦的化工岗位刷油漆。
虎林的冬天漫长阴冷,全是黑白底色,一直往东走,边界线就快到了,对面是更远的异国,茫茫一片,没有边际。外公的身上开始沾上油漆,黑白的,或是彩色的,总要费力地去洗掉。
油漆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生活依旧是一成不变的懦弱。外公的眼神更加空洞,头发更加零散,走起路来歪歪斜斜。那些年,他很颓然,渺小得连自己都觉得陌生,疾病也不停突袭。一生中,人的皮囊总是艰辛。好多个冬天就这样过去了,他重复着这样的生活线条:劳动,回家,劳动,回家,同时变得懦弱和迟钝。外公的人生,正在滑进深不见底的隧道。
一九七四年,真正当头一棒、令他猝不及防的,是身体的彻底崩塌。他开始弓着腰走路,大把大把地掉头发,脸颊总是滚烫滚烫的,身体里全是呕人的药味。这一切交汇于心,让外公再也吃不下东北杂粮,饥饿感让他精神更加涣散,他无比思念南方的大米。
胃继续在疼痛,并且已经止不住了。“身不由己”的病症,让外公最终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有一天夜晚,虎林下了大雪,外公收工回家,走在路上的时候,忽然胃里一阵剧痛,他使劲用手顶住胃,跪在地上,呕出几口鲜血。那一晚,他被架上了手术台。那台手术切除了他二分之一的胃,被推出来时,他变成了肋骨凹陷的老人。
时间就是手术刀。在谵妄状态里,外公一遍遍喊着故乡。他在武昌黄鹤楼脚下长大,而今的十多年,他都踩在东北陌生的土地上,屡望黄鹤楼的方向。一次又一次,他都试图理解一千年前崔颢的心境,黄鹤在那时就已经飞走了,一千年后,黄鹤楼也成了他心底深邃的哀伤。
外公从病床上爬起来,看了一眼镜子,这一瞥让他害怕。那是藏在镜子里的死神啊。一个瘦骨嶙峋的老者,一米八五的身体,干核桃一样蜷在衣服里。那些日子里,外公不停念叨,“我们为什么回不去?越是回不去,越是想回啊。背井离乡的日子啊,武汉啊——湖北啊——”
直到有一天,事态有了新的进展。这天,“十堰”两个字忽然出现在妹妹锦锦寄来的信件里。纸张软软的,带着南方的水汽和米香。
外公和外婆把信读了好几遍。
锦锦在信里说,他们已经在十堰待一年了,日渐习惯了这个鄂西北小城的生活。而促使他们来到十堰的原因,是热烈响应国家参加支援三线建设的号召。毛主席说过,中国这么大,光是一个一汽制造厂是不够的,要建设第二汽车制造厂。所以,她和青浦马上就从襄樊农科所申请调到了十堰,重新开启革命生涯。
信里还说,他们曾经犹豫了很久,到底是回青浦的南阳老家,还是去三线十堰。青浦果断,认定在新十堰会更好。她相信自己的爱人。事实上,这个选择真的无比正确。十堰山沟沟里到处都是东北话,十堰需要技术人才,哥哥,你是工程师,嫂嫂是教师,你们能来吗?
书信里还夹着一张黑白照片。锦锦穿着长裙子靠在一棵树下,一个肿眼皮敦厚面容的男人牵住了她的手,目光炯炯。远处是山,再远处还是山。锦锦在照片背面写下一排小字:一九七三年,和青浦在十堰。
外公把照片和书信庄重地锁进了抽屉。他盯着窗外看,大自然一切如故,没人打理的花朵们正自繁茂,越开越艳丽。在东北的几年,即使他身体和精神都抱恙,也完全留意到了,他身边的邻居、朋友、同事,都在背井离乡地搬迁。东北是共和国的长子,东北人嘴里说到三线建设,说到在西部的大山里建设中国的工业基地,又说到中国经济建设史上的壮举,便摩拳擦掌,总像全身都燃起了沸血。
身体衰弱到不由人的时候,外公倒是没有精力想过去参加建设三线。但此时,他恍然大悟,明白了——这正是一场冥冥之中的时代感召。
外公又找出了一沓沓旧报纸,一张一张地翻,零零碎碎地拼凑信息。原来,一九六九年九月,第二汽车制造厂大规模的施工建设在十堰开启了,这是国家三线建设的重点工程。这些年,长春一汽对二汽的支援很强,派出了百名干部参加二汽的筹备,之后又派去了大量管理干部、工程技术人员。
一九六九年,湖北省委下发通知:决定撤销“郧阳十堰办事处”,成立湖北省十堰市。放下报纸,军人的血性再一次汹涌而来。外公自一九五二年从解放军高级防校无线电专业毕业后,一直在部队从事无线电教学工作。当年他和外婆主动要求去边疆,去离家最远的、祖国最北的黑龙江。而今再次报效祖国的方法唯有此,而回家的办法亦如此,十堰,这是时代送给他的新家乡。
手术后,他壮实了一些,凹陷下去的脸颊又平缓了。他看向窗外的远处,树干萌发了新枝,他闻见空气里初夏的松脂味越来越浓,恍若身体终于收到了回音。他毕恭毕敬地敬了一个军礼,无声地说,该走了。
一九七五年的三月,外公和外婆带着一对儿女返回湖北大地。火车南下了三天三夜,最后绕开了江汉平原,往西北奔去。和江汉平原比,沿途的景物索然无味,没有太多变化,接近鄂西北,铁路不断被群山包围。车厢暗一块,又明一块,在山洞里钻进钻出。所有人透过玻璃窗眺望,窗外鲜草的香气引爆了他们的情绪。这应该难忘的一天,漫长又乏味。北大荒的昔日时光一瞬,犹如长夜离去前公鸡长鸣的寂寥,怅然所失。
他们对面同样坐着几个东北人,一问,是从一汽来的。几个人无比兴奋地告诉他们,一汽是在全国人民支援下建设起来的,人员都来自五湖四海,现在战备需要,要建立新的汽车工业基地,他们毫不犹豫就出发了。
锦锦新来的信里也告诉他们,大山里也是通火车的。一九六九年的时候,铁道兵和沿线各地民工就开始在襄渝铁路奋斗了。经过两年挖掘,火车终于通到了十堰。锦锦说,如果你们一九七四年能来,也许可以赶上十堰火车站的竣工。
火车钻进了山洞里,他们看着车窗,窗外墨黑。一切都是那么不可思议,一把风枪,一把铁锹,一辆推车,一双手,铁道兵们打出了通往深山的隧道。火车沿着青色的血管,裹挟着外来的杂草、砂砾,攀爬过一根根枕木。如同他们这些外来者,一边匍匐前行,一边又重振旗鼓。外公看着玻璃外,天色暗下来了,眼前的山群无比荒凉。火车又一次钻进隧道,外公听见身边的外婆在哼唱歌曲,那是俄罗斯民歌《三套车》。三套马车飞奔前方,在寒冬伏尔加河岸上……
沉闷的汽笛声传来,歌声跟着往山里走。
他们也许在时代的隧道面前,显得微不足道。但小城移民的光亮开始闪耀了,肌肤,身体,鲜血,心脏,青春,在这里重新打通。
外 婆
一九七五年,黑龙江邮来的老木料家具占满了十堰柳林沟招待所,外婆一件一件地抚过来,餐桌、扶手椅、五屉柜,全都在。家还在。
整个十堰城就是小村镇,绿色的植被和褐色的灰土,翻个底朝天都买不到一件家具。
幸好在虎林的时候没有丢掉。外公外婆听从了朋友的意见,提前两个月在虎林寄出了一众家当。除了锅碗瓢盆,还有产自东北林场的杉木五屉柜子,那是兴趣浓时二人亲手刷漆打制的。结婚时的大皮箱子则是更早投放到了南方。大皮箱子先来,里面装满了衣服,狗皮背心、大皮袄子,大衣服包裹着小衣服。
外公从包裹里翻出一支口琴,翠绿色的,他用手绢擦拭干净,吹了起来。欢快的曲调,却吹得清清冷冷。他的眼睛越来越蒙眬,青筋在脖颈上抽动,似乎闻见了北大荒的泥土味。四合的暮色里,这里没有听众,曲调如哀悼之乐。
山里清凉,城镇的建筑没有踪影,路上往来的面孔都是陌生的。外婆心里惶惶不安,她侧在餐桌上备课,英语教材来来回回地翻,一页、两页,翻到最后一页,丢到了一边,什么都没有进心里。不,是未知侵入她的心里。外婆和外公一样,也是军人。从俄语专科学校毕业后,她走进了部队,成为中苏合作的翻译。四五十年代的青年人钟情俄国文学作品,外婆也如此,她把虎林想象成契诃夫的小镇。那时候,留住他们的是浪漫、热血和无畏。
后来,中苏关系破裂了,她从部队转业,成了虎林一中的英语老师。原来辛苦跋涉到达的生活,竟是这样一大团混沌。她感到窒息,感到命运即将了了。
好在六堰中学对外婆施予厚爱。一天课间,外婆剧烈地咳嗽,嘴唇没了颜色,当地的同事下午就给她带来一件衣服披着。也有几个学生调皮,一句一句念给了她顺口溜,全是方言,让她哭笑不得。歌谣说:
山沟里面把楼盖,不分城里和城外;
下雨打伞头还歪,工厂里边种白菜;
红薯叶子当菜卖,石头当成黑煤块;
一条街道通老白,电话没人走得快;
汽车进城要人拽,来到十堰跳起来。
这番情景传染了她大半年后,忽然有了剧变。——十堰半导体厂的领导侠义相助,给外公分到了一套老虎沟的房子。老虎沟在山里的平地上。平地是开山填沟换来的,散落着一些农村建房,它们衰老了样的,气息还停留在二三十年前。
半导体厂的大院在老虎沟的一条岔路里,被一股泥巴味包围起来。大院被分割成了两半。一般在大门的右手边,那里全是半导体厂房。大家称之为车间。车间里的物件密集归密集,还是很有心思地隔出了一块空地。空地里忙着的不是工人,而是哞哞欢叫的牛群。
另一半是一排破败的红砖平房。其中有一间是他们的家。平房又叫职工宿舍,里头住了十来户人家,都是外公的同事。每一家门口都放着一个蜂窝煤炉子,炉子里的烟随风摇曳着。墙壁上的红砖已经褪了色,成了灰白的疤。墙壁太老,被撕出了裂痕,风尘不费力就吹了进来。他们是在冬天搬进去的,山里的冬天很快把平房淹没了,进屋没有了热炕头,蜂窝煤烧出的火苗颤颤巍巍。
尽管是一间四十平方米的旧房,却让外婆的嘴角柔软了不少。她用一块大木板隔出了里外两间房,又花上一整天的时间洗水泥地、擦玻璃、糊报纸。冬天的风吹进来,房间里灌满了寒气,也灌满了烟火气。
生活像锯齿。一齿轮一齿轮,磨合得不太轻松。但是,他们终于找到了回家的钥匙。老虎沟——老虎沟和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深山老林黑龙沟没有关系,也从来没有老虎出现过,反而是在市委市政府的所在地六堰山脚下,十堰的老百姓无人不知。贫瘠的老虎沟日日听得见鸟叫声,从湿湿的山谷那边传来。日光远了,暝色弥漫的时候,糯米黄酒的香气也飘了过来,连备课都有了趣味。
外婆的大儿子再一次问,为什么琳妹妹不能上幼儿园?她都四岁了。等过阵子再说。外婆解释说。我们刚刚才安顿下来。
“等过阵子”似乎就是戏言。这里从来不缺丛密的山林,可是没有柏油路,街道都没有,房子全长在山里。同样,这里也没有幼儿园。琳琳却对什么都好奇,她在房间的各个角落翻翻捡捡,总想探索点什么。天气好时,她又在整个半导体大院里漫游、倒立,在蓝天和绿山之间,没有人跟她讲话,她和几只土鸡一起研究泥巴土地,烂泥沾满了全身,她挖出一颗一颗的卵石。
母 亲
一九七五年的春天,更多的人坐上了拥挤的省际长途班车。他们的鞋底还沾着故乡的泥土,混杂的气息让他们的眼神坚毅。武汉还在春天中,我母亲也攀上了班车。她收到了爸爸妈妈的电话,他们已经在十堰的老虎沟整顿好了小家。她的反应很缓慢,久久地盘桓,直到她爷爷拉着她在四十六中请了个假,她才拾掇了几件衣服,跳上车离开。
班车朝大山走着,进入了无边无际的麦茬儿里。这是她第一次独自远离故乡。沿途的植被绿得让眼睛沉迷,浑厚的山越来越多,山路干枯,沿途除了植被,什么都没有。她有点饿了,便从包里掏出新鲜的红豆包吃了几口。她奶奶疼她,一早就颠颠去黄鹤楼边上买鲜豆沙包。豆沙包在嘴里嚼着,她却觉得满嘴都是苦涩。这一次,尽管是去见自己的爸爸妈妈,她却完全不甘愿接受这一场见面。想着从前的经历,她的内心无比陌生。心神不宁间,她把抱在胸前的斜挎包收紧了,包里面有七十多块钱,那是她奶奶塞给她的生活费。她清楚,是全家这一个月的开销。
这是十五年间的第二次见面。
临出发前,她奶奶专门拉住她的手,一字一句地教育她,不管爸爸妈妈怎么对待你,都要说我很想念你们,不然他们会伤心,他们最爱的就是你。
这话她从来不相信。
她的奶奶根本不知道,武昌的胭脂路才是她的胞衣,爷爷奶奶才是她的挚亲。
她的思路被一阵双方压得很低的对话惊醒。她四处看了看,说话的是一个漂亮的中年女人,沙沙的嗓门说着熟悉的乡音。听了一会儿,她终于品出了女人的生活。她是妇产科的医生,一九六九年就进十堰定居了。她们当年是跟着武汉市第一医院搬迁来的,这次刚刚从武汉见亲人回来。车厢摇晃着,女人的表情平坦干净。
终点站到了,在漫长的黑夜,三堰客运站并不安静。班车大概走了十四五个小时,她从车上下来时,小腿直发抖,空荡荡的陌生感从四野八荒袭来。她四处张望,车站的路面高低不平,轮胎印淹进了水里,泥巴被无数鞋子踩得纵横交错。灰蒙蒙的空气里,还有好多人举着纸牌子也在东张西望。她麻木地往前走了几步,大脑里有风在吹,她没有找到她的小姑姑锦锦。
这时,有人在远处喊她名字,那个说武汉话的声音在风里大笑,她一恍神以为又回到了武汉。接着,锦锦姑姑从一团黑暗里跑来,带着一张年轻的脸,刘海被风吹得乱飘。“小微小微。”锦锦姑姑像踩着一团发光的云,两个麻花辫在肩膀上甩荡,有好闻的香皂味。
“欢迎欢迎!”锦锦姑姑搂住了她的肩膀。她记得奶奶说锦锦姑姑有三十八岁了,可眼前却是一个少女,强韧得没有一点年长的痕迹。
一股子味道,你要洗个头了!锦锦姑姑嘴巴依旧不饶人,她听了,放松地笑了,笑着笑着,眼睛也湿润了。锦锦姑姑嘴巴还在继续唠叨,却伸出手把她的头发松开了,一缕一缕地扭成了俏皮的麻花辫。
说说笑笑间,两人上了一辆破旧的吉普车。她把车窗打开,继续打量这个山里的小城。街道没有树木,路上全是厚厚的干泥巴。锦锦姑姑说,这条路是十堰的主干道,叫人民路。她把头伸出车窗外到处张望。吉普车慢慢走在人民路上,风飒飒的,带着一股偏远荒原的冷空气。锦锦姑姑从布袋子里掏出了几片馍馍干,一看便是刚在炉子上炕好的,脆脆黄黄,上面撒了一层白糖。她也没客气,狼吞虎咽几口就吃完了。
吉普车越走越慢,她知道家要到了。她从贴身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老虎沟半导体厂院子”。从车上下来后,她把纸条在手心里窝成了一团,喉咙干干的,她尝试着把爸爸和妈妈喊出声。
一家人
几天的工夫,母亲就和分别多年的弟弟妹妹混熟了。有时小姑父青浦也来帮忙,他抱来一沓旧报纸,在窄小的房间到处粘贴。没有太多家当要打理,她和锦锦姑姑又是跪在地上擦擦抹抹,又是整叠衣物。锦锦姑姑拎来了糯米粉和红豆沙,故作心疼地说这是托人从武汉带来的,两人一阵打闹后,坐在桌边一勺粉一勺粉地包糯米汤圆。锦锦姑姑有时偷偷注视自己的妈妈,来了几天了,妈妈显得兴致不高,总在门口的走廊踱步,或者怏怏地坐在床边,或者伫立在门边,一待就是半天,目光恓惶。
她想和妈妈对视,寻找温暖潮湿的话,然而她失望了。小时候,她就隐隐约约地听说了些什么,十几年前,她在北京才刚出生四十五天,爸爸妈妈就态度坚定地要去东北搭建事业,那里荒无人烟,那里什么都荒凉,可谁都撼动不了他们的决心。她被径直送到了武汉,丢进了奶奶的怀里,留在了妈妈口里富饶的中原大地。这一整趟流程很快,并没有花去几天工夫,像是丢弃了一只小动物。除了她攥着拳头哭到声嘶力竭,没有人流下死去活来的眼泪。
那个时候,她忽然就断了奶,奄奄一息。奶奶整夜整夜不睡觉,搅动着汤勺,熬出一顿又一顿的米糊,终于让她活了下来。她慢慢长大了,却永远失去了爸爸妈妈的陪伴。陪伴她的只有武昌的老砖古墙,抑或是古老的长江和黄鹤楼。好在爷爷奶奶家底殷实,她在物质上从来没有受过苦,早早地就有了棒棒糖,吃上了面包和牛奶。
十几年的漫长日子,爸爸妈妈的爱完全没有眷顾到她,但是奶奶坚持给她讲述爸爸妈妈的英雄故事。奶奶不停地讲,她从抵触到接受。于是,故事就和她的童年捆绑在了一起。
寄养的孩子,从小就幻想修筑一座房子。可没过几年,弟弟便出生在了遥远的北方。又过了十多年,她听说又诞下一个女孩。她从别人口里得知,自己的爸爸妈妈在北方兢兢业业地工作,还成了儿女双全的优秀父母,感动天地。她终于懂了,她从来就不是家庭成员。建了的房子摇摇欲坠,最终变成了一堆碎石,把她的心砸得全是窟窿。她和妈妈鲜有联系,也鲜有牵挂。她清楚地记得,妈妈从未给她写过一封家书。她们假扮成天南海北的母女,仅仅靠汇来的一笔笔生活费维系着血脉。
前两天,半导体院子里的邻居凝视她们母女,说,脸若银盘,眼如水杏,同样是庄重淡雅的美。那是薛宝钗的相貌。若是她和妈妈都戴上眼镜,就和亲姐妹无异。这是回避不了的事实。邻居夸奖时,她偷偷看着妈妈,妈妈正在削土豆,只是淡淡地笑了笑,手里的动作没有停下来。大土豆的皮一点一点被削光,妈妈的眼里全是光秃秃的土豆。
她听说,妈妈年轻时因为端庄貌美,曾被电影制片厂相中,拍摄过纪录片《英雄战胜北大荒》,那个角色美极了,鲜红的大围巾,军绿色的衣裤,在麦田里欣喜地收割麦子,又欣喜地眺望远方。她从没有听妈妈说过这事。当这件事传到她的耳朵里时,她不知道该骄傲还是该怅然。
如果不是因为长得太像,她必定要怀疑自己是从外面抱养的。
她和妈妈互相沉默着,屋子里的气息沉甸甸的,除了弟弟妹妹在喧闹,其余的人都心事重重,发霉了一样。她的童年在妈妈心里一点价值都没有,所以她祈祷变成一个大人。讨好,驯良,绞尽脑汁的小心翼翼。
一天前,她站在房间外听见里面的说话声,“扭扭捏捏的,见到我就躲在锦锦后面,从来不和我亲近,也不叫我妈妈。”
她听了不想作声,只是用手掩住了脸庞。连续的劳作,她纤细的手指已经被脏水侵蚀了。她依旧沉默,她的疼痛在妈妈眼里是模棱两可的,她十五年的生活也是无关紧要的。
她偶尔看到琳琳在妈妈怀里撒娇,心里一哆嗦,开始惶恐不安地假设,倘若换作她自己,会不会全身都要发抖?——她从来没有胆量尝试。她想爷爷奶奶了。
“小微,你在这里习惯不习惯?”
爸爸的语气里满是疼爱,家里唯有他会说武汉话,也唯有他给自己写家信。
“嗯……”
她不知道怎样去表达。
有几次,爸爸把三个孩子喊出去散步,他们一起走出半导体厂的大院,沿着老虎沟的岔道前前后后地走。如幽幽山谷里出来的跋涉者,不知不觉会走得很远。又沿着人民北路继续走。那条还冒着灰尘的沙土路里,沿途都缠绕着灰暗的风景。她好奇地看过去,有快要被抛弃的芦席棚住房,有干打垒,有简易小楼房,还有曾经养着黄牛的荒地。路窄窄的,爸爸的步调很有规律,不受路况的干扰,还是军人的模样。走上十几分钟,他们四个人又钻到简易棚子里看公交车,五路车摇摇晃晃要去哪里,他们一无所知。
一晚,十堰城下起了暴雨,老虎沟沿途都沉淀了泥沙。她正无聊地翻着书本,爸爸下班回家了,他把旧布鞋丢在了门口。布鞋夹杂着泥巴的湿气,把整个房间都困在了泥巴里。妈妈夸张地露出了愤怒,“地刚刚拖好,你又带进来脏水!”
妈妈越说越生气,提起布鞋把它们扔了出去。布鞋在远处哐当一声,溅起黑黄的脏水。爸爸疲惫地应付,“到处是山路,怎么干净得了?”
妈妈把窗户用力地推开,窗外一片湿黑。妈妈满脸都是悲凉感,气息快要被冲散了。“到处是山路,开窗见山,开门见山。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山,一点城市样子都没有。要不是你,要不是你们,我就回大连了!那是我的家乡!”
爸爸没有反驳,他无奈地坐下,静静地抽了一会儿烟。许久才说,“芳华,你不容易,我不该和你争的。我们慢慢会好的。”
妈妈不看任何人的脸,肩膀背对着爸爸。她看见,妈妈的手指穿进头发里扯动着,乌黑头发里开始有了白头发,微微在发光。妈妈忍不住大声哭了起来,“我们在这里要待多久?几年,还是一辈子?”
亦如灌下一碗烈酒。
锦锦姑姑
锦锦姑姑中午又来了一趟,又背来了糍粑、糯米汤圆和红豆沙包,她几番托人从武汉带回的,都是武汉人爱吃的。饭后,妈妈抱着琳琳,温柔地抚摸着她的头发,靠在床头读高尔基的《海燕之歌》。妈妈朝她也招了招手,让她也坐在床头。她怯怯坐了过去,妈妈怜惜地摸了摸她的麻花辫,搂住了她的肩膀头,她没有躲闪开。
她还在上高一,赶着要回武汉上课。不巧半导体厂有要紧事,爸爸一大早就在车间里忙碌。妈妈就带着她一起去三堰客运站。
没有多说什么,她们母女俩只是沿着老虎沟沉默地走着。大山垂直在她面前,空气里有木质的温香,她知道那是太阳炙烤过的植物散发的。十堰的山太多,她觉得压抑。她看见妈妈的白衬衣上粘着米饭粒;她还看到妈妈袖口的布快要裂开了。她几次想张开嘴,却什么都没有说出来。
她看到妈妈的脸塌陷了下去,妈妈摘下眼镜,用指尖揉了揉眼睛,她思忖下一秒也许妈妈会流下眼泪。
可是没有眼泪。
上车时,妈妈递给她几个馒头,妈说,给你的爷爷奶奶带个话,你爸爸现在在十堰半导体厂当高级工程师,你妈妈在六堰中学当英语老师。我们都很好,让他们不要担心。
“我不会再来十堰了,这里什么都没有。”
她的嘴巴开始变硬,她理想里的事情没有出现。她们的交流很安静,她的心似乎被剪破了。听到这句话,妈妈叹了口气,没有再说话。于是她忽然转过了身,直接上了班车。她的眼睛里隐隐闪着泪珠,她依旧没有等到一个拥抱。
她们再也无法亲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