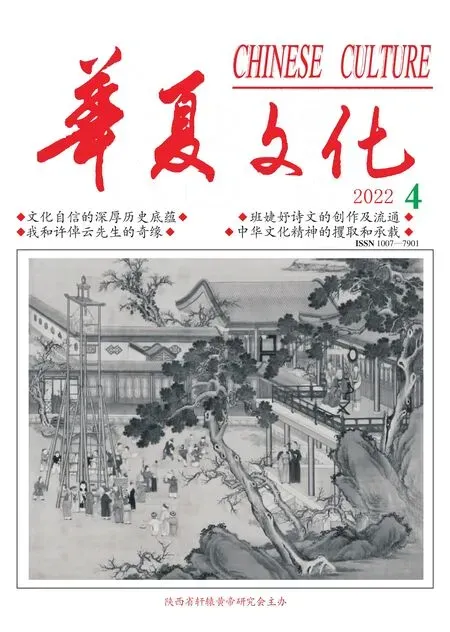海盗与亚历山大、盗跖与孔子
——中西两篇相似的对话
□程 旭
在中西方文化相遇之前,它们就独自孕育出了两个极为相似的故事。这两个故事都以善者对不善者的发难或规劝开始,却都以善者被指责为不善者而告终,并且都以国家产生于恶作为主题。它们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与海盗的对话和孔子与盗跖的对话。它们在历史上究竟是如何产生的或许已无从考证,但它们都在经典文本中被留存至今,并成为作者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者见于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后者见于《庄子·盗跖》。在惊叹二者的相似之余,我们更应深入比较文本的异同,揭示作者思想的特征。
一、海盗与亚历山大的对话及其内涵
奥古斯丁关于亚历山大与海盗的叙述只有寥寥几句。尽管笔墨不多,但是奥古斯丁成功地道出了故事所必需的各种元素:作为皇帝、统帅以及审判者的亚历山大,曾经侵扰海域而如今被俘虏的强盗,以及二人之间的对话。如果只从故事本身来看,这段对话至多只能算得上是一个以开放式结局结尾的故事。奥古斯丁对这一对话的描述是:“一个被俘获的海盗对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所作的答复是非常准确而且正确的。皇帝问那人,他侵扰海域算是怎么回事?他放肆地回答:‘同你在世界各处进行战争一样。我在一艘小船上作战,他们叫我海盗;你率领大舰队作战,他们称你统帅。’”(奥古斯丁著,庄陶、陈维振译:《上帝之城》,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7页)
如果只从对话本身来看,亚历山大和海盗并没有在辩论上分出胜负。一方面,就行为本身来看,人们确实无法否认战争和杀人放火是一回事;另一方面,常识却又使人们无法相信自己心目中的英雄与海盗没有本质区别。然而最重要的是,故事中的亚历山大与海盗也没有进一步给出论证来证明或反驳这一观点。整个故事虽然戛然而止,却又保持了一定的完整性。对话的语境在这里可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作为审判者的亚历山大与正在接受审判的海盗之间本来就没有平等交流的必要,而海盗的回答也可以被视为答非所问。然而,最终保持故事完整性的是奥古斯丁本人。他是整个故事真正的法官。正是他宣判了海盗言论的正确性,也正是他解释或赋予了这番言论唯一的意义。可以说,对话本身和对话语境所创造的开放性都只是为奥古斯丁本人的思想做铺垫。
奥古斯丁直接宣判了海盗观点的正确性,打消了人们出于常识考虑而产生的顾虑。他的理由如下:“在缺乏正义的情况下,主权不就是有组织的土匪帮吗?因为土匪帮派不就是小型的王国吗?他们同样是一群人,在一个领袖统治下,由一个共同的协定相联结,根据一个既定的原则进行分赃。如果这伙罪犯通过招募更多的罪犯获得了足够多的是势力,去占领成片的区域,攻占城市,再制服所有人,然后它就更有资格采用王国的称号。在公众的评判中,它享有这个称号,不是因为它弃绝了贪婪,而是由于它可以更加为所欲为。”(《上帝之城》,第46页。)根据这一理由,奥古斯丁赋予了海盗言论以唯一的内涵:海盗和亚历山大都是缺乏正义之徒,二人的灵魂最终无法得到上帝的救赎,只能接受无尽的惩罚。
然而,这一理由的问题在于:即使人们能够轻易接受海盗缺乏正义的结论,但是断定亚历山大和海盗一样缺乏正义却需要更加有力的证据。仅靠亚历山大所发动的战争和自己的海盗行为是一回事这一论点,难以令人信服。因为,人们可能会以战争和海盗行为的目的不同作为理由,拒绝接受这一观点。
其实,奥古斯丁所说的正义,并非是指社会公平的现代术语。他根据爱的种类的不同将人分为两类。一类人所怀有的是对上帝的爱,另一类人所怀有的是对俗世的爱,更准确地说是对自己的爱。世界上有且只有两个社会,一个是公正的社会,另一个是缺乏公正的社会,它与前者完全对立。任何人必须属于其中的一个社会。只有那些爱上帝的人,才能成为公正社会的公民。他们拥有一切真正美好的品德:注重公共利益、心灵宁静、诚实、爱邻如己等等,并且最终会和上帝同享至福。而那些只爱自己的人,也无法逃离那个缺乏公正的社会。他们只能在那个缺乏公正的社会中,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择手段,不断地侵犯他人的利益,而等待他们的是绝望。正如艾蒂安·吉尔松在《上帝之城》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奥古斯丁根本没有谈到过人类能够仅靠着对世俗的爱就构建出一个公正的社会,他把世俗和邪恶理所应当地结合在了一起。(《上帝之城》,第18页。)
由此可见,奥古斯丁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把亚历山大和海盗归为同类,又是在什么意义上指责他们贪婪和为所欲为。在他看来,他们都忽视了灵魂的幸福,沉沦于世俗和肉体。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以满足自己的欲望为最终目的。他们的本性都是利己主义者。他们与其他人所建立的协议和分赃原则不过是所有不义之人勾心斗角的产物,他们所建立的国家本身就是幻象,他们永远都是孤身一人。倘若其中一人能够获得吕地之戒,那么他将完全漠视这些协议和原则,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为所欲为。他的一切行为仅以满足自己的肉欲为唯一目的。那个被其他人称为国王的人其实就是最接近吕地之戒的暴徒,他所具有的品质无非是更多的狡诈而已,而他最终得到的是将会比其他同类更严厉的惩罚。
以上便是海盗与亚历山大的对话以及奥古斯丁所赋予该故事唯一内涵的全部内容。就对话本身而言,并不完整。而奥古斯丁则基于上帝之城和不义之城的思维模式,赋予了对话以唯一且明确的内涵。
二、孔子与盗跖的对话及其内涵
与奥古斯丁的寥寥数笔不同,《盗跖》篇用了两千字左右的笔墨来描述故事。除了对话过程本身,它还交代了对话的前因后果。对话的发生并非偶然,而是孔子有意为之。孔子对好友柳下季说:“夫为人父者,必能诏其子,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诏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则无贵父子兄弟之亲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为盗跖,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窃为先生羞之。丘请为先生往说之。”(《庄子·盗跖》)由此可见,孔子此番造访的目的就是说服盗跖停止烧杀抢掠的暴行。此外,孔子还向盗跖交代了具体方法:“将军有意听臣,臣请南使吴越,北使齐鲁,东使宋卫,西使晋楚,使为将军造大城数百里,立数十万户之邑,尊将军为诸侯,与天下更始,罢兵休卒,收养昆弟,共祭先祖。此圣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愿也。”(《庄子·盗跖》)孔子说,只要盗跖愿意,那么自己就作为盗跖的外交官,替盗跖游说诸侯,使天下不但对盗跖曾经的暴行既往不咎,而且还封其为诸侯,赠与城池和百姓。然而,孔子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在被盗跖说教一番之后,他仓皇而逃,并向柳下季表明自己的所作所为无异于自寻死路。这些前因后果表明,孔子的愿望彻底落空。孔子与盗跖孰胜孰负见者自知,整个故事的完整性也因此大大超过了亚历山大与海盗的对话。
然而,这种完整性并不能真正说明二人孰是孰非。就像亚历山大和海盗的突然沉默造就的开放性结局一样,孔子最后的狼狈不堪和懊悔也并不意味着盗跖的言论一定就是作者所认为的真理。事实上,这样的结局至多只能说明孔子在盗跖的淫威之下被迫表示顺从。然而,诉诸暴力并不是一种好的论证方式。因此,我们必须暂时悬置上述内容,关注盗跖的言说本身。
盗跖的言论大致可分为五个主题,非孔、非利、至德之世、非君王圣贤、论人之情。非利和非君王、非圣贤其实也是非孔的重要部分,但是就内容本身而言,它们与针对孔子本人的非难不同。本文所说的非孔特指后者。盗跖非孔,最重要的一点是他认为孔子其人虚伪、其言不实。而非利和非君王、非圣贤就是这一点的重要论据。甚至可以说,非孔不是主题而是结论。非君王、非圣贤和其他三个主题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盗跖正是从君王、圣贤如何破坏至德,他们又是如何受利益的诱惑最终死于非命来论述为何非君王、非圣贤的。因此,本文将主要讨论其余三个主题。
针对孔子提出的与天下和好的具体方案,盗跖表示:“夫可规以利而可谏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谓耳……今丘告我以大城众民,是欲规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久长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尧、舜有天下,子孙无置锥之地;汤、武立为天子,而后世绝灭。非以其利大故邪?”(《庄子·盗跖》)他认为,城池、领地、百姓都是会导致非命的外表鲜泽的毒果,只有蠢人才会认不清究竟什么样的东西才是真正美好、具有价值的东西,才会傻傻地被这些东西诱惑,死于非命。
既然如此,那么究竟什么样的东西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呢。盗跖从人的本性出发,给出了结论。他说:“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瘦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悦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庄子·盗跖》)在他看来,虽然人的寿命本身有限,与无穷的时间相比,犹如白驹过隙,不值一提。这有限的人生又可能常常被疾病、死丧和其他各种忧患所困扰,少有真正欢乐的时光。但是,声色味触等等身体的感觉、身体的动静消息、精神的愉悦以及维持生命自身的存在才是符合人的本性的、合理的、正当的欲求。不能追求并满足于这些欲求的人,就与大道无缘。
在盗跖看来,这种欲求既不是毫无根据的空想,更不是死后上帝的恩赐,它是活生生的事实,是生活在至德之世中的人们共有的经验。他说:“且吾闻之,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炀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庄子·盗跖》)由此可见,盗跖认为,在黄帝之前,人们皆能找到与自然、与他人和谐共处的生活方式,既能使身体和精神的欲求得到满足,保全性命,尽其天年,又能不侵害他人和自然万物。
然而自黄帝以来,这种美好的人性就彻底被破坏了。盗跖说,“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舜作,立群臣,汤放其主,武王杀纣。自是之后,以强陵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庄子·盗跖》)他认为,自黄帝以来,人们就开始相互侵害,原本美好的品性丢失得越来越多,而国家也正是在人类堕落的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国家的产生与发展和人类的堕落实际上是一回事。那些被人们尊为天子的人,更是丢失了美好的品质。尧不把天下留给自己的儿子,所以不慈;舜总是遭到自己父亲的厌恨,所以不孝;大禹因为治水,最终落了个半身瘫痪的下场;商汤放逐了自己的君主,武王对纣使用暴力,文王被纣关押了七年。而那些被世人称为贤士的人,更是为了所谓的道德仁义死于非命。至德之厚的沦丧清晰可见。
由此可见,盗跖认为在同一个时代,人类只有一种生存状态或者说社会关系。这种状态或关系的差异只存在于以时代为尺度的纵向比较当中。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因为盗跖与孔子都处在一个仅凭个人力量无法逃避的堕落时代,所以,盗跖、孔子以及当时的所有人都是属于恶的同类。然而,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事实上,盗跖从来没有选择要与孔子一同堕落。与之相反,他在非难孔子为文武布道、招摇撞骗、弄虚作假,看似教化实则戕害他人的同时,也宣布了自己与孔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在他看来,自己自始至终都处在至德的状态。就言论的内容而言,我们与其说盗跖是一个善于诡辩的强盗头子,不如说他是一个道德高尚、洞察秋毫的智者。他并没有谈及自己的暴行,更没有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辩护。他也没有谈及,在至德之世之后,人性沦丧的时代,个人又如何摆脱时代的桎梏,继续保持独善其身、通达大道的状态?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回事。尽管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盗跖确实没有谈及。
或许《胠箧》篇中“盗亦有道”的命题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庄子·胠箧》曰:“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先入,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大盗必须具有五种品质,能够从蛛丝马迹中窥探出哪里有财宝,能够率先士卒,能够为小弟断后,能够判断局势知进知退,能够公平地分赃。这五种品质分别就是圣、勇、义、知、仁。然而,本文认为这一命题与《盗跖》篇中盗跖的言论有很大出处。首先,《盗跖》篇所论述的偷盗行为与人情不符。前者仍是为利所诱,忽视了那些真正值得追求的东西。其次,偷盗行为与至德之世相悖,与人人不相侵害的美好生活相矛盾。最后,在《盗跖》篇中,盗跖多次嘲讽那些笃行仁义的贤臣死于非命。既然如此,他决不会以仁义道德来规范自己,更不会标榜自己具体拥有哪些品质。
因此,本文认为,在《盗跖》篇中,是一位道家学者借盗跖之口阐述自己的观点。《盗跖》篇中的盗跖其实是一位能洞察社会真相的道家智者,他不必为原来那个盗跖的杀人放火行为辩护。他本人能凭借对社会现实的敏锐观察力,对历史真相的了解以及独立思考和怀疑的能力,免于沉沦,独善其身。
总而言之,就对话而言,故事的完整性并没有赋予故事以明确内涵。就对话内容而言,盗跖从非孔、非利、至德之世、非君王圣贤、论人之情这五个方面来论述自己的观点。事实上,盗跖的言论并没有为强盗行为作任何辩解,而盗跖本人也被偷换成了一位道德高尚的智者。
三、两篇对话之异同
至此,关于两则故事及其内涵本文均已说明。本文将根据以上内容,对二者的异同进行总结。
首先,就对话本身而言,海盗与亚历山大的对话以二人的沉默告终,这导致了一个开放性的结局。海盗与亚历山大孰是孰非,海盗最后的话究竟意味着什么成为了悬而未决的问题。而最终解决这些问题,并赋予故事以唯一内涵的是奥古斯丁本人。盗跖与孔子的对话,由于交代了对话的前因后果,致使整个故事与前者相比更加完整。然而,这种完整性也不能说明故事的寓意或内涵究竟是什么。沉默和诉诸暴力都不是一种好的论证所应当采用的方式。二者虽然采用了不同的方式,但事实上都造成了同样的未决状态。
其次,就从未决状态到明确内涵的过渡方式而言,奥古斯丁以审判的形式直接宣判了孰是孰非,并给出了明确的意义和理由。而在《盗跖》篇中,作者将本是强盗头子的盗跖偷换成了道家智者,隐晦地表达了唯一的内涵。
再者,就内涵所表达的人物性质而言,海盗与亚历山大都是不义之城的公民,是一同堕落的罪。而被偷换了的盗跖则成了始终保持着至德之厚的好人。他已不再是那个强盗头子,也不必为杀人放火的行为辩护。孔子则是巧伪之人。
最后,就内涵本身而言,二者的思维模式在两个方面有巨大差异。一方面,二者对事物进行善恶分类的标准不同。奥古斯丁基于精神与肉体、此岸与彼岸相对立的思维模式,将世俗的、肉体的欲望与恶绝对地联系起来,而与之相对的是对上帝、灵魂、和来世幸福的爱,这种爱是圣洁的、美好的、真正值得追求的。盗跖则基于物己对立的思维模式,认为人类自身肉体的欲望、精神的欲望和自身的存在是一个整体,对于这个整体的欲求本身就是正当的,与之对立的则是外在于己的事物。具体而言,这类事物就是诸如城池、领地、百姓、名誉等等事物,盗跖将其统称为“利”。在他看来,这类事物不但与人的本性实际上毫无关系,而且必然会导致那些被诱惑的人们最终失去真正具有价值的东西。
另一方面,二者对国家或社会的思维模式不同。在奥古斯丁的思维模式中,有两个始终存在着的相互对立的社会。前者是以基督为王的正义之城。而后者则是利己之人汇聚而成的不义之城。后者与其说是社会,不如说是装满了蛊虫的罐子。不同的是,那个装满蛊虫的罐子中最终会有一个胜利者,而在不义之城中,所有人最终的结局都是不幸的。事实上,他们彼此之间根本没有社会或国家可言,有的只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而在对话中,奥古斯丁所论述的正是在不义之城中的虚假国家。就对话及其内涵而言,奥古斯丁并没有谈及上帝之城。然而,在《盗跖》篇中,作者则认为整个人类在同一时代只有一种生存状态或社会关系,而国家正是在人类由美好时代向堕落时代过渡的过程中产生的。除此之外,并不存在任何其他国家。然而,个人也未必完全受时代的主宰,他可以凭借自身的修养在乱世中独善其身,保持至德。
四、结语
总而言之,这两篇对话并不像我们一开始所认为的那样,具有极高的相似性。首先,对话人物的身份与对话内容所要表达的内涵实际上并没有直接关联。其次,就奥古斯丁的国家思想而言,不义之城中的国家其实只是海市蜃楼,上帝之城究竟如何才是更为根本的问题。最后,如果说奥古斯丁没有谈论过人类能够仅靠着对世俗的爱就构建出一个公正的社会,那么相较于奥古斯丁,《盗跖》篇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则更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和启发意义,这一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