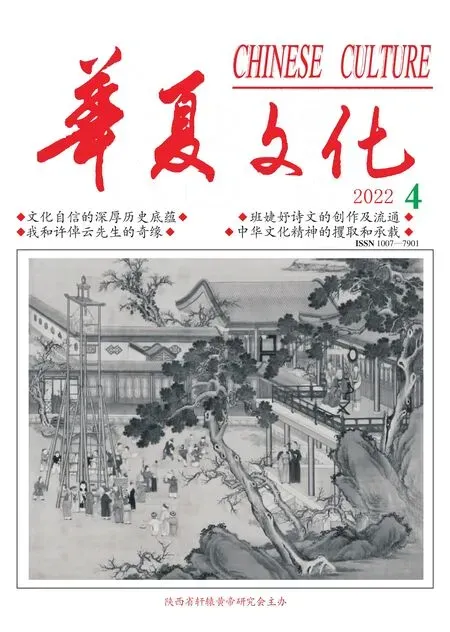略论《孝经》之孝及其困境
□靳天成
构设了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底色的孝文化,不仅全方位地影响了个人生活方式与社会结构,而且还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人民的认知模式和价值观念。《孝经》作为孝文化的经典代表,以“天”作为基本依据,将孝作为天赋之德性,勾画了人以“严父”事天,借“孝”来上合天道、下顺民用的天人合一图景。《孝经》编刻了网罗社会全部人的道德之网,其行事法则约束各级阶层、涵摄生命始终,使得个人在行孝中安身,在尽孝中立命、使得社会在“孝”文化中坚实稳进。然立足于氏族治理的孝文化在面对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时,显示出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这种张力也显明了《孝经》中所固有的理论困境。
一、孝的三重含义
《孝经》一书简约明了,然其涵义不可小觑。《孝经》对孝的阐衍至少包括了三个层面。在德性层面,《孝经》采取始于天道,中于人道,终于政道的逻辑进路。“孝”作为人性在《孝经》中首先具备普遍必然性,《孝经·三才章》有言:“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本文所引《孝经》原文皆以(清)皮锡瑞撰、吴仰湘点校:《孝经郑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为准)。这意味着“孝”上升为天道,进而通过天赋人性的方式将“孝”落实为人的德性。由于孝是由天赋予人的,故而《孝经》认为行孝道是达到天人合一的不二法门,认为人只要能贯彻孝道,就可以“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孝经·感应章》)于是在道的高度上,孝就成为人之“至德”、是“德之本”,是人最应该依循的道德公约。
“孝”作为天性具化到人事关系当中就体现为父子之道,或者说父子之道就是“孝”这种天性。父子之道具体表现为子女对父母的敬爱之心,子女能尽父子之道就要“爱敬尽于事亲”。(《孝经·天子章》)但是《孝经》并未过多阐释德性之孝的内涵,这也显明了《孝经》的孝治之旨,其特色在于不独论德性之孝,而用孝涵摄其他伦理概念,使“孝”通达“至德”和“要道”。《孝经》将“孝”推而广之,涵摄母子之爱、兄弟之悌、君臣之忠。针对士阶层来说,《孝经》认为:“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孝经·士章》)即是将父子之道通过孝的心理机制,延伸到其他领域当中。这意味着孝在其中不局限为父子之间的家庭伦理道德,而渗漏为君臣之间的政治伦理道德。统治者依靠孝这一道德对百姓和庶民进行教化,以实现“民用和睦”、“上下无怨”的政治图景。
德性之孝必然要落实到具体的行为当中,形成种种孝行。在《孝经》当中,孝行依托始终这一范畴进行展开,构筑了多维度、立体的孝行准则。从阶层来看,孝行贯穿于氏族社会各阶层,在《孝经》看来,“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经·庶人章》)《孝经》从五等人分论孝行,孝行于天子而言,则为能敬爱其亲、德加百姓;于诸侯而言,则为能长守富贵、保其社稷、和其人民;于卿大夫而言,则为能服先王法服、言先王法言、行先王德行,进而“守其宗庙”;于士而言,则为能“忠顺不失”、保其禄位、守其祭祀;于庶人而言,则为能“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孝经·庶人章》)由此来看,孝行约束了社会的各个阶层。
其次从时间维度来看,孝既囊括了父母之始终,也贯彻了个人的整个生命历程。对父母而言,《孝经》既要求在父母在世时尽孝,也要求在父母逝世后尽孝。父母在世时,子女要求做到“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孝经·纪孝行章》),以此来表达对父母的敬爱之情。在父母逝世后要“哭不偯,礼无容,言不文,服美不安,闻乐不乐,食旨不甘”,(《孝经·丧亲章》)以此来表达对父母的“哀戚之情”,并且要举办相应的葬礼、挑选相应的阴宅、制作宗庙牌位来安置父母。这样孝行就贯通了“死生之义”,伴随于父母的生前身后。对个人而言,《孝经》规定的孝行也伴随着个人生命的始终。从始来看,《孝经》要求个人保全父母所给予的,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经·开宗明义章》),既然父母全而生之,人就应当全而归之。从终来看,《孝经》规定了人终身的使命和责任,认为“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孝经·开宗明义章》)。从个人这一点来看,孝既有始终,始指基本的孝行,终则指最理想的孝行;孝又无始无终,从时间维度来看,孝在个体生命进程中不断开显,个人也始终在追寻最理想的孝行路程中不断挺立,故而《孝经》认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经·庶人章》)。
天人合一始终是儒者追求的境界,孝作为儒家核心的伦理范畴,孝亦有天人方面的含义。前文已提及孝作为天赋予人的德性,人可以通过立身行道以“通于神明”,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孝经》借神明观念阐发天人观念,最后落实为整个社会“民用和睦,上下无怨”的和谐愿景。神明观念的发展首先起于殷商时期的自然神崇拜,《国语·周语中》有言:“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而后自然神崇拜逐渐发展为上帝崇拜,多神演变为一神,自然神变化为人格神。至西周时期,神明的观念再次变化,“将上帝神与祖先神分离,出现‘德’和‘孝’的道德范畴。并且对祖先神的祭祀在其中尤为重要,周人认为‘追孝’‘享孝’祖先,对祖先‘继序思不忘’,可以祈福长寿,使族类获得幸福,并将其含义从‘事死’扩大到‘事生’,认为孝的对象不仅有父母、祖父母而且包括诸亲”。(张岂之:《中国思想史》,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6年,15页)周人新式的祖先神观念形成了两个后果:一是“孝”由此成为道德伦理范畴,二是祖先是的的确确存在的人,而并非同自然神和上帝神一般只是人想象的产物,这为通神提供了可行性与可能性。
《孝经》接续周人的神明观念,在讲求“生则亲安之”的同时,也注重“祭则鬼享之”。从个人来看,“祭”是孝行的一种,在宗庙祭祀中保证“敬”,那么人就可以“通于神明”。但“祭”更是一种政治行为,是治理氏族社会的不二法门。“祭”必然要求固定的祭祀场所、固定的规格,这意味着执政者必须保有高度的政德,去保有天下、社稷、宗庙。《孝经》的孝治之旨亦在于将“孝文化”推广到整个社会,如果整个社会遵循孝文化,那么就会如周公一般“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孝经·圣治章》)。这一过程概括来说则为执政者能够立身行孝、推广孝文化、不辱于先,即“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孝经·开宗明义章》)由此可见,“祭”是个人贯通天人、治理社会的重要环节,统治者因为要达到“孝之终”,故而要保天下、社稷、宗庙,孝成为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同时统治者通过“孝治”来顺理社会,“孝”又成为社会治理的原则与手段,最后结成“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孝经·孝治章》)的和谐社会。
二、“孝”的理论困境
“孝”在《孝经》中虽然被上升为“先王之至德要道”,但是面临许武等伪孝之人却能举孝廉,李世民弑兄逼父却有贞观之治等社会现实,这种发端于个体,延伸到社会的“孝”观念面临诸多困境。这些现实的困境背后隐含的是《孝经》本有的理论困境。
首先“孝”作为伦理范畴,在《孝经》中是逻辑上的必然存在,而不是应然方面的存在。如上所述,《孝经》认定“孝”是由上天赋予的,是人所当然、人之必然。《孝经》这种结论实际上是出于“例证式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以一再重复的事例,力图证明历史的发展是否是合于‘道’的、“道德”才是决定历史的主要因素”。(张丽珠:《清代义理学新貌》,台湾:里仁书局,1999年,第14页)。从“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的重复事例出发,《孝经》得出“孝”是稳定社会的主要因素,并且赋予“孝”以“道”的高度。这种例证式的历史意识必然要对不合道的反例给予回应,以保证相对的逻辑自洽。但《孝经》并没有对此进行回应,这在理论上直接导致了“孝”是不能成为全部人幸福的必要条件,也就不能解释“非孝”之人得到了实际利益的现象。
其次《孝经》之“孝”意欲融贯个人与社会,故《孝经》分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与庶人五等之孝。从社会背景来看,西周宗法制度的特色是家国不分,政治的上级即是家族的长辈,对上级的“孝”自然能够保证社会的平稳。然而自春秋以来,国与家不断的分离,形成了“诸侯无土,大夫不世”((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七》,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288页)的局面,“孝”这种偏重家庭的伦理范畴就不再适用于政治,《孝经》因此对“士”阶层提出了“移孝作忠”的构想,认为“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孝经·士章》),而“移孝作忠”的理论构设难以适应于时代嬗变,且忠孝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一方面进入中央集权制社会后,忠与孝的对象判然为二,故有忠孝难两全的现实困境。一方面土地所有制转型后,限于士阶层的“移孝作忠”难以涵括愈发丰富的社会阶层,故有《忠经》加以辅充。
最后于个人而言,难以践履完满之“孝”。《孝经》规制个人“孝”,人能行孝悌,则能安身立命;不能行孝悌,则归“五刑之属”。此诚可保全“臣民”行孝,然天子之“孝”则完全依托于天子的个人审视与“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孝经·五行章》)的道德恐吓。引申而来的问题则为:若父不慈、主不仁,臣、子是否要行忠孝,《孝经》对此规定了臣子“铮谏”之责,而全无上位者纳谏之义。对此儒家在面对“世道日微”的现实中,也只能发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737页)的道德感叹。
综上所述,虽然《孝经》构筑了一套以“孝”为理据的社会模型,希冀以“孝”和顺天下,但是《孝经》所勾勒的“孝”文化不能够完全适应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演进,逐渐失却“要道”的政治属性。故而“孝”文化只能借取诸子的部分思想,以焕发生机与活力。
——以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为讨论中心
——从明代朱鸿《孝经》类编著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