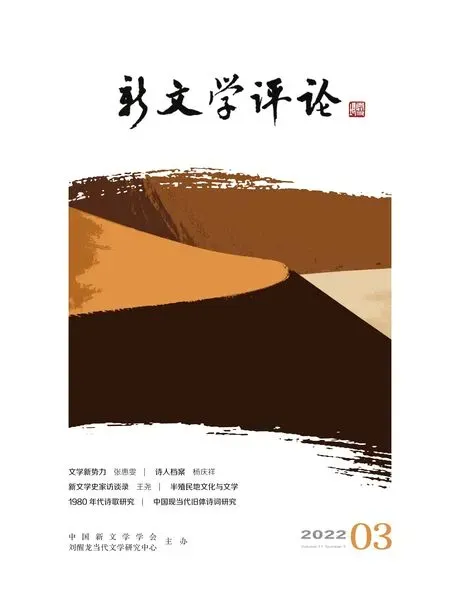半殖民文化语境中的教堂与教堂体验
□ 危明星
“空间不是一个预先存在的真空,从而独自具备各种形式化的属性”①,空间的属性有待于“填充”。作为空间的教堂,不同的文化与时代背景赋予其迥异的空间属性,空间的体验者则因其身份的不同进一步强化了教堂空间的复杂性。在西方,基督教是思想文化的源头之一,教堂则承载了基督教的宗教文化属性,是一个区别于世俗空间的神圣文化空间。而在中国,教堂的空间属性一再演变,由迎合中国社会、在地化为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属性的空间变为一个异质空间。教堂的空间属性在纵横交错的时空中显得复杂多样,给它的体验者带来多重观照维度。教堂与人形成双向互动,带给知识分子不同的教堂体验,身份各异的知识分子,其打量、体验教堂的角度也千差万别。
一、中国教堂空间属性的演变
(一)中西历史文化背景中的教堂
按照《圣经》的记载,耶和华帮助以色列人逃出埃及,并与以色列人立下为其造圣所的约定,于是,在以色列人逃出埃及后四百八十年,所罗门王按照与耶和华的约定开始为他建造圣殿。这座圣殿无比恢宏,“长六十肘,宽二十肘,高三十肘。殿前的廊子长二十肘,与殿的宽窄一样,阔十肘。又为殿做了严密的窗棂……”不仅如此,殿内的装饰也极尽奢华讲究,精金、香柏木、橄榄木等被用来装饰圣殿②。高大、奢华的教堂空间,给人以威严、庄重之感,与世俗的空间隔绝开来,是“人间与天国的接点”③。这一方面安抚信徒的心灵,另一方面凝聚信仰,成为基督徒寄托宗教感情的主要所在,实现人与神的对话。
所罗门圣殿是基督教教堂的原型,但事实上,根据相关研究著作,早期的基督教会及其社团组织聚会的场所主要是犹太会所、聚会所等一些相对简陋的场所,当基督教会处于受迫害的境地时,还一度把信徒的住宅,甚至山洞、地下墓穴作为聚会、传教的场所。随着宗教宽容政策的实行,基督教及其组织的壮大,基督教渐渐成为西方普遍的宗教信仰,教堂也如雨后春笋般遍及西方社会。根据规模大小,西方的教堂有多种样式,英文church指的是普通的教堂,cathedral则指大教堂,basilica则指早期的巴西利卡式的小礼拜堂,而chapel指的则是小型的礼拜场所;根据建筑风格,西方的教堂又可以分为巴西利卡式、罗马式、哥特式、文艺复兴风格、巴洛克式等多种。西方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教堂,如英国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德国的科隆大教堂、法国的巴黎圣母院等。
西方的教堂通过建筑布局与基督教义的结合、文学等艺术作品的阐释,被赋予独特的空间内涵,承载着浓厚的基督教文化属性。如雕塑艺术家罗丹认为:“大教堂强迫人接受信仰、安全、和平的感觉……大教堂屹然直立,是为了俯览围绕在它身边或者仿佛躲在它翅膀底下的城市,为了给远方迷路的朝圣者用作重新集合的地方,当作避难所,成为他们的灯塔,使活人的眼睛能在白昼瞭望到它,使活人的耳朵能在黑夜听到它的三钟和警钟。”④又如,教堂“通过高侧窗宣泄而下的光线象征了光明的基督世界,而半暗的两侧通廊在加深纵深感的同时,更加强了中心的光明……表达人类从世俗走向光明的忏悔与领悟”,而教堂“中心”与“路径”的建筑模式,则象征通往天国的漫长之路和神圣的天国⑤。在西方文学作品中,教堂同样包含着神秘、威严、崇高、救赎等基督教的文化内涵。如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的巴黎圣母院是美与丑、善与恶形成鲜明冲突的神秘空间;而哈代《枉费心机》《无名的裘得》等作品中的教堂一方面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另一方面则通过教堂里的钟声、音乐渲染神圣氛围和人物心理⑥;贯穿艾略特《荒原》的教堂意象,则象征着宗教的救赎……
教堂进入中国社会已有相当的历史,不过中国文化背景中的教堂与西方文化背景中教堂的空间属性大相径庭。
中国最早的教堂可追溯至唐朝初期的大秦寺。7世纪中叶,罗马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传入中国,史称景教。唐朝统治者采取宽容政策,并允许其在长安、周至等地建立景教寺。陕西的大秦宝塔及修道院,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教堂。据学者考证,陕西大秦寺的建筑风格、寺内的塑像、碑刻融合了中西方艺术传统,历史上的大秦寺也几易其主,先后经历了基督教、佛教、道教⑦。由此可见,西方基督教的教堂一经传入中国,就不可避免地体现出在地化特征。基督教传统中教堂威严、神秘、救赎的空间属性多少被抹去。宋元之间,景教主要活跃于西北边疆。由于统治者支持,元朝景教复兴,该时期的教堂又称十字寺,据学者考证,“在中国各地,如蒙古、甘肃、山西、云南、河北之河间,福建之福州,浙江之杭州,江苏之常熟、扬州、镇江等处,皆有聂斯托利派或其教堂”⑧。而景教通常被当作基督教的异端,一般认为,所谓的基督教的正统派在明朝才传入中国。
明朝基督教的传入体现出更加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一时段最先传入中国的是天主教。秉持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思想传统的中国人对外来思想、文化具有极强的排斥性。为了迎合中国社会,特别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士大夫,天主教传教士在传教的过程中采用了灵活、宽容的手段。据相关研究资料,利玛窦等传教士进入中国之后着儒服、学习四书五经,与中国士大夫广泛结交,向中国知识分子展示时钟、地图等新鲜的西方科技,“一切以不引起中国人士的猜疑和反感为原则,先以劝善戒恶符合大众心理的天主十戒为传道的开场白”⑨。经过努力,利玛窦、罗明坚两个传教士终于获准在肇庆建立教堂,为了吸引人们到教堂去,利玛窦一度把教堂称作寺庙。据统计,到1667年,中国教堂明显增加,耶稣会所属教堂159处,多明我会21处,方济各会13处⑩。相对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的传播稍晚。1695年,清政府为满足俄俘的请求而批准建立教堂,史称“罗刹庙”,又称“北馆”。1732年,“北京传教士团”又在东江米巷道建造了一座永久性教堂,又称“奉献节教堂”“圣母玛利亚教堂”或“南馆”。在列强战火的掩护下,新教教堂以燎原之势在中国扩散。
从以上基督教的传播历史可以看出,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始终受到中国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左右。与之相应,教堂的修建也受到当朝统治者的约束。如18世纪初期,罗马教皇规定中国的天主教堂内不准悬挂“敬天”匾额,入教者不许入祠堂、孔子庙行礼。这一规定很快遭到清朝统治者反对,甚至取缔天主教,把教堂改为关帝庙、天后宫、谷仓、公所等。由此可见,中国文化在早期基督教的传播中占据绝对优势,作为人—神沟通神圣空间的教堂,被中国文化改造为极具中国特色的寺庙。为了迎合中国文化,极具神圣色彩的西方教堂不得不一再改变其空间属性,或融合中国文化元素,或改头换面,称作“寺庙”。但随着中国国力的衰弱,基督教传教士在列强炮火的掩护下大批涌入中国,大大小小的教堂遍及中国社会。在半殖民的文化语境下,教堂的空间属性又一次发生变化。
(二)教堂:“闯入”的异质空间
17世纪初叶,因西方传教士屡次反对中国的敬天、祭孔等礼仪,康熙开始颁布诏令,贯彻禁教行动,雍正登基后,严厉禁教的趋势更加明显。总体来看,清朝经雍、乾、嘉、道四朝,禁教的趋势越来越严。如果说清朝前期的禁教出于“礼仪之争”,那么清朝后期的禁教则掺杂了统治者对西方的忌惮与恐惧。随着国力的衰弱,清朝统治者已然失去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底气,面对西方一次又一次的公然挑衅,只能关起门来被动应对。清朝保守的外交政策一方面与西方日益扩张的商业贸易需求形成剧烈的冲突,另一方面也让传教士的传教事业频频受阻。因此,传教士把目光投向了奉行殖民侵略的列强,坚信“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西方的商业扩张给基督教的传教事业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意识到这一好处的传教士便不可避免地参与列强殖民扩张的行径,“最初的基督教传教事业不可避免地与殖民主义的因素羼杂在一起”。
西方列强是以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在与西方一次又一次的被动较量中,羸弱的清政府屡战屡败;通过签订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把侵入中国的口子越撕越大。在签订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过程中,传教士发挥了相当的作用。由于长期在中国传教,传教士精通汉语,熟稔中国文化,在签订不平等条约时,他们自觉自愿地承担起翻译的工作,并竭尽所能促成条约的签订。如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就离不开传教士的“功劳”,美国驻华公使列威廉就对参与《望厦条约》签订的传教士丁韪良、卫三畏给予高度评价:“传教士和那些传教事业有关人们的学识,对于我国的利益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他们充作翻译人员,公务就无法办理。我在这里尽责办事,若不是他们从旁协助,就一步都迈不开,对于往来文件或条约的规定,一个字也不能读、写或了解。有了他们,一切困难或障碍都没有了。”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一方面尽可能保障、扩大了西方的商业利益,另一方面也尽可能地保障了传教士的利益。在近代中国,基督教传教事业可以说就是西方殖民扩张的一部分。
在中国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有不少提及建立教堂的特权。如中美《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规定“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法国则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项保护教堂的条约,“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甚至通过不平等条约最早在我国取得在内地置买房地产的特权,进一步扩大了传教士的特权,《法国教堂入内地买地照会》规定:“嗣后法国传教士如入内地置买田地、房屋,其契据内写明‘立文契人某某(此系卖产人姓名)卖与本处天主教堂公产’字样,不必专列教士及奉教人之名。”这一条约实际上默许传教士在内地修建教堂,并借由修建教堂置办地产,获得财产权,这无疑对中国主权造成了侵犯。而《中法北京条约续增条约》等条约则赋予传教士“还堂”的权利,传教士借此条约不仅要求清政府归还教堂旧址,还趁机霸占寺庙、房屋等田产。由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列强的支持、清政府的一再纵容,教堂开始遍布各地,“西方传教士从沿海的通商口岸深入内地的穷乡僻壤自由传教,从一望无际的漠北到烟瘴笼罩的苗寨,到处建立起矗有十字架的教堂”。分布于全国各地的教堂事实上构成对中国社会的点状殖民宰制,这种殖民控制是多层次、不完全、碎片化而又强烈的半殖民主义控制。传教士借由不平等条约获得修建教堂的特权以及附属的财产权,构成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由于各殖民势力在华的控制范围以及程度不一,依附于本国殖民势力的教会及其教堂分布、控制范围也不同。分布于全国各地的教堂,正是各国殖民势力在我国殖民控制的写照,也是半殖民中国社会的缩影。
传教士借不平等条约获得修建教堂的“合法权利”,为民族冲突的爆发埋下伏笔。1860年以后,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在各地霸占田产,肆意扩展教会势力,“遍布中国农村的天主堂一般都拥有大量土地,农民称呼天主堂为地主堂”。传教士霸占田产不仅侵犯了普通农民的合法权益,也侵犯了拥有大量田产并以此为生的大量官绅的权益,因此,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教案频频发生,屡禁不止。1851年的定海教案,因“给还旧址”引发,教徒侵占寺庙,由此引发冲突。在1860年代的贵州教案中,清政府最后屈服于列强淫威,竟把提督衙门拨给天主堂使用。在1862年的衡州教案中,民众愤怒于教会的“邪佞奸污”,焚毁教堂。在其后的重庆教案、天津教案、济南教案等教案中,教堂亦成为教案爆发的导火索以及冲突发生的所在。在教案中,大刀会、义和团等民间组织、团体的加入进一步加剧了中西冲突,据统计,天主教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教堂损毁的估计有四分之三”。源于宗教传播所引发的冲突实质上变成了民族冲突,演变为中国人民自发的反殖民斗争。在冲突中,教堂就是斗争的主要空间。
在半殖民的中国,教堂是在西方列强的战火硝烟中强行“闯入”中国的。教堂进入中国的这一方式从一开始就为其打上了文化霸权的烙印,也为其成为中西民族、文化冲突的主要场所埋下伏笔。教堂进入中国社会后,其实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在地化,在半殖民的中国,教堂是一个异质空间。教堂进入中国社会的漫长的历史中,教堂的空间属性几经变迁:由一个异域的宗教空间在地化为一个与中国本土寺庙表面无异的宗教空间。在半殖民的语境下,教堂的空间属性又一次发生变化:一方面,西方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赋予教堂空间以政治、文化霸权;另一方面,传教士为了传教又通过教堂空间及其附设机构把西方的文明成果带给中国,教堂成为现代性的萌生之地。在半殖民的文化语境中,无论在共时的层面上还是在历时的层面上,作为异质空间的教堂始终矛盾重重,其空间属性是含混、多元的。
二、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教堂体验
随着中国国门的打开,教堂开始成为作家日常生活经验的一部分。教堂这一异质空间,从不同层面参与作家的成长,影响到作家的知识结构,形成其复杂的教堂体验。通过作家在纪实性文学作品中对教堂的记述、回忆,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知识分子在半殖民文化语境中充满矛盾张力的文化心态。作家所看到的教堂,经由教堂所获得的文化体验,无不带有半殖民的文化烙印,反映出半殖民中国知识分子对教堂这个“闯入”的异质空间复杂而真实的感受。
鸦片战争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传教士取得在中国建立教堂的“合法性”。因此,他们深入中国内地,足迹从沿海一直延伸到内地的穷乡僻壤,“从一望无际的漠北到烟瘴笼罩的苗寨,到处建立起矗有十字架的教堂”。上自知识阶级,下至贫苦百姓,教堂都成为其日常生活经验的一部分。作家的传记、访谈等纪实性文学作品真实地再现了教堂对作家、普通百姓的影响,这些作家中,有的与基督教关系较为亲近,有的则反之,由于与基督教关系的亲疏远近,他们的教堂体验也就各不相同。
(一)真实而个人化的教堂体验
在现代中国作家中,冰心、林语堂、许地山、曹禺等几位作家与基督教关系比较密切。教堂构成了他们个人化的人生体验,进而影响其文学创作。
1914年,冰心入读美国人办的公理会贝满女子中学。她后来在自叙中回忆了当时读书的情形,其中一段记载颇有意味:
我们每天上午除上课外,最后半小时还有一个聚会,多半是本校的中美教师或公理会的牧师来给我们“讲道”。此外就是星期天的“查经班”,把校里的非基督徒学生,不分班次地编在一起,在到公理会教堂做礼拜以前,由协和女子书院的校长麦教士,给我们讲半小时的圣经故事。查经班和做大礼拜对我都是负担,因为只有星期天我才能和父母亲和弟弟们整天在一起,或帮母亲做些家务,我就常常托故不去。
由这段文字可以看出,作为学校里的非基督徒学生,冰心也要参加教堂礼拜,只是教堂礼拜对尚且年幼的冰心来说却是负担,她的兴趣并不在教堂礼拜,而是与家人待在一起。与教堂礼拜相比,家庭的温暖与亲人间爱的体验对冰心更具有吸引力。年幼的冰心不得不在周日教堂礼拜的负担与亲情之间寻求平衡,这似乎可以看出冰心“爱的哲学”的早期雏形。“爱的哲学”是冰心创作的底色,她的这一创作理念,融合了中西文化,是在自己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的基础上建立起的一种调和的观念,“所依据的并不是一个真正宗教信仰中的上帝,冰心借助基督教中的上帝观念,人的观念,大同世界的景观,天使形象等等,以及从泰戈尔、歌德那里接受的泛神思想影响,在自己生命体验的基础上,结合宗教感悟和审美感觉,进行了一系列哲学性的调和,在强烈的入世救人精神的激励下,建立起来一个爱的信仰”。早期的教会学校生活经历,给了冰心最初的宗教体验,但在后来的创作中,冰心所建立的创作理念虽有基督教的影响,却更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或许,早期求学中教堂礼拜的负担就为冰心日后“爱的哲学”的形成埋下了伏笔。
于林语堂而言,基督教则是“最难撕去的一种情感”。林语堂与基督教最早的联系,源于他做牧师的父亲林至诚,其父早年的传教经验无疑成了林语堂人生体验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常常不断地为人做媒,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令鳏夫寡妇成婚,如果不是在本村礼拜堂中,就是远在百里外的教堂中。在礼拜堂的教友心中,他很神秘地施行佛教僧人的作用。”在中国农村,作为牧师的林父就像是“群羊的牧人”,在广大教民心目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父亲的榜样与家庭氛围的熏陶,林语堂早年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但随着阅历的增加,他慢慢发现了基督教的伪善,对基督教教义产生怀疑。据林语堂回忆,清华同事刘大钧的一番话,斩断了自己与基督教的最后一丝联系。林语堂始终想摆脱与基督教的联系,并因此而经历了“长远而艰难的程序”,内心遭受了“许多的痛苦”。林语堂为什么一直想摆脱与基督教的联系,除了基督教的伪善还有没有其他原因?答案是肯定的。其实,林语堂早年所获得的宗教体验带有极强的中国特色,做牧师的父亲在乡村所充当的角色与中国的佛教僧人并无区别,其父所在的教堂,与中国传统的寺庙、道观并无区别。在童年的林语堂眼中,这样的父亲或许威风凛凛,但随着其知识经验的增长,他渐渐明白基督教之于贫苦农民的意义——无非是求财、求子嗣,获得治外法权的保护,而这一切,正来源于半殖民中国土地上基督教的特权。因此,林语堂后来在自述中写道:“今日我已能了解有些反基督教者对于我们的仇恨,然而在那时却不明白。”在成长的过程中,林语堂渐渐明白基督教及其教堂的侵略本质,因此离教堂越来越远。
有研究者认为:“许地山是儒,同时也是佛,也是道,也是基督。他什么都是。什么都是,意思就是说,什么都不是。亦儒、亦佛、亦道、亦基督结果也就等于非儒、非佛、非道、非基督。”确实,许地山相对其他作家而言,其宗教体验与信仰更为混杂。1916年,二十多岁的许地山在福建漳州英国人办的一所教堂里受洗入教;从此以后,基督教徒似乎就成为许地山的一个身份象征,“不管到何地,在‘主崇拜日’的时候,他必到附近教堂里和教友一起认真地做弥撒,严格遵守教会的一切仪式规则”。不过,除了基督教,许地山也吸纳佛教的空无哲学,儒家的入世精神,道家的清净无为观念,并以一个宗教学者的身份研习基督教、佛教、道教的教义与精神。许地山尽管是一个受洗入教的基督徒,但却更是一个冷静客观的宗教研究者。因此,对许地山而言,早年在教堂受洗入教的经历似乎只是增加了他一层基督徒的身份,构成其价值理念的一部分而非全部。
教堂之于曹禺,则更像是一个寻求人生意义、寻找生活道路的处所。据曹禺回忆:“我接触圣经是比较早的,小时候常到教堂去,究竟是个什么道理,我自己也莫名其妙:人究竟该怎么活着?为什么活着?应该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所以,那时候去教堂,也是在探索解决一个人生问题吧!”教堂对年幼且迷茫的曹禺具有极大的诱惑力,教堂的钟声、弥撒仪式、复活节仪式都吸引着曹禺一次又一次跑到教堂去——“当他第一次跨进法国教堂时,他被吸引住了。当风琴奏起弥撒曲时,使人进入一个忘我的境界,他也被消融在这质朴而虔诚的音乐旋律之中。似乎这音乐同教堂都熔铸在一个永恒的时空之中。由此,他迷上了教堂音乐,特别是巴赫谱写的那些献给天主教徒的风琴曲。”幼年时的教堂体验对曹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但教堂独特而神秘的宗教氛围,却形成他生命底色的一部分,并时时反映到其创作中。
从上述几位作家早年的生活经历来看,教堂这个在半殖民语境下大量“闯入”中国的异质空间,却成为他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场所,并间接地对其价值理念、创作观念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只是,这种影响是有限的。对少年冰心而言,周日的教堂礼拜不过是个负担,并不得不在这种负担与家庭的温暖之间寻求平衡;林语堂则从奔波于各地教堂的乡村牧师身上看到了基督教世俗的一面,并在日后的成长中发现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侵略本质;许地山自从入教后虽每到一个教堂,必和教友做弥撒,严格遵守教规,但其价值观念却是混杂的;幼年即对教堂产生浓厚兴趣的曹禺,到教堂去则是为了解决人生困惑。在半殖民的语境下,即使是与基督教保持密切关系的作家,其教堂体验也剥去了宗教神圣的外衣,真实而富于个人特色。无论如何,遍布中国各个角落的教堂,为作家们打开了一扇了解西方文化的窗户。
(二)教堂怪象
对半殖民的中国社会而言,教堂不仅仅是一扇了解西方文化的窗户,也是一面反映半殖民中国千疮百孔社会现实的镜子。在半殖民的中国社会,传教士及其教堂因西方列强的庇护而具有政治与文化特权;同时,教堂又往往因其空间特权而引发一系列冲突。可以说,近现代的中国教堂,汇聚了半殖民中国的种种光怪陆离的景象。
在萧乾的回忆里,教堂是政治难民守望的虚无之所,也是愚昧百姓汇聚的乌合之地。十月革命后,大批俄国贵族流离失所,成为政治难民,他们曾经的仆人也被迫背井离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俄国在中国建立的教堂竟成为穷苦白俄守望的精神圣地。萧乾在回忆录里写道:“有些穷白俄就徒步穿过白茫茫的西伯利亚流落到中国,在北京住下来。由于东直门城根那时有一座蒜头式的东正教堂,有一簇举着蜡烛诵经的洋和尚,它就成了这些穷白俄的麦加。刚来时,肩上还搭着块挂毡什么的向路人兜售;渐渐地坐吃山空,就乞讨起来。”事实上,在中国教堂所能提供的庇护非常有限,流落到中国的白俄只能与贫苦的中国人一起到粥厂乞求施舍。在生存的绝境里,贫苦的中国人不得不驱逐与自己分一杯羹的白俄难民。无可奈何之下,白俄难民只好“踱回”自己心中的麦加。但对最基本的生存欲望都难以保障的白俄难民来说,精神上的麦加——东正教堂不过是一种虚无的存在。因此,毫不令人惊讶,穷困潦倒的白俄难民只能客死他乡。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本应为受苦的教民提供庇护的教堂失去了效力。在萧乾的记忆里,教堂还汇聚了一批愚昧的乌合之众:“我在旧中国的农村(仿佛是香河县)甚至还看到过一次神召会‘做礼拜’。教堂院子里跪了几十个信徒,每个人面前摆了几块砖。信徒们祈祷时,就用头硬往砖头撞,撞得青一块紫一块,以致鲜血淋漓。然后就像疯子般狂喊乱叫起来,说是在‘讲万国方言’。”萧乾回忆中,这座怪力乱神的教堂,折射出旧中国人民愚昧无知的一面。
民族冲突最激烈的时刻,教堂也往往首当其冲。据相关研究资料,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北京被焚毁的教堂就有二十座。在非常时期,像林语堂这样与基督教关系亲近,经常出入教堂的中国教民也就招致普通百姓的仇恨,“跟在洋枪洋炮后头进来的”成为一般百姓对基督教及其教堂的普遍认识。所谓跟在“洋枪洋炮后头”有两重含义:一是由此而引发冲突,另一种含义就是附着在“洋枪洋炮后头”的特权。因此,鲁迅在《灯下漫笔》中写道:“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战争,稍富的迁进租界,妇孺则避入教堂里去了,因为那些地方都比较的‘稳’,暂不至于想做奴隶而不得。”鲁迅的这篇杂文旨在批判国民性,但也深刻反映出教堂之于普通百姓的意义——战时的避难所。除了充当战时的避难所,教堂有时候也发挥慈善机构的作用,丰子恺的漫画《最后的吻》就揭露了这一现实:在漫画中,穷困的母亲不得不把自己幼小的孩子送进教堂里附设的育婴堂,教堂成为走投无路的百姓无可奈何的选择。由于基督教及其教堂拥有的特权,“吃教”也就成为旧中国社会的一种特殊乱象。据萧乾在回忆录中记载:某堂兄为了糊口,在教会里谋了一个职位,但作为中国人,堂兄本质上并不信基督教,因此,只好在教堂里装作信教,回家则“既念《金刚经》,又信狐狸精”。对“吃教者”而言,作为权力空间的教堂造成他们信仰分裂,不得不在教堂和家这两个代表不同文化内涵的空间夹缝中艰难求生。在半殖民的中国,教堂既是战场也是避难所,既是特权空间也是慈善机构;普通百姓既借教堂谋生,又从内心深处深深排斥教堂。他们对教堂的体验,“糅合着痛楚与憧憬,悲哀与欢乐,怨恨与羡慕等复杂心情”。
诗人贺敬之的经历最能反映教堂在中国广大农村的现实。贺敬之出生于山东绎县贺家窑(今山东枣庄市郊)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在贺敬之家茅草房的背后,就是贺家窑教堂。贺家窑教堂是一座天主教堂,属于兖州教区。贺敬之全家都是天主教徒,但贺敬之的父母忙于养家糊口,入教也只是一种养家糊口的策略,并不算虔诚的天主教徒。因为入了教,贺敬之和他体弱多病的弟弟也确实得到帮助,吃过教堂给的药,渡过了难关。除了物质上的帮助,教堂也是贺敬之精神启蒙的一个重要场所。贺敬之很小的时候便经常跟随奶奶去教堂祈祷。除了贺家窑教堂,贺敬之还经常到附近涧头集宏伟的大教堂里瞻礼,“性格平和的贺敬之,深受这种虔诚、庄严、崇高气氛的感染,悲悯人类的博爱情怀,拯救苦难的一片善心,在他的心中肃然启蒙”。此外,童年时的贺敬之在私塾上了半年学后,便转入天主教堂办的小学学习新学。天主教的熏染与小学新学的学习为贺敬之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基础,在天主教堂的小学里,贺敬之就表现出艺术创作的天赋,其创作的《黑山远足记》得到了老师的表扬和鞭策,使贺敬之一直铭记于心。虽然天主教及其教堂给贺敬之的成长带来不少正面影响,但随着环境的变化,教堂渐渐成为贺敬之成长中的一个幻影。后来,贺敬之的父亲想凭借天主教徒的关系,把贺敬之送到教堂里当修士,但一心想求学的贺敬之拒绝了,并进了一所私立小学。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民族救亡的呼声传入学校,贺敬之受到当时进步国文教师的影响,加入进步运动中,担任拉丁文字学会会长,并给北京拉丁化新文字总会写信,得到总会的鼓舞和支持。在私立小学毕业后,贺敬之又投考了滋阳简师,在战火硝烟中,贺敬之艰难求学,直至考上延安鲁艺。对于像贺敬之这样贫苦的农家子弟而言,教堂所提供的有限的物质和精神帮助却在其成长中发挥了巨大的能量。只是,贺敬之们选择教堂多迫于艰难的生存环境,随着知识与阅历的增加,他们渐渐认识到教堂在中国的本质,因此,才会毫不犹豫地与教堂划清界限,投奔新的人生之路。
结 语
西方列强用武力强行打开了清朝闭关锁国的大门,打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传教士借机大量涌入中国,在中国的广袤土地上建立教堂,教堂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一部分。更多的作家得以近距离感受教堂,并形成其真实而个人化的教堂体验,看到半殖民语境下中国教堂的种种怪象。在体验中国教堂中成长起来的作家,其对教堂的感受无不带有特定时代的文化烙印,现代性与民族主义的纠缠始终是他们最普遍的文化心态。在半殖民的中国,不论与基督教关系的亲疏远近,教堂带给作家们的体验都是复杂的。他们真切地感受到教堂这一“外来强势力量的威逼与挤压”,既受到西方先进文化的熏陶,也看到落后中国的惨状;既从中受到基督精神的感染,又看到附着在教堂背后的殖民侵略与文化霸权。整体来看,教堂是近现代中国“半殖民性”的缩影;作家们的教堂体验,体现的则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半殖民与解殖民”的“主体走向与风貌格调”。
注释:
①亨利·列斐伏尔著,刘怀玉、罗慧林译:《空间的建筑学》,选自陶东风、周宪主编:《文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②《圣经》,中国基督教协会2013年印发,第53~93页。
③斯坦克利夫著,吴丹青译:《教堂建筑》,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
④罗丹著,啸声译:《法国大教堂》,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191~192页。
⑤彭建华:《基督教堂建筑空间的发展与演绎》,《建筑与文化》2008年第8期。
⑥张宣:《哈代小说的基督教堂文化检视》,《淮北煤炭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⑦关英:《景教与大秦寺》,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
⑧朱谦之:《中国景教》,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页。
⑨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3页。
⑩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