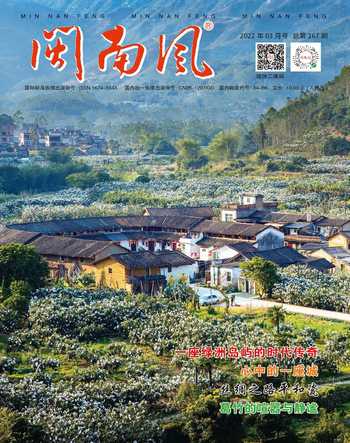丝绸之路平和瓷
黄荣才
我曾经在平和县五寨乡的洞口陂沟窑捡到一块瓷片,小小的,它斜插在泥土之中,一角露出泥土,如果不经意,绝对会被忽略,但因为寻找,它进入视线之内。把这块瓷片从泥土之中抽出来,放置在巴掌中,有种泥土的温暖和青花的温润在掌中散逸。在旁边小河里冲洗之后,这块瓷片显露真容,淡雅的青花,有种纯朴之美,乖巧的柔顺。这是平和瓷历史的一个小小的碎片,类似于烧制平和瓷高岭土中的一个土块,甚至就是一粒沙土,宛如它出土前那小小的一个角,但因为有这个角,明末清初的平和瓷就得以从历史深处走出来,好像镜头里淡出的技巧,让我们可以搜寻到历史的那一段。青花瓷、彩绘瓷和素三彩瓷,这当年平和窑瓷器的三大种类就一直回旋在脑海。
去五寨洞口陂沟窑,自然是为了寻瓷,平和瓷的瓷花一直闪耀在脑海之中,独具平和区域色彩。因为“克拉克”商船,让平和瓷的身影从历史深处拉近。如果不是这艘葡萄牙“克拉克”商船,也许平和窑青花瓷留给我们的是另外一种背影。但历史没有如果,历史只承认存在。远在明万历三十年(1602),荷兰东印度公司截获了一艘商船,这也许仅仅是商业竞争的行为,历史的真相已经被埋在厚厚的尘埃后面。无论如何,这样的截获很容易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不会泛起多少涟漪。但因为船上那近10万件的青花瓷器,这艘葡萄牙“克拉克”商船被烙上历史的印痕,在时光的河流中沉浮。偶然之间,“克拉克”商船让我们窥探了某种真实,其实能够留下身影的历史片段很多纯粹就是偶然。

洞口陂溝窑处于寨河村西南? 2000米的岩内海溪左岸陂沟,车从五寨乡政府出发,几分钟就到了。铺设完整的生态停车场,一棵棵树绽放春天的气息,嫩芽在阳光下欢畅地舒展,类似充满希望的舞蹈。刚刚完工的绿化工程,小草已经开始站稳草根,有几棵茶花那些移植带来的蓓蕾已经绽放。沿着鹅卵石铺设的道路走数十米,在洞口陂沟窑的管理房,因为保护窑址工程捡拾到的数十块碎瓷片,铺在几张报纸之上。曾经依靠一块碎瓷片的想象一下子就清晰丰富起来,仿佛武侠高手,从修炼而成的一丝真气,突然感受到澎湃的力量在涌动。盘的碎片、残缺的罐身、烧制变形的香盒、拇指头大小的香料罐等,我一下子有眼花缭乱之感。虽然从资料里早已得知,洞口陂沟窑最主要的产品是青花瓷盒,其次为瓶、罐、碗,少量盘、碟、盅、盏,造型大多规整端正,器表线条流畅、匀称,文字可能放飞想象的空间,但也可能限制目光的抵达,目睹总是比想象来得直接,所谓的“百闻不如一见”大略就是如此。尽管是碎片,但可以看出,洞口陂沟窑瓷器的装饰图案非常丰富。
沿着河石铺成的步行道前往窑址。洞口陂沟窑原来和平和县数以百计的窑址一样,隐藏在山野之中,掩映在现实的泥土和时光的帷幕之下。1998?年?6?月,洞口陂沟窑发掘,发掘面积?162.5平方米,这不大的一块区域,揭露出保存较好的窑炉两座,均为由火膛、窑室和出烟室构成的横式阶级窑。多年前曾经来过,当时前往窑址的是一条小河流的山间小路,杂草丛生,行走困难,小心翼翼还有点担惊受怕,担心一脚踩空或者有蛇或者蜥蜴等小动物窜出,但现在步行道修成,就有了轻松漫步的雅致,寻瓷就有了从容、平和的淡定。洞口陂沟窑的两座窑炉,成前后、上下排列,总体呈西北——东南走向。两窑间距5米,高差约4米,均背依山坡,面向溪流。当年的窑火不再,也没有窑工穿梭忙碌,只剩下两座窑址,成为勾引想象的触发点。这个触发点其实也不是当年的全部,两窑火膛部分都遭受破坏,窑顶均已坍塌,经历时光,总是有些东西会毁坏或者消失,时光之下,能够一成不变的已经成为奢侈。
值得庆幸的是,洞口陂沟窑窑址的形制保存较为完整,窑墙仍保存一定的高度,没有委顿到地面,和地面的泥土融为一体或者消失,而是依旧以站立的姿势,呈现当年的存在。两窑炉的形状结构大体相同,平面都是长方形,各窑室、出烟室单体也是长方形,只不过是横的,形态一样,只是姿势不同。窑底都是斜坡式,由火膛、窑室、出烟室三大部分组成。每间窑室的前端左右两侧都各有一道窑门,两道窑门之前的连接线为长条形,截面呈凹弧形的燃烧沟,低于窑床。沟底和侧壁都有坚硬的青灰色的烧结面,这种坚硬和色彩是当年烈火焚烧的结局,窑墙上那瘤状突起被称为“窑汗”,透露出当年的高温反复炙烤的信息。部分残留炭粒和灰烬,没有随风飘散,留在那里传递信息。沟底与窑门底面持平。

从火膛到窑室、前后室、窑室到出烟室之间都设有隔墙,下方都有一排整齐的栅栏状的通火孔,各墙孔数不等,单孔都是竖着的长方形。窑室内,从燃烧沟到后隔墙之间的斜坡窑床上,自左而右成排铺设支垫匣钵的窑底砖,自前而后呈阶梯式砖台。这种铺垫用砖多为楔形,水平铺设,大端朝前,小端朝后,层数不等。可以想象,当年平和瓷的胚体就是以不同的姿势排放,接受窑火高温的炙烤,完成涅槃一般的变化,从高岭土到胚体到成品,期间实现了多少的斗转星移,所有的文字都仅仅是一种描述,唯有平和瓷瓷器本身,才置身其中。出烟室底部未铺砖,但铺垫一层粗砂,窑床上也散见少量砂粒,因为这些砂粒,想起了平和瓷的一个特色——砂足器,这些因为焙烧时釉水下淌而使器体与匣钵内铺垫的砂子相粘形成的无意之举,成为判断平和瓷的依据之一。此外,两座窑炉外侧,前后窑门之间都发现有用毛石或残砖垒砌的护墙体,平面成半圆形。后室从窑门向侧后方也垒砌弧形挡土墙围护。这应该是属于保护性质的附属设施,也许这和平和瓷的出产没有决定性的关键因素,但在今天,依然可以知道这个环节,虽然不灿烂,但仍有自己的光芒。
一片碎瓷片,是关注洞口陂沟窑的触发点,而洞口陂沟窑,是平和窑的触发点,这多少有“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的意韵。说到平和瓷,一定要说到平和窑,数以百计的窑口分布在平和的土地上,这不仅仅是数字的概念,也不仅仅是阶梯式夯筑的风景。因为松脂量足而劈啪作响的青松枝在炉膛里挥霍自己,火力正旺的平和窑升腾起的窑烟从历史的深处腾空而起,在平和的上空飘荡弥漫。窑烟、瓷器、忙碌的窑工,挥洒的汗水,变幻的画面钩沉起平和窑当年的繁荣身影,给人留下许多遐想的空间。在遥想当年的窑烟,我们没有办法不把目光定格在王阳明,这位明朝的都察院左都御史王阳明,当年的他奉旨平乱。平定寇乱后,意气风发的他行走在崇山峻岭之中,回望的目光有了若隐若现的忧虑,明正德十三年(1518)三月,平和县置县,“寇平而民和”的寓意是王阳明的良好愿望,跟平和窑相关的是,王阳明为了“久安长治”,在军队中挑选了一些兵丁留在平和,没有跟随他远上平叛的征途,这些充役于县治衙门等的德兴籍兵众,还有首任县令是江西人罗干以及自明正德十三年到崇祯六年(1633),相当大部分的平和县令是江西人。这些,让江西景德镇烧瓷工艺传入平和成为水到渠成,如今平和旧县城的九峰镇,依然留存的“江西墓”昭映历史的那一段。
平和瓷的兴起,王阳明是一个触发点,但不是全部。平和窑的辉煌不能不牵扯到景德镇。明万历(1573—1620)年间出现的原料危机,让景德镇的官窑曾两度停烧,民窑也因横征暴敛,一再受阻乃至被扼杀,矛盾的冲突,窑工的抗争,还有朝代更迭的动荡,景德镇的窑烟几近停歇。而当时外销市场需求强劲,仅仅在公元1621-1632年之间,荷兰东印度公司就曾经在漳州收购瓷器,数量动辄上万,还有日本人等。这给了平和窑千载难逢的机会。历史总是这样,危机也可以是生机,一些人的绝望却是另外一些人的希望,平和窑的窑烟升腾得更有生机和活力。
天时有了,和技术密切相关的人有了,还有地利。平和窑的代表性窑址——南胜窑址。主要位于平和县南胜镇、五寨乡,包括花仔楼窑、田坑窑、大垅窑、二垅窑、洞口陂沟窑、新美村后巷田中央窑等,分布在九龙江支流花山溪及其小支流的两岸山坡地带,依山傍水在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形容词,更重要的是满足了窑址存在的两个关键因素:泥土和水。并且,这土并非随便的泥土可用,而是高岭土。水,则是和平和的水运发达有关。漳州六条主要的河流,漳江、韩江、东溪、鹿溪、南溪等五条的源头在平和,唯一没有被认定发源在平和的是西溪,源头的认定和径流量、流程等有关,虽然西溪的源头没有被认定在平和,但平和县依然是西溪重要的干流,甚至在六条河流中,西溪的名声最为响亮,是平和当年最重要的对外航道。平和可谓是交通便捷,也就不难理解,众多的窑口主要布点南胜、五寨。
在交通基本靠水运的年代。从南胜出发的船只可以沿花山溪顺流而下直达月港,我们可以想象五蓬船在后来林语堂充满深情描写的西溪航道繁忙穿梭。回望明朝,月港取代了泉州港,成为“闽南一大都会”,在朝廷对海上贸易严格控制的背景下,原来偏安一隅的月港被朝廷的目光忽略,超越福州港,甚至广东港,造就了“市镇繁华甲一方,古称月港小苏杭”。另外一条路,从五寨出发,手提肩挑,到达漳浦,经过漳浦旧镇,船只很轻松抵达汕头。无论是月港,还是旧镇、汕头,船帆竞发,平和瓷就从平和出发,抵达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荷兰、葡萄牙、埃及、土耳其、美国、南非等东南亚、欧洲、美洲、非洲等国家和地区,如今在世界各地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出土和收藏的平和瓷产品,见证了平和瓷曾经来过以及昔日的辉煌。看到境外平和瓷的消息,宛如看到熟悉亲邻的身影。
平和瓷也就在历史文献的字里行间闪烁它的娇容。在清朝重修的,刊于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的《平和县志》有一句话“瓷器精者出南胜官寮,粗者赤草埔山隔”,?南胜官寮就是南胜窑址,赤草埔距离当时的平和县城九峰镇数公里。明万历元年(1573)《漳州府志》卷二十七的记载“瓷器出南胜者,殊胜它邑,不胜工巧,然犹可玩也。”则是另外一种肯定。

如果没有清政府的“海禁”,也许月港依然繁华,也许平和窑的窑烟依然是今天的风景。但“海禁”实行了,朝廷的稳固肯定是清朝统治者的首选,何况当年他们的目光也许根本就没有在平和的窑烟停留过。一条政策足以改变许多,月港衰落了,平和窑的窑烟也熄灭了,就像一首歌曲,突然戛然而止,成为逐渐消失的背影,在历史的巷道中渐行渐远。据平和縣的文物专家杨征在《平和窑》一书中写到,平和窑烧制的鼎盛时期为明代万历至清代顺治之间。杨征的另外一本书《从花山溪到阿姆斯特丹》写出平和瓷遥远的航程,平和美术家黄堂生的美术作品《十里窑烟》则是另外一种传递。
曾经相当长的岁月,平和瓷在已经湮没在荒草之中的平和窑寂寞地躺着,和岂止是千里之外的阿姆斯特丹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而在外声名鹊起的青花瓷因为无法对接来自平和的家乡生命密码不得不流落他乡,以“克拉克瓷”“汕头器”“吴须手”“吴须赤绘”“交趾香合”等名字漂泊江湖。宛如流落他乡的流浪艺人,在不同的区域总是留下不同的容颜,耳边突然回响起“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姓”的歌声,歌声之后的辛酸和无奈随附在平和瓷回荡在不同的角落。1603年的阿姆斯特丹的拍卖让平和瓷一鸣惊人,直到上个世纪那场“晚到了400年的中国瓷器来了”的大型拍卖会,阿姆斯特丹成为平和瓷的福地,平和瓷在这里以它温润骄人的青花身影晃亮了西方人的眼睛,类似于“子贵母荣”,寻找平和瓷的身影日益活跃。
流浪注定是要回家的,平和瓷的回家之路尽管艰辛漫长,但没有中断过。学术界的努力,考古工作者的劳动,平和人对沉睡山野之间窑址的发现,平和瓷生命密码的对接尽管错乱或者艰辛,但上世纪九十年代,流浪江湖四百年的平和瓷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出生地——福建平和。也许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仅仅是考古的一个发现,没有太多实质性的触动,只有考古界专业人士,才理解1999年那“建国50周年福建考古十大发现”对于平和窑来说是怎样的弥足珍贵。只有同业中人,才理解日本东洋陶瓷学会常任委员长,关西近世考古学研究会会长,素有“日本陶瓷之父”之称的楢崎彰一闻讯率领学术团体前来实地考察时,多名学者长跪在平和窑窑口的痛哭流涕。
“克拉克”贸易商船复活了一种传说,在平和窑青花瓷靓丽的身影回旋在不同场合的时候,2012年,沉船“南澳一号”让这种传说更为厚重、充实,从“南澳一号”打捞出水的上万件瓷器是何等的冲击力,平和窑,平和瓷屡屡从专家学者、播音员的口中出现,冲击我们的耳膜。无论是电视画面,或者在平和观看实物,平和瓷那温润的质感,典雅的色调不仅仅是古、雅、趣的感觉,更是心灵平静,心境平和的催化剂,总能在面对的时候意境悠远。而曾经的平和窑窑烟,只能是故事传说一般,回旋在记忆里。
(本文图片由平和县新闻中心提供)
sdjzdx202203231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