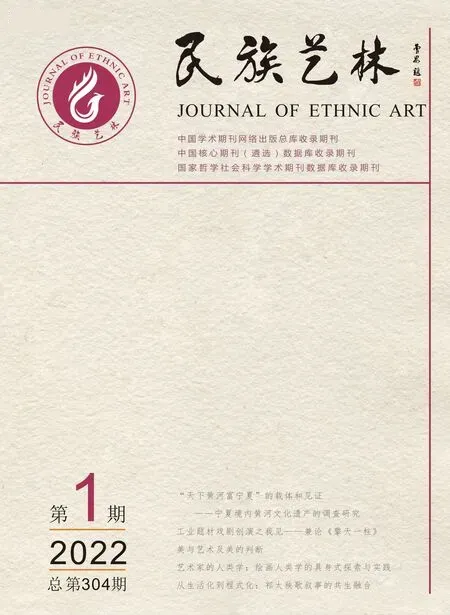艺术家的人类学:绘画人类学的具身式探索与实践
薛其龙,张 方
(云南艺术学院 美术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4;昆明文理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221)
人类学多以文本形态呈现,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解决各种文化事项和社会问题,是文字写手们所擅长的。在这个“多学科交叉的‘后学术科学’(post-academic science)时代”[1]已有诸多非写手们的参与,可惜非写手主体们因不符人类学知识的主流生产方式而关注度较低。弱声非无声,倾听其不同,可扩展学科之音域,或许胜有声。作为绘画人类学团队成员之一,笔者时刻忧虑着团队内艺术家的当下境遇。绘画人类学融人类学家、艺术家于一体,既有文本写作又有绘画创作,艺术家像人类学家一样工作和思考,产生文化意义,定义自我和对未知的、未被探索的他者进行解释性书写。艺术家对人类学的多维解读,通过找到一些视觉文化元素,抓住一些触发感受的他者要点,获得交叉性发展,这可以帮助艺术家更好地“换脑”,还会带来更多的竞争性优势和研究活力。艺术家对人类学的表达方式及解释路径,无论是在创作手法上还是写作文风上,与人类学家差别很大,那么如何看待艺术家主体的这一探索?其优势为何?发展如何?
一、艺术家从事绘画人类学的因缘
“跨学科”作为当今学术研究的热门词引导着艺术家的行动,他们不安于现状,尝试着多学科之间的互动。绘画人类学就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与发展,最初由人类学家庄孔韶引导、整合,后来逐渐展现出一定的创造力和人类学知识的生产性。当然,艺术家与人类学的关联甚密,且不同时期关注的要点有所差异。[2]例如,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以20 世纪30 年代的巴黎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与人类学合作的案例为论述点,认为超现实主义与人类学结合始于现实问题,不像19 世纪异域主义以寻求暂时的震撼和奇异的经验,艺术家的态度与田野工作者的态度相当,努力使不熟悉的东西变得可理解,试图将科学严谨的研究与个人经验结合起来。[3]但真正以“绘画人类学”之名的创作发生在21 世纪初期,至今不过20 余载。目前国内从事绘画人类学的艺术家涉及的画种有油画、国画、版画、农民画等,他们兼修不同程度的人类学知识,可以有效地与艺术创作结合,完成了百余幅绘画人类学作品。这些艺术家分散在北京、福建、云南等地,皆因志趣相同而聚,显出一种跨学科实践的自觉性和聚合力。笔者针对这群艺术家参与观察的访谈调查,概括了他们之所以从事绘画人类学的因由有二,即跨学科实践与创作转向。
(一)跨学科实践
艺术家的人类学实践起源于人类学家的跨学科实验。庄孔韶发现某些仪式活动中的影像记录禁忌,但画家却不受影响,可凭记忆完成,与人类学家的观察逻辑相近,不同的是用画笔可以表现更加复合的思维模式。实际上这是画家基本功的体现,像《韩熙载夜宴图》是画家顾闳中参与观察的产物,于是庄孔韶邀画家林建寿尝试为人类学教材进行插画创作。又如《祈男》由人类学家提出创意,画家完成创作,随后他们合作了《刮痧》《临门》等作品。人类学界逐渐形成了绘画与人类学“联姻”的学理,其成果用于帮助阐述人类学意涵的必要性,认为“除了可以运用这些手法画画,人类学绘画作品一定是画家参与田野观察的产物,即画家在田野工作时作跨族群、跨文化的体验,然后透过其构想与直觉之判定作画,展示‘什么才是作为文化的(或跨文化的)绘画艺术与技法,以及何以呈现绘画人类学的思维、情感、文化与社会的交流。’”[4]在此,绘画的人类学应用价值和实践价值得到了成功检验。
经过与人类学家的接触及在田野中的感悟,艺术家知晓人类学的优势,并在创作中独立摸索。林建寿后来在云南诺邓地区的写生中深切体会到田野调查所带来的新体验,所创《古镇诺邓的小康之路》(图1)展现了云贵山区的物质生产习俗。诺邓村因山道狭窄,骡子是腌制火腿过程中重要的交通工具,画面描述了两名男子装载货物的日常生活,而其背后包含多少劳作的辛苦、生活的辛酸,“假如不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根本无法体会火腿的味道为何有别于其他,因为他们用的不是普通的盐。”[5]当然,写实性的画面难以言说画家的具身性体验,但从题材选择、物象组合、表现细节等方面可感受绘画人类学作品的文化意味。2019 年12月的绘画人类学跨学科展让艺术家与人类学的合作成果充分展现,让更多的人看到两者结合的希望,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参与其中,是绘画创作与人类学研究取得双重价值的学术探索。

图1 林建寿《古镇诺邓的小康之路》
可见,人类学家在绘画人类学的发展中起到了提供学科视野、整合资源、引导创作的作用,让一群年轻的艺术家找到了一种新的跨学科创作方式,同时,艺术家也经历着从合作实践到独立创作的转变过程,实现了与人类学的完美“联姻”及全新创作。这一新的尝试折射出了不同学科之间已经被卷入到彼此关联的世界之中的新特征,同时也反映出人类学强烈的应用属性。
(二)创作转向
当下的绘画创作面临着内容与方法上的双重困境,人类学成了艺术家们突破重围的一种探索途径。以云南为例,少数民族题材绘画是画家采风实践、情感表达的创作的结果,“民族地区独特的自然景观、丰富的人文资源、多彩的民族风情、神秘的宗教信仰等,已成为当代画家绘画创作中不可或缺的题材内容。”[6]云南在20 世纪80 年代形成的“云南画派”“新具象绘画”汲取了少数民族题材的养分,曾一度引领中国绘画的新潮流。在他们的影响下,无论是本土画家还是外地画家都在这片红土高原上写生采风,每年生产几百幅少数民族题材绘画。但是,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绘画在创作上难再有新的发展,画家们仅关注少数民族表面上的特征,村落中人物的描画与画室中人物的描画一样,模特多是穿着少数民族服饰摆姿势罢了。在采风地点上,画家集中于个别域内,形成了画家采风村等艺术场域,其他省区的画家们每年前来云南,采风兼旅游,全然失去深入搜集素材的真谛。当前画家在题材上整体表现出来的特点是缺乏艺术思考,民族文化“浅描”,绘画创作模式化,采风实践“旅游式”,局限了美术创作。
绘画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能够给予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绘画以启示和有效建议,能够解决绘画采风问题和发展局限。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法让画家充分了解他者的生活进而认知他们独特的审美习惯,真实生存状态及精神内涵。例如,《人类学对于绘画的适用性——我的〈守望者〉系列作品阐述》认为:“运用人类学参与观察的方法,通过充分的田野工作,把地方性知识、文化比较、主位与客位等研究视角,植入画家下乡体验生活、写生并创作中,可以改变一个画家盲目地对着一个农村的人并景和物,使写生更加有文化内涵和社会意义。”[7]林建寿的绘画人类学创作颇受欢迎,证明了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在绘画创作中的可行性和重要性。作者认为拥有绘画人类学知识与方法能够更直接作用于绘画采风之中,进而更有效地传达画家的艺术情感。当今艺术家跨人类学实践兴起的原因,正与艺术家试图通过对人类学的整合使用而重建艺术统一性和文化整体性有关。绘画人类学对绘画创作转向具有如下实际意义:(1)延伸了绘画题材的深度,使画家能够“深描”绘画背后的族群、文化知识,进而使作品更具有生命力。(2)扩展了画家视域,不仅仅聚焦于个别区域或民族,田野范围扩大。(3)使写生采风更具实用意义,加深艺术写生采风在绘画中的重要性。绘画人类学的建议能够给予画家反思,进而提供可行性的路径转向,为未来绘画创作中提供实际有效的经验及启示。
二、艺术家探索绘画人类学的手段
艺术本体与人类学本体在观念表达上有着一致性的一面,但在表达方式上,两者有着天壤之别。艺术家即便运用了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艺术实践有了新的理解,其创作始终围绕艺术本体,也唯有如此,才能构建艺术家与人类学的关系,才能在更为广阔的语境中触摸到艺术的真实,才能创作无愧于时代的艺术精品。目前看,绘画人类学实践既用画笔创作包含人类学特质的作品,又书写绘画人类学创作心得,形成图本与文本的双重表征形态。
(一)通过画笔创作
绘画创作擅长表现包含多重内涵的复合性意义,传递人类对各类文化事项的理解。画笔的“不浪费性”是绘画人类学实践的基础,以此生产平行于文本的主题性、意涵性人类学知识,这一点在绘画人类学创作中得到了很好的呈现。蔡志鸿《莫色布都》(图2)是在云南宁蒗彝族地区现场写生的作品,后根据莫色布都致力于“小凉山”彝族禁毒宣讲工作的事迹进行了人类学式的理解和修改。常见的写生训练被赋予了文化的意涵,如眼神画得更加坚定,手表象征了时间的紧迫,姿态呈现了决心和毅力,彝族服饰表征了民族身份及地域特色。人类学的整体性观察融于创作活动之中,无须直观再现或刻意强调,作品最终呈现出的独特性足以说明人类学式的引申性和隐喻性的处理。又以胡继宁《神石》(图3)为例,表征绘画人类学的独特性艺术语言和创作价值。仅从作品图像观之,只不过是一块普通的山石,但该石头背后承载着重要的文化事象,凝结着当地彝族价值信仰的物象符号,已经超越了物象所指进入能指阶段。作者融入当地人的生活环境中进行田野调查式的写生创作,从族群内部挖掘彝族文化的精神内核,进而转化到绘画语言里,形成具体的艺术视像。艺术家只有对他者文化进行深度研究和对物象进行广泛积累,才能自由地进行画笔表现和语言转换,最终创作出具有人类学语义的绘画作品。艺术家视绘画为地方性文化的载体,通过各种途径去了解、发现他们背后的文化隐喻,发掘作品的每一个细节的指向性意义,这样的作品更有灵魂,能和观者形成跨时空、跨地域的交流。进一步看,通过绘画人类学语言和形象,显现出一种文化的生气、情感、灵魂和精神,这就是艺术作品的意蕴。从意涵到意蕴的转变,或为绘画人类学创作的取向,进而窥探艺术形态的内在价值和文化意义。

图2 蔡志鸿《莫色布都》

图3 胡继宁《神石》
(二)通过创作释读
艺术家同样进行着文本的写作,无论是对知名画作的论述还是自我创作的叙述,他们的观察视角、文笔风格不同于学者写手,更加贴近艺术本体,且伴有自我认知、情感、经验的阐述,实际上这让人类学更加贴近“人”的感性面向。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人类学图本及文本写法。
(1)作品分析上。林建寿以《医生》为例[8],借助场景描述、故事情节、心理活动和多种复合神情,分析作品中的人物关系及不同符号可能的隐喻指向,再现19 世纪欧洲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现状。《医生》虽然取材于现实生活中菲尔德斯(Sir Samuel Luke Fildes)的亲身经历,但糅进去的不只是个体的经验与情感,而是将医生对遭疫病的贫困家庭的悲悯置于画作核心,以此消解了当时社会有关疾病暗含的道德谴责。艺术家的人类学分析始终围绕作品本体,从画作内部解构人物构成及人物身份、社会情境和情感层面的多重关联,借助个体经验和艺术创作,获得超越个体局限的理解视角和情感方式。
(2)创作叙述上。艺术家擅长书写创作体验和情感经验。例如,胡继宁于2014 年至2019 年期间,数次前往云贵民族地区做田野调查和创作采风,记录和绘制了大量的文本和速写图像,回到画室继续创作,完成《苗族鼓藏节》系列、《苗族印象》系列等作品。创作者在画文化的同时也在记录着这一过程,所以有大量感官的体验与表达的文字,让人类学有了更多细节和具体的“深描”。相对于文本、影像的客观性和现实性,绘画人类学的语言构建具有民族志意味的创作叙述性。
由此可见,艺术家掌握了两种探索绘画人类学的手段,这让绘画人类学知识的表征更加多元与立体。艺术家对绘画人类学的具身性叙述,让人类学有了另一主体的图本和文本书写呈现及生产方式;通过构图、形状、冷暖、色调和节奏等思考所见事物的方式,帮助表达艺术感觉并塑造艺术形态。艺术家的书写让复合型思维的绘画作品更加面向受众,此时的人类学知识也就更加直白地表征出来。
三、绘画人类学的具身性优势
绘画创作研究一直暗受认知心理领域研究的影响。在漫长的艺术发展史上,学界常坚持行为主义“刺激-反应”二段分法模式,即创作行为置于思维之后的“意在笔先”认知。尤以20 世纪60 年代兴起的以信息加工理论与计算机表征方法研究大脑抽象功能的离身认知(Disembodiment Cognition)最为著名,使艺术家的创作研究指向内部心理的解释。中西方艺术研究方法一般强调“刺激”的先行性和重要性,似乎他们所有的创作发生都必有一个完整的想法及因果关系。传统的心理学理论解释创作行为、过程、习得、意义等方面总是不够全面,明显地忽视了绘画创作过程中的能动特质,不能有效地反映创作发生的灵活性与复杂性。直到20 世纪80 年代后,拉考夫(Lakof)与约翰森(Johnson)提出了新的认知观点,改变了离身认知范式,认为人类的认知活动具有身体性、情境性和非表征性,提出认知科学研究应该是一个注重身体及语境的动态过程,注重体验和经验对认知的作用。[9]认知科学转向以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及动力学为特征的“身体”研究,旨在探求身体的生理属性对思维、情绪等心智的重要影响。“笔在意先”,是指先行的身体在认知中的作用,为绘画人类学创作的认知思考及人类学式采风写生提供了依据和方向。这一理论重提身体的重要性,以身体为讨论中心建构人类认知活动,由此涌现出诸如具身性、嵌入性、延展性、情境性、生成性和动力学等一系列新的研究角度和范围。
从具身认知视域来看,绘画人类学创作具有具身性优势。艺术家创作发生之初归于感知认知阶段,这一认知阶段受限于主体身心活动及经验表达的时空因素。绘画创作不仅是大脑的工作,还是涉及身体的工作,也就是说,只有“当身体理解了创作,当身体把创作并入它的‘世界’时,创作才能被习得。”[10]创作能够被习得的前提是身体已经被学习者所理解,即身体已然投入其自身的“世界”,并通过“世界”以某事为目标而模仿某人的身体。这一点在绘画人类学家田野调查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实施。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反思了具有主体意义的身体,“事实上我们也看不见一个心灵何以能作画。正是在把他的身体借用给世界的时候,画家才把世界变成绘画。”[11]于是,人们在创作时不全是通过理论和智性去控制行动,也会是优先使用身体去认识、感受、体验、创造艺术,更加注重在创作行为中逐渐显现其情感世界。因此,在绘画人类学画家那里,身体先行是艺术家创作发生中的常有之事,他们通过身体动作提高与优化认知水平而获得他者文化,尔后具身与离身交相互动,形成“笔意同行”的创作结果。
绘画人类学的具身性不可忽视相关语境的影响,语境为绘画创作提供了一个实时的发生场或情景场。绘画人类学创作倾向以精神生产为目的,包括“笔”“意”和语境等诸多因素间不断交互、相互协同、反复构建的生成系统。当中,作为“笔”的身体本是整个系统演化的基础必备环节,连接着作为“意”的心灵并嵌入到语境之中,控制或限制着创作行为、动作的变化。或者说,绘画创作不单是外部语境的“刺激-反应”所致,也不单是内部大脑符号的表征,而是“笔-意-语境”之间交互作用的复杂动力系统模式。例如《“虎日”民间禁毒仪式》(图4)是林建寿身体力行的回访“虎日”盟誓仪式时,面对“小凉山”彝族文化语境“以文化的力量战胜人类生物性的成瘾性”[12]的态度与方式,受震撼而作。“笔-意-语境”共筑为一个有机整体,缺一则行为无法形成或难以运转。

图4 林建寿《“虎日”民间禁毒仪式》
总而言之,从身体出发的具身特性让身体的动力本源凸显,展现了不一样的创作动力学特点:(1)整体性。绘画创作不只是“刺激-反应”的线性关系,更是“笔”“意”和语境等各个子系统彼此间相互联系、交互作用的整体,应该顾及彼此,联动看待。(2)交互性。艺术家与他者在交互过程中的持续性变化及身体、语境交互时形成的个人感知、经验因素,构建了具身性创作过程。(3)动态性。绘画人类学创作是一个“笔-意-语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生成过程,它由多种错综复杂的变量构成,是一个不断运动的有机体。(4)参与性。由于具身性强化了身体的重要性,所以这一动力模式也就突出了实践者及他者在创作生成过程中的参与互动关系。
传统绘画创作的认知视域是二元相对的,只把身体作为创作观念的载体,而忽视了身体的主动性。其实,身体不但是绘画创作发生的外在工具,也支配着创作行为进而影响艺术家的思维观念,最终通过身体实现我者-他者一体化的艺术途径。绘画人类学让身体在创作行为中的作用凸显出来,重视身体的物理感受、感知运动及情绪体验等方面的在场性。在此,绘画人类学作为新时代文化氛围中的交叉学科探索,它既承续着艺术家创作追求,也表现出一种人类学语境中的复杂感知形态和具身性质,指向更为现实的、真实的多模态共生性。
四、结语
本文围绕绘画人类学中画家主体的人类学探索与实践,通过发生因缘、探索手段、具身性优势及绘画作品的分析,旨在讨论艺术与人类学的跨学科特点及其中交叉新生的知识价值。无论是艺术家的创作还是写作,都拓展了人类学的文本模式,让更多的主体能够利用人类学发多声部之声,为未来人类学或艺术学的多元性发展提供可借鉴方案。当然,绘画人类学发展至今已形成了独特的风格,绘画语言更加复合性地表征着人类学知识,但在意涵、题材、形式上仍需进一步探索自己的道路。艺术家对人类学的探索与实践或有更大的启示意义:(1)注重学科发声的多元性与多方法性,即便是非主流主体,其价值依旧重要,不能因此忽略其声音。还有像绘画人类学一般,艺术家的作用由弱变强,催生了更为紧密的创作共同体,成了人类学知识生产的图本方式。(2)绘画与人类学的双向流动及互涉、互嵌、互融的间性状态,超越以往图本-文本、画家-学者、我者-他者等二元对立的局限,体现了绘画人类学主体寻找一条更加开放的道路,扩展学科维度的努力。作为文化先锋的艺术家介入人类学,印证了这一跨学科的强大生命力,进一步拓展了其社会时代价值。(3)在面对当下多重文化互动交叉的背景下,绘画人类学实践不是去“艺术本体化”,恰恰相反,是在多维度中再识本体特征,在艺术本体基础上不断吸收诸多新学科,新观念与新思想。艺术家本是一群不断创新的群体,绘画人类学即是这一实验结果,目前看颇有创造性且“笔-意-语境”具身性优势明显,却仍需接受时间的检验。(4)跨学科的发展需要有更多人的实验与开拓,为诸学科之新生找到可能性基因。当两个不相关的能力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创造出他人难以模仿和超越的优势,每次跨界,都是一个新维度的拓展。维度多了,竞争力自然变强,值得庆幸的是,绘画人类学率先跨出了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