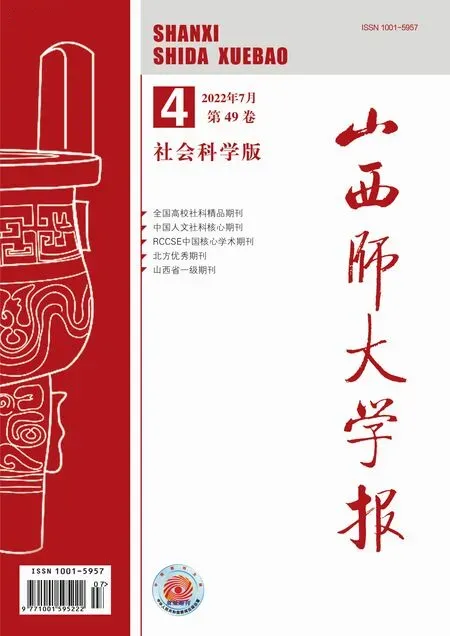文学“特殊性”之认识论意义
——基于对奥尔巴赫的理论分析
周 琦
(北京交通大学 语言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044)
埃里希·奥尔巴赫是20世纪著名的罗曼语文学家与文学理论家,他的集大成之作《摹仿论》拥有贯穿古今的广阔视野和令人赞叹的深刻洞见。奥尔巴赫对于欧洲文学的分析立足于对具体文本片段的细读,通过分析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体裁的作品,从文体分用和文体混用的双重视角,对欧洲文学史及欧洲思想史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分析。奥尔巴赫理论的核心词为“摹仿”,相较于文学史的普遍规律,奥尔巴赫本人尤为重视充满了偶然性、随意性和特殊性的文本和历史细节。那么,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和特殊性的文学作品,如何达成一种普遍意义上的摹仿与呈现?本文从特殊时刻与共同人性、特殊个体与时代状况、特殊文本与人类历史三个视角出发,试图透视奥尔巴赫理论架构中文学“特殊性”背后之认识论意义:正是文学“摹仿”对特殊性的把握与展开,才使得独特的表现形式呈现出人类历史中的普遍性因素,从而赋予文学以独特的意蕴。
一、特殊时刻与共同人性
作为博古通今的语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奥尔巴赫清楚地认识到,一切文学作品都离不开“人”这一核心主题,《摹仿论》本身的研究重心即是对欧洲文学对于人类活动的诠释方式的研究。在众多欧洲作家中,奥尔巴赫对意大利诗人但丁尤为重视。在《尘世诗人但丁》(Dante: Poet of the Secular World)一书中,奥尔巴赫于“论再现”(The Representation)一章中着重论述了但丁在人物塑造方面的独到之处。
在《尘世诗人但丁》的开篇,奥尔巴赫叙述了古典文学中的角色塑造传统。他指出,人物的行动、性格与命运是相符的,角色的本质特性首先在一个行动中展现出来,又在随后一系列相似的行动中得以自然地流露,最后,这一切事件的总和就是角色的命运。(1)Auerbach,Erich, Dante:Poet of the Secular World, Trans.Ralph Manheim,(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1),1.换言之,角色塑造依赖于“命运”,而命运又依赖于一系列的“事件”。事件首先预设了一个含有选择的场景,而众多事件的依次相序构成了角色的命运,角色通过做出选择来展现自身的性格。例如,在《奥德赛》中,奥德修斯的勇敢与机智就是在对于危难事件的一次次回应中体现的,在屡次化险为夷中我们得到了关于角色性格的印象,这是从众多的事件中抽取出来的共性。
与古典作家不同的是,但丁所描写的并不是个体生命的长期历程,而是通过“时刻”(moment)来描绘角色。《神曲》中的角色并不是被动地走向他们所属的命运,而是在个体生命的特殊时刻通过选择书写了自己个体性的最终归宿。他们沉溺于尘世的某一个时刻中,这种时刻也将在永恒的时间中一直持续下去,成为角色个体性的永恒的烙印。在他们的回忆中,人世间的一切起伏似乎都不如回忆中的这一时刻更能直击自己人生的本质,成为他们自身的“尘世存在的具体总和”。(2)Auerbach, Erich, Dante:Poet of the Secular World, Trans. Ralph Manhei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1),143.它可能只是一次事件中的一个选择,或用奥尔巴赫自己的话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具体事实”。(3)Auerbach, Erich, Dante:Poet of the Secular World,Trans. Ralph Manhei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1),146.当《神曲·地狱篇》中的但丁偶遇法利那太之时,后者并没有追忆自己一生的兴衰荣辱,也没有因身处地狱而对尘世进行追悔和反思。但丁为我们展现的是他生命中最为辉煌的一个时刻——作为吉柏林党领袖的法利那太。他的个体性并不是通过一系列的事件表达出来的,他对于自己的童年、老年时代没有丝毫追忆,生命中的种种组成部分——例如亲情、爱情、友情等,都无法在他身上找到一丝痕迹,似乎尘世命运之中的种种事件已消失殆尽、不留痕迹。从他那“昂首挺胸直立”的气度,“稍微看了看”的上位者姿态,以及“轻蔑的表情”(4)[意]但丁:《神曲·地狱篇》,田德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50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此时法利那太依然沉浸在权力巅峰的生命印象之中,这也是他的个体性的写照。他对于尘世生命留下的唯一印象是权力与政治,是将贵尔弗家族赶出佛罗伦萨的时刻,是党争胜利的时刻,这个时刻可以揭示法利那太的个体性中的本质特色。
然而,这似乎与我们的认知相悖:时刻所承载的是特殊性,它有可能是由某个不同寻常的偶然事件而引起,也有可能是在冲动之下所作出的不合常理的行为。它是个体生命历史之中的“一”,具有极强的片面性和特殊性,在此意义上,它不可能成为角色历史的“具体总和”。但奥尔巴赫认为,“时刻”更能直击个体性的本质的原因在于,它是从“回忆”这一对个体生命的整体印象中所抽取出的一点,而它往往蕴含着不被回忆者所意识到的本质性:“在回忆中,所有事件的潜在的同时性永远是在一个明确的形象中展现出来的;但是这个形象本身是被一种意识塑造出来的,这种意识的全部经历都为这种塑造作出了贡献;相反,事件的某个时刻是隐晦的;尽管在这个时刻他人可以理解我们,但我们不能理解我们自己。”(5)Auerbach, Erich, Dante:Poet of the Secular World,Trans. Ralph Manheim,(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1),144.
奥尔巴赫在此赋予了具有特殊性的“时刻”以启发性的意义。个体的生命经验具有连续性的特质,生命中的所有事件都以个体的自觉意识为串联而形成了对自身经历的流畅印象,这种自我认知的方式与古希腊式的悲剧角色定义如出一辙,均是以个体经验中的大量“事件”堆叠的方式来抽取共性。但在奥尔巴赫看来,在文学创作之中,描写具有特殊性的“时刻”更能直击人性的本质,因为在他者的视角中,从这种特殊性“时刻”往往能够追索到不为个体所意识的内心深处的奥秘。如果将法利那太的生平详细道来,众多事件的堆砌使得细枝末节盖过了本质特征,读者看到的可能只是一个陷于无数政治事件的忙忙碌碌的掌权者,又如何能看到法利那太在叫住但丁的那一刻所展现出的强烈的政治欲望和权力的锋芒呢?正是因为它是众多事件中的“一”,它的特殊性才得以更加鲜明、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进一步说,但丁以三界中的众人百态为读者描绘出了一幅栩栩如生的人间图景,所涉及的角色有百余位之多,其历史跨度从古希腊时代一直到但丁所生活的13世纪,描绘了智者、哲学家、诗人、政治家、教皇等分属不同社会阶层和生活领域的人物,并以此为媒介间接表现了西方历史中尤其是佛罗伦萨政治中的重大事件,展现了不同时代人物的精神风貌。奥尔巴赫将此命名为“但丁现实主义”,但这与西方文学流派中的“现实主义”有着显著的不同。在《神曲》一书对于角色的塑造中,我们没法找到19世纪以降欧洲现实主义对于时代的重视,所能看到的唯有个体性的差异所造成的截然不同的灵魂归属。例如,维吉尔和奥维德同为古罗马诗人,但由于信仰的差别,前者成为了但丁的引路人,而后者只能身处地狱最外围的灵簿狱。甚至在同一个历史事件中,不同角色对于现实的关注也截然不同:法里那太和加瓦尔甘底为政治联谊的双方,同属佛罗伦萨党争中的党派领袖,但前者对于政治纷争念念不忘,后者却只挂念着父子亲情。(6)法里那太和卡瓦尔甘底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前者对于亲情无动于衷,后者却为儿子的命运而感到痛不欲生,这从他们的动作和姿态中可以看出。参见[意]但丁:《神曲·地狱篇》,田德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54页,注释20。单一的个体事件最终导向了个体的生命史,人的形象比古典作品中的更加有力,更加具体,更加富有特色,《神曲》为我们展示的绝不仅仅是作为结果的具有偶然性的片段,而是“整个过去的生活”,是“一个个体历史的发展过程”和“一个独特的生命史”。(7)[德]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吴麟绶、周新建、高艳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37页。正如奥尔巴赫对但丁作品所评价的那样,“个体通过其非凡的特殊性而达成普遍性”(8)Auerbach, Erich, “The Discovery of Dante by Romanticism”,Time, History, and Literature:Selected Essays of Erich Auerbach, Ed. James I. Porter. Trans. Jane O.Newman,(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140.。在这众多个体生命的合奏中,角色的极致的个体性最终表达了人类生命所蕴含的一切欲望、情感与挣扎,成为超越一切时代、超越一切民族的共同人性。
二、特殊个体与时代状况
奥尔巴赫对于文学传统中的细腻变化有着超乎寻常的敏感性,他清晰地觉察到了从古典时期到中世纪、再到现实主义文学这一发展过程中的文体变化——从文体分用到文体混用。但奥尔巴赫对此的研究显然不仅仅止步于文体本身,他所看到的是在文体表象的背后所隐藏的对于社会、时代和世界的观念变化。从古典到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角色塑造越来越脱离了“性格”与“命运”这自古希腊传统流传下来的两大主题,而致力于以个体生命来表现时代与社会。
在古典文学作品中,几乎不存在“社会环境”这一文学母题。个体生命的经历几乎只源于“命运”这一形而上的概念,而丝毫不受历史现实变动的影响。正如奥尔巴赫所说,“在古典时期的摹仿作品中,福祸变化的形式几乎总是从外部突然降临某个范围,而不是世界历史内部运动的结果”。(9)[德]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吴麟绶、周新建、高艳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35页。古典文学作品所体现的“社会”是一种作者预先设计好的先验模式,所有角色都已事先安坐在作者为他设计好的那个位置上,说着符合自己身份的华丽套话,一切个体性的思考都仅仅局限于自己所在的社会等级之内。这一创作传统一直到了骑士小说时代依然在延续,并已成为一种逐渐僵化的文本创作的固定格式,与现实丝毫无涉。对此,奥尔巴赫在《摹仿论》中以对安托万·德·拉萨尔的作品的分析为例,做了如下精要概括:“在这种固定的生活等级秩序中,一切都有其自己的位置和形式,都保持着自己的位置和形式,这种固定的生活秩序则反映在修辞中:说出的话庄严、烦冗、体态语丰富、信誓旦旦。每个人都有与其相应的称呼……每个人的举手投足都符合他的社会等级和状况,好像依照的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模式……”(10)[德]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吴麟绶、周新建、高艳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82—283页。
虽然在古典作品中存在类似现实主义的文体创作,例如佩特洛尼乌斯(11)佩特洛尼乌斯,古罗马作家,奥尔巴赫在《摹仿论》第二章中对其作品有过详细评述。的小说即通过对于下层民众的描写而为读者展现出一幅生动的历史画面,奥尔巴赫称之为“古典现实主义”。但他的作品仍然没有对历史的具体时间、地点和环境进行暗示,可见佩特洛尼乌斯对于作品的时代性并不重视,作品对于现实描写的落脚点并非是反映时代,而是反映作者对于道德伦理等方面的观点,其现实指涉性无非是一种空洞的修饰。
奥尔巴赫的创见在于,他在文体分用的传统中发现了文体混用的前兆。文体混用来源于基督教传统内部,此后薄伽丘的《十日谈》以及宗教神秘剧已打破了古典文体中只描绘贵族阶层的传统。但是这种文体混用的支流依然与文体分用的主流混合在一起,例如莎士比亚的戏剧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虽然也描写下层人物,但他们的关注点依然是道德观念或者是一种对于世界本源的认识,依然没有指涉具体的历史、时代和社会现实。
现实主义作品描写个体,但与古典作品不同的是,其目的并不是表现“命运”这一超验的文学母题。时代环境并不是苍白的背景板,而是会对个体生命产生深刻影响的历史动因。现实主义作家将人物放置于具体的社会、时代和历史情境中,以单个角色的生命经历为焦点,对整个时代进行透视。在奥尔巴赫看来,德国的席勒首先进行了这种尝试,但并不成功。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品应该把人物“置于具体的、不断发展变化着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总体现实之中”,(12)[德]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吴麟绶、周新建、高艳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546页。在此意义上,司汤达才是严肃现实主义的创始人,他对所观察到的现实状况进行详尽的描述,但他在单个事件的描述上依然采取了“古典的伦理心理学”意义上的道德立场,(13)奥尔巴赫认为,司汤达依然试图通过事件来表达自己的道德倾向,因此事件中的角色的塑造更取决于作者本身的立场,而不是环境。参见[德]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吴麟绶、周新建、高艳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547页。角色与环境之间的联系并不密切。相反,巴尔扎克的作品将人物和环境统一了起来,个体命运随着社会、时代和历史的境况而起伏,使人物与历史并置而行,或者用奥尔巴赫自己的话来说,“人物和环境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但事实上它们始终被作为历史事件和历史动力中的现象加以展示的”。(14)[德]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吴麟绶、周新建、高艳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569页。福楼拜则在此意义上更进一步,将个体意识和环境更密切地联结起来。例如在《包法利夫人》中,福楼拜对爱玛与丈夫吃饭时的一个场景进行了细致描写,这种描写深入到了个体主观性的内部——个体意识——之中,以最极致的个体特殊性来展现现实。爱玛的一切个人感受,都是对于她所身处的环境的生动展现。在此之外,福楼拜避免插入作者自身的评论,个体完完全全成为环境本身的产物。由此,“个体性”一词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偶然性的因素被减弱了,相比但丁所描述的万花筒一般的角色群体,对于个体生命史的深入描写可以使角色在不同事件中与社会现实的不同侧面进行剧烈碰撞,更能触及时代状况的深层,也因此成为反映普遍的时代现实的最好素材。
现实主义得以发展的原因并非在于文学发展的内部,而在于社会和思想的变化。奥尔巴赫对此有着深刻洞见,他指出,以德国为例,一直到席勒的文学作品都难以触及社会发展的深层,难以反映整个时代现实,原因即在于德国的四分五裂的政治现实使人们限于传统的地域性,缺乏对于人类整体状况的直观感受和主观重视。当波及全欧洲的法国大革命发生后,人们才开始关注世俗社会,更为关键的是,由于革命的大范围影响,各国人民的生活和思想开始产生交集,有了“比过去更加宽泛的现实生活基础和更加广阔的生存环境”。(15)[德]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吴麟绶、周新建、高艳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540页。这使得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具有了普遍性的意义。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讲,想要在有限的文字范围内反映时代样貌无疑是一件具有挑战性的工作,经历历史的大浪淘沙,流传至今的现实主义作品的主题基本都是个体的生命史,而非但丁式的对于众多人物的均匀描述。个体命运具有偶然性和特殊性,它往往只是复杂的历史运动的边缘一角,但奥尔巴赫的分析无疑使个体命运的意义从特殊性上升到了普遍性,将特殊的个体作为展示整个时代的出发点,赋予了“现实主义”一词以真正再现时代与历史状况的宏大视野。
三、特殊文本与人类历史
奥尔巴赫的著作《摹仿论》的副标题为“西方文学中现实的再现”,这个“现实”并不仅仅指个人的生命史或者某个时代。奥尔巴赫在此书中论及的作品众多而庞杂:在时间上跨越两千多年的历史,从“两希”传统的古典文学一直延伸到现代小说;在地域上涉及法、德、西班牙等多个国家,覆盖几乎整个西方文明。这给予了《摹仿论》以异常广阔和宏大的视野。奥尔巴赫的研究也绝不仅仅局限于文体本身的变化,而是从文体中发掘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人类对于现实的观点的变迁。换言之,奥尔巴赫所写的不单单是文学中“摹仿”的历史,而是一部真正的人类思想史。当然,将几十部具有强烈主观性和想象虚构成分的文学著作作为研究整个人类思想状况的素材,相比历史记录等其他文本形式,似乎有失客观,因此,若要研究奥尔巴赫作品的意义,就应厘清奥尔巴赫选择文学文本背后的理论合法性依据。
萨义德在其所作的《摹仿论》导论中清楚地指出,维柯是奥尔巴赫所终身关注的理论家。(16)[美]爱德华·W·萨义德:《五十周年纪念版导论》,见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吴麟绶、周新建、高艳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v页。“奥尔巴赫对维柯的历史决定论(historicism)——有时称为历史主义(historicism)——的迷恋支持着他的解释学的语文学。”(17)[美]爱德华·W·萨义德:《五十周年纪念版导论》,见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吴麟绶、周新建、高艳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viii页。维柯认为,人类创造了历史本身,这个历史就是天神意旨(Providence)在不同阶段和不同地域所产生的各种人类文化变体的总和,或者说,这个历史就是“各民族的世界”。维柯的《新科学》致力于发现各民族间的共同之处,它体现为对一切民族都适用的、全人类都拥有的共同意识(common sense)(18)共同意识是“一整个阶级、一整个人民集体、以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所共有的不假思索的判断”,它是天神意旨教给各民族的准则,也因此产生了一种“心头词典”(mental dictionary),可以构思出一种理想的永恒历史,为一切民族历史提供判断的原则和基点。参见[意]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08页。。因此,要研究民族世界和历史,就需着眼于人类心灵,“这个民族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所以它的面貌必然要在人类心智本身的种种变化中找出”。(19)[意]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70页。因此,维柯的《新科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历史的客观性本身,而是人类思想史、人类习俗史和人类事迹史。(20)[意]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82页。
维柯的语文学基于“诗性智慧”这一概念,它的本质是对原始人表达事物的语言方式的理解。原始人类处于人类的幼年时期,他们的理性能力还很薄弱,与之相对的,他们的想象力就蓬勃发展起来。(21)维柯认为,“推理力越薄弱,想象力也就成比例的愈旺盛”。见[意]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19页。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是生动而充满隐喻的,往往使用幻想式的语言——即诗性的语言——来表述事物,因此“在世界的童年时期,人们按本性就是些崇高的诗人”。(22)[意]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20页。这并不是毫无根据的推论,维柯发现,“一切野蛮民族的历史都从寓言故事开始”(23)[意]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23页。,这些寓言故事即是人们运用诗性智慧对真理进行想象的产物,可以说,任何民族的历史在起源时都具有诗的特性。因此,文学作品进入了维柯的研究视野,在《新科学》中,他多次引用《荷马史诗》,并认为《荷马史诗》是古希腊人民共同的文学作品,他们以诗的方式编制自己的历史。(24)[意]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486页。因此即使文明发展到理性阶段,依然有必要回到原始人的视野中,以把握人类的共同意识:“共同意识便不再只是一切都能自我协调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客观原则。它还是我们如何理解历史的内在基础……因此,当人类发展阶段一个接着一个地达到最高的文明阶段,也就是得以完全发展的理性阶段时,人类只能通过强烈的自我反思才能在它们最遥远的起源中把握它们。”(25)Auerbach, Erich,“Vico and the National Spirit”,Tim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Selected Essays of Erich Auerbach. Ed. James I. Porter. Trans. Jane O.Newman.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52.
“最遥远的起源”自然是指诗性智慧,而诗性智慧本身就是一种以想象、隐喻等方式而看待事物、看待世界的方式,它的产品就是诗。维柯说过,“世界在它的幼年时代是由一些诗性的或能诗的民族所组成的,因为诗不过就是摹仿”(26)[意]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26页。。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创作已与维柯所说的“诗”大相径庭,但它仍然是人类所具有的最富想象力、最接近诗性智慧的表达方式,也是最接近原始人诗性智慧的素材。若想把握人类心灵的共性,即共同意识,仅仅有理性分析是不够的,必须通过文学文本,在文学传统内部分析人类心灵的变化。
维柯的理论实际上赋予了奥尔巴赫的文学研究以充分的合法性依据,因此《摹仿论》中所引述的众多文学作品,本身即可称为探索人类历史的可靠素材,甚至历史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通过想象力而进行诗性创作的产物:“书写历史是如此之难,以至于大多数历史作家不得不退而采用传说的写作方法。”(27)[德]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吴麟绶、周新建、高艳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4页。当然,奥尔巴赫所采用的材料远远称不上全面,他所摘取的不过是每个历史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几部作品而已,在时代与时代之间必然会有断裂。他所采用的方法论完全是一种对个人信仰的承认,即认为独立的特殊性可以表现真理,因此对于文学史的每一个阶段,他均相应选择了一组文本进行阐释。(28)Auerbach, Erich & Leo Spitzer. Literary Criticism & the Structures of History,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2),37.奥尔巴赫所论述的时代有长有短,时代之间常有空缺之处,然而,时代本身就是历史的一个变体,也是历史展现自身的方式。奥尔巴赫认为,事物的本质不过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条件下显现的,这也为历史多元主义(historical perspectivism)奠定了基础。历史的整体面貌只能在不同的、特殊的、具体的时代中进行把握。同样地,文学创作虽然是具有强烈主观性和特殊性的素材,它的优势在于其更能体现时代的特殊性,并在特殊性中把握历史的普遍规律:“哲学语句愈升向共相,就愈接近真理;而诗性语句却愈掌握住殊相(个别具体事物),就愈确凿可凭。”(29)[意]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27页。相比于力求客观准确的枯燥的历史记录,文学作品以其独特的灵动、洞察和把握特殊性的能力,为奥尔巴赫对人类思想史的梳理提供了最可靠的素材。
结语
从个体生命的特殊时刻、特定时代的特殊个体以及人类历史的特殊阶段出发,奥尔巴赫论述了“特殊性”背后的“不特殊”之所在。当然,奥尔巴赫自己也承认,个别性、特殊性和偶然性甚至在他自己的论述过程中也无法避免:“在知识史中,没有什么同一性……必须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整理,就是允许个别现象自由存在、展开。”(30)[德]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吴麟绶、周新建、高艳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689页。的确,《摹仿论》全书所重点论述的不过是十几部作品中的文本片段而已,相比广阔宏大的文学史而言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奥尔巴赫对于但丁和维柯的极度重视似乎也证实了他的理论重心的“特殊性”和“个别性”。但奥尔巴赫失败了吗?当然没有。
在一系列的特殊案例中,奥尔巴赫不但生动地再现了文学发展史及其内在的动因,更通过文学为我们徐徐展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人类思想史画卷。他通过详尽而有力的分析告诉读者,文学创作特殊性的着眼点在于普遍性,因此但丁对于角色“时刻”的描写旨在表现共同人性,现实主义作家对于个体命运的塑造反映了时代的风云变幻,文学创作通过对特殊性的把握而达成了不同于客观事实的另一种历史呈现。由此,奥尔巴赫赋予了文学以认识论意义上的崇高地位,深刻揭示了文学与现实在本质上的联结和纠缠,作为主观创作的文学已不单单具有审美趣味上的意义,而是可以透过其对特殊的“摹仿”而上升到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共同人性、时代精神和人类状况。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文学史构成虽然不同于思想史但同样具有普遍性、实在性的认知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