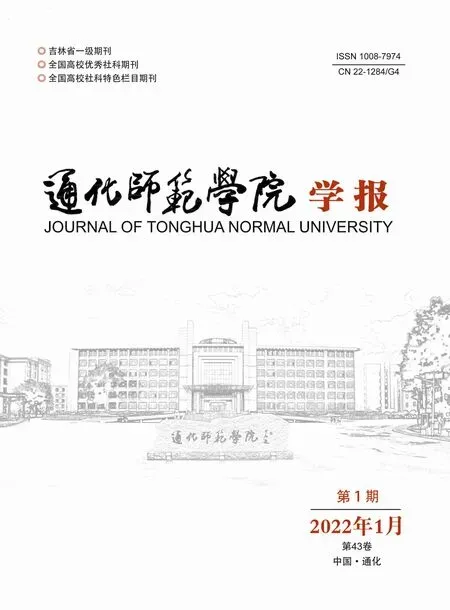《贾汉吉尔回忆录》英译本及其史料价值研究
付 喆
贾汉吉尔皇帝在位期间是莫卧儿帝国发展的重要阶段,对外交往繁多,尤其是与中亚、西亚及欧洲的政权。因此,应重点关注此时间段里西方国家向东方遣使与殖民的活动。然而,相比其他莫卧儿皇帝,学界对贾汉吉尔的研究集中于对其的批评。相比《巴布尔回忆录》与《阿克巴纪》,学界对《贾汉吉尔回忆录》的研究不够充分。本文旨在梳理《贾汉吉尔回忆录》英译本,探究《贾汉吉尔回忆录》的史学价值,澄清对贾汉吉尔的误解。
一、《贾汉吉尔回忆录》的译本及相关研究
1605年,贾汉吉尔即位,继承了父辈的传统开始撰写传记。《贾汉吉尔回忆录》(以下简称《回忆录》)由贾汉吉尔本人写作而成,属于自传题材,正文详细叙述了贾汉吉尔在位时前十九年的统治。《回忆录》与其父传记《阿克巴纪》一起构成了那个时代的一个重要参照点。《回忆录》由波斯文写成,受限于语言和材料,原版波斯语文献的梳理仅能通过英文译本管中窥豹:原始文献及其抄本的来龙去脉详见于1999年英译本[1]。限于作者对原始文本波斯语的了解,难以针对一手抄本进行分析研究,而如今英译本的研究价值已经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因此本文将主要通过梳理英译本来分析其史料价值。现存英译本《回忆录》有以下四种,这四个译本在每个阶段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研究价值较高,下文按照时间顺序对四个译本进行对比分析。
第一个版本出版于1825年,是现存最早的《回忆录》英译本出版物[2]。译者大卫·普莱斯少校(PRICE D)服役于孟买军队,是亚洲文会、东方翻译委员会和皇家文学学会的成员。书中前言写到:为这部作品提供素材的“波斯手稿”(the Persian Manuscript)没有任何特定的标题,因此译者自拟标题为《贾汉吉尔皇帝回忆录》。对比其他版本,这个译本内容非常详尽,篇幅较大,主要体现在许多修饰性话语也被事无巨细地翻译了出来。①对比《回忆录》正文的第一段内容,1825年译本详细地描写了许多涉及宗教的祷告、祝福词:“致敬名字被铭刻在一切存在之上的他。他的光辉形象被印在宇宙的墙壁和门户上。致永恒的造物者,他用一句话,从一切虚无中创造了天体和创造自然的元素。致敬作为无所不能的造物者的他,他在我们头顶上铺展着苍穹中交替环绕的穹隆,用他的强大力量把土地装饰得光彩夺目。致收获了无尽的赞美和无限的感激的他,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他是安拉创造的最优秀的成果,他把人类从错误的迷宫中解放出来,指引他们走向真理和责任的大道。致敬从安拉那里得了无数的祝福的人们,得到了凌驾于一切地球力量之上的权威,并且超越了所有其他先知的显赫地位。”而后续版本中,这一段大多删改省去。对于当时受众者来说,1825年版本不失为一本历史研究的好工具。可是,苦于时代久远,也无新的注释版出现,其中较为古老复杂的英语语言用法,如词语拼写、语法结构、修辞对读者来说较难读懂。②现代英语中较少出现的变位与变格在1825年译本中无处不在,如:thee,thou,thy等等。还有许多与现代英语拼法不同的单词多次出现,如受早期近代英语影响下的单词结尾不发音的“e”的残留。此版本的内容中还有许多比较古旧的计量单位,虽然译者都以作者所处时代的单位为标准进行了注释,但原书中的计量单位和用于解释的计量单位现在大多已废弃不用,所以现代读者很难理解这些单位的含义。此版本作为19世纪早期的翻译研究成果,在之后的50年内流传了很久,对于学者研究印度的历史文化宗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第二个版本出版于1875年,译者是学者亨利·迈尔斯·埃利奥特(ELLIOT H M)[3]。埃利奥特最负盛名的成果是由中世纪的波斯编年史翻译而来的《印度史家笔下的印度史》(The History of India as Told by Its Own Historians)。与1825年译本相比,1875年译本借鉴的抄本有所不同。埃利奥特在序言中写道:“我们现在开始考虑真正的《贾汉吉尔回忆录》。一开始,我们对如何称呼这本自传感到困难,前面的文章已略微提到了这个问题。给《回忆录》起的名字,不论真假,差别很大”。由此可见,抄本的多样性使得译者难以统一标准,因此在研究中不必强求于原本的准确无误,而是要注重相同的部分。这个译本相较于1825年译本内容上略有删减,许多修饰性的词语相比第一个版本明显少了许多,字数也明显较少。令研究者较为不便的是,此译本注释比较稀缺,其中许多专有名词对于现代研究者来说难以理解。同时,相较于其他版本,作者并不是专业译者或历史学家,因此,此译本在当时与现代运用情况都较少,对其评价也低于其他译本。
第三个版本是皇家亚洲学会丛书中的译本,出版于1909年。译者为亚历山大·罗杰斯(ROGERS A),序言中编注者亨利·贝弗里奇(BEVERIDGE H)提到,《回忆录》第一本波斯语的出版物是由萨义德·艾哈迈德(AHMAD S)1863年在加齐普尔(Ghazipur,现印度北方邦城市)印刷出版,1864年又在阿利加尔(Aligarh,现印度北方邦城市)印刷[4]ix-xii。译者运用了前文所提的第一本波斯语出版物作为底本,相较于前几个版本运用各式波斯语抄本来说,印刷物底本相对精确,翻译质量相对来说更有保障。此外,著名东方学者亨利·贝弗里奇对译本进行了编注,明显提升了此译本的翻译和学术质量。贝弗里奇与夫人安妮特(BEVERIDGE A)都是著名东方学者,安妮特还翻译了《巴布尔回忆录》(Baburnama)等诸多突厥文与波斯文文献。夫妇二人的成果对后世研究影响颇深。1909年译本首次对《回忆录》进行了全文翻译,语言典雅,可读性高。脚注和尾注也都十分细致,能帮助读者更好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提供了许多有用的前人文献供学者们研究。唯一不足之处就在于篇幅过长,略显繁琐。由于之后约90年间,都没有新译本出现,1909年译本发行量极大,传播非常之广。并且,由于此版本相较前两个版本更易于阅读,因此成为了20世纪学者研究莫卧儿帝国和贾汉吉尔皇帝的首选译本。因此,许多二手文献和后人研究都由此展开[1]ix-x。后世《回忆录》的译者萨克斯顿曾说到:“罗杰斯和贝弗里奇的翻译格外精确和正确,除了语气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批评的”[1]ix-x。综上,现今研究《回忆录》与莫卧儿历史文化宗教时,这个译本仍是学者们参考的重要来源。
距今最新的版本于1999年出版,由著名学者、翻译家惠勒·M·萨克斯顿(THACKSTON W M)翻译、编辑和注释。译者对波斯语颇有研究,是美国著名的波斯语语言学家,编写了许多波斯语手册或教科书,也翻译了许多波斯语历史文献。据译者在前言中所述,现存的《回忆录》有两种原始版本,最“原始的”的版本藏于全世界许多图书馆中,如旁遮普大学图书馆(此版本上甚至有贾汉吉尔皇帝和沙贾汗皇帝的印章),英国和巴黎的高校图书馆中也有留存。1999年译本也是基于此原始版本译出,因此,来源与可靠程度较高。另一“原始”版本则是1909年版本所依照的1863与1864年印刷的波斯语版本[1]ix。1999年译本的翻译相较于前几个译本更加贴近当下,对许多被之前古旧晦涩的版本而吓退的读者有很大的吸引力。如上可知,萨克斯顿对1909年译本评价颇高,但是对译本的语气有所保留,在前言中进行了批判:“然而,像许多早期亚洲作品的译者一样,罗杰斯和贝弗里奇并没有直接反映出贾汉吉尔散文的通俗性,而是倾向用生硬、或笨拙的英语来表达。这代表了一种翻译流派,似乎译者认为很久以前的人们都必须用‘thee’和‘thou’来表达交流。往好了说,就像现在听到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说话那样……”[1]x萨克斯顿认为《回忆录》的语态更加偏向于“正常的、日常的波斯语口语”,不需要译者用“翻译一部巧妙的复杂修辞作品”的方式对译文进行美化和修饰[1]ix-x。译者对于译文风格的取舍也契合了《回忆录》的体裁与行文方式,增加了译本的可读性,不失为一大创举。此译本中还增加了许多奢华的莫卧儿绘画彩色插图和其他艺术品图片,以便于读者理解人物关系和时代背景。同时,译者所加的序言、注释、附录和索引,对学术研究产生了极大帮助。并对许多不具有文化历史背景的读者来说难以理解的波斯语词语,如人名、地名、物品名称、习俗名称、计量单位等等,提供了详细清晰的页边注释。而老译本中大多直接由波斯文进行英文转写,使人不知所云。这个版本也是现在研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译本,尤其是21世纪以来,许多研究莫卧儿历史的文章与著作都采用此译本。因此,本文主要以此译本为底本展开对《回忆录》的分析研究。
国内外对《回忆录》本身系统的研究较少,大多研究都集中在以《回忆录》为文献史料来源,对文章的观点进行佐证,仅有对于诸多译本的评论散见于序言、文中注释、译本书评等等。18世纪,一位名叫穆罕默德-哈迪的学者在回忆录结尾处增加了续篇[1]455-460及前言,前言中简述了贾汉吉尔的生平[1]3-18。许多学者分析了《回忆录》的文学价值,如R.C.马宗达(MAJUMADAR R C)等在《高级印度史》(An Advanced History of India)中提到《回忆录》是贾汉吉尔文学造诣的光辉例证[5]503。陈溯在《波斯语印度史文献》一文中对《回忆录》史料真实性予以了肯定,但认为其文学、史料价值相较于《巴布尔回忆录》和《阿克巴纪》相差甚远[6]161-176。近些年来,国外许多学者也运用了《回忆录》从较为正面的角度研究了贾汉吉尔的生平,如科琳·勒菲弗尔(LEFEVRE C)认为,虽然贾汉吉尔以嗜酒如命而闻名,对统治自己的帝国兴趣不大,但事实上从他的回忆录中可以发现许多贾汉吉尔对政治感兴趣的例子[7]452-489。泰米亚·R·扎曼(ZAMAN T R)通过《回忆录》中作者主观性与对自身权力的认知,探讨了家庭生活与性别观念对这些认知的影响[8]。
本文在前人对莫卧儿帝国研究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将《回忆录》英译本的史学价值进行了梳理与概括,论述了其真实性、稀缺性与不可或缺性。同时,也运用了《回忆录》中许多内容破除对贾汉吉尔及其治下的时代的刻板印象与偏见。
二、《贾汉吉尔回忆录》英译本的史料价值
《回忆录》的波斯文原名为“Tuzuk-i-Jahangiri”,意为“贾汉吉尔的章程”。波斯语中的“tuzuk”来源于突厥语“tiiziik”,意思是“管理”“命令”等,专门用来指统治者或军官纪律严明、井然有序地维护和部署他的军队和参谋[1]ix。因此它们被赋予了辅助标题“tuzuk”,这个术语也成为统治者传记的通用标题。贾汉吉尔本人没有用“tuzuk”作为标题,他特别把《回忆录》称为“Jahangirnama”(《贾汉吉尔回忆录》),意为“贾汉吉尔的书”。1605年,贾汉吉尔即位,开始撰写《回忆录》。1622年,贾汉吉尔停止了回忆录的撰写,由其私人秘书穆塔马德·汗撰写回忆录并交其校订[1]386。他们的合作一直持续到1624年,《回忆录》在此突然中止。
(一)作为一手史料的真实性
贾汉吉尔生活在一个较为和平安稳的大环境下。在他的父亲阿克巴统治时期(1556—1605年),莫卧儿帝国①莫卧儿帝国在英文语境中称Mughal Empire,又称Mogul或Moghul,波斯语转写为Hind-e Moǧulān。现在人们使用的“莫卧儿”和“Moghul”的术语在19世纪开始流行,据学者考证来源于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中的“蒙古”(Mongol),它强调了帖木儿王朝的蒙古起源,可见DODGSON M.The Venture of Islam:Gunpowder Empires and Modern Tim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9:62.但是,巴布尔的祖先与成吉思汗时期意义上的“蒙古人”截然不同,因为巴布尔及其父辈们更倾向于波斯文化而不是突厥-蒙古(Turco-Mongol)文化,这也反映出了“Mughal”或“Moghul”一词的复杂性。从历史上的各种名称来看,最初巴布尔称建立的帝国为帖木儿帝国(Timurid Empire),这反映了他帖木儿后裔的身份(可见AVARI B.Islamic Civilization in South Asia:A History of Muslim Power and Presence in the Indian Subcontinent.Routledge,2004:83).莫卧儿人对他们自己王朝的称呼是廓尔卡尼(Gurkani,波斯语“Gūrkāniyān”,意为“女婿”),参见MOHAMMAD Z,ed.,THACKSTION W M.The Baburnama:Memoirs of Babur,Prince and Emperor.New York:Modern Library,2002:xlvi.莫卧儿帝国另一个名字是“印度斯坦”(Hindustan),这个名字在《阿克巴的章程》(Ain-i-Akbari)一书中有记载,许多学者通常认为“印度斯坦”是最接近于这个帝国的官方名称(可见以上书目及VANINA E.Medieval Indian Mindscapes:Space,Time,Society,Man.Primus Books,2012:47).的边界已经扩大到包括了整个印度北部的次大陆地区。除了在西北部与萨法维伊朗的边界发生了一些小规模冲突之外,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已经恢复平静。唯一活跃的军事前线是南部德干高原地区(莫卧儿帝国享国三百余年,也没能统治印度南部)。经过祖辈的扩张征伐,莫卧儿帝国此时正处于权力和繁荣的巅峰。相对于父亲阿克巴命人书写传记,贾汉吉尔则选择了自己撰写。相对于父辈的流亡败走或四处征战,安稳的内外部环境或许给予了这位皇帝书写传记的客观条件。
通过对《回忆录》的研究可以反映贾汉吉尔在各种政治、宗教和社会问题上的想法。但总的来说,主要部分还是他在《回忆录》中事无巨细描写的享乐生活,关于军国大事的篇幅则相对偏少。这是与其祖辈传记的不同之处,也是大多数史家忽略或轻视这本传记的原因。曾祖父巴布尔的《巴布尔回忆录》详细地记述了他即位后发生的大事小情,不仅提供了强大完备的一手史料,同时也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关于其父阿克巴生平的《阿克巴纪》也体现了极高的史料及文学价值,作者通晓多种语言,水平较高。珠玉在前,贾汉吉尔的《回忆录》就相形见绌了。但是在关注《回忆录》的不足之外,也应注意到,其中对细微之处的描写让此书显得更加真实。
贾汉吉尔的《回忆录》描写的是他统治时期的历史,与他的前任和继任者不同,他没有聘请或委托专业史家,而是自己记录其治下的重要事件。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这些可能不是特别有趣,但它们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贾汉吉尔喜欢记录他日程表的细节,展示了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这部分对于普通读者很有吸引力,也对体现贾汉吉尔的性格具有一定意义,但这部分几乎没有史学研究价值[1]xxi。尽管如此,这些琐碎的记述记录了其治下发生的各类事情,从侧面反映了时代背景。在研究印度历史时,由于“他们很少倾向于去记录历史事件”[9],因此,了解某个人物和群体时,考察其生活方式和时代背景极为重要,体现了《回忆录》珍贵的史学价值。
(二)作为波斯语印度史文献的稀缺性
在英国殖民印度次大陆之前,波斯语是印度次大陆的通用语言(lingua franca),也是印度北部广泛使用的官方语言。这种语言被许多突厥王朝及阿富汗王朝,尤其是德里苏丹国和莫卧儿帝国所使用。波斯语在宫廷和国家的行政系统中具有官方地位,它对许多地方语言产生了重大影响,包括现代的标准印地语与乌尔都语。虽然波斯语已不再流行于南亚地区,但《回忆录》的波斯语对我们追溯波斯语的发展历程能够有所帮助,为外国语言文学、历史语言学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一手文献。
贾汉吉尔的祖辈并不是波斯语母语者。莫卧儿王朝的开国君主巴布尔是突厥化蒙古人,父系为帖木儿后裔,母系为成吉思汗后裔。因此,在这种复杂的生长环境下,巴布尔从小受到了非常好的教育,其母从小教授他波斯文和察合台文,青年时就具有了极高的艺术修养和文学造诣。《拉失德史》(又译《赖世德史》)的作者米尔咱·海答儿评价巴布尔的诗才仅次于察合台语之父纳瓦依[10]。《巴布尔回忆录》也是以察合台文写成,这种语言现今已经消亡,给人们研究早期莫卧儿历史造成了一些语言上的障碍。据记载,贾汉吉尔的祖父胡马雍和父亲阿克巴都是察合台母语者。阿克巴自己虽不能读写波斯语,但聘请了许多学者创作了波斯语的历史著作[6]171。《胡马雍纪》和《阿克巴纪》虽以波斯语写就,但作者都不是传主本人,《胡马雍纪》由胡马雍的同父异母妹古尔巴丹·贝古姆(BEGUM G)写作,《阿克巴纪》则由宫廷历史学家阿布法兹尔·穆巴拉克(MUBARAK A)完成。贾汉吉尔虽声称自己也懂一些他的祖传语言,“尽管我在印度斯坦长大,但我并不是不知道如何说或写突厥语”[1]77。贾汉吉尔懂得察合台语,但并不影响他运用波斯语撰写日记。《回忆录》的行文也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反映了其波斯文水平,例如1999年译本的前言提到了《回忆录》与某些呆板、古老或浮夸的波斯语文献不同,语言坦率而清新[1]x。《回忆录》作为第一部皇帝的波斯语自传,其地位非常重要。
(三)作为家族系列传记一部分的不可或缺性
从个体出发,贾汉吉尔家族书写传记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帖木儿时代。1425年完成的《帖木儿武功记》(Ẓafarnāmah,意为胜利之书)是15世纪波斯史家歇里甫丁·阿里·雅兹迪的作品。贾汉吉尔的祖辈们也都有传记流传,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史料链条,对后世学者了解莫卧儿帝国前期历史有着极大作用。自德里苏丹国与莫卧儿帝国时期,国王传记类的历史叙述才开始不断增多;同时,国王传记吸收了阿拉伯和波斯的历史写作传统,关注史料的准确性和真实性[11]63。
随着专制统治的增强,以传记和谱系为题材的著作数量越来越多,常被用来树立君主的政治权威。通常,波斯史学中的传记暗含说教意味,通过君主的形象塑造来呈现个性和王权[8]677-700,这些在早期莫卧儿帝国君主的传记中有明显体现,《回忆录》也不例外。贾汉吉尔认为《回忆录》可以作为维护帝国统治的方针。他声称自己制作了很多副本,“奖励送给仆人们、送给了自己的儿子或送往其他伊斯兰国家,供统治者作为统治手册使用”[1]271。通过传播《回忆录》给如穆斯林国家的君主们等特定人群,贾汉吉尔运用政治宣传来宣扬自己的统治[12]279-281。
在大环境下看,波斯史学中撰写“君主之鉴”(Fürstenspiegel)的传统由来已久。自中世纪起,历史研究就逐渐得到了宫廷的赞助和支持,受君主资助的宫廷历史学家开始活跃在史学书写的舞台上。许多历史学家转向写作当代的历史,王朝史和传记书写得以兴起。史学的官僚化和世俗化由此慢慢发展起来[13]37-38。
莫卧儿帝国君主的传记便是在这两大背景下形成,既迎合了贾汉吉尔家族内部的传承,也继承了中亚南亚地区的文化传统。《回忆录》因此也成为一系列“君主之鉴”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对整体研究莫卧儿君主传记文学起到重要作用。
三、《贾汉吉尔回忆录》的重要作用
尽管《回忆录》的史料价值颇丰,但也应认识到《回忆录》相比其他史料仍有许多不足之处。与先辈的《巴布尔回忆录》与《拉失德史》相比,《贾汉吉尔回忆录》的文学价值与史学价值逊色很多。《回忆录》中对政治发展、社会生活及经济情况的描写明显不足,对深入研究造成了一定的阻碍。总的来说,《回忆录》仍是研究贾汉吉尔时期历史的重要来源,此章也试图从两个方面展开。
(一)纠正对贾汉吉尔的“刻板印象”
人们对贾汉吉尔的鄙夷与不屑往往源于他的无所事事和对政事的懈怠。在传统的历史写作中,人们常常赞叹于其父阿克巴的丰功伟绩,感叹于其子沙贾汗的深情款款,却往往忽略了这位皇帝。他普遍被认为是一个软弱无能的统治者,受制于他的妻子努尔·贾汗(JAHAN N),沉迷于酒精和毒品,整天无所事事。后世学者对贾汉吉尔有许多生动却片面的描述。亨利·贝弗里奇将贾汉吉尔比作罗马皇帝克劳迪亚斯(CLAUDIUS),因为他们都是“软弱的人……不该作为统治者……如果贾汉吉尔是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馆长……他会是一个更好更幸福的人”[14]311。意大利旅行家尼科劳·马努奇(MANUCCI N)曾在贾汉吉尔的孙子达拉·希科(SHIKOH D)手下工作,他在谈到贾汉吉尔时说:“一个经过经验检验的真理告诉我们儿子们总会挥霍父亲留下的一切”[14]311。即贾汉吉尔挥霍了其父阿克巴留下的财富与威望,以此来证明贾汉吉尔的无能和软弱。《新编剑桥印度史》(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Mughal Empire)的作者约翰·理查德(RICHARDS J F)也提到,贾汉吉尔频繁地回到私人生活而躲避政事,将国家大事都交给其妻努尔·贾汗与宠臣们,反映了他的懒惰与无能,因为他每天沉迷于酗酒和吸食鸦片而不干正事[15]102。
事实上,通过对贾汉吉尔个人的研究,以及对《回忆录》的分析可以看出,《回忆录》反映了贾汉吉尔在各种政治、宗教和社会问题上的思想和行为手段,这对前代学者的偏见和刻板印象进行了鲜明的反驳。
在其继任之初,贾汉吉尔便打破了在其父阿克巴时期订立的诺言,剥夺了长子的领地;摒弃了中亚式帖木儿帝国传统的继承法则,即君主死后,诸子分治;强化了其父阿克巴期间的继承传统,即由继承人独自统治并打击其他潜在继承人的权力。同时,贾汉吉尔还限制了许多近支宗室王公,如其叔父与早逝兄长的子孙等的权利[16]33-34。通过这些措施,贾汉吉尔运用权术排除异己,加强了皇帝的权利及个人的专制,将分散在宗室手中的领地和特权尽可能的收归皇室[16]33-34。从贾汉吉尔即位初期的诸多举措来看,他在政治上的举措绝不是后世所评价的“无能”。同时,贾汉吉尔还继承了其父阿克巴的“宗教宽容政策”,实行“宗教融合主义”。①大多数研究专注于阿克巴的“宗教宽容”与奥朗则布试图加强伊斯兰教的宗教地位,企图使印度完全伊斯兰化的举动,对贾汉吉尔宗教政策基调与阿克巴的相似性的研究不够成熟,但共识是认为贾汉吉尔延续了其父的“宗教融合主义”,可参见张忞煜.多元帝国下的“王法—教法”博弈——以印度锡克教—莫卧儿政权关系演变为例.世界宗教文化,2019(1)。因此,贾汉吉尔没有进一步激化伊斯兰教与印度教及其他宗教之间的矛盾,平衡了信仰不同宗教之间地区的稳定,从而维护了帝国对多民族、多宗教信仰下的印度的统治。同时,贾汉吉尔不断地试图加强君主集权,对地方分裂势力进行打击,例如颁布“十二敕令”这类立法政策,鲜明地表达了他的政治倾向[1]26-27。这些法令旨在保护普通臣民的利益,尽量减轻他们所受的剥削和迫害。总的来看,贾汉吉尔在政事上颇为懈怠,但也不能抹杀其即位初期的积极举措与影响。
贾汉吉尔最为后世所诟病的除了寻欢作乐的作风,就是“受制于”其妻努尔·贾汗。但学者们在说明此类情况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两个很重要的时代背景。第一,努尔·贾汗虽然在贾汉吉尔统治时期拥有很大的权力,但这种权力只是相较于其他皇帝的后宫而言;而这种权力究竟是否超出了宫廷妇女干政的限度,今人并不得知。在笔者看来,努尔·贾汗之所以成为“牝鸡司晨”的代表,只是因为其身处宗教的压迫下(尤其在伊斯兰教的限制下,妇女们较少抛头露面,参与政治决策),当时社会的女性地位总体来说十分低下,因此她显得颇为特殊。与此同时,学者们往往忽视努尔·贾汗的成长过程中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及其优越的家庭背景,因此她具有一定的政治智慧并不令人奇怪。有趣的是,后世史家在描述她对家族的提拔时,却忽略了其父本为波斯贵族,早在阿克巴时期就已任喀布尔省的财政官这一事实。第二,后世学者在论证努尔·贾汗对贾汉吉尔的影响时,往往援引其在贾汉吉尔去世前皇子们争位中的表现。由于莫卧儿帝国一直没有形成完善的储君制度和继承制度,皇子们在父亲去世前后进行继承战争司空惯见,常有后宫势力参与其中。但是,努尔·贾汗支持的皇子在斗争中落败,其兄阿萨夫·汗(KHAN A)支持的沙贾汗成功即位。由此可见,努尔·贾汗的影响力被后世史家有所夸大。因此,对努尔·贾汗在贾汉吉尔时期的政治影响力还有待研究。
(二)对印度历史“偏见”的回应
近现代史家和哲学家曾经深受偏见的影响,认为印度是一个“隔绝于世界的次大陆地区”,或认为“印度文明没有历史”,①详见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哈尔福德·麦金德《印度次大陆》、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黑格尔《历史哲学》与《世界史哲学讲演录》、亨利·迈尔斯·埃利奥特《印度史家笔下的印度史》、詹姆士·米尔《英属印度史》等著作。或是沉迷于以“西方中心论”的概念先入为主产生偏见。例如以《剑桥印度史》和《牛津印度史》为代表的“正统印度史学”以詹姆斯·米尔在《英属印度史》一书中阐述的“印度文明”概念为基础,借用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建构了“雅利安历史叙事”[17-18]。
近年来,对这些偏见的反驳也在理论上回击了这些问题。罗米拉·塔帕尔(THAPAR R)指出“几百年前,有人说印度文明因它缺乏历史书写而独一无二。含蓄地说,因此也就缺乏一种历史感。除了极少数的例外,自那以后几乎没有人尝试去检验这种普遍性。这种观点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现在人们几乎不敢去争辩否认这种对历史的否定。我想说的是,尽管在过去的早期,可能没有以目前被认为恰当地属于既定历史体裁的形式进行的历史书写,但那个时期的许多文本反映了一种历史意识”[19]3。其著作反映了其对“正统印度史学”的停滞论的反驳,而主张印度社会的“发展”特性。《新编剑桥印度史》也对“地理决定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在本书“新印度史学”的建构中,不再将印度看成一个“单一而封闭的自然区域”,即“封闭的印度斯坦地区”,而是将“印度的地理环境描述为一个多元而开放的地理空间”的概念[17]。同时,该书以“早期现代”概念为基础构建的“莫卧儿帝国叙事”,学者将其形容为“正统印度史学的历史叙事建构了一种传统性的历史空间,而新印度史学的历史叙事则建构起一种现代性的历史空间”[18]。其实如果稍加分析《回忆录》,这些偏见都将不攻自破。
在《回忆录》中可以明显找到许多证据驳斥“封闭的、单一、东方专制主义的”印度的说法,尤其是贾汉吉尔对外国使节的大篇幅描写。他大量描写了与萨法维帝国的阿拔斯一世的“友谊”,以及两国的频繁来往。书中不厌其烦地描写了萨法维帝国来使们的人物、赠礼,以及对使节们的优待等等。②由于《回忆录》中作者提到阿拔斯一世与萨法维帝国的使团次数过多,例如,仅阿拔斯一世的名字就被提及500余次,因此将不具体标注页码。贾汉吉尔对于西亚、中亚各国的诸多描写、对于与伊斯兰国家来往的重视体现了莫卧儿君主的伊斯兰世界整体观,为驳斥上述理论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贾汉吉尔通过持续不断地对外来往和相互交流,不遗余力地将莫卧儿印度与西亚各国联系起来,尤其是西亚与中亚的各个穆斯林君主与国家。贾汉吉尔也将其视作身处于“一个大的穆斯林君主世界”之中。巴布尔以降,莫卧儿诸王在统治印度次大陆的基础上,始终立足于自身的波斯传统,并未将其统治与亚洲割裂开来。
并且,在贾汉吉尔在位期间,欧洲与印度交往密切。从《回忆录》中可见,葡萄牙人和英国人都在他的宫廷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尤其可见于贾汉吉尔时期时任英格兰大使托马斯·罗伊(ROE T)的日记记述[20]。直到贾汉吉尔时期,欧洲人在与莫卧儿帝国的交流中,并未将莫卧儿统治者视为除“交易伙伴”以外的形象。欧洲诸国与莫卧儿交往期间也并没有将其作为一个“低劣”或“次于”欧洲国家而存在的对象。贾汉吉尔的态度也是如此。他在《回忆录》中对许多欧洲来访者有所提及。但贾汉吉尔及当局的态度,仅仅是将欧洲来访者作为潜在的“贸易伙伴”,远不如中亚的穆斯林统治者重要。例如,贾汉吉尔在《回忆录》中数次提到了“Franks”以此用来称呼其宫廷中的欧洲人,包括葡萄牙人(Franks of Goa)与英国人等等,但次数上比提到中亚的次数少得多。①提到“Franks”和“Frank”(欧洲的外国人)的情况见[1]第40、133、154、201、218、228、298、299页。虽然贾汉吉尔的宫廷中有许多欧洲来访者,但他们的存在更像是一种新鲜事物,而不是一种贾汉吉尔本人与帝国政府应该认真对待的关系,因为他们各自的国家并没有表现出作为亚洲世界舞台上的政治角色所必需的那种外交和政治重要性[12]280。虽然两者之间的关系还有待考察,但是将莫卧儿帝国视作“孤立于世界潮流之外”之说,还是略微不妥。《回忆录》的记述为后世学者以客观的态度对待印度历史提供了积极的例证,也能帮助研究者逐渐以开明客观的态度进行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