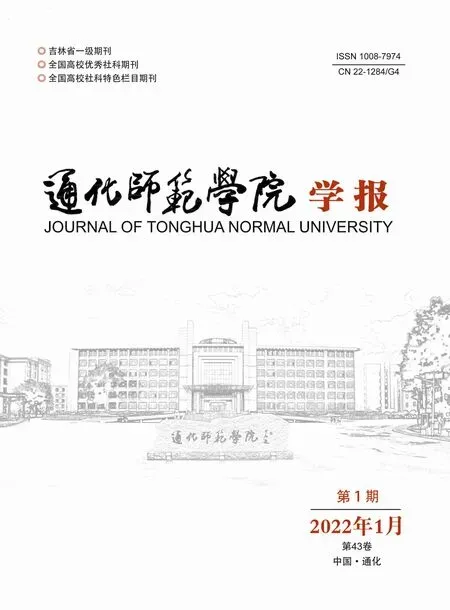2000年以来大运河漕运史研究综述
邵 波,钱升华
始凿于公元前5世纪的大运河,不仅是中国古代沟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更是深刻影响了沿线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自1890年代有关大运河漕运研究的文章见诸报刊后,一些论著先后问世,如清水泰次《明代漕运》、高殿钧《中国运河沿革》、汪胡桢《运河之沿革》、张崑河《隋运河考》、陈隽人《南运河历代沿革考》等文章对大运河的历史沿革、河道变迁、漕粮输送等问题进行了探讨[1]。史念海《中国的运河》与全汉昇《隋唐帝国与运河》是这一时期大运河漕运研究的重要专著。1949年后,朱楔《中国运河史料选辑》,庄明辉《大运河》,常征、于德源《中国运河史》,邹宝山《京杭运河的治理与开发》,姚汉源《京杭运河史》,吴琦《漕运与中国社会》等一系列重要著作相继发表,使大运河漕运史研究更加深入。而一些专题性的研究论文如谭其骧《黄河与运河的变迁》、邹逸麟《山东运河历史地理问题初探》、孙寿荫《京杭大运河的历史变迁》、朱玲玲《明代对大运河的治理》等则进一步丰富了漕运研究的内涵和外延,将漕运史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自2000年以来,大运河漕运史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态势,各类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研究领域更加广阔,研究取向更加多元,研究方法不断创新,研究内容更加深入。鉴于此,本文拟就21世纪以来有关大运河漕运史研究情况略作述评。囿于作者史学功底及学识水平,所涉内容难免挂一漏万,故以此文求教于各位前辈方家批评指正。
一、大运河漕运通史类研究
通史类论著对于系统把握大运河漕运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在研究著作方面,运河研究大家邹逸麟先生《舟楫往来通南北:中国大运河》围绕大运河开凿的历史地理背景展开论述,着重分析运河工程、管理制度、运输能力和漕运对推动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作用,同时阐释漕运发展的局限性及由此造成的影响[2]。陈桥驿先生领衔编著的《中国运河开发史》汇集邹逸麟、王守春、朱士光等史学大家,对我国各个历史时期主要运河的起源发展、演变、现状及历史作用进行详尽探究,是近年来大运河漕运研究的扛鼎之作[3]。安作璋先生《中国运河文化史》将大运河开凿整治史与运河文化史进行有机融合,着重考察漕运引发沿线区域的经济社会变迁、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及社会组织与对外交往等问题,深刻阐释运河流域性文化的总体特征及在推动中华多元传统文化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4]。陈璧显主编的《中国大运河史》在收集占有丰富史料的基础上,以时间顺序为轴就大运河流经区域的政治、经济、军事及社会风俗等展开论述,探析运河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5]。此外,特别需要关注的是《京杭大运河遗产保护出版工程》丛书,该系列丛书内含三卷12分册,涉及大运河历史、文化、保护三个方面,是全面深入介绍大运河漕运文化的重要著作。丛书中比较重要的作品,如李跃乾《京杭大运河漕运与航运》对大运河漕运发展脉络做了系统梳理,重点研究漕运与大国崛起的关系、与历代战争的联系以及与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关联。毛峰《京杭大运河历史与复兴》将大运河兴衰隆替置于历史演进的大环境中,指出大运河畅通繁荣,必是国家统一兴旺之时,而国家分裂衰败之际,大运河也必然梗阻荒弃。蔡蕃《京杭大运河水利工程》将研究的视角伸向大运河各河段的重要水利工程,详述运河上各种水工设施的构造及其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历代运河管理机构和管理方式,以及历史上与运河有关的代表性治水人物及著作等。
除了大运河漕运全域史研究外,不少学者还对地域运河漕运史问题进行了探讨。如,钟军等编著的《隋唐运河故道地名考》对隋唐大运河中广通渠、通济渠、永济渠的流经线路及河道整治和地理名称进行了考证[6]。戴兴华等《隋唐运河汴河段漕运探考》研究了汴河漕运的兴衰过程,对汴河漕运的机构设置、管理制度、仓库设置、转运物资及沿线城镇等情况进行了考察[7]。王栋《山东运河航运史》以山东运河漕运为主线,全面揭示山东运河漕运的演变过程及在航道治理、船舶修造、运河管理等方面的情况,论述大运河对山东乃至全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影响[8]。孙忠焕编著的《杭州运河史》对大运河杭州段的历史演化及社会、经济、生态变迁进行了梳理[9],浙江省港航管理局编写的《大运河航运史(浙江篇)》则汇集各类史料和港航部门的资料数据,对大运河浙江段航运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10]。邱志荣等在《浙东运河史》中,阐述浙东运河的历史发展变迁,用大量史料论证“浙东运河为我国最早的人工运河”之一,并阐述“浙东运河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影响”[11]。
在通史类论文方面,顾建国、范新阳对大运河各个历史时期的称谓进行了梳理和考证[12]。王明德从时间跨度上将大运河的发展划分为发生、发展、繁荣与终结等不同历史阶段,并指出各个阶段既相互衔接又自成系统[13]。王健对大运河沿线的三大入海通道问题进行了考察[14]。孙竞昊对浙东运河的发展历程及各个历史时期的功能进行了研究[15]。吴琦对古代漕运线路的变更进行考察,指出漕运方向的变化实际是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在空间地域上的变动,一方面漕运成为北方统治集团牵绊南方经济重镇的绳索,另一方面则有效调控和制衡沿线的社会功能并促发运河经济带的产生,而这些变动背后隐含着大一统王朝以内河漕运为主的价值取向问题[16]。李泉对运河文化的内涵、特点及形成演化过程进行探讨,认为运河文化萌芽于先秦汉晋,形成于隋唐宋元,兴盛于明清两朝,是中华民族文化大系中的南北地域跨度大、时间积累长、内容丰富多彩的区域文化[17]。对于大运河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邹逸麟指出,大运河在推动中华大一统国家形成和延续中华文明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8],王健也认为大运河对中国古代统一疆域的形成与巩固作用巨大,并推动了国家政治、经济、地理由东西之争向南北背离的转换[19]。
二、大运河漕运管治研究
漕运之制,为中国大政。自大运河开凿以来,历代王朝都不遗余力地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财力和制度成本来管理和整治大运河,以保障和维系漕运的畅通。对于漕运管治问题,经粗略汇总梳理,大体可分为漕运管理、河道整治、黄淮运维系及漕运与民生矛盾等多个方面。
在漕运管理方面。马晓峰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漕运管理机制、物资运输类型、协调维护机构及保护管理体系等诸多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此时漕运主要服务于军事活动[20]。张晓东梳理了这一时期漕运政策的发展变化和政令统一与漕运体系之间的关系[21]。曾谦研究了隋唐洛阳运河体系的构成与漕粮运输问题,指出洛阳漕粮存储地点在该时期发生了由河阳仓至洛口仓再到含嘉仓的变化[22]。陈朝云对唐朝河南地区的粮食运输与仓储体系的变迁同陆、漕线路变化关系进行了分析[23]。苏毅围绕中晚唐时期政府对运河漕运争夺、管控与维系等一系列重大政策举措作了梳理回顾[24]。五代十国两宋时期,政府继续开展隋唐大运河的整治与管理。王颜、杜文玉对以开封为中心的运河水系变化及南北方自然水道通航情况进行分析,初步勾勒出五代时期的漕运交通运输网络[25]。张晓东研究了该时期中原各国利用漕运支持东北边防的措施和作用,指出此时有关漕运的一系列战略决策对后来赵宋王朝的军事行动产生了重要影响[26]。吴同围绕北宋时期汴河、淮南运河的通航能力进行分析,认为尽管中央政府对淮南运河进行改造,但受制于开闸频率、过闸船只数量、船只载重量等因素的限制,运河通航能力始终是制约北宋财政调拨与民间商货运输的重要原因,致使大批东南廪粟无法北运[27]。终元一代,漕运以海运为主,河运为辅。孟繁清指出,元代海运的开辟和发展同元朝政府推行的各类制度措施密不可分。他对元武宗时期的海运政策进行分析,认为“至大新政”的施行极大促进了海运的发展,提升了海运漕粮的数量[28]。钟行明对元代漕运管理机构的设置运转与空间分布特征问题进行了探讨[29]。王培华研究了元朝设立的负责水利管理机构都水监及河渠提举司的废立问题[30]。育菁则分别对元代都水监的设置年代[31]、山东分都水监建置[32]、江南行都水监建置[33]、汴梁(河南)分都水监建置问题[34]进行了考论。
明清两朝是漕运发展的鼎盛时期,京畿供养皆仰仗江南。学界对这一时期的漕运管理问题研究颇深,这其中不得不提的是黄仁宇先生的《明代的漕运》一书。该书以详实的数据和充足的考证论述了明代京杭大运河沿线地形地貌对漕运的影响、漕运管理的行政机制、漕粮输运制度与组织、宫廷供应品的运输以及由此引发的征税、商业、旅行和劳役等问题,探究明代的政府模式、官僚体系、财政政策、地理环境、社会风俗及思想观念等诸多方面的内容[35]。谢宏维、李奇飞对明代设立的漕运总督的权力职责、地域来源和任职期限等问题进行考察[36]。张艳芳研究了明宪宗时期设立的总理河道的职权问题[37]。他们均认为这些官衔的设立对于保障漕运水道的畅通和商品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吴士勇以首任文官总漕王竑为研究对象,指出其任职改变了明初武将主导漕运的传统,开创了文官理漕的先河,并成功地将总漕官职制度化[38]。柏桦、余同怀对明代闸坝官的设置、职责、功能及作用作了研究[39]。刘凤云对清代中期两江总督从临时性介入河务到通过制度明确责权规范现象进行考察,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18世纪社会环境的转换为行政官僚向技术官僚的转型提供了平台[40]。此外,郑民德对清代直隶河道总督的设置、功能和裁撤等问题进行考证,揭示清代对直隶地区河务的管理情况[41]。金诗灿则从清代河道总督与地方督抚职权存在交叉为分析的着力点,以时间演化为轴,分析了清朝初期、雍正时期及嘉道时期这种复杂管理体制给河务管理整治带来的影响[42]。吴琦、肖丽红对清朝中期以后出现的“废漕督”问题作了分析,认为该呼声的出现既体现部分官员对漕运总督及其漕运政策的失望,也从侧面反映出清廷政治格局、官僚体系及社会治理亟需进行调整和改变[43]。倪玉平对晚清时期漕粮海运取代河运之后的漕运官制变革进行了阐述,认为义和团运动是漕粮运输方式不断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并最终引致晚清漕政的终结[44]。此外,谭徐明等人以黄淮改道、漕运终结等标志性事件为切入点,从社会和自然层面对我国古代水行政管理体系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认为1930年代统一水政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现代水利管理体系形成雏形[45]。
漕运管理不仅涉及行政体系,也包含法律制度的建构与执行。为了保障漕粮北运的安全,明清两代均制定了比较齐备的漕运律法,促成近600年的漕运兴盛局面。吴欣对明清时期的漕运法规制度变革进行研究,认为明清两代漕运法规总体具有延续性,但在具体条款上清朝比明朝更加严密苛刻,这些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政治变革与经济发展[46]。李群在《清代漕运法研究》一书中从法制角度对清代漕运法立法背景、立法机构、诉讼案例等进行了论述[47]。吴琦、肖丽红对清代的漕控问题进行研究,指出漕控案件频发反映出官绅民之间的利益纠葛与漕政危机,以及清代国家事务在地方社会的执行及地方社会秩序格局的变迁[48]。肖丽红还以陆名扬闹漕为例,考察地方官员在漕粮征发中的作为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秩序问题,进而揭示清朝中期漕案频发、官民冲突加剧的内在原因,探究地方官员的治漕理念及对社会治理的影响[49]。此外,管婷婷[50]、张光辉[51]、杨品优[52]、孙伟平[53]、张小也[54]等人也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漕运律法问题进行了探讨。
在运道整治方面。刘建国、王克飞讨论了宋代江南运河修建和复建的澳闸系统,认为北宋与南宋在澳闸系统的建设方面侧重点不同,缘由在于为了适应漕运格局和转运功能的变化[55]。张勇从两宋漕运转输方向变化的角度对淮南地区水利建设进行考察,认为北宋时期淮南地区修建的一系列辅助漕运的水利工程,随着南宋政权漕运格局的变迁,其水利建设由以漕运为主转向集漕运、灌溉、防洪、御敌为一体的多功能布局[56]。薛磊对元代开凿的胶莱运河进行了研究[57]。崔建利、王欣妮考察了郭守敬关于大运河弃弓走弦的设计理念和规划思路,以及主持开凿通惠河的相关情况[58]。路征远、王雄[59]和张帆[60]等人也对通惠河的开凿、修治、疏浚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潘清考察了元代对太湖流域的水利治理活动,内容包括江南运河疏浚,开凿里运河、会通河,修建海塘等[61],同时还将研究视角扩展到江淮地区,指出元代运河治理的特点是国家大规模强势参与主要运河的贯通运营,以保障和恢复旧有水利设施满足漕运的功用[62]。张欣也认为,元朝对江浙地区的淮扬、练湖、镇江及苏杭运河的整治多以疏浚为主,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持运河的输运功能[63]。卢勇、刘启振对明初大运河南旺分水枢纽工程进行研究,认为这些水利设施构建了一个和谐的系统工程,是维系大运河长久畅通的保障,也是我国乃至世界水利工程的杰出典范[64]。赵珍对清政府在北运河张家湾段改道问题上的处置情况进行历史考察,指出人们适应水情和改造河道的过程反映出当时社会整体的认知程度和思想观念[65]。吴欣对明清时期浅铺的起源、构成和功能进行分析,指出浅铺兼具解决运河淤浅的水利设施与疏浚沟渠的河工组织两种性质,其功能在于疏通运道保持畅通[66]。水利设施的废立往往会带来不同群体对运河利益的争夺,从而对漕运制度产生不同的影响。张程娟以明代瓜洲闸坝更替为例,认为此举不仅推动了江南地区的长运法改革,而且对明代漕运制度改革与工部运河费用体系重构产生了重要影响[67]。袁飞考察了有清一代“以漕为先”理念下水利治理的方法,认为各种济运护漕工程的实施在保障漕运畅通的同时,也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给沿线百姓生产生活带来灾难[68]。
在黄、淮、运关系处理方面。田冰对有明一代治黄保漕问题进行研究,分析黄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水患对运河的影响,指出受制于黄河裹挟巨大黄沙及治河技术低下等原因,治黄保漕问题始终未得到较好解决[69]。展龙、陈志刚对明相张居正在黄淮运及三吴水利等方面的管理运营问题展开研究,分别从人事政策、水利资金和河工夫役三个方面进行探讨,认为这些管理手段保障了三河的正常运维和三吴水利工程的修建[70]。胡梦飞以运河徐州段为中心考察了明中后期为避黄保运而实施的一系列水利工程的影响,认为新河开挖对于避开黄河水患威胁和维护漕粮运道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对沿线城镇的兴衰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71]。王建革、袁慧对明清时期黄、淮、运、湖的水环境变化进行考察,认为随着黄河堤岸淤高和蓄清刷黄治理模式的失效,在加重里下河地区水灾的同时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苏北地区圩田体系和垛田体系的发展[72]。马俊亚从治水、盐业、生态经济等方面对明清时期淮北的社会生态变迁进行研究,指出为保障漕运命脉畅通,两朝强力推行“蓄清刷黄”“减黄助清”“筑堤束水”等治水方略,最终导致泗州城的沉没和淮北地区社会生态环境的恶化,成为“保漕济运”大政下的局部牺牲品[73]。袁飞回顾了清代的济运护漕政策,指出清廷在“漕运为先”的理念下采取的束水攻沙、蓄清敌黄等诸多治水方法,在保障漕运的同时却给运河沿线的生态环境与民众生活带来灾难[74]。曹志敏也认为,清政府为避免黄淮运大堤溃决而建立一系列减水闸坝在水利上是有利的,但也加重了苏北地区的水灾,对农业造成不利影响[75],并由此指出清代黄河河患的频仍与中央政府的治黄策略密不可分[76]。此外,韩昭庆通过考察南四湖的演变及其背景发现,虽然四个湖泊的形成原因和演化过程各自不同,但均与黄河泛滥、运河的改道及人工干预有着密切的关系[77]。
在漕运与民生协调方面。受制于水源问题,国家层面的保水济运及地方层面的保民耕作之间始终矛盾重重,由此引发一系列争水利、避水患的利益纷争。为了维系漕运畅通,明清中央政府先后颁布一系列保障水源补给的法令,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运河水源补给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灌溉和济运两者之间的矛盾始终未能得到根本解决[78]。吴琦、杨露春认为,这些问题需要从统筹漕运与灌溉之间的关系入手,妥善协调国家与地方在水资源利用方面的利益分配[79]。高元杰、郑民德对开凿会通河后运西地区的排涝问题进行研究,指出在保漕济运思想指导下,清廷对运西河渠的疏浚与排水纠纷置之不理,导致运西水患严重,严重影响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和地区经济的发展[80]。王婧对明清时期卫河漕运的修浚与用水制度问题进行探析,认为其秉持的“漕运尤重于民田”的指导策略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不利影响[81]。凌滟对南旺湖由天然湖泊经工程改造为水柜的历程进行研究,指出水柜、水壑概念的提出与实体的应用是明代河臣为确保漕运畅通而创造的政治术语,其实质是以“祖宗之法”行劳民伤财之举,从侧面反映出漕运对周边资源长期的侵蚀和占有[82]。此外,她还对运河水柜与民间泊洼的权益纷争及政策演化进行了研究[83]。
漕船管制和漕粮调配问题同样值得关注。李德楠对运河上行船的次序问题进行研究,指出运河上的行船也分三六九等,特权船只的存在不仅攫占了有限的交通资源,还妨碍了物品的输运效率和资源的有效配置,由此反映出管理机构在漕河管理上的弊端[84]。于宝航、田常楠也认为,基于封建等级制度的运河通航次序造成南北物资运输更多依附于具有官方背景的船只,不仅挫伤了民船输运的积极性,同时也影响了运河钞关的税收[85]。吴琦对清代漕运行程中最为关键的漕限、水程和土宜等问题进行研究,探讨了当时漕运的秩序、成本及与沿线地区商贸交涉等问题[86]。郑民德则将目光转向漕船的制造机构,对淮安清江和临清卫河两个明代最大的漕船修造厂进行研究,重点讨论了其设置沿革、管理运作和功能作用等问题[87]。关于漕粮的调配,胡铁球对明代漕粮的改折数量规模和价格问题进行考证,认为受制于稳定京师粮价、保障粮食供应和储备等原因,漕粮的货币化规模难以拓展[88]。吴琦、王玲对清代康雍之后中央政府漕粮截拨问题作了探讨,指出清廷经常把漕粮截留调拨作为一项应急制度,在出现社会矛盾的时候用于充实地方粮储、发放兵饷及赈灾平粜等,从而有效缓解繁重的漕运劳役给社会治理带来的影响[89]。此外,胡梦飞对明清徐州漕粮救荒问题[90]、李德楠对清代江浙漕粮输闽问题[91]、李俊丽对清代天津截漕转运问题[92]也进行了相应的研究阐述。
三、大运河漕运与沿线经济研究
漕运自产生之日起,便是一项社会性很强的经济活动[93]3。漕运的兴衰隆替对沿线经济的发展有着巨大影响。唐晓峰指出,古代中国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的背离是造成中央集权政府过度依赖运河的地理和政治根源,大运河作为商业活动的动员轴心,是联结不同经济区域的纽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沿线区域的发展[94]。张晓东认为隋代漕运系统的建构与政治、经济、地理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中央政府以运河为纽带借助漕仓的选址来加强南北地域间政治经济的联系与战略控制[95]。冯兵、黄俊棚对隋唐五代时期运河的开凿维护同沿线城市勃兴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认为运河改变了沿线城市的发展轨迹和规模等级,并赋予新的政治、经济、交通功能。同时城市发展也为运河的疏浚保养与经济效能发挥提供了物质基础,即运河与城市相伴而生、相互依存,互为影响[96]。张剑光指出,唐朝前期对江南运河的疏浚和利用,推动了江南地区经济尤其是粮草物资、农业种植、人员交往与城市商业的发展,并为“安史之乱”后国家财赋中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础[97]。张勇、曹卫玲对两宋时期淮南地区向中央转输物资问题进行研究,认为该区域在北宋前期居于枢纽地位,但随着蔡京将漕粮转搬法改为直达法及宋金战争的影响,淮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地位随之下降[98]。朱年志考察了元代会通河开凿对山东沿线商品经济与城镇建设的影响[99]。叶美兰、张可辉指出漕运对于促进国内经济的交流发展及政治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有清一代江苏运河城镇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漕运的通塞盛废休戚相关[100],叶美兰、李沛霖通过大量详实的数据论证,江南运河的畅通促进了该地区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推动了城市工商业的发展繁荣[101]。
运河不仅是漕粮转输的孔道,也是商品集散流通的重要路径。许檀认为,明中期至清中期,运河商品的流通量远远超过漕粮运输量,并对商品流通规模、类型、特点及地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李想通过考察明代漕军的私货贸易活动,认为私货贸易虽对正常漕运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这种政府优恤漕军的方式客观上推动了大运河沿线的商品流通与经济发展[102]。王明德指出,明清运河商人在经商过程中,为了开展贸易、休闲、联络乡谊等活动的需要,在沿线城市建立了一些商人会馆,这是运河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结果[103]。王云着重对活跃在山东运河区域的徽商活动范围、经营业态以及与当地社会交往融合问题进行考察,认为徽商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部分山东运河城镇的居民结构,促进了南北物资文化交流与社会经济发展[104]。杨轶男通过研究发现,漕运和民间运输的兴盛带动了山东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推动了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和人口的流动及消费观念的更新,为沿线城镇服务业兴盛创造了巨大空间[105]。张照东对清代运河在航运、灌溉、南北物资运输、商业贸易和城镇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展开论述,并就影响运河效益发挥的诸因素进行了比较具体细致的分析[106]。廖声丰以运河榷关税收为例,考察了清朝前期运河地区的商品流通问题[107]。此外,窦萍还就大运河对茶叶等经济作物输运流通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108]。
漕运是国之命脉,沿线城镇兴衰与之休戚相关。季鹏回顾了“东南一大都会”扬州由繁荣走向沉寂的变迁过程,从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的角度探讨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指出近代城市的发展转型单靠贸易或商业是难以完成的[109]。叶美兰赞同该观点并指出,盐商消费集团的解体和水运交通优势的丧失,是近代扬州城市现代化进展缓慢的外在原因,而政府及市民阶层的保守意识是内在原因[110]。李德楠从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两个维度来分析和看待运河对沿线城镇的损益。他以开凿泇河为例,指出泇河的开通有利于漕运畅通,由此带来的城镇兴替于国家利益无损,而于地方而言,河道的变迁会直接导致一地的兴盛和另一地的衰败,进而给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带来严重影响[111]。金兵、王卫平对曾是运河重要枢纽的清江浦近代走向衰落的原因进行分析,指出近代交通线路、交通方式的变更对清江浦的打击是巨大的[112]。江太新、苏新玉则对漕运城市淮安的兴衰问题进行了考察,并在梳理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今后淮安经济社会发展的对策[113]。李俊丽从商业、语言、信仰及文学四个方面探究明清漕运对天津地区的影响[114]。郑民德也从漕运的角度对大运河沿线的聊城[115]、景州[116]、沧州[117]等城市的历史变迁进行了考察。
古之中国,以农为本,漕运的运维与沿岸农村农业发展密切相关。王元林、孟昭锋研究了元明清时期引汶济运的影响,指出汶水作为运河重要的补水源,在引汶济运工程保障运河航运的同时,却危害了汶水沿线的农业生产,加剧洪涝灾害的发生[118]。肖启荣对明清时期下河地区的农业种植与运河水利工程维护进行考察,指出淮扬地区优质的稻田是政府赋税的重要来源,为了维持政府运转,地方当局更倾向于保障稻田垦殖而不是运河水利维护。这一现象反映出地域社会对环境资源利用的微观化策略[119]。孟祥晓对明清时期卫河漕运与沿岸水稻种植之间的关系进行历史考察,指出当卫河水量充沛时,漕运与水稻种植相安无事,而当水量不足时,政府控水济漕,水稻种植受到影响[120]。李纲认为,漕运改变了枣庄地区的农业生产结构,扩大了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推动了农业生产技术提高,不过也造成农业耕地减少、农田水利破坏、农业劳力流失和农村生境恶化等问题[121]。陈冬生以棉花、烟草、果木的经营为例,对明清山东运河地区经济作物种植发展问题进行了探究[122]。胡其伟通过对明清时期沂沭泗流域及里下河地区的研究,发现该区域一直存在以保漕济运为目的的官方漕运水利体系和以维持生计为目的的地方民间防洪灌溉体系,两种体系围绕运河治理、防患水灾等问题斗争尖锐、矛盾重重,其实质是在有限资源面前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之间难以达到有效协调和平衡[123]。
运河沿线的生态环境问题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李德楠在《明清黄运地区的河工建设与生态环境变迁研究》一书中通过对河道开挖、堤防修筑、闸坝创建、物料采办等河工建设活动的分析,揭示运河对沿线河流、湖泊、土壤、植被、河口、海岸等带来的环境影响。他和胡克诚还对南四湖“沉粮地”的形成过程与历史称谓的演变进行研究,指出“沉粮地”是黄运地区水环境变迁以及国家漕运政策、河工建设等一系列因素影响下适应生态保护而发生的土地利用方式转变[124]。王元林、朱永亮对卫运河流域的盐碱地问题进行研究,指出元代卫运河的开通导致该区域的盐碱地由唐宋御河以西扩展到卫运河以东,而盐碱地的扩张引发棉花豆类等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并导致草编业和畜牧业的兴盛[125]。殷振兴则以明清两代水利工程设施修建最多的清口为例,详述为实现治黄、导淮、济运、通漕、减灾等目的而先后对清口水利枢纽实施了挖河导流、建坝束水、修闸控水等方面的治理工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南北航运的畅通,但也对沿线生态环境造成危害[126]。
四、大运河漕运与区域社会研究
漕运制度的运行,对沿线区域社会也产生了诸多变化。王云《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的历史趋势及特点》将明清500多年间山东运河区域的兴衰轨迹和社会变迁置于整个历史社会环境中进行考察,分析漕运对鲁西地理环境、交通条件、商品经济、城镇法及社会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从上层精英文化与下层平民文化两个维度对山东运河区域文化变迁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指出该区域在社会变革中经历了从荒僻到繁荣复归沉寂的类马鞍型过程,其动力源于交通环境与漕运政策的变迁[127]。孙竞昊将视角投向地方社会结构,认为明清时期的社会经济环境滋养了以地方利益为取向的济宁士绅社会,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在文化、社会政治和商业舞台上展示自己,获取在地方中的支配或霸权”[128]。吴欣则以山东苫山三个宗族的势力变迁为例,认为山东运河区域聚落的形成,与京杭运河、外来移民以及宗族自身组织化、制度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地域族群的构成及空间环境的变化以及与之相关文化、水利、商业等因素一并决定了村落宗族凝聚纽带的变迁和村落社会关系的构成[129]。漕运的繁荣为地方宗族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吴欣以聊城地区为例探讨了运河区域宗族社会组织发展的内在逻辑,揭示宗族组织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130]。其他学者关于运河区域社会的考察同样值得关注。凌滟对宋礼、白英的立祀及其后裔的宗族建构问题进行研究,认为宋、白后人通过编造文献、辅以河职等方式,以“社”的名义联结宗族形成地方宗族势力[131]。戴鞍钢通过研究发现,自黄河改道、太平天国运动导致运河停航后,大批以漕运为生的下层民众缺乏谋生途径而引发社会矛盾加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晚清社会转型面临的困境和难题[132]。李俊丽将研究视角转向天津,着重阐述了漕运对天津地区商业、文化、人口、民生等方面的影响[133]。
运河对沿线的文化影响深远。李泉、王云开展了山东运河流域文化研究,考察了齐鲁文化的发展和变迁历史,从山东运河的变迁、运河漕运与漕运文化、运河城镇及文化特色、商人商帮与商业文化、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等多个维度,梳理和探究山东运河文化的特点和内涵[134]。运河文化的传播刺激了沿线坊刻图书业的发展,张弘、韩帅对明清时期运河区域坊刻图书业的经营活动作了考察,内容涉及刻印图书选择、坊刻内部运营管理、图书营销网络构建等方面[135]。杨轶男对清代聊城兴盛的坊刻业进行研究,认为其兴盛原因,一方面与运河贯通带来的城市交通优势和经济繁荣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运河文化交流尤其是市民文化的崛起有着密切关系。可以说两者的交融助推了坊刻业与市民文化的整合与重塑[136]。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藏书成为一种时尚。韩梅花采用数量统计方法计算出清代有81.3%的私家藏书楼聚集在京杭大运河沿岸。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原因在于运河沿线商品经济的发达、藏书风尚的历史传承及清初文化政策的贯彻实施[137]。
运河道阻且险,为保障运道安澜和社会稳定,政府与民间社会不仅不排斥对神灵的信奉崇拜,反而采取鼓励支持的态度。陈高华指出,元代天妃崇拜与漕粮海运密不可分。为了保障漕船、漕粮及海员安全,官方极力将民间信仰通过敕封天妃的形式使之由人变神以佑漕运[138],李倩[139]、黄太勇[140]也对元代天妃崇拜问题进行过探讨。胡梦飞对明清时期的运河区域水神信仰兴起与传播的自然和社会因素进行了研究[141],同时对京杭运河沿线区域水神信仰种类和构成、
庙宇分布和管理、信仰人群和祭祀活动、信仰传承和演变等内容作了介绍[142]。吴欣对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地区的官方与民间共同构建下形成的“正祀”与“杂祀”的水神问题进行分析,指出保漕济运的政治目标与神道设教的文化控制是正祀河神大量存在的原因,而运河区域固有的经济结构、文化传统与运河畅通之间的矛盾,又造成这一区域水神的差异性和多样性[143]。杨渝东以苏北皂河镇安澜龙王庙为例,分析了运河沿线庙宇皇家化与地方化的演化策略与文化逻辑,认为皇权与民间力量在治水问题上存在多元互动关系[144]。郑民德研究发现,山东地区的运河由于对水源需求迫切,所以对“水神”真武大帝推崇备至,各地建有大量庙宇进行祀奉,维系信仰的长久与延续性[145]。杨志娟对伊斯兰教的传播路线进行考证,指出运河贯通带来的商业利益引发聚居江南和西北的回商迁移至运河沿线,成为运河商业的重要经营者。他们在定居后大量修建清真寺,推动了运河回回商圈和伊斯兰文化中国化的形成[146]。赵树好考察了运河沿线基督教的传播路径与影响,指出来自西方的基督教与东方固有宗教信仰在运河流域曾展开激烈交锋,尤其是教会组织发展教徒、兴办学校、医院及各类慈善事业等行为,使很多沿线群众放弃传统习俗改为信奉基督教,并由此部分地引致了运河流域的习俗变迁[147]。刘飞则对近代以来西方教会在运河沿线城市设立的教会医院进行了时空分布考察[148]。曹金娜对民间宗教组织罗教在漕运水手中的传播与水手行帮组织变迁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149]。吴琦认为,清代对罗教的打压是导致漕运水手的组织活动由公开转向秘密、由具有宗教性质的罗教演化为具有民间秘密组织性质漕运行帮会社的重要原因,而这一组织伴随漕运的衰废而转变为早期青帮[150]。孔祥涛[151]、郑孝芬[152]等人也对此有所研究和涉猎。
五、大运河漕运史料整理与运河学研究
史料即史学。大运河漕运研究,离不开各类历史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中国古代关于漕运的专门著作达百余种,其内容涉及运河开挖挑浚、漕运管理维护、运河水利治理、沿线经济发展和区域生态环境等方面,这些文献大都扃藏于书库而未被发掘。由此,中国水利史典编委会组织编撰了《中国水利史典·运河卷》,收录了明清时期的重要运河史料,包括《漕运图志》《通惠河志》《北河纪》《北河续纪》《山东运河备览》和《南河志》等运河文献,成为大运河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王云、李泉对散藏于各地图书馆中与运河史相关的著作进行研读,遴选100种学术价值高的运河古籍分成“治黄保运”“运河工程”“运河水利”“漕运关志”四个大类,形成《中国运河文献书目提要》。在此基础上,他们披荆斩棘,历时多年整理辑录涵盖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四库存目等四库系列中所有的运河文献及民国以来的珍贵图书130余种,编纂出版《中国大运河历史文献集成》81册,内含7 000余万字5 000余幅图片,是我国历史上首次对大运河史料文献的集中大规模整理。此外,一些专家学者也对地方运河史料文献进行整理。如陈述编撰的《杭州运河文献》分上下册收录了10多篇与杭州运河相关的历史资料,孙忠焕、王国平组织编著的《杭州运河(河道)文献集成》,共收录整理了1949年以前,与大运河杭州段相关的38种文献资料,其中不少为藏之深阁的珍本、残本,较为全面地展现了大运河对杭州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近年来,搜集整理和研究与运河相关的水利舆图成为漕运史料研究的重要补充。姜莉莉等人对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水利地图进行梳理,考察其主要特征及在地理学、地图学、水利学方面的价值[153]。李孝聪对收藏于国外重要图书馆的黄河、运河河工图进行研究,认为这些水利舆图不仅描述历代治河的空间形态与管理制度,而且还提供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自然人文地理信息,是研究中国古代运河的重要实物资料[154]。刘凡营等人对济宁境内档案珍藏的明代《河防一览图》《河湖图石刻碑》和清代《九省运河泉源水利情形图》《九省运河泉源水利全图》《八省运河泉源水利情形总图》《皇朝中外一统舆图》等舆图进行整理,辑成《明清朝代档案珍藏运河彩绘图说》,是大运河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席会东对高斌《南河图说》进行了考证,认为《南河图说》反映了乾隆首次南巡的模式、路线,为了解河务水情以及乾隆朝河政运作、治河政绩和治河政见及相关研究提供了实物佐证[155]。王耀则对国内外关于清代京杭运河全图进行分析,并根据用途和内容的不同将其分为运河河工图、漕运图、运河泉源图和运河景观图四类,以此观察运河及沿线历史文化景观的变迁[156]。
随着大运河漕运史研究的方兴未艾,著名古建专家罗哲文先生提出建立并发展“运河学”的倡议,由此引领众多学者进行探索。张强认为,“运河学”是一门以运河为基本研究对象的学问,通过研究运河与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城市等之间的关系,可以充分认识运河在历史进程中的价值以及它对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157]。吴欣将运河学定义为归纳、理解、抽象与运河相关的人类活动及其产生经验后形成的知识体系,是围绕运河形成的一整套研究、保护、利用的理论与方法,将运河学研究内容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关于运河开挖疏浚引发的环境变化、漕运制度的历史变迁、运河区域人文情态的沿承与渐变[158]。李泉支持这一观点,认为运河学是以运河及其区域社会为研究对象,以史学为基础,融地理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理论和方法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门类[159]。姜师立从运河学提出的背景意义出发,探讨运河学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和内涵特点,将运河学分为理论运河学、应用运河学和运河史学,并对运河学学科建设、完善学术体系及今后发展方向等问题进行了探讨[160]。李玉岩、潘天波则从概念史的角度对大运河的概念演进进行了研究[161]。作为运河学的积极推动者,李泉先后组织编著出版《运河学研究》《运河研究年度文选》《中国大运河发展报告》等丛书,致力于从运河学理论、运河历史文化、史料解读等方面不断推动“运河学”研究向纵深发展。
六、结语
综上所述,自2000年以来大运河漕运史研究取得骄人成就。通论类研究硕果累累,专题性研究不断深化;研究时间跨度大,但以明清时期为重,近现代运河问题研究进入史学家的视野;研究领域逐步扩大,延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历史、城镇、社会习俗等方面,摆脱了早期“就漕运研究漕运”的窠臼;在研究过程中引入诸多学科理论,同时辅以丰富多元的研究方法,从而使得研究更加深入。当然,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在大运河漕运史研究方面还存在一些需要持续关注和不断深化的地方。
一是文献资料整理有待加强。史料是大运河漕运史研究的基础,只有全面系统地占有各类历史文献资料,才能更加深化对相关史料的解读与对史实的重构,科学客观辩证地开展研究,即“不能夸大历史或任意想象历史。应当实事求是研究大运河历史”[162]。虽然近年来学界先后整理出版了大批运河历史资料,但依然还有很多运河史料舆图散存于各类正史、档案、文集、方志之中,它们对于丰富大运河历史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有必要对现存文献开展拉网式的细致搜集梳理并出版发行,由此更好地推动大运河漕运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二是研究呈现冷热不均状态。虽然近年来大运河漕运史的研究受到普遍关注,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在研究范围、研究地域、团队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发展不均衡的情况。如在研究范围上,对运河沿线交通、水利、生态的研究关注不够,跨学科多角度开展史学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在研究地域上,对山东、江苏等运河大省及沿线城市的大运河漕运史研究较为深入,而其他省市的研究不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存在不少欠缺;在研究团队上,以聊城大学、扬州大学等院校为代表的大运河漕运史研究高地正在形成,而大运河沿线其他高校的科研团队建设还处于零散状态,尚未形成合力。
三是大运河文化研究尚需深化升华。大运河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与河的长期交互融合过程中,孕育并滋养了京津、燕赵、齐鲁、中原、淮扬、吴越文化。大运河文化既有显性的、有形的,如各类文物古迹、水工遗存,又有众多隐性的、无形的却已融入到沿线民众基因里表现在日常中的,如商业、宗教、民俗、艺术、饮食等文化传统。当前,学界对大运河文化的研究还处于比较粗放的状态,大都停留在对文化现象和文化符号的解读上,缺乏从更高站位上思考大运河文化对沿线区域及整个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影响。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古为今用,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163]重要指示上,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大运河文化研究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让研究成果更好地赋能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进而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