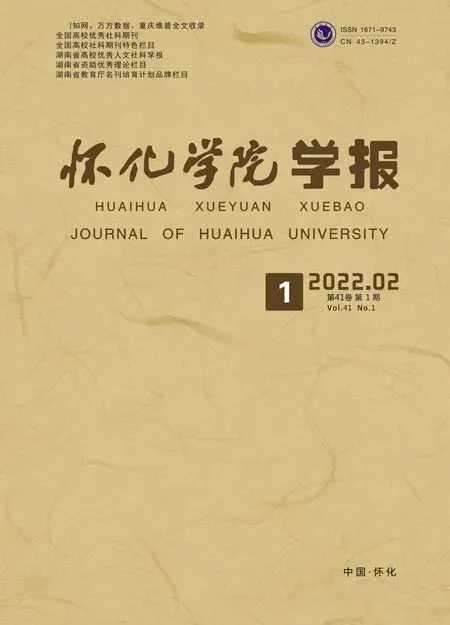基于苗族史诗《亚鲁王》多元文化特征的文化整合研究
刘康凯, 赵 东
(1.巢湖学院文教学院,安徽 合肥 238000; 2.贵州财经大学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2)
史诗研究专家朝戈金将苗族史诗《亚鲁王》描述为“复合型史诗”。他指出:“《亚鲁王》的面世,为我们思考‘复合型史诗’(跨亚文类) 提供了一个鲜活的当代案例。”[1]复合型史诗囊括了北方史诗和南方史诗的诸多文化特征,甚至还会带有一些西方史诗的文化特征,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宽广的文化外延给亚鲁王文化研究带来一定的难度。史诗《亚鲁王》的文化研究需要从多角度入手,除了史诗研究常用的母题研究、比较神话学研究之外,还需运用西方人类学的文化研究观念和民族志书写的方式对史诗中的文化现象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
鉴于史诗《亚鲁王》文化的复杂性,对于史诗文化的研究可以采取“分”与“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分”的基础上突出“合”的研究。首先是立足于“分”的研究,最终归结于“合”的研究。所谓“分”的研究是针对具体的文化现象分别进行个案分析式的点上的研究,对史诗《亚鲁王》中重要的文化现象进行重点挖掘和分析,从而得出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观点或依据;所谓“合”的研究是指站在跨文化比较的角度进行面上的研究,即文化整合研究,通过搜集整理相关文献资料和进行跨文化比较,对史诗中的主要文化现象进行归纳总结。目前学术界关于亚鲁王文化的研究成果,点上的成果居多,面上的成果相对不足,缺乏对亚鲁王文化更为深入的整合式研究。
文化整合研究在西方人类学理论中并不少见,特别是涉及跨文化比较领域的人类学理论中,带有鲜明的文化整合色彩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较为成熟。文化人类学发展史上出现过一些著名的文化整合理论,具有代表性的有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理论”,法国神话学家列维- 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神话学”,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原型理论”和苏联民间文学专家普罗普的“母题理论”,等等。这些文化整合研究理论为史诗《亚鲁王》的文化整合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参考。面对苗族史诗《亚鲁王》繁复多姿的文化现象,还要充分发挥民族志书写的长处,对史诗进行多视角的文化呈现和表达。
一、史诗的稻作文化模式
本尼迪克特将人类文化看成一个整体的“文化模式”理论是典型的文化整合理论。她认为如果把全世界的文化比作一个圆弧的话,每一种类型的文化出于自身的选择或者历史的发展,终将成为这个圆弧上的一段[2]。这个文化之弧规定了某一种文化类型的性质,每一种文化类型都是对于世界某种文化资源的一种选择,不加选择的文化类型是无法独立存在的,也无法传承。本尼迪克特从行为主义心理学出发,长期观察不同文化的类型,她发现文化具有地域性的特色,这种文化特性是由于不同类型的文化对人类共有文化资源的不同选择和占有而造成的。
亚鲁王文化带有鲜明的中国南方文化的印记,西部苗族以稻作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历经千年传承而得以保留至今,在社会功能上和民间信仰层面均有所表达。史诗中不断描绘了远古时期农业生产的图景,鱼虾成群,河汊密布,稻米飘香,是典型的长江中下游稻作文化现象。稻作文化还孕育出发达的商业意识,史诗中描写亚鲁王支系善于利用山地文化资源,开发矿产,兴建集市贸易,稻作文化还积累了丰富的战争文化传统,早期的稻作文化区经济繁荣,带来军事实力的强大,这些都是亚鲁王文化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传承下来的文化特色。经过笔者的实地调研,亚鲁王文化的核心地带,贵州省麻山一带的苗寨至今仍然保留着稻作文化区的饮食文化,比如在丧葬仪式上,要不断用米饭供给亡人,让亡魂在“返家”途中保持体力。贵州省麻山一带水资源稀缺,湖泊河流稀少,当地苗人十分珍视鱼类资源,就算是在很小的河沟中抓到的小鱼,也要精心制作成鱼干,以备他日丧葬仪式之用。
亚鲁王文化的复杂性在于,尽管史诗《亚鲁王》反映的大多是南方文化传统,却也夹杂了一些北方文化。史诗中对于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英雄屡经挫折不断成长的过程又带有北方英雄史诗的文化特征。亚鲁王文化中对动植物的描述极其丰富,特别是动物的神性表达带有北方游牧文化的特征,这也有力地证明了本尼迪克特所说的任何一种文化的性质都是源自对人类共有的文化资源的选择和占有。贵州省麻山一带土地贫瘠,当地最为常见的农作物是耐旱的玉米、土豆和麻类,但当地人对有限的耕地和匮乏的水资源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利用,在麻山地区竟然可以找到幸存数量很少的二十多种农作物,而且一半以上农作物是北方常见的麦子、小米和各种豆类等。这一方面说明亚鲁王文化本质上是南方文化,但同时可能在长期的迁徙过程中也不断吸收了北方文化。麻山苗族主要饲养的牲畜有猪、牛和羊,他们对各种动物均有着较为深厚的情感,当地人严禁捕杀鸟类,认为鸟类是祖先的信使,可以传递祖先的信息。亚鲁王文化中的十二生肖对十二种动物的起源和使命均有着细致的描述,这些描述大多反映出西部苗族的文化历史传统,也少量夹杂着北方游牧文化的元素。
亚鲁王文化有着超常的稳定性,既有先秦春秋战国时期的礼仪特征,又有三国和唐宋时期的制度文化特征,在这样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下,具有稳固文化结构的苗文化礼仪、制度带有强烈的制约性和传承性。用文化模式理论来研究亚鲁王文化,可以把苗文化放到数千年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文化模式理论的先进性在于,它始终保持着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将文化类型的特色视作文化多样性的表现,而不是以先进和落后或者原始和现代等标签来界定文化类型。文化模式理论的科学性在于,它坚持以行为主义心理学作为基本研究方法,强调田野调查的重要性,在社会调研的基础上对文化模式中的群体进行大量的观察和研究,针对调查中得到的现象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从而实现文化整合研究的目的。亚鲁王文化作为苗文化的重要代表,通过对亚鲁王文化进行整合研究,不仅可以对苗文化的特征和类型有整体的把握,同时还可为研究整个中华文化,乃至全球文化提供很好的借鉴。
二、史诗《亚鲁王》的神话学结构
列维-施特劳斯的神话学理论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从潜意识出发研究神话的内在结构,二是神话结构可以折射出特定文化类型的深层文化结构。列维-施特劳斯认为,科学与巫术需要同一种智力操作,与其说二者在性质上不同,不如说它们只是适用于不同种类的现象。其中一个大致对应着知觉和想象的平面;另一个则是离开知觉和想象的平面。这两条途径中的一条紧邻感性直观;另一条则远离感性直观。从列维-施特劳斯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神话和仪式对应着的是人类的感性直观,这种感性直观导致的并非只是美学意义上的文化积淀,同时还蕴含着深层次的理性认识,虽然神话和仪式在形式上与科学有很大的差异,但在反映人类文化成就上,却具有同样的价值和意义。列维-施特劳斯的神话结构理论基础是社会学的“问题意识”,即神话的深层结构是为了解决人类早期面对自然问题和社会问题时的解决方式。他的神话结构解释方法深受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同时他采取了社会统计学的方式将神话故事的各种元素进行排列组合并做出深度阐释。列维-施特劳斯坚信神话是人类理性的心灵表达而非简单的臆想,因此,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理论是按照严肃的社会学统计和语言学分类的方式来研究的。他将神话的不同元素进行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的分类排列,然后再将这些元素进行整合分析,以获取某种特定文化类型的整体性特征,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神话学研究实质上也是文化整合研究。它的科学性不仅在于采用的方法具有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特征,更为重要的是他始终坚信神话反映的是人类心灵无意识的结构,不管神话如何叙述和表达,也不管神话如何随着历史发展演变而产生变化,同一类型神话的基本结构都不会发生变化。列维-施特劳斯的后期理论中更加鲜明地反映了他对于神话的整体性思维,他认为个别神话只能放在神话整体中才能体现神话的真正意义。“所有神话共同表明了事物的总和,这种总和不是任何个别的、具体的神话所能确切表达的,这种总和应该是所有神话共同表达的一种必然的、富有诗意的真理。”[3]
亚鲁王文化是上古神话的沃土,西部苗人保留了中华民族上古先民对自然环境的神奇想象和人类社会独特的心灵结构,研究亚鲁王文化的神话现象可以从整体上把握中华民族上古神话认识世界的逻辑。以往的神话学研究曾倾向于认为神话是古代原始思维的产物,对于现代社会并没有多少社会功能和学术价值,而亚鲁王文化自远古走来,传承至今,融合了不同时代的文化特征,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和精神价值。首先是“家国一体、天下一家”的家园文化。亚鲁王的神话中流露出天下万物和全人类同宗同源的生态文化思想。史诗的“创世”部分对上古时代的宇宙观和人类的家族谱系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史诗认为,宇宙是由早期的若干位女性祖先创造,而且人类拥有共同的文化家园,不仅具有现实层面的家园,还具有理想化的终极家园。其次是对于自然界的敬畏之心。神话中对于动植物有着大量详细的描述,在史诗中所有动植物皆为祖先,因为它们同样是祖先的创造,而且它们比人类出现要早。史诗中对每一种动植物的起源和在世间的使命以及与人类的关系都有着详细的阐述,这个动植物的神话体系十分精密,动植物各司其职,与人类共同完成祖先的心愿。最后是生生不息、生死循环的生死观和世界不断复制繁衍的宇宙观。亚鲁王文化的神话结构中透露出明确的混淆生死界线、生死循环不止、世界不断复制的宇宙观。按照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神话学理论,史诗《亚鲁王》的诸多神话内在具有严谨的整体性特征,这个整体性特征恰好反映出这个文化现象的内在深层的文化意蕴。亚鲁王文化的神话学内在结构反映出上古神话中蕴含着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的生态文明思想和家国同构的人类共同体意识。
三、史诗文化原型的“模子”意识
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的核心是原型。追溯原型这个概念,可以发现古希伯来文化和古希腊文化中皆有较为明确的“模子”意识。史诗《亚鲁王》涉及的文化原型几乎涵盖了人类生活和心灵结构的各个层面,其中和荣格重点分析的文化原型一致的大致如下:诞生原型、复生原型、死亡原型、权力原型、巫术原型、英雄原型、树的原型、太阳原型、月亮原型、河流原型、火的原型、动物原型、武器原型等。然而还有很多荣格没有重点分析过的其他文化原型,比如洪水原型、女性原型、嫉妒原型、灵魂原型、家园原型等。《亚鲁王》包含的文化内容覆盖了苗族文化的各个层面,从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到历史记忆,乃至民间信仰和伦理道德。《亚鲁王》以亚鲁王的英雄事迹为主线,描述了苗人开疆拓土、征战迁徙、信仰仪式等各方面的内容。《亚鲁王》中的文化现象十分繁杂,如何透过这些错综复杂的文化现象,找出其背后的内在规律?首要的任务就是对文化现象进行整合性归纳。荣格的原型理论恰好可以帮助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对史诗中各种神话故事和传奇事件的分析,可以找到亚鲁王文化现象背后的那些原型,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亚鲁王文化,并将之与异质文化进行对比,从而从整体上研究苗族文化的发展脉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亚鲁王》的文化原型丰富而多变,如果从上古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些神话原型一再强调创造宇宙的始祖大多是女性,后期才出现了几个男性的祖神,而这些男性祖神本身就是那些母性祖神的孩子。史诗神话中的万物之间可以自由沟通,而且动植物和自然界的其他无生命的物质与人类同为家人。在亚鲁王神话体系中生命是永不停止的循环往复,生命终止的同时也是生命的开端,亡魂要回到祖先的家园成为新的祖先,同时祖先们又要创造出新的生命,历经数千年传承的文化原型里包含着中华上古时期先民的智慧和理想。在贵州省麻山一带的苗人的社会生活中,各种生活用具中大多可以体现出文化原型的思想:麻山一带的古代军事文化表现得十分明显,在丧葬仪式中保留着大量军旅生涯的文化印记;主持丧葬仪式的“东郎”身着象征古代战袍的青色长衫,手持古代将军使用的长剑,脚下还要踩着一块当地叫作“铁铧”的大铁片,象征古代战士的铁鞋。丧葬仪式上还有模仿当年作战的“征粮”环节,而且每一个寿终正寝的亡人都要被“封侯拜将”,成为亚鲁王旗下的将军,踏上漫漫征程。丧葬仪式上要不断地敲击战鼓以鼓舞亡魂作战,笔者调研中发现有些丧葬仪式上使用的鼓是当地世代相传的古代战鼓,而在亡魂发丧之时,扮演成古代战士的亲属要向四方不断射箭为亡魂开路。这些器物和仪式无不折射出亚鲁王文化的军事文化原型。
四、史诗三大母题的文化功能整合
母题概念目前在学术界的论述较多,很多专家学者针对母题概念提出自己的界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汤姆森在《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中曾提出的,“一个母题是一个故事中最小的,能够持续在传统中的成分”[4]。苏联著名民间故事专家普罗普发展了汤姆森的母题理论,在他的代表作《故事形态学》中他提出了对母题的功能性分析,并对传统民间文学母题进行功能单位的进一步划分。普罗普的母题功能性切分理论大大拓展了民间文学的研究思路,他将汤姆森的母题索引分类体系进一步进行功能切分,对民间文学的深层内涵和故事功能分类提出新的研究方法。神话学家陈建宪指出,“母题”在各门学科中都被用作一种结构单位,可见这是它的一个约定俗成的属性[5]。母题是民间文学中的一个可以构成文学框架的基本结构单元,在民间文学中具有文本生成功能和艺人讲演或传唱时候的结构文本的功能,这是在任何一种文化现象中都会存在的基本元素,因此母题分析是民间文学研究的基本手段之一。普罗普的神话母题研究的前提是任何母题都是来自生活的逻辑和规律,而且他认为母题研究是一种纯粹的形态研究,和内容没有太大关系。因此,普罗普认为从母题中可以反推出生活的逻辑。普罗普的想法在今天看起来有些简单,因为他分析的那些民间故事来自俄罗斯,结构简单,类似童话故事。
史诗《亚鲁王》几乎涵盖了苗人生产生活和精神信仰的全部,相当于苗人的百科全书。面对亚鲁王文化中盘根错节的文化母题,我们要如何从众多的母题中找出内在的结构性元素,对苗族文化进行整合性研究以发现其内在规律呢?史诗中最为突出的三大母题,创世母题、迁徙母题和战争母题可以统摄整部史诗的众多母题,从三大母题入手可以对史诗母题进行整合性研究。面对《亚鲁王》大母题和小母题融混为一体的现象,就不能像普罗普那样将母题和内容割裂开来,简单地做出直观判断。以史诗中的洪水母题为例,亚鲁王文化中的洪水母题里融合了多种文化元素。史诗中洪水的起因就涉及苗族的音乐起源,起初吒牧造的乐器都不能发声,做了很多铜鼓和其他乐器都是没有声音的,后来因为吒牧的儿媳妇波尼冈孃无意中在月经期间坐到铜鼓上并把经血流到了铜鼓上,铜鼓竟然就发出了声音,于是吒牧就把波尼冈孃杀掉,用她的血来祭奠他的乐器,从此铜鼓和其他乐器都发出了声音,于是音乐就出现了。吒牧把死后的波尼冈孃藏在谷仓之中,可是波尼冈孃之死终究还是被她的父亲雷神知道了,雷神震怒就降下暴雨毁灭人类,雷神的外甥女波尼虹蓊甩下三只银簪戳出三个龙洞,洪水流进龙洞里,于是洪水就退去了。洪水之后,萤火虫寻来火种,蝴蝶寻来谷种,老鹰找到了新的疆域,所以老鹰获得在秋天可以到人间捕捉小鸡作为食物的特权。亚鲁王文化的洪水神话除了上述故事,尚有其他版本的再造人类的神话传说流传在民间。比如尚未出版的史诗《亚鲁王》第二部的田野调查资料中就记载了洪水神话中兄妹成婚繁衍人类的传说。迄今为止,亚鲁王文化的洪水神话可能是各种洪水神话再造人类母题中最为复杂的版本之一,亚鲁王文化的丰富性和包容性从这个案例就可以窥见一斑。在亚鲁王文化的洪水神话母题复杂多变的文化现象背后,还是可以发现一些内在的规律性。亚鲁王文化起源于上古时代,经过数千年的演变形成洪水神话母题,亚鲁王洪水神话中包含着大量的上古文化信息,甚至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之前的远古文化现象,从神话学的角度来看,亚鲁王文化保留着一些大洪水时代的文化信息,可是又融合了一些后世的洪水神话元素,不难看出,亚鲁王的洪水神话具有时代的跨越性。
五、结语
目前对于亚鲁王文化的研究,从苗文化本身出发的研究成果是数量最多、水平最高的。这些以亚鲁王文化的个案分析作为切入点的文化研究成果是开展亚鲁王文化整合式研究最为重要的基础,正是这些研究成果让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苗文化的特征和亚鲁王文化的内涵,给进一步深入开展亚鲁王文化的整合式研究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针对亚鲁王文化的丰富性,从更为宽广的学术视野出发,通过民族志书写和人类学经典理论的综合运用,对史诗进行整合性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为深入而系统地理解亚鲁王文化的原貌。
亚鲁王文化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变异,“但无论如何变异,这些变异都是有限度的,不可能完全不顾及原来故事的情节结构而另编一个话题”[6]。面对具有如此丰富而又多元的史诗文化,在对亚鲁王文化现象进行田野调查之后,有效借鉴西方文化整合理论,合理地利用他山之石,打开藏在亚鲁王文化背后的文化之玉,是文化整合研究的出发点。在文化整合研究中,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既不能生搬硬套西方理论,迷失本土文化的基本特征,也不能固步自封,陷入文化保守主义的怪圈。在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对苗族史诗《亚鲁王》进行文化整合研究,也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