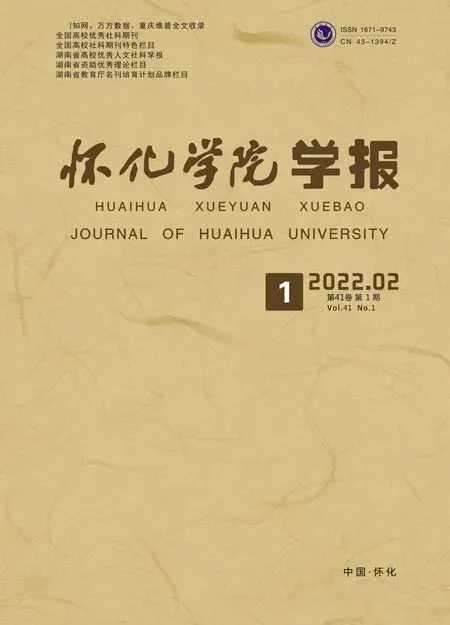清代湘西苗疆边墙民族贸易探析
侯有德
(吉首大学武陵山区发展研究院,湖南 吉首 416000)
一、引言
清代中后期以来,清廷重修苗疆边墙,并围绕苗疆边墙推行一系列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措施,通过对社区土地的法制化建设、调整民族经济、实施有限开放的民族贸易政策、调整民族婚姻政策、建设非武装化社区等具体措施来重构湘西苗疆的民族关系。由于清代对民苗之间的婚姻时禁时许,且以禁为主,故民族贸易就成为清代湘西苗疆民族交往的重要方式和有效途径。清代湘西苗疆民族贸易与苗疆边墙密切相关,带有深深的“边墙格局”的印记。
二、民族贸易政策的变迁
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参将朱绂在平息镇竿红苗之事后,以湖广总督郭琇为代表的地方官员就针对汉土民与苗民的现实生活需要,提出在苗汉居住地设立集市,并规定“每月三日,听苗民互市,限时集散”[1]。与此同时,也重申了贩卖火药军械、汉民迎娶苗妇的禁令。“清朝政府对民、苗每月三日互市异常谨慎,严格规定了交易的具体地点、日期,以及市场交易时间的长短,交易物品的种类与范围等。”[2]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湖广提督俞益谟在《戒苗条约》中对苗、汉交易问题进行了分析。文曰:
盐、布二项,尔苗急需。皆因尔性好劫杀,以致无人进来交易,即有转卖进来的,其价又贵,是以尔苗历来常受寒冷淡食之苦,殊属可怜。尔若不劫杀,则汉人进来交易者多,将尔土产,以换盐、布,岂不两得其利?尔若守法,可以到乾州五寨司买去,其价更贱[3]。
可见,清康熙年间,民苗之间的盐、布交易是比较普遍的,民苗交易并未受到限制。虽然俞益谟在《戒苗条约》中将对苗汉贸易的管制归咎于苗民“性好劫杀”有失公允,但我们可以从中窥见清廷对民苗贸易政策的调整与苗疆社会稳定与否密切相关。换言之,清廷在湘西苗疆贸易政策的调整都以稳定、治理湘西苗疆为最终目的。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时任湖广总督的郭世隆对民、苗交易提出了“以塘汛为界”的要求。清光绪《湖南通志》卷一百三《名宦志十二》载:
郭世隆,汉军镶黄旗人。康熙四十六年,总督湖广条奏防守红苗三事。谓:沿边塘汛周密,惟盛华哨至镇溪所一带,山高箐密,难于瞭望,应酌拨镇竿兵八百名,另设四营分驻,每日派官一员,带兵五十名游巡。旧日民苗来往,每滋事端,今以塘汛为界:苗除纳粮、市易,不得擅入塘汛,民亦不得擅出塘汛,违者治罪。从前汉奸与苗人结亲,致勾通为匪,不可究诘。嗣后如有,前事应断离异[4]。
从上可知,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 苗汉边界塘汛周密,盛华哨至镇溪所一带亦有驻兵把守,苗汉通婚被禁,集市贸易成为苗民与汉土民交往的主要途径。
康熙五十年(1711年),地方官员正式将民间贸易管理起来。傅敏在苗疆巡视时开始在湘西苗疆推行“国家在场”的集市贸易制度。对此,清鄂海在《抚苗录》中有详细记载。文曰:
今卑职等公同会议,得中营汛属之宜都营,前营之箭塘营,右营之西门江,左营之窑头坡,四处具系民苗出入适中之地,应于各该地方设立集场,每月定以初十、二十五二日,令苗民两次会集贸易,即着该管百户与该汛弁目带领兵丁监督稽查,令民苗集于辰时,散于午时。……民人售卖货物,亦止须盐米服食等项,其余硝磺军器有干禁令者一概不许货卖[5]。
由此可知,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 官方加强了对集市场址、场期、场时以及赶场人员、交易货物的管理。官方于民苗交界之地设立集场,规定赶场日期为每月初十、二十五,辰时聚、午时散,由百户与汛弁领兵丁监督稽查,只允许盐、米等的交易,禁止火药、军械交易。
清雍正五年(1727年) 官方进一步限制了民族贸易的交易内容,严禁民苗之间的土地贸易和借贷活动。这一点在傅敏《奏苗疆要务五款》中有详细记录。文曰:
请自后除粜籴粮食,买卖布帛,现钱交易,毋庸禁止。民与苗卖产借债,责之郡县有司。兵与苗卖产借债,责之营协汛弁。自本年为始,许其自首,勒限赎还,犯者照律治罪,失察官弁,严加参处[6]。
奏折中规定,民、苗交易内容限于粮食、布帛,交易方式限于现钱,严禁“卖产借债”即买卖田产和民间借贷。对于之前有卖产借债行为的民苗,允许自首,从轻或免除处罚。对此后违反此条者,严惩不贷。
清雍正七年(1729年),湖广总督迈柱《条奏苗疆事宜》中对民苗贸易的管制更加细化。文曰:
湖南民人往苗地贸易,令将所置何物,行户何人,运往何处,报明地方官。给与印照,填注姓名、人数,行知塘汛验照放行,不得夹带违禁之物。如官吏、兵役藉端需索,一并查究。苗人至民地贸易,请于苗疆分界之地设立市场,月以三日为期,交易而退,不得越界出入,令各州县派佐二官监视[7]。
综上可见,清雍正年间,清廷对参与贸易的汉土民、苗民均有严格管制。要求前往苗疆边墙之外贸易的汉土民填报行程,登记货物,并办理证件。对于进入苗疆边墙以内贸易的苗民只准许在“边界”市场交易,每月三日,完成交易及时返回边墙之外,不得越界,全程派官员监察。
清乾隆年间,为有效管控民苗往来,仍允许民苗交易。清乾隆《凤凰厅志》卷二十《艺文》中有湖南巡抚蒋溥奏请准许民苗交易的记载。原文如下:
民苗宜许其交易。查从前定例苗地不许汉人来往,原以苗性愚顽犷悍,奸人一入其地,贪利鱼肉,久之积成仇衅,易至蠢动,是以立法禁止。即楚南永顺、永绥等处建城安营,不过以□弹压,并非为苗人开贸易往来之路。若如□□所奏,许其当官、交易、买产借债,恐奸民毫无顾忌,公然来往,转得借端欺占,别生事端,殊为不便。应令该抚仍照定例遵行[8]。
当然,清廷对民苗贸易的种种严格管制政策也一直延续下来。清乾隆《凤凰厅志》卷五《疆域》载:
凤凰厅民苗兼辖,既不欲使民苗私相往来,以杜其勾引之渐。必别为之所,伸之易粟易布,以通有无,则市集之在苗疆,更宜加在意矣!但开集设场,或称经纪,或号牙行,大约均非善类,藏奸聚匪,启争致衅恒出于此,选择以慎。初稽察以善后享其利勿□其弊……西门江集,城东北四十里。箭塘集,城西北三十里。凤凰集,城西南六十里。以上三集,系从前通判设立,文武衙门弹压。永宁哨集,城西南四十里。靖疆营集,城东北六十里。新寨集,城西北六十里。竿子哨集,城东北六十里。以上四集俱系乾隆十九年新设[8]。
由此可知,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凤凰厅另设永宁哨集、靖疆营集、新寨集、竿子哨集的目的是为了杜绝“民苗私相往来”,以“杜其勾引之渐”。
清乾隆年间,政府官员执行着严格的集市管理制度。为了禁止客商贩卖私货,官府加强了对进入苗地贸易客商的管控。一方面,执行严格的印票核验制度,“凡各商贩必于所在官司讨一印票,以便查验。如某处某人于某地买某货至某地发卖,止许写大地名……所在官司关市验实放行,若无□票即同私贩,贡□□官”[9];另一方面,规定客商至苗地贸易时,由“苗长赴本哨交易,不许贩商擅入巢穴与诸苗交通,违者,以军法从事”[9]。
值得注意的是,相同的贸易政策在湘西苗疆各个地方的实际执行过程中存在明显差异。凤凰厅的地方官员多“选择以慎,稽察以善,后享其利,毋槛其弊”[10],颇有消极应付之意。永绥厅“惟是地方辽阔,村落零星,苗人来城买卖,往返担延时日。必择大村寨适中之地,立集场数处以便就近交易,庶货物流通,民苗两利云”[11]。可见,治理永绥厅的地方官员出于民、苗便利考虑选址建立集场,态度更为积极。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政府“定番界”,颁布了“苗疆禁例”,明令规定“各省民人无故擅入苗地,及苗人无故擅入民地,均照例治罪。若往来贸易,必取具行户,邻右保结,报官给照,令塘汛验放,始往”[12]。按这一规定,民苗之间交易要受到三重监管,首先要“取具行户”即到商行领取备办,然后要“邻右保结”即邻里左右做担保,最后由塘汛官兵勘验核查无误后才能通行。
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 至乾隆三十年(1765年) 之间,政府官员一度提议解除对民苗贸易的种种限制。清乾隆《辰州府志》卷十二《备边考》载:
湖南民苗贸易于雍正七年禁止。凡有往土苗贸易者,务将取置货物、铺店报明地方官查明,行户邻右保结存案,给以印照,注明人数,令塘汛点验,始准入。土苗交易殊多不便,后然雍正八年议改市场,民苗定期交易,汛弁官役弹压稽查,但彼时设立市场未能普遍,且现在各村庄俱有苗人买取什物,原难禁阻,前例已属虚设,徒滋兵役,籍索无益防维。今民苗既准共互相结姻,凡苗人赴内地贸易似可听从其便,应请将限定场期、官弁监视交易之例一概停止,俾得贸迁有无,以资生计,将见苗人感皇仁益无涯涘,苗疆风俗日臻淳厚矣[13]!
由此可知,针对清雍正七年以来清廷对民苗贸易设置的重重关卡,部分地方官员提议“凡苗人赴内地贸易似可听从其便”并要求将“限定场期、官弁监视交易之例一概停止”。
乾嘉民苗起义平息后,建在苗地的集场基本被迁到了民、苗交界处。和琳《善后章程》中就要求在民、苗交界地设立集场,民苗交易仅限于集场之内定期举行,由官兵监视交易过程,且规定赶场之日,驻守碉楼、哨台的兵丁“只准一二人赶场”,“卡内亦不过酌令数人赶赴,不许多人远出,其出外者,仍需迅速赶回,不许逗留,逛久”[14]。
嘉庆元年(1796年),和琳在《善后章程》中重申了限制民苗交易内容即民苗交易限于粜籴粮食和布帛买卖,进而强调了禁止民苗买卖田产和借贷的政令[15]。在《善后六条》中,和琳指出“苗地所需盐斤,布匹等类,均籍客民负贩,就近易买,以资日用。过于禁绝,苗情转有不便”[16],故而建议“嗣后民苗买卖,应于交界处所择地设立场市,定期交易,官为弹压,不准以田亩易换物件,以杜侵占盘剥衅端,则民苗永可相安无扰矣”[16]。
嘉庆五年(1800年),傅鼐在办理苗疆均田事务时规定:“每逢场期,准令民、苗两相交易。各卡门务须查明,不准苗人混带枪械进内,民人及勇丁等与苗人买卖,须皆照时价公平交易,不得欺骗肇衅。倘有滋事者,立即严拿重究。”[15]
嘉庆十四年(1809年),傅鼐针对“生苗区”苗民私自在寨内开设集场交易的情况,重申了民苗贸易的定例。对此,清嘉庆《湖南通志》卷六十五《职官九》、道光《凤凰厅志》卷八《屯防一》、光绪《乾州厅志》中均有记载,原文如下:
现在民苗界址划分清楚,应申明旧例。汉民仍不许擅入苗地,私为婚姻,以免滋事。惟各处集场,原许民苗按期赶趁,以有易无,应令汛屯员弁亲为弹压,无许市侩侵欺,一切公平互市,交易而散[17]。
可见,清嘉庆年间,仍然严格执行着“汉民仍不许擅入苗地,私为婚姻”的禁令,民苗之间的交往仍然主要通过有限的民族贸易来实现。
三、“边墙格局”与民族贸易
明清修建边墙客观上对湘西苗疆的民族分布格局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随着围绕苗疆边墙一系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政策的推行,逐渐形成了“边墙格局”。受“边墙格局”的影响,湘西苗疆的民族贸易特色鲜明。
(一) “边墙格局”与集场分布
通过对清代湘西苗疆民族贸易政策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清廷对湘西苗疆地区民族贸易的管控愈来愈严格。这主要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一,清廷治理和开发湘西苗疆之初,苗民与汉土民之间的关系相对缓和,故一度出现准许民苗通婚、民苗自由贸易的局面。乾嘉苗民起义以来,防苗、控苗成为了地方官员治理湘西苗疆的重要目标,苗汉通婚被禁,民苗之间的贸易往来作为民族交往的主要途径自然备受地方官员关注,从而在交易时间、场地、方式、内容等方面设置层层限制,成了清代未有间断的,如“戴着镣铐的舞蹈”一般的民族交往方式。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民族关系紧张的阶段,尤以乾嘉年间苗乱为典型,清廷也未禁止民苗之间的民族贸易,而只是针对民族关系的紧张程度对民族贸易的场地、时间、内容、交易方式等相关内容进行适度调整。这主要是因为,苗汉之间的民族贸易是稳定湘西苗疆社会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是满足民苗现实生活需求的主要途径,是安抚民苗的有效手段之一。
其实,在湘西苗疆地区形成以依托边墙为特征的集场之前,民、苗之间的贸易就一直存在,只是以一种相对隐蔽的方式进行着,故未受官方管控。这些集场主要分布在边墙汛堡、哨卡附近。这一分布格局与明代始修苗疆边墙和推广卫所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明代在边疆地区推广卫所制度,驻守者们便在此安居下来。他们有着客观的生产生活需要,各类交易活动也因此在驻屯、汛堡、哨卡附近兴盛起来。这类自发兴起的“民间集场”最初的交易群体主要是驻守边墙沿线的屯兵及其家眷,此后,随着民苗交往的日益频繁与密切,社会生活需求的增多,集市的扩大和兴盛,世居于湘西苗疆的苗民、土民等群体才加入进来,成为民族贸易对象的主要群体之一。这类“民间集场”的形制“实在有些简陋,多由夯土围墙圈成,场内或搭草棚或堆乱石,用于杂陈货物,买卖人或蹲或立叫卖、交易。”[2]然而,这并不影响民苗之间的贸易往来,亦不影响民苗之间民族贸易在稳定苗疆社会以及促进经济发展与民族文化交流中发挥积极作用。
从布局和设置来看,湘西苗疆地区的“民间集场”一般位于“汛堡外城之内或紧邻汛堡内城,或位于边墙外部靠近苗人地界一面”[2],旁边多有瞭望台、护城壕等防御设施。这主要是基于防范民、苗勾结“构乱”以及苗人趁赶场之机闯入城中劫掠的目的。集场位于汛堡外城之内或邻近汛堡内城,有利于场内“构乱”之时屯防兵勇很快介入管控。集场设于边墙外部靠近苗人地界一侧主要是为了方便苗民的交易,当然也不妨碍汉土民的积极参与,一些驻防的哨兵屯勇往往会定期赶集,故才有了如前文所述清代“卡内亦不过酌令数人赶赴”以及赶场屯兵“仍需迅速赶回,不许逗留,逛久”[14]的规定。
清嘉庆二年(1797年),乾嘉苗乱平息之后,政府在民苗交界地广设集场。明代以来,湘西苗疆地区的“民间集场”业已形成沿墙布局的地理分布特征,清代湘西苗疆“官方集场”的地理分布基本上延续了这一特征。其原因有二:第一,也是主要原因,清廷在明边墙旧址上重修了苗疆边墙,并围绕边墙推行了一系列治理政策,最终形成了“边墙格局”,民族贸易亦呈现出以边墙为中心的特征;第二,清廷开发和治理湘西苗疆之时,这些沿着边墙汛堡、哨卡分布的“民间集场”依然悄然进行着,且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焕发着生机和活力,逐渐引起了官方的重视,被纳入官方层面,成为清廷开发和治理湘西苗疆的重要手段之一。
(二) “边墙格局”与民族贸易之禁
在“边墙格局”的影响下,清代民苗之间以集场交易为核心的民族贸易在重重限制下持续进行着。为了维护湘西苗疆社会的稳定,防止民苗的贸易纠纷,治理湘西苗疆的地方官员不仅严格限定了集场交易的地点和场期,而且对交易过程和交易物品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形成了一些“贸易之禁”。
第一,禁止“奸民”“凶苗”欺行霸市,保障贸易公平。嘉庆十年(1805年),湖南巡抚阿林保就在《苗疆经久章程》中提出,在集场附近要派官兵对参与交易的民、苗进行督查,“惟各处集场,原许民、苗按期赶趁,以有易无。应令汛屯员弁亲为弹压,无许市侩侵欺。一切公平互市,交易而散”[18]。
第二,严禁田产买卖及民间借贷,严禁贩卖火药、军械。如前文所述,民苗之间的贸易以盐为贵,以粮食为大宗,兼有布匹、牛、马、南杂、桐茶油等生产生活用品。民、苗之间严禁田产买卖及民间借贷,严禁火药、军械买卖。清雍正五年(1727年),傅敏在《奏苗疆要务五款》中已言明禁止民苗之间“卖产借债”,即禁止民苗之间的土地买卖和民间借贷行为。清嘉庆元年(1796年),和琳在苗疆《善后章程》 中又重申了相关禁令。清嘉庆五年(1800年),傅鼐在经理苗疆屯田事务时就明令禁止民苗之间的枪械买卖,言明“每逢场期,准令民、苗两相交易。各卡门务须查明,不准苗人混带枪械进内,民人及勇丁等与苗人买卖,须皆照时价公平交易,不得欺骗肇衅。倘有滋事者,立即严拿重究”[15]。
(三) 边墙与集场:张力的展现
在以集场交易为中心的民族贸易中,边墙与集场之间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边墙-集场结构”。“边墙- 集场结构”展示了清代民族界隔与民族交往之间的内在张力,展现了国家在治理地方社会时刚性政策与柔性政策之间的内在张力。
在“边墙-集场结构”中,集场成了湘西苗疆苗民与汉土民交易、交往、交流的合法途径和重要平台;边墙的军事防御与界隔民苗的功能淡化,其作为国家与地方紧张关系的象征符号意义也日趋弱化,并被赋予了新的功能,成为民苗交易交往交流的依托。由此可见,对湘西苗疆边墙的定义不应只局限在其军事防御、界分民苗的显性功能之上,还应把握其在保障边墙内外不同群体交往交流中的平台作用,把握“边墙-集场结构”所反映出的民族界隔与民族交往之间的内在张力。
湘西苗疆边墙是明清政府为了防“苗乱”、界隔苗民而采取的军事防御措施,体现了国家在深入治理地方社会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刚性。集场的设置和管理则以在维护地方稳定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满足边墙沿线汉土民与苗民现实的生产生活需要为目标,通过对清代湘西苗疆民族贸易政策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清廷在集场设置和管理上的灵活多变,亦可窥见国家在深入治理地方社会的过程中所具有的柔性。集场依托边墙而起,依托边墙而兴,形成了粘连紧密的“边墙-集场结构”。随着集场经济的繁荣,围绕边墙而兴的民族贸易逐渐兴盛,苗疆边墙逐渐成为了民族交流的平台,具有了新的功能和意义。因此,“边墙-集场结构”展现了国家治理湘西苗疆刚性政策与柔性政策之间的内在张力。
四、结语
清代重修苗疆边墙之后,民族贸易成了苗族与汉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主要方式和有效途径。随着对湘西苗疆管控的日益增强,清廷对苗汉之间的民族贸易的管制也越来越严格,具体到集场选址、集市时间、交易内容、交易方式等,事无巨细都有规定,且要求官弁对交易过程进行严格监督。为了方便民苗贸易,清代湘西苗疆集场多设在苗疆边墙碉堡、哨卡以及边墙沿线村庄。因此,清代湘西苗疆民族贸易呈现出紧密围绕苗疆边墙的特征,带有深深的“边墙格局”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