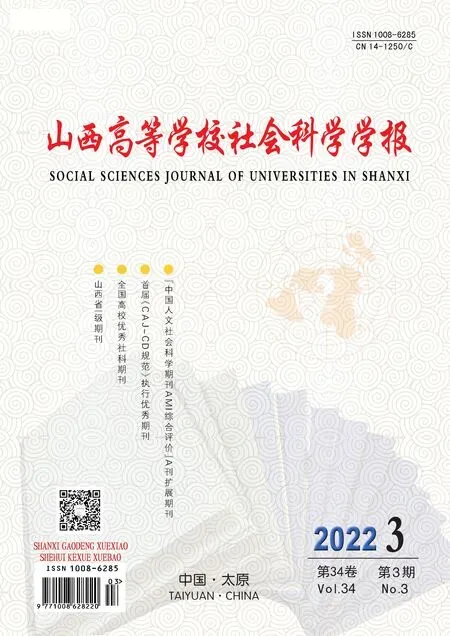五国外长会议与战后欧洲和平的构建
袁明杰
(山西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二战末期,如何妥善处置战败国,尽快恢复和平秩序成为欧洲面临的首要现实问题。对此,美、苏、英等大国选择设立五国外长会议(Council of Foreign Ministers)(1)国内学界对Council of Foreign Ministers的翻译不尽相同,如“外长会议”“外长委员会会议”“外交部长理事会”等,分别见于王绳祖编《国际关系史》(第七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徐之凯硕士学位论文《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始末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2年;杨军等编《美国社会历史百科全书》,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本文沿用学界惯常译文“外长会议”,因会议成员为五大国外交部长,故称“五国外长会议”。,谋求以国际合作的方式起草对战败国和约。关于处置战败国的问题,尤其是对冷战起源、盟国对战败国政策等史学问题的研究,学界成果颇丰(2)沈志华、余伟民:《斯大林是怎样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战后苏美从合作走向对抗的路径和原因》,《俄罗斯研究》2019年第1期;李娇娇:《二战后美苏对德国管制上的分歧及其影响》,《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增刊;郭尚鑫:《论美国对战后德国的处置》,《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方连庆等编《国际关系史》(战后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John C.Campbell.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Affairs,1945—1947.New York:Harper &Brothers,1947.,主要关注了美苏等大国的安全观、国家利益、全球战略以及国家元首意志等因素,对多边国际合作机制扮演的角色与主要盟国外交部长的谈判表现关注较少。而学界关于将国际关系史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运用相结合的呼声都有着共同的指向:根据具体问题选择相适应的理论有益于历史研究的叙事与解释功能(3)卢凌宇、沙子舒:《国际关系学与外交史研究的借鉴与融合——从约翰·加迪斯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谈起》,《国际政治研究》2021年第5期;白建才、梁志:《中国冷战史研究70年及其思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王立新:《跨学科方法与冷战史研究》,《史学集刊》2010年第1期。。事实上,外长会议能否就某一具体问题达成协议,不仅从外部受到东西方大国关系的影响,也受制于其作为国际合作机制而天然具备的诸多内部因素。
美国政治学家海伦·米尔纳对国际关系学界主要学者的合作论研究进行理论性分析和总结后,提出的“国家间合作理论”揭示了影响国际合作的诸多因素[1]。对此,笔者联系五国外长会议的具体实践,择其四点作简要介绍。其一,行为者追求绝对收益时有利于国家间合作的形成,合作者的互惠性政策(reciprocity)有助于合作的实现,行为者追求相对收益时将给合作带来消极影响(4)合作论中的绝对收益指的是国际关系行为者参加合作相较不参加合作而言,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或减少更多的损失,是各国参与国际合作的直接动力;相对收益指的是在合作中某一合作者相较其他合作者而言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或减少更多的损失,如果合作者们开始追求相对收益时,也会担心对方获益大于自身从而带来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实现合作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其二,合作者数量的增加会带来更多分歧,实现合作的可能性将会降低。其三,国内政治的一致性对国际合作会产生影响,在合作中,行为者追求的国家利益是其国内政治争论的结果,政治精英会干预或推翻(reverse)先前的国家行为。其四,合作者之间认知一致性之影响,要实现合作,行为者应在问题的解决办法、价值取向上取得一致的认知。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尝试将处置欧洲战败国的问题置于国际合作的场景中,借助“国家间合作理论”重新梳理五国外长会议的设立与实践历程,探讨其在构建欧洲和平过程中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不足。
一、贝尔纳斯方案与五国外长会议的设立
欧洲停战后,美苏英三大国在欧洲问题上追求的绝对收益存在着显著的差别。简要来讲,杜鲁门希望欧洲国家(包括东欧国家)尽可能快地进行美国认可的“民主选举”、组建“民主政府”,以便让欧洲恢复秩序。苏联要求大规模的德国赔偿,并且希望美英两国能够承认东欧一带的亲苏政权,在此基础上,斯大林认为最好可以实现一些有利于苏联的领土变更。英国面临着经济的崩溃,在处置战败国问题上势必不遗余力地为自己争取利益。不过,英国在三强中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需要来自美国的经济援助以及来自苏占区的粮食供应[2]。相较而言,美苏两国的“欧洲方案”更为全面,其矛盾也必然更为对立。事后看,此时的三强均认为通过谈判获取收益的时机已经成熟,波茨坦会议为大国间的利益分歧寻找到了具体的政治解决方案。
1945年7月17日,波茨坦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杜鲁门利用主持会议之便率先提议,其首个提案就是设立由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中国外长组成的会议。他根据外交经验作出判断,认为和谈之前应事先制定“一些步骤和机构”,否则“混乱局势、政治和经济上的不景气将继续严重地危害欧洲和全世界”[3]296。会议开幕之前其他官员曾建议杜鲁门应将更为重要的德国问题作为美方的第一项提案[4]296,但是并未被他采纳。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杜鲁门通过设立合作机制解决战后欧洲问题的决心。
需要指出,国内学界一般将五国外长会议的缘起追溯到杜鲁门的提议。事实上,设立外长会议的最初构想源自美国国务卿詹姆斯·F·贝尔纳斯。任国会议员时期,贝尔纳斯就对解决两次大战后的国际和平会议产生了独到的见解,他总结凡尔赛会议经验教训的同时又借鉴了联合国组织的建立程序。直接进行和平谈判意味着届时全体交战国将带来规模庞大的代表团和各种争议性问题,贝尔纳斯担忧各国互相角逐将导致会议陷入混乱。反观建立联合国的筹备工作,它是由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和雅尔塔会议先行完成,减少了在重要问题上的分歧,这为贝尔纳斯提供了灵感来源。此外,他还注意到由大国主导的和平会议,弱小国家甚至会和战败国一样没有什么机会来“审查和修改”条约[5]70。基于上述考虑,贝尔纳斯认为要想妥善安排欧洲和平秩序,就必须设计一种既可促成大国合作,又能让小国充分表达观点的机制。贝尔纳斯的具体方案就是设立一个成员由五大国组成、负责准备和约草案的外交部长会议,并向杜鲁门提交。关于会议的任务,他认为应首先起草对意大利、巴尔干国家的和约,原因是“争议最小”,对德和约应置于最后[5]70-71。
贝尔纳斯方案一定程度上符合杜鲁门政府的欧洲政策,因此得到了决策层的认可与接受。波茨坦会议召开之前,东欧一带业已成为苏联的实际控制区域,对此,杜鲁门宣称东欧“不应是任何一个大国的势力范围”[6]36,意图在欧洲建立美国的领导地位。由于直接进行和平谈判就会扩大会议基础,美国决策者们担心苏联会主张波兰和南斯拉夫等亲苏国家参与其中[4]284。为了在安排欧洲秩序的多边合作中孤立苏联,杜鲁门批准了贝尔纳斯方案。参谋长联席会议也支持设立外长会议以应对苏联——“各国政府拖延(delay)解决紧迫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各国政府,尤其是苏联政府,不愿将权力委托给他们的代表”[4]289。
杜鲁门的提案在成员构成上遭到了苏联和英国的反对。斯大林一方面想以法律形式稳固苏联在欧洲通过战争取得的诸多政治、军事成果,故在原则上同意由盟国外交部长起草对战败国和约。另一方面,他认为中国没有权力介入欧洲事务,对中国参与解决欧洲问题心存疑虑。丘吉尔对中国的资格也表示质疑——“中国对击败欧洲敌人没有任何贡献”。他甚至反问杜鲁门:“没有中国就不可以决定德国的未来吗?”[7]53-59据此,丘吉尔提出外长会议成员应是四个国家(不包括中国)。斯大林则更进一步,要求将外长会议成员限制为三国(不包括中法)。此时的斯大林已经警惕地意识到五国外长会议将会让美国形成对苏联的多数优势。在丘吉尔的建议下外长会议的草案交由三国外长审议。之后,美苏英三国外长围绕成员资格进行讨论时仍大致遵循本国首脑先前的主张。尤其是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以中法两国没有在停战书上签字为由,继续反对将中法囊括进外长会议[7],竭力防止苏联成为被孤立的对象。
为挽救外长会议方案,三方采取互惠性政策,调整先前的立场以适应其他合作者的需求。根据在前敌国投降书上签字的原则,法国被视为有权参与对意和约的准备,中国在对任何欧洲战败国和约的讨论中均无表决权,该协议写入了波茨坦会议产生的《柏林会议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此外,《议定书》还有两项重要规定:一是外长会议“当前之重要任务”为准备对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及芬兰五国和约,其后准备对德和约,由“合乎此项目的之德国政府成立时”接受;二是讨论相关国家的问题时,“此一国家应被邀派遣代表参加”[8]。贝尔纳斯方案的核心主张基本得到了实现。大国在措辞上对五国外长会议成员权力进行限定,实际是为多边合作的展开找到了一种折中方案。
波茨坦会议闭幕后,法国和中国很快接受了《议定书》的邀请,外长会议随即展开对欧洲战败国和约的准备工作。作为肩负安排欧洲秩序、建立欧洲和平使命的多边合作机制,五国外长会议是战胜国根据决策层意志和国家利益的需求,在分析大国力量对比变化的基础上设立的。在全新的多边合作中,外长们既要构建战后欧洲和平,又想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美国对苏联的孤立也势必引起苏联的反制,苏联对中国和法国的排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可以说外长会议在设立之初就同时具有了合作与对抗的因素,当合作者在日后的核心问题上追求相对利益时,会议的前景就不容乐观了。
二、五国外长会议与五国和约的缔结
法西斯仆从五国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在战时力量较弱、危害较小,较早与盟国签订了停战书。并且,外长会议在解决五国和约问题时,既可以通过折中方案匹配大国对绝对利益的追求,也能利用成员权力的非对称性促成合作,因此对五国的处置相较德国更为容易。
1945年9月11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英国外交大臣贝文、法国外长皮杜尔和中国国民政府外长王世杰出席伦敦外长会议,正式讨论五国和约问题。对外长们来说,诸多意见均为首次在外长会议上正式交换,自然分歧也较多。
会议首日,外长们尚未讨论和约条款就在成员权限问题上再生龃龉。莫洛托夫意识到苏联有极大可能会被其他四国孤立,遂援引《议定书》相关表述,企图在重要问题的讨论中将中法排除在外。贝尔纳斯强调中法虽无表决权,但作为会议成员拥有讨论权,并以退出会议相要挟[9]88-89。莫洛托夫虽暂时作出妥协,但成员权限之争让伦敦会议充满了火药味,随后外长们在意属非洲殖民地的处置与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外交承认问题上大肆争论。
起初,各国关于殖民地的处置方案各不相同。美国认为殖民地应置于联合国托管之下,英国主张意大利放弃殖民地,法国为保证法属非洲殖民地的稳定,要求延续意大利对殖民地的统治权。当苏联提出要单独托管一处意大利的北非殖民地时,立刻遭到美英法的集体反对,王世杰也支持贝尔纳斯的立场,苏联还是不可避免地遭到孤立。经过争论和让步,会议同意对原意大利殖民地进行“某种形式”的托管。其后,贝尔纳斯在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两国的外交承认上大作文章。彼时,苏联对东欧的控制已成既定事实,贝尔纳斯表示除非罗、保重新进行自由选举,否则不会得到美国承认。这无疑激怒了莫洛托夫,他重新提出中法的资格问题来进行回击。外长们又围绕如何准确解释《议定书》文本进行辩论,结果会议没有签署任何协议。
伦敦会议的失败让美苏认识到欧洲和平的恢复需要建立在双方合作的基础之上。此后,杜鲁门决定不再举行三国首脑会晤,外长会议因此一跃成为盟国最高级别的多边机制。为使外长会议继续举行,贝尔纳斯主动作出了妥协。他通过美国驻苏大使向莫洛托夫转达召集美苏英三国外长举行非正式会晤的意愿,并希望在莫斯科举行,这就保证莫洛托夫作为东道国代表可以率先提出议程。三外长莫斯科会晤期间,美苏双方频繁地互换意见,均表现出强烈的合作意愿,贝文只能接受现实[9]102-106。
从国际合作中权力的非对称性角度出发,观察三大国在前期解决争端的方式,可以发现美苏强权决定了五国和约谈判的前景。二战结束后,欧洲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苏在欧洲东西侧翼的兴起意味着英国在解决欧洲问题时不得不看他人脸色,以维系英国在合作中的话语权。
三国外长在莫斯科明确了五国和约的起草工作按照“四三二原则”进行,由曾在相关停战协议书上签字的各国外长负责——美苏英法四国外长会议。美苏英法起草对意和约,美苏英起草对罗、保、匈和约,苏英起草对芬和约,中国被排除在外。此外,三国外长“劝告”罗、保政府适当扩大,吸收其他党派参与,其后美英两国即可给予外交承认[9]105-109。很显然,大国为通过合作解决欧洲和平问题均作出了较大的让步。盟国间的妥协为起草五国和约廓清了障碍,欧洲和平秩序的构建终于向前迈出第一步。莫斯科会议化解了外长会议破裂的危机,但也表明外长会议的主导权掌握在美苏手中。美国邀请中国参会的本意是组成对苏的政治包围圈,形成多数优势,并非真正希望中国参与欧洲和平问题的解决。美国以牺牲中国的资格为代价与苏联进行利益互换,是典型的大国强权政治。此后,由于中国的长期缺席,五国外长会议实际成为了美苏英法四国外长会议。
1946年4月25日,四国在巴黎召开第二次外长会议,主要讨论对意大利和约草案。其中,盟国在意属殖民地问题上的分歧最大。伦敦会议决定将意大利殖民地置于某种托管之下,因此具体由谁负责托管成为巴黎会议的首个争论焦点。皮杜尔为维持法属非洲殖民地的稳定,希望由意大利负责托管原意属殖民地;苏联为在南地中海建立据点,主张由苏意联合托管的黎波里塔尼亚;英国坚决否定意大利的托管权,并主张英国托管昔兰尼加;美国则坚持由联合国集体托管全部意大利殖民地[10]23。由于大国都试图从中获利,经过十几天的争论,意大利殖民地问题仍未解决。不过,盟国就意属殖民地的前途展开争论具有历史进步意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继续控制殖民地的美梦开始破灭,预示殖民主义在国际政治中已经很难拥有市场。
意南边界和对意索赔问题也是此次会议上的主要谈判内容。关于意大利与南斯拉夫边界划分,外长会议存在三种不同方案。苏联主张伊斯特里亚半岛大部划为南斯拉夫领土;美英主张应从半岛中线将其大致一分为二,但是划线偏东,对意大利更为有利;法国则建议居中划分。经过争论,外长会议决定采纳法国方案,在中线附近设置自由区[10]27。外长会议并未按照章程邀请有关国家参与讨论,大国主宰的意南边界划分遭到意、南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抗议。关于索赔问题,苏联强调意大利军队的侵略行为给苏联、南斯拉夫、希腊等国造成严重破坏,盟国应制定严格的索赔方案。苏联要求获赔1亿美元,其他国家获赔2亿美元,共计3亿美元。美英认为这一方案过于严苛,屡次拒绝苏联的要求。经过多次磋商,外长会议最终达成初步协议:苏联7年内获赔1亿美元,以意大利军事设备、海外资产和工业产品作为赔偿来源,其他国家的赔偿留予和会继续讨论[9]127。由此可见,外长会议能够按照折中的方案处理关键问题,得益于大国间的互相让步。
巴黎四国外长会议是盟国在战后成功通过多边合作协商解决争端的先例。虽然大国合作存在着诸多困难,未能一揽子解决五国和约的全部问题,但实际是“把要激化的矛盾冷却下来”,为后续欧洲问题的和平协商提供了以资借鉴的经验[11]13-14。此外,外长会议在对罗、保、匈、芬和约的领土、政治、军事和赔偿条款上基本取得了一致意见。1946年7月,巴黎和会开幕,外长会议的前期谈判工作对和会起草五国和约创造了便利条件。盟国间即便存在一系列分歧,也大致可以通过外长会议达成的共识作出修正。和会在处置原意属殖民地、边界问题、赔偿问题等争议性问题上取得实质性成果。草案经过11—12月间的纽约四国外长会议审议后,于次年初正式签订。
三、四国外长会议对德国问题的处理
对德国的处置处于战后欧洲问题核心位置,西方与苏联在该问题上都谋求利益最大化。相较五国和约,外长会议准备对德和约的工作异常艰难。借助“国家间合作理论”对会议围绕德国问题的谈判进行观照,不难发现,合作者数量、合作者对相对利益的追求、合作者国内政治的一致性以及合作者之间认知的一致性等因素可以为后期会议的失败作出恰当解释。
盟国关于处置德国的设想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早在1943年底的德黑兰会议,美苏英三巨头一致认为应通过肢解德国一劳永逸地消除其发动战争的潜力和可能。1945年初,反法西斯战争形势趋于明朗,三巨头又在雅尔塔会议上聚首。苏联红军西进促使沿线的东欧各国在政治上也倒向苏联,通过分裂政策削弱德国以拱卫苏东安全的需求于苏联而言不再迫切,保持德国的统一反而有利于实施索赔方案,也关系到苏联的战后经济重建。美英意识到东欧局势朝着于苏联有利的方向变化,由此产生的防范心理促使其开始主张维持德国的统一,认为“不如通过占领和控制的办法,把德国控制在自己手里”[12],作为在战后对抗苏联的前沿地带。1945年中,三巨头在波茨坦会晤时一改初衷,决定将德国视为完整国家,这意味着对德处置的目标转变成了缔结对德和约。
然而,美苏英法四大国分区占领德国后,均要求按照各自意愿对德进行处置,为外长会议解决德国问题设置了巨大的障碍。尤其是五国和约签订后,美国正式采取强硬的对苏政策,由此蔓延开来的冷战氛围导致西方与苏联在对德政治、经济政策上严重对立,四国外长展开了艰难的谈判。
1.会议围绕德国问题的争端暴露出合作者数量的不合理性。1946年7月,第二阶段的巴黎外长会议上,四大国首次就德国问题正式交换意见。法国并未参加波茨坦会议,并且基于法德关系中的世仇因素,皮杜尔主张肢解、削弱德国。其主要计划是在德国建立松散的联邦制,由国际共管鲁尔,法国接收萨尔。法国的方案遭到了美苏英的一致反对。美英要求将德国视为一个完整经济体,在各占领区公平地分配资源,实际是想把苏占区纳入西方体系。贝文渲染苏占区的封闭等同于分裂欧洲、危及和平,贝尔纳斯则试探性地提出对各占领区进行经济联合。对此,莫洛托夫发表“关于德国命运与对德和约问题”的声明,主张应先行建立全德中央政府,有利于德国履行非军事化、非法西斯化以及赔偿等义务,尤其强调了鲁尔工业区应置于四国共管之下,明确拒绝了法国肢解德国和美国主导德国经济统一的方案[13]861-873。法国的强硬立场表明,由于合作者数量的增加为国际合作带来新的分歧,不利于四方在对德处置上达成共识,会议也因此陷入了混乱局面。
2.美国国内政治的一致性发生了变化,总统与国务卿关于对苏外交的政策分歧对德国问题的解决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如前文所述,贝尔纳斯为促成美苏合作主动作出了让步,外长会议得以在五国和约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然而杜鲁门却对贝尔纳斯的外交工作十分不满,认为后者在欧洲问题的谈判中取代了总统的角色。对此,杜鲁门在给贝尔纳斯的亲笔信中要求对苏采取“强硬方式”,因为他“已厌倦于笼络苏联人”[3]544-552。此后,贝尔纳斯迫于压力,在外长会议上的谈判都亦步亦趋地服从着杜鲁门的意志。
贝尔纳斯在巴黎会议上尝试统一德国经济的计划失败后便不再谋求对苏妥协。1946年8月,美国在占领区宣布了美英成立双占区的计划,要求美占区的德国官员与英占区进行合作,英国随即也如法炮制。美英绕开苏联和法国成立联合经济机构,外长会议遭受了重大挫折。9月6日,贝尔纳斯在德国斯图加特发表了美国对德政策的演说。在经济上,他主张各占领区应首先采取共同的政策,将德国视作一个经济体;在政治上,他希望德国组建“民主政府”,反对他国政府干涉[5]189-190。贝尔纳斯与莫洛托夫针锋相对的政策表明双方对德国前途的设想大相径庭,在德国统一的步骤上也截然相反。双方的分歧成为后续外长会议困难局面的预演。
在1946年11—12月的纽约四国外长会议期间,美英在大国合作的立场上彻底松动。虽然贝尔纳斯在开幕词中对外长会议表达了美好的愿景,希望可以在纽约结束旷日持久的谈判,但是另一方面,美英却在12月2日绕开外长会议成立双占区,正式迈出了分裂德国的第一步。苏联对美英在谈判桌外擅自合并占领区的行为大为不满,反对苏占区被纳入西方的轨道、按照西方模式恢复德国经济。对德经济政策的分歧成为外长会议走向破裂的导火索。国内学界最新研究也认为,这一时期美苏关系从合作走向对抗正是缘于西方与苏联之间的经济问题或“经济切割”[14]。
1947年3月10日,莫斯科四国外长会议召开。因杜鲁门对贝尔纳斯长期不满,后者最终称病辞去了国务卿一职。新任国务卿马歇尔与贝文继续鼓吹合并占领区的重要性以及必要性,称其对世界未来的和平“至关重要”,以此为由再次邀请苏联参与合并[15]256-257。莫洛托夫则认为解决德国问题的首要任务是成立中央政府,坚持由四大国共管鲁尔工业区。他还对美英成立双占区的行为进行了谴责,并要求予以撤销[16]。这样一来外长会议的争论焦点就从对德经济政策变成了政治政策。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国情咨文演讲,渲染共产主义威胁,鼓吹所谓“自由世界”和“极权政体”的对抗,冷战拉开了序幕。两种制度之争也波及外长会议。
3.东西方大国认为,在德国确立与自身相符的政治制度,才能保证获得比对方更多的利益。换言之,外长会议在后期陷入了合作者都试图追求相对利益的困境。1947年3月13日,外长们就德国的政治前途展开辩论。莫洛托夫认为德国中央政府应通过“比例代表制”的方式产生,美英则希望德国实施普选制,选举产生联邦议会,两种对德政治政策引爆了外长会议的谈判桌。贝文讽刺莫洛托夫想让德国回到希特勒时代,指责苏联的选举制度无异于极权主义,而且对战后的“其他选举”(东欧亲苏政权)表示否定。在外长会议中一贯保持中立的法国也走近美英,认为德国的民主化与其经济的稳定是相互依存的,应将四个占领区各项工作统一起来[15]251。苏联在外长会议上彻底陷入孤立局面,会议偏离了预设的议事轨道,开始转变为外长们互相攻讦的场合。莫洛托夫揭露西方盟友攫取了西占区的专利、技术和黄金等,马歇尔则挑明苏占区的重要工厂或是被苏联自行拆除,或是被并入了苏联企业[15]847-848。双方通过无谓的辩论竭力将无法合作的责任推卸给对方,会议只能走向失败。这表明在冷战爆发的背景下,外长会议面对内部尖锐的矛盾缺乏行之有效的措施,任何关于对德和约的实质性讨论都无法开展。
需要指出的是,在莫斯科外长会议开幕之前,王世杰曾提请外长会议讨论德国问题应邀请相关(欧洲)国家代表出席,但是四大国一致认为缔结对德和约的工作应仅限于四强[13]944-945。尽管会议上的对立已经十分尖锐,外长们仍然不愿意扩大会议基础。外长会议的封闭背离了贝尔纳斯方案尊重小国主权的初衷。大国强权控制下的外长会议,断绝了其他打破会议僵局的可能性,是对《议定书》设立外长会议章程的公然违背。
两种水火不容的对德政治经济政策,让外长们无法在德国统一问题上形成任何共识,盟国的合作关系岌岌可危。双方已经没有多少耐心等待对方作出让步与妥协了,紧随其后的马歇尔计划进一步加深了西方与苏联的政治经济裂痕,“两个对立的政治路线业已形成”[6]55。西方的冷战政策刺激苏联开始采取消极应对的策略,外长会议沦为双方滥用否决权的工具。
4.随着冷战的爆发,外长会议内部彻底分化出两种对立尖锐的共同利益和价值取向,拟议的“对德和约”也因合作者一致性认知的缺乏成为会议直至破裂都悬而未决的问题。1947年11月25日,伦敦四国外长会议开幕,外长们并没有带来什么崭新的观点与提议。对于这场被认为是“碰运气”的会议,法国外长皮杜尔笃定已无促成四大国合作的可能,做好了与美英政策接近、与苏联关系破裂的心理准备[15]738-739。西方指责苏联所谓的德国中央政府实际是“独裁政府”和“傀儡政府”[15]792,要求苏占区参与合并。莫洛托夫则继续要求四国共管鲁尔区,对美英双占区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会议日报显示,西方提出的几乎所有建议都会遭到莫洛托夫的否决,而当莫洛托夫提议时,西方三国外长的做法也别无二致[15]704-709。因为莫洛托夫常用俄语词汇“Nyet”(不),他也因此被谐谑为“否决先生”。最终,会议在无休止的指责中陷入僵局,外长们唯一达成的共识就是立即休会,此次会议成为最后一次外长会议。
四、五国外长会议在构建欧洲和平中的得与失
起草对欧洲战败国和约是波茨坦会议精神与《议定书》赋予五国外长会议的历史使命。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外长会议用五国和约取代停战协议,从法律意义上结束了欧陆大部分地区的战争状态。缔约后,外长会议的设计者贝尔纳斯评价五国和约是“人类智慧可以使四个主要盟国达成一致的最好的(best)和约”,外长会议是“恢复欧洲和平的令人满意的途径”[10]35。具体来讲,外长会议对欧洲和平的贡献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会议通过政治手段打击了蔓延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势力,巩固了盟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的军事胜利,五个法西斯仆从国由此走上了正常化道路。第二,外长会议也为日后欧洲海外殖民地的独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以意大利失去非洲殖民地为起点,欧洲老牌殖民国家的殖民体系开始松动并最终瓦解。外长会议消除了引发欧洲国家间争夺与战争的殖民主义因素,也促进了战后世界政治民主化。第三,大国在外长会议框架下通过合作“探索出一条和平发展道路”,五国和约及其谈判过程为后世的国际合作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依据”[11]14。此后,国际社会通过设立多边合作机制解决国际问题渐成常态。
随着冷战的爆发,东西方大国转而追求相对利益,都唯恐德国问题朝着有利于对方的方向发展。外长会议在德国问题上几乎无所作为,暴露出了明显的历史局限性。苏联希望组建德国中央政府应对西方在外长会议上的孤立攻势,保障苏联取得的一系列权益[17]。而这恰好是西方所不愿看到的,它们要阻止苏联在欧洲的扩张,让苏联放弃染指西占区的打算,杜鲁门主义散发出的“危机气氛”打破了双方在德国问题上实现合作的可能[18]。伦敦会议闭幕后,美英法三国外长立即举行了非正式会晤,决定联合起来组建“西方的精神联盟”,坚信这种“强大的整合”将让苏联在欧洲无法再进一步。他们认为德国的统一将是一场排除苏联因素、由西方主导的运动,因此必须尽快合并占领区,进行货币改革[15]823-826。这表明三国在德国问题上具有区别于苏联的共同价值取向。外长会议的破裂导致对德和约长期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此后,西方国家成立西德政府、发行B记马克的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苏联也联手东欧国家,以成立东德政府、发行D记马克作为对等回应。西方与苏联坚持不同模式的对德处置与改造,使得双方最终丧失了合作基础,德国不可避免地分裂了。贝尔纳斯总结道:“它(外长会议)不能满足被设立的目的了。”[5]199在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时期,德国一直处在东西方集团对抗的最前沿,屡次爆发的冲突与危机让它成为欧洲乃至全球安全的热点地区。
综上所述,作为专门解决战后欧洲问题的多边机制,五国外长会议自设立之日起就包含了大国合作与对抗的因素。前期,大国虽谋求一系列相互矛盾的绝对收益,但是合作者能够采取互惠性政策,并且美苏作为具有合作主导权的两极对大国合作的实现起到了保障作用。因此,外长会议可以调和各方矛盾完成五国和约的准备,为欧洲和平作出历史性贡献。冷战爆发之际,拟议“对德和约”的外长会议在外部受制于大国关系的恶化,在其内部又受到严重的消极影响,即法国主张对德采取严苛的肢解削弱政策增加了合作的障碍,合作者对相对利益的追求,美国国内政治的一致性的转变以及合作者之间认知一致性上出现了东西分化。内外交困的外长会议失去了促成大国合作的基础,外长们始终无法突破这一困境。同时应当看到,大国对中国的排挤以及对弱小国家的忽视均违背了贝尔纳斯方案的初衷。强权政治因素居主导地位的五国外长会议,在构建欧洲和平的过程中最终未能完全实现其预设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