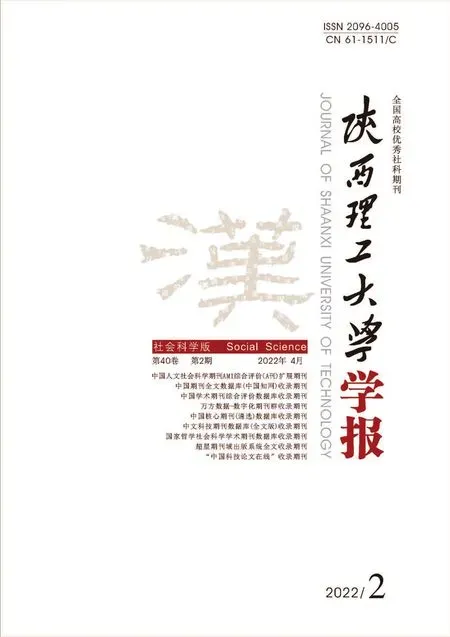文学地理学视域下的陕西新诗
李 洁
(西安财经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从地理学意义上来讲,人们对地域文化的感受首先来自该地域的自然景观与物质生活方式的差异,而文学地理学更多关注的则是文学要素的地理分布、组合与变迁,文学要素及其整体形态的地域特性与地域差异以及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三者的关系当中,地理学与文学的相互作用更为重要。因此,通过地域知识来理解诗歌,继而在诗歌作品当中认识地域文化,是文学地理学研究中相互作用的主要体现。在研究当代诗歌的过程中,将诗歌与地理区域的关系进行考量也是诗歌研究过程中的重要方向。正如美国哲学家欧文·拉兹洛的分析:“诗歌能有力地帮助人们恢复在20世纪同自然和宇宙异化的世界中无心地追逐物质产品和权力所丧失的整体意识。”[1]3作为文学大省,陕西新诗的发展历史由来已久,尤其是在当代文学领域,陕西诗人从来就没有缺席过。但是在极具影响力的小说和散文面前,新诗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制约,一方面是由于前两者的光芒太过于强大,多少掩盖了新诗的成就,另一方面也与新诗在文学界不受重视的现实不无关系。相较于陕西小说研究已经形成的较大规模,目前学界对于陕西诗歌的关注明显不足,仅有的研究主要是对于陕西诗歌史的梳理以及陕西新诗在发展过程中所涌现出来的重要诗人以及对重要的诗歌作品进行总结挖掘,因而对陕西诗歌做系统的研究显得必要而迫切。陕西诗歌作为一种地域性的文学现象,它所包含的地域因子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化意蕴是其中的关键,本研究拟从地域文化中的地理元素、历史文化意象以及地域迁徙等方面进行考察,探讨文学地理学视域下的陕西诗歌,并对其做系统性的观照。
一、陕西新诗的多重自然景观与地域空间特色
触发文学家生命意识的地理物象和地理事象具有空间属性,这种“应物斯感”“缘事而发”的生成机制促成了大量文学作品的产生[2]78。普列汉诺夫曾指出人类的精神产物正如活的自然产物一样,只能由它们的环境来说明。因此,作家的创作行为与作品的风格只能由作家的个性特征和地域环境的相互作用来解释。体现在诗歌写作当中,地域决定了诗人写作行为的空间范畴,地理景观和地域文化对诗歌写作存在或隐或显的影响,诗人的写作往往也被看作是某一区域的文化表征。陕西中部的渭河平原有着辉煌的农耕文明史,同时也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古都西安所在地,陕西北部有红色革命根据地延安,这片土地上所呈现出来的地理物象一直是陕西新诗永不枯竭的创作源泉,陕西诗人也从未停止对这片土地的歌咏。文化地理学认为,“现实世界的文化并不完全依靠对其物理特征的记录来呈现,要体会现实世界的文化,还需要阅读地方文本和异地文化对本地文化的观照以及二者传递给人们的文化意义才能完全获得。”[3]按照这一思路,如何在陕西新诗当中挖掘出独特的精神脉络,这对于阐述陕西文学多元化的艺术思维和创作风格具有重要意义。陕西新诗作为一种地域性的文学现象,它所承载的内涵是多方面的。首先,地区特殊的文化意义以及地方在形成主体意识过程中的建构作用形成了新诗发展的空间条件,在此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诗人独特的空间感受往往是基于个体之上的地域认知。其次,在这一认知过程中,地域性的诗歌现象所揭示出来的地方历史性和社会性能够深刻挖掘这一地域的自然历史所蕴含的美学意味以及道德内涵。最后,在地域化的诗歌书写过程中,还能够体现出诗人逐步把外部空间改写为自我疆域的构建过程。虽然人生轨迹与写作理念不同,但对大多数诗人来说,写作素材中最为熟悉的莫过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共同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滋养造就了陕西诗人写作中的某些共性,因此,归纳陕西诗歌的群体特征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法国学者波特兰·韦斯特法尔的地理批评理论中,地方成为文本研究的中心,他曾经指出:“空间指涉是分析的基础,而不是作者及其文本。”[4]112在这一理论中,文学地理学的目的更加侧重于人类的生活空间与文学的互动关系,而不是仅仅着眼于文学中的空间再现。陕西身处西北内陆,位于中国西北地区东部,东隔黄河与山西相望,西连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北邻内蒙古自治区,南连四川省、重庆市,东南与湖北省、河南省接壤。从地域上一般分为陕北、关中、陕南三个部分,从大的方面来说,关中和陕北则是以北山山系为分界线,关中和陕南以秦岭为分界线。北山作为陕北黄土高原和关中渭河平原的分界岭,它的北部是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南部是一马平川的关中平原,而秦岭以南,则是秦巴山区,这就形成了陕西独特的陕北塞外文化、关中西秦文化和陕南楚蜀文化。陕西不同的自然空间也形成了陕西文学不同的气质类型,正如李建军的分析:“从文化气质来看,陕西文学可以分成三种形态,即高原型精神气质、平原型精神气质和山地型精神气质。”[5]不同的文化形态滋养了丰富的文学元素,为诗歌书写提供了众多的表现素材,也使得读者能够在诗歌当中领略地域之美。成长于陕北的诗人阎安曾写道:“天下人都知道 秦岭以北/是我的故乡 山水的月亮透着羞愧的红 像刚刚哭过的样子 它的河流在草丛中……天下人都知道 我的故乡/但他们不知道 这些年来拖儿带女在外漂泊”[6]14。(阎安《我的故乡在秦岭以北》)作为鲁迅文学奖的获奖诗人,阎安笔下的故乡深情而悲凉,尽管土地贫瘠,生活不易,但故乡的烙印在游子的心目中却是难以祛除的,陕北自然条件艰苦,但这块土地上却流淌着天然的诗意与厚重。“我是黄土地上唱响的一支民谣/淳朴悠扬/直白苍凉//大风席卷/我在尘埃之上嘹亮……我在小米饭缭绕的香气里升腾/我在窑洞炕头前的油灯上闪烁”[7]166。(流沙《我在黄土地上唱响一支民谣》)特殊的地理地貌形成了陕北一带别具一格的风土人情,白头巾、小米饭、窑洞、火炕是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灵魂,苍凉、贫瘠、粗犷、热情成为这里特殊的文化标签,萦绕在这片土地之上的除了高亢的信天游,更不乏诗歌的深情吟诵。“铺在泥土的裙边/一卷纸上长安,像秦岭从北坡上/悬挂下来的水墨……我要迈开,描写或丈量/大地的手足,从秋风反复吹落的/渭河边上,捡一封秦岭/写来的家书”[7]9。(耿翔《纸上长安》)秦岭作为古城长安的屏障,也是陕西境内最让人熟悉的自然景观。书写秦岭,就是书写陕西人自己的家园,这里的草木鸟兽,都是诗人笔下最亲近的朋友。渭河更可谓是秦地人民的母亲河,是农耕文明的见证者。诗人从“秦岭”写到“渭河”,展现了他对故土的缱绻深情。
从陕北黄土地到关中平原,从秦岭到渭河,再到古都长安,这些地理元素是陕西诗歌当中比较常见的组成部分,不论是地貌形态的自然呈现还是情感脉络中的地缘情结,呈现在诗歌文本当中就自然形成了这一区域性的群体特征,成为研究陕西诗歌最容易捕捉到的信息,也是读者理解、进入诗歌文本的钥匙。一般而言,“自然景观的单调与繁复除直接影响着文风的质朴与瑰丽外,更多的通过在地理环境基础上形成的有着独特区域特点的经济类型、生活方式,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民风民性等方面曲折地影响着文学家,进而影响其风格。”[8]就陕西省独特的地理环境而言,黄土地的贫瘠与厚重,平原的宽广和包容,山川的灵秀与险峻,这些空间元素的存在无一例外不渗透到陕西当代诗歌的肌理当中,使得陕西诗歌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风貌。
虽然不能简单地认为通过阅读陕西诗歌作品就可以了解陕西的地域特征,但是在诗歌地理的解读中,我们能够窥见该区域的自然轮廓与文化概貌,共同形成诗歌的地方性经验,而这些地方性经验经过诗人的创造,在诗歌作品中形成的一定的地理空间,反过来又帮助创造了这些地方的文化特色。曾大兴在《文学地理学研究》中就曾提出:“文学作品包含思想、情感、景观、实物、人物、事件、语言、风格等诸多要素,如果这些要素具有地域性,再通过文学家的创造完成空间组合,就构成了文学作品形态各异的地理空间。”[2]3陕西地处祖国的西北,虽然因为璀璨繁荣的历史文明而声名远扬,但深处内陆的地理环境也造就了相似的集体无意识心理,沈奇的诗《上游的孩子》《过渡地带》均是这种心理最真实的表达。“上游的孩子/还不会走路/就开始做梦了/梦那些山外边的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身处内陆地区的人们对于山外世界的总有一种迷恋与希冀,无数次的想象与期待可能会“很快回来/说一声没意思/从此不再抬头望山”[9]3,(《上游的孩子》)但是这种蛰伏却不会熄灭内心深处的躁动,山外的世界早已在内心深处生根发芽。这种躁动除了对陌生事物的向往之外,也是对区域地理特征的一种深刻揭示,“在这里长大的/总想走出去/从这里走出去的/总想回忆”[9]12,(《过渡地带》)内心的矛盾和精神困境的选择相关,更与地方感的认知相关。这种认知的过程不仅体现了全球化背景之下的文化多样性表达,同时也强调了地理空间在个体心理建构过程中的重要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地缘情结的形成往往会加强人们的身份认同感,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有着这样的观念:“地域决定着人的存在,地域给人们一种身份认同感、集体归宿感、时空确定感以及内心安宁感。文学地域主义从地域出发,但又超越地域,它从地域中获得素材和启示,将其沉淀成思想,传达的是终极的人文关怀。它虽然是时代的产物,但它超越时代,它在全球化时代的复兴见证了其永久的意义。”[10]这里的文学地域主义与文学地理学的概念类似,通过地理空间的同一性来建立一种认知符号。如:“无定河边柳色青青/可是那春闺梦里人儿的相思/纤手一样拂去赶脚人的征尘与倦怠/古长城的遗迹”[11]146。(和谷《高原脚夫》)这里出现的地名不只是一种地理学意义上的客观存在,同时也是从历史文化层面达成的心理共识,无定河是陕西境内的黄河支流,从“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开始,这里就是边塞要地,从征战古战场的将士到如今奔波的赶路人,陕北的苍凉与厚重感也随之而来。诗歌作品书写参与并见证了这些地方的古今变迁,同时也建构了这些地域的空间特色。
二、陕西新诗的历史文化意象与审美内蕴
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意义在于“以文学空间为研究重心,其目的首先在于重新发现长期以来被忽视的文学空间,其次是从文学空间的视镜重释与互释文学时间”[12]。书写历史一直是陕西文学创作的重点之一,秦汉风采与大唐气韵笼罩的厚重同样也是陕西新诗创作不可或缺的内容,作为时空变迁中文化传承的标志,这些历史物象在新诗中呈现出了较为复杂的意蕴。尤其是以古都西安为中心的古迹遗存,作为地理景观在时空浸染中获得了不同的文化阐释,如大雁塔、碑林等具有历史意义的物象一直以来都是文学创作的重点,这些书写一方面承载着后人对这片古老土地的深深敬意,一方面也寄寓了现代诗人面对历史古迹的细微感受,体现了陕西诗人的历史意识与文化审美内蕴。
历史古迹在不同时期的诗人笔下呈现出了不同的意蕴,如佛教圣地法门寺,“发光的七月/不能把它读成一个词组/除非这一切都被事物重复/无辜的眺望照亮一座石砌的佛塔/千年前的一滴醉意/吹成今日浩荡的景色”[7]40。(三色堇《法门寺》)这座千年古寺经历了辉煌与坎坷,成为后人瞻仰的佛教圣地,这一切在时间长河中虽然具有偶然性,但历史遗迹的厚重与底蕴在诗人笔下展露无遗,“文字依旧/任意一丝神秘的碎片/都能裸露路人的敬仰/谁能经得起它的触摸/谁能雕铸那透明的骨头/亦如那透明的语言”[7]40。古老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它的神秘,能够触摸历史,与历史对话,更能够增加后人的敬畏之情。还在于“当人们将意义投向空间,开始赋予它情感和价值的时候,空间就成了地方,有其独特的社会性和政治性”[13]。在现代意识的浸染之下,诗人们也对这些地方文化圣地赋予了独特的意蕴,如沈奇的诗《碑林与现代舞蹈》中就呈现出了一定的现代元素,“他们只知道这是公园碑林是它的名字/这城市到处是古迹古迹就是公园/他们只有到这里来/可他们也实在发了昏/在如此古老如此神圣如此辉煌/如此庄严的——碑林/跳起了现代舞……”[9]21将古都西安著名的文化艺术宝库——碑林与奔放、嘈杂的现代舞放置在一个空间当中,以往被称为书法爱好者朝圣之地的碑林无形之中就失去了它原本被赋予的神圣意义。符号化的概念在很多时候往往会导致简化与偏执的产生,尤其是对已经被先验固化了的物象来说,某种约定俗成的紧密联系往往会束缚人们的想象力与行动力,而诗歌在这里的功用就是揭开这些在历史积淀中所形成的文化负累,还原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已经被遗忘或者遮蔽了的真相。
大雁塔作为古都西安的历史地标之一,它的意义早已超出了建筑本身,它是繁荣大唐的见证者,也是这座古城最喧闹、热情的现代文明的参与者,在20世纪80年代多次成为先锋诗人们书写的对象。陕西诗人杨于军写道:“远看是塔/近看 还是塔/还有无法开启的经书/被更加庄严的围墙守护//走上去却发现自己再看别的什么/塔在脚下/不再是塔/而是似懂非懂的文字/亦真亦幻的感觉”[11]357。(杨于军《再见大雁塔》)在这里诗人的笔直指大雁塔的内在本质,摒弃了历史所赋予它的一切意义,还原了作为建筑学意义上“塔”的功用,在这里看到的不仅仅是佛教文化的庄严,还有“登塔者”内心的独白与感受。杨于军作为曾经“从陕西高校之大学校园起步,成名于其他诗歌版图的青年诗人”,其所处的这一诗人群体被认为是“有效推动陕西诗歌发展的另一潜在源流,虽变动不居而生生不息,以其青春色彩与纯粹心态,不断提供新鲜的活力和勃勃的生机”[14]。虽然他们在陕时间短暂,但这一股年轻的力量在陕西诗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首《再见大雁塔》即是以开放性的姿态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意图寻求与历史对话且保持清醒思考的旁观者形象。
突破了历史意蕴的现代言说曾经以其强烈的探索精神和充满现代意识与诗美追求的诗歌品质将陕西诗歌带向了更加广阔的天地,使得陕西诗歌开始与国内甚至全世界最新潮的诗歌观念接轨,融入了先锋诗歌写作的队伍。但经过了数十年的一路狂奔之后,曾经的先锋也逐渐呈现出了不同的样态。或转向传统寻找全新的支撑,或在求新的道路上不断挖掘,但是历史文化的痕迹即使在抛却了地域的定义之后,仍然是诗歌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存在而已。“秋深了 云/在天空闲着//植物和动物/忙他们的收获//有信仰的人/是安详的//一尊佛 从寺庙/走出 渴望爱情//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9]233。(沈奇《朗逸》)在一片和谐的声音中世间万物各寻其道,构成了一副“清朗舒逸”的意境图,结尾处以耳熟能详的唐诗为这种宁静增加了古典的意蕴。沈奇先生曾提到:“仅就基本语感而言,我是将这些诗作为相当于古典诗歌中‘词’的形式感觉来写的,尤其是在字词、韵律、节奏和诗体造型方面,不过换了现代汉语的语式……”[15]举这个例子并不是说古典就代表了历史,但是这些诗句中流露出来的诗性生命却是相通的。这片土地的滋养使得这种诗意的基因跨越了时空的界线,成就了汉语新诗的永恒魅力。
三、陕西新诗的现代化反思与新乡愁主题
在地理批评的概念中曾经提到:“空间的再现来自于‘他性’与‘主体身份’两个焦点的互相碰撞与补充、丰富与创造。”[16]在诗歌写作过程中,诗人作为地域信息的传递者,在他们的作品当中往往会渗透某地方的地域特色与人文因子,成为该地域的代言人或言说者。与此同时,他们的诗歌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该地域的文化基因。具体到诗歌创作,这种相互影响的关系会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尤其是在地域迁徙日益频繁、传播途径日渐多元的今天,这种“他性”与“主体身份”之前的相互关联成就了诗歌地理书写的丰富内涵。
陕西诗歌作为一种地域性的文学现象,它所包含的地域因子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化意蕴是其中的关键。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城乡二元模式逐渐转向多元,与现代都市相比,一些传统的乡村或者经济条件欠发达的区域逐渐成为较大的人口输出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离开故土,寻找新的发展机遇,生活场域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地理空间。面对这样的社会语境,按照波特兰·韦斯特法尔的观点来看,当一个行为主体通过一系列的关系进入到某一空间之后,由这些关系的亲密程度决定了不同的视角,大致可分为内生、外生或异生三种[16]。而地域迁徙过程中所产生的视角则属于异生,即在某一个地方长期定居下来的异域视角。这种观察方式从后殖民的视角来看,呈现出一种立体聚焦的状态,促进了第三空间的产生,保证了话语的多元。那么在诗歌创作当中,生活迁徙使得流动主体经历了多个文化区域,这对诗歌地理的多元化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部分诗歌创作者来说,这种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或者流动所产生的怀旧情绪以及陌生感逐渐成为他们关注并书写的重要对象,促成了“新乡愁”诗歌的产生,同时也唤醒了人们对于现代性的反思。“这种怀旧也促成了文学、文化之间全新的选择、替换、组接和融合,在原生活地域与迁徙地域的关联变动中,催生出了新的文学品质。”[17]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古都西安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一环,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以西安为代表的现代都市也逐渐摆脱了乡村文明的影响,取得了相对于乡村的异质性和独立性,而文学在这种社会潮流的影响下,由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一统逐渐转变为多元文化诉求下的真实表达。全新的文学环境使得诗人们的创作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也必然导致诗歌创作的变化。对于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关注,也是对于陕西诗歌未来的思考。
作为西北最大的现代化都市,西安是很多西北人“寻梦”的第一站,虽然这里与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化大都市”还有一些差距,但作为曾经繁荣的古都,这里依然承载着众多期待,“入城那阵,二十有六,时值秋天/小寨一带,梧桐树的雨滴,停在额头/确有着十三朝之凉。那片已被砍伐的树林/和谁,留在谁的记忆里;就像曾经不存在一样/东、南、西、北、中,这古长安的期盼”[7]126。(邹定国《长安客》)与古诗词中描写的“长安”不同,在“长安客”的眼中,现代化的西安不仅与记忆中的期待有所差异,而且产生了现代都市所特有的疏离感,人与人、人与物之间逐渐陌生化是最显著的体现,“十三朝古都”的繁华与眼前的落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除了对现代都市的质疑与反思之外,对“全球化”的适应与认知也是地域迁徙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在当下社会,全球各个角落都与其他地区发生了联系,任一地方传统都在开放的世界语境中成为个人选择的资源之一,但往往因为个体认知能力有限,人们面对全球一体化的世界时又会遭遇巨大的无根焦虑和自我认同的磨难。“远离家园与亲情/于都市的奔波中/阅读繁华 感受/孤独与无助”[7]177。(流水平子《打工族》)城市化的过程加速了地域之间的迁徙流动,但很多时候迁徙即预示着传统生活方式的危机,意味着乡愁的产生。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认识到社会需要传统,这是完全理性和合理的。我们不应该接受世界应该废弃传统的启蒙思想。传统是必须的,而且总是应该坚持,因为它们给予生活连续性并形成生活。”[18]46但经历了“出走——回归——再次出走”的自反性循环,一些地方传统已经很难保持最初的模式,而是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复合状态,异质元素不断地出现,形成了新的地方经验。所以,“在全球化时代重读经典地域文学,会对乡土和田园意象产生全新的体认”[19],在此意义之上,地域化的诗歌书写将成为强化“全球化”自反性的重要力量。对处在现代化过程中的陕西诗歌而言,这样的地方性经验正是它能够逐渐成熟的基础,同时也是它得以彰显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地理空间作为文学发生的现场,是文学意义得以实现的基础。新诗发展的百年历史形成了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同时,地域之间的差异性又使得这种同一性更加丰富。陕西新诗首先作为地域文学而存在,该地区的空间地理文化决定了它最初的基因,对于地理空间的书写和吟咏也成为陕西新诗的独特魅力。历史文化的传承使得陕西新诗从古典诗歌的辉煌底色中脱颖而出,成就了一系列既能够立足本土文化,也能够在对传统的反思中不断求新的佳作。对于陕西诗歌这一地域性的文学现象做系统性的研究,一方面有利于提高人们对地域文学的自豪感,另一方面对诗人在创作过程中拘囿于地域影响无法自拔的现象有一定的纠偏。在现代化进程中,地域迁徙的现象不可避免,而这种现象的存在对于文化心理结构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地域文化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而存在,从全球化的视角来看,这种迁徙作为文化结构内部的双向流动,一方面能够丰富“地域诗学”的内涵,另一方面也能够对传统的地域文化进行反思。
——喜迎十九大 追赶超越在陕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