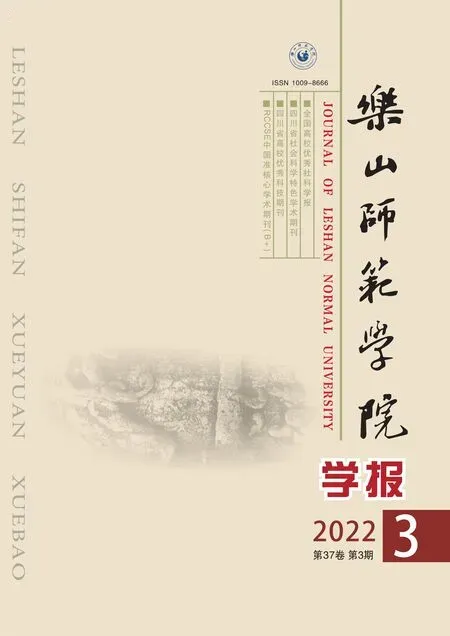少年中国学会的妇女解放思想探微
——以《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为考察
常 慧,张 文
(贵州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少年中国学会从1919 年7 月1 日正式成立,到1925 年7 月20 日解散,历时七年之久,是当时影响最大、人数最多的进步社团之一。学会存续期间,正是中国思想空前解放、各种主义盛行的时代,妇女解放思潮也是当时流行思潮中的一种。面对空前热烈的妇女解放思潮,少年中国学会明确提出:“我们要创造‘少年中国’,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妇女问题。”[1]为此,学会在《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中设置“妇女号”特刊,作为主要的宣传阵地,积极动员学会会员和名流人士撰写文章,专门讨论和研究妇女解放问题,介绍国内外妇女运动的情况,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对妇女问题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推动了五四时期妇女解放的进程。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少年中国学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主要人物、演变历程以及与五四运动和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关系等方面。在报刊方面,学术界侧重于研究《少年中国》,对《少年世界》的关注较少。本文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挖掘《少年世界》的价值,从“妇女号”特刊入手,将《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相结合,集中考察少年中国学会的妇女解放思想。
一、少年中国学会关注妇女解放问题的缘起
少年中国学会对妇女解放问题的关注并不是一时兴起、凭空产生的,而是国内外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客观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工业革命的发展
国外方面,少年中国学会成立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整个世界处于新旧交替的剧烈变动时期,出现了许多新迹象。一战以前,整个人类历史大都是男性的时代,女子的领域只有家庭,家庭之外便没有插足的余地。而且在家庭里,女子也只是丈夫和家庭的奴隶。她的行动要服从丈夫的安排,只能做男子喜欢的事,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愿去求知识,完全没有独立的人格可言。一战爆发后,“因社会状态的变化,欧西妇女竟得到了实验的机会。男子出去打仗,女子便在国内做工。开电车、当巡警、在各种工厂里作事、造军需咧、造日用工艺品咧、甚至还打铁,这种工作,从前的人都以为女子不胜其任的,现在做了,而且成绩居然很好”[2],妇女的社会地位逐渐提高。此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快速发展,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程度日益加深,欧美国家的妇女纷纷要求享有选举权和劳动自由,以保障自身利益,但是政府政策和社会观念限制她们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和劳动权利。为了谋求更多的话语权,她们发起了女权运动,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妇女解放理论,号召各国的妇女团结起来,共同为自身解放而奋斗,使得妇女解放运动逐渐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世界潮流。
国内方面,一战爆发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一个短暂的“黄金期”,加快了自然经济的瓦解。与此同时,“因为机械的利用,一方面需用的人工极少,其他方面生产的工业品又多,家庭的手工业已经不能够继续维持,平时在家里营自给自足的生活的妇女,受内外形势的交迫,自不能不舍家庭而就工厂。”[3]再加之面粉、纺织等轻工业的迅速发展,使得一些适合妇女工作的职业应运而生。为了维持生计,男子只能同意妇女离开家庭,参加社会劳动。一时间,女工人的队伍不断壮大,妇女再次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妇女问题也成为社团组织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将妇女问题看作社会革新的主要方面加以研究,喊出了人格独立、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等口号,积极探索实现妇女解放的现实途径。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就是其中的一份子。
(二)思想基础:西方民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入
五四时期是一个思想争鸣的新时期,各种新理论、新学说如潮水一般涌入中国,使中国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得以了解各国妇女运动的历史,认识到女子争取权利、寻求自身解放的重要性。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就是其中的代表。
一是受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民主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学会会员主张男女平等,抨击封建礼教是一个万恶欺人的圈套,提出女子要实现经济独立,以摆脱圈套的束缚,形成独立的人格。王会吾指出,“中国数千年的习惯说,什么‘夫为妻纲’、什么‘男尊女卑’、什么‘将夫比天’、什么‘柔弱卑弱’、什么‘三从四德’父母用以告诫、师傅用以教训、道学先生们用着去劝诱奖励都说‘这是做女子的天经地义’。唉!什么天经地义呢,不过是一个欺人的圈套罢了!”[4]李大钊将妇女解放与民主政治联系起来,指出:“没有妇女解放的Democracy 断不是真正的Democracy,我们若是求真正的Democracy,必须要求妇女解放。”他强调“一个社会里如果只有男子活动的机会,把那一半的妇女关闭起来,不许他在社会上活动,几于排出于社会生活以外,那个社会一定是个专制刚愎横暴冷酷干燥的社会,断没有Democracy 的精神。”[5]
二是受教育救国思想的熏陶,学会会员将教育看作是一切问题的根本,主张从教育入手解决妇女问题。王光析在总结学会会员的意见时曾说道:“我们这回讨论妇女问题的结果,几乎每篇文章都归根结底于教育,都主张应该从教育下手。”[6]黄日葵认为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一步就是要求得男女受平等的教育[7]。杨钟健也提出:“要让妇女有跳出火坑的能力就要普及女子教育,使其有根本上的觉悟,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人,不是别人的玩物,知道世界大势和国家的安危,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一份子,国家的一个国民,不是终身囚禁在牛棚大的一个小家庭里过几十年机械生活的人。”[8]
三是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引起国人关注,中国的报刊杂志刊登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和译作,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受其影响,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也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和研究中国妇女问题,强调无产阶级妇女运动对于妇女解放的重要性,将实现妇女的彻底解放和改革社会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学会会员田汉在《第四阶级的妇人运动》一文中,把妇人运动分做“君主阶级”“贵族阶级”“中产阶级”“劳动阶级”四层,指出:“前三阶级的运动,都是政治的教育的,不过说男子是人,女子也是人,男子参政,女子也要参政,男子受得大学教育,女子也要一样,不思最初女子何以屈服于男子而失去其地位的缘故。所以比较的是反射的作用,而非自觉的作用。真正彻底的改革论便是第四阶级的妇人运动,或谓之为‘妇人的劳动运动’。”[9]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考察各个时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指出中国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私有制度,主张废除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实现真正的妇女解放。“妇人问题彻底解决的办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10]。
(三)现实动力:国外妇女运动的激励
一战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的妇女解放运动日益发展,各国相继出台一系列法规政策,保护妇女的选举权、参政权,普及女子教育,扩大妇女就业的范围,使妇女在精神和物质上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男女日益平等。如:“1908 年巴黎选举之际,激进派妇人有候补者一人;同年十一月妇女有为劳动争议调停裁判所委员的权利。其后可得拿破仑法典之改造,结婚契约立会人的权利,及既婚妇人的财产所有权等。”[3]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妇女的地位提高。“妇女现在享受社会上政治上绝对的自由权,这些自由和改良的事业推行,使离婚变得容易了,市政婚娶也不须牧师的批准了,这一来给俄国妇女一个特别的自由,是别国姐妹们所得不到的。”[11]这些成果和经验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
在亚洲,日本的妇女解放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就连向来重男轻女程度大于中国的印度,也逐步认识到妇女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开始谋求妇女解放、实现男女平等。如:印度国会通过了很多决议案来保护妇女的自由,尤其1914年的决议案极大地支援了印度妇女的解放运动。“(一)本会为促进本国女子教育起见,当督促政府广充女子小学教育及高等教育,多办女子学校,女子中学及美术医业等专门学校。(二)本会当劝告一般的人,多办家庭学校、长期演讲、俱乐部、联合会等等,广布有用的知识于妇女界,做进步的基础,庶幾妇女的地位,得以一天一天的加高,而得共负社会国家的责任。(三)本会对于女子服务社这一类的会,所做的事业,当加以尊重。(四)本会当督促女子之父母或保证人,增高女子的婚龄,使他能够得到上进的教育。(五)本会当督促一般的人,赶快废除Purdab(是一种帐幕挡住女子,不给外人看见,这是回教的风俗,在印度最盛)的风气,注意于女子的教育与健康,使他能够参与社会的事业。”[12]这对中国的思想界和妇女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在研究各国妇女运动时,不可避免会将其与中国妇女的生存状况进行对比,发现两者的差距,进而主动关注和思考实现中国妇女解放的方法。
二、少年中国学会妇女解放思想的关注内容
五四前后涌现的妇女解放思潮,其内容是丰富多彩的,涉及到女子生活各个方面。少年中国学会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进步社团之一,其对妇女解放问题的研究几乎囊括了当时社会讨论的所有话题,主要有教育平等、社交公开、婚恋自由、家庭改制、经济独立、人格独立等。
(一)教育平等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推崇男尊女卑、三从四德,把女子当作男子的附属品,只允许男子接受教育。近代以来,随着男子受教育的程度越来越高,一些父母为了在婚姻上能与男子般配,开始送女子进学校,妇女受教育程度有所改善。但五四以前,中国只有少数的女子高等学校招收女学生,其他大学不招收女学生,而且这些女子学校仍是按照“贤妻良母”的标准来培养学生,并未传授女子真正的科学知识和生存技能。中国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对男女教育上的不平等感到十分不满,指出这种女子教育的本质仍是培养为男性服务的女仆,纷纷要求大学开女禁,实行男女同校。少年中国学会也就此展开激烈的辩论。
1.大学开女禁
少年中国学会中只有少数反对派认为大学不应开女禁。一方面,他们认为中国女子向来柔弱,一直以来接受的是贤妻良母教育,与自小接受正统教育的男子相差甚远,知识储备不足,不具备上大学的能力。另一方面,他们主张女子“尚无进大学修业之必要”[13],认为女子在大学毕业后,一部分依旧会选择做贤妻良母,另一部分选择就职的女大学生,所从事的工作基本上还是与音乐、文学、刺绣等相关,而这些技能即使不上大学也可以学会。因此,大学不应开女禁。
但绝大多数学会会员赞成大学开女禁,并一一驳斥了反对派的理由。首先,对于女子“弱”的问题,恽代英指出,女子身体较男子柔弱最大的原因,是由于女子长居家中、缺乏运动训练所致,“与教育,与男女根本上强弱问题无关”,“人不可以妇女既已弱矣,遂承认其弱为天定应受的体格也”[14]。其次,对于女子不具备上大学能力的问题,沈泽民反驳道:“为什么男子可以学训练理性的工程科学等功课,女子却叫她学音乐?从生下来就变了分途的教育,到长大来还能怪女子能力不及男子么?”[2]他强调女子与男子只有生理上的差异,并无智力上的差异。会外人士胡适进一步提出大学当先收女子旁听生,“旁听生若能将正科生的学科习完、并能随同考试及格、修业期满时、得请求補行预科必修科目的考试、此项考试如及格、得请求与改为正科生并授予学位”[6]。这样既可以弥补女子在知识储备上的缺失,也让大学生之间平等竞争,保证学生的质量,得到支持派学会会员的一致赞成。最后,对于女子没有上大学必要的问题,支持派认为妇女问题不能依靠男子,必须由女子自身起来解决,提出女子教育是解决妇女问题的根本途径。最终这场辩论以北京大学招收女大学生宣告结束。
2.男女同校
大学女禁一开,必然会面临男女同校问题。以王卓民为代表的部分会员反对男女同校。他们认为男女授受不亲,如果男女同校,相互之间必有交往,偶有不慎,就会做出违反封建道德的事情,损坏学校名誉,破坏社会风气。支持派则认为,社会道德的堕落都是封建礼教过于“防闲”所致,男女同校可以让男女双方了解各自的生活习惯和人生观,消除对彼此的好奇心,建立起纯洁的友谊关系,减少不道德事情的发生。康白情指出:“勿论什么东西,总是愈觉得希奇我们愈需要他,又是愈不常见面愈觉得希奇。性欲的要求也是这样的。寻常人男女相见就脸红,便是性欲行动的表示,不过发露于不认不知罢了。这都是男女过于间离生出来的。试看惯于男女交际的,何尝有彼此见着就脸红的事?这就是不以为希奇,所以不容易激发性欲的行动。”[15]大多数学会会员持此类观点,并提出实行共校制。“我大中华民国教育界诸公,当仁不让之义,蓦地奋起,各尽所能,将我全国所有学校,无大无小—自国民校以至大学—一齐开放,举行共校制。”[16]此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大同学院、浦东中学以及四川外国语语言专门学校等先后实现男女同校。
(二)社交公开
数千年来,中国妇女在“男女有别”“授受不亲”“男女大防”等封建礼教的约束下,一直都是深处家庭,不与社会交涉。“因为女子闭锁的时代中,‘男女授受不亲’就是一个天经地义,谁敢去触犯呢?就是有一二不守这天经地义的,都因为要充足他不正当的欲望,所以私自交际起来,而那男女社交也就认为一件顶不名誉的事了!”[17]五四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就男女交际问题进行了一场论争,其中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主张男女社交公开。一方面,他们认为男子女子都是人类,凡人类都是自由、平等、不受束缚的,每个人都有自由交往的权利,女子也不例外,故“男女当公然交际,没有什么忌避”。[18]潘仞秋指出:“女子的道德,不比男子的多一种,也不比男子的少一种,……,女道德就是‘不做奴隶’、‘不受束缚’、‘扶助男子’、‘自立自活’、‘守男子所守的法律’、‘公然的交际’。”[18]另一方面,学会会员还强调男女交际不是罪恶,社交公开可以让男女双方互相了解、彼此借鉴、共同进步,增进彼此的自治的能力,形成一种向上的“合力”,减少不道德事情的发生。康白情在谈论此问题时,就以北京学校学生开联合会时,女子参加会议前后会场秩序的变化为例,证明男女交际可以互相克制双方一切放肆和不合礼的行为。“北京女学生会某日开联合会,正值议场上争辩纷纭的时候,有某女士起立解释没打架立刻就镇静严肃,(那天我亦在议场的确令人叹服)更加是一个顶好的例证了。”[19]会外人士胡适也赞成此种观点。他曾说:“女子因为常同男子在一起做事,自然脱去许多柔弱的习惯。男子因为常与女子在一堂,自然也脱去许多野蛮无礼的行为(如秽口骂人之类)。最大的好处,在于养成青年男女自治的能力。中国的习惯,男女隔绝太甚了,所以偶然男女相见,没有鉴别的眼光,没有自治的能力,最容易陷入烦恼的境地,最容易发生不道德的行为。”[20]
(三)婚恋自由
少年中国学会认为婚姻是影响妇女解放的重要因素,在批判中国传统婚姻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了恋爱自由、结婚自由、离婚自由三种不同层次的婚姻主张。
一是恋爱自由。少年中国学会认为婚姻是以自由恋爱为基础的,若是没有恋爱,婚姻就没有意义。“夫妇的关系,要以男女间双方的、光明的、真挚的、神圣的恋爱为基础。”[17]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支持公开恋爱,反对秘密恋爱。他们认为,秘密恋爱会滋生“恶”,最后伤人伤己。男女双方如果确定恋爱关系,最好公开地讲出来,这样既可以让恋爱双方安心立命,又可以省得旁人多心与误解,减少悲剧的发生。田汉就指出:“古今东西,因为秘密恋爱所演出的悲剧,不知几千百幕。或是子女雨下有意,父母不知别与订婚;或是男子爱了女子,又不肯对他直接说出来,生女子的误解;或女子有心与男子,也不肯直接表明或故意生疏,也生出男子的误解。”[21]
二是结婚自由。少年中国学会支持自由结婚。他们指出,中国传统婚姻制度推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子女婚姻皆由父母包办,导致夫妻双方之间没有爱,生活不幸福,害了不少人。而结婚作为男女双方恋爱后所发生的种种合意事实中的一种,是以爱为基础的,是两个人的事,是不能有第三方参与的。子女的婚姻可以听取父母的意见,但不应服从他们的决定和安排。会员王光析指出:“结婚即为诸种合意事实中的一种,以恋爱为根本要义,以彼此合意为前提。故结婚的事实发生与否,只问两性间的恋爱怎么样?对于结婚的事实与否,彼此合意?决不许有第三人批评或参加。若是任意批评他人两性间的事实,便是侮辱他人的人格。若是未得本人同意,任意参加他人两性间的事实,便是侵犯他人的自由。”[22]同时,学会会员还强调每一个男女都有选择结婚对象和是否结婚的自由。恽代英提出:“结婚主权应该由青年男女自己掌握,因为结婚是他们自己的事。”[23]苏甲荣曾说道:“如无相当的配偶,吾宁独身”[17]。左舜生也指出:男子和女子如果自己“找不着一个相当的配偶,就只有暂时的、或永远的、抱着那不婚不嫁的独身主义。”[24]
三是离婚自由。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一致主张离婚自由。他们认为“婚姻关系可以随着爱情的变化而自由解除与缔结”[25],离婚是合法的表现。近代社会是以个人为单位,而不是以家庭为单位。男女两性即使结了婚,彼此依然是独立的个体,如果婚姻生活不幸福,各自仍有选择离婚的自由权。少年中国学会鼓励妇女要敢于离婚,勇敢追求婚姻自由。在他们看来,离婚是婚姻变化的自然现象,任何外力都不能干预离婚问题,包括法律和道德。易家钺指出:“无恋爱的结婚,十有九是早已播下后来离婚的种子,到离婚时,不过是由那粒种子,而发芽,而分裂罢了。”[26]
(四)家庭改制
少年中国学会认为要实现妇女的彻底解放,必须改革中国传统的家庭制度。“若是中国的少年要改造这个国家和社会,定不可不先把这腐败的家庭推翻,若要人民人人有独立精神和自立人格,亦不可不先把家庭制度打破。如不先从个人和家着手,那社会革新的事业,就更没有办法了!”[27]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强烈批判“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教育观和“养儿防老”“光宗耀祖”的“父母心理”,指出中国封建家庭制度是以教育为手段,以婚姻为目的,用封建礼仪和陈规陋矩将女子束缚在家庭这个狭小的范围内,扼杀女子个性的发展,使其沦为男子生育的工具,“把在家里弄饭煮菜、洗衣服做衣服、料理翁姑和小孩子,服务男子,当做是为天经地义的事”[7]。吴弱男指出:“西方家庭的父母,只把教育一事当作为父母的责任,子女的婚嫁与他们毫无关系了。中国的家庭正是相反,做父母的第一件大事,不是娶媳就是嫁女,第二件事不是‘要抱孙子’,就是说‘要传宗接代’,至于教育一事丝毫不去研究。”[27]王会吾还指出:“女子生育时期本来享受一定的权利,男子有赡养女子的义务,但是欺骗不履行,而且还用伦理关系束缚女子。”[4]在批判旧式家庭弊端的同时,少年中国学会还将中国大家庭制和西方小家庭制进行对比,发现小家庭强调独立自强,经济负担轻,家庭氛围和谐欢乐,更有利于社会进步,而大家庭强调共财,容易养出多数人的依赖性,生出无穷的弊害,妨碍社会发展。“西洋家庭乃人生最乐的区域,不像中国家庭中那样多的鼠牙雀角、烦恼龌龊,不是姑媳口角,就是妯娌相骂”[27]。在此基础上,少年中国学会提出要改革中国式的大家庭,实行小家庭制,建立理想中的模范家庭。少年中国学会理想中的家庭,“是由一夫一妇和少数他们亲生的尚未婚嫁的子女共同构成,儿女由父母共同抚养,享受同等地位,接受同等教育;男女都有经济独立的能力,每个人都劳心劳力地工作,不做寄生的夫和妻;男女都有亲戚、朋友和社会的交际,而且能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他们各自的或共同的朋友”[28]。左舜生就提出要建立一个“男女互助、人格平等、饮食起居‘莫不静好’,还有一些朋友交游之乐,无忧无虑的小家庭。”[24]
(五)经济独立
中国封建社会奉行“男主外女主内”的劳作方式,妇女的活动范围只局限于家庭里,加之“女子无才便是德”传统教育观对女子的束缚,使得她们既没有机会走向社会也没有能力参加工作获取劳动报酬,只能依靠男性生活。对此,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明确指出:“生活上只有男女扶助,没有什么依赖的。”[17]一方面,他们强烈谴责男子一边用名教礼法约束女子,一边用金珠饰品、华丽衣裳、美味食物等丰富的报酬诱惑女子的行为,指出男子就是凭借这种恩威并施的手段来欺骗女子,使女子甘愿待在家中被其豢养,成为他的奴隶、玩器和所有物,以确保自身的统治地位。“自来社会男子恃其强力欺凌弱女,视女子为物品,不为人格,积渐既久,女子恃男子而生存,不能独立,嫍媚容悦,亦自视为物品,不为人格,历数千年之久,人格日愈夷而不发展。”[29]另一方面,他们一致主张女子要实现解放,首先要实现经济独立。因为经济不独立,必然会导致女子人格的丧失。“我们要求独立的人格,必须脱离他。脱离的法子,第一要求我们经济的独立。我们姊姊妹妹要个个有自己生活的职业,那就不怕男子的压迫了。”[4]至于如何实现经济独立,少年中国学会强调教育是女子实现经济独立的首要途径。“第一要使女子能自立,要能自立,先要有职业,要有职业,先要有学问,要有学问,自然应当先受教育。”[18]他们指出女子接受教育后,不仅可以提高自身觉悟,免上男子的当,还可以培养独立的智能,习得新的谋生技能,进而在工作上和男人平等竞争,获取报酬,摆脱对男子的经济依赖。实现人格独立。“若要征服一切诱惑或压迫女子的魔力,自然是极应注重教育,使女子的智识日增,有澈底的觉悟,有极强的抵抗力。”[22]
(六)人格独立
经济独立是物质层面的解放,人格独立则是精神层面的解放。实现真正的妇女解放,两者缺一不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猛烈抨击“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对女子人格的残酷压迫。首先,他们批判封建婚姻制度对女子人格的压抑和摧残,强调传统的婚姻观完全是是父权制度的产物,要求废除娼妓制度,禁止男子买妾买婢,实行真正的一夫一妻制。其次,他们批判封建纲常伦理强制妇女守节的传统,主张寡妇有再嫁的权利和自由,妇女是否要守节应该遵循她个人的意愿。“贞操是男女相待的一种态度,乃是双方交互的道德,不是偏于女子一方面的。”[30]“女子没有男子应守以外的法律。‘三从’‘贞操’,不是人人所承认的公理,因为女子不是男子的奴隶,所以不应该叫女子从父、从夫、从子,更不应该女子贞节,而男子得重婚再婚。”[18]最后,他们提出了女子人格健全的标准,即“崇尚实际人格不慕虚荣;研究真实学术,具世界眼光;真诚热烈之心胸;优美高尚之感情;强健活泼之体格”,并指出要实现中国妇女人格的健全发展,一在使妇女与男子受同等的教育,习同等的知识,以促进妇女自心之觉悟;二在破除男子轻视女子的心理,使妇女享政治上社会上同等权利,以“求男女人格之平等”。只有这样才能养成人格健全的男女国民,才能建成理想的“少年中国”[29]。此外,少年中国学会还强调妇女解放问题要由女子自己来解决,不应当依赖男子,呼吁全社会的妇女团结起来,自己起来解救自己。“若要解决女子教育问题,仍须女子自身起来解决,不是男子所能代庖的。一则因为男子脑筋中大多数充满了升官发财的念头,绝无余力顾及女子教育。二则因为男子怕女子受了教育,自己便专制不成。”[6]学会会员周炳林还指出,已受高等教育的妇女要担起指导和启发一般没有受高等教育及完全没有受教育的女同胞的责任,这样“时间久一点,全国的妇女就能团结起来,对于一切不好的旧制度行总攻击,那时完全解放一定能够成功”[31]。
三、少年中国学会妇女解放思想的影响
(一)扩大了少年中国学会的社会影响力
《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作为少年中国学会的两大机关刊物,前者注重“文化运动、开发学理、纯粹科学”,后者侧重“实际调查、叙述事实、应用科学”[32],两者分工明确,互为补充,是少年中国学会重要的发声载体。一方面,学会会员在月刊上发表文章,表达自己对妇女问题的意见和看法,引起了部分社会民众的共鸣。“我近来看了贵会的少年中国月刊第三期,佩服的很,并且知道诸君对于妇女问题是很注意的,这真是我们人类的一线曙光呢!”[33]另一方面,《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发表的文章也被五四时期一些社会影响力大的重要报刊杂志大量转载。如:“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选读’栏里选录了《少年世界》‘妇女号’上的许多文章,如甘乃光的《岭南大学男女同校之历程》、沈泽民的《妇女主义的发展》、杨寿珣等翻译的《女子教育进步小史》、杜威夫人的《美国的男女同校历程》等等。”[34]这些都极大地扩大了少年中国学会的社会影响力。可以说少年中国学会能够成为五四时期影响力最大的进步社团之一,离不开这两大机关刊物的有力支撑。
(二)促进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少年中国学会积极参与五四时期关于“大学开女禁”“男女同校”和“社交公开”等问题的讨论,对我国女子教育的解放和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少年中国学会不仅亲自邀请蔡元培、胡适、杜威及其夫人等社会知名人士撰写文章或召开座谈会,公开谈论大学女子教育问题,还在《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四期刊登了胡适关于《大学开女禁的问题》的文章,在《少年世界》第一卷第六期刊载了南京分会会员与杜威教授的谈话,公开支持大学开女禁。同时,学会会员还在各地成立了女子工读互助团,宣传男女教育平等思想。
此外,少年中国学会还积极介绍欧美、日本等国推行女子教育的先进方法和办学经验,推进大、中、小学的教育改制。如:《少年世界》专门介绍了美国女子大学、日本帝国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学校实行男女同校的历史进程,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为全国大学推行男女同校提供借鉴。1920 年2 月,北京大学招收王兰、邓春兰、杨寿壁等九名旁听生入学,开近代中国大学招收女学生的先河。随后,全国各地的学校纷纷效仿,陆续开始招收女学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长期以来男女教育不平等的状况,推动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这其中,少年中国学会的大声呼吁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推动了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进程
《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作为五四时期社会影响力最大的报刊之一,其“妇女号”专栏,内容异彩纷呈,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对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许多妇女在少年中国学会的启发下,开始认真思考妇女解放的真义,脱离封建礼教的束缚,参与社会活动,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话语权。有的在《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上发表文章,呼吁女子团结起来自己解救自己,如:1919 年7 月,邓春兰在前往北京前写了《告全国女子中小学毕业生同志书》,呼吁妇女通过自身奋斗来争取男女教育平等。有的创办学校或在学校里担当教员,普及女子教育。1916 年向警予从周南女校毕业后,怀着“妇女解放”和“教育救国”的抱负,回到家乡创办了男女合校的溆浦小学堂,并担任校长,聘请进步青年任教员。学校在她的主持下,规模不断扩大,由一个班几十个学生发展到八个班300 多人,培养了不少人才。还有不少妇女进入工厂做工,赚取劳动报酬,逐渐摆脱男子的经济控制,实现经济独立等等。总之,在少年中国学会的努力下,妇女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她们自发地组织起来,要求享受与男子一样的平等权利,有力地推动了五四妇女解放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
李大钊作为少年中国学会的创立者之一,同时也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率先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妇女地位低下的原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妇女被剥削、被压迫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李大钊以游猎时代、畜牧时代、农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时代男女社会地位的变化为例,指出“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是随着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动而变动的”[35]。他强调妇女不是生来就受压迫的,而是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物,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近代中国妇女地位低下就是中国封建大家族制度的产物。这种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它以男子独占生产资料为特征,女子无经济权利,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封建伦理、名教、道德、纲常、礼仪等,保证了男子在家族中的优越地位,导致中国广大妇女日益丧失独立性,沦为男子的附属品。因此,妇女解放首先要解决经济问题,“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36]这是实现男女平等的第一步,根本途径是废除私有制。只有彻底废除压迫妇女的私有制,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保证妇女的经济政治权利,才能真正实现妇女解放。李大钊把中国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不仅进一步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理论,也为中国的妇女解放找到了新的道路。
少年中国学会作为五四时期一个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社团,聚集了当时中国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通过理论探索和实践活动,传播了马克思主义,部分会员成为了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1921 年10 月16 日,少年中国学会为了学习、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思潮,专门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社会主义研究会。学会会员毛泽东、邓中夏、刘仁静、赵世炎等人作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发表和翻译了一大批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