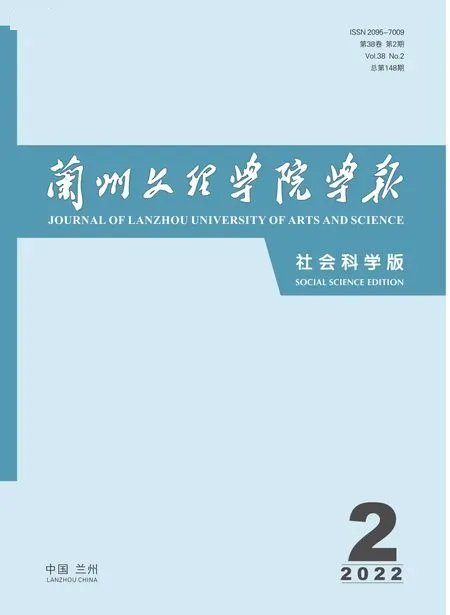民间信仰映射下的中国影戏角色行当
陈 旭 龙,陈 旭 凤
(1.白银市平川区经济合作局,甘肃 白银 730913;2.白银市平川区档案馆,甘肃 白银 730913)
作为中国戏曲的重要分支,中国影戏自诞生形成起,就具备了强烈的戏曲表演特征。按日本学者狩野直喜所述:“凡中国戏曲,乃由歌舞而演故事之谓也,其至少须有以下之要素:唱(含白)、乐、科(舞)及剧情。具备上述之要素,方可谓之戏曲。”[1]正是由于影戏表演具有的戏曲唱腔、音乐伴奏、影人操纵及其依剧本程式展开的故事化表演过程,使影戏成为了中国戏曲的重要组成。
21世纪伊始,随着国家层面对传统民俗文化的关注,特别是2004年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起,关于中国影戏的研究重新回到大众视野。众多学者、专家、传承人投身于对影戏的研究与保护工作。截至目前,在近20年的研究中,学术界普遍将影戏纳入了移植于戏曲的行当体系,忽略了影戏中长期存在的传统行当。造成了众多研究者过度关注于对源自戏曲的生、旦、净、丑行当的套用,忽视了对影戏本身固有的传统行当体系的挖掘与研究。现就两个体系分别做以分析。
一、移植于戏曲的行当体系
与中国传统戏曲行当体系的形成同步,影戏在其自身发展中,不断与各种地方戏曲融合发展、相互促进,在表演中引入了以生旦净丑划分的戏曲行当。
(一)移植戏曲行当的原因分析
在中国戏曲中,被经常提及的生、旦、净、丑(或生、旦、净、末、丑)各行当都有各自的形象内涵和一套不同的程式规制。每个行当也都有其鲜明的造型表现力和形式美。整体而言,中国的戏剧角色体制形成以明代为分界,明以前各角色名称并不统一,至明以后,逐渐被固定,历经明清之际的发展,才确立了生、旦、净、丑的四大行当。
在传统戏曲发展形成中,中国影戏始终参与,不曾缺席,其不断吸收接纳其中的有益成份以促进自身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历代影戏艺人都曾长期专注于对各种地方戏曲的吸收与借鉴。也使地方戏曲中依主流大戏划分出的生旦净丑角色行当有意无意间对影戏的表演产生着影响。但这也仅限于影戏表演中的唱腔念白、音乐伴奏、影人操纵三个方面,至于影人的雕刻制作、整理收纳则另当别论。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层面针对戏曲界的革新,成为影戏移植戏曲行当体系的一个主要原因。这对影戏从形式上被不断强化为与戏曲一致的生旦净丑行当起到了外力推动作用。以1951年,由当时政务院制定、周恩来签发的《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即《五五指示》)为标志,在其推动下展开的“改戏、改人、改制”的三改方针下,中国戏曲在国内取得了新的发展,各剧种均呈现出了百花争艳、竞相发展的盛况。同期戏曲院团化的转制,使影戏与众多地方戏曲一起被纳入了统一的管理体系,这无形之间促使影戏与戏曲在体制中产生了更多的关联。而当时“大戏为主、小戏为辅”的主导思想,和大戏流派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加速了影戏向大戏的靠拢过程。在“被动”参与和主动借鉴中,戏曲行当体系进入了影戏表演范畴。
(二)戏曲行当在三大影系中的差异表现
移植于戏曲的影戏行当普遍按照生旦净丑做出了划分,含义运用上虽与大戏一致,但具体至不同地域时,因地方习俗和艺人称谓习惯的不同,并未形成统一的标准,该体制在不同地区的发展和运用存在不平衡现象。以陕西、甘肃、河南、河北、东北地区、广东陆丰、台湾为例,会发现这种不统一的情况较为明显。
以中国三大影系之一的陕西影系为例,其流布区域内的河南、陕西、甘肃便存在这种不统一的情况。以河南豫南罗山为例,其影人行当总体上分为生旦净丑4类。生行包括了老生、三生、小生。其中三生、小生又分出文、武2行;旦行包括老旦、花旦、闺门旦、丑旦4种;丑行包括官府丑、老丑、小丑、杂丑4种;净行的分类则在不同班社有所区别。其一类包括苍净、大净、丑净3种;一类为大杂、二杂2种,但又在大杂之下分出了奸净、正净、杂净、丑净。同属河南的灵宝地区则与之不同,其同样以生旦净丑做了划分。生行包括了正生、贫生、富生、武生、官衣、帅盔、小生、老生、道生、奸臣、忠臣11种;旦行包括小旦、老旦、丑旦、花旦、武旦、么旦6种;净行包括大花脸、二花脸、三花脸3种;丑行则又有老丑、小丑2种。
而与灵宝相邻的陕西渭南,在影戏行当划分上与之类似,也划分为生旦净丑4个行当,但在生、旦的分类上有所区别,其生行包括了文生、武生、小生、老生、三绺5种;旦行则包括了小旦、老旦、花旦、丑旦、道姑旦、贫小旦、官小旦、富老旦8种。同属陕西的宝鸡,由于其与甘肃相邻的原因,在行当划分上又出现了差异,在生旦净丑四大行当之下,生行包括了须生、小生、头把须生、二把须生4种,其中的须生被列为独立的一行。旦则有青衣、花旦、闺门旦3种;净包括大花脸、二花脸、三花脸3种;丑分为大丑、二丑、小丑3种,分类上较前几个地区较为简单。
在滦州影系中,其流布区域内的冀东、东北地区,影戏角色行当被划分为生、小(旦)、大(净)、髯(老生)、丑5类,其中旦角下又分为正旦、闺门旦、花旦、老旦;生角下分为小生、文生、武生、花生;髯则特指老生;净角包括黑头、毛净、怔净子3种;丑包括小丑、老丑2种。而在河北承德,在丑与髯的划分上则更加细化。其髯角被细分为文髯、开髯、骚髯、三尖髯、五绺髯、长满髯、老髯7种;丑角则细分为文丑、武丑、贼丑、邋遢丑、民族丑5种,而在文丑之下又细化为老丑、小丑、衣冠丑、官带丑4种,与东北、冀东对髯、丑的划分相比更为繁复。
在潮州影系地区,因其早期盛行纸影及属闽南语系区域的原因,与滦州影系、陕西影系又产生了不同,以当下存在影戏的广东陆丰和台湾地区为例,其行当包括了生、旦、公、婆、净5类,其中公特指老年男性,婆专指老年妇女。
二、影戏固有的传统行当
由于中国影戏流传的历史性,在漫长发展过程中自身形成了一套完备的行当体系,这主要表现在传统影戏艺人在影人制作、表演前的影人摆放,日常对戏箱的整理收纳三个方面。在这三个阶段,他们均会按照区别于生旦净丑的传统角色体系进行分类。在影人制作之初,艺人们便会对影人进行角色分类,多按照世代传承的画谱作以区分。除了对戏箱中破损的个别影人道具进行正常的修补替换外,他们会按照一个完整戏箱所需影人的数量标准去规划制作。这种从一开始便谋划的过程也是与后期的表演使用、戏箱的整理收纳连为一体的综合考量,其本身便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系统。
(一)传统行当体系的历史变迁
中国影戏的传统行当蕴含了早期戏曲转化过程的残留,对它的研究可以一窥早期戏曲的特点。通过对两宋之际文人笔记的研究会发现,宋代的影戏人物包括了小将、架前、茶酒、杂使公、马军5类,该分类迎合了当时社会动荡的现实,而上演剧目也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相一致。加之两宋城市经济的发展,大量失地人口涌入城市,推动了城市娱乐业的兴起。以南宋出现的勾栏瓦舍为代表,为包括影戏在内的各类民间戏曲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明清之际在统治层的刻意推广下,影戏取得了较宋元之际更为宽松的发展环境,该时期从剧目创作到影人制作直至地方唱腔的形成,均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以致我们今日所见的众多古代影戏实物均由该时期遗存而来。
关于民国时期影戏行当的分类,以20世纪初顾颉刚的《中国影戏略史及其现状》为代表,其对当时影具的收纳论述为:“今考其存储法,乃先分二大部,一为大篇幅之布景及特别之彩切等,一为演员及服饰等,其演员之部又约为十二小部,名曰十二包。”[2]这里明确说明影戏“人物”包括了演员及服饰两类,而演员则以影包的形式分类存放。其所见到的影包内按人物身份地位分为帝王、纱帽相貂、文生员外、文女、将帅、武生、武女、反王、下手(龙套)、吉祥人物、神仙11个类别,另外,桌椅、刀枪之类单独存放于一个包装,共计12包。这里顾颉刚所描述的影包尺寸较大,可将影身、头茬一同装入,而当下甘肃乡村艺人仍在使用的影包仅可将头茬纳入。“此处所谓包,乃用厚纸糊裱而敷以布之夹子,长约一尺五六寸,宽半之。中有隔叶二,是以一包有相等之夹子三。其当中一部放置影人之身部,因每一影人身部下俱附有三只铁丝及细菽术杆而至上下薄厚不同,放时乃相互颠倒其位置。其本包影身所需用之首部则略分公忠、奸邪二类,而分存于其旁之二部。放法亦与身部同。”[2]126通过这些记录于20世纪30年代的文字,可以对当时北京影戏角色行当的划分有所认识。
(二)建国以来影戏发展的四个阶段
自1949年以来,中国影戏的发展与传统戏曲一致,经过了1949—1965年的繁盛期,1966—1976年的曲折期,1977—2003年的振兴期,2004年至今的转型期四个阶段。
其中1949—1965年繁盛期的出现是对清末民国以来发展的延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1966—1976年特殊历史时期的破坏之下,依照样板戏产生的新式影人与剧目也颇具时代特色;1977—2003年随着中国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戏曲表演得以恢复并进入了振兴期。该时期一方面是在继承传统中恢复了前期的成就,另一方面是在不断革新中尝试了探索和创造。在影戏上,前期被破坏的剧本、影具迅速得以恢复;一批早期著名的老艺人重新回到本行;早期的表演、制作程式得以延续;各地乡村中与民俗相关的各类影戏活动得以延续;一大批中青年从艺者开始走上前台,实现了新老交替。
进入21世纪,以2004年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为标志,中国开始了对各类民间艺术形式的全面挖掘与保护。该时期适逢中国经济高速崛起的新时期,伴随着国内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千百年来传统农耕文化孕育下的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依存于传统农耕文明存在的影戏,也面对了新的挑战。在社会转型之际,对中国乡村的定位和与之相伴的各类民间艺术的发展走向,成为各领域持续关注的焦点。自2004年起至今,可被视为影戏发展的转型期,该时期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持续存在于中国社会。
(三)地域分布对影戏传统行当的影响
拥有2000年历史的长城将中国境域内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做出了分割,长城沿线以南的范围,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农耕文化区域,在这一区域内生存的群体,拥有着共同的人生观、价值观,遵循着相同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人工修建的长城成为了中国影戏分布地域的参照,在该线以南的所有区域,早期均有影戏的存在,而以北的东北、内蒙、青海河湟影戏的存在,可视为特殊历史时期出现的民族融合的结果。即中国影戏产生于黄河流域的陕西、甘肃地区,随着历史的发展及中国政治经济重心的不断南移,向南向东转换中心区域,形成了以陕西西安、河南开封、浙江杭州、河北、北京的转换过程,其中包括了辽宁沈阳这一在明清之际满清兴盛之地发生的影戏逆向传播。
结合陕甘地区在清代之前行政区划未予分割的历史,通过比对中国版图的变化就可发现,作为早期黄河文明发源地的陕甘地区在漫长历史进程中,随着两汉以来经济重心的不断南移,长期作为中原农耕文化抵御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入侵的前沿所在,而自先秦以来不断延伸修造的长城伴随了这一历史过程。
先秦时期北方为乌氏、胡,西方为犬戎、羌所包围,虽有长城相隔,但连年战争不断。秦汉之际秦统一中国,但北方为匈奴、乌桓,西部为乌孙、羌、月氏、氐等少数民族所环绕。两汉之际北方为鲜卑、匈奴,西部为乌孙、大宛、龟兹及羌包围。唐代中期,来自北方的威胁变为突厥、靺鞨,西部的吐蕃。北庭都护府、安西都护府的存在使西北实现了相对的安定。北宋、辽、西夏时期,西夏势力范围一度扩展至宁夏、内蒙、陕西、甘肃、山西南部。辽占据山西大同、河北、北京及东北全部。北宋在西夏、辽的压力之下不断收缩。南宋则受到来自北方金、西夏的威胁偏安长江流域。直至明清之际,疆土才实现了相对的统一。而明代来自北方鞑靼的威胁仍旧影响着宁夏、陕甘、山西、北京一线的安危,明建立的九边防御体系,使陕甘长期处于西北边陲的境地。至清一代,则近代以来的中国版图格局基本确立。[3]而陕甘地区至此也正式脱离了自古处于边地的历史。
由此可以认为:古代中国以长城作为两种文化区域的分界,其南部属农耕文化区域,北部为游牧文化区域,长期以来,处于其中的陕西、甘肃成为了这两种文化的胶着之地。
长城沿线社会动荡的现实也在该地域传播的影戏中得到了映射。在陕西影系传播区域影戏中有两类特殊的角色——番和网值得注意。其中番角的出现,为该地域长期处于战争夹缝的写照,网角的出现则从另一个角度强化了对正义战胜邪恶力量的追求。这些蕴含了早期影戏特点的角色得以保留,也是陕甘地区作为中国影戏发源地的明证。作为与南宋临安相接的浙江海宁,其影戏表演中的中原官话残留,亦成为宋室南迁时政治被动下的产物。“《浙江风俗简志》中录‘海宁皮影戏’条目提到:海宁皮影戏起源于南宋,为我国南方皮影戏中独具一格民间艺术。据传是南宋建都临安时由北方皮影戏艺人流入杭州而演变形成。”[4]该情况正如顾颉刚所言:“中国影戏之发源地为陕西,自周秦两汉以致隋唐当皆以其地为最盛。宋以后方盛兴于河南,自后其最盛之地即随帝都而转移。……此盖由于各地皆有特殊之风俗技艺,以致同源之影戏,及染地方色彩以后遂呈极大差别之现象也。”[2]135
(四)民间信仰映射下的传统角色行当
除了自先秦产生的巫文化遗存外,神仙、妖魔鬼怪角色的设立则反映了该地域内的群体对其生存环境的抗争,其更易通过借助民间信仰来寻求对平安幸福生活的期盼。
在陕西影系分布区域的甘肃陇东南地区,与前文所述移植戏曲的行当不同,传统艺人按文、武、旦、王(帝王)、耻(奸臣)、番、神、道(出家道、僧、尼)、妖、鬼(阴间冥府)、网(不戴冠冕的囚犯、败将)将影人划分为11类。[5]而同属陕西影系流布区的河南豫南地区,则包括了生、旦、王帽、纱帽、貂尾、帅盔、扎巾、神仙妖怪8类。这里的生、旦均细分为文、武两类;王帽则包括正王、反王两种;帅盔与扎巾也分列为正、反两种。两地相对比,区别最大的分类体现在对神、道、妖、鬼的不同划分上。甘肃陇东南地区,因其境域陇南为先秦发源之地,陇东与陕西相接之故,两地民俗风貌均与自秦汉以来形成的传统紧密相关,在同属黄河流域的特殊地域影响下,两地在文化上具有了诸多相似之处。被豫南地区归为一类的神仙妖怪在甘肃予以单列,可视为在形制上保留了影戏更多祀神功用的原始风貌。而其在影具中存在的大量神怪题材影人,也与早期影戏劝人向善的民间宗教信仰相互配套。而道角色的单列则可视为早期影戏与佛教、道教相互利用的遗存。
与陕甘地区强化了早期祀神功能一致,处于湘水流域的湖南衡山地区,早期与道教关系紧密,其境内因有五岳之一的衡山,自秦汉以来便享有特殊的政治文化地位,其间生存的群体经济生活富足,政治相对稳定,但因受楚文化影响深重,域内影戏虽然为后期传入,但仍然保持了众多早期文化特征。①以其境内影戏为例,包括了工、农、商、学、仆、术、地、天、释、道、妖、侠、贫、富、宫、王16个行当。其中除工农商学明显为1949年之后受戏曲改制影响而设立外,其余12个行当均为早期传承而来。尤以其中的仆、术、地、天最具楚文化特点。作为湘水流域的重要宗教活动场所,在佛道教与楚文化融合下,其保留至今的角色体制中早期祀神功能的人物以仆、术、地、天的形式得以独立出现。
清代以来兴盛于北方的滦州影系延续了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记录的行当分类传统,其影人包括了生、旦、将帅、反王、官纱、王帽、神仙、妖怪8个类型。而生又细分为武生、文生;旦包括文旦、武旦;官纱、王帽有时也一并归入官王。其中官纱多指三品以下官员;王帽则包括了丞相、太子、皇帝三类人物。另外神仙、妖怪有时也会归入神妖一类。这些情况虽各地有所区别,但并不影响其大的分类标准。而同属早期滦州影流布主要区域的北京西派皮影,则有些许变化,其分类包括男、女、神、卒、文、武、杂7类,较之以前,看似简化,实则一脉相承。
三、两种角色体制并存在功用上的差异表现
中国影戏存在的两种不同的角色体系共同存在并相互影响,一同促进了当下中国在社会经济、文化转型时期影戏的发展与传承。但在具体功用上,也呈现出了一定的差异化特点。
(一)戏曲行当体系对影戏人物造型及表演的推动
1.戏曲体系对影人造型程式的影响。由戏曲移植而来的生旦净丑行当体系主要运用于艺人对影人操纵、唱念表演之中,其在实际运用中直接影响到了影人造型的变化。作为套用的戏曲体系,影戏艺人借助戏曲的繁盛发展,合理吸收传统戏曲中对生旦净丑各行当人物的塑造特点,将其运用于影人的雕刻设计,对早期传承而来的影人程式化造型有所突破。
在整体上遵循“正貌与丑形”这一传统影人造型观念的基础下,在形体上的“创新”也体现在制作时对影人的着色设计。与早期制作中生旦净丑脸部造型区别不大的情况不同,戏曲体系的引入,使仿照大戏脸谱化的色彩运用于影人面部敷彩。其敷色多以红、黄、蓝、白、黑5色,后由于蓝色会随时间长久变暗发乌,便以绿色替代。即形成了红、黄、绿、白、黑的5色规制。在程式化造型雕刻与不同属性色彩的结合使用下,更易于人物性格特征的表现。其以红色表示忠勇义烈;黑色表示刚烈勇猛或粗率鲁莽;黄色表示刚强粗犷,骁勇或桀骜不驯;绿色表示刚勇、强横、猛烈暴躁;黄色表示剽悍、凶残,工于心计;白色表示阴险狡诈。其中代表性人物红色如关公武勇,黑色如包拯公正廉明,绿色如程咬金鲁莽暴躁,黄色如宇文成都彪悍残暴,白色如曹操奸猾。具体制作中,色彩的使用与雕刻相互结合,共同构成了影人造型的程式,而不似戏曲脸谱单一依靠色彩来实现。关于影戏人物的服装冠戴,是人物身份地位的重要体现,不同人物的身份地位,通过配套的服装穿着加以区分,而对舞台戏曲的借鉴,使戏曲服饰样式与纹饰得以进入影人造型。作为影人头茬的重要组成部分,冠戴的运用与服饰的合理搭配,塑造出了不同身份地位的人物,这里如武将的盔,帝王的冠,书生的帽,官员的纱,均成为所处时代相关特定阶层人物的标志。
2.戏曲体系对影戏表演的影响。影人脸部造型的程式化、色彩运用的程式化、服饰冠带的程式化一同构成了中国影戏人物造型的程式化特点。另外,影戏与戏曲间的这种互动,促使影戏伴随戏曲发展,艺人们注重了表演中对戏曲唱腔、音乐、角色身段三方面内容的吸收与模仿。
在唱腔上,注重吸收各种地方戏曲、民歌、小调艺术形式的同时,按照戏曲生旦净丑行当,影戏艺人也会做出区分,以使自身的表演更具吸引力;在音乐上,大戏乐器的丰富性为影戏所借鉴,两者在很多时候会发生交融。而伴奏乐器的不断丰富,也会促使艺人在唱腔上更加丰富,即通常提及的“唱念做打”中的“唱、念”。因戏曲表演是以歌舞演故事,其唱念为戏曲表演的音乐化。为强化各角色的表现力,关于影人操纵,主要反映在对戏曲表演中“做、打”的模仿,即戏曲表演的身段化。艺人们正是通过对影人的熟练操纵,以表现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与心理活动。而做、打在影戏中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其剧目中存在的大量武戏,这可视为最直观的动作展示。同时在文戏中,艺人对影人喜怒哀乐情感细节的把握则更具艺术性。依靠仅有的三、四根操纵杆如何更好地表现出角色在剧中复杂的心理活动,这也为艺人的技艺提出了挑战。在看似程式化的翻转操纵下,生的阳刚、正气,旦的娇羞、贤柔,净的勇猛、奸诈,丑的滑稽、调笑均得以在咫尺舞台展现。
(二)传统行当体系的民俗表现
传统行当体系是从影人社会地位、身份做出的区分。其作用体现在起始阶段的影人雕刻制作和收尾阶段的影具整理收纳,即所谓首、尾两处。另外还作用于剧目的编创。
1.对影戏剧目编创的推动。由于影戏表演时的程式化,使得艺人可以很容易依据传统角色行当实现剧目的编创。在传统影戏学习中,师徒制的传承特点使每位艺人均须接受长期的训练才可出师,而影戏表演中对不同人物的上场、定场、下场均有程式化的用语、口白;在表演中只需构架大的故事发展脉络与人物关系即可实现对剧情的编排。期间艺人们只须从记忆中抽取看似零散杂乱的人物唱词、道白运用于对应人物,即可实现表演。另外,前场与后台伴奏常年形成的默契配合,也使伴奏音乐的程式化成为了可能。以湖北云梦地区影戏茶馆艺人对提纲本的使用为例,当地艺人表演时使用的剧本形式普遍为与提纲相似的故事梗概,仅显示大的故事线索或出场人物,但经过艺人的创排,可以实现长篇剧目的连续上演,其剧目多为《杨家将》《岳飞传》《三国演义》《陈桥兵变》《西游记》《水浒传》等。正是由于人物唱词与伴奏音乐的程式化,才使当地艺人得以实现对这些长篇剧目的常年上演。
2.影具整理收纳中蕴含的民俗文化特点。关于影具的日常整理,可以从甘肃通渭影子腔艺人对戏箱的收纳得到体现。通渭当地影人头身分离,其头部称头茬,身部为线子。头茬按角色行当分为将、神、旦、生、须、丑6类,其中生包括丑小生、水头(头发披散的罪谪之人)、生3种。旦包括武旦(头饰多有野鸡翎子,如穆桂英)、花旦(多指年轻女性),旦(中年女性,如秦香莲)、老旦(老年妇女,如佘太君)。须指有胡须的中年人,如《四郎探母》中的杨延昭。神角包括人物众多,如《封神》中的姜子牙,《三国》中诸葛亮、关公,神话人物如土地公等。还包括当地受道教影响下形成的所谓“三教”的专用人物。将则有2类,包括有头盔的将与头饰带野鸡翎的番王、番将等,均归于一类。另外丑角由于角色不多,一般与将一同收纳。当地对影人的收纳与前文顾颉刚所录北京旧时习惯不同,仅将头茬按角色收于头包之中,其所用头包有将头包、神头包、旦头包、生头包、须头包5类,丑与将安置于同一包。而影人身体部分则按武线子、文线子、跑线子(衙役等)3类分别整理。其中有一类服装造型为古代将军盔甲,谓之靠,被归于武线子一类。靠在当地分为普通人穿戴的靠和神靠两种,是按不同人物进行的区分。因其造型威武,也使用于《封神》故事个别神灵中,谓之神靠,该类影身在通渭当地常被视为具有庄重神圣的意味。至于一些小型道具,如神话剧目中的法宝,传统剧目中的圣旨等,则统一存放于一木制小罐保存。
3.关于影戏表演的各种禁忌。旧时艺人多在外演出30—40天后会返回家中,这个过程被称为一绺子戏唱完了。归家后的艺人便会在把式家集中演出一晚以答报神灵,之后才会对戏箱进行整理收纳。具体收纳时,人物头茬按角色类别分置于头包之中,人物影身(即线子)则按照6杆线子为一把的方式,按前后颠倒顺序一层层装入戏箱。其装箱顺序为:底箱(即箱底)为马、龙、虎、麒麟、鹿、驴等动物及地狱垛子等较大的影具,再依次按武线子、文线子、跑线子、头包、道具小木罐的顺序逐层装入戏箱。值得注意的是,按习俗,入箱时跑线子的腿部会以红色线绳拴住,以防止影人“活起来”,而这在当地也被称之为“卧箱”,直到下次外出前才会解开绳索。整个装箱过程谓之“匣箱”,即收纳影具关箱。收纳影具的戏箱当地人称之为线箱,另一个收纳乐器的戏箱为家伙箱,两者合称戏箱。②
戏箱因其祀神功能的原故,在当地艺人及普通群众中具有很强的神秘性及神圣化的特点,因此也围绕着戏箱产生了众多禁忌。如唱戏当日,艺人早上起来未吃干粮,乐器不可响动;晚上演出前,艺人必须穿戴整齐方可动乐器;表演时进入后台不能乱说话;亮子上不敢乱放东西;影人坐场后(演出时影人先出场)艺人才能上弦动乐器。而当应邀外出时,按当地风俗,戏班会在出发前先唱一晚,以示敬神;外出一般30—40日后演出结束返回家中,在把式家再唱一晚,以答报神灵护佑平安,这样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演出阶段。而正是由于影戏表演各阶段的高度程式化和其中蕴含的民俗特点,才使得影戏传统行当得以长久存在并不断传承。
(三)两种行当体系的应用规律
在影戏表演中,新旧两种角色行当共同存在并有其规律可循。这主要表现于影戏表演剧目的不同类型。在反映征东、征西、扫南扫北的征战题材剧目上,两者差别不明显。在以男性角色为主,神怪角色多的剧目中,戏曲行当成份较少,传统行当成份较重。而在表现婚姻爱情为主的剧目中,则以戏曲行当为主。该规律反映出了影戏作为祀神工具的功能化特点。主要是由于影戏相比舞台戏曲,更适于展现神怪故事。其演出时间多为黑夜,灯火阑珊之间,被灵活操纵的影人更适于表现对风雨雷电、神仙踏云飞升等效果的营造。这也就是神怪题材剧目在传统行当体系中占比多的原因之一。第二个方面,是自1949年起在中国传统戏剧的三改运动中,按照当时的改革政策规定,很多传统戏曲剧目将其中涉及到的神怪内容作了删减,革新后的剧目以故事性为主,少了传统信仰习俗的展现,而广泛分布于中国乡村的影戏,因其根植于传统民间信仰的原因,在当时的改革中并未触及根本,所以保留了很多的民俗信仰成份。
1.男性角色为主剧目对传统行当体系的倚重。以男性为主的影戏剧目,因其多表现传统价值观下的忠孝节义、礼义廉耻主题,宣扬仁义礼智信的传统道德规范,所以在剧目内容及表演上,更适合于通过传统角色体制去表现。该类剧目,帝王将相、贩夫走卒等社会各阶层人物,包括基于民间信仰构建的各路神灵均会出现。按照传统影戏的剧情程式,英雄人物多为男性,且每逢遇难均会得到神灵的救助,所以从本质而言,该类剧目与传统表演更为接近,也更适于通过传统角色行当加以表现。
2.婚恋题材剧目对戏曲行当体系的运用。反映婚姻爱情的剧目,因其多为才子佳人故事,戏剧生旦净丑的角色行当则更易于与其人物相对应。该类剧目表演中,传统舞台戏曲程式化的人物设置、唱腔表演,尤其是对女性角色身段及动态的表现,均成为影戏艺人乐于参照并主动汲取的创作源泉。在这种成功模式的借鉴之下,该类更善于表现男欢女爱的剧目,潜移默化间成为了以生旦净丑为主要行当标准的表现形式。
3.两种行当体系的共存。涉及征东征西、扫南扫北征战题材的剧目,因其剧目冗长、剧情复杂、情节曲折、人物众多的特点,该类剧目上演时间段多则数月,少至一月以上,所以在具体表演中,艺人既需要表现故事背景宏大,荡气回肠的特点,也要在每一次演出中强化出场人物的性格特点。在这种既要依照影戏传统体系把控戏曲剧情发展走向,又要在每一幕中刻画人物细节的需求相互作用之下,无意中形成了两种体系的共同存在,而影戏表演中惯常运用的一场文戏、一场武戏交替上演的文武相间戏曲程式,无形中便形成了在该类剧目中两种体系占比相当情况的出现。
四、结语
中国影戏传统角色体系的建立,具有历史传承的特点,其自影人雕刻伊始,便按照历代传承的角色体制展开制作,该体系中对“人物”的头、身及影人社会地位有严格的划分标准。对其角色行当的研究,可从对影人头包的分类保存入手。即依照艺人对头茬的分类保存可一窥其划分标准。这里面,神、道、仙、妖、鬼、怪占据了很大的比重,而这部分影人,正是影戏在早期得以存在的基础。当下学界将研究重点过多放在了迎合戏曲的行当划分上,有本末倒置的嫌疑。生、旦、净、丑行当是依传统戏曲发展而做出的划分,其本身存在一个被动“去其糟粕,留其精华”的过程,其中涉及到的早期表演中出现的神怪陆离场景与人物已被剔除。这里的剔除包括了从剧本、舞美、角色设置上整体进行的优化选择。加之1966—1976年特殊历史时期对戏剧舞台的影响,早期戏曲中的很多有传统民俗文化特征的内容已成为历史尘埃,我们也无从去了解之前的状况。影戏作为自1976年之后重新被唤起的“新戏曲”,其只能被动地依赖被反复删减过的行当去演绎故事。这也就使得当下对影戏的研究会产生偏移,忽略了对其本身固有传统角色行当的关注。当下对影戏角色行当的研究,应该建立在关照两种体系并存的基础上全面展开。
【注释】
①湖南衡山地区影戏相传当为清顺治初(1644)由彭凤举带入,经历了由纸影向皮影的转变。
②该节头包的角色分类内容来源于2021年11月对通渭影子腔市级传承人杨永忠的访谈。其家族将角色分类为:将、神、旦、生、须、丑6类。而同期经过与通渭影子腔国家级传承人刘满仓的沟通,其家族按头包将角色分为:官、生、旦、番、奸、神6类,线子分为官衣、旦、袍子、跑线子4类。可见当地艺人对角色的划分在总体框架下,会按照个人使用习惯的不同而产生差异。
——以1907—1921年《东方杂志》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