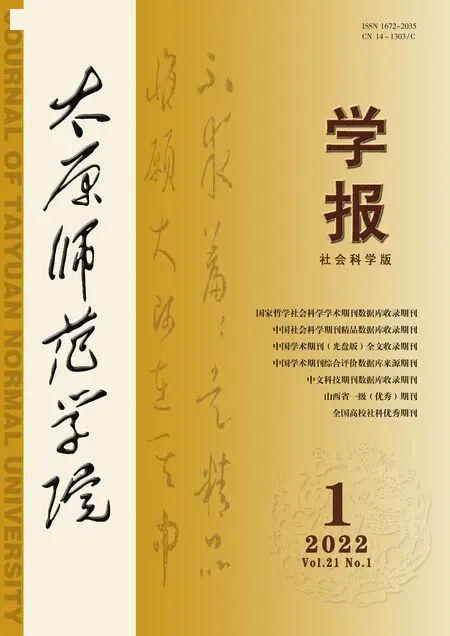“边缘空间”:论费德勒文化批评的空间指向
傅婵妮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20世纪末,有关“空间”的跨学科研究崛起,空间被从时间与历史编织的牢笼中解脱出来,被视作分析问题的本体,其价值与内涵被重新发现。空间被赋予了深刻文化意义的同时,也为文化研究的推进提供了新维度。美国文化批评先驱莱斯利·费德勒(Leslie Fielder,1917—2003)是后现代的领军人物之一,在其文化批评实践中,频频从边缘空间向中心发起挑战,拒斥传统与保守,倡导开放与多元,在边缘空间构筑起其独特的文化批评的空间景观。但目前国内对费德勒文化批评的研究尚不多,相关研究主要是从时间维度展开,用历史的眼光评论其文化批评,或探讨他对种族与性别问题的关注,或分析他对大众文学与文化、神话批评的兴趣,或解析他的文化批评的特点,或阐释他对某一经典名著独特的解读。本文将从空间维度解析费德勒的文化批评,试图为理解费德勒的文化批评提供一种新视角。
一、费德勒与他对边缘空间的倾注
费德勒的研究常引领时代精神,被誉为美国当代文化批评的先驱。费德勒生于新泽西州最大的城市纽瓦克(Newark)的一个犹太移民家庭,从小对犹太传统文化耳濡目染。后来,他随家人移居到了犹太人稀少的东奥兰治市(East Orange),并在该市继续其学业。但因他的同学多信奉清教与天主教,集体中产生的排犹主义使他被边缘化,这让他一度非常苦闷。少年时,他还在叔叔的鞋店帮忙,通过这份兼职,他不但对黑人有了更多的了解,与黑人同事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还广泛接触到了更多来自底层的劳动人民,对他们的生存状态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加上当时美国正经历经济大萧条,来自社会底层人民的困苦生活令他印象深刻,这催生了他青少年时期对社会主义的憧憬,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他在日后的文化批评实践中始终对身处边缘空间的个人或群体倾注了更多的热情。
边缘这一名词本身就指涉了一种空间位置,是界定空间的参照之一。复兴空间维度的主要功臣之一、法国社会理论家列斐伏尔认为,边缘不仅是地理学意义上区分空间位置的概念,其本身也构成了一种空间存在的特殊形式,即“边缘空间”。边缘空间不但是某种独特的空间类型,而且还体现出属于该空间区域的文化心理诉求、话语、权益、感受力等诸多特征。
费德勒在其文化批评中研究发现,“边缘空间”是美国经典文学故事时常发生的地理空间,并在《回到竹筏子上来吧,亲爱的哈克!》《美国小说中的犹太人》《美国小说中的爱与死》《厉声说不!》等诸多评论著作中对美国经典文学作品中的“边缘空间”进行了研究,“边缘空间”成为了其文化批评实践中的空间指向。在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人文地理学兴起前、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1974年)出版前,费德勒的文化批评就具有了空间性,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提出“后现代就是空间化的文化”这一观点也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了。由此可以说,费德勒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为20世纪末学界历经的“空间转向”发出了时代先声。
费德勒指出在《哈克历险记》《白鲸》《红色英勇勋章》等美国经典作品中,男主人公均逃往某一“边缘空间”,在那里续写或实现某种未完成的梦。“纯洁的大自然——这是男性神圣婚姻不可避免的背景。以实玛利和奎奎格手挽着手,准备出海,哈克和吉姆在密西西比河平静的木筏旁游泳——是水的流动完成了孤独漂浮着的美国梦。”[1]9他还指出,在库珀的皮袜子系列故事集中,原始森林不仅是故事展开的地点,也在小说中有着类似于以上提及的作品中的海洋、河流同样的寓意,参与着故事意义的建构,因此他强调要特别注意森林和大海前的形容词。不难发现,“原始的”或是“不可侵犯的”这些修饰名词的形容词,都含有少有人参与或干预之意。在以人类为中心的都市不断形成并扩张、都市文明不断发展与繁荣的背景下,原始森林、大海等地理空间便是相对于都市文明的“边缘空间”了。他进一步发现,“边缘空间”在美国小说《瑞普·凡·温克尔》中具有标志性意义。在该小说中,温克尔去往了又一“边缘空间”——山林喝仙酒,并发生了穿越时空的故事。他认为继《瑞普·凡·温克尔》之后的美国小说,无论是《白鲸》还是《两年水手生涯》等都叙述了主人公离开都市文明转向荒野的故事。在费德勒看来,大海、森林、河流等荒野——“边缘空间”是美国经典文学故事不断上演和续写的重要空间,即使在美国当代的文学作品中,诸如戈尔·维达尔的小说中,主人公也和他最亲密的朋友一起逃到了海边。
“空间”不仅是地理学或几何学的概念,根据列斐伏尔所言,还是社会空间的社会生产,这便指涉了人在空间中的主体性行为与活动。“空间”与身处空间的人的行为融成了一种社会生活的经验,空间也是“社会空间”。由是,“边缘空间”与身处其中的人难分难解,且是体现边缘群体心理特性与变化、精神状态以及身心体验和生存经历的空间。
费德勒长久痴迷于被边缘化的人。边缘人是费德勒文化批评关注的主要群体,他也用“外人”(the Outsider)或“陌生人”(the Stranger)、“他者”(the Other)来指涉。他说:“我一直沉迷于陌生人、外人的形象,他们的形象体现在小说所描绘的他者中。也就是说,我集中关注美国盎格鲁-萨克逊新教白人(WASP)所写的小说或诗歌中的黑人、犹太人和印第安人的神话”[2]189。 但实际上,除了以上提及的边缘人,他关注的边缘人还包括青少年、女性以及怪胎在内的身体异常的人。他在文化批评中研究的边缘群体,囊括了美国社会中的不同种族、性别、阶层,甚至是残障人士。
费德勒的文化批评,以边缘空间—人—社会—历史的思路展开。他将种族、民族、性别、阶级等问题与个体或群体所处的边缘空间勾连起来,研究处于边缘空间中的人的文化状态、政治权利诉求与他们被忽视的感受,从处于边缘空间的人而非处于中心的人来探析、定义“人”。需要指出的是,费德勒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的文化批评既有一种历史维度,又具有对现实的批判眼光。因此,他的文化批评是融时空两维度于一体的,其文化批评也并非像他之后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学者那样将空间摆在一个十分显眼的研究位置。这也说明20世纪后半叶的“时空转向”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费德勒是较早参与这一过程的学者,他对边缘空间的研究起到了引领的先锋作用,又扮演了在空间成为主导之前向空间转向的这一过程中承前启后的角色。此外,费德勒对边缘空间的关注,或多或少与他犹太人的身份有关。他谙熟排犹历史,也经历过被边缘化的过程。他结合自己在边缘空间的体验,从边缘空间向中心发出挑战,为处于边缘空间的群体发声,实则也是他对于生存的一种深刻的内心体验。
二、边缘空间中的文化心理诉求
文化与空间密切相关,文化的生产均是在一定的空间中进行,不同的空间势必孕育出不同的文化。边缘空间与中心地带是辩证的一组空间位列。边缘空间生产的文化和中心地带生产的文化,与边缘和中心的辩证关系对应。边缘空间总是相对于中心地带而言的,中心地带若发生变化,必将波及和影响边缘空间。中心地带是权力中心,主导着空间整体秩序的位列与位移,中心地带生产的文化是社会主流文化,主导社会的文化风向。边缘空间,远离中心,虽被中心地带所主导,但常遭到忽视、冷落,甚至遗忘。边缘空间的文化势必受到主流文化的控制与影响,被主流文化排挤和压迫,其价值也得不到承认与认同,从而沦为“他者文化”,边缘空间亦成为“他者空间”。关注“边缘空间”,能够揭示出潜抑在统治秩序深层的盲视,发掘被排斥在中心秩序和既有历史阐释之下的价值观念、民族心理、文化心理诉求等。美国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索雅认为,空间不仅是具体的物质形式,还是精神的建构,可以表征出生活的意义的观念形态。
据索雅的空间表征观念形态,“边缘空间”为何是美国经典文学故事反复上演的地理空间?它表达了何种观念形态与文化心理诉求?因深受弗洛伊德的影响,费德勒的文化批评倚重精神分析,这为他提供了一把洞悉文本世界精神建构的钥匙。
美国经典文学中的“边缘空间”,常是少有人侵扰或未被开发的大自然。大自然原始的状态,仿似婴儿,拥有未经世事的天真、纯真。在原始的大自然中,一切都是原初模样,人处其中,也摆脱了都市的复杂纷扰,回归到了单纯、简单。“边缘空间”隐射了美国作家向往纯真,渴望回归天真的文化心理诉求。费德勒认为,美国生活的回归,在于其对婴孩不可抑制的怀旧之情。对美国白人而言,其白人中心的建构充斥着对印第安人的逼赶与杀戮、西部大开发中对自然的征服与掠夺、黑奴制度的血腥与无情、对华裔劳工的压榨和欺凌等种种黑暗。在历经了人性的黑暗、饱尝人性的恶之后,美国白人更向往天真与简单了。经历过多世事的人往往厌倦复杂纷扰,而渴望抵达天真。这并非说明他没有见过黑暗与邪恶,恰是因为见过,才深知天真的可贵。“天真是种状态,但只有你失去天真后才知道。类似于亚当直到他身处伊甸园之外才知道他曾经一直在伊甸园之中。”[3]136在此种意义上,费德勒指出美国这一新世界比欧洲更古老,是古老美德的最后避难所。但更确切地说,新世界的“边缘空间”是美国白人的天真回归之处。
天真何以在边缘空间回归?从中心地带与边缘空间的关系看,费德勒认为“边缘空间”是实现被文明抑制的梦想的重要空间。“瑞普·凡·温克尔这一角色标志着美国想象的诞生,尽管显得戏谑,但将它作为我们首个成功的本土传说来铭记是合适的。一个逃离泼妇的梦想家——进入山区,远离家乡和城镇的单调职责,寻找佳侣和神奇的啤酒。”[4]70这揭示了温克尔的双重身份:逃跑者、梦想家。温克尔逃离家中凶悍的妻子与城镇的工作,即是逃离婚姻的压迫、文明与制度的束缚。家庭、城镇或都市这些文明之地成了抑制、阻碍人潜意识中某些欲望实现的空间。温克尔本以为家庭是温柔乡,哪知家庭也是争斗场,他败下阵来,男权显得羸弱不堪,家园的失落迫使他遁入“边缘空间”。身处城镇或都市空间的人,如同都市文明中各司其职的一颗铆钉,只有履行了各自应有的责任与义务,才能保持都市空间的井然有序。但文明的制度何其不是一种对人性的束缚,脱离都市的束缚或某种文明的教条,去追求道德的自由,成了精神自由挥洒的必要因素。边缘空间是挥洒精神自由的重要场域,在这里被文明抑制的梦想才有了得以实现的可能。
“边缘空间”也可实现哈克和黑人吉姆、班波和印第安人钦加克、以实玛利与奎奎格的跨种族的爱之梦。跨种族爱恋一直是美国社会的禁忌,在20世纪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的争取下,1967年跨种族婚姻才得到美国法律的认可。在现实中,美国社会肤色的差异足以激起人们的不信任和仇恨,而美国经典小说中却在欢庆白人与有色人种间的爱恋——这一社会禁忌。在边缘空间,大自然涤荡着人的心灵,充满歧视与傲娇的白人与因白种文明压迫而产生卑贱意识的有色人种挣脱了制度、禁忌的枷锁,人得以回复到本真的道德与情感层面。
跨种族的爱恋说明,回归天真在于回归到没有偏见、歧视和基于平等构建的爱中。美国经典文学作品中跨种族的男性情谊,以超越种族的身姿冲撞着现实社会传统的文化、种族、恋爱观念,诠释着社会转折时代的意义。离开中心意味着疏离主流文化的霸权或经主流文化排除而被边缘化,与他者文化交流意味着承认文化的差异,这为种族与文化的平等创造了契机,也为他者文化获得承认提供了可能。跨种族男性情谊摆脱了种族、性别的羁绊,祛除了白人文化的霸权欺凌以及黑人、印第安人等他者文化的卑下轻贱。因此,以跨种族爱恋为象征的跨文化联结,既是对白人文化至上主义的抗争,也是对文化交流与沟通以及文化和解的期盼与向往,展现出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美好图景。“当库珀重新想象自己就是钦加克在与班波对话,或斯托夫人假装自己就是汤姆在和乔治说话,或吐温假设自己是吉姆在和哈克对话,他们因为剥削和仇恨而分裂为两派,却以这种方式,使长期被一分为二的美国灵魂找到了一种沟通的方式。”[5]xx费德勒觉得像“黑鬼”这样的贬损词,不仅让美国人想起他们血腥的历史,还提醒美国人历史所塑造的他们的态度和价值观,这令大多数美国人对血腥的历史感到羞愧,而感受不到任何轻松自由。费德勒以此解读美国经典作家在小说中书写的跨种族爱恋,正是现实中对美国黑暗历史的愧疚无法释怀的表达,这一文化心理诉求也只可能在边缘空间传达了。
三、边缘空间的文化政治使命
所有或直白或隐晦的文化诉求的表述,都是为了满足和实现某种文化愿望。边缘空间中的文化诉求,表达了一种在试图消解中心霸权的基础上,重新规划空间秩序的期望。边缘空间里的主体性行为,具有推动社会更加正义的文化政治使命。
边缘空间是反主流文化的抗争之地,抗争是为获得权力中心的承认与尊重。中心地带文化的强权,致使他者文化需以边缘空间为突破口,才能牵动权力中心的变化。跨种族交往与情谊的建立及其所代表的文化交流,实际是他者建构的抵抗共同体,以抵抗权力中心的主流文化及其背后的制度或体系。他者文化的联合是社会空间中的他者群体采取的抵抗策略之一,以从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体系中夺取某些局部的胜利,缓解边缘性压迫带来的物质与精神创伤。而创伤的根源,来自边缘空间中由不同民族、种族、性别、阶级等组成的他者的身份与文化无法获得承认。抗争是为了得到承认,对其身份、文化等的承认。费德勒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美国人的身份必然在边缘人、外人、怪人、格格不入者和陌生人中才能发现,即通过他者来确定自我的身份。费德勒还通过解析美国小说家与欧洲中世纪游吟诗人间的关联,研究美国小说家对主流文化的抗击。他认为,虽然这两类人所处的时代迥异,但两者关键的联系在于作家与他者的关系。游吟诗人和美国小说家,似乎均未与主流文化保持一致。他们有意制造与主流文化的紧张关系,似乎以此作为一种抵抗当时主流文化的手段。中世纪的游吟诗人,拒绝教会文化对性的妖魔化,拥抱接受女神的概念;美国白人小说家则拒绝接受资产阶级和女性化的文化对文明的肯定,而在森林、海洋等原始的大自然中拥抱有色人种。
边缘空间是多元文化崛起之地,因反抗是为获得承认。多元文化主义,是处于边缘空间的他者获得承认的一种文化政治实践,是对空间进行差异性规划的政治尝试,是以空间为基石的后现代对空间秩序的重新规划。“在后现代空间里,我们必须为自我及集体主体的位置重新界定,继而把进行积极奋斗的能力重新挽回……加入我们的确能发展一种具有真正政治效用的后现代主义。”[6]444多元文化主义,强调多种文化和平共存且并行发展,承认不同民族、种族、阶级的文化差异,突破种族、性别、阶级的对立,组构因差异而产生的多样性的空间。空间成为多元多层的新空间,承认、包容不同文化的差异,形成了一个多元共存、互不排斥的反抗空间,为边缘空间中的他者群体获取文化政治身份的承认开辟了道路。边缘空间是文化开放之地。
美国是多族裔多元文化共存的社会,其文明起源就是一部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史。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一轮亚裔与拉丁裔移民大量涌入美国,再次改变了美国的族裔结构,也对美国白人文化形成了巨大冲击。同时,美国国内黑人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印第安人的自主权力运动高涨,加之反文化运动的推进,促使美国的少数族裔迅速觉醒,与白人中心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这一背景下,原来的种族主义和文化同化主义已明显不合时宜,阻碍了美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二战后欧洲的多元文化主义观念的兴起,推动了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崛起与发展。“‘多元文化主义’争取的不仅仅是对美国社会不同种族和族裔的文化和传统的尊重,而是对传统的美国主流文化提出全面检讨和重新界定,它要求的不止是文化和民族传统上对有色种族的尊重,而是改变美国政治的基础,要求将种族平等落实到具体的政策和经济生活中去,‘多元文化主义’所包含的‘文化’的内容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化’范围,实际上成为一种明显而直接的政治诉求。”[7]62
费德勒是最早支持多元文化主义的学者之一,种族与性别是他文化批评中的核心议题。他的文化批评一开始就带有一种文化政治使命。费德勒曾言及在其生活中,文学和政治是他生活中的两大主题,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揭露所有的政治幻想。在他的评论集《莎翁笔下的陌生人》中,他专门解析了女性、犹太人、摩尔人、印第安人等莎翁戏剧中的边缘人,并横向比较、探讨了美国经典文学中的边缘人。美国当代著名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评价莎翁的作品时曾指出过,莎翁作品的一个普遍的基本特质是多元文化性,它在所有语言中能被普遍地感觉到,所以也就在全球实际上构建了一种多元文化主义,并认为这种多元文化策略,比以政治化的笨拙努力去实现这一理想要高明得多。
除在文化研究中对种族与性别问题不断开掘与钻研,费德勒还是美国文学经典拓宽派的主要倡导者。自“瓦斯普主义”(waspism)在美国占居文化霸权的地位后,美国的文学经典就是以新教白人的作品为中心建构的经典。这一经典建构标准,导致美国文学经典的组成几乎都是已故白人男性作家的作品,而在美国生活的其他族裔和女性的文学作品被排除在经典行列之外,这既包括非新教的白人,如犹太人、东欧和南欧白人的文学作品,也包括黑人、印第安人、亚裔等有色人种的文学作品。由此,在这一标准与视野下的美国文学经典,表征更多的是文学的政治属性与价值。“伟大的经典”,实质是“选择的经典”。费德勒作为多元文化主义的倡导者,认为美国文学经典应该被拓宽和修正,作者的阶级、种族、性别、身份,不应该是他们的文学作品被包含或排除于经典的理由,经典应该将其他族裔及女性的文学作品囊括进来,代表真正的社会多样性和更广泛的文化遗产。美国文学经典的空间,应该唱响多种声音,应该是多种声音的大合唱。
费德勒以其批评实践,对美国传统经典进行了拓宽与修正,以示他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支持。如他一直推崇劳伦斯和马西森对美国经典文学的评价,但即便如此,费德勒仍以他自己的标准对经典进行了修正:“我颠覆了些许他们(指劳伦斯和马西森)的经典。在《美国小说的爱与死》(1960年)中,我选择了几位女作家的作品,她们的作品一直是畅销书,但却被劳伦斯和马西森忽略了”[4]147。费德勒选择了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玛利亚·卡敏的《点灯人》、 苏珊·华纳的《广阔世界》等女作家的作品,尤其对支持废奴的作家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作了深入的分析。费德勒对女性畅销作品的选取,打破了仅有白人男性作家的作品选入经典的惯例。“作为经典修正的反应……其标志是莱斯利·费德勒和霍斯顿·贝克主编的《英语文学:打开经典》(1981年)一书的出版”[8]3。从他的文化批评实践看,他对经典拓宽的支持并非一时之热情,而是一种持久的坚持,至少他的这两本相隔了二十一年出版的代表作就是证明。之后,费德勒还出版了《文学是什么?》(1982年),并以“颠覆标准”“开放经典”作为此书上下两部分的标题,再次发出了拓宽经典、修正标准的呐喊。这一呐喊后来在《新标准》《希思美国文学选集》等著作中得到了回应,少数族裔以及女性创作的文学作品被纳入其中,这均推动了美国文学经典的修正。
四、结语
关注边缘空间、从边缘空间发起挑战,是费德勒文化批评消解中心、削平价值的后现代策略。他眷注身处边缘空间的不同种族、性别、阶层的群体,挖掘其被潜抑的文化心理诉求。他通过解读美国经典文学作品,发现美国经典作家笔下的边缘空间常是森林、大海、河流等原始大自然,并常在笔端设计边缘空间的跨种族爱恋的情节,他认为此隐射出美国人回归天真的文化心理,表征出身处边缘空间的人抗争白人文化至上主义,渴望享有平等的身份,企盼不同文化能展开交流并实现文化和解,展现出多元文化和谐共处的图景。推行多元文化主义,是费德勒文化批评空间指向的文化政治使命。费德勒在其文化批评中,对种族与性别不遗余力的研究、对拓宽美国经典文学与修正美国经典文学标准的实践,极大地支持了多元文化主义。他的文化批评融入了阶级、种族、性别等多个视角,他对边缘空间的文化故事和文化心理诉求的解析、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声援,有力地唤起了社会道德,促进了社会正义的发展。他以自己的文化批评,坚决地践行了他提出的“越过界线,填平鸿沟”这一响亮的后现代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