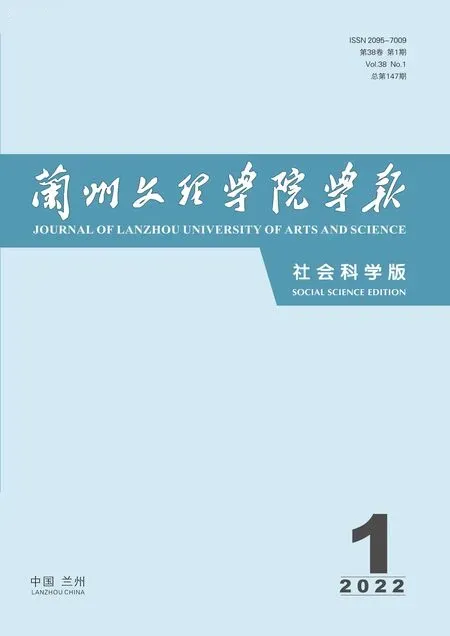真诚而有力量的文学批评
——读李建军文学批评札记
张 吉 山,马 学 永
(1.烟台文化旅游职业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3;2.临沂大学 文学院,山东 临沂 276000)
李建军的文学批评,是严格和尖锐的,但也是严肃和认真的。在他的批评意识里,有高度的理论自信和学术勇气,也有一丝不苟的求真态度和务实的客观倾向。他的自信和勇气来自于对文学的虔敬。因为虔敬,他热情歌颂文学的真善美,无情揭批文坛的假恶丑。他以雅驯的语言、细腻的感受和朴拙的文本细读功夫,裁衡所谓大家名家的大作名篇。
一、批评的标准:肯定指向
当前文学批评存在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文学批评标准的混乱。毋庸讳言,中国新文学发展的百年历程,一直深受外国文学的影响,从创作实践到技巧理论无一例外,即使是一段时期内被封为文学主流与正典的左翼文学——抗战文学——解放区文学一脉,也不完全是中国文学自然生发的本土产物。真正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的文学作品至今仍为罕物,而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的文学批评理论则付之阙如。因为长期以来的移植与借鉴,我们在确立自己的文学批评标准时,总是将国外的文学理论奉为圭臬,在对自己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外国文学作品进行批评时,发不出自己的声音。
而李建军却敢于对国外的文学作品进行鞭辟入里的批评。他对唐纳德·巴塞尔姆后现代主义小说《白雪公主》反规范写作的批评,对劳伦斯《查特莱夫人的情人》道德狂热症的剖析,对纳博科夫《洛丽塔》中道德冷淡症的揭示,对乔伊斯《尤利西斯》展现出的傲慢的修辞与黑暗的精神的不满,对罗兰·巴特及其影响下的新小说的抨击,都显示着自己的文学立场和文学观点。与此同时,李建军对T·S·艾略特的批评观、新批评的“细读法”、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修辞理论、新历史主义、布斯的小说修辞理论,尤其是别林斯基、别尔嘉耶夫的文学批评观又极为赞赏,多次在自己的文学批评中引用这些外国文学理论。
另外,李建军对中国传统文论曾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对中外文学的兼容并蓄,体现了李建军博采众长、执中守正的胸襟与气度,别具手眼、为我所用的锐气与自信。其胸襟与气度使他确立了属于自己的文学批评标准,对这一标准一以贯之的坚守,又反过来催生了其批评实践的锐气与自信,尽管它不是一套结构繁复、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
在李建军确立的文学批评标准中,一个关键性指标是“肯定指向”。“不是对惩罚和地狱的恐惧,而是无私的和牺牲的爱,才应该被认为是肯定的道德动机,这爱是对上帝的爱,对生命中神圣事物的爱,对真理和完善的爱,对肯定价值的爱。”在此意义上,“充满爱意的道德力量,是一切力量的源泉,是将人从动物的野蛮状态提升出来的‘肯定指向’”[1]。具有肯定指向的文学“具备这样的条件:视爱和悲悯为具有核心意义的心情态度;具有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和尖锐的反讽性;不仅充满孩子般纯洁的道德诗意,而且达到了高度成熟的伦理境界;具有‘教育’读者的自觉意识和崇高理想,充满从精神上提高人和拯救人的宗教激情,致力于改变人们的文化气质,为人们克服懒惰、怯懦、势利、贪婪、残暴、冷漠、僵化等人格病变提供道德启示和精神支持”[1]113~114。 “肯定指向”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人物形象的肯定性指向。即作品人物以自我肯定(否定)的姿态,以无言的方式,却又明确无误地向读者传达出哪些动机、道德、情感、价值等等是人类应该共同拥有的,哪些是应当摒弃的。二是作家态度的肯定性指向。即作家在叙事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态度,让读者感受作者在宣示什么,在批判什么。批评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发现哪些作品是具有肯定性指向的,并且揭示其肯定性指向的具体内涵,以宣扬文学作品中“有可能被转化成一种积极的力量,完全有可能被升华成真正人性的东西”[1]104。
另一方面,李建军的文学批评标准注重“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其实,卷帙浩繁的古今中外文论无非围绕“艺术”与“生活”两大主题而展开。“艺术”与“生活”在文学创作中孰先孰后,孰轻孰重,一直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即以中国文论而言,从古代“载道派”与“言志派”的势不两立,到五四文学革命派与保守派的论争;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围绕左翼文学的论战,到上世纪末“纯文学”是否为伪命题的论辩,这些争论大都不由自主地陷入了“非此即彼”的泥淖。而忽略了这样一个常识:优秀的文学作品是艺术的完美形态与生活的完善呈现的有机融合,二者须臾不可分割。失去前者,文学作品不会产生艺术上的长久生命力;失去后者,文学作品不会形成社会历史的影响力。而即使最优秀的文学经典也不可能两者各占百分之五十,这不仅仅因为文学本身不可量化的性质,更重要的是,文学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品创作的时代和作品流传的时代。“文学的价值,既决定于它在艺术表现上,达到什么样的完美程度,也决定于它在道德诗意和伦理境界的追求上,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而在一个文化脱序的消费主义时代,强调后一点,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1]2李建军因而将文学价值标准的重心移向了道德人生,把那些“对读者产生积极的人格影响和道德影响,当做自己写作的重要责任和根本目标”[1]3的作家视为优秀的作家。这一标准的确立,反映了李建军对中国当代文学在生活表现上的深广忧思,他企图用这一标准来裁衡并批判那些对病变人格无力做出肯定性指向的作家与作品。
二、批评的律令:说真话
在李建军看来,文学批评的“第一律令是说真话”。然而,“由于中国文化自古就是一种‘求同’而不容‘异’(‘存异’与‘容异’是有区别的)的文化,由于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乐道人善因而把‘人情’看得高于真理的民族,所以,批评的生存和发展一直就很难,不顾情面地说真话的文学批评向来就很少”[2]。我们缺乏说真话的文化传统,鲁迅先生曾在《野草·立论》中对这种“老好人哲学”做过画像,将之视为国民“劣根性”的一种表现,进行过辛辣的讽刺。这一痼疾至今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工具理性、实用理性仍旧大有市场,大行其道,要冲破“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畸形批评生态,就必须具备鲁迅式的战士品格,才能旗帜鲜明地亮出批评之剑,不计后果地“得罪人”。
李建军批评刘震云的小说《手机》混淆了文学与影视之间的“艺术距离”,忽略了小说艺术的“文学品质”时,毫不客气地点了海岩、石钟山、周梅森、池莉四位著名作家的名字,说他们也是“影视文化屁股后面言恭貌谨的小跟班”。在批评刘震云的小说缺乏美感时,则由此及彼地带出了贾平凹、莫言、余华当代文坛三位极具影响力的大家,“像贾平凹、莫言、余华等人一样,刘震云也是一个‘善真美感受贫弱症’患者”[2]74。这种“指名道姓”的批评方式可谓锋芒毕露,而锋芒所向,对准的却是“一种现象”。这种现象既是创作界普遍存在的“贫弱”现象,也是批评界中否定性批评含糊其辞的“软弱”现象。批评的“软弱”,滋长甚至纵容了创作的“贫弱”。许多作家之所以成为“贫弱病患者”而不自知,除了自身原因外,与批评家的一味叫好密不可分。“好评如潮”带给作家身外之物的同时,也麻醉他们的审美感知能力,矮化他们的精神追求标准;而普通读者无力改变由作家和批评家构成的文学话语权域,也无法确证自己的阅读感受和审美判断是否准确。因此,如果文学批评不敢指出真相,总是温吞水,则批评家既是对自身职业的不负责任,也是对作家的不负责任,更是对广大读者的不负责任。
文学批评本质上是一种对话,是批评家与作家作品之间的思想交锋、观点碰撞和审美沟通。这种对话不是批评家与作家之间两军对垒前的直接叫阵,而是以作品为媒介,从作品出发,返回作品,达成对作品共识的双向交流。文学作品之所以为文学作品,而不是简单的生活故事,是因为文学作品中的故事包含了作者和生活的意指关系,是作者主观化、艺术化的物化形式。如果作家不能以虔诚的态度对待文学创作,认为自己有凌驾一切的权力,不按照人物可能的样子去塑造,不按照事件可能的逻辑去演绎,而任意役使人物,随意照搬或编造故事,甚至模糊作品人物、叙述人物和作者之间的界限,简言之,作家没有创作出合格的作品,那么这样的作品是没有资格充当批评家和作家之间进行对话的媒介的。在这种情况下,正常的交流将无法实现。此时,有职业操守的批评家就有必要跳将出来,对作家进行直接“叫阵”。
这是麦其土司领土上出现的第一家酒馆,所以,有必要写在这里。我听人说过,历史就是由好多第一个第一次组成的。
这是李建军所批评的阿来《尘埃落定》中的一段文字。很显然,《尘埃落定》的叙述人傻子“我”僭越了作者的身份——他怎么可能“写在这里”?面对如此低级的错误,李建军似乎已经出离愤怒,他如同唤醒梦中人似的,吆喝道:“嗨,嗨,那是谁在说话呢?哎,是作者。”[2]192
李建军批评的犀利不只体现为一针见血的正面交接,还体现为迂回反复的辛辣讽刺:
我只有与上官瑞芳坐在湖边的长椅上,看着围绕湖上岛盘旋的鸽群,感知(看着?)些许的金色阳光,在照耀我们裙角的看麦娘草,只有这样,我们的心便(才?)会一刻一刻趋于安宁[2]225。
李建军的这段文字,重在批评池莉小说的小家子气,批评《看麦娘》结尾处“轻飘飘的小满足、小陶醉”,值得注意的是本段文字括号中的内容。在本段文字之前,李建军已经就池莉小说的用词进行了批评,两个括号看似不经意,却一次次在提醒读者:自己此前所指出的池莉小说中存在的语言问题是多么的普遍而严重!
他在批评余华的所谓“新小说”《古典爱情》肆意地复制情节和重复手法时指出,主人公柳生三次赴京,第三次“依然赴京”,“却已不是赴京赶考”,却又莫名其妙地“故而当又是榜上无名”,这三句话显然颠三倒四,不合逻辑。在此,李建军仍然不忘顺手一击,进行讽刺——在“故而当又是榜上无名”后,用括号补充了一句:“(这显然是个病句嘛)”[3]这一补充看似漫不经心,细细体味,却意味深长,嬉笑之中让我们充分感知了余华创作时混乱的思想状态和草率的情感态度。
三、批评的基础:文本细读
文学批评要想具有说服力,前提是对批评对象的熟稔。试想,如果连文本都没有读过,或者是走马观花式地跳读泛阅,就率尔操觚的话,其结论怎么可能站得住脚?哪怕是溜须拍马,都可能闹出文不对题的笑话,偏偏这样的笑话在当今文坛并不鲜见,而肯在文本细读上下“笨”功夫的批评家却实在太少。李建军在文学批评中重视对关键词的数量统计,这并不是他在故弄玄虚地借鉴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在搞繁琐论证,而是在用事实说话,用数字说话。做过文学批评的人都清楚,以论代史式的下笔千言往往比“上穷碧落下黄泉”式的数据搜集更费时费力也费神。
在批评贾平凹小说《废都》的语言,模仿古典小说,尤其是《红楼梦》,而又画虎不成,倒人胃口,呈现出“反对话性”特征时,李建军如警察探案一般,一一摘引出《废都》中的“小蹄子”“好姐姐”“就是了”“可怜见(儿)的”“的”“了”“的了”“兀自”等词。他统计出“兀自”一词,在《废都》中,至少出现过26次,并对该词在明清的白话小说《醒世恒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中的出现频次,分别进行了索引、统计,从而得出结论:类似“兀自”这样的冷僻词,在近代小说中,用得越来越少。而贾平凹不仅用得较多,而且没有一次运用正确——其在小说语言运用上的“反对话性”“反现代性”由此可见一斑。
他对余华嗜痂成癖的粗鄙话语,做了如下统计和列举:
表现“屁股(放屁)”秽语事象至少5次(第4、11、12、15等页);
表现“裤裆(裤头、裤衩)”秽语事象至少7次(第10、15、90、97等页);
表现“王八蛋(小崽子、狗娘养的)”骂人事象至少18次(第29、30、39、131、151、153、163、170、171、172、174、178等页);
表现“婊子(妓女、骚女人、破鞋、烂货、下贱女人、骚娘们)”骂人事象至少11次(第38、90、114、147、175等页);
表现“做乌龟(老乌龟)”秽语事象至少12次(第71、82、88、90、94、163、157等页);
表现“强奸”秽语事象至少5次(第78、107、108等页);
表现“野种”骂人事象至少4次(第147等页);
表现“禽兽不如”骂人事象至少三次(第108、109、114等页)[3]184。
我之所以像李建军不厌其烦地将他所批评的作品大段引用一样,罗列出上文,也是为了“再现文学的现场”。通过这段文字,我们能够更深入、更真切地感受到余华语言的粗鄙程度,信服李建军对余华的批评所言非虚,也能更直观地体察到李建军在“考证”上所下的“笨”功夫。
李建军的文本细读功夫还体现在对字词标点的细腻品读。如果我们承认文学是关于语言的艺术,则语言是一切文学的起点。“诗到语言止”固然不是文学的至理名言,但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学,没有好的语言就没有好的文学,语言不过关,是无法窥见文学的堂奥的——这,恐怕是没有多少人会产生质疑的。然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推崇各种时髦理论和现代技巧成为一种潮流,“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似乎只是落伍腐儒们的行为。于是,作家们对字词的差遣随意任性,标点符号的准确运用更不在考虑范围之内。批评家们对此也见怪不怪,任其泛滥。对某些批评家而言,如果揪住字词、标点进行批评,那就太小儿科了,不仅有吹毛求疵之嫌,更显示不出自己理论的高深和见解的高远。
而李建军偏偏不愿在文学批评的队伍中“随大流”。他像中小学教师批作文一样认真地指出了王蒙、阿来、池莉等一众作家在字词使用、标点规范等方面的诸多弊病。中国文学的纯洁与优美如果不能在专业作家们手中成长、完善,我们又能指望谁呢?一百年前,胡适就提出了“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文学命题,但直到今天,我们似乎并没有彻底完成,以至于有人认为,是汪曾祺的创作“拯救了我们的汉语”[4]。汪曾祺是否能够享有此誉姑且不论,但就语言而言,我们当代的不少作家在面对汪曾祺的小说时,是应该感到汗颜的。有些名家或许因为作品发表无虞,在写作过程中,漫不经心,心浮气躁,一味骄纵地逞才使气,以至于出现大段大段的文字不加标点、直接引用不加引号、不合语法比比皆是等怪象、乱象。
汪曾祺曾说:“我们不能说:这篇小说不错,就是语言差点。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使读者受到感染,小说的魅力之所在,首先是小说的语言。小说的语言是浸透了内容的,浸透了作者的思想的。……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5]汪曾祺在这里谈的语言问题显然是指语言的深层问题,并不包括诸如标点符号、语法规范等写作常识,因为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对一名作家来说是无需强调的。反言之,如果连标点符号和语法规范都不懂,这样的“写家”是不能称为“作家”的。由此看来,李建军对此的指弊,就不是无可观者的“小道”了。
四、批评的用语:雅驯
或许因为批评了太多作家语言的粗鄙与不雅,李建军的批评用语格外“讲究”,这种“讲究”概括起来,就是雅驯。所谓雅驯,一是修辞优美,语句顾盼有序,整饬匀称,精心组织的字里行间流动着艺术的韵律;二是语言洗练,字词锤炼准确,典雅纯正,文白相间处尽显灵动与生趣。
譬如,李建军批评冯小刚电影:“我们从他的电影里可以看到小打小闹,小情小调,小奸小坏,小腻小歪,但是,永远别想看到重大的问题,严肃的思想,深刻的痛苦,可怕的真相。”[2]71“小打小闹”“小情小调”“小奸小坏”“小腻小歪”结构形式相同,前两个词语中的“闹”与“调”押ao韵,后两个词语中的“坏”与“歪”押ai韵,四个词语挤挤挨挨地排列在一起,又押韵上口,充满了幽默滑稽的意味;而后面的四个词语“重大的问题”“严肃的思想”“深刻的痛苦”“可怕的真相”呈排比之势,整饬庄重。两组词语前后对比,鞭辟入里地抨击了冯小刚电影为取悦观众,而不惜消解严肃主题的商业行为,其讥诮的口吻、戏拟的用词、对比手法产生的喜剧效果与冯剧浮滑的风格可谓相映成趣。
李建军对文字的细腻雕琢并非兴之所至的偶然为之,在他的评论中可谓俯拾皆是,成为他文学批评话语的普遍现象。比如,在评论王小波为文时,他写到:“他知道自大和自负是背离幽默的坏德性,而自审和自嘲则是接近幽默的好品质。”[2]166“自大”“自负”“自审”“自嘲”“背离”“接近”“坏德性”“好品质”,这些极普通的常用词组合、并列在一起,自然熨帖地将对比效果呈现出来,看似漫不经意,实则别具匠心。
他批评《许三观卖血记》充满了余华一贯的创作弊病和行文习气:“情感冷漠而苍白,想像随意而任性,描写外在而浅薄,语言干瘪而呆板。”[2]182这段排比句子除语言形式协调对称外,语气肯定,气势充沛,概括简洁,评点大胆,如老吏断狱,成竹在胸,一字不易。
他批评女作家池莉小说的语言,“既没有宗璞的渊雅圆熟,也没有王安忆的清通严整,也没有张洁的飘逸流丽。”[2]216这段批评尽管不是从所谓的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但如果将池莉与随机挑选出的几个当代小说家进行比较的话,就会因缺乏标准,而失去对池莉批评的公正性。毕竟,语言的风格因人而异,以彼之长,攻人之短,是难以服众的。在此,李建军选择了当代有影响的三位女性作家,与池莉进行了对比,同为女性作家,自然有一定的可比性。更难得的是,李建军对三位女作家语言的细致体察与准确概括,如果没有对三位作家作品的广泛阅读与精心研读,断难得出这样要言不烦的点评。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论的点评方式往往只寥寥数语,点到为止,却很“吃功力”,我们当然不能由此而断言李建军赓续了古典批评传统,但这种吉光片羽的点评语言还是给人以珠光乍现的惊喜。
李建军的语言之美,并非为修辞而修辞,在论及作家对唯美主义与功利主义选择时,他这样写道:“具体地说,它是这样一种选择:是象牙塔和十字路口之间的选择,是形式经营与意义追寻之间的选择,是无动于衷的静观与不能自已的介入之间的选择,是对纯美的迷恋与对至善的热爱之间的选择。”[1]31这段精美的文字看似信口抒情,却是在罗列大量实例和理论之后的一种总结,是对诸如王尔德、谢林、普列汉诺夫、利哈泽夫、别林斯基等人关于唯美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分门别类的形象概括和条分缕析的生动提炼。它以排比的方式,优美、准确地揭橥了作为一般意义上“具有内在的、封闭的倾向”的唯美主义与具有“外向的、开放的倾向”的功利主义在价值立场、形式技巧、道德伦理、艺术倾向等方面的不同特点,更显明地指出了关于唯美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纷争焦点和产生根源。
李建军在文学批评中常用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名句,往往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他批评北京实验教材编选 “——岂止是不负责任,这简直就是令人愤叹的文化渎职!”之后,意犹未尽,加了一句“噫!‘彼君子兮,不素餐兮’!”[2]177“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出自《诗经·伐檀》,这句话本身讽刺意味十足,如同指着那些尸位素餐者的鼻子在斥责和嘲弄。李建军古为今用,白话文中突然跳出《诗经》的句子,既显得文笔生动,意趣盎然,其表达情感也更加强烈,具有跨时空的叠加效果。
类似的还有:李建军倡导在自传写作中,一旦涉及他人,应该秉笔直书,美恶并录,如果只写其恶,不彰其善,是缺乏宽容心和仁爱心的,以此为标准,他批评王蒙的自传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在引用了明人吕坤的《呻吟语》之后,他感慨古人之风,山高水长,随后一句“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将孔子之叹用于此处,并非李建军在甩书袋,“都都平丈我”的笑话想必读书人都知道,此语意在表明作者与孔子对文化传承的感慨可谓若合一契,即对古风高义的仰慕,和对世风浇漓的失望。这就不由让人联想到,自孔子至今世,千载之下,宽容心和仁爱心在我们的社会是多么的缺乏和可贵!
如果上述用典属于直用典故的话,李建军还运用了不少隐用典故。隐用典故含蓄沉着,引而不发,不露痕迹,如“水中着盐,饮水乃知盐味”,使李建军的文学批评更加蕴藉厚重、意味深长。如他在描述俄罗斯作家近现代所罹受的艰难处境时,这样写道:“他们的生存境遇一直都是险恶的:缇骑四出,爪牙密布,广场上高竖着狰狞的断头台,西伯利亚的矿井便是流放者葬身的墓坑,古拉格群岛简直就是可怕的人间地狱,但是,伟大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无所畏惧,毅然前行。”[1]47这段看似平淡无奇的话,隐含了四个典故。一是“缇骑四出”。该典出自明代张溥的《五人墓碑记》,其中有“缇骑按剑而前,……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之语,生动写出了魏忠贤擅权一时、气焰熏天的黑暗政治。另外三个则是“广场上的断头台”“西伯利亚的矿井”和“古拉格群岛”,分别暗指艾特玛托夫的《断头台》、普希金的《在西伯利亚矿井底层》和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这四个典故消泯了中俄两国地域与时间上的差异——险恶的政治处境古今中外所在皆是也,而能在艰难处境中大义凛然、秉笔直书的,才更显知识分子的风骨!
如果说使用古典用语体现了李建军批评语言的“雅”的话,那么方言词的使用则体现为“活”。在方言词中,李建军特别喜欢使用“哩”这个方言语气词。他质疑余华《在细雨中呼喊》封底的广告语:“(余华)就像伟大的哲学家用一个思想概括全思想一样,伟大的小说家通过一个人的一生和一些最普通的事物,使所有人的一生涌现在他笔下”,批评这一广告语言过其实,“‘使所有人的一生涌现在他笔下’,这恐怕是自人类有文学以来,最伟大的成就了,是无论莎士比亚,还是托尔斯泰,无论曹雪芹,还是歌德,似乎都没有达到的境界哩”[2]185。“哩”字作为方言,在李建军的家乡陕西运用较为广泛。当他运用词语时,你仿佛看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浮夸风时期,一位陕北老汉背着手,面对一片歉收的庄稼,在和逼其虚报高产的上级干部进行对话一般,其活色生香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其中夹杂的猜疑、不屑、否定、嘲弄、戏谑等各种况味也随之氤氲纸面。
如果一定要为李建军的文学批评寻找一个喻体,以呼应本文的开头的话,则“山涧溪流”差可形容。山高壑深,清流激湍,一泻而下,自有涤荡泥沙之势;溪水清澄明净,一碧如洗,几无纤尘微埃,必定难容污泥浊浪。当今批评界,如同李建军这样的溪流,毕竟太小、太少,还不足以汇成大江大河,更不足以形成汪洋大海。我们期待着评论界有更多的李建军,期待着我们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海洋将变得广阔浩瀚,蔚为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