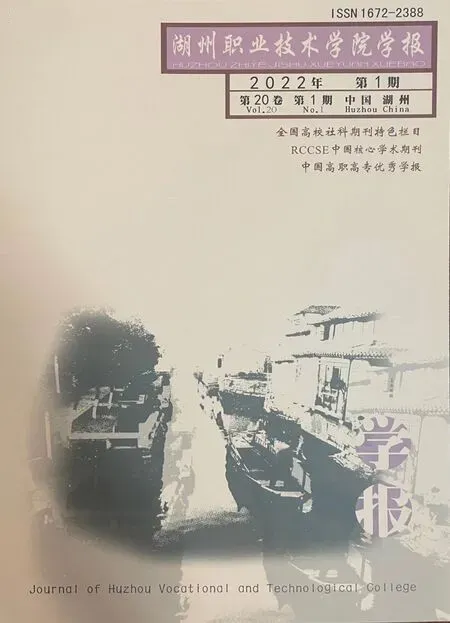韩愈灾害诗初探*
刘小琳 , 戴永新
(聊城大学 文学院, 山东 聊城 252000)
韩愈是中唐诗坛的重要一员,被陈寅恪先生称为“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1]332。近年来,学界对韩愈诗歌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但是对其灾害诗的研究却不多。本文主要探讨韩愈灾害诗的内容、特点以及成诗原因。
要研究韩愈的灾害诗,首先要明确何谓灾害诗。《左传·宣公十六年》中记载:“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灾。”[2]840意思是说,人为生火叫“火”,天降的火叫“灾”。《现代汉语词典》对“灾害”一词的解释是:“自然现象和人类行为对人和动植物以及生存环境造成的一定规模的祸害,如旱、涝、虫、雹、地震、海啸、火山爆发、战争、瘟疫等。”[3]1 618可见,古人和今人对“灾害”的界定是有所出入的:古代对于“灾”的界定是天降之“灾”,而现代汉语认为,“灾害”不仅仅指自然灾害,还包括战争等人为灾害,即“天灾”和“人祸”两类。我们研究古代诗歌,不能简单地将现代概念等同于古代概念。因此,本研究的灾害诗遵从古意,是描写自然灾害的诗歌。
一、韩愈灾害诗的主要内容
(一)灾情描写
在现存的韩愈诗歌中灾害诗共有25首,涉及水灾、旱灾、风灾、疫灾、火灾、虫灾、冷冻灾害七种灾害。其对各类灾害描写的次数如下:旱灾9次、水灾7次、疫灾6次、冷冻灾害5次、风灾3次、虫灾1次、火灾1次。
对自然灾害本身的描写是韩愈灾害诗的主要内容。如《永贞行》描写了现在不太常见的虫灾:“湖波连天日相腾,蛮俗生梗瘴疠烝。江氛岭祲昏若凝,一蛇两头见未曾。怪鸟鸣唤令人憎,蛊虫群飞夜扑灯。雄虺毒螫堕股肱,食中置药肝心崩。”[4]168诗中出现的“一蛇两头”“怪鸟鸣唤”“蛊虫群飞”等怪异景象令人不寒而栗。
除了对自然灾害的描写,还有对灾害中灾民状况的描写。如《龊龊》一诗写道:“秋阴欺白日,泥潦不少干。河堤决东郡,老弱随惊湍。”[4]40在阴雨连绵的秋日,泥泞的路几乎不见干,东郡河堤决口,体弱的老人们被湍急的水流冲走,水灾之中的人们非常无助。《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简称《赴江陵》)中也有一段描写旱灾之中灾民惨状的诗句:“传闻闾里间,赤子弃渠沟。持男易斗粟,掉臂莫肯酬。我时出衢路,饿者何其稠。亲逢道边死,伫立久咿嚘。”[4]159诗人听闻灾荒之中竟然出现了弃子于路和易子而事的有违人伦的情况,亲眼见到了路边无数的饥民和因饥饿而死的人,不由得伫立在旁久久叹息。诗人将灾情之中灾民的惨状描写得淋漓尽致,表达了对他们无限的同情。生活在最底层只能靠种田为生的农民,一旦遭遇天灾,粮食欠收,随时会跌落到生存线以下。又如《归彭城》:“前年关中旱,闾井多死饥。去岁东郡水,生民为流尸。”[4]53诗中写到前年关中的旱灾和去年东郡的水灾这两次灾害。其中,去岁东郡发生的水灾就是前文《龊龊》中提到的发生在郑、滑二地的水灾。韩愈灾害诗中还存在不少这样一诗多灾和一灾多诗的情况。
(二)救灾措施
韩愈的灾害诗除了描写灾情外,还涉及到一些救灾措施。这些措施以官方救灾措施为主,主要有赋税减免和祈祷祭祀两种。
《赴江陵》中提到:“上怜民无食,征赋半已休。有司恤经费,未免烦征求。”[4]159为了应对旱灾带来的损失,皇帝下令减免赋税,希望减少损失,挽救生命。但是,相关部门却阳奉阴违,依然征收赋税,给农民造成更大负担,也加剧了社会的混乱。
用于为消灾而祈祷祭祀的灾害诗,要数《郴州祈雨》最为典型:“乞雨女郎魂,炮羞洁且繁。庙开鼯鼠叫,神降越巫言。旱气期销荡,阴官想骏奔。行看五马入,萧飒已随轩。”[4]135-136前两句描绘了祈雨时的场景:祈祷用的精美肴馔洁净且种类繁多,巫者在进行祈祷的仪式,庙宇打开之后鼯鼠在不停叫着。第三句借神灵之言,表达了旱情早日消散,雨神快快来到人间的愿望。最后一句回归现实,希望太守施行仁政,为民解忧。可见,在当时寄愿于天的大环境下,韩愈还是相对清醒的,在祈雨的同时也希望官员能够为民办事。
(三)自我诉求
韩愈的灾害诗除了描写灾情状况和救灾措施之外,还表达了对当权者不作为的不满,并借此表达自我的诉求,希望自己能有机会发挥才能,为国效力。
在《龊龊》中,诗人借“龊龊当世士,所忧在饥寒。但见贱者悲,不闻贵者叹”[4]40两句,讽刺当时士人志向微小、目光短浅,只担忧自身的功名利禄。作者笔下的社会是一个急需改造的社会,但是,作为中坚力量的士人群体却呈“龊龊”状。诗歌后半段的“愿辱太守荐,得充谏诤官。排云叫阊阖,披腹呈琅玕。致君岂无术,自进诚独难”[4]40,明显地表达出作者希望得到引荐,向君进言,痛陈治国之道,为国效力的愿望,尤其是在灾害横行,民不聊生之时,希望通过自己的一番作为能改变现状。韩愈这种愿望在《归彭城》中也有体现:“我欲进短策,无由至彤墀。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辞。上言陈尧舜,下言引龙夔。言词多感激,文字少葳蕤。”[4]53韩愈的许多灾害诗都有表达自我诉求的内容,一方面是由于唐朝皇帝广开言路的政策,另一方面源于韩愈自己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二、韩愈灾害诗的主要特点
(一)审丑特性
韩愈的灾害诗具有很明显的审丑倾向。这里的“丑”主要有两个维度:一是灾害之丑,二是灾害下的人性之丑。审丑的一个维度灾害之丑,一方面是灾害本身之丑。例如《永贞行》中的两头蛇、鸣叫的怪鸟、群飞的蛊虫以及雄虺毒螫等,读来令人感到不适甚至恐怖。“毒雾恒熏昼,炎风每烧夏”[4]115,“狐鸣枭噪争署置,睗睒跳踉相妩媚”[4]168,毒雾、炎风、狐鸣等怪诞甚至丑陋的意象常见于韩愈的灾害诗中。这些意象多用于灾情的描写,表明作者痛恨灾害的态度。因此,作者常选取一些荒诞丑陋的意象,以丑为美,营造出荒诞陆离的意境。另一方面是如“河堤决东郡,老弱随惊湍”[4]40一般的灾情之丑。古代的人们应对灾害的手段是十分有限的,既不能做到有效的预测,也很难做到灾后的及时救援,因此在灾害面前往往束手无策。在韩愈的笔下,人们对灾害的恐惧、厌恶显得十分传神。审丑的另一个维度就是灾害之中的人性之丑。封建制度下,灾害给权贵带来的伤害,最终会转移到底层百姓身上。百姓们饱受水深火热之苦,而权贵们往往并无同感,这一点在《龊龊》一诗中比较明显。韩愈在《赴江陵》一诗中还提及,京师旱灾后,官员不仅不减少赋税征收,反而阳奉阴违,对底层百姓照例征收。韩愈对这种丑陋行径大加批判,毫不留情。灾害对生命的威胁会使人性之丑充分显露,比如“传闻闾里间,赤子弃渠沟。持男易斗粟,掉臂莫肯酬”[4]159所描写的丢弃婴孩、持男易粟这些看来有违伦理的行为。作者一方面否定灾民的这些行为,另一方面又对他们报以同情之心。
(二)视角转换
韩愈灾害诗的篇幅大多较长,内容丰富,生动地展示了灾害中的人生百态。韩愈在对灾害进行描写时,经常会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之间进行转换,第一人称叙事是身临其境,第三人称叙事则是全知全能。“云昏水奔流,天水漭相围。三江灭无口,其谁识涯圻。暮宿投民村,高处水半扉。犬鸡俱上屋,不复走与飞。”[4]588-589这几句描写了遭受水灾后的状况。作者用第三人称视角,将水灾过后的景象进行整体叙述:先是宏观介绍水天相接,三江茫茫,视野开阔;然后从宏观转到微观——村庄里犬鸡上屋。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将水灾程度之深、危害之大展现出来:“我时出衢路,饿者何其稠。亲逢道边死,伫立久咿嚘”[4]159这两句展现了作者亲眼所见的“何其稠”的饿者,以及作者本人看到路边饿死灾民时的“久咿嚘”。诗人以第一人称视角描写了灾民的人数之多和状况之惨,读来令人感同身受,仿佛身临其境。
(三)语言艰涩
在韩愈的灾难诗中,许多词语艰涩难懂,遣词造句十分独特。这类诗歌极力避免使用常见易懂的词语,刻意追求奇崛险怪的语言风格。例如在《陆浑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韵》里描写山火:“山狂谷恨相吐吞,风怒不休何轩轩。摆磨出火以自燔,有声夜中惊莫原。天跳地踔颠乾坤,赫赫上照穷崖垠。截然高周烧四垣,神焦鬼烂无逃门。”[4]354这里运用的词语,如山狂、谷很、风怒、天跳、地踔、颠乾坤、神焦、鬼烂等词语,令人心惊胆战,声势浩大的山火跃然纸上。诗歌还描写了一些在山火中逃亡的动物:“三光弛隳不复暾,虎熊麋猪逮猴猿。水龙鼍龟鱼与鼋,鸦鸱雕鹰雉鹄鹍。燖炰煨爊孰飞奔,祝融告休酌卑尊。”[4]354韩愈特意选取了许多不常见的动物。这些动物真的在这场山火中逃亡吗?或者说山上真的有这些动物吗?其实不见得。但从他选取的这些动物中,恰恰可以看出,他在用词方面力求新奇,不落俗套。
三、韩愈灾害诗的创作原因
(一)灾害频发
创作灾害诗的直接原因是自然灾害的发生。因此,灾害频发是韩愈灾害诗创作的首要因素。灾害诗的创作并不是诗人无病呻吟,为了创作而创作,而是在诗人看到穷苦百姓的惨状和政府官员的不作为之后的有感而发。唐朝是一个灾害频发的朝代,除水旱等常见灾害外,虫灾、风灾等较为罕见的灾害也有较多的记载。据统计,有记载的唐朝自然灾害共有1 063次。其中,韩愈经历的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五朝共有319次自然灾害[5]104-105。频发的自然灾害为韩愈灾害诗的创作提供了直接素材。
(二)文风影响
唐代盛行诗歌,诗歌创作在唐代蔚然成风。唐人在诗歌创作方面推崇风雅,自初唐以来一直在进行诗歌改革。韩愈所处的中唐时期正是诗风的转变时期,作者自然受到他所处时代文风的影响。初唐时期文坛改革的主要方向是去除诗歌中的齐梁靡靡之风。陈子昂将汉魏风骨与风雅兴寄的传统结合起来,确立了诗歌的基本精神内涵。那时,以建安风骨和风雅兴寄为主要内容的诗歌创作观念已经成为共识。中唐时期诗风发生转变。随着国家动乱的开始,原来风雅兴寄的传统逐渐变为怨刺讽喻。混乱的社会现实和动荡的国家局势使文人开始用批判的笔触抒发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这一时期的诗作内容多为反映社会现状,批判社会不公。韩愈的灾害诗就诞生于这样的社会与文坛背景。韩愈的许多诗歌都直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状,尤其是其描写灾情的诗歌,不但生动刻画了自然灾害带来的破坏,而且也将贫苦百姓的艰难生活刻画得栩栩如生,既表达了对贫苦百姓不幸遭遇的无限同情与悲悯,也表达了对压迫和剥削百姓的统治者的批判。
(三)自身原因
唐代继承了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多元文化,“三教并行”是其文化思想的重要特点。但是,韩愈作为一个深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封建知识分子,家国天下、积极入世等思想在他身上随处可见。他倡导的以“载道”“明道”为核心的古文运动,就是儒学复兴思想在文学上的反映。韩愈是一位有担当、有责任感的诗人。他的灾害诗一面描写百姓之苦,一面批判统治者之不仁,同时也表达了对社会不公的不满。韩愈参与政治的热情极高,他在许多诗歌中表达了渴望参与国家决策、积极进言献策的愿望。“适会除御史,诚当得言秋。拜疏移閤门,为忠宁自谋。上陈人疾苦,无令绝其喉。下陈畿甸内,根本理宜优。”[4]159在《赴江陵》中,韩愈认为作为御史的他,就应该积极和真诚地向皇上进言献策。虽然因此被贬,但他在《县斋有怀》中回应:对此事无怨无悔,忠于职责是自己的坚守。不仅如此,在一些诗歌中,他还对当时的官员表达不满,在《苦寒》中他写道:“贤能日登御,黜彼傲与憸。”[4]78韩愈曾经直接表达对当朝宰相的不满,认为应该罢免宰相,任用更加贤能的人。非得有极强的使命感和为民请命的大无畏精神的人,才有胆量冒着得罪权贵、搭上仕途的风险,直接而坚定地指出当朝宰相德不配位。
综上,韩愈将自己在灾害中的所见所闻记录成诗。他同情底层百姓苦难,批判不仁之官的剥削,展现了强烈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其整体上怪诞不落俗套的诗歌风格,也为唐代诗歌注入了一股清新之风,具有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