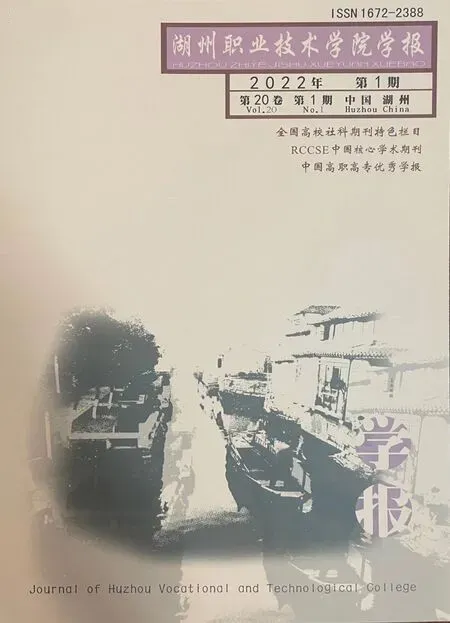马克思关于英国评述中的外交思想分析*
钟媛媛 , 赵安琪
(1.外交学院 基础教学部, 北京 100037; 2.北京市统计局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社会调查队, 北京 100055)
马克思针对18世纪英国的社会现状,分别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角度阐明了各方的外交思想,深刻揭露了英国资产阶级推行的“均势”原则和秘密外交等行为,及其背后谋求利益最大化的本质目的。马克思呼吁,无产阶级作为“旧时代的终结者”,应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反对秘密外交,实现正义外交;同时,在对外交往中,应明晰外交准则,规范外交行为。马克思对英国外交的评述,对当代中国外交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马克思关于英国评述的时代基础
英国的现代化与经济的全球化是马克思评述英国外交的时代基础。通过科学分析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马克思发现无产阶级具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性,这为马克思外交思想找到了有力的执行者。同时,英国现代化进程要求扩大对外市场,在全球范围内拓展殖民地,这也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一)英国的现代化
马克思认为,在经过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后,人类社会才可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18世纪中叶,凭借雄厚的工业实力,英国成为继西班牙之后第二个“日不落帝国”,同时成为研究人类社会演进的最佳观察对象。伴随着新兴工业的兴起,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随之产生。二者之间的矛盾,基于社会化生产和私人占有的对立性,逐步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马克思在1847年的一次演讲中曾说:“同别的国家比较起来,英国是一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最为尖锐的国家。”[1]410对于马克思的这一论断,恩格斯随后给予解释:“由于现代工业,由于运用机器,英国一切被压迫阶级已经汇合成为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庞大阶级,即无产阶级;因为对方阵营里的一切压迫阶级也由此联结成为一个阶级,即资产阶级。”[1]411
无产阶级是与资产阶级相伴而生的。无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是马克思外交思想产生的阶级基础。马克思认为:“要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他们就必须有共同的利益。要使他们的利益能一致,就必须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因为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1]409经过科学的分析,马克思得出结论:要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就必须发动最有力的力量——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因为,“对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最关心的只有工人阶级。只有工人阶级能做到这一点”[1]409。通过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无产阶级独立开展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无产阶级不断积蓄力量,并逐渐作为独立的、具有革命性和彻底性的政治力量,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工人运动为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性质和特点的分析,为日后马克思外交思想的产生与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经济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马克思外交思想产生时期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美洲和环绕非洲的航路的发现,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1]467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在全球范围快速扩张。因此,必然要求用资本主义性质的国际规则,来发展原有的交往习惯或惯例。虽然,在最初阶段,这种国际规则仅仅适用于欧洲国家,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欧洲的国际规则逐渐被应用于全世界。基于这样的历史事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加强国际合作。“1844年还没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从那时起,首先是并且几乎完全是由于马克思的功绩,它才彻底发展成为科学。”[2]372由此,马克思外交思想也逐渐成形。
二、马克思关于英国评述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针对当时英国的社会现状,分别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角度,阐明自身的外交思想。
(一)资产阶级外交推行“均势”原则,使攫取的利益最大化
马克思对英国外交行为的评述在《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彼时,英国统治阶级的亲俄倾向十分明显。“英国外交界公开信奉的正统的信条已经是:‘把大不列颠和俄罗斯帝国联在一起的纽带是自然形成的,是破坏不了的’。”[3]267英国传统的政策是推行“均势”原则,即在占有海上霸权后,促使欧洲大陆国家之间形成“均势”。为了维护波罗的海的“均势”,英国对强势的沙俄总是显得“天真”,甚至“天真到糊涂”,以至于表示到后来才发现俄国的侵略与扩张意图。马克思否认英国是英俄交往中的“受害者”。他认为,英、俄两国的这种“亲密关系”并非两国共同物质利益的自然产物。英国并非没有察觉到俄国的扩张意图,因为“在安娜女皇时期,英国已经向俄国出卖过自己的盟国……甚至在安娜时期以前……俄国的意图就被理解了。”[3]269英国的寡头政治集团,看中了当时俄国手中的有利资源,例如航海器材、工业原料等,这些对于英国来说都是具有诱惑力的。因此,英国政府罔顾当时英国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一味纵容俄国对波罗的海的控制。这是英国的政治家们为了维护自身小群体的特殊利益而造成的后果。
马克思认为,英国与俄国目前的外交关系,是一种满足英国寡头政治集团及其同盟特殊利益的外交关系。例如,在1700年初,英国和瑞典结盟;同年8月,俄国向瑞典宣战。在瑞典受到俄国攻击时,英国并没有采取任何遏止俄国扩张的措施,反而采取了一种更为消极的甚至无动于衷的态度。这样的不作为是一种对瑞典的赤裸裸的背叛。“比这一事实或许还要更奇怪的,是对它采取的沉默阴谋。现代历史学家们以这种沉默阴谋完全抹杀了这一事实……”[3]288这种利益至上的外交观念使得英国资产阶级认为:在必要时不仅可以牺牲盟国利益,甚至可以牺牲英国大众的民族利益,使攫取的利益最大化。大不列颠的联合内阁希望以牺牲本国的民族利益的方式,“让东方年轻的专制制度加强,以期为自己在西方的虚弱的寡头统治找到支持者”[4]23。
(二)反对秘密外交,推崇正义外交,并号召工人阶级监督外交
在当时,秘密外交一直是国与国相交的主要方式,英国也不例外。马克思在撰写《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时就发现:18世纪的英俄践行秘密外交的程度之深、范围之广“令人吃惊”。他写道:“我们在细读这些文件时……所有这些信件都是‘机密的’‘私人的’‘秘密的’‘绝密的’。”[3]267马克思强烈反对秘密外交,认为假借“天真”之名推行秘密外交的英国是“无耻”的。
马克思之所以旗帜鲜明地反对秘密外交,是因为秘密外交带有很大的欺骗性。这种欺骗性表现在资产阶级内部的自欺欺人、尔虞我诈,以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交往时所带有的阴谋性和利益至上性。比如1700年俄国在波罗的海扩张时,秉持“均势”原则的英国并不加以阻止,反而与俄国密谋,支持其对自己的盟友瑞典发动进攻。英国资产阶级并不以此为耻,反而沉浸在外交所取得的巨大贸易成就的喜悦之中。事实上,从1700年开始直至此后的60年间,在英国的对外贸易中,英俄贸易仅仅是很小的一部分,其占比甚至不到2%。因此,马克思谴责道:“彼得大帝及其直接继承者们的俄国这个巨大市场向大不列颠开放的贸易规模被吹得天花乱坠。那些丝毫经不起批评的说法被许可抄来抄去,以至终于成了历史家产……”[3]288资产阶级的欺骗性,由此可见一斑。
这种带有欺骗性质的秘密外交使社会秩序被破坏——社会是不公正的,世界是不正义的。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全球扩张,这种不道德、不正义的秘密外交还使其他国家被迫进入世界市场,比如中国。英国用坚船利炮的暴力方式,向中国强行输入鸦片。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天朝上国”的自大与对封建秩序的自守被鸦片和大不列颠的枪炮所击溃。自此,中国的闭关状态迅速被打破。这个古老而庞大的封建国家开始与资本主义世界建立了联系,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资产阶级秘密外交的欺骗性还表现在与无产阶级的交往中。无产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然而在与资产阶级打交道时却常常被其利用、蛊惑、欺骗。例如1832年的英国议会改革,担任绝大部分斗争任务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却并没有获得选举权。“对于他们来说,改革犹如一场骗局。”[5]311马克思曾愤怒地抨击这次改革:“恐怕从来还没有一个这样强大的、看来似乎成功的人民运动得到这样微不足道的表面的结果。”[6]437正义、公开、平等是无产阶级的价值追求。马克思认为,外交应该具有正义性。但是,如何在对外活动中保证外交的正义性呢?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一文中,马克思呼吁并要求工人阶级要在正义外交方面采取积极行动。比如,对所在国政府的外交行为和活动要进行监督;要学会洞察国际政治的内幕和秘密;对一些外交活动,如果不能有效阻止,就要进行深刻揭露等等。他说:“……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国际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7]14
(三)总结归纳当代的外交准则雏形
在评述英国外交的一系列文章中,马克思彰显出一种高于当时社会历史环境的国际主义视角,从宏观视角看英国外交实践,总结出外交人员不得干涉驻在国内政、外交人员应遵守外交礼节、使领馆应保护本国公民的利益等等规范。这些规范已显示出当代外交准则的雏形。
1.外交人员不得干涉驻在国内政 马克思对于外交人员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是坚决反对的。英国驻德意志联邦议会公使亚历山大爵士,曾公然干涉他国内政,对普鲁士国王及其内阁进行粗暴和激烈的攻击。马克思把亚历山大的行为作为典型,写入《外交上的失礼》中。他认为:“这种攻击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具有值得最严肃看待的后果。”[3]244外交人员不得干涉驻在国内政是国际法准则。亚历山大是英国的外交公使,代表英国;他公开攻击普鲁士国王与内阁的行为,会被看作对驻在国内政的干涉,这是与国际法准则相悖的。事实上,当外交人员对驻在国内部事务妄加干涉的行为遭到指控时,按照准则,外交人员可被驻在国要求召回,甚至可以被驻在国强行驱逐出境。当然,派遣国对公使的态度也是两国关系走向的“晴雨表”。假如外交公使的态度和行为受到英国政府不同程度的袒护的话,那么公使之前的所作所为很有可能是英国未来政策的征候;反之,公使肯定被派遣国召回。
2.外交人员应遵守外交礼节 在现代外交中,国家间的对外交往都是建立在国家平等的基础之上的,“以礼相待”是国家平等原则的重要体现。外交人员作为国家行为的代表,在对外活动中应遵守外交礼节,对驻在国充分尊重,不宜作出失礼举动。在《新的对华战争》中,马克思无情揭露并深刻批判了英国公使普鲁斯对中国政府采取的失礼行为。马克思指出,普鲁斯的寻衅行为,并不代表他本人的主张,而是在英国授意下的行为表征。作为外交人员理应遵守外交准则,遵守外交礼节是马克思始终坚持和推行的。其深刻的意义在于,外交礼节是对驻在国国家主权的基本尊重。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这也是国家之间形式上平等的体现。但事实上,我们也不难发现,西方列强会公然践踏这一准则,常常对其外交人员不遵守外交礼节的行为进行姑息袒护,甚至为了掠夺和侵略而授意为之。英国驻马德里大使亨利·布尔韦尔爵士,曾经罔顾该准则,公然向西班牙宫廷寻衅,结果被迫离开西班牙。马克思通过这一事件向世人提醒道:“……当上院辩论这个‘不快事件’时,证明了布尔韦尔并非遵循阿伯丁的官方训令,而是奉行当时坐在反对派席位上的帕麦斯顿的秘密训令。”[8]573
3.使领馆应保护本国公民的利益 各个国家为了更好地进行对外交往,相互设立常驻外交机构,这在马克思所生活的年代已经是很常见的了。马克思十分支持这一做法。他认为,外交机构能够较好地发挥保护国民利益的作用。马克思的亲密战友恩格斯,在关于设立使馆和大使的问题上,有更为直接和系统的论述。恩格斯认为,外交机构是保护本国公民在国外的利益的机构。并且,使领馆对本国公民的保护程度与本国国力是成正比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国力越强,保护本国公民利益的能力也就越强,甚至还可保护第三国国民的利益。如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中写道:“德国商人不管走到哪里,到处都请求外国——法国、英国和美国——保护,或者很快就归化于新的祖国。”[9]466当时德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水平不及英国,其国民在海外的地位较低,甚至“德国大使本身,在海外也是被人看做像擦皮鞋的人那样的”[9]467,而英国作为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有能力对第三国公民的海外利益提供保护。
三、马克思关于英国评述对当代外交的启示
马克思对英国外交的评述良多,其蕴含的外交思想对当今外交仍有积极意义。深入研究马克思的外交思想,并积极挖掘其思想的当代价值,对发展中国当代外交有重要意义。
(一)坚持外交的正义与道德,致力于建设公正的世界秩序
马克思认为,秘密外交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避免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使得资产阶级必然采取违反国际法的形式,维护其阶级利益和政权统治。因此,就会出现“那种为追求罪恶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见并在掠夺战争中洒流人民鲜血和浪费人民财富的对外政策”[10]3。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也持有相同观点。“为了延长专制政权的寿命,唆使各民族互相残杀,利用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11]177这是恩格斯对资产阶级外交活动之根本目的的深刻且无情的揭露。工人阶级正是为了反对这样的阶级压迫和国际秩序而产生的。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与这样的对外政策进行的斗争,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正义与道德是人类社会的美德,也是国际关系中至高无上的准则。马克思吸收并继承了这一美德,并把正义与道德的原则纳入无产阶级外交活动中,反对恃强凌弱,呼吁各民族之间和睦共处,积极同资产阶级外交进行斗争。
(二)坚持“外交高于战略”,走实用外交之路
“外交高于战略”是马克思针对18世纪末英国与俄国一系列秘密外交总结出的规律。马克思强调外交主体的能动性与实践性,认为外交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与停留在思想形式的形而上学的战略相比,外交活动无疑更具有实践意义。英国外交的一大特性就是实际、实用。不论其具体的政策是怎样的,总是以英国的国家利益为中心,不因“日不落帝国”“工业革命先锋队”等虚名而罔顾实际利益。这样的英国外交虽然不具有马克思所期望的正义、道德,但具体到这一时期,英国的外交政策确实是为其本国资产阶级、为资本主义的利益服务的。“自由贸易意味着改革英国全部对内对外的贸易和财政政策,以适应工业资本家即现在代表着民族的阶级的利益。”[9]225全球自由贸易制度是当时英国为了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而量身定做的,这一制度使英国获得了长达几乎100年的全球外交优势地位。
(三)坚持外交合作理念
马克思深刻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是一种国际势力。资产阶级通过掌握资本,进而控制国家机器与全部经济命脉,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剥削者;而无产阶级一无所有,无法在资本上与资产阶级抗衡。那么,无产阶级想要战胜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应该怎么办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总是联合起来反对各国无产阶级;同时,资产阶级为了其共同利益,不得不和平共处。而无产阶级之间,不仅有共同的利益,还有与资产阶级软弱性、妥协性相反的革命性和斗争性。如果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那将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因此,无产阶级唯有联合起来,相互支援,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推翻封建主义统治上也是存在着合作空间的。如英国1832年议会改革,无产阶级是斗争的主要力量。马克思认为,凡是能够促进新的社会制度建立的国际合作,都具有历史进步意义,都应当给予支持。
(四)坚持外交为民宗旨
马克思在《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批判资产阶级为维护自身的阶级利益,罔顾国家利益,牺牲大众的国民利益和民族利益的行为。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一国的对外政策显示其国内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利益所在。18世纪的英国寡头政府受到属于英国贵族、金融寡头和工业巨头的商业利益的支配,使得英国的外交行为受资产阶级利益链条的支配。在与瑞典是盟国的情况下,英国之所以作出支持俄国反对瑞典的决定,就是因为英国的俄罗斯贸易公司与俄国商人的利益一致。马克思毫不客气地指出:“就是这些先生们发出了反对瑞典的叫嚣。”[3]292
当今世界,维护国家利益应是国家对外政策的核心,一切意识形态利益、宗教利益、政党利益和利益集团的利益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利益。具体到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思想必须秉承外交为民宗旨。因此,在确定外交战略时,必须不屈服于任何外界压力,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维护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严格防止外交活动的“市场化”“私人化”倾向。
四、结 语
纵观马克思对英国外交的评述,可以看出:马克思外交思想产生在英国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生产力及其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是其产生的背景。讨论马克思外交思想不能脱离这个基础。在英国现代化进程的初级阶段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英国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无视国际法原则和国际道德,对外实行秘密外交。这不仅不利于国际社会的发展,也不利于世界市场的繁荣,更不利于人类文明的进步。
事实上,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对资本主义外交的批判上,还进一步探寻了改变这种外交现状的方法和途径。马克思认为,外交应该实现正义、道德,因为正义、道德体现了人类思想进步的方向。同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应该加强相互之间甚至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合作,促进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马克思对英国的评述中体现的外交思想,与后来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国际法原则宣言》都有不少相似之处,可以说是这两者的先声和源流。马克思对英国的评述中的外交思想对于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也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马克思强调了外交的重要性:外交是正义的、道德的,应致力于建立公正的国际秩序;外交的目的是维护国家的实际利益,树立合作意识;在人民当家做主的今天,外交更应秉持“外交为民”的宗旨。马克思的外交思想对当代外交,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外交有着更为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