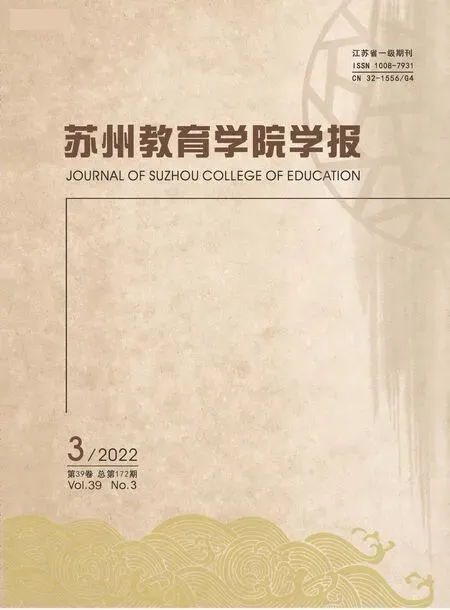致力于诗歌内部规律的探索
——论小海的诗歌批评
吕周聚
(青岛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评论诗歌的标准是多样化的,我们既可从社会、政治、时代等外部因素来分析,也可从语言、结构、表现手法等内部因素来品评。相对而言,前者更易于发现和把握,而后者则须具备一定的诗歌经验和诗学理论才能落笔,这与诗歌文体的独特性密切相关。小海既是诗人,又是诗歌评论家;既有丰富的创作经验,又有扎实的诗学理论,这使得他的诗歌评论呈现出一种独特性——善于凭借诗人敏锐的艺术感觉从语言的角度切入探讨诗歌的内部规律,以诗歌的内部要素为标准来衡量、评价诗人及其作品,形成一种感性与理性兼具的批评气质。
一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诗人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对语言有一种特殊的敏感,表现为一种特殊的语言掌控与表达能力。对大多数人而言,语言只是一种交流的工具;而对于诗人而言,语言是其感知世界、呈现自我思想情感的第六感官,语言与诗人是一种共生共存的关系。不同诗人对语言的运用会有所不同,语言是诗人个性呈现的载体,是把握诗人特性、区分诗人特质的一个重要标准。小海善于从语言的角度来分析诗歌作品,把握诗人的创作个性,语言是其诗歌评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代诗歌的语言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北岛为首的朦胧诗派打破了之前诗坛流行的标语口号式语言,要将诗歌语言还原到美学的层面,因此当时诗坛展开的关于“懂”与“不懂”的论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诗歌语言密切相关的。1986 年出现的第三代诗打出了“PASS 北岛”的旗号,第三代诗对朦胧诗的反叛表现在许多方面,语言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以韩东为代表的“他们”诗群是第三代诗的重要构成部分,作为“他们”诗群的重要一员,小海正是在这一诗学背景之下开始了诗歌创作,对“他们”诗群的诗歌理念有着深入的了解。作为“他们”诗群的代表人物,韩东提出了“诗到语言为止”的主张,并由此进行诗歌创作实践,在当时的诗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小海从语言的角度讨论韩东的诗学主张,分析其诗歌的语言特点,并从理论的高度对其语言主张进行辨析,指出其存在的局限和意义:“‘诗到语言为止’也是一个过激的和矫枉过正的命题,从后来的实践效果可以看出,它所传达的信息和实际操作意义是‘诗从语言开始’,‘诗是一门语言艺术’,这是一个大实话。”[1]162以矫枉过正的形式达到还原诗歌语言本质的目的,这是韩东诗歌主张的手段和结果,也是“他们”诗群对中国当代诗歌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作为诗人,小海写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其语言简洁含蓄,形成了鲜明的语言风格。他通过自已的创作实践,深切地体验到诗人与语言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形成了自已的诗歌语言观。在他看来,“诗人和语言不是一种二元对立关系而是一种交锋,也是一种媾和。诗人通过语言来探索人生和世界,有了这样的条件,即使在石缝里,诗歌的种子也会慢慢长出来,甚至成材”[1]447。诗人依靠语言而存在,他既要与语言交锋,也要与语言媾和,然后才能形成自已的语言,发出自已的声音,“大多数诗人并没有意识到,之所以不能发出自已的声音,是因为没有自已的语言,其面目就是模糊不清的。不能找到自已的面孔与方式,语言就履行不了对自已的忠实和对诗歌本身的承诺,处于语言的流放状态。许多诗人可能用了十年二十年在研习语言,虽然也成天和诗歌‘厮混’在一起,在他们摸索自已的声音之时很容易就妥协了,貌似也有一些成功的‘悄悄话’在一两首中闪现,但在总体语言的把握上却落空了,依然处于成长之痛中”[1]93-94。换言之,诗人要有语言自觉,要有意识地进行语言操练,然后才能有自已的语言,形成自已的诗歌风格。小海由此出发考察车前子的诗歌创作,认为车前子独特的诗歌风格与其独特的语言形式密切相关,“车前子的许多诗歌,是从字、词出发的,对每一个汉字的象形母题进行重新追溯、挖掘,命名意象,其中不乏隐喻、象征、揶揄、蒙太奇等现代技法,目的在于请君入瓮,让读者在他营造的迷宫中徜徉”[1]136。小海从语言的角度来分析车前子的诗歌风格,抓住了其诗歌的主要特点。
语言是人类适应生存的需要而发明的交流工具,在经过了漫长的发展之后,每个字、词都有一个或几个内涵,然后按照一定的规则构成句子、段落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这样语言就有了约定俗成的、大家都须遵守的语法规范。然而,这种约定俗成的语法规范彰显出语言的通约性和共性特质,对追求个性表现的诗人来说则成了一种束缚。诗歌语言是诗人的个性表达与文体创新的重要形式,那么诗人如何才能摆脱束缚创新语言?这是每个诗人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每一次言说,不是使得语言得以更新而是衰减和意义贬值,使用频率越高反而越难以打动人心,就是说量的增加不会带来质的变化,最后反而让人麻木甚至憎恶。无效的重复运用,语言经过磨损、消耗以及意义的稀释,会令读者审美疲惫”[1]96。小海认为,从语言论及诗歌的风格,诗歌的问题就是语法的问题,诗歌的语法就是专政,“诗人不断对外界的刺激和自已的体验加以过滤,去甄别那个诗歌女神的声音。他要用心去倾听,而不是已被尘世污染了变得麻木的那个大脑;他要在所有的言说中去找寻那个召唤他的声音,既有的、现成的语言和词汇常常都变成了障碍,不足以表达这一刻的感受;他要创造一种新鲜的言说方式,语言的局限有时让他绝望和半途而废,他不能拥有他捕捉到的那个声音,他的语言不能及物,有时现成的语言体系会像审判异端一样将那个声音自动赶尽杀绝”[1]442。诗人处于语言的遮蔽之下,对语言产生一种焦虑感,只有打破这种公式化、模式化的语言,创造一种新的言说方式,才能表达出自已对世界的独特认知,呈现出自已独特的思想情感。从这一角度来说,诗人被赋予一种特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传统的语法规范,赋予语言一种新的生命活力,在这种情况下,诗人往往会有一些神来之笔。
语言是在社会生活中产生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从这一角度来说,语言具有时代性和变化性,这也是胡适提倡新文学革命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胡适将语言分为死的语言和活的语言,在他看来,那些远离社会现实生活、已经失去生命活力的语言(文言)是死的语言,而那些在日常生活中运用的口语则是活的语言。实际上,这一理论在今天仍然有效。小海也从这一角度出发阐释诗歌与当下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但他切入的角度有所不同,他认为诗歌语言的生长可分为有机和无机两种,“有机的语言生长离不开天地之气,跳不出自然界,有自已的节奏、呼吸、周期和规律,有‘虫害’和缺陷的,却闪烁着天然、人性的光芒;无机的语言有点像无性繁殖、克隆一样,是机械的,貌似‘无可挑剔’,没有‘瑕疵’,方法论上看却是单一的、单向度的”[1]445。无机的语言就是死的语言,有机的语言就是活的语言,“活的语言是蕴藏于诗人生命之中的,真正的诗人是以其气血精魂维系语言之命脉的,让语言呈现出的是一种心灵的状态”[1]98。活的语言具有及物的功能,它与现实生活、与诗人的内心世界是一体的。小海从语言的角度来分析杜涯的诗歌,认为她的诗歌语言不是高蹈凌虚的文字游戏,“她的语言高度明晰,数字般的精确、透彻,不混浊、不依赖于自相内耗的所谓言语张力”[1]94。小海认为杜涯的诗是架设在语言与现实之间的桥梁,通过活的语言将现实生活与诗人的内在生命联系起来,其诗歌作品具有一种鲜活的生命力。同样,小海从语言的角度来分析李德武的诗歌,考察其人生经历与诗歌创作风格之间的关系,指出北方诗歌与南方诗歌的差异,认为李德武在南方创作的诗歌的语言更加自如、简洁、纯净、灵动,有参禅者的自在与平静,“作为诗人,他是用语言在呼吸。佛说,人的生命就在一呼一吸之间。语言是构成一个诗人的生命,也是生理生命之外的第二生命”[1]453。小海将“用语言呼吸”视为诗人的第二生命,这既指出了李德武诗歌的语言特点,也指出了语言与诗人之间的复杂关系。
诗人的一生都处于与语言进行搏斗的状态,“在半个世纪之间/与名词动词助词形容词和问号在一起/磨炼语言生活直到今天”①谷川俊太郞:《自我介绍》,转引自小海:《小海诗学论稿》,北岳文艺出版社2018 年出版,第344 页。。诗人经过长期的搏斗最终会与语言达成一种共谋,达到一种“相看两不厌”的境界,这种境界的具体表现就是沉默。日本诗人谷川俊太郞认为诗歌的根源是沉默,语言最后的指向是沉默,小海从语言的视角来理解沉默,“也许正是语言的局限性迫使诗人反复追问‘沉默’在诗歌中的意义,从而力图扩展诗歌语言的向度、维度”[1]343。他从语言的角度来分析谷川俊太郞的“沉默诗观”与禅宗之间的关联,指出“诗人在沉思默想中穿越语言的屏障,返回生命的本源,从内观、静思、自省中求得智慧,从沉默中生发诗情。一个悖论是,诗人又时时在用语言和沉默做抗争。因此,他的诗歌中无疑蕴含着‘不以物喜,不以已悲’的洒脱宇宙观和‘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的空灵禅意”[1]344。小海发现了语言和沉默之间的这种悖论关系,并上升到一种语言哲学的高度看待理解诗歌与语言之间的关系。
小海阅读了许多西方的现代哲学理论著作,如维特根斯坦、雅斯贝尔斯等人对语言问题的论述成为小海诗学理论的基础,但他并没有生搬硬套这些理论,而是在理解的基础上灵活地运用这些理论来分析诗人及其诗歌作品,从而将具体的文本分析与理论概括融为一体。
二
诗歌固然是语言的艺术,但小说、散文、戏剧同样是语言的艺术,那么诗歌的语言和其他文体的语言有何不同?这不仅是诗人应该思考的问题,也是诗歌评论家应该关注的问题。
中国古代诗歌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文体特征——格律,格律的主要构成因素有平仄、押韵、对仗等,这些因素都与语言密切相关,是充分地利用语言的特点而形成的一套诗学规范。中国的格律诗在唐代发展到了顶峰,此后便开始走下坡路,这也就意味着成熟的格律已经成为诗人创新的束缚。20 世纪初,胡适提倡新文学革命,主张用白话代替文言。在诗歌领域,他提倡诗体大解放,“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样方才可有真正白话诗,方才可以表现白话的文学可能性”[2]。由此,他将传统的格律当作“遗形物”而无情地抛弃了。他主张用白话、口语写自由诗,强调诗歌语言的自然音节。郭沫若在胡适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了自由诗的发展,提出了“内在律”主张,“诗之精神在其内在的韵律(Intrinsic Rhythm),内在的韵律(或曰无形律)并不是什么平上去入,高下抑扬,强弱长短,宫商徵羽;也不是什么双声叠韵,甚么押在句中的韵文!这些都是外在的韵律或有形律(Extraneous Rhythm)。内在的韵律便是情绪的自然消涨”[3]。郭沫若解构了诗歌的外在律,确立了新诗的内在律。胡适和郭沫若的诗学理论阐明了自由诗语言的特征,为后来的自由诗创作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后的新诗创作基本上是沿着胡适、郭沫若所确立的路线向前发展。
胡适提倡用白话写作自由诗,所谓自由诗,就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这大大降低了诗歌写作的难度,并导致诗歌与散文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小,新诗发展表现出一种散文化倾向。尽管如此,许多诗人还是强调诗歌语言的独特性,力求形成自已独特的语言风格。小海对诗歌语言的独特性有着深切的理解,他从诗歌节奏韵律的角度来分析诗歌作品,进而把握诗人独特的语言风格。小海认为,诗歌的音调、语感、句式和内在的韵律、气质是辨识诗人的重要特征,并由此来分析杜涯的诗歌,发现了杜涯诗歌的独特之处,“杜涯的诗歌中有一种当代诗歌中少见的内在韵律——缓缓升起、绵延起伏的音乐之美”[1]101。他特别欣赏杜涯《风》的结尾:“穿林的声色也穿过了云空/告秋风:你不吹送/我心不白,不悦,不化鸿”①杜涯:《风》,转引自小海:《小海诗学论稿》,北岳文艺出版社2018 年出版,第106 页。,认为它“巧妙地化用和接续了古诗的意境和气脉,又彰显了歌者的节律和风度”[1]106。杜涯诗歌中也有一种“沉默”现象,她的部分作品直接用《寂静》《沉默》作为题目,小海不是从哲学孤独的角度来分析这一诗歌现象的,而是从音乐的角度来分析,“在她的许多诗篇中,结束段落或者尾句都以静、空、肃穆、无人之境收场,在整首诗呈现出的寂静与沉默之后,意犹未尽的仍然还是沉默与寂静”[1]110。同样,小海从音调的角度切入讨论吕德安的诗歌创作,认为他的诗歌善于从民谣中汲取营养,其创作从一开始“就显示了一种独特的音调,他是‘他们’诗群的重要诗人,可他的诗歌题材与风格、韵致,使得他显得别具一格”[1]58。小海概括出吕德安诗歌独特的音调,并以此将其与“他们”诗群区别开来。
我们平常所谈论的“诗歌”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形式,即“诗”和“歌”的合称。在古代诗歌中,诗与歌是融为一体的。换言之,诗是可以唱的。但到了现代诗歌中,随着新诗散文化的日趋严重,诗与歌处于一种脱节的状态,诗好像成了只能默读不能朗读更不能吟唱的文体形式。如何解决新诗的散文化问题,成为诗人和诗歌评论家苦苦思考的问题,寻找诗与歌融合,也就成为解决新诗散文化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小海非常关注诗与歌的关系问题,在其文论中经常涉及这一问题。小海从鲍勃·迪伦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谈起,提出了诗与歌的关系问题,从发生学的角度分析诗与歌之间的同体共生关系,小海提及了美国诗人对鲍勃·迪伦作品的评价,“他的作品帮我们恢复了音乐与诗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①转引自小海:《小海诗学论稿》,北岳文艺出版社2018 年出版,第349 页。。小海认为鲍勃·迪伦的获奖对于诗歌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是一次诗与歌跨界密切关联的明证,也堪称是诗歌史与音乐史上的一个传奇,收获了来自诗歌与音乐两个领域人士的关注”[1]349。鲍勃·迪伦的创作实践证明,诗与歌是可以融为一体的,并且诗与歌的合一将会达成一种合作共赢的结局,产生一种一加一大于二的格式塔审美效应。
节奏、韵律、音调既是诗歌的语言特征,也是诗歌的文体特征。小海善于从文体的角度切入诗歌作品及诗人的创作,如对丁及的诗歌创作的探讨,“丁及的诗歌,是他与生活的一种对话文本。对话关系,在他诗歌中,呈现了一种独特的戏剧韵味,这是他基于生活与文本的‘两度言说’”[1]456。小海注意到了丁及诗歌的戏剧化特征,“丁及诗歌中对话关系的确立和戏剧元素的运用,还让诗歌有了注重音律、调节节奏的效果。这是基于对话双方对位关系基础之上的音乐性。这种音乐性内化为个人的节奏与风格,或者说文本与诗人个人精神气质的呼应。与此同时,丁及将这些内心的叙事和独白,情感的能量与释放,巧妙放置于诗歌的空间结构中,从而形成了一种交换、体验的对话关系,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他与生活世界对话的独特文本”[1]460。这样就准确地概括出了丁及诗歌的语言文体特征。小海也注意到车前子从文字出发进行的拆字、拆句实验,“如此一来,车前子的形式印戳又是如此的显明,有时显明到自我风格化了。他的写作貌似随意放逸、漫不经心,其实是最有文体经营意识的一种写作。他想创造一种兼有诗歌体式和诗体论意义的一种诗歌,一种语言现象”[1]138。也许其他人会对车前子的这种探索持有异议,但小海却非常赞赏他的这种文体试验。
长诗是诗歌中一种独特的形式,其语言、结构、节奏等都具有独到之处。小海自已也创作长诗,他对长诗的体裁特征有着深入的了解,认为长诗考验一个诗人综合的制衡能力,长诗要有稳定的创造力来支撑,而不是刹那间的灵感。他由此反思自已《影子之歌》的创作,“《影子之歌》的写作初衷是力求使这部作品成为一个和我设想中的诗歌文本一样,是动态的、创造性的、开放的体验系统,是关联性的关系总和。这个集子里面的《影子之歌》,结构是松散的又是紧致的,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开始循环去读,读其中一节也能代表全部”[1]464。这种诗体带有试验性和先锋性,是诗人的个体特征的具体呈现,“能够被我们看见的,如长诗的总体结构、布局、骨架、形制、脉络、段落、句式等,所组成的仅仅是外在的形式规范,还有一种内在的韵律、气息、呼吸、节奏,那是一种属于个人精神气质层面上的”[1]464-465。他认为自已的《影子之歌》具备了这种潜在的结构。小海从韵律的角度来反思自已的诗歌创作,发现了自已诗歌创作中存在的问题,认为自已在写作《村庄与田园》时存在调息不行的问题,即诗歌自身的节奏和语言呼吸不和谐、不一致,由于诸多原因,他很多年的写作处于时断时续状态,“常常是挤出一点时间仓促记下几句诗行,甚至是心浮气躁的,没有培养、积淀、过滤、安息,等等”[1]440。能够反思,找出自已诗歌所存在的内部问题,这说明诗人很有自知之明。对于小海来说,找到自已的节奏,也就找到了自身言说的方式;改变言说的方式,也就是改变自已的生活方式和写作方式。
小海不仅在诗歌写作过程中大胆地探寻诗歌的节奏、韵律、音调等内在规律,而且也运用这些相关诗学理论来分析诗歌作品,把握诗人的风格,无论是分析诗歌作品,还是讨论诗人的风格,他都能切中要点,抓住要害,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
三
古今中外的诗歌史上出现了一大批经典作品,它们既是后来者学习借鉴的榜样、超越的目标,同时也是诗歌批评家的参照坐标。诗人要与这些经典文本对话,评论家也要与这些经典文本对话。在诗歌评论家的大脑中贮存着大量的诗歌文本,当他们在分析评论某一诗歌作品时就会动用这些文本,自觉或不自觉地要与所要评论的对象进行多维比较,从而判断所要评论的对象与经典文本之间的复杂关系,判断其是否超越了传统的经典文本。从这一角度来说,评论家的阅读视野是否开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评论水平的高低。在现实中某些评论家之所以经常用“之最”之类的词语来吹捧某些作家作品,其阅读视野狭窄是一个重要原因。由此来看,小海的阅读视野非常开阔,他读过大量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并在其脑海中成为一个个诗歌的模板。他在进行诗歌批评时会自觉地将当代诗人的作品与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进行比较,通过与经典的潜对话来发现所要评论对象的优劣成败,从中发现其文学价值与意义。
诗人与经典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关系,诗人既要向经典学习,又要与之对话,同时还要力求摆脱经典的束缚,只有这样才能超越经典,创造出新的经典。如果只是一味地模仿经典,只能成为经典的复制品。通过与经典作家、经典作品的比较,才能看出一个诗人、一部作品是否具有创新性,才能看出他是否对经典构成了挑战,是否具有成为经典的潜质,才能衡量评价一个诗人、一部作品是否具有文学史的地位与意义,这也是小海评论诗人及其作品的一个重要方法。他善于将诗人及其作品放在文学史的坐标上进行纵向或横向的比较,从而确定其文学价值。车前子是小海熟悉并喜欢的诗人,小海认为车前子的诗歌传统是他自已发明的、内生的,同时他又发现了车前子诗歌创作与外国诗歌之间的关系。1991 年,车前子与王绪斌、黄梵和周亚平等人成立“形式主义诗歌小组”,以“反抗第三代诗作为起点”,创办了同仁刊物《原样》,发表了《东方乡村目录》《简谱》《椅子片断》等作品,探讨“文字主义”,进行以拆解文字为实验内容的语言诗写作。“也许是英雄所见,上世纪60 年代的法国,以菲利普·索莱尔斯为代表的一群年轻的知识分子,在巴黎创办了一份文学杂志《原样》,他们怀疑与拒斥一切固有的文学形式和美学原理,认为创作应该以文字为中心,以文本创新为中心,他们的格言是:‘小说不是历险的文字,而是文字的历险。’他们用‘文字主义’来消解与对抗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形成了‘原样派’。虽然中文与法语分属迥然不同的语系,文字构成与规则也各不相同,正如德里达把中国文明命名为‘文字中心主义’文明,跟西方逻各斯‘声音中心主义’截然不同。但这种以文字为中心,以解构现实主义为己任的文学抒写方法上的实验,可以称作‘文字诗’或‘语言诗’,都起到了留存文字文本的效果,中外可谓异曲而同工。”[1]137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指出车前子的诗学理论主张与法国“原样派”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既彰显出车前子“文字诗”的特点,又揭示出其与法国文学之间所存在的影响关系,对帮助读者认识车前子的诗歌理论及创作非常有帮助。
在长诗创作方面,中国传统叙事长诗所取得的成就比较有限,而西方的长诗创作则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长诗创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出现了大量的长诗作品,小海在分析这些作品时经常将西方的经典长诗作为参照系来衡量评价国内诗人及作品,他将任白的长诗《耳语》与艾略特的《荒原》进行比较,有了自已的发现:“《耳语》的艺术结构与艾略特的《荒原》有异曲同工之处,或者说是‘英雄所见’。现实之旅与主人公的追忆悼亡构成了长诗中的两重奏。任白巧妙化用了艾略特《荒原》的复调式结构,比如近景与远景的设置,不断的返场(80 年代的现场)与背离(与现实的当下),以及内在的节奏和韵律。”[1]152艾略特的《荒原》是现代主义诗歌经典,对中国现代诗歌创作影响很大,以前人们更注重从思想主题的角度探讨其对中国诗歌的影响,小海则从结构形式的角度分析《耳语》与《荒原》的相通之处,一方面揭示出《荒原》对《耳语》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指出了《耳语》的文体形式特点。
中国传统诗歌形成了一套系统的诗学理论,有一些独特的诗学理论术语,如“意象”“意境”“境界”“趣味”等,它们既概括出中国传统诗歌的美学风格特征,也是评论诗歌作品的重要标准。小海对中国传统诗学理论并不陌生,他特别喜欢用“趣味”来衡量评价诗歌作品,对“趣味”有着独到的理解。在他看来,“趣味,一般来说,是探究意味的形式,也是艺术家体己的一种自恋方式”[1]138。每个诗人都有自已独特的趣味,“趣味所以独特,是因为趣味中蕴藏着个人密码,常常属于孤芳自赏式的,充溢着‘自拟’与‘自吟’的况味,需要读者具备解码的能力。趣味又是惺惺相惜、相见恨晚的,其弦外之音与言外之意,是只能意会而难以言传的”[1]139。趣味有高下、真假之分,趣味是诗人个性的体现,不属于公共知识范畴,他由此来评论车前子的诗歌,并给以很高的评价:“他的诗歌中有独特的趣味,这种趣味体现在他的审美观上,就是特立独行的、排他性的个人性。这种趣味一旦落入文字,就又成为敞开式的邀约,即文人趣味。”[1]138同时,他还发现了车前子诗歌与中国传统诗歌之间的联系,“车前子诗歌中的一些精彩华章,常常是李渔式的,直接诉诸眼耳鼻舌身的对生活的热爱,起心动念是从身体出发的,从心开始的”[1]139。对于车前子的那些晦涩难懂的先锋试验,小海用形象化的富有诗意的语言来予以理解与表达:“车前子诗歌中常常有一些自已生生蹦出来的单词与意象,不在正常逻辑和秩序中,仿佛后现代的一个舞场里,一串忽明忽暗的光突然照亮了它们,出人意料地在一个瞬间出场了。这是词语的直觉运动,又保持着创作者灵感乍现时词与词的奇特串联方式,可以是传奇般的碎言私语,可以歧路忘羊,可以柳暗花明,可以剑走偏锋,一种直觉甚至错觉的正确打开方式。”[1]141这就像羚羊挂角,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美妙境界。对于小海来说,他与车前子趣味相投,能够理解欣赏车前子诗歌的这种独特趣味。
小海借用中国古代诗学中的“风骨”理论来评论诗人及作品,从诗歌主题、风骨的角度出发探讨杜涯的诗歌,指出其诗歌重要的取法对象是中国古典诗歌,“她的诗中规中矩,是‘一言以蔽之,诗无邪’的当代注脚。她的诗歌中同时兼具中原地理文化的影响,其抒情性又是与《诗经》以降的中国古典诗歌抒情传统是一脉相承的。杜涯的诗歌质朴、典雅、宏阔,有国士之风”[1]88。同时,他也看到了杜涯所接受的外来诗歌影响,指出叶赛宁、荷尔德林、华滋华斯等诗人对其诗歌创作所产生的影响,“这是另一种源头性的探寻,使得她的诗歌中也就饱含和蕴藏了无限精神游历的浪漫主义精粹和追索理想世界的现代主义的人文情怀”[1]93。同时吸取中西诗歌的丰富营养而形成自已血肉,这正是杜涯诗歌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原因。
诗歌批评有多种方式,哪种才是最好的方式?对此人们的看法并不相同。波德莱尔认为,“最好的批评是那种既有趣又有诗意的批评,而不是那种冷冰冰的代数式批评”[4],这种批评方式应是既有诗歌创作经验而又有理论素养的诗人评论家所喜欢并擅长的,这也是小海的诗歌批评的基本特点。在评论过程中,他不是简单地套用相关理论来分析作品,而是在理解的基础上灵活地将其化用,并运用形象化的语言来阐明抽象的学理问题,加之他与所批评的诗人多有交往,了解他们的生活经历和创作经历,因此他的诗歌批评显得既有趣味又有诗意。在小海看来,“真正的艺术评论,是相马术而不是拍马术,是艺术上的真知灼见;不是投名状,不是权衡术,不是概念轰炸。它是评论上的‘恶之花’,是诗的直觉与哲学洞见的结合体”[1]356。这是小海对评论的理解,或者说是他对诗歌评论的一种理想的想象,亦或者说是他对自已所写评论的自我期待。我们必须承认,这种理想化的评论与当下的评论界现实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当下评论家与作家的圈子化成为一种令人思考的现象,前不久出现的“贾浅浅事件”就给评论界提出了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高兴地看到,在小海这儿,这种追求已经部分在成为现实,另一部分还有待他在以后的评论生涯中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