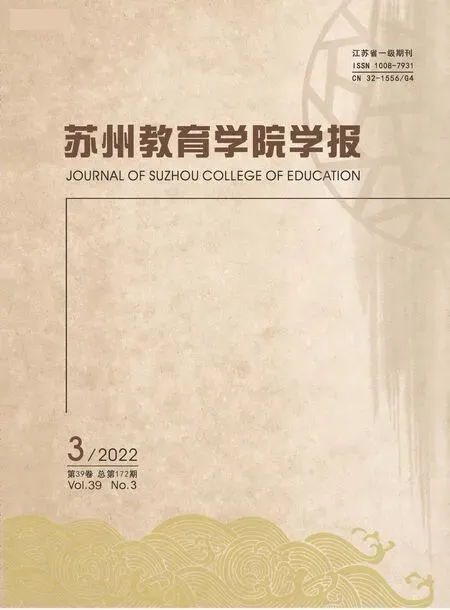小海诗歌:“独异个人”的精神确证和艺术观照
白 杰
(太原师范学院 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12)
自1979 年创作开始,小海已在诗坛行走了四十余年,见证了新时期归来者、朦胧诗、第三代诗歌的演进流变,经历了20 世纪90 年代以来诗坛的裂变、分化与突围,其自身创作也从少年的生命冲动转向青年的生活抒写,再至中年的历史回望,每一阶段在主题、题材、技艺、风格等方面都有调整。值得注意的是,小海诗歌的演变轨迹与诗坛主潮的转向并无直接、明显的关联。哪怕是“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激烈论争,都未在其诗作中留下碰撞印迹。小海的一个重要的诗学价值就在于他主动疏离主流权威,自觉与集团、群落保持距离,在自我流放的过程中完成了“非典型性”写作。在急遽的诗潮起落和时代的错动中,小海的诗歌在持续成长中也保持了某种相当稳定的艺术底色、抒情调式和创作姿态,这与其性格的深思内敛、艺术方式上的间离内视、精神上的返观自省都有密切关联。
一、“独异个人”的精神根基
就作品而言,小海诗歌没有明显的“学徒期”。阅读1980 年他在年仅15 岁写就的《狗在街上跑》,就不得不为其早熟、早慧的心性所折服。诗的首节借助孩童视角讲述了狗的命运:“狗在街上跑/看着我们/向我们摇尾巴/跟着我们奔跑/快快给它东西吃/让它摇尾巴/我们把它打死/又吃了它的肉”[1]3。笔调冷静且略带戏谑,寥寥数笔,即描绘出欢快生命突遭诱杀的惨烈场景,激起人们强烈、持续的情感漩涡。及至第二节,诗人轻轻带出一句,“我们时常往街上跑/因此/我们领略了狗的/快乐和悲伤”[1]3,语义陡然严肃,犹如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2]任一人物都同时接受着“看”与“被看”的双重角色,“我们”在戏狗、食狗之时,又何尝不像狗一样摇尾乞怜去献媚、去乞食,去消解生命的自由与尊严。
很难想象如此深刻之思、悲悯之情竟然出自少年之手。尽管小海涉世未深,文字清浅、纯净,然而其诗却包孕了青年的愤激热烈、中年的睿智通达,甚或老年的宽容慈悲。如果抹去创作时间,我们很容易误将《狗在街上跑》归于中年写作。当然,将此作品置放在20 世纪90 年代或21 世纪的任一时间节点上,也不会感到任何违和。可以看出从创作初始,小海就以过人的天赋据守在时代水平线的艺术高点。
少年时代即拥有如此心智的小海,令人欣喜、羡慕,但也预示了其未来路途的坎坷。无论是行走尘俗世间,还是潜入艺术空间,小海都不断警醒自己,要厘清“人”与“狗”,“我”与“我们”间的界限,一旦不甘寂寞而随波逐流,或为功名诱惑加入“我们”之列,势将沦为“庸众”之一员,状如走狗,为食而奔波,又难逃被食的命运。为此小海自愿踏上一条“荷戟独彷徨”的孤绝道路,无可避免地承受独异个人可能遭遇的孤独、偏见、诅咒和无尽的苦痛。
作为小海的早期代表作之一,《狗在街上的跑》犹如胚胎一般蕴藏了小海成长为“独异个人”的精神基因,相当程度上规约了诗人的价值根基和艺术向度。在此后的40 年里,小海能够在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中安然于边缘者地位,能够无视代际断裂和经典焦虑而静心从事个人化写作,都离不开这份基因的强大作用。内化于生命的诗学观念和写作立场,最终在作品层面得到清晰显现。
小海无意借助某种激进的诗歌观念和先锋的艺术形式去开疆拓土、跑马圈地,争夺话语权,也不屑标举任何旗帜去充当诗派领袖、艺术导师。对他来说,只有忠诚于自我的生命体验,不为一时一派所拘囿,不为集团、群落所裹挟,才能创造出富有个性和生命力的作品。“我要不断地回到我自身,回到源头来,也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地拓展,形成自己的特色,甚至使自己的诗歌有一种体系。”[3]正因如此,小海诗歌的艺术轨迹,很少同构、同频于时代错动和诗潮起落,而是以一种柔和平滑却又异常清晰坚定的方式前行;即或与某一诗派、某一潮流交相叠合,也绝非刻意的追随、附和,而是自我精神理路和艺术探索实践在行进过程中所发生的自然契合,一切都自在从容、精熟畅达。
在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风起云涌的诗歌运动中,小海的诗学抱负显得非常不合时宜,甚至带有一些乌托邦的色彩,个体的生命书写总不如集团作战更引人注目,内心吟唱难以被广场集会所聆听,但小海没有表现出任何愤愤不平。他坚信诗歌是个体劳动,真正的诗人愿意为这种劳作方式承担必要的代价,“纵观当代诗坛,投机取巧、苟且钻营、结党营私、盲目短视、夜郎自大……,不少诗人忽视了诗歌产生之于诗人个体劳动这种健康、正常的关系,忽略了诗人必须为此付出代价这个关键环节”,“这代价有时是残酷的、致命的,但也不是逼迫的,是诗人自愿的,非如此不可”。[4]
小海长期驻留在诗歌现场,亲历了许多重要运动、事件的发生,譬如参与了作为第三代诗歌重要的策源地——《他们》——内部期刊的创办,但他仍以旁观审慎的态度远观诗坛变局,不愿轻易认同、追随。当反理想、反文化、反崇高的旗帜遍布山头时,小海在严肃思考诗歌与民族传统的关联,“中国古典诗歌不断回到民间、回到源头获取营养,不断获得返本开新的能力,这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实践,无疑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5]240;当“诗到语言为止”[5]162俨然成为先锋写作的律令时,小海却严格限定这一策略性提法的效度和边界,“单纯追求语言系统内部操作快感和无序原则的做法是得不偿失的”[5]163;当“民间”诗人与“知识分子”诗人势如水火时,小海拒绝选边站队,“我不赞成知识分子写作的主张……但我想指出,知识分子写作不是我的敌人,我的敌人还是我自己”[6]。
秉持“独异个人”的精神姿态,小海在众声喧哗的时代语境中争取到了难能可贵的独立思考空间,习惯性地以“我”来质询、校验、修正“我们”,始终将“这一个”置于“这一类”之上。他宁可忍受独立探索所带来的迷茫无助和孤独寂寞,也不愿为获得集团声援和群体认同而盲目加入“我们”。他对诗坛许多激进主张的纠偏,容易给人留下保守、中庸的印象,似乎无论在理论建构,还是在创作实践上都缺少锋芒,偏于保守一派。但其实小海更具远见地看到了一轮轮“推倒——重建”的理论主张和运动实践所带来的方向错乱和严重内耗,故而先行一步、先着一棋,更早展开否定之否定的先锋探索。唯独异之个人,方可拥有开阔眼界,去偏颇、存中正,独领诗坛风骚。这一过程会异常漫长,因为这不仅是对诗歌技艺的检验,更是对诗歌信仰的考验。
二、戏剧场景中的抒情
小海长于抒情短诗创作,包括诗剧《大秦帝国》[7]、《影子之歌》[8]也是由诸多抒情短诗组成。这类作品个人化风格鲜明,具有较高的辨识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对戏剧技法的吸纳。通常来讲,各类文体承担着相对明确的功能分工,诗歌、散文主情,小说、戏剧主事。但事实上,诗歌往往具备一些戏剧性特征,抒情诗亦不例外。新批评派主将兰色姆就充分意识到戏剧场景在抒情诗中的作用,“要理解诗歌,‘戏剧情境’差不多应是第一门径……抒情诗脱胎于戏剧独白。抒情诗完全可以直抒胸臆般‘慷慨陈词’,但它更喜欢让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一员作为‘人物’代言”[9]。小海就在戏剧场景的创设方面作出了一些卓有成效的探索。
小海的抒情方式相当内敛节制,既不是郭沫若、惠特曼一路的袒露胸怀、恣意喷发,也不似废名、卞之琳那样沉溺于冥想玄思,他的情感往往隐匿于雅致疏落的画面之后。读者首先触摸到的是偏于静态的场景描绘。乍一看来,这一技法或美学效果并无任何新奇,毕竟中国古典诗歌所尊崇的“意境”就是要绘制浑然圆融的画面。但究其实质,二者有很大区别。古典诗歌所表现的是那种天人合一、主客交融、物我两忘的东方美学境界,而小海的抒情主体却跳脱画面,以旁观者、台下观众的身份去绘制场景。抒情主体后撤、隐匿,使场景趋向某种自然主义状态,人、物、景都被还原为原初的物质状态。由于抽离了社会政治的背板,清除了历史文化的色彩,诗歌场景变得异常简约、清新、自然。
抒情主体和抒情对象之间的“间离”关系,不仅为作品带来了“陌生化”的美学效果,更重要的是破除了读者习惯性捕捉诗人情绪而产生的精神幻觉和审美惰性,使其保持理智的思考、敏锐的知觉,诚如布莱希特在论述“记叙性戏剧”时所说的,“让观众对所描绘的事件,有一个分析和批判该事件的立场”①转引自童道明:《对布莱希特戏剧理论的几点认识》,《论布莱希特戏剧艺术》,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 年出版,第26 页。。
《必须弯腰拔草到午后》一诗就是由数帧摄影画面连缀而成的。它没有直接的情感表露,甚至连人物独白、对白都取消了,场景中的全部人物和事件几乎就是男孩、女孩不断地“弯腰拔草”,画面显得单调乏味、空空落落。但同时,抒情主体的缺位,却又为读者的创造性阅读创造了条件,或为类似于罗兰·巴特所说的可写性文本②参见罗兰·巴特:《罗兰·巴特:作者的死亡》,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11/2011-11-07/104997.html。提供了可能,使读者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去填充画面中的空白区域。
男孩、女孩过早地放弃了孩童的嬉戏游乐而从事繁复的农事劳作,是为命运所限,“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在拔草”;是为生存所迫,“如果不让它们枯掉/谁来除害虫”。[1]46在苦难生活的重压下,其内心似乎是空洞苍白的,没有勇气去追逐信仰、反抗命运、创造人生,所能做的仅仅是,“有时候/他停下来/看手背/也看看自己的脚跟”[1]46。何时才能结束此般畸态的生活,挺直腰板、眺望远方呢?哀恸之心、愤激之情溢于言表,但这样的情感,不是作者直接抒发的,而是读者经由作者营构的客观化的戏剧场景而生发的主观体验。
《男孩和女孩》一诗同样是戏剧场景的典范文本。无论是男孩、女孩最初的相恋,还是阴阳相隔,诗人都极尽保持客观叙述的笔调。浪漫缠绵的两性爱恋被抽象为“居然/发现一个女孩/也适合他”[1]48,男孩因车祸惨烈丧生被轻描淡写为“男孩后来撞山了/连同他所坐的公交车”[1]49,没有甜甜蜜蜜,也没有悲悲戚戚,诗人的“零度叙述”丝毫不会削弱读者为有情人难成眷属的喟叹;相反,读者会在抒情主体有意间离出的情感真空中更加自觉、充分地去体味、思考命运的无常,进而予以形而上的哲学观照,将激荡内心的复杂情绪谱成一曲雄浑庄严的弥撒曲,“偶然加意外/才成全了世界的总和”,“世界/将分解为明天/以及,未来的/男孩和女孩”。[1]49
三、别具一格的素描风景画
小海抒情短诗有强烈的画面感,所呈现的画面一般尺幅较小,背景素洁纯净,所绘事物多见于日常生活。他非常注重事物间的空间关系以及轮廓、细节的描绘,精心于色彩、明暗、质感的调配等,他的诗作给人一种素描风景画的印象。
《有鸟儿的风景》一诗的构图就非常精巧。首节聚焦于冬日鸟巢,“寒冬里/光秃树梢上的/鸟巢,逐一现身/却难觅鸟儿的身影”[1]169。图中景物稀疏,且均以速写勾勒,不多施一分颜色,不多添一枝一叶,画面保持大面积留白。处在画面中心的“秃树”与“鸟巢”被置于白色幕景上,形成了“灰/ 白”“有限/ 无限”的强烈反差,“鸟儿”与“鸟巢”也存在“有/ 无”“静/动”“生机/死灭”的鲜明对照。诗人聚焦于“在场”的“秃树”和“鸟巢”,但实际上是在反复召唤“缺位”的“鸟儿”,只是呼而不得,更突显了万物萧瑟。进入第二节,诗人兴致勃勃地迎接春天,可春景图中的事物依然寥寥无几,仅有“树叶”“鸟儿”和“巢”,“树叶长起来/鸟儿们渐渐飞回/听得到喧叫/却再也看不到/它们的巢了”[1]169。候鸟归巢,秃树抽新叶,已然宣告了春的到来,但春景的明媚盎然,还需在虚实、隐显的对照空间中加以体现。不可见的“喧叫”写出了鸟儿的繁多,隐失的鸟巢写出了树的茂密,画面无一处不为生命活力所充塞激荡。形式上看似单一素朴的平面图景,内中却搭建了多维度的比照空间;看似恣意点染的笔墨,实际上却力透纸背,神韵尽得。
不妨再取《店主与鸟儿》一诗来分析。首节表现为,“今天,那个年轻的店主/打开了鸟笼/让鸟儿自由地/飞翔在/货架上”[1]16,画面幕景是堆满货架的小店铺,空间异常杂乱拥挤。鸟儿从笼子到货架的腾挪,就已唤作“飞翔”,自由之局限、生命之禁锢可见一斑。进入第二节,画面迅速切换,“晨光/照耀着/广场上的/白云和积雪”[1]16,虽然“广场”亦有边界,但与小店铺相比已足够开阔。再有“晨光”“白云”“积雪”等意象都偏于亮色,并且有一定的时空感,它们远远突破了画面的限制,营造出明丽辉煌、辽阔无垠的境界,表达了诗人向往自由的情感体验和生命空间。
小海这类题材的诗歌具有很强写实性,主题、语言、意象等都很贴近日常生活的原生态,所营构的画面也如同风景写生、静物素描。但事实上,从观照对象的择取到空间结构的设置,再到色彩、光线的调配,每一元素、每一环节都离不开诗人的精心安排与情感投射。我们所看到的写实图景,更准确地说是展现诗人内心的真实。而这也如画家塞尚所言:“绘画并不只是要追求外表上的完美画面而已,而是透过不断的创作,来逼现隐含在完美之后的绝对与真实。”①参见梅洛-庞蒂著、张颖译:《塞尚的怀疑》,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1025/11/40249364_697947573.shtml。小海诗歌中的画面,一景一物都是主体的凝视,都灌注着生命的信息。
小海写诗是其生命的内在需求,正是通过写诗才得以不断确认自我、坚守自我、超越自我,在“独异个人”的道路上一往无前。诗歌写作是诗人对自身精神状态的一种评估,也是一种命运使然;当诗歌真正扎根于生命时,那么写作就少了许多集团式的运动和自我的分裂、拧巴,“写作在今天看来是不需用坚持或者坚守这个词了,常常自然得像是生活自己在展开”[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