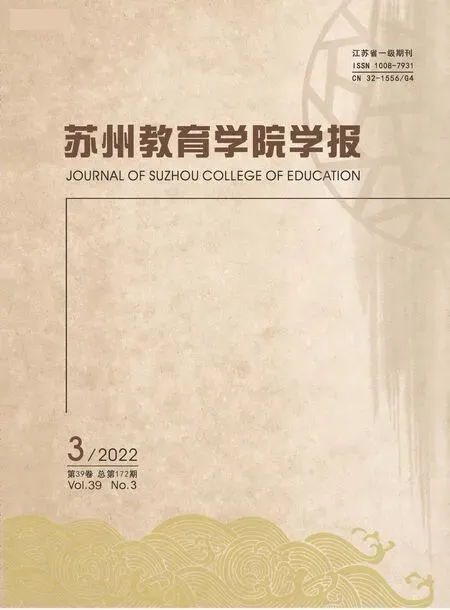诗是发现自我并重构关系的认知事件
——论小海的诗
陈爱中
(广西民族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如果算上小海将自己诗歌写作的精神谱系放置在“中国新诗派”诗人陈敬容那里的话,在百余年的汉语新诗史上,小海的诗歌创作是具有诗歌“史”的逻辑结构的。小海从改革开放初期接受陈敬容的指导和推介,到20 世纪80 年代和韩东等人创立“他们”诗群,在第三代诗歌的浪潮中成熟,并有作品入选《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1]、《朦胧诗后——中国先锋诗选》[2]等标志性诗歌选本,这些都可视为其写作历程中的重要事件。20世纪90年代,《北凌河》[3]、《村庄与田园——小海和他的诗歌》(以下简称《村庄与田园》)[4]系列组诗问世,小海构建出属于自己的故乡写作的精神谱系,这可以看作是小海积累个人经验的重要阶段。进入不惑之年,小海的诗风有了新变,创作出《大秦帝国》[5]和《影子之歌》[6]。从史学意识的维度来看,小海的诗歌创作彰显出汉语新诗不断解构农耕叙事结构而趋于现代性的建构方向,在发现自我与重构万物关系中,呈现为重要的认知事件。
一、社团化生存:自我还是“他们”
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民间刊物为核心的社团化状态是汉语新诗的生成方式,这是百年汉语新诗在现代身份认同上理性预设的延续。据诗人韩东回忆:“和20 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相比,诗歌界的气氛已经为之一变,文学社团在全国全面开花,可以说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人以文学或诗歌的名义结社。众多的文学社有民间的,也有官方批准的,亦有半民半官的,遍及学校、工厂和机关单位。”[7]韩东、于坚、小海等人创办的《他们》杂志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尽管“《他们》杂志既无纲领、宣言,也没有统一的写作原则,本质上就是一个空间,供相互欣赏的作家、诗人自由进出其间。以作者为本,作品直接呈现——后来的《他们》历史证明这个名字是恰如其分的”[7]。从《他们》创办者的回忆来看,这显然不是一次简单的“沙龙”聚会,而是理性的诗歌活动,前有《老家》杂志作铺垫,后有一系列回忆文章为之总结,主要是在诗歌文本的刊发上有着清晰的美学边界。20 世纪末,韩东在与于坚等“他们”诗人的一次对话中说:“《他们》到今天,并未四分五裂。十几年来,新老《他们》交替重叠,但以艺术为准则的评判原则并未改变。”[8]于坚干脆地回应说:“非常纯粹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团体就是《他们》。”[8]后来,小海曾以关于《他们》为题写过三篇对“他们”的回忆性文章,分别发表在《上海文学》《美术文献》《西湖》上,他以在场者的身份对这个诗歌社团进行了梳理,小海与韩东一样对“他们”诗歌社团的认同是清晰的。[9-11]正如柏桦评价的那样:“语言消解了抒情的权势,诗歌回到了语言并从政治、社会、道德、价值中脱颖而出。”[12]188这实际上是应和韩东“诗到语言为止”的观点。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作为以诗歌为主的“他们”从1985 年开始出版《他们》,无论是创办者,还是后来者都对《他们》津津乐道,就如朱文若干年后所言:“谈论诗歌不谈论《他们》,你们还谈什么?包括当代文学也是这样。我以前不愿谈论《他们》,怕别人说抱成团什么的。现在我特别愿意谈《他们》。”[12]188小海对《他们》的主要办刊人韩东是非常敬佩的,对他在“他们”中的地位评价也是固定的:“《他们》是一份民间文学刊物,1985 年创办于南京,截至1995 年,一共出过九辑。韩东是这份刊物实际上的主编和‘灵魂’人物,他对诗歌的理解和个人趣味对刊物有很大的影响。”[13]
“他们”诗派中的同道人扮演的诗歌史家的角色,与民国时期的那些诗歌社团的“局中人”对结社的态度和文学立场的看法是相反的。众所周知,由于民国时期的诗歌社团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再加上新诗的写作本身就强调个人经验,和而不群,这就决定了很多诗歌社团犹如“一盘散沙”。叶公超在20 世纪80 年代的一篇演讲中对新月社有这样的评述:“‘新月’不是一个正式的社团,最初是民国十三年在北平的一些教授们,其中包括有胡适、徐志摩、饶孟侃、闻一多、叶公超等人定期聚餐的一种集会。虽然是由徐志摩所集成,但是他这个人既不会反对什么,也不会坚持什么,只是想到要做,就拉了一些朋友,一些真正的朋友。因此,没有领袖,也没有组织,七八个人,几乎是轮流着到各人家里聚会谈天。”①转引自尹在勤:《新月社的形成——新月派研究之一》,《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 年第1 期,第61——67 页。徐志摩和梁实秋也表达过类似的看法,甚至不承认有文学史意义上的新月社或者新月诗社的存在。实际上,1949 年以前的汉语新诗社团基本是以某一种传播媒介为核心而取得在诗歌史上的地位的,如新月诗社与《新月》杂志,戴望舒、施蛰存等因为常在《现代》杂志上发表诗作而成为“现代派”,20 世纪40 年代的西南联大诗人群也因为《中国新诗》而被称为“中国新诗派”。严格来说,这种命名显然只是诗歌史便于叙述的需要,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概念框定,并没有鲜明的理论旗帜,即便如闻一多在《诗的格律》里提出“三美”主张,但在写作现实中,连他自己也没有多少成熟的样本可供参考。
因此,正是对《他们》的归属感,使小海早期的汉语新诗具有鲜明的“他们”的美学风格,如《搭车》里的口语化描摹:“下午,你搭车/来我这儿/你跟我说过的话可不要忘记/是或者不是/这样的天气承蒙你来看我//你看我变得花言巧语/善于幻想而终归现实/看见你,我打心眼里高兴/你没变,还是老样儿/总喜欢提起往事/在往事里你可不是主角王子之类/你究竟厉害/忧郁也总能化成泪水”[14]10,或者是《少年行》里解构色彩的叙述:“少年的孤独、白蜡、皮影/少年的烟斗,悬吊的猫,遇鬼,被俘/引颈高歌,或者是麻雀们的/无所事事,或者只为我的板凳儿”[14]14,等等。这些作品都较好地消解了朦胧诗色彩的意象式抒情,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以诗集命名的《必须弯腰拔草到午后》的那首诗更是如此,诗中对男孩和女孩生活场景的客观性呈现,很有艺术张力,“男孩和女孩/像他们的父母那样/在拔草//……那些草/一直到她的膝盖/如果不让它们枯掉/谁来除害虫//男孩和女孩/必须弯腰拔草到午后”[14]46-47。这首诗除了对艰辛生活的历史轮回带来的感叹以外,并没有过多的阐释空间,但其中的口语还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实际上,“他们”让诗歌回到了口语语感,回到了“拒绝隐喻”,恢复了最初语词的能指功能,小海就是在这样的诗歌场域里写作的。
如果从汉语新诗的整个发展历程来看,朦胧诗在诗学观念和语言意识上的古典化,已将新时期以来的汉语诗歌引向“歧途”。作为第三代诗歌的主流,“他们”诗派开始对朦胧诗进行反叛,在汉语诗歌获得现代性身份的路途中,“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复现了20 世纪20 年代前后汉语新诗草创期的场景,只不过是在技巧和表现方式上升高了一个维度而已。这一点从胡适《尝试集》中的古风体占优势,到康白情《草儿》、周作人《一条小河》等诗歌中的白描见长,都呈现为对应性的特征,正如新时期提出的“回到五四”的口号一样,汉语新诗也需要类似的回望。写作姿态上的民间性和语词上的口语化,都和胡适强调的作诗如作文和对引车卖浆者之语的青睐相似,或者殊途同归。但开风气不为师,正如20 世纪初期象征派诗人穆木天说胡适是新诗的罪人一样,如果新时期的汉语新诗依然停留在朦胧诗或者第三代诗歌的诗学标准里,显然不是汉语新诗所需要的。这就需要身处其中的诗人们实现从诗学理念到技法的更新。
离开“他们”,或者至少保持必要的距离,是诗人小海对写作的必然要求。
二、北凌河以及海安:为什么总是故乡与童年
20 世纪80 年代,素有“运动”型特征的众多汉语新诗群体,他们在二元对立和追新求异等思维惯性的引导下,在对话语权的争夺远大于汉语新诗本体建设意义的背景下,纷纷打出了各种诗学理论旗帜,一时间旌旗招展,煞是热闹,令人眼花缭乱。在这众多缤纷的旗帜中能够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或者能拿出较为充分的文本来支撑理论主张的并不多见。所以无论提出什么主张或理论,最后的发言权还要归结于创作的实力。对于现代诗而言,雅克·马利坦认为:“诗人的基本的需要是创造;但诗人若不跨越认识自己主观性这一门槛,他是无法进行创造的,尽管这种认识似乎是模糊的。因为诗首先意味着一种本质上是创造性的智性活动。诗赋予事物以形体,而不是被事物所形成。”[15]92-93也就是说,诗人主体要对自我有清醒的认知,并藉此逐步形成处理主体同外界关系的洞察力。对于这种要求,那种基于校园青春荷尔蒙的狂欢化写作显然是权宜之计。进入20 世纪90 年代,诗人们逐步进入中年状态,年轻时的那种激情勃发的荷尔蒙冲动早已让位于沉稳、理性的哲思。换言之,作为从事以个体经验为核心的创造性活动的诗人,一旦消费完外界的刺激,那么其必定要回到自身的建构中,也就是诗人到了要各自寻找家园的时候。哈罗德·布鲁姆认为:“诗歌极少能够帮助我们与他人融为一体;这只是一种美丽的理想主义罢了,除了在某些奇异的时刻,如同坠入爱河那一瞬间。孤独是我们生命状况中较常见的标记;我们如何使这孤独住满人?诗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和更充分地跟自己讲话,以及无意中听到那讲话。”[16]
小海在写作现实上偏离韩东为“他们”设置的理论预设方向,当是其20 世纪90 年代的“北凌河”和“村庄”系列作品的出现。后来,小海将这种转变的潜在线索归结为陈敬容老先生的教诲,“刚刚开始学写诗的时候,/光明、黑暗,白昼、夜晚/这两组词汇几乎是出现频率最高的,/阴影、影子是时常要蹦出的主题词”,诗人将“厚厚一沓子”的《光明和阴影之歌》作品寄给陈敬容点评,结果只有“为了不让乌鸦们飞出来,大地上布满了黑色的绞架”这样的两行诗得到赞许,被用红笔画上波浪线,这让“一颗少年的心就在这红色的五线谱上跳荡不已”(《影子之歌》十三)。[6]23-24
小海“除了早期与‘他们’有些关系,后来则几乎不属于任何诗歌群体或帮派,只认写诗”[17]。对于作家来说,记忆基础上的回忆,是重构自我与周围世界关系的重要依据,也是得以评判现实和想象未来的维度。童年和故乡是所有作家得以叙事的起源,如鲁迅的绍兴、巴金的成都、老舍的北京、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刘震云的河南乡村,等等。在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的衔接口,无论是从古朴、简洁的视角批判城市文明的复杂、狂乱,还是从城市文明的视角反观农耕文明的落后、愚昧,农耕文明的故乡和童年经验都是现当代作家着力经营的精神资源。对于出身乡村的小海来说,当他意识到建构诗人主观性认知的必要性时,乡村是他唯一可以凭借的资源。他重新打量和赋予诗意的乡村就如在《劝喻》一诗中看到的那“一双脚印”,映现出的是对故乡经验的重新发现,“我确信,在这附近/还没有谁有这样的一双大脚/而且,在这个季节/匆匆穿过这不成形的荒芜的坡地/这是只有我才能感知到的/一只神奇的大脚/而不是惯常/我一早起来,仅仅收获它的薄雾”[14]112。
从《男孩和女孩:小海诗集(1980——2012)》中收入的关于小海的《北凌河》和《田园》的诗来看,乡村和田园成就了他诗歌的思想锐度,书写出“异托邦”的景象。20 世纪80 年代初,小海诗歌中的故乡是田园牧歌式的,升起袅袅炊烟般的葱茏诗意,“这些村子的名字/很久就流传下来/而今,这些村子/只有在黄昏来临时/才变得美丽/人们愉快的问候声/也在黄昏,才特别响亮”(《村子》)[14]87-88,亘古不变的生命节律,都来自孕育万物的太阳,“简朴而有节制的生活/都源于太阳”(《太阳》)[14]91。如果只是写这些,小海同样要归于当时流行的“麦子”或者“土地”等乡村意象的共识性写作,就创造性来说,并没有意义。随着20 世纪90年代初的乡村呈现出另一番景象,小海陌生化的诗学经验纷至沓来。在城乡二元对立的格局中,田园荒芜成一片贫瘠的土地,“它要照耀我的生命/最终让我什么都看不见/陌生得成为它/饥腹的果物”,“我怀着绝望的期冀/任由那最后的夜潮/拍打我的田园”(《田园》)。[14]93“我”不得不成为“浪子”,“完全不顾全村老少的反应/就像春分后无缘无故到来的浓雾/一味追逐着内心的秘密召唤”,“屋顶、窗框甚至皮肤/和装扮一新的店堂/都在空中闪烁/放弃退行的巨兽/消失于恐怖的飞行中”(《浪子》)[14]95-96,浪子不再回头,现实的故乡和农耕文明潜意识中的所指都杳然远去。诗人五岁时知晓北凌河,到三十一岁时发现北凌河仍旧没有多大变化,“现在我三十一岁了/那河上/鸟仍在飞/草仍在岸边出生、枯灭/尘埃飘荡在河水里/像那船上的孩子/只是河水依然没有改变”,但我必将老去,“我爱的人/会和我一样老去”,诗人用复踏的语调感叹“逝者如斯夫”,“失去的仅仅是一些白昼、黑夜/永远不变的是那条流动的大河”(《北凌河》)[14]120-121。于是,我们看到海安的河堤“像突然降落一阵风/野蜂追着大堤飞过/天黑以前,蜂巢/连同留守的王/被人端跑”(《河堤》)[14]97,淹毙的童年伙伴让回忆变得凄凉,“和村上的鬼魂握手言和吧/我回到九月/死者使人英俊、年轻”(《伙伴》)[14]98。村庄不复有灵魂栖息地的安稳,而变成“摇摇欲坠的房子扯着风的四角/遥远的山上,石块是村庄的锁”,充满了不安和固执,“河谷的山羊、海上的乌贼/以及飞过平原的鸟儿/都是我美丽富饶的兄弟”,但这些景象却出现在“两次飓风之间”(《村庄(组诗节选)》之二),[14]102那安逸始终是个转瞬即逝的幻象。在《老地方》一诗中,通过两个村民对一棵树被伐前后的对话,以反讽的方式揭示出人性的荒诞。也许是受陶渊明开创的隐逸风气的影响,农耕文明先天性地同悠闲、素朴的生活状态联接在一起,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乌托邦。废名、沈从文、汪曾祺、海子等都试图构筑这样的精神家园。但现代工业文明却是背离乡村的,是在城镇化的基础上对传统的农耕文化的解构中得来的。告别传统的田园牧歌之后,小海的诗从现代性的角度塑造出一个“异托邦”的乡村,如“他是个浪子/不想家/也不要老婆”(《老家》)[14]4,或者“骆驼死在山中/恐惧使驼峰膨胀/大象死在沙漠/恐惧使心脏缩小/我们死在村庄里/恐惧使全身发绿”(《村庄(组诗节选)》之六)[14]104-105,又或者“是个不愿成为女人之身的女人/将在村庄上度过虚幻的一生”(《村庄(组诗节选)》之十)[14]106,诗人通过现实生活和想象的方式消解掉农耕文明推崇的彪悍的生命力。小海从村庄意象延伸到对传统文化的质疑,他以现代人的真诚和坦率诉说自己对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的隔膜,“今天,我感受到那股气息/却不能持久 不能应和/像沉闷的月明之夜”,与“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中的夜晚怀思相对的,是“我抒写过一个呈现之夜/一个沉痛之夜/一个敦煌的飞天女神/和无法相应的音律/一个失传之夜”(《失传的,沦丧的……》)[14]131,于是他借古人李清照之口喊出了“一个时代的终结”,“我们为什么还要洛阳 开封/还要回到羞愧中去/面对长江的浩浩波涛”(《一个时代的终结》)[14]133-134。
三、观照自我与历史的方法:为什么会有《大秦帝国》《影子之歌》
一般认为,小海2009 年创作的《大秦帝国》和《影子之歌》,当属其转折性的诗作,这几乎是批评家们的共识。
小海在创作《大秦帝国》之前,关注更多的是身边的日常,写历史题材的诗作并不多见。谢林认为“真正的历史学”是“建基于给定事物或现实事物于观念事物的综合”,作为兼具现实性和观念性的东西,“同时超越了现实事物,提升到更高层次的观念事物的领域”。[18]诗人能够从诗学角度将“大秦帝国”的历史内容“提升到更高层次的观念事物的领域”,除了其熟知相关历史资料外,更重要的是,有从容驾驭和整合这些历史资料的能力,并在历史的判断中建构出新的历史观念。从诗剧《大秦帝国》的整体构图来看,涉及嫪毐、始皇帝、李斯、赵姬等众多历史上存在的人物,并重新赋予他们新的生命内涵。比如,作为赵姬男宠的嫪毐从“没学会谋生”的孩子逆袭成“为秦帝国营造了那么多新坟”[5]18的所谓成功者,最后被车裂而死,他的一生也不过是在时代“巨大、静默的尾巴上”,“发出一点声响”[5]18而已。诗人对赵姬的心理分析可谓鞭辟入里,“白天充满黑夜的气息/有人在街道摸索前行……内部的痛苦犹如潮汐/用再现的形式暂时消失/像善于找回梦境的天使”;她和嫪毐生下的两个孩子被杀掉之后,悲凉和爱使她产生幻觉,“摔死的两个孩子受到夸奖/在晨雾中彼此拥抱/直到挂在树枝上的雾/阳光下蛇一样迅速消逝”。[5]18-19诗人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既对嫪毐、赵姬等人物的命运进行了反讽,同时又揭示了人性的丑恶与贪婪。《大秦帝国》这部诗剧涉及诸多历史和故事传说,以及诗人虚构出来的“战神”“秦俑”等意象都能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其架构层层叠叠,秩序井然,起承转合,张弛有度。诗剧共分六章,即《始皇帝诞生》《将士一去不复还》《咸阳宫的骊歌》《帝国回音壁》《秦俑复活》《秦俑颂》。这六章内容内涵丰富,思想深刻。诗人在对《秦俑复活》和《秦俑颂》的吟唱中表现了历史的沧桑感和不屈的民族血性:荆轲刺秦王时的决绝刚烈,“我就是秦帝国天空中的第一道裂纹”[5]40;霸王别姬时的洒脱,“一颗流(将)星衔着神圣使命/静寂中独自离开群体/闪烁牺牲者的耀眼光芒/划过长空,永不回返”[5]40-41。诗剧的尾声将大秦帝国对传统文化的奠基功绩和统一全国的政治贡献通过“秦俑”的倾诉表现出来:“早上出征/不会想着日落后归来/他们使土地有了粘性/山河有了起伏/他们在扬起的漫天风雪里/无声地呼吸//他们是坚不可摧的/就像黄河上的波浪”[5]46。《大秦帝国》对历史的重构,显示出诗人把握历史题材的建构能力。正如里尔克评价歌德的《漫游者》那样:“把故事讲得活灵活现,让读者身临其境,是诗人真实而高明的艺术,——现在的时空仿佛避开读者而去,他不单纯是在感受一件艺术品,由于这件艺术品具有清晰的自然性,使他忘掉了艺术,而体验着其中的情节。读者的感受一定很像看西洋镜的人,他见到了壮丽的景色,并陶醉于其中,甚至还闻到了花香,听见了树叶沙沙响。”[19]
承继《大秦帝国》而来的长诗《影子之歌》则是诗人运用散点透视的技法对影子意象进行发散性想象之作,长诗开篇用排比句式赋予了影子的多种身份与可能性,“是附着于我们身上的祖先”“肉身的盔甲”“当面的背叛”“成为乞丐的国王”“热恋、嫉妒中一生的奴仆”(《影子之歌》一)[6]3,等等。然后在这样的预设中,影子便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童年的影子,“好像是我一个并不存在的同胞弟兄似的”,“在异地老去后的晚年”,“认出了旧时的小主人,/泪水涟涟,失魂落魄”(《影子之歌》二)[6]4,这是经过岁月磨砺,沉淀下来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20]的孤独感;或者是“影子脱口而出的‘否’,/死亡档案里记载的‘是’”(《影子之歌》五十)[6]78之类的荒诞场景;又或者是“如果不是用所谓的文明来装点/如果不是矛盾、对立和拒绝/人就是阴影的玩偶”(《影子之歌》六十二)[6]94这样的带有历史虚无主义色彩的哲理沉思;或者是“影子常常一分为二,/影子是一种实际发生的世界”(《影子之歌》一四三)[6]204之类点破机械认识论的过于简单的鄙陋,等等。如果说《大秦帝国》的结构是闭合的,强调的是逻辑推理格局下的一种有限性的处理关系的能力,那么《影子之歌》则是以开放的姿态将思想的芦苇一根根编织到影子的本质里,宇宙之大,苍蝇之微,哲理之深奥,日常之惊讶,都会在影子的随意赋形中映现出来。
对于现代诗人而言,拥有建构主体性的诗性认知能力,并重建自我与外在世界的关系,实现诗性世界的重构,这是成为真正意义的现代诗人的重要标志,藉此脱离“集体无意识”的浪漫感伤抒情,或者是“他者”意识的复现。对于这种从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有人用诗人主观性的概念来表述,雅克·马利坦说:“诗人的主观性对于诗是何等地重要。不过,我不是指那些多愁善感的读者能从中发现他们自己廉价的奢望的那种轻浮感情的无止境的流泻,历代诗人正是通过这种感情把献给情人和负心人的歌曲疯狂地硬塞给我们。我指的是最深的本体意义上的主观性,也就是说,人的实质的整体,一个朝向自身的世界。”[15]92在这个世界里,主观性建构的诗人主体是自由而完善的,具有重组自我与对周围关系的判断能力和想象能力,“通过把握作为主体的自我便能认识客体。正如神的创造以上帝拥有它自己的本质认识作为先决条件那样,作为诗性创造最初要求的是诗人把对自己主观的把握当做先决条件”[15]92。不妨说,从“他们”的发生学意义上的文本创作,经历《村庄与田园》的经验重构,到《大秦帝国》《影子之歌》的萌生,小海建构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诗人。在究竟是歌德成就了《浮士德》,还是《浮士德》成就了歌德的辩题面前,《大秦帝国》和《影子之歌》让小海的诗歌创作走向了另一个层级,成为新时期,尤其是21 世纪以来的强力诗人,“他们”自此成为背景,一个回味的青春历史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