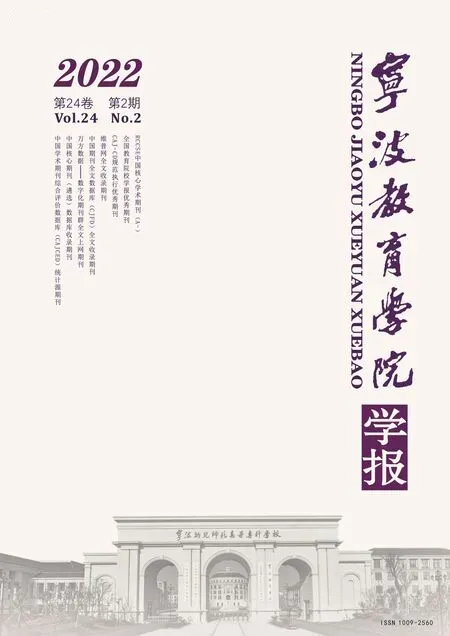从《宁波小说七日报》看晚清通俗小说的现代转型
陈诗雯
(宁波大学 人文与传媒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转型时代”。自“小说界革命”后,先进知识分子一反往昔视小说为“不入流”之定式,纷纷率尔操觚,“残丛小语”一跃坐上了文学的头把交椅,以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寅半生在《小说闲评·叙》中发出了“十年前之世界为八股世界,近则忽变为小说世界”的惊叹。正如范伯群所言:“过去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总是以1917 年肇始的文学革命为界碑,可是中国现代通俗文学步入现代化的进程要比这个年代整整提早了四分之一世纪。”[1]晚清文坛的作品汗牛充栋,埋藏着巨大的文学宝藏,在观念、题材与表达方式上均开始显现“现代”意识,即呈现出明显的转型特质。
宁波最早的文艺期刊是1908 年由倪轶池创刊的《宁波小说七日报》,该刊分设有“小说”“论著”“戏剧”等各栏,甫一面世便大受欢迎,远销海外,后因经费不足仅出12期而停刊。作为宁波第一份文艺期刊,其刊载了极为珍贵的清末小说和文论资料,反映了时代的文学思想以及学术批评,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然迄今为止并未有学者进行研究,其中涉及到的小说也并未见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和遵本照雄《新遍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收录,只有散见于各类报刊史中的零星介绍,或多与谈小莲主编的《小说七日报》所混淆,难以显现其作为宁波第一份文艺期刊所具有的实证性价值。本文将以《宁波小说七日报》为考察对象,在掌握文本的基础上,以通俗小说在清末语境中的创造性转化为线索,审视其在观念、题材及叙事等方面产生的新变。
一、通俗小说在创作观念上的转型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观念。严峻的社会现实使晚清知识分子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国所面临的亡国灭种之灾,志士仁人无不备受帝国主义者的欺凌压迫而痛心疾首。1902 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毅然把“不出诲淫诲盗两端”的中国传统小说推上了“断头台”,正式拉开了“小说界革命”的帷幕,将小说抬到了空前的地位并予以推崇。在此等认识的驱使下,一时间内以启蒙为主旨的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般批量涌现、骤然博兴,小说创作的数量呈现出加速的态势。
从《宁波小说七日报》的发刊词中便可管窥这一旗帜鲜明的政治立场,且在发刊词中有几个信息值得注意:其一,《新小说》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停刊,虽昙花一现,但它的存在一经问世足已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其巨大的冲击力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小说这一文学体裁,如同星星之火,在全社会已成燎原之势,尤其就上海《小说七日报》的成功实践极大地触发了《宁波小说七日报》的仿效;其二,《宁波小说七日报》的主编视小说为“开通风气”“辅助教育”的利器,积极主张用小说对民众进行教育、裨益于社会改良,显然,《宁波小说七日报》承接了梁启超等人提倡的“开发民智、改造国民”的思想,从根本上撼动了人们传统意义上对小说的理解,小说与改良群治之间有着莫大的联系;其三,作者在历数“旧小说之陷溺人群”的情状后,将中国传统小说中的“才子佳人”“英雄豪杰”“神怪魔仙”一并否定,优秀的小说如同广陵散绝、被置于永劫不复之地,其言辞之犀利、行文之激昂几乎可视作为一篇声讨中国旧小说的檄文。虽将“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归咎于“旧小说”俨然有些言过其实,但借此匡救“旧小说”中的腐朽思想,换之以现代民主政治和科学精神的创作主旨是显然易见的。
与此同时,他们还注意到了“小说”这一文体对下层社会平民阶层的巨大作用。痛心于“下等社会之鼓吹为尤艰”,要扭转社会风气,必须加强社会教育。不同于经书、正史等大部头的晦涩难懂,小说的通俗化和雅俗共赏的特性天然与民众欣赏水平相投,具有撼动人心之“不可思议”力量。但面对一批文化层次并不甚高的读者,为了达到宣传和启蒙的目的,唯有使用浅显的语言才能让广大民众参与阅读,在这其中使用白话便成为了当务之急。《宁波小说七日报》充分考虑到了社会各个阶层读者的接受能力和接受心理,在《本报简章》中明确了“本报文字雅俗并行,以便不甚通文理者亦得浏览”的创刊理念,同一杂志、二者兼有,以便最大限度地进行文化普及,迎合各类读者的需求。
在肯定“小说界革命”所带来的功利效果并取得创作繁荣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这种“开口便见喉咙”的创作也在根本上支离了小说本身的审美属性,其所承载的思想内容不断挤兑小说与生俱来的审美娱乐本质。如前所述,出于政治的需要,“梁启超们”揠苗助长般地将小说抬到了“文学之最上乘”的要位,社会的急剧动荡使得小说创作骤然博兴,而当立宪、革命势力落潮后,以“改良社会、辅助教育”为宗旨的作品也在根本上失去了立身的土壤,注定了此类小说终究不能拥有长久的生命力。自第六期始,《宁波小说七日报》就陷入了“经济支绌”的滞销困境,相较原定的出版时间已愆期一个月有余,不得不“为发达商业、推广商务,起见第七期,凡有行号店铺,欲登招徕广告者”(《本报特别启示》)。不难理解,那些“拚将吟风笔,代作警世钟”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只锁定了某类读者群体,其结果必然是刊物只能向某类读者群体提供一种风格的作品,实在难以得到阅读市场的大众认可,这也意味着《宁波小说七日报》自诞生之日起危机已潜伏于期间,也暗示了其终究只有几个月左右的光景。
二、通俗小说在题材内容上的创新
《宁波小说七日报》是在清末特定的历史时代、特殊的文学思潮背景下产生的。赖于小说观念的变革和特殊政治环境的影响,作为“小说界革命”的产物,《宁波小说七日报》中的通俗小说也普遍打上了时代的精神印记,在题材与风格上发生了相应的变革。
《宁波小说七日报》中所刊载的小说大多都与政治相关,包罗世态万象,尤其是记录了大量与预备立宪相关的纪闻报道和言论文章,容纳了作家本人的生活体验和所见所闻,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长篇小说《黑海回澜》(未完)以主人公郑醒华的游历为线索,通过串联起一大堆人物故事,对上海十里洋场、宁波烟馆赌场等社会场景均有真实的记录,反映出了末世封建社会的时代风尚以及世态人情。有感于中国现状,作者“十里花中小隐主”借主人公郑醒华之口对“预备立宪”后出现的怪现象极尽讽刺之能事:
光阴几何,人生易老……但朝廷力尚维新、预备立宪、岂知至今并没有实际,即如近来国会,约以九年,当国会年限未发表的时候,那一省、那一州没有请愿书,一闻有九年之诏,各省噤同寒蝉,也不言九年内如何整顿、如何预备。政府固知吾国民之易欺,故以九年笼络之。如今中国的现象,如漏船驶至江中,船中人不知堵塞漏处,只顾自己性命,你道可痛不可痛么[2]?
不难看出这段议论于现实有多重的映射含义,不仅写出了作者对清廷立宪诚意的质疑,更暴露了官僚的劣迹丑行,勾勒出了中国官场群丑共舞的末世乱象,而在这种情势下想要“立宪改良”,企图建立一个极文明、极自由的宪政国度终究是痴人说梦,其结局也只能是一场换汤不换药的政治闹剧。
无论任何时候,家长都必须充当孩子100%的可靠后盾、无话不说的朋友的角色。孩子的自信心和安全感来自于家长的支持,而不是打架的能力。这不仅仅是被欺负如何解决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孩子未来一生的成长。当你让孩子“被欺负了就自己打回去,别来找我”, 那可能孩子遇到任何事情,不管自己能否解决,一辈子都不会来找你了。
庚子事变后,清政府由盲目排外变为一味媚外,于1901 年1 月下诏宣布实行新政,派遣留学生即是新政之一。随着留学潮的兴起和留学生数量的激增,固然一部分青年留洋学生担负起了救国图强的重任,然而实际达到人们预期的新学青年却少之又少,反倒是那些无才无行、把接受新式教育当作自己发迹晋身的青年占大多数。短篇小说《留学生》刊载于《宁波小说七日报》第一期,在病骸(庄禹梅)的笔下就记录了甬籍一个不学无术的少年通过自费留学回国后摇身一变为“地方学务”,甚至还要“作蒙使馆”教书育人的故事,然而实际上这个张某既不学无术,又品质败坏、以吃喝嫖赌为能事,如同一个跳梁小丑在社会上沽名钓誉,正如作者在文末所言“此实录也,留学生之写照也。虽然言乎我友,我汗颜无地”,形象地浓缩了社会上某类留学生群体的真实写照。再如,连载于第五、六期的警世小说《迷信圈》就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社会上以装神弄鬼敛财圈钱的故事,表现了作者欲改革习俗、破除迷信的愿望和决心。小说写的是一个“以巫祝为业”的张某在穷困潦倒之际找到了老乡冀其照拂,在这位“高人”的指引下,二人利用鬼神之说谋获了大量“酷信寿祝”土财主陈某的金银财物,而所谓“巨人之迹”“张巫之疾”实际上只不过是别有用心之人假借鬼神敛财的惯用伎俩,尤其是作者对杨某算卦时那“手捻烟袋,皱眉、蹙额、摇首,再叹息不已”神神叨叨的神态拿捏,可谓精准地活画了这类招摇撞骗假算命先生的丑态,无情地剥下了他们身上乔装的画皮,还原出其丑陋无耻的嘴脸。
可以说,处于变革时代而创作的这类新小说,摆脱了旧小说只写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才子佳人的话题,不再假借于过去发生的事件,而将广阔的社会现实作为描写的对象,直面人间百态,以暴露黑暗、批判现实为取材,将晚清社会的阴暗面批判得淋漓尽致,而这一部分小说不仅保存了预备立宪等重要的社会变迁史料,也有力地影响了“五四”新文学中“问题小说”的创作,直接参与了近代小说在题材内容上的转型进程。
三、通俗小说在叙事艺术上的变革
清末小说在“小说界革命”的影响下呈现出了多样化的局面,在表现形式上也相应地呈现出了新的格局,尤其是伴随着晚清报刊业的日益繁盛,小说这一文体也相应地有了史无前例的突破性发展。“晚清小说是一个巨大的坩锅,传统叙事手法和试验性的革新手段在此熔为一体。”[3]可谓一语道出了其中的箴言。受新的传播方式影响,“新小说”不仅借着报刊业的东风迎来了创作数量的激增,随写随刊的发行方式也在无形中重塑着小说的面貌。
在叙事艺术上,《宁波小说七日报》中的章回体小说开始采用了“旅行者的限知叙事”,突破了传统章回小说的全知全能。晚清社会乱象迭生,“旅行者视角”便于记录见闻、尽可能囊括了时代的巨变,无疑成为了反映乱象的绝佳手段,连载于《宁波小说七日报》的《黑海回澜》即是一例。《黑海回澜》从主人公郑醒华视角出发,以“旅行者”的身份记录了其所观察的社会状况,勾连宁波、上海、杭州等地,也由他带出了社会上烟鬼无赖、妓女老鸨、纨绔子弟、洋行买办等诸色人种。作为小说的叙事线索,郑醒华的行踪不仅贯串起了相对琐碎的各个故事,借其耳目也让我们清晰地感受到了当时社会在轰轰烈烈、红红火火的“新政改良”下,骨子里却没有一点实质性的变化:吸水烟的依旧吸水烟、轧姘头的照旧轧姘头,假借“自由”之名却行放纵之实的“假志士”不乏其人,甚至还出现了借“新政”之名图谋私利的局面。通过他走南闯北时的见闻,以实录的方式客观地呈现了当时社会在推行立宪时的窘迫和艰难。倘若涉及郑醒华不在场而发生的事情,作者也不会代主人公来补述,而是“命旅行者拉长耳朵倾听各种‘友人云’或‘邻女闻’”[4],务必使第三人称叙事者始终在场。例如第二回,正当郑醒华大梦初醒,好友潘哀陆便上门寻访,听他讲述了当下新式学堂在一帮乡愚的操纵下竟成了投机倒把的盈利工具;在第五回中,郑醒华来到了上海外滩,听友竺虚中道出了当下官场“谋划几千两银子”便可官运亨通的事实。很明显,作者希望尽可能地将现实世界纳入郑醒华的眼睛,即使在郑醒华的身上发生不了这么多事,作者也会略作变通,安排一连串人物不断给他“讲故事”,这就抛弃了以往说书人全知全能的腔调,增加了叙事的真实感,使中国小说由传统的权威叙事开始向人物叙事过渡。
此外,在短篇小说中同样出现了新变,如短篇小说《拒款会》开头的一段描写:
拒款——拒款——
开会——开会——
标斗大红,大书特书曰:《江浙铁道之拒款会》
会之场宽敞,
会之台崇高,
会之内,表面国民,冲口祖国之青年志士猬集[5]。
与中国传统短篇小说大多“起笔多平铺,结笔多圆满”(徐念慈语)大相径庭的是,此篇开头并不作任何铺垫而直接奔入主题:开会前这帮西装革履的“爱国之青年志士”无不热血沸腾,张嘴闭嘴把“拒款”挂在嘴边,可一到需要他们“募款”的时候,全场便鸦雀不惊、万籁俱寂,“咸相顾而莫知所对”。在《拒款会》中没有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情节,也不像过去那样追求情节的离曲折奇和跌宕起伏,它更像是一件事情的“速写”,但就是在这个短短的片段中却完美地将社会上一批所谓“爱国青年志士”的肮脏丑恶嘴脸展现的淋漓尽致。而此类“经济”的写法就非常类似于“横截面”式结构的短篇小说,它不仅多用“一起之突兀”的布局方法,在叙事中还淡化了故事情节,打破了古代短篇小说中多以情节为中心的写作套路,广泛地影响了小说内部结构的变革。
四、结语
晚清的中国如同一只在狂风巨浪中即将面临倾覆危险的海船,面对窘迫惨淡的现实,有识之士莫不对国家的前途而奔走焦灼。甬上文艺期刊之首《宁波小说七日报》来势汹汹,以“辅助教育、改良社会”为重任,敏感地捕捉到了当时的社会思潮与文学风向,从各个侧面留下了甬上地区文艺界的创作印迹;尽管其去也匆匆、出版未久就遭到了停刊,所刊小说也囿于对社会功用性的强调而忽略了其文学特性,但正如有论者所言,“晚清文学为现代文学提供了多种文学实验的产物”[6],在中国古典小说由传统转向现代的过程中,我们不能抹平晚清小说家为之而付诸的努力,其自觉地革新传统小说理念及创作手法、关注社会和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等,都为新文学的转型提供了必备的文学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