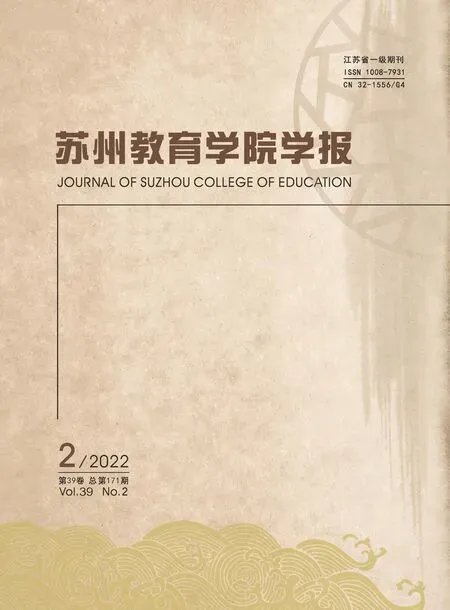作为“记忆之场”的族谱及其民俗学价值*
王霄冰
(中山大学 a.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b.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275)
在传统中国,几乎每个家族都拥有自己的族谱(又称家谱、宗谱)。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修或续修族谱的风气大盛,成为新时期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随着族谱及其所代表的宗族文化重返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族谱的研究也趋于兴盛,甚至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学术分支—谱牒学。族谱对于民俗学、民间文学而言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资料形式。然而,迄今为止,中国民俗学界对于族谱的专门研究却较为少见,只有少数学者在研究传统村落社会及其习俗、秩序的过程中使用了族谱资料,并对族谱中的神话传说、祭拜仪式等进行了讨论。①如刘晓春:《仪式与象征的秩序—一个客家村落的历史、权力与记忆》,商务印书馆2003年出版;张士闪:《乡土社会与乡民的艺术表演—以山东昌邑地区小章竹马为核心个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毕业论文,2005年;张青:《习俗与家族的再生产—基于苏北H村的田野考察》,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毕业论文,2013年;龙圣:《论明代杨家将小说对族群认同的影响—以湖南杨氏家族为例》,《明清小说研究》2014年第3期,第58—68页;张运春:《困局与应对—对沂水刘南宅家族神话的一点看法》,《民俗研究》2017年第6期,第76—84、159页;李海云:《乡土社会边界研究—山东潍北地区东永安村烧祭仪式考察》,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毕业论文,2017年;龙圣:《屯堡家神祭祀的起源与变迁—四川冕宁的案例》,《宁夏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第234—242页;任雅萱:《口头传统与华北宗族历史的叙事结构—以莱芜吕氏祖先传说为中心》,《民族文学研究》2020年第4期,第157—165页。
面对来自民间的数量庞大的族谱资料②参见:国家档案局二处、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图书馆编的《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中华书局1997年出版),共收录451个姓氏的14719种族谱条目;上海图书馆编、王鹤鸣主编的《中国家谱总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共收录2002年之前刊印的中国各民族族谱52401种,全书共10册、1200万字,涵盖608个姓氏。,民俗学似乎还未能找到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西方学者提出的记忆学理论,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族谱的本质与功能,并将其开发为民俗学研究领域有所助益。
一、作为“记忆之场”的族谱
“记忆之场”(lieu de mémoire)概念由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在《历史与记忆之间:记忆场》中提出,但他并没有对此给出一个十分明确的定义,而是提供了一个供人思索和想象的意念框架。[1]94-113在“记忆象征物”这一理念下,“记忆之场”所涉及的范围很广,正如诺拉所言:“我们记忆中那些承载着象征意义的事物:档案以及如蓝白红的国旗,图书馆,字典,博物馆还有诸如纪念庆典,节日,万神庙,凯旋门,拉鲁斯字典以及巴黎公社社员墙。”[1]991984—1992年间诺拉指导编撰了三卷本的法兰西民族的《记忆之场》,2001年慕尼黑一家出版社也发行了三卷本的《德国的记忆之场》,入选其中的事物分别是对于法兰西和德意志这两个民族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事物。这些事物的特征之一,是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并在19世纪的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被不断地重塑和建构,也就是那些被重新“发明的传统”;特征之二,是它们作为文化符号不仅得到大多数法国人和德国人自身的认同,而且也被来自外部的人们公认为是这两个民族和国家的标志性符号。诺拉在《记忆之场》第2卷的引言中就指出:要想理解像法国这样一个尺度的国家的民族传统,我们只有把内部人的看法,即人们假定的对于一项遗产的理解,和使这一遗产客体化并将其建设为‘传统’的那些外部人的看法结合起来。[2]
尽管“记忆之场”概念带有模糊性,但它还是在国际学界迅速传播开来。在英语中它被翻译为realm of memory,德语为Erinnerungsort,汉语学界至今没有固定的译法。笔者此前在一篇文章中将其译为“记忆之所”,[3]冯亚琳和阿斯特莉特·埃尔主编的《文化记忆理论读本》用“记忆场”“记忆场所”“记忆场域”“纪念的场所”等不同译法来指称这一概念,而“记忆之场”的名称则由王晓葵先生最早从日本引入[4]。此处的“场”“所”“场所”是一种比喻说法,带有抽象的意义。它们并非仅就空间性的场所而言,而是包括了空间在内的各种机构性的存在,如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一些被视为“记忆之场”的事物与空间场所毫无关系,如字典和历史书籍等。当然,在汉语中,我们也可以把“场”理解为某个领域,就像通常所谓的“名利场”“官场”“场域”之中的“场”。
欧洲学者有关“记忆之场”的研究,多集中于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出于认同建构的需要而被重新发明的各种文化传统。由于中国的民族众多,国家形态与西方有所不同,不可能形成像西方那样带有单一民族性的现代国家,而只能在承认族群多样性的基础上强调多元一体的中华性特征。因此,中国的记忆文化也就更加丰富且具有多层次性。大传统与小传统、文本与仪式、口头性与书面性、文化记忆与社会记忆交相融合,很难清楚地加以区分。单就历史记忆而言,在存在形式上既有国家层面的正史、文库、博物馆和档案馆,也有地方层面的方志、地方博物馆和档案馆,还有民间层面的野史、文人笔记以及家族层面的族谱。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个层面的记忆形式都是相互关联、互为印证的。以下就以族谱这一文类为例,分析其作为“记忆之场”的文化特征。
首先,从其历史发展脉络来看,随着族谱的现实功能不断走向衰落,其记忆功能日趋增强。族谱的源头,最早可追溯至青铜时代。在西周时期(前1046—前771)遗留下的大量青铜器铭文中较长的一些篇章,如《史墙盘》《逨盘》等铭文都记述了周代贵族的祖先世系。当然,这些铭文还只能算是族谱的前身。真正可以称得上是早期族谱的文本,当数大约成书于战国秦汉时期的《世本》以及《大戴礼记》之“帝系”“五帝德”等篇章。
截至汉代,族谱的编修都由国中的史官负责,因为族谱关乎王公贵族的出身和世系,后者又决定着他们在封建制度下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所以至关重要。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方面皇族谱牒仍然十分重要,如魏、齐两朝的宗正卿、少卿、丞等官职都是专门掌管皇族谱牒的;另一方面,民间修谱也开始兴盛,士族和庶族家庭也都纷纷修谱,国家设有专门的主谱官员和修谱机构,对各地宗族所修的“私谱”进行考核和审定。[5]当时的世族大家编写家谱的目的,一是为了证明其血缘的纯正,以保证本家族的政治地位和享受免除徭役等阶级特权;二是为了贵族家庭之间联姻时查对门第之用,因为当时各大家族在男婚女嫁时讲究门当户对,往往要查阅族谱,避免本族的子女与地位卑下的家庭联姻是这些家族维持其特权地位的策略之一。《魏书·崔巨伦传》有记:“初,巨伦有姊,明惠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内外亲类莫有求者,其家议欲下嫁之。巨伦姑赵国李叔胤之妻,高明慈笃,闻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岂令此女屈事卑族!’乃为子翼纳之。时人叹其义。”[6]与此相对应,庶族—无仕宦或只有极低官位的家庭—修谱,则是为了跻身士族阶层。人们为了提高自身的门第,不惜使用各种手段,伪造家谱之风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如《南史·尚之弟子昌寓传》:“尝有一客姓闵求官,昌寓谓曰:‘君是谁后?’答曰:‘子骞后。’昌寓团扇掩口而笑,谓坐客曰:‘遥遥华胄。’”[7]
隋唐时期,科举制的推行极大地动摇了中国社会固有的等级制度。庶族阶层子弟可以通过读书、参加考试成为国家官员,从而彻底改变家族地位。反之,如果士族家庭三代之内出不了大官,也可能沦落为庶族平民。尽管如此,隋唐两代在宗族管理制度上还是沿用了前代惯例,选官品人和谈婚论嫁时依然讲求士庶门第、等级尊卑。直到唐末五代十国时期,由于连年征战,凭靠战功而不是出身来取得官位的例子逐渐增多,魏晋以来盛行已久的门阀制度日趋消亡。原本用来炫耀门第的家谱在此时也走向低迷,民间修谱的动力明显不如前代。
到了宋代,族谱的政治功能几近消亡,在维护门第的同时,管理宗族、道德教化和历史记忆的功能大为增强。如“族田”记载族内公产,“族规”则被用来统一家族成员的思想行为,根据风水观念做成的“墓图”有时能为宗族之间或族内各房争“风”夺利提供依据。另外,由于官方对民间修谱干预较少,族谱作为民间文献的特征日益显著,除了形式更加自由之外,谱中所记世系的虚假成分也越来越多。到了明清时期,族谱多已放弃只上溯至五世祖的“小宗之法”,而采用“大宗之法”,以标高其家族身世。[8]那些将世系上推至几十乃至上百代、必以古代帝王或名人为先祖的宗族世系图,事实上已不具备历史价值,而更多地带有神话性的文化记忆功能,满足的是人们通过追宗问祖来建立家族与文化认同的需求,客观上也将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即我们通常所谓的“家国情怀”融入到了每个家族的记忆当中。
其次,从族谱的内容来看,所记虽然是家族的过去与现在,但却并非都是真实客观的历史记录,而是带有记忆性文本的特征。即从本族的利益出发,有选择地记载一些能为家族荣誉增光的人物、事件、文章等,有时也允许使用夸张的语言加以渲染。笔者在田野调查中搜集到一本编修于1996年的《大桥金氏宗谱》,其开篇就使用四页纸刊印了用龙纹装饰的四句话:“帝室遗宗裔,金枝玉叶家。诗书礼乐族,文章华国斋。”龙纹一般代表圣旨,但谱中并没有标明这几句话出自哪朝哪代的哪位皇帝,况且把金氏称为帝室后裔,也不符合史实,因为金氏所认的第一代祖先金日磾是汉代北方匈奴族休屠部落的王子,被霍去病俘虏后变为汉臣,汉武帝赐其金姓。他在汉朝虽然得到了重用,官至侯爵,但毕竟不能等同于帝室遗宗。可见这几句题词不过是金氏后人为了往自己脸上贴金而使用“山寨”版圣旨所进行的自我吹嘘罢了。
从族谱的编修方式来看,多是在族内集资,委托族中专人负责。修谱对于一个家族来说是重中之重的大事,当事人的态度不可谓不虔诚,也不可谓不认真。过去在修好新谱之后,旧谱往往要被收集起来销毁。族谱的印制数量也十分有限,且每册都有编号,所藏之处也在“领谱字号”中留下了记录,以便日后统一收回。族谱平时只供族人查阅使用,不可外传。据说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冒宗”和偷印。这些都体现出了族谱所带有的家族档案和“圣书”的特征。但另一方面,“抢夺”修谱权在当代也是十分常见的现象。由于修谱赋予了直接当事人编撰家族历史的话语权,从而间接地映射出了参与者在家族和社会上的地位,所以很多家族成员都以能主持或参与修谱为荣。按照传统的长幼秩序,有关修谱的各项事宜应该由族中长老协商后共同决定。但在近年来的修谱热潮中,经常会看到不在其位而谋其政的“越级”现象,比如在大宗或族中长者长期无所作为的情况下,小宗或一些政治、经济地位较高但辈分不高的家族成员会出面张罗修谱,并主宰了新修族谱的内容和形式。
族谱一般都由以下几部分构成:1.谱名。一般由“地名(里籍)+姓氏+家谱或宗谱”构成,如《秀峰周氏家谱》《紫阳朱氏宗谱》等,有时会请名人题字,如民国时期编修的《清漾毛氏家谱》就请著名学者胡适为其题名。2.目录。有的族谱会在开篇印上古代皇帝御赐的圣旨、匾额题字、诗词,有的会在目录后附上本族的排行字谱。3.谱头或曰卷之首。包括凡例、姓氏源流、历代谱序等。4.祖公遗像、像赞、人物志传、坟茔图、墓志铭。有的族谱印有皇帝颁发给一些家族祖先的敕命诰书,及后者的疏表文书;也有的会收入一些本族祖先及与他们有所交往的社会名流的艺文作品。5.世系图,又叫“牵丝图”“支系图”。用红线标示出各代家族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6.行第,又称“齿序”。按照辈分将同一家族中的男性成员进行排列。7.祠图、祀典与祠享、宗族规范(家规、家训、家语)。包括家族的公产,如祠田、义仓、义学、公有牲畜等,以及捐款、资读、资婚、资殡的相关内容。有的还印有地契合同。8.领谱字号。在最近新修的族谱中往往还有附录或编后记,多记录修谱的前因后果,以及族人为修谱所捐款项的具体数额。
以上除了谱名、凡例、祠图、公产与家规家训等大多是对于现实情况的真实记录之外,敕书、疏表、历代谱序、像赞、墓志铭、艺文等也可被看作是真实的历史文献,但不排除包含有各种牵强附会的因素。世系图和行第中的人名虽然大多也是真实的,但他们并不代表家族的全体成员,因为在修谱时难免会有遗漏,还有些成员因支派相争而故意被省略。其中涉及远代祖先的一些世系牵丝图,则很可能是后人根据家族传说推断连接而成的。
与事实完全无关的则是“谱头”或“卷之首”中有关远代世系的部分,所记载的多是与姓氏来源有关的神话或传说。例如畲族的《马羽雷氏宗谱》中的“雷氏源流序”就记录了畲族的起源神话:高辛氏的皇后刘氏因耳中生了一个东西,被医官取出后变为一条“龙犬”,取名“龙期”,号“盘瓠”。后有外敌来袭,高辛氏出榜招募义士领兵解救国难,并答应功成后把自己的三公主嫁给他。没想到除了龙期没有人敢揭榜。龙期退兵后,高辛氏想用别人代替公主,龙期潜入宫中,在公主腰带上写字作为记号,自己藏在一口金钟下面,预言将在七天七夜后变为人身。但皇后担心他不吃不喝会死去,忍不住在第六天私自窥探,结果发现龙期身体已变为人,但头、发还未成形。高辛氏最终还是把三公主嫁给了他,并加封为“忠勇王”。后来又给他们的三个儿子分别赐姓“盘”“蓝”“雷”。①参见:《马羽雷氏宗谱》卷之一“雷氏源流序”,1932年重修。
和少数民族的神话式书写相比,大部分汉族的姓氏更倾向于以去除神话色彩的历史书写形式来建构本族祖宗和传说时代的三皇五帝之间的传承谱系,内容则多抄袭百家姓源流一类的书籍。①如何光岳:《中华姓氏源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徐铁生:《中华姓氏源流大辞典》,中华书局2014年出版;刘永生:《姓氏源流》,辽海出版社2010年出版,等等。以笔者的王姓为例,在族谱中就被描述为出自上古的姬姓,即黄帝之姓。
姬姓之王源于周族,大约与夏(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前十六世纪)、商(公元前十六世纪—前十一世纪)两族同时,长期居住在今山西渭水中游以北。《史记·周本纪》记载:有邰氏之女名姜原,在野外踩了“巨人”的脚印,就生了一个男孩,名弃。姜原时,周族处于母系氏族时期,她是周族的始祖母。至弃时,已过渡到父系氏族时期,弃是周族的始祖。这个传说,说明周族处于母系氏族过渡到父系氏族时期。弃善于经营农业,尧举他为农师,舜封于邰(今陕西武功),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弃的四世孙公刘时,迁居豳(音:宾,今陕西彬县/旬邑一带)。公刘之后又九世,至古檀父,为躲避戎狄的侵扰,率领族人迁徙到岐山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县)。季历和文王时期,周族击退了西北方向的游牧部落的威胁,兼并了许多部落,文王消灭了崇(今陕西西安沣水西)后,把国都迁到崇的故地,名为丰,亦称丰邑。武王时,把国都迁到镐(今陕西沣水东)。丰、镐相近,均为都城。继后,武王联合周边和方国,打败了商纣王,于公元前十一世纪建立了西周王朝。公元前771年,申侯联合缯侯和戎,举兵攻周,杀幽王于骊山(在今陕西临潼)东南下。是年,宜臼继位,是为平王。次年,平王放弃丰、镐,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武王称帝,传二十三世至灵王,历时五百余年,周灵王废太子晋后,其子孙以王为姓。②参见王荣兰:《王氏姬姓时期发派序》(未刊稿)。文中有注明,该段文字根据张传玺编写的《中国古代史纲(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中的“西周”“春秋”二章整理而成。
对于这样的姓氏源流神话或传说,当事人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会以引述正史中相关叙述的方式以证明其“真实可靠性”,另一方面,大家心里也明知这是一种附会,所以在调查中笔者往往被口头告知,这些内容不一定完全真实。由此可见,记忆不等同于客观的历史,而是人们的一种回忆过去的方式,是他们主观上愿意相信的历史。其中的史实虽不一定可靠,但所反映的文化、情感和心理却是完全真实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族谱对于研究历史的学者而言也许并没有很重要的参考意义,但对于民俗学者而言却是极好的研究资料,因为民俗学所要研究的,正是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域的人们的心态与风习。
二、民俗学的族谱研究
既然族谱之于民俗学而言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那么,民俗学又可以从哪些角度出发去挖掘这类民间文献的学术价值呢?如前所述,迄今为止民俗学对于族谱的研究十分有限,而且往往只是把它作为佐证地方史、家族史、风俗史的参考资料。真正以族谱本身为研究对象的、从民俗学视角出发的中文论文少之又少,且多为硕士论文,关注的多是民间重修家谱的社会风习、仪式内涵及其知识再生产过程。③如周钰:《当代宗族修谱现象研究—以闽西地区为中心》,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硕士毕业论文,2008年;章芳:《农村宗族活动中族员的行为策略研究—以皖南Z县H村建祠修谱事件为例》,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硕士毕业论文,2011年;赵华鹏:《家族行动—镇原慕氏修谱的田野报告》,宁夏大学人文学院硕士毕业论文,2014年;林永雪:《乡村社会的“谱系”与秩序的建构—以小汉镇蓝氏族谱修订为例》,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硕士毕业论文,2017年;史连祥:《在教化中形塑生命共同体—民国〈孔子世家谱〉撰修仪式的文化阐释》,河北大学教育学院硕士毕业论文,2020年。对此笔者以为,民俗学至少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对族谱资料展开研究。
第一,古代神话传说的活态传承以及体现在不同异文中的叙事策略。过去我们通常认为,随着人类科学知识的增长,唯物史观日益得到贯彻,人类在天真蒙昧时期用以解释世界万物起源包括神灵诞生的神话业已消失,在中国,神话已经变为历史或历史性的传说故事。但在民间家谱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大量的神话传说文本的存在。人们对于它们的态度虽然并非全信,但也不是完全不信。在修谱时,这部分内容也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通过比较异文,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神话传说在当代的活态传承形态,其流传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再创作的过程,表现出不同作者的不同叙事风格与策略。①偶有其他专业的研究涉及家谱的叙事模式问题,如王忠田:《私修谱牒叙事的主要模式及文化内涵—以河洛地区若干家族谱牒为例》,湖北师范学院文学院硕士毕业论文,2014年。仍以上述的畲族起源神话为例,在《马羽雷氏宗谱》的版本之外,笔者在网上找到了另外一个出自《盘蓝雷钟氏族谱》的版本。虽然内容大体一致,但一些表述方式还是有所变异的,例如前者称刘皇后梦见“娄宿降凡除夜妖”,后者则直接说是“娄金狗降凡除妖”。当讲到高辛氏试图赖婚的情节时,后者的表达也比前者更明确,说他“假装宫女,称为公主,赐盘瓠为亲”。在讲到龙期献上吴王之头时,后者用的是转述的口吻,并对人物心理有较为细致的描写:“呈上辛帝殿前,头吐在地,龙期奏谕:‘此头是吴王正身也。’辛帝验了将头,心忻大喜,苍天有感,从腾愿心,回想咬时,龙期大有功也。”前者使用的则是更为形象具体的描述和对话的形式:“呈上高辛殿前,头放在地下矣。龙奏曰:‘此是燕寇头首也。’高辛验了,遂大喜曰:‘天下定矣,皆尔有功也。’”②《盘蓝雷钟氏族谱》,http://www.lanshiw.com/bbs/read.php?tid=10875,访问日期:2016年5月25日。该网页目前已不存在,但很多畲族族谱都在“得姓源流”中保留了这则神话。总之,在我们今天已很难通过田野调查搜集到完整的得以活态传承的神话传说文本,而往往只能得到一些碎片化的讲述的情况下,民间家谱中的相关资料可以部分地补足这方面的材料欠缺。尤其是对于我们研究民间讲述中的口头性和书面性问题比较有参考价值。
第二,历代族谱、不同姓氏或支派的族谱以及民间族谱和国家正史之间的互文性。任何参与过修谱的人都知道,族谱的内容很少是原创的,其中大部分都是承袭、翻印前代的族谱,或者摘抄自正史类的文献资料。历代族谱之间、不同姓氏或支派的族谱之间以及族谱和正史之间的互文性,体现出了族谱作为“仪式性文本”的特征,即通过不断重复的讲述和程式化的表达以达到整合历史观与价值观、实现文化认同的目的。每当我们阅读家谱中的文本,往往都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而这种熟悉感恰恰正是认同感所需要的基础。以下摘录壬午年重修《嵩高朱氏宗谱·谱序》中的几段文字为证:
今天下衣冠礼义之士,所以联其宗,尊其祖者,其道有二:一曰宗祠,一曰宗谱。宗祠虽设而古制寝湮,大宗、小宗之法,不复行于天下。有志古礼之家,莫不以宗谱为先;务宗谱之设,盖以导一源而联九族,谨名分而辨昭穆也;其道甚隆,而其义至远矣。
(明)李义壮、稚大甫《江阳嵩高朱氏谱序》
自来九族叙而敦睦之化行,风俗之醇厚,治教之休明,其道皆由于此。迨宗法渐废,族无统纪,盖有亲未尽,而名次不相知,庆吊不相闻,况其远焉者乎?世之仁人君子,思所以反古还醇,收涣散之心,而兴礼让之化,非有谱系以联之,则其道无由矣。
(明)陈吾德《嵩高朱氏族谱序》
民气之涣而不聚也,由其不能服善率教,以归于礼义风化之同。然欲习礼仪,振风化,聚吾民之涣,则道莫重于敦族情,而事莫要于修宗谱。盖宗谱克修,庶几上有所承,而尊祖敬宗之心油然动焉;下有所待,而孝子慈孙之愿蔼然生焉;旁有所治,而合族展亲之念勃然兴焉;其事岂细故哉?
(清)徐敦蕃《嵩高朱氏重修谱序》
当然,在“互文”的同时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变化和创新。特别是在民国和当代续修的族谱中,除了承袭前代的一些说法之外,当事人会根据时代风气的转换而增加一些新的内容。例如嵩高朱氏写于1938年的《续修宗谱序》中就有“五大民族之中国,本诸黄帝之子孙”的说法,显然受到了民国时期“五族共和”思想的影响。而2004年续修的延陵郡珊塘至德堂《吴氏宗谱》序言的开头则明显带有今天的时代特色:
众所周知,家是社会的细胞,家谱是以特殊形式记载本族世系和事迹的历史图籍,涉及历史、人口、经济、人类、遗传等学科,是研究社会发展的重要史料。国家正史、地方志书、各姓氏之家谱是构成中华民族历史的三大支柱,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今读司马迁之《史记》,又阅延陵吴氏宗谱,始知珊塘吴氏,源远流长,今趁续谱之机,将此历史简述如下。并为之序。①浙江衢州石梁珊塘吴氏宗谱续修理事会:《吴氏宗谱》校正本“序言”,2004年11月吉日续修。
事实上,很多新修的族谱都像《吴氏宗谱》一样,直接抄录史书中的一些篇章,或对其加以编写后,作为本族的历史记录在家谱之中。家谱与正史的这种互文性一方面是为了增加族谱的正统性和权威感,另一方面也可看成是社会记忆对文化记忆的一种消化和融合方式,从而使得家谱这种民间文献承载了特别的家国情怀和大一统的中华特征。此外,家谱中的家规、家训往往也体现出了家族小传统与文化大传统融为一体的倾向,例如像“耕读传家”这样的治家格言,还有“仁、义、礼、智、信”等为人处世的原则,都是对儒家社会理想的具体阐释和贯彻执行。
第三,通过修谱行为以及族谱中的世系图和行第排列观察中国家族的组织方式。如前所述,并非所有的家族成员都能进入族谱,有些是因为修谱者的失误而被遗漏,也有一些是因为宗族内部的矛盾而被故意排斥在外。载入家谱的人名在排列上也会有所讲究,仔细考量后便可看出孰轻孰重、孰近孰远。在当代的修谱行为中,则往往根据族人捐款的数目大小决定其在家谱中占据的位置和分量。通过对修谱时族人登记过程的追踪,并将家谱中的人名及其相关信息与现实状况加以对比,就可以发现很多修谱的潜规则,从而揭示中国家族社会的基本运作模式。
第四,族谱的传播及其在地化特征。中国族谱不仅被境内的满族、蒙古族、畲族、回族、纳西族等很多少数民族模仿和接纳,而且也传播至了韩国、越南、日本等地,包括古代的琉球。特别是在韩国,17世纪后汉文族谱一度十分流行,成为了韩国儒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研究,韩国族谱受中国宋代儒学的影响最深,日本、琉球、越南等地的谱书则主要效仿中国晋唐阶段的谱牒。[9]北京图书馆收藏了大量的韩国族谱,而日本、琉球、越南的古代谱书在中国则极为罕见。②上海图书馆藏有一部来自日本的《大藏朝臣原田家历传》,但目前还没有见到国内有相关研究。从记忆文化的视角出发,对来自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族谱的体例、功能、内容、话语等进行比较,特别是对族谱在当代各国社会中的传承情况加以对比,应该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③目前已有一些关于东亚族谱的比较研究,特别是由台湾国学文献馆每两年一次主持召开的“亚洲族谱学术研讨会”在这方面有开启先河之功。但现有的研究多从历史学、谱牒学、文献学、社会学等角度出发,而没有把族谱当成一种文化记忆的载体来考察,也很少有人把族谱看成是民间文学研究的资源。因为集体记忆是由文化所决定的,基于每一个民族对待自身传统的态度,不同的文化记忆也会造就不同的民族气质,并最终改变民族的历史。
民俗学通过对族谱的上述研究,最后还可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即用来自中国乃至东亚各民族的实例,修正和发展由西方学者提出的文化记忆理论,特别是“记忆之场”的相关理论。从以上对于中国族谱的宏观考察出发,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结论,即中国式的文化记忆由国家、地方和家族三个层次的历史记忆相互交织而成,与西方学者针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所提出的单一维度的公共性记忆形式有所不同。在这一多层次的记忆复合体中,礼与俗、文本与仪式、口头性与书面性、大传统与小传统交互作用,从而形成了十分牢固的文化记忆体系。这或许也可看成是人口众多的中华民族为何能够拥有如此巨大的凝聚力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