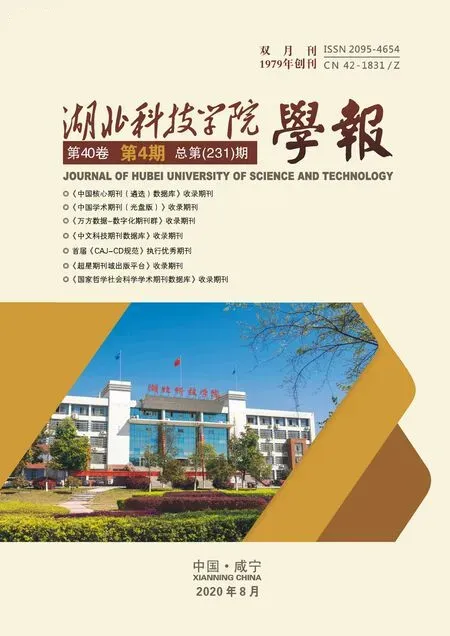延续七百年的生命档案:湖北嘉鱼湖西李氏纂修族谱考述
张 霞,朱志先
(湖北科技学院 人文与传媒学院,湖北 咸宁 437005)
中国传统社会属于宗法伦理性社会,强调以父系血缘为基准形成一定的家庭,由家庭进而扩充为家族,随着人口的增加及各种客观主观的原因,由聚族而居,变为散处各地。但是对于祖先的崇拜,父子、兄弟、同族人的认同是传统家族认同心理的重要表现[1]。在这种心理作用下,居住地距离的远近不影响族人之间的认同。当然,家族认同有多种表现形式,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多种途径来实行。通过编修家谱,明晰世系,确定行辈字号,以文本的形式增强家族的凝聚力及其认同感即为途径之一。诚如苏洵所言“自秦汉以来,仕者不世,然其贤人君子犹能识其先人,或至百世而不绝,无庙无宗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势宜亡而独存,则由有谱之力也”[2](P371)。
族谱是承载一个家族记忆的载体,是族人回顾家族历史、瞻望前贤的有效依据,是一个家族的生命档案。一个有影响的家族会定期整理家族的记忆,使家族历史得以延续,使家族成员具有一定归属感,亦即增强家族成员的家族认同感。“成文族谱的存在,不论其是否刊行,也予人宗族纽带依然维持的宽慰之感”[3](P111)。在传统社会里,嘉鱼湖西李氏属于当地望族,仅有明一代,嘉鱼湖西李氏就产生了六位进士、十余位举人,有以理学扬名的“嘉鱼二李”,以功勋著称的三部尚书李承勋,以清廉直谏享誉的言官李沂,以道德节义被赞述的李宙裘等。李氏家族史从宋代到晚清七百年间,谱系清晰,历历可考。其由在于不同历史阶段,李氏都有编修族谱的活动,根据相关谱序及其他史料所载,从南宋庆元元年到清朝咸丰八年,李氏共有十次大规模的修谱经历。为更好了解这个荆楚右族的历史传承及家族认同,兹从修谱目的、时间、参修人员及族谱特点诸方面,对李氏修谱情况予以考察。
一、嘉鱼湖西李氏历代修谱目的探析
南唐时,李璠由江西武宁迁到嘉鱼,世世耕读于此,以第四世李宗儒、李宗仪创立湖西义学而名播四方,故称其为湖西李氏,但此时段相关事迹留存较少。从第七世李格开始,不同时期,都有相关李氏子弟牵头编修族谱,借以维护和彰显一个地方望族的形象。许孚远在《嘉鱼湖西李氏族谱序》中称修谱的目的在于“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惇族,惇族故重谱”[4](卷一)。修谱是从心理上增强家族成员对宗族的认同感,“我国传统的家族认同心理,是一个多层次的整体结构。它的第一个层次,也是最高的层次,是对祖宗的认同。因为只有在对同一血源的祖先认同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对血缘亲属关系的家族的认同。”[1]除了尊祖、敬宗、惇族,嘉鱼李氏屡次修谱还有如下原因,兹述之。
其一,加强族人之认同感,“知身之所自来”
宋代嘉鱼李氏第七世李格在修谱时,指出“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为人而局天履地,讵可不知其祖之所自。今吾祖虽曰上下宅,而祖派未远,惟不知所自,遂至相疏。今粗录大概,以分示族人,若家置一本以传子孙,庶知身之所自来,亦见亲疏之次序”[5](卷三)。李格希望通过修谱使李氏子弟知道自己源自何处,从而增强家族的凝聚力。李占峥亦言“盛衰之相形,盈虚之迭至,千万人之身,其初一人之身也。岂一人之身,福泽所被顾有钟于此而遗于彼者?岂一人之身,气类所通或有杂于内而信于外者?是又不可不严且慎矣。吾族之人,知有谱则知有身,知身之所至,不忍怠弃,则知一人之身即千万人之身,而本原之地不敢不严,不敢不慎矣”[5](卷三)。亦如科大卫所言“成文族谱成了子孙身份的便利‘证据’”[3](P151)。
李承箕认为一个家族经过数世变迁,子孙繁衍,倘若不及时整理家族史,会导致同宗子弟关系疏远。然而,“家可远也,身不可远也;身可远也,心不可远也。培之则愈崇,疏之则愈深”[5](卷三)。因“分之亲疏,本之源流,无所于征据以永其持循,而生民本末上下逆顺之理,盖荡然矣。”[6](P227)只有通过不断地修撰家谱,才能加强族人之间的认同感,故其叹曰“世慎其支哉!世慎其支哉!”[5](卷三)康熙间,李占颐主持修谱时,指出“夫家之有谱,犹国之有牒也。旧章不率不循,惧其日久而无徵;子姓不收不检,恐致涣散而失序。慎其支者,溯其源也,穷其流也。”[5](卷三)乾隆年间,李正规在续修族谱时,征引元代许衡的观点“管摄人心,和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进而,指出“凡名家巨族皆宜溯其祖宗之所自出,因源寻流,记世系、传世行,以成其谱也”“苟历世久远而族谱不续,其不至相视如途人,并祖宗之嘉言善行湮没无闻也者”,通过修谱达到“和宗族而厚风俗”[5](卷三)。
其二,明晰家族之派字辈分
李承勋《荣四府君继嗣考》载李承箕修谱时,曾与其讨论有关旧谱中是否有需要改定之处。李承勋指出荣四府君李天赋一支因继嗣导致辈分出现淆乱的情况,应该予以改定。于是李承箕在谱中予以注解,使“昭穆之序不紊”[5](卷三);康熙间,李占乾在分析李氏各支谱系时指出,“迨后子姓衍繁,各以庄居。天平之后以李明远传;天文之后以李继名传;天性之后以李公辅传;天岳之后以李仲祥传。派次紊乱,凡三百五十余年,有由来也。其宗仪后子孙,仍遵原派,故今考二十二世荣字派与占字例,详且确矣。中分以往,难以序同。兹值续谱嘉会,凡名远、继明、公辅、仲祥后裔,通序为正大光明四派,俟其毕后,百世子孙另同新派,此亦涣而复萃之道也”,只有通过续修族谱,拨正淆乱之处,才能“联百世之宗亲,序奕祀之昭穆”[5](卷三)。在明辨昭穆、世派清晰的情况下,才不会出现辈分混乱、“族人同宗而通婚姻”的现象[5](卷三)。
其三,传承家族之历史记载
一个绵延不断,枝叶繁茂的家族,如果族人没有载记整理家族历史的习惯,那么这个家族的既往,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烟消云散。嘉鱼李氏的族人,对于家族史颇为关注,尤其是其中的精英人士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家族史得以绵延传承。“很显然,族谱是宗族机构中一个重要的工具。它确定了宗族成员的界限。大约一代或者两代,它便续修,至少认为应该续修,经过一个精心策划和耗费钱财的过程,婚姻的嫁娶、家族成员的生死等累积起来增加到已经记录下来的资料中”[7](P88)。
李承勋曾言:“夫人情,爱之则思敬之,敬之则思永之。闻一善言,见一善行,在疏远犹将速传之,矧其亲乎?吾观旧谱,六世而上多阙文。为是揣一日二日,虑有遗忘,二纪而始续怠缓是惧遽乎哉!”并且在族谱中,“附以墓图志,何也?”其由在于“先人托体之所,敢不慎。诸祖茔散在邻邑,远或数百里,有窃据于人而势未能复者,谱牒无徵故也,大崖常深恨之。吾知惩矣。”[5](卷三)
李占颐指出李氏从光禄大夫李憭修谱到康熙年间,经历了一百多年,“时代变更,兵燹屡经,旧刻无一完片,文献亦多阙略”“倘以数代之湮没无闻,后有作者安稽文献乎?抑保无有星罗棋布,散处东西者乎?此谱之不能不申明于今日也”[5](卷三)。李玉大认为李氏修谱能够保持连续性,其因系“前之作实有望于后之述”,但“年更代嬗,无以联人心之涣,萃宗支之繁,此亦世家巨族所歉然者”[5](卷三)。从康熙年间修谱到乾隆时期经过了六十多年,“族大则生齿日繁,居迁星布,今不更加修辑,则子姓之蔓延四方者日失其绪,而祖宗历来绍修萃涣之意于兹坠矣”[5](卷三)。嘉庆元年,李铭钟又指出乾隆间所修谱经过四十年,族人已很难找到全谱,“倘再迟之岁月不加修辑,安知不澌灭殆尽乎?此即异日有贤子孙恢复前烈,旁搜远绍,其如文之不足何?”[5](卷三)
明清时期,嘉鱼李氏历代族人对家族历史的传承有着危机意识,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家族史能够保存下来,故而每隔数十年就要重修族谱。
其四,宣扬家族之明贤事迹
家谱的修撰不仅是家族史的延续,更是要宣扬家族中的楷模人物,使后辈子孙在瞻仰前贤的基础上学习之。
李承勋言嘉鱼李氏“子姓绳绳,生长日众,中间可法可戒可喜可悼者,无日无之不忍言,不忍不言,或详之,或略之,观者可僾然而深思矣”“吾先人以孝友清白胥教诲,而‘忍让’两字尤我李传心之法,世世谨守,庶不得罪于乡党州闾,而又润之以文章,振之以节行,流风余韵,久而益光,所以庇我后昆者,尽在此而不在彼也。今吾老者宽衣缓步,优游卒岁,少者得肆力于诗书、稼穑之场而无所扰焉,可不知所自耶,可不知所继耶”[5](卷三)。李占颐指出“今夫乾坤,蘧庐也,万物萍聚也,光阴石火也,而惟藉此精神萃合,溯源祖考,启迪来兹,非谱牒何观焉?我李在昔,一时鼎贵,理学、功业、文章,艳称海内”[5](卷三)。乾隆年间,李仕大、李滨大在《李氏合修谱序》曾自豪言嘉鱼李氏“自宗仪、宗儒公大建义学,远贻书香累世,人文有赫,国恩世袭,前谱已备述矣……要以孝友信义培其根,诗书礼乐永其泽。理学则师东峤、大崖公,经济则仿约庵、康惠、幼泉公,世德则怀遂庵公周济三邑,正气则效太清公忠传百代。且若仕钦州之桂西公勳名不替,任丰城之梅庵公词赋奇宕,能近法数公,亦足振先而启后,仰承乾父坤母之化,庶无忝矣”[5](卷三)。嘉庆间,李铭钟亦言“我李之盛于南楚也久矣,其世系之渊源,家声之赫奕,与夫义学、勋名、道德、文章之勒诸鼎彝,垂诸志传者,先人谱之详,亦叙之详矣”[5](卷三)。嘉鱼李氏先贤的种种事迹,正是凭借族谱使李氏后辈膜拜之、仿效之,此可谓一个科举世家历经数百年绵绵不息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嘉鱼湖西李氏修谱时间考述
嘉鱼李氏一世祖南唐时由江西武宁迁往嘉鱼,其曾孙李宗仪、李宗儒于宋朝庆历间居住湖西之滨,建立义学,“延师训其子弟,而同里及蒲圻、咸宁、临湘来会学者率数百人,并廪于李氏,而李氏行谊始高三楚矣”[4](卷一)。对于李氏家族史,到第七世李格始有记载。
嘉鱼湖西李氏第一次修谱,是在1195年,由第七世李格所为,李格称“绍兴以前文籍焚荡,无从考据,故不能备述矣”[5](卷三)。
第二次修谱,具体修谱时间不详,系第十六世李田(1428-1484)主持,据嘉鱼李氏相关谱序,可知李格之后,系李田再次修谱。
第三次修谱于1504年,系第十七世李承箕主持[5](卷三)。
第四次修谱于1530年,系第十七世李承勋主持[5](卷三)。
第五次修谱,具体修谱时间不详,系第十九世李宝蒙(1523-1581)主持[4](卷一)。
第六次修谱于1597年,系第二十世李憭主持[4](卷一)。
第七次修谱于1694年,系第二十二世李占颐主持[5](卷三)。
第八次修谱于1756年,系第二十四世李玉大主持[5](卷三)。
第九次修谱于1796年,系第二十六世李铭钟主持[5](卷三)。
第十次修谱于1858年,系第二十八世李士型[8](P18)。
按:从上述十次修谱的时间来看,明代修谱五次,清代修谱四次。第一次修谱是由第七世李格所修,以二十年一世来计算,距李璠迁到嘉鱼应该有一百余年。而第二次是由第十六世李田所修,以李田的生卒年月及李格的修谱时间,此次修谱距第一次修谱应该有两百余年。第二次修谱到第九次修谱,每次修谱的间隔时间大概是40年左右(除了第三次与第四次之间间隔不到30年),第九次与第十次修谱间隔时间为60余年。
从修谱间隔时间来看,嘉鱼李氏对族谱的编修并非严格按三十年一大修的原则,但从明代到清代,修谱的间隔时间未超过三代。从修谱的代际间隔而言,并没有突破朱熹所言“人家三代不修谱,则为不孝矣”[9](P300)。
从参修者的世系而言,从第十六世到第二十世,历经五世,共修谱五次,可见此段时间内修谱比较频繁,基本上符合家谱三十年一修的说法。而这五代基本属于湖西李氏的鼎盛时期,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望族必修谱的道理。
从修谱者时间意识来说,李承箕曾担心家谱如果不及时编修,会导致部分家族事迹被淡忘,“后之于今犹今之于昔,吾甚惧之,乃续旧谱”[5](卷三)。李承勋言“旧谱创于先伯祖定斋府君,定于先考中丞府君,续于伯氏大崖先生,相去远或八世,近亦三四十年。闻见相质,词义备矣。绝笔甫尔,何续之遽?惧心之萌也。”[5](卷三)李占颐指出“定斋府君之始创,约庵府君暨崖、逊、惕斋诸府君之续修,景颖府君之衍派,中间又隔百十年。至今,生齿日蕃,家规日颓,安得不着意图维者?”[5](卷三)李玉大言“国朝以来,玉祖衡玉公、康惠孙长儒公暨贞子公辈出,亦勤缵述,而旧章为之一新。迄今六十有余岁矣。夫族大则生齿日繁,居迁星布,今不更加修辑,则子姓之蔓延四方者日失其绪,而祖宗历来绍修萃涣之意于兹坠矣。”[5](卷三)嘉庆年间李铭钟有云“国朝贞子公续修,而后至乾隆丙子年间,虽又有偏瑞班公续修,而刷印未编,越今四十年,族中已不复见全谱矣。倘再迟之岁月不加修辑,安知不澌灭殆尽乎?”[5](卷三)从修谱者李承箕、李承勋、李占颐、李玉大、李铭钟等人的表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嘉鱼李氏在族谱的编修方面,都是具有较强时间间隔的危机意识,担心间隔久远,家族历史的记忆会逐渐变得模糊,乃至消失,这一定程度上也促使李氏后辈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会主动编修族谱,使李氏家族史得以传承不衰。
三、嘉鱼湖西李氏修谱人员考察
国有国史,家有家谱。国史修撰者的水平高下决定了国史的价值,同样,族谱编纂者的水平、知识储备,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族谱的价值。根据嘉鱼李氏相关谱序及其他史料记载,嘉鱼李氏历次族谱编修者的情况清晰可见,如李占颐在谱序中言“定斋府君之始创,约庵府君暨崖、逊、惕斋诸府君之续修,景颖府君之衍派”[5](卷三),第九次修谱者李铭钟言“国朝贞子公续修,而后至乾隆丙子年间,虽又有偏瑞班公续修”[5](卷三)。按:定斋府君为李格,约庵府君为李田,大崖即李承箕(大崖先生),逊庵即李承勋,惕斋即李宝蒙之父李虔,景颖即李憭,贞子公即李占颐,瑞班公即李玉大。通过对每一位修谱人予以考察,可以窥见李氏族谱之编修质量及其价值。
嘉鱼湖西李氏第一次修谱者——李格,系湖西李氏第七世,号定斋,南宋嘉定庚午(1210)举人,其父李泳“绍兴间,初竭力辅赞父兄,创立家产,跣足荷笠,栉风沐雨,往来黄溪,然犹好学,常恨不得从费当时。日干事,夜读书,必五百遍而止。《尚书》《左传》可全篇背也。置文籍,常不吝买,衡鑑赋用钱三千,其后经史稍稍全备,悉亲手装楷”[10](卷一)。李格在父辈的影响下,“为人性质清高,词翰俱美,为世通儒,治《春秋》《周礼》,本州解魁,入太学”,因未能考中进士,回乡“主持义塾,编叙族谱”,撰有《定斋诗集》《春秋诗》行于世,被誉为“一族之白眉”[10](卷一)。
第二次修谱者——李田,系湖西李氏第十六世,字舜耕,号约庵,景泰庚午(1450)举人,甲戍(1454)进士,“仕至副都御使,茂著贤声”[4](卷二),“居官以勤慎著名,而尤称其有才干”[11](卷四)。李田荣登高第,在其教诲及影响下,李氏子弟人才辈出、接连登第,“家声由约庵府君而复振”[4](卷二)。
第三次修谱者——李承箕,系湖西李氏第十七世,字世卿,号大崖,成化丙午(1486)举人。曾从学于明代大儒陈献章,与学界、政界名流多有交际,以理学名世,参修《新会县志》《嘉鱼县志》。李承箕在江门游学时为不少岭南家族作过谱序,有《大厓李先生诗文集》二十卷传世。
第四次修谱者——李承勋,系湖西李氏第十七世,字立卿,号逊庵,谥号康惠,弘治癸丑(1493)进士,历任太湖知县、南昌府知府、浙江按察使、河南左布政使、都御史、吏部尚书、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对于家族事务颇为关注,撰有《世祀堂记》[4](卷二)、《嘉鱼李氏家范》等[4](卷二),许孚远称“康惠公《家范》载所报本之礼、睦族之道、赈济之方、赋役之制、居乡之宜、劝惩之法,亦既明且尽矣”[4](卷一)。
第五次修谱者——李宝蒙[10](卷一),系湖西李氏第十九世,字汝发,号出泉,嘉靖壬子(1552)举人,“淡于仕进,惟以读书明理为务。性方严,与人不妄交,日静坐一室,取古今上下载籍,手批心玩,日无废晷,奥辞疑字,人所未经见者,悉力综研”[12](卷二)。
第六次修谱者——李憭,系湖西李氏第二十世,字景颖,号幼泉,万历戊子(1588)举人,己丑(1589)进士,仕至光禄卿。李憭“幼即警敏不凡,卓有远志,从塾师,受博士家,言辄吐惊人语,塾师避席,诧曰:余不敢受子北面矣。突弁后,题读书之室,曰:求放心斋。取秦汉以上诸书,咿唔至丙夜不休。其为文也,期自具手眼,绝不寄人篱下。试于有司,鹤台褚公以郡节署县三试首选生,声噪江汉。”[11](卷四)
第七次修谱者——李占颐[5](卷三),系湖西李氏第二十二世,遗憾从嘉鱼李氏相关族谱及其他史料中未能找到李占颐的生平记载。
第八次修谱者——李玉大(1707-1759),系湖西李氏第二十四世,属于湖西李氏白杨分,字瑞班,号价轩,别号怀邨,“少时颖异,长而通经,年三十岁入庠。意欲立志高攀青云,迨年五十,数战棘闱,取贡不售,绝意仕进。公为人端方,族众举理户事,倡续宗谱,公领其责。艰辛三载告竣”[13](P45)。
第九次修谱者——李铭钟(1737-1834),系湖西李氏第二十六世,字芳久,号丰山,“邑庠生,学识渊博,诗赋名誉郡邑”[8](P3)。
第十次修谱者——李士型(1815-1879),系湖西李氏第二十八世,字文典,号席珍,亦号聘臣。李士型“读书勤奋,寒窗六载,博览经书”,道光丙午(1846)进士,未仕,以行医为己任,因博学被嘉鱼知县所看重,称其“有才干,议叙六品顶戴,授例为赐进士”。修族谱时,李士型任督修,历经四载,“一秉大义,督修告竣”[8](P18)。
依修谱者的谱系情况而言,主要源自湖西李氏教谕分一支(除第八次修谱者李玉大来自湖西李氏白杨分),且多为叔侄续修、兄弟连修、祖孙继修、父子续修等。以明代的五次修谱为例,李田是湖西李氏进入明代后第一位修谱者,李承箕系李田侄子,李承勋系李田之子,李宝蒙系李承箕之孙,李憭系李宝蒙之子,明代这五次修谱的主持者属于湖西李氏第十六世、十七世、十九世、二十世,修撰者均属于直系亲属,时间间隔比较短,且属于同一支——湖西李氏教谕分。另外,明清时期九次修谱,有八次的主持者属于湖西李氏教谕分,这有效保证了明清时期嘉鱼李氏修谱的连续性及真实性。湖西李氏教谕分,在湖西李氏南颖、教谕、白杨、东、西分中属于大宗,影响较大,故而修谱由大宗倡导,颇具号召力。诚如李占颐所言,“年方周甲,贫贱立身,曷敢举大动众?但缘祖签户管,裔列大宗,不採谫陋,敢剖愚衷,启族间父老而急商绩著,是非疑忌,在所不问”[5](卷三)。
从修谱者的身份构成来说,李格的父亲李泳善于置产,在当地颇有声誉。李格以乡试第一名的成绩考中举人,被誉为李氏之“白眉”,是族人引以为豪之人;李田系湖西李氏在明代考中的第一位进士,仕至都御史,是湖西李氏走上复兴之路的开创者;李承箕为举人出身,以理学著称,被视为家族典范;李承勋系进士出身,历任吏部、刑部、兵部尚书,以功勋名世,是李氏家族走向辉煌的代表性人物;李宝蒙为举人出身,以学问见长;李憭为进士出身,官至光禄卿;李玉大系庠生,且为湖西李氏户长,具有一定的号召力;李铭钟为庠生,以诗赋享誉州郡;李士型为进士,善于医术,乐于公益,为当时县令所看重。恰如李占颐所言,“时吾族谱牒,从前未有以白衣操觚染翰者,有之自复始”[5](卷三)。即湖西李氏历届修谱的主持者多为有功名之人,李占颐虽然没有功名,但其属于李承勋嫡传子孙,深受当时族人的拥戴。湖西李氏历届主持修谱者,都是家族中有地位或有声望之士,以自己的人格魅力能够在家族事务中主持公道,这样在修谱中自然会有很大的号召力,便于修谱相关事项的顺利展开,有力保证了修谱的进度。同时,也说明了在湖西李氏造族过程中,作为士大夫或地方乡绅的李氏子弟发挥了重要作用。恰如艾尔曼所言,“教育不只是社会身份的标志,在一个充斥着文盲或只会讲方言土语的社会中,那些掌握经典书面文字的人就拥有政治优势。家谱的编写、契约文书的制订,典当及其他经济契约的确定,都急需专业知识和社会关系,所有这一切,惟有家族内部的士绅精英才能提供”[14](P16)。
从修谱者的文化修养来看,湖西李氏修谱的主持者多为进士、举人、庠生等,博通经史,学识渊博。李格曾撰有《定斋诗集》、李承箕有《大厓李先生诗文集》、李宝蒙好读书、李憭善为文等。尤其是李承箕曾撰有《续李氏族谱序》《李氏世系记》,并为广东多家姓氏作过谱序,深谙为谱之道;李承勋撰有《续谱叙》《疑谱考》《荣四府君继嗣考》《省吾诗考》《李氏家范》;李占颐撰有《续谱序》《续谱引》等。主持修谱者的知识储备、文化素养及其阅历,对族谱的编纂有很大影响,湖西李氏的诸位修谱者多为文化名流,可以说是李氏家族中的精英人士,从而为族谱的质量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人才和智力保证。
四、嘉鱼湖西李氏族谱撰写特点分析
嘉鱼湖西李氏族谱虽历经十修,但从相关谱序及传承下来的咸丰八年所修《嘉鱼李氏族谱》来看,嘉鱼湖西李氏族谱在编纂方面颇有特点。诸如修谱者的编撰态度、族谱的编写体例及族谱的载记内容等方面有其独到之处。
其一,彰善求是的编撰态度
一般撰写族谱时,为提高家族的声誉或表明家族历史的悠久,虚构家族历史或援引名人为祖的现象较多。还有,一个家族绵延数百年,族谱中谱系难免出现记载淆乱的情况。但嘉鱼李氏历代修谱者在这方面做得比较详慎,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编纂族谱,力求存留一部真实的家族史。
李承箕在修谱时指出,可考者写之,不可考者则略之。“璠而上十四世传至郁林,始无可考也。今吾惟以璠为第一世者,有可考也,至箕十七世矣。”[5](卷三)“尝见庐陵欧阳氏谱、眉山苏氏谱,其先皆出于三代之圣君贤相焉。是以有如永叔、明允父子者,后之箕何敢窃迹其迹,而妄祖其祖耶。乃记其世系之所自,而并著其疑者于右,以俟同宗者览焉”[5](卷三)。
李承勋在李承箕的基础上续谱,利用在南昌任知府的机会,为考察源自湖西李氏发源地江西武宁的李氏宗谱记载是否真实,通览樱川、磨刀、滁平一带的李氏族谱,得出湖西李氏的确是源自唐代李世民第三子李恪。同时,李承勋对三谱所载宋代以前的世次持怀疑态度,“其世次之详则诚有不敢尽信者矣”,并悉数其不妥处,“或以一人名字为二人,合二父所生为一父”,还有宋代谱序中有附会失实的现象。面对樱川、磨刀、滁平三处李氏族谱与嘉鱼族谱所载出现差异时,李承勋没有固守己见,而是据理推断,采取众家认可及文献足徵的观点,即“从众与足徵”,最终的取舍是“谨考正其可据者,而阙其不可知者,以示后之人”[5](卷三)。
康熙年间,李占峥指出湖西李氏族谱编纂时,所采取的原则是“夫定其所知,不妄援于已远;详其所至,不轻遗于已疏”“吾家谱系其本,固其源,远其流,愈长其末益疏,不妄援、不轻遗前人之记载,不既严且慎乎?则今日任纂承之责者,亦惟不诬而有序焉?”[5](卷三)李占颐亦言,“毋僭毋滥,秉南史之笔,以彰信后世,使我子孙目击而道存,秩然有度,聿念尔祖中兴焕发,则是举也,不亦救时良剂矣哉”[5](卷三)。
李承箕、李承勋、李占峥、李占颐在编纂族谱时,均以求是为原则来记载彰显李氏之家族史。尤其是李承勋曾专门到江西考察相关李氏族谱,撰有《疑谱考》《荣四府君继嗣考》《省吾诗考》等文章,借以考证、补录族谱中相关史实。
其二,书写规范的编纂体例
湖西李氏在族谱编纂体例方面,应该对欧阳修、苏洵的修谱之法有所参照。李承箕曾言“尝见庐陵欧阳氏谱、眉山苏氏谱,其先皆出于三代之圣君贤相焉”[5](卷三);李占峥亦言“昔人云:为谱系于家者,惟眉山苏氏书法最具其详略、远近、亲疏之殊,可引而观也。”[5](卷三)
湖西李氏修谱在体例上对欧阳氏、苏氏修谱之法有所参照,但有自己的编写体系。李承勋主持第四次续修时,言“谱何所续,续大崖之笔也。续何所书,书后之世次、言行与谱法,得收者收之,旧谱创于先伯祖定斋府君,定于先考中丞府君,续于伯氏大崖先生”[5](卷三)。对于族谱如何修撰,李承勋在体例方面予以统筹,整个族谱分为上中下卷及附录,上卷收录诰敕御笔及义学,中卷收录谱序、疑谱考、世系图及墓图志,下卷备录世行(六世以前按李格的笔法善恶无隐,十七世以前遵循李田的标准书善隐恶),附录收录湖西李氏相关诗文。总其名曰《嘉鱼湖西李氏族谱》。[4](卷一)应该说李承勋所定下的修谱体例,对李氏后世修谱有很大影响。李占颐称编修族谱“一遵祖制,凡世系必详,世行必录”[5](卷三)。嘉庆间,李铭钟修谱时,指出“惟圣恩、世泽、叙考、徵献、遗文,与自一世至二十世世系、世行,固分之而无可分者,于是每分各出微资,公同补修。”[5](卷三)咸丰八年所修谱亦是按照李承勋所拟定的体例进行修撰。
其三,系统翔实的载记内容
湖西李氏族谱的编纂从明代李田第二次修谱开始,修谱的间隔时间不超过三代,甚至是隔代修及同代修,这种修谱模式具有连续性、承接性,历届所修谱保持着内在的有机联系,保证了族谱所载内容的翔实性。诚如第八次修谱者李玉大所言,“派衍郁林世泽长,支分南楚遍潇湘。搜寻旧牒漏遗远,续补新编收录详。征信前贤无谬笔,联合宗族有成章。从来继述窥先志,岂漫增修不自量”[15](卷五)。
康熙间,李占颐修谱时,采取的方法是先把旧谱整理好,然后再拿着旧谱逐家逐户核对信息。李占颐将修谱事宜,先“与诸季父昆弟子姓讨论商兑”[5](卷三),接着,“于三十一年三月三日特牲告祖,集户众,鸠梓人,聘书写,陡胆搜囊开局于家,将旧卷发梓,日夕董理,于三十二年三月而旧谱告成矣”,然后,“携仆担嚢,无问远近,不辞劳苦,挨庄别户,详前此阙略之系行,询后起未登之字派,以及生卒葬向,误者改之,弃者补之。非其种也,锄而去之。散轶四方者,收而梓之。上自白叟,下及黄童,一一注集,只无遗漏”[5](卷三)。嘉庆间,李铭钟主持修谱时,指出“虽然家之有乘犹国之有史,传信也,而非以传疑,其可不严,其可不慎乎!则亦惟据老谱与所存板互相参考,于其有缺者补之,可信者收之,无稽者阙之而已”[5](卷三)。
正是凭借这种持续的修谱方式,规范的修谱程序,认真的修谱态度,严谨的修谱理念,一定程度上使族谱载记内容更加真实。诸如历代朝廷的诏、敕、谕,历次修谱的序、考、世系图、相关墓志图、契约,历代人物传记、墓志铭、诗文等,都比较完整地保留下来,使湖西李氏家族史的生命得以延续。
五、结语
嘉鱼湖西李氏家族从南宋到晚清,历经数十代,间隔数百年,但谱系清晰,家族史保存完整,正是囿于嘉鱼李氏众多修谱者始终持有“国有史,家亦有乘”[5](卷三)“夫家乘之修,史义与焉。先世之事固当处事直书,然于义有未安,亦不得而不正之也”的理念[5](卷三)。而嘉鱼李氏历代修谱者的名望地位、文化素养,不仅有利于修谱工作的顺利进行,也为族谱的修撰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嘉鱼李氏族谱合理的编纂体例,是李氏家族史得以有序、翔实保存的有效保障。同时,嘉鱼李氏历经数百载,族谱持续的续修,为维系家族凝聚力提供了精神依靠。像明代中叶,嘉鱼李氏十六、十七世是李氏家族由发展到鼎盛时期的代表,两代人共修了三次谱,说明此时李氏家族具有很强的向心力及家族实力,希望通过修谱增强族人之间的联系,借以扩大家族的影响力,毕竟族谱是一个家族是否为世家大族的标准之一。同时,有序的家谱修撰,很好地增强家族成员对家族的认同感。并且“以纂修和管理谱牒为中心,将儒家伦理道德中的个人、家庭、宗族与国家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形成了宗族与国家相呼应的良性互动局面。”[16]
族谱不仅承担着家族史的记忆功能,同时是研究传统社会的宗法关系、社会管理、文化教育、人口变迁等方面不可或缺的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诸如咸丰八年所修湖西李氏族谱中完整保留了宋代、明代及清代所修的李氏家范,是研究不同时代家族管理的珍贵史料。还有大量朝廷下发的诰、敕、谕,李氏家族历代修谱的谱序,李氏家族相关成员的传记[17](卷三百三十七)、墓志铭、诗文,以及李氏家族有关族产、坟地等所签订的契约,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史料参考。诚如乾隆年间修谱者李玉大所言,“达而上者,丰功伟烈之昭垂;穷而下者,嘉言懿行之灿著家乘也,可备国史采摭矣”[5](卷三)。
但是,正如史书的书写者具有一定的价值倾向一样,族谱的修撰者亦是具有一定的价值取向,这势必会影响到族谱修撰过程中的思想导向。以明代的五次修谱为例,这五次修谱者均是源自湖西李氏教谕分,这与教谕分在五个分支中发展势头最好是有密切关系。不管是由谁执笔,通过修谱追求家族认同的目标肯定是一致的,而由谁执笔自然避免不了出现“淡妆”与“浓抹”的差异,这也是我们在研究家族史时应该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