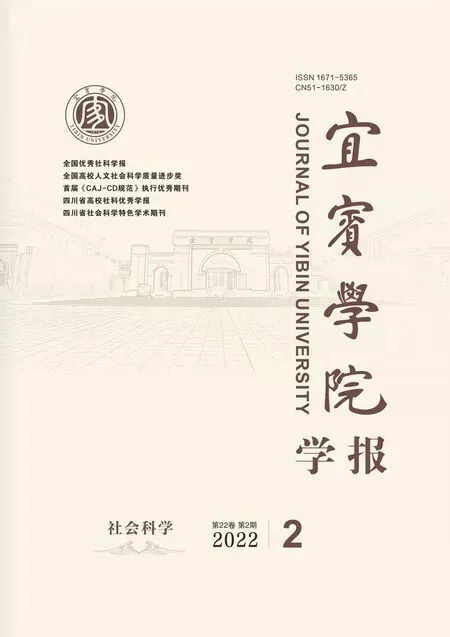论德勒兹对尼采永恒回归的继承与发展
李方明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尼采是理解法国后结构主义的重要切入点,而德勒兹的早期作品《尼采与哲学》则是这个切入点中注定无法绕过的部分。《尼采与哲学》被认为是法国哲学界对尼采接受的转折点,法国“新尼采主义”开启的重要标志。目前,国内针对德勒兹尼采诠释的研究多以整体论述为主,如马成昌从欲望、差异、生成三个维度切入德勒兹的前后期文本[1],姜宇辉基于“时间性”视角阐释了德勒兹对永恒回归的后续发展[2],邰蓓从“生成”概念入手探讨了尼采哲学与德勒兹思想的亲合性[3],陈炳辉、王东明浅析了尼采对德勒兹整体思想的影响[4],李科林基于《尼采与哲学》比较了海德格尔与德勒兹对尼采的不同解读[5]……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虽然对我们理解德勒兹整体思想具有重要意义,但也无意间忽视了德勒兹对于尼采具体概念的继承与发展。因此,本文选择从尼采永恒回归的问题场域出发,在尊重尼采原意的基础上探究德勒兹对这一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这对我们更好地理解德勒兹的先验感性论,乃至于整个法国后结构主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如何使生存成为无辜:尼采永恒回归思想的问题场域
尼采“永恒回归”思想从雏形到成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快乐的科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永恒回归的雏形首先出现在《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中,呈现为赫拉克利特与阿那克西曼德二人关于“生成”的不同态度;随后,《快乐的科学》第341段格言以寓言的形式正式提出了这一思想;永恒回归学说的最终完成体现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具体表现为侏儒与查拉图斯特拉之间的交锋。倘若读者足够细心,就能发现一条串联起永恒回归三个阶段的暗线:对生存有罪论的绝弃以及对生存之无辜的肯定。换言之,无论是阿那克西曼德与赫拉克利特,魔鬼与人类,还是侏儒与查拉图斯特拉……这些“概念性人物”都是生存有罪与生存无辜的转喻和暗喻。因而,理解尼采永恒回归思想的问题场域,就意味要把肯定生命及生活世界、反对本质及超验世界作为理解其学说的出发点。所以,永恒回归涉及的问题只有一个:如何肯定生命,如何使生存与生成成为无辜。
在《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中我们不难发现,尼采对前苏格拉底哲学的理解是基于自己生命哲学之视角的。例如,阿那克西曼德认为拥有属性就意味事物的产生和毁灭都是注定的,为了使存在者保持永恒和不朽,他选择将“无定形”理解为“本源性存在”(Urwesen)。这种做法使得现象世界与本源存在产生了分离,从无定形到现象,就是从本源跌落至现象。也就是说,分离过程产生出了原始的罪。因而,阿那克西曼德将“多”之存在视为赎罪,即将事物从生长到衰亡的过程视为赎罪的具体方式。为了驳斥阿那克西曼德的观点,尼采引入了赫拉克利特的观点。尼采认为,赫拉克利特从根本上拒绝为现象世界寻找一个超验本体。“除了生成之外,我什么也没看见”[6]29。在赫拉克利特那里,生成是永恒且唯一的,现实性的全部本质是生成,而对立面的斗争又是一切生成的发源地。赫拉克利特坚信的周期性世界大火被尼采理解为生成与艺术,新的世界产生于孩童和艺术家觉醒时的游戏冲动,多样性的斗争通过艺术塑造出关于自身的规律和法则。因此,世界所需要的绝非负罪与救赎,而是生成与艺术。肯定生成是为了肯定多样性,但尼采为什么要肯定艺术?这一点要追溯到尼采的早期作品《悲剧的诞生》,书中他认为悲剧艺术为希腊人提供了一种形而上学的慰藉,正是凭着这一慰藉希腊人才承受住了悲苦的人生。沉醉于悲剧的希腊人并没有放弃他的生命意志,而是通过艺术直面了人生之痛苦与不定,成为一位具有悲剧性的艺术家。后来,可能是因为“瓦格纳事件”的缘故,中期尼采对艺术的地位和作用产生了一些怀疑。所以,他逐渐从鼓吹悲剧文化转向采取格言(Aphorismus)体写作,从颇具浪漫色彩的艺术形而上学转向具有实证主义倾向的科学思想。
《快乐的科学》在尼采的全部著作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它回应了《人性,太人性的》中科学与艺术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它引出了后期尼采的核心思想——永恒回归。尼采在《瞧,这个人》中亦坦言,《快乐的科学》中的第341段格言首次阐释了查拉图斯特拉的基本观念——永恒回归。所以,第341段格言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存在对偶性,该格言开头“最重的分量”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部分“重压之魔”遥相呼应。随后的第342段格言亦证明了这个看法,第342段格言的内容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开头部分几乎一致,即查拉图斯特拉将要“下行”,到人群中去传授“超人”。《快乐的科学》中的这两段格言给读者留下至少三个疑难:魔鬼(德语:Dämon)的形象代表着什么,怎样理解“最重的分量”,永恒回归如何与查拉图斯特拉建立起关联。这些问题在《快乐的科学》中没有答案,读者必须要继续前行,到尼采的下一部著作中寻找启迪。
Monika Langer曾指出,尼采之所以采用寓言来描述永恒回归,是因为他不愿意将永恒回归总结为一个概念或命题[7]209。倘若读者将永恒回归理解为一个哲学概念或神学命题,那么这一思想所激起的就是读者的智慧或好奇,而非有关生命的想象与情感。毫无疑问,第341段格言所描绘的Dämon就是一个寓言。尼采故意以寓言的形式向我们刻画了一个超自然的Dämon,作为Dämon的永恒回归将激发我们对寓言本身投入想象和情感。Dämon的形象从根本上说就是生命的敌人,这一点详细地体现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部分“重压之魔”一节,即尼采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将“重压之魔”视为宿敌。“重压之魔”代表着他律的道德法则,这种法则妨碍了生命意志的张扬,限制了生命的自由活动。“它像骆驼一样跪下来、让人给它装上很多的重负”[8]225。“重压之魔”重拾了生存的“有罪论”,对生命冠以善与恶的限制,一如阿那克西曼德那样将负罪与救赎引入人世。至此,我们解决了《快乐的科学》中的第一个疑难,魔鬼的形象代表着查拉图斯特拉的敌人,生命与永恒回归的敌人。
接着,我们来到了第二个疑难面前,如何理解第341段格言的开头“最重的分量”?结合文本,我们不难得出“重负”与魔鬼的恶言存在巨大的关联。尼采借恶魔之口向我们发出质询:假如生活周而复始,你是否还愿意肯定它?“你是否还要这样回答,并且,一直这样回答呢?”[9]将重负与人生相关联,这一重负与《悲剧的诞生》中“人何以承受悲苦人生”的命题是相通的。很显然,叔本华关于生命意志的论述曾深刻地影响过尼采,《悲剧的诞生》的核心思想就是由叔本华意志形而上学支撑的。不过,虽然尼采完全认同生命意志的基本预设,即人生是悲苦的,但是他坚决反对将悲剧之意义视为认识到生存之原罪,坚决反对叔本华将人生之悲苦归因于生命意志的悲观主义论断。“叔本华对意志的基本误解是典型的:把意志贬值到萎缩地步”[10]498。所以,理解“最重的分量”就等于理解尼采所区分的两种面对人生的方式:消极的与积极的。消极的做法就是否定意志和欲望,像叔本华一样悲观地认定人类绝无逃出意志支配之可能;而积极的做法则是对永恒回归的肯定,愿意回答并且一直回答,生命通过回答实现了自由和张扬。
《快乐的科学》第341段格言首次提出了永恒回归,第342段格言则第一次公开启用了查拉图斯特拉的形象。孙周兴曾考据过二者的关联,并认为尼采创造查拉图斯特拉之目的就是为了宣告永恒回归思想[11]。换言之,永恒回归就是“超人”学说的核心内容,而查拉图斯特拉作为“超人”的教师则担任了永恒回归的代言人。永恒回归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是通过查氏与侏儒之间的交锋呈现的,侏儒像寓言中的魔鬼那样,向查氏抛去了最严厉的质问:你所高举的思想会像石头一样落在你身上,你迈出的每一步都要受尽内心折磨,“重压之魔”会使一切努力落空。沉默了许久之后,查拉图斯特拉悟出了永恒回归思想。人类靠勇气征服了一切的动物,靠军乐克服了一切的痛苦……但这些都没有改变深渊本来的面目,人类的痛苦仍然最沉重的痛苦。不过,勇气克服了人们直面深渊时产生的绝望。这使得人生虽然是痛苦的,但是人们依靠勇气毅然作出了继续生存的决定。由此,拥有了永恒回归的查氏不再为侏儒的存在而感到困惑。“这就是以前的生存吗?好罢!再来一次[3]178!侏儒在跳下查氏的肩头后并未善罢甘休,他又将两条通往永恒却又背道而驰的路径(身后的路是过去,向前的路则是未来)指给查氏看。然后,继续发言:“一切真理都是曲线的,时间本身就是个圆周”[3]179。听完侏儒的话,查拉图斯特拉勃然大怒,因为侏儒并没有理解永恒回归,他依旧秉持着生存有罪的看法。换言之,侏儒口中过去决定未来、二者形成一个圆环的看法与永恒回归之间只存在外表上相似,其本质始终是不同的。侏儒缺乏勇气和肯定生命的态度,所以查氏为他过于轻率的说辞感到愤怒。像查拉图斯特拉这样的人是下定决心求生的,因而他必须用自己的力量克服掉任何虚无、悲观、否定生命的思想。这也是“幻影之谜”和永恒回归的真正答案——任何热爱生命之人都必须克服掉虚无主义,避免将生存和生成视为原罪,唯有这样才能保证生存之无辜,从而保证生命之价值得到应有的张扬。
二、作为差异者的永恒回归:德勒兹对永恒回归的继承
在《尼采与哲学》出版前近十年,德勒兹一直在钻研尼采的文本。1958年索邦大学的秋季学期,他就曾在课堂上教授过关于尼采《道德的谱系》的课程。这也是为什么在《尼采与哲学》中,德勒兹会选择从“谱系学”(Genealogy)角度出发切入尼采哲学的根本原因。换言之,在德勒兹看来,正是谱系学的存在催生了尼采对世界和生存的悲剧性理解,即将世界和生存视为多样性和差异性的,这一点亦是尼采与基督教、辩证法存在的最大不同。
不过,针对尼采哲学究竟有无内部统一性的问题,西方学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12]。前者以海德格尔、施特劳斯学派为代表,他们都认为尼采哲学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而后者则以德勒兹、福柯等法国后结构主义者为代表,他们特别关注尼采哲学的开放性和多元性。具体到对永恒回归的理解上,海德格尔和德勒兹各自代表了一个流派,前者将“相同者的永恒回归”理解为存在者整体之具体存在方式,而后者则在不同、不似的基础上对尼采“相同者的永恒回归”进行了创造性解读。需要注意的是,海德格尔对尼采的解读是基于“存在之存在”的。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形而上学思考的都是存在者之存在,而忽视了真正的存在问题。尼采固然颠倒了柏拉图主义,但这种做法仅仅只是将超验世界的全部意义搬运至生活世界当中,永恒回归所思考的依旧是存在者之存在(他将永恒回归视为存在者整体之实存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将尼采认定为“形而上学终结者”的同时又是“最后的形而上学家”。很显然,德勒兹并没有像海德格尔那样将永恒回归判定为构成形而上学的铁证,而是通过将永恒回归视为差异和多样性走到了形而上学的对立面。永恒回归就是生成和多样性的规律,是排除了所有否定因素、只在生成之中被肯定的存在。
在《尼采与哲学》中,德勒兹通过“掷骰子”意象对永恒回归进行具体的解释。尼采本人曾读过马拉美的《骰子一掷,永远无法取消偶然》一诗,并亲自将“掷骰子”这一意象纳入永恒回归思想。不过,尼采与马拉美对于“掷骰子”意象的理解却是截然不同的。马拉美认为必然是对偶然的取消,只有取消偶然,游戏才能成功,掷骰子的第二个时刻必须否定第一个时刻,而第一个时刻也只能抑制第二个时刻;尼采所理解的“掷骰子”却是对差异的肯定,一切都是偶然的,一切都完成于瞬间,它是肯定偶然和多样性的唯一方式。随后,德勒兹还将帕斯卡的“赌博”与尼采的“掷骰子”进行比较,帕斯卡的“赌博”没有肯定作为整体的偶然,而是将偶然转化为输赢的概率,将自己的选择权交给禁欲主义;尼采却明智地将“掷骰子”和帕斯卡的“赌博”进行区分:“掷骰子”是悲剧性的,它使混沌成为值得被肯定的对象,而非相信上帝存在与否的生存方式。很显然,对于马拉美和帕斯卡而言,偶然是必须被否定的,因为必然才是绝对理念或永恒本质的固有特征。因而,德勒兹断定马拉美“掷骰子”和帕斯卡“赌博”的真实目的在于使生命在一个超验世界中获得救赎。真正的掷骰子游戏应该发生在大地和天空两个场所,“大地是骰子的掷出之地,而天空是骰子落回之地”[8]38。因为该游戏最后显示的组合数目是有限的,而这有限的组合数目又必然会导致掷骰子结果的重复。所以,掷出行为是对偶然性的肯定,而它最终显示的结果则是对必然性的肯定。在这个意义上,尼采将偶然理解为对差异的肯定,并且这里的偶然直接等同于多样性。尼采以偶然/必然、偶然/命运的对应关系取代了原因/结果、可能性/结果的对应关系,在掷骰子游戏里,不是投掷次数决定骰子回落显示的结果,而是“注定的数的性质决定投掷的重复”[8]42。所谓永恒轮回就是骰子显示结果的时刻,它既是投掷的重复,又是对偶然性的再生与肯定。
由此德勒兹断定,马拉美和帕斯卡彻底败坏了“掷骰子”意象,他们宣扬二元对立(现象/本质)的做法与尼采所痛斥的否定生命、排斥偶然和差异的“虚无主义”如出一辙。尼采语境中的虚无主义表现为怨恨、内疚以及禁欲主义,永恒回归的任务就是要认清并摆脱虚无主义,打破原有定见之主观预设,提供出一种基于差异的思维方式。所以,永恒回归是一种动态的差异运动,它是对纯粹的偶然和多样性的绝对肯定。“肯定是悲剧性的,因为它肯定偶然以及偶然的必然性,肯定多样性以及多样性的统一”[8]55。并且,悲剧并不存在怨恨、内疚和虚无主义,生存在悲剧中不受谴责,生命意志亦不再为自身之存在感到内疚,而是成为孩童的游戏、绝对的无辜。
另外,德勒兹还从查拉图斯特拉与狄奥尼索斯这两个“概念性人物”出发,探究权力意志与永恒回归的关系。他认为,每个哲学体系都想要揭示被前人视为理所当然的“假设”,因而每位哲学家都必然要创造属于自己体系且用具有识别度的“概念性人物”来界定概念之性质。在德勒兹眼中,权力意志和永恒轮回之间的差异,就是查拉图斯特拉同狄奥尼索斯之间的差异。查拉图斯特拉是狄奥尼索斯的前提条件,没有查拉图斯特拉,狄奥尼索斯就无法存在。“权力意志把偶然置于它的中心,只有权力意志才能肯定一切偶然”[13]78。所以,为了确保永恒回归所描述的是差异与不同之物的回归,我们必须将永恒回归理解为权力意志的表述。尼采的全部教诲就放置在永恒回归中:所有意愿者都是命定的,而命运就是我所意愿的。查拉图斯特拉能够把世界理解为命定的,也能够意愿这个世界,却无法同时思考二者,于是只能以中介的方式运思;而狄奥尼索斯却能够通过直观运思,它是一种斯宾诺莎式的递归性。在这种递归性中,“他并不是从外部意愿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同时也命定了他”[14]。查拉图斯特拉是第一个肯定,而狄奥尼索斯则是第二个肯定,第一个肯定总是伴随着第二个肯定。第一个肯定有且只有在它作为第二个肯定的对象时,它才是存在。换句话说,查拉图斯特拉是‘变形’的先知或原则,是他首次把否定转化为肯定,把意义的失败或最高价值之缺席转化为一种新形式的意义与价值。也就是说,从查拉图斯特拉上升到狄奥尼索斯的时刻,旧的价值在此时毁灭、新的价值在此时创立,一个新的谱系学诞生,并实现从骆驼、狮子再到孩子的“精神三变”。因此,尼采最大的贡献就是将价值和意义引入哲学,永恒回归的目标就是建立一种无超验性的总体性,进而使一切事物及起源返回到价值,再让这些价值返回到那些成其所是的事物里。后来,德勒兹并没有满足于书写像《尼采与哲学》这样的哲学史评述。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他必须创造出属于自己哲学体系的概念。于是乎,他通过对尼采永恒回归思想的重构,创造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哲学概念——拟像(simulacra)。
三、作为先验感性论的拟像:德勒兹对永恒回归的重构
众所周知,尼采通过对生活世界、超验世界的倒转,彻底废除了超验世界,进而揭示了西方形而上学之本质是一种虚无主义——由于形而上学将超验世界视为一切意义的聚集之地,这直接导致了现实世界处于无意义状态。所以,尼采终生反对以超验世界为终极的形而上学和基督教。很显然,德勒兹创造性地继承了尼采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只不过,德勒兹将柏拉图主义转化为“表象”(Representation)思维,又将永恒回归纳入“拟像”的范围。至此,他所探讨之重心不再是尼采与黑格尔、生命与辩证法之间的对立,而是以同一性为代表的表象思维与以永恒回归为代表的拟像领域之间的交锋。
德勒兹之所以要批判“表象”是因为其存在意味着哲学内部存在一些前哲学的“主观预设”,而这些预设则制造出种能够作用于思想层面的先验结构,这意味着终极存在并没有被视为一种哲学概念对待。在他看来,形而上学思维试图以表象为中介,进而将差异抛入“再现”模式,以普遍的概念来将“差异”同一化。表象式哲学最根本的特征就是超越性,即通过理念、抽象概念来将“绵延”运动切断,从生命中截取出的抽象概念进而构成表象之基础。正如美国学者詹姆斯·威廉姆斯(James Williams)认为的那样,柏拉图主义的基础是一种神话,这种神话预设了读者从好与坏、真或假之间作出选择[15]。因此,柏拉图主义就是一种超越性哲学,而德勒兹则希望通过对永恒回归的吸收试图建立起一种真正“内在性”的哲学。所谓“内在性”哲学就是说,它并不预设某种绝对的、超越的哲学开端,而是克服了柏拉图主义将事物本身与拟像划清界限的做法,意味着以一种非表象、非中介的方式去思考差异。换言之,“倒转柏拉图主义(to reserve platonism)就意味着要否认原本高于摹本,意味着要拒斥原型高于影像,意味着要赞美拟像和映像之主宰”[16]66。
从《尼采与哲学》再到《差异与重复》,德勒兹对于永恒回归的理解和把握始终建立在差异的基础之上。需要注意的是,差异并不存在于事物与拟像之间,也不存在于某种源始与派生之间。恰恰相反,“事物就是拟像本身,拟像是事物的高级形式”[11]67。德勒兹认为,《智者篇》的结尾恰好证明了柏拉图辩证法的失败,即将拟像与事物本身相区分开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事物存在的使命就是去成为自己的拟像,去达到一种符合永恒回归之一致性的符号状态。换言之,拟像就意味着永恒回归与一个诸差异独立存在的世界联系在一起、与一个去同一性的“混沌”(chaos)领域关联在一起。而永恒回归则意味着一种遴选:在回归之前消除否定地重复、同一地重复,消除作为表象之前提的相似与相同、类比与否定。否定与同一不会回归,相同与相似、类比与对立也不会回归;只有肯定会回归,只有不同与不似才会回归。永恒回归不是同一给一个变为相似的世界造成的结果,不是被一个强加在世界之混沌上的外在秩序,“而是世界与混沌的内部同一性——混沌宇宙(Chaosmos)”。永恒回归是至高的思想,它通过“自我解体”排除了思维主体的同一性,并排除了作为笛卡尔式“我思”之保障的上帝的一致性。“永恒回归使存在直接向差异敞开,且全然无视概念的一切终结和一切和解”[11]58。所以,德勒兹认为尼采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将永恒回归中的重复同时奠基在上帝之死和自我之解体的基础上,因为这种做法完全消除了表象的前提——相似与相同、类比与否定。“永恒轮回中的重复是相同,但前提条件是它只诉说差异和不同者”[11]300-301。
在德勒兹看来,差异不能等同于康德意义上的“杂多”。因为杂多是经验原理之所予,而差异则是先验原理,即使所予得以被给予的关键。差异就其本质而言是肯定的对象,肯定对象就是肯定自身,而肯定自身就是肯定差异,它作为自在之差异而存在着。差异站在所有事物的背后,但它背后却没有任何东西,这一观点在后来被德勒兹总结为“先验感性论”。“先验感性论”之所以被提出,是因为德勒兹希望以一种不涉及经验的方式来描述先验的真实结构。在柏拉图那里,迫使我们进行思考的始终是给予感官以相反刺激的事物,即识别对象身上的那些具有对立的性质(轻与重、大与小)。换言之,柏拉图希望从经验层面追问先验原理,这种做法直接导致先验的真实结构,即我们所遭遇(rencontre)的对象被贬斥为经验之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勒兹判定柏拉图混淆了纯粹质量性的存在与感性本身,误解了真正遭遇的对象——强度差异(difference of intensity)。所以,“倒转柏拉图主义”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倒置本质与现象之间的次序,而是借助拟像之强力以消解柏拉图的主观预设,以此来确保我们所遭遇的对象没有被误读。
由此可见,德勒兹对尼采永恒回归的继承与发展,实际上是以哲学史评述的方式来构建“内在性”。所谓哲学史评述就是哲学自身的再创造,它包含复身的所有变化之最大可能性,而且要“把历史性的评注整合到我们的文本自身之中”。对德勒兹而言,任何哲学都试图思考先验者背后的“内在性”,然后再将这个“内在性”变为另一个先验者,这种继承和创造使“内在性”源源不断地呈现在哲学史上。在这个意义上,拟像理论就是对以往形而上学的反拨,它揭示出那些在形而上学中被视为理所应当的主观性预设,然后从“内在性平面”内选取新的组件、形成新的概念,创造出独特的体系以重新追问哲学之起源。究其根本,德勒兹首先通过将经验视为一个多元性的存在(拟像)来破除形而上学给予“我”的规定性,借助尼采的“永恒回归”建立起一个无超验性的总体性,进而使多摆脱对一的再现、使经验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体,从而让经验在自我中生成出了超验的维度。
结语
尼采的永恒回归之所以将生存视为绝对的无辜,是因为他继承了德国古典人文主义关于“人本位”的思想。在德国古典人文主义那里,人性是最为关键的存在,神性不过是人性之补充力量。任何先验结构都不过是神学之变种,只要承认有比人更强大的力量存在,思者就已经进入一种神学的思考,而以永恒回归为代表的真正的思是不产生负罪且取消神学的。换言之,永恒回归的维度是悲剧性而非负罪的,人类之最高维度就是与命运斗争中激起的崇高感。在尼采看来,世界上“没有真理,只有解释”,神和逻辑不过是人类为实现自我保存而创造出的观念。世界之存在绝无客观上的目的,而只有主体自我预设之价值。因此,他将先验结构还原为权力意志/永恒回归的谱系学问题,以此来保证对生命与多元的本质直观。德勒兹对尼采永恒回归的继承与发展正是建立在谱系学基础之上的,权力意志的本体论被他改造为绝对差异的本体论。如果说尼采设想的世界秩序是权力意志在力的竞赛中的力量序列,那么德勒兹的世界秩序就是一个由拟像与其他拟像共同构成的混沌宇宙。德勒兹认为,“倒转柏拉图主义”意味着世界并非理念之集合而是拟像之集合,没有什么绝对的、超越的哲学开端,现代世界是一个拟像的世界。上帝死后,人类从蒙昧的经院神学走出,却又走进了看似黎明的虚无。为了不堕入虚无主义深渊,我们必须以一种从拟像到拟像的方法来看待世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摆脱辩证法和神学,才能基于真实的经验,从自我中生成出一个超越性的维度。这种思路与尼采是一致的,早在《荷马的竞赛》里尼采就曾表露出类似的看法:前荷马时代世界是一片深渊,荷马通过竞赛区分优秀与平庸,进而将人类导向对整个群体有建设意义的轨道。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柏拉图和基督教会成为德勒兹和尼采批判的对象。在深渊面前,柏拉图用理念贬斥生活世界,而基督教则将负罪感内在于人的存在中,他们都处于生命的对立面。而尼采和德勒兹则以肯定生命和差异的姿态来面对深渊,犹如转向悲剧和竞赛的希腊人一样,肯定差异并将面临深渊之恐惧转化为一种能够激发人类创造性的积极力量。以肯定之姿态面对虚无、以竞赛之精神拒绝负罪,就是永恒回归的真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