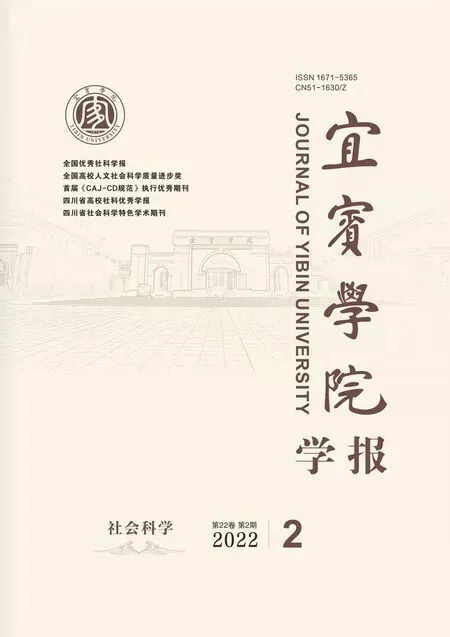论“清朗”行动中社交网络账户的双务合同性质
阳庚德,张俊韬,李敏
(1.华南师范大学 法学院,广东 广州 510063;2.湘潭大学 法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社交网络账户是由社交网络服务运营商提供给用户,使其得以通过互联网使用即时通信、信息展示等功能的交互通路。自2021年5月初,中央网信办开展“清朗”系列专项行动①以来,多家网络平台顺应政策法规开展网络专项整治工作,禁言、封禁了一系列扰乱网络秩序的违法违规账号。诸如“郑爽”“张哲瀚”“赵丽颖工作室”等“微博大V”的社交网络账户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治。社交网络账户作为网络虚拟财产的一种,其上附有用户协议所享有的由社交网络服务运营商提供的社交网络平台服务,以及创设、使用、转让社交网络账户等方面的权利。但“清朗”行动的开展限制了这些账户上的用户权利,由此引发了社会对社交网络账户法律属性的疑惑。
一方面,我们应旗帜鲜明地支持国家对互联网环境的依法整治;另一方面,我们也有必要借此机会梳理清楚社交网络账户中的法律关系。尽管我国《民法典》第127条对网络虚拟财产作出了原则性规定,明确了社交网络账户的财产属性,但就社交网络账户究竟是一项什么财产,在转让、继承、救济等具体问题上应适用何种规则,目前立法并未给出明确的解答。此外,学界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关注游戏账户或抽象探讨网络虚拟财产整体的法律属性,较少有专门涉及社交网络账户的研究。因此,现以霍菲尔德权利分析理论为基础分析社交网络账户的法律关系,以明确其法律属性,进而明确其在转让、继承、救济等主要方面所应适用的法律规则。
一、社交网络账户的法律基础关系解构
欲探究社交网络账户的财产属性,首先需要明确用户与运营商各自对社交网络账户享有何种权利,明晰围绕社交网络账户所产生的法律关系。在分析法学家眼中,权利意味着一段法律关系,权利的本质内涵并不重要,权利概念在法学话语中所起的作用才更值得注意。如凯尔森就认为,权利是一项法律技术,其作用在于权利人得以通过权利的行使启动法律的强制[1]91-93。因此,当我们在论证一项法律权利时,实际上是在论证法律对处于某种关系中的特定行为的效力。
结合霍菲尔德权利分析理论与霍兰德和萨尔蒙德的权利结构原理,可以得出法律关系主要包含三项基本要素——法律关系的主体、法律关系的形式和法律关系所指向的行为。每一个法律关系有且只有一个行为、一个形式、两个主体,无论两个法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复杂,最终均可以分解为若干单一的法律关系[2]123-126。据此,围绕社交网络账户的法律关系可以提取出主体、形式和行为三种要素。
首先,法律主体作为法律关系中的一方,是权利、义务的承受者。在社交网络账户法律关系中,主体无疑是提供社交网络服务的运营商和享受社交网络服务的用户。在特定情况下,还可能会涉及运营商和用户之外的第三人。因此,围绕社交网络账户,一般存在运营商与用户、用户与第三人以及运营商与第三人这三种法律关系。
其次,法律关系的形式是指法律关系所呈现的规范形式,与法律关系所指向的行为紧密相连。根据霍菲尔德权利分析理论,其基本规范形式(元形式)有四种:(狭义)权利(claim)—义务(duty)关系、自由(privilege)—无权利(no-claim)关系、权力(power)—责任(liability)关系、豁免(immunity)—无权力(disability)关系。其中每一种元形式的法律概念都是法律关系中的“最小公分母”,因此需要严格遵循其概念含义。
法律关系所指向的行为则是法律关系的客体。霍菲尔德坚信人才是法律关系的主体[3]101,法律规范的调整对象仅限于人的行为。即便物在法律关系中的作用巨大,本质上也只是行为的客体,而非法律关系的客体[2]184。因此,每一种元形式都指向主体的每一种行为模式,权利和义务最终都会依据元形式的指引汇聚到主体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中;反之,通过对行为的定位,我们也可以反推其背后的元形式,从而理解其法律关系的结构,也即权利的结构。
(一)用户与运营商之间的法律关系
首先,在账户由运营商“转让”给用户之前,即双方未达成用户协议时,运营商就整体的社交网络服务产品应存在如下四种法律关系:第一种,claim—duty关系,运营商有权利要求任何人不侵害其对自身产品的任意行为,任何人有义务不侵害运营商的这种权利;第二种,privilege—noclaim关系,运营商有不允许他人使用其产品的自由,任何人都无权利要求其允许;第三种,power—liability关系,运营商有权力处分其产品,任何人都有责任承受因该处分而发生的法律关系的变动;第四种,immunity—disability关系,任何人都无权力处分其产品,任何处分行为都不对运营商产生法律效力。账户作为整体产品的一部分,自然地为运营商对该产品的权利束所辐射。因此,未达成用户协议前,运营商对该部分账户同样享有上述法律关系中的各项权利。它们最终会聚合成一个类似于完整的所有权所应包含的法律关系。
其次,在达成用户协议后,不论不同社交网络服务产品之间的产品功能或权利义务约有何不同,基本上都存在如下六种法律关系:第一种,noclaim—privilege关系,即运营商无权利要求用户不使用社交网络服务,用户有使用社交网络服务的自由。第二种,duty—claim关系一,即运营商有提供社交网络服务的义务,用户有要求运营商提供社交网络服务的权利。第三种,duty—claim关系二,即运营商有保障用户个人信息安全的义务,用户有要求运营商保障其个人信息安全的权利。第四种,claim—duty关系一,即运营商有要求用户遵守法律、法规和网络社区公约等相关行为规则的权利,用户则有遵守这些规则的义务。第五种,power—liability关系,即当用户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公约的规定时,运营商有限制、终止用户使用社交网络服务的权力,用户有承受这种结果的责任。第六种,claim—duty关系二,即运营商有要求用户同意其收集、使用用户的特定使用信息的权利,用户有同意运营商收集其特定使用信息的义务②。
(二)用户、运营商与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在用户与第三人之间,围绕社交网络账户一般存在着如下法律关系:第一种,privilege—noclaim关系,即用户有使用自己的社交网络账户享受社交网络服务的自由,第三人无权利要求用户不使用自己的社交网络账户享受社交网络服务。第二种,claim—duty关系,即用户有要求第三人不故意侵害其社交网络账户的权利,第三人有不故意侵害用户社交网络账户的义务。第三种,immunity—no-power关系,即用户与运营商之间的法律关系不会因第三人的行为发生变动。此外,运营商基于对自身整体产品的权利以及对用户的数据安全保障义务,与第三人之间也存在claim—duty关系,即运营商有要求第三人不故意侵害其用户的社交网络账户的权利,第三人有不故意侵害其用户社交网络账户的义务。
二、社交网络账户的双务合同性质
社交网络账户作为网络虚拟财产的一种,对其财产属性之论证需要以过往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学说为基础。目前,学界以物权说和债权说为两大主流学说。在此基础上,通过社交网络账户相关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可揭示社交网络账户的双务合同性质。
(一)社交网络账户的债权属性证成
网络虚拟财产债权说认为,虚拟财产应属于用户的债权范畴[4],相对于物权说突破了对物的有体性和支配性等传统物权理论。债权说未对目前物权与债权的学理通说带来体系性突破,是一种相对合理且解释成本较低的学说[5]。但以往的债权说缺乏全面性,仅基于用户视角认为社交网络账户只存在用户的单方面权利。用户对社交网络账户的权利确是一种债权,同时运营商对社交网络账户的权利也不容忽视。
1.用户权利是具有相对性的债权
用户与运营商因用户协议而产生的法律关系是一种合同关系,用户对运营商的claim是一种合同权利。用霍菲尔德的术语体系表述前,应区分物权关系的claim和债权关系的claim。有学者指出,物权关系与债权关系的本质区别不在于权利内容上的差异,而在于一方主体成为物权人时,将自然地与世界上全部人产生法定物上关系,其内容为排除第三人干涉;但在合同关系中,任何一方均不因合同本身而与第三人自动产生法定的法律关系[6]。这与霍菲尔德对物权绝对性和债权相对性的概括性描述相一致。在霍菲尔德的术语中,债权关系的claim是一种特定的claim,它所针对的义务人自始至终特定。而物权关系的claim则不然,其天然地辐射至权利人之外的人,通常具有消极属性,即要求他人不为行为。
在用户与运营商之间的法律关系中,用户拥有“要求提供服务”和“要求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的两项claim。后者实际上是一种人格权请求权,是法定的不特定的claim,不论双方是否存在协议,运营商也负有不侵犯用户个人信息的duty。唯独前者因双方达成协议而产生,且用户并不因此就该项claim与第三人之间自动产生法定的法律关系。用户就该项claim只能要求运营商承担duty,即要求运营商提供社交网络服务,用户只能通过运营商的配合来行使有关社交网络平台及服务的权利。而第三人并不因用户协议负有为用户提供服务的duty,用户也无权要求其为自己提供社交网络服务。因此,用户依据用户协议所享有的针对运营商的claim,仅是一种具有相对性的合同债权。
2.用户协议是双务合同
(1)用户协议存在具有依存关系的对待给付
社交网络账户的注册取得通常并不需要用户支付金钱,但这并不意味着用户与运营商之间的合同关系是无偿、单务的。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合同的对价并不限于金钱,社交网络账户的注册使用实际上以“数据支付”取代“金钱支付”为主。“免费”获得账户的用户在使用服务时所产生的登录记录、消费记录及其他客户服务记录等零散的行为数据,将作为用户协议中的对价为社交网络服务运营商收集使用。正如张新宝教授所指,“所谓免费模式其实只是虚假的表象,其实质是用个人信息③的提供(同意收集使用)代替了‘金钱’支付,因而它并不免费。”[7]用户与运营商之间的用户协议本质是“以物易物”的有偿合同,进一步而言,该类协议应为一种双务合同。用户协议不仅规定了用户享有要求运营商提供服务的claim,也规定了运营商享有要求用户同意其收集使用用户信息的claim,这实际上构成了对待给付关系。用户在注册账户时,往往需要点击“我已认真阅读并同意该用户协议”才能完成注册,而协议通常也包含了用户对个人信息的授权使用条款。一旦用户拒绝授权,协议就无法达成。为了获得社交网络服务的使用,用户不得不“同意”运营商对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一方当事人愿意负担履行义务,旨在使他方当事人因此负有对待给付的义务[8]569,这说明用户与运营商之间的给付具有依存关系[9]75。
(2)用户协议具有权利义务的对应性
同时履行抗辩是认定双务合同的关键要素[10]114,用户协议的双务合同性质更多表现在用户对运营商获得其使用设备相应权限的授权上。这些权限的授予并不必然包含在用户协议中,但其本质是相同的,即不授权则无享有。以微信为例,若用户想通过通讯录添加好友,就必须授予微信读取手机联系人列表的权限;若用户想使用微信运动功能,就必须要授权微信收集用户的步数信息。用户必须以自身的信息作为对价获得相应服务,而当用户拒绝提供这些信息时,运营商也可以拒绝提供相应服务,这是一种同时履行抗辩的体现。用户“免费”获得的社交网络账户,实际上是以其个人信息作为对价与运营商交换的结果,因此,双方所达成的用户协议自然是一种双务合同。
有相反观点认为,用户基于用户协议与运营商形成合同关系,取得社交网络账户,并不能证明社交网络账户的债之属性[11]377。但实际上,社交网络账户是用户协议的具现化数字凭证,其存在代表着用户与运营商之间的合同关系。所谓社交网络账户的本质,在于其所包含的法律关系。通过上文对社交网络账户法律关系的解构可以发现,无论是运营商提供的服务,还是用户对个人信息收集的同意,都是一种具体的行为,而这些行为统合在社交网络账户之下,最终构成了双务合同关系。因此,社交网络账户的本质就是双务合同。
(二)社交网络账户的物权定性障碍
网络虚拟财产的物权说认为,网络虚拟财产是一种特殊的物,即虚拟物,是互联网时代物的特殊形式④。用户在此之上享有所有权,可以依其意愿对网络虚拟财产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且此种权利是绝对、排他的。该说持有两个基本观点:一是认为物权的客体不应只局限在有体物中,凡具有法律上排他支配性的,均可认为是物;二是认为网络虚拟财产的依附性并没有影响到用户对这一网络虚拟财产本身的排他支配力,用户对该财产仍拥有最终决定权[12]96。霍菲尔德的财产概念同样认为“物”在财产体系中并非必要概念。法律关系终究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非人与物的关系,因此不论有体物是否作为权利的对象,财产都可以存在[2]96。如商业秘密、商誉等,都早已脱离了有体物的范畴。但对于社交网络账户而言,其是否能够被视为一种物,仍需要从其法律关系的构造着手,对用户权利的产生与对世排他性之有无两方面进行商榷。
1.用户权利来源证明其并非物权
用户就社交网络账户所拥有的权利是否为物权,可优先通过权利的产生路径判断。暂且不予讨论有体物的限制,试假定社交网络账户是整个社交网络服务产品的可分割部分,运营商通过用户协议将该部分“转让”给用户,用户据此取得账户的“所有权”,此时以处分行为或负担行为模式作为路径,可以分析得出原本运营商对该账户所拥有的权利发生了何种变化。在霍菲尔德的术语中,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均导致了法律关系的变动,但前者是产生claim—duty的行为,是对privilege的变动;而后者是导致claim转移、内容变更、消灭等的行为,是对claim的变动。正如梅迪库斯所言,“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不同,它并不以产生请求权的方式为作用于某项既存的权利做准备,而是直接完成这种作用行为。”[13]163privilege是一种受法律认可的自然自由,不存在转让的问题,其变动结果只能是否定privilege从而产生duty。相反,claim是一种积极的请求他人为或不为的权利,因此处分行为对claim的变动既包括否定,也包括转让。
在上述假设中,若将用户权利视为一种所有权的继受取得,则说明运营商通过处分行为处分了自己的权利。由于处分行为针对的是claim,效果是发生claim的转让,将“有权利要求任何人不侵害其对自身产品的任意行为”的权利让渡给用户后,运营商失去该权利并退出了原本的法律关系。此时,哪怕认为运营商针对该账户仍有“对其产品进行任意行为”的privilege,但由于claim的丧失,也将导致这种没有claim的privilege毫无意义。这意味着,运营商对该账户将不存在任何积极作为的权利。然而现实中,一旦运营商丧失了账户“所有权”,用户将有权利拒绝其对账户中的服务内容作任何改动、调整、更新等变动,致使运营商丧失对自身产品经营环境的控制和管理能力,从而导致正常运营秩序的崩坏。这就是大多数运营商在用户协议中规定“所有权保留”条款的正当性缘由⑤。将处分行为替换为负担行为后,对运营商的claim不会发生变动,但将否定针对该账户的privilege,即“运营商有不允许他人使用其产品的自由”变成了“运营商有义务允许他人使用其产品”。相应地,用户从“无权利要求运营商允许其使用”变成了“有权利要求运营商允许其使用”。这显然是通过否定privilege产生了新的claim—duty关系,即“用户有要求运营商提供社交网络服务的权利,运营商有提供社交网络服务的义务”。可见,认定该权利的债权属性更契合用户与运营商之间的法律关系结构。
当然,此前已有学者敏锐地意识到,运营商与用户之间的关系“类似”于许可使用关系[14]。从“许可行为”⑥的维度看或许更为直截了当。霍菲尔德术语中的“许可”意味着许可人免除了被许可人原有的不得侵犯许可人财产的义务,是产生免除被许可人duty进而产生privilege的行为[15]。在该情形中,若将运营商许可视为用户对账户的权利来源,运营商对整个社交网络服务产品的权利依然存在,对整体产品的管控力也依然存在。运营商只是通过许可的方式,免除了用户不可侵犯其社交网络服务产品的duty,从而赋予其可以使用社交网络服务的privilege。
2.用户权利不具有对世排他性
社交网络账户无法成为物权客体的重要原因还在于用户权利缺乏对世排他性。霍菲尔德认为,所谓对物权,实质上是权利人对每一个不特定的人所拥有的相似权利的集合,是数个法律关系的结合体[3]101。简要而言,在claim-duty关系上,一个正常的所有权人应拥有除法定或约定限制之外“要求每一个人不侵占其财物、不妨碍其对财物的任意处置”的权利。但在社交网络账户的三方法律关系结构中,用户却没有此类针对运营商的claim。如“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中⑦,针对应援集资、造谣攻击、侮辱诽谤等有害内容的违法违规账号,运营商有权依据政策法规及用户协议以“禁言”“注销”“关闭”等方式处置。被处置账户的用户只能依据用户协议申诉,无法以所有权主张运营商恢复原状。
曾有观点认为,社交网络账户的支配性不应局限于“实际占有”,而应体现在用户通过“权利联系”对储存于网络环境中的特定信息形成现实支配[12]96。该观点扩张了“支配”的内涵,但这种“权利联系”的支配仍不能脱离“排除他人干涉”的本质[16]108。如在信托中,受益人所享有信托受益权,因信托财产的独立性而得以对抗受托人的个人债权,且受益人亦享有对受托人行为的撤销权,故符合“排除他人干涉”之特性,可以视为一种“权利联系”的支配。但这种“权利联系”的支配路径在社交网络账户中随时可能被运营商切断。依上文所列举的各项法律关系,运营商实际上拥有单方面改变与用户间的法律关系的权力(power)。这种power或源于约定,如服务设备检修维护所造成的服务中断、长时间未使用而造成的账户回收等⑧;或源于法定,如《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简称《公众账号规定》)第8条规定,运营商应终止向擅用他人名义且拒不改正的用户提供服务。这说明,用户并不享有此种claim以排斥运营商对其账户的干涉和限制。此外,社交网络账户的内容甚至无需用户意愿,仅依运营商的意愿即可改变。即便用户有要求改变服务内容的privilege,没有关键的claim也不能使账户内容发生变化。可见,用户权利并不具有对世排他性,并非物权。
三、社交网络账户的适用规则
立法目前仅对网络虚拟财产作了原则性规定,但并不意味着各类网络虚拟财产在现行立法中均无法可依。通过上文分析可知,社交网络账户的本质是用户与运营商之间的双务合同关系,因此,应遵循合同之债的思路探析社交网络账户的法律规则适用。
(一)转让规则
社交网络账户的转让应遵循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移的规则。虽然大多数运营商都在用户协议中禁止了用户对账户的流转,但已有学者从格式条款无效的角度进行过论证[11]378,因此,其转让问题的核心不在于能否转让,而在于如何转让。这可以从《公众账号规定》中得到启发。《公众账号规定》第11条规定,“公众账号信息服务平台应当依法依约禁止公众账号生产运营者违规转让公众账号。公众账号生产运营者向其他用户转让公众账号使用权的,应当向平台提出申请。”该规定并未否认账户的可转让性,且将用户对账户的权利明确为使用权,充分凸显了用户与运营商之间的合同关系。但债权让与并不需要债务人的同意,如果仅是使用权的转让,哪怕认为运营商有确保账户实名制的责任,用户对其账户的转让也应该是“通知”而非“申请”。
显然,该条背后的法理并不是债权让与,而是合同的概括承受。一旦用户转让其账户使用权,就意味着其与运营商之间整个合同关系的改变,原用户退出,新用户进入。而唯有原用户承担着相应的合同义务,才会存在运营商“同意”的空间,否则,其使用权的转让仍是一个单纯的债权让与。因此,《公众账号规定》实际上揭示了社交网络账户的转让方式,即应根据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移的规则进行。
(二)继承规则
本文认为,社交网络账户可以作为一项财产被继承,运营商对死者隐私利益的保护与其继承人继承其账户并不矛盾。在我国继承法体系内,仍应承认对社交网络账户的法定继承,在尊重被继承人意思自治的前提下,只有被继承人明示其账户不得继承,继承人才无权继承取得该账户。
围绕个人隐私、通信秘密等死者人格利益,社交网络账户的继承问题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方面,有学者认为,死者的账户承载着死者的隐私利益,不能被继承[17],除非死者有相反且明确的意思表示[18];另一方面,也有观点认为,尽管死者账户中含有死者隐私利益,但运营商向用户继承人开放账户的使用权并不违反其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义务[19]91。本文持后一种观点。基本前提是,社交网络账户不是一个具备高度人身专属性的合同关系,否则不存在账户转让的问题。尽管社交网络账户具有一定的人格属性,涉及用户的隐私利益,但这并不能成为阻碍继承人取得死者账户的理由。
运营商对用户隐私的保护义务和用户继承人的继承权,实际上并不存在对立的矛盾。自2012年德国“Facebook案”⑨后,德国司法实践认为社交网络账户是普通的遗产,作为虚拟财产的一种构成死者财产的一部分,符合《德国民法典》第1922条关于死者财产概括继承的规定。该案的焦点在于Facebook公司为继承人提供死者账户是否违背《德国电信法》第88条向运营商规定的通信秘密保护义务。一审柏林州中级法院认为,协助继承人取得死者的Facebook账户与通信秘密保护并不冲突,因此支持了原告母亲的诉求。二审中,柏林州高等法院认为运营商在用户去世后仍负有《德国电信法》第88条上保护用户通信密码的义务,因而推翻了一审判决。德国最高普通法院最终在三审时认为,运营商向继承人提供死者账户符合《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6条第1款b的选项(1)和第6条第1款f的规定⑩,因此又重新认可了一审判决,推翻了二审结果[20]。
该案所涉《德国电信法》第88条有关运营商通信秘密保护义务的规定与我国《电信条例》第65条类似,其中《电信条例》第65条第二款规定“电信业务经营者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擅自向他人提供电信用户使用电信网络所传输信息的内容”。此条重点在于对“他人”的理解。实际上,从法律关系的结构和我国立法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路径可以推断出,“他人”不应包括用户的继承人。一段法律关系中必然有两方法律主体。在保护死者隐私的问题上,运营商显然是承担义务的一方,那谁是主张权利的一方呢?我国《民法典》第994条明确,对于死者的人格利益保护,由其配偶、子女、父母或其他近亲属来依法请求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对于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而言,无论是采直接保护说还是间接保护说,死者近亲属最终都是死者人格利益的法定维护者[19]90。因此,在保护死者隐私的问题上,与运营商的义务相对应的是死者近亲属的权利,享有继承权的近亲属并不是运营商为保护死者隐私的防范对象。死者近亲属通过继承取得含有死者隐私内容的账户并不会对死者的人格利益造成侵害。
不可否认的是,死者在生前的意思自治亦应当得到尊重。为了平衡死者隐私和继承人的利益,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制定并通过了修订版的《统一受托人访问数字资产法》(RUFADAA),该法案规定“受托人”可根据“三层优先访问体系”访问数字资产,即“线上遗嘱>线下遗嘱>用户协议”的效力体系。若用户生前已利用在线工具制定数字资产披露指示的,该指示优先,即线上遗嘱优先于网络服务协议条款。若用户生前没有上述指示的,带有处理数字遗产指示的书面授权优先,即线下遗嘱为第二优先。若二者均不存在,数字资产将按照用户生前与运营商签订的网络服务协议条款处理[21]。
美国这一立法值得我国参考借鉴,但需对其本土化。一方面,依我国《民法典》第1142条对遗嘱效力顺位的规定,线上遗嘱并不必然优先于线下遗嘱。因此若移植该规定,仍应遵循《民法典》第1142条的规定,以最后的遗嘱为准。另一方面,RUFADAA将原本对于线上数据披露授权的默示规则改为了明示,以此限制受托人的权限,导致社交网络账户只能通过遗嘱方式继承。但结合德国的司法实践以及我国《民法典》第1122、1123条的规定,只要是遗产就可以继承。遗嘱、遗赠扶养协议是对法定继承的修正,是被继承人意思自治的体现。因此在我国继承法体系内,仍应承认对社交网络账户的法定继承,只有在被继承人明示不得继承的前提下,继承人才无权获得对社交网络账户的继承。
(三)救济规则
对于社交网络账户的救济,核心在于债权是否受我国侵权法的保护。在第三人故意侵害用户的账户时,第三人应承担侵权责任。社交网络账户存在着来自运营商或第三人侵害的风险,若侵害来自运营商,通常可依据合同关系向其主张违约责任;但若来自第三人的侵害,即第三人侵害债权,用户如何向第三人主张权利则一直是学者们争议的焦点。曾有观点以此对债权说提出质疑,认为第三人侵害债权本质是因第三人原因导致的合同履行瑕疵,根据合同的相对性用户只能向运营商主张违约责任,而不能直接向第三人主张权利救济[22]。这使得在用户权利受到侵害时,债权说的保护力度较之物权说稍逊一筹[23]。
但对于社交网络账户而言,其遭受第三人的侵害更多是第三人有意为之的结果,因此要求其对此承担责任并不会造成对其行动自由的过度限制。现实中用户在账户遭受第三人的侵害后,因难以查明第三人的具体身份,通常只能第一时间向运营商申请使用技术手段恢复自己的账户。但用户依然有依据直接向第三人主张其权利。如《德国民法典》第826条规定:“以违反善良风俗之方法对他人故意施加损害之人,对受害人负有赔偿损害之义务。”这实际上就是对第三人故意侵害债权的一种规制[16]61。日本民法理论也认为,以自由竞争为根本原理的社会中,自由竞争行为即便事实上妨碍了债权给付的实现,原则上也不构成侵权。但如果加害人主观上具有侵害债权的故意,则成立侵权行为[24]57。可见,在大陆法系中,债权并不是完全不受侵权法保护的。
目前我国《民法典》已对第三人侵害债权作出了体系性安排。以往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条对侵权法的保护范围采“一般列举+概况”的模式,列举的民事权益中未列入债权。仿佛有意将债权排除在外,使得寻求第三人侵害债权的侵权法救济依据只能从“等人身、财产权益”中的“等”字解释。但随着我国《民法典》的通过和施行,这一情况得到了改变。《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1164条采全面概括模式立法,明确因侵害“民事权益”而产生的民事关系为侵权法的调整对象。其中,民事权益的范围又以总则编第5章民事权利的范围为参照,而该章第118条明确规定,“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债权”。至此,我国侵权责任编已明确将债权纳入其保护范围之内,这为民法典时代下以第三人侵害债权为理论基础,构建关于社交网络账户的权利救济路径提供了立法依据。
注释:
① 2021年网络“清朗”系列专项行动举行新闻发布会,载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www.cac.gov.cn/2021-05/08/c_1622061067961460.htm,2021年9月10日访问。
② 如《微信软件许可及服务协议》第9.3条规定,“你理解并同意腾讯为实现产品目的,对你发布的特定公开非保密内容如‘视频动态’‘自拍表情’和‘视频号内容’等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使用,包括但不限于予以存储、向有关用户播放、供有关用户获取及再次使用等。”载微信网,https://weixin.qq.com/agreement?lang=zh_CN,2021年2月7日访问。类似规定还有《微博服务使用协议》第1.3.1、4.7、4.8条等,载新浪网,https://www.weibo.com/signup/v5/protocol,2021年9月7日访问。
③ 张新宝教授认为“个人数据”与“个人信息”无实质区别,本文亦采此立场。
④ 物权说的观点一度成为学界主流,如杨立新、王中合《论网络虚拟财产的物权属性及其基本规则》,载《国家检察官院学报》2004年第6期;屈茂辉《关于物权客体的两个基础性问题》,载《时代法学》2005年第2期;许可《网络虚拟财产物权定位的证立》,载《政法论坛》2016年第5期;杨立新《民法总则规定网络虚拟财产的含义及重要价值》,载《东方法学》2017年第3期;谢江东、梅慎实《论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载《南海法学》2017年第5期;沈健州《从概念到规则:网络虚拟财产权利的解释选择》,载《现代法学》2018年第6期等,都持物权说观点。
⑤ 如《QQ号码规则》规定:“QQ号码是腾讯按照本规则授权注册用户用于登录、使用腾讯的软件或服务的数字标识,其所有权属于腾讯。”载腾讯网,https://zc.qq.com/chs/agreement1_chs.html,2021年2月7日访问。
⑥ 负担、处分和合同、许可、授权是对霍菲尔德术语中power的不同维度类型化,两种维度是否相融,目前仍未有定论。
⑦ 中央网信办启动“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见中国网信网www.cac.gov.cn/2021-06/08/c_1624735580427196.htm,2021年9月10日访问。
⑧ 如《微博服务使用协议》第3.5.6条。
⑨ 2012年,一名德国母亲希望登录已去世女儿的Facebook账户,因该账户已被设计成纪念账户而无法登录,在要求Facebook公司协助登录无果后,这名母亲最终诉诸法院。参见腾讯研究院:《从德国Facebook案看社交账号的继承问题》,载“腾讯研究院”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jEpSxa3XClPZyr3Rl RdiDA,2021年8月31日访问。
⑩《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6条“只有满足至少如下一项条件时,处理才是合法的,且处理的合法性只限于满足条件内的处理……(b)处理对于完成某项数据主体所参与的契约是必要的,或者在签订契约前基于数据主体的请求而进行的处理……(f)处理对于控制者或第三方所追求的正当利益是必要的,这不包括需要通过个人数据保护以实现数据主体的优先性利益或基本权利与自由,特别是儿童的优先性利益或基本权利与自由。载“人大未来法治研究院”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uE4PUdw-uZhMUbcBoQf K_A,2021年2月10日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