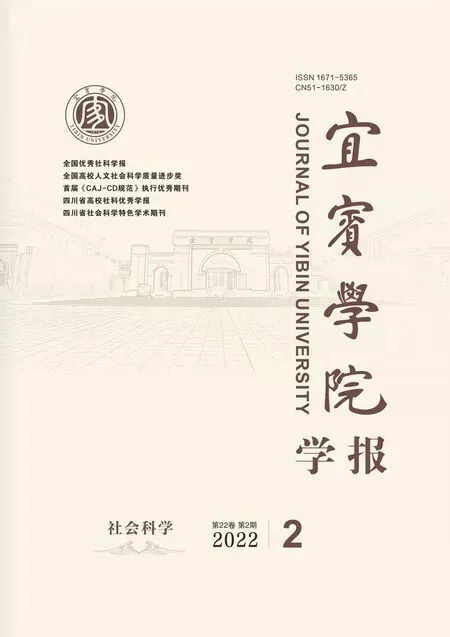微信公众平台赞赏功能的交易属性及制度分析
鲍强强
(郑州大学 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2019年9月18日,微信订阅号“呦呦鹿鸣”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布《致在新房里痛哭的女子》一文,文章中有女业主在房间里哭泣的视频素材。9月20日,该女子以文章使用其哭泣视频且获得读者赞赏为由,要求文章作者向其支付版权费2 000元。根据当时新浪与网易发布投票,支持付费与不支持付费人数相当①。读者的财产权通过“赞赏”转移给了文章作者,文章作者是否应当将其获得的部分财产转移给视频素材的提供者,大家对此产生了不同的认识。部分网友认为自媒体平台发布文章获得的赞赏是对文章作者付出劳动的报酬,该女子对文章也做出贡献,因此应当得到与其劳动相应的报酬,这或许是网友支持其索要“版权费”的理由之一。这种说法看似符合约翰·洛克的“劳动财产理论”,即财产权是对勤奋劳动的合理报酬。但具体到知识产权,此“劳动”并非彼劳动。洛克的“劳动财产理论”并不是强调在一个现存物品上贡献了某种新的物品,而在于通过付出劳动,对现存物品加以转化[1]36。即视频素材提供者并不是简单的通过哭泣并拍摄,付出了劳动,文章作者就应当向其支付一定的财产作为对价,而是视频素材提供者的付出对文章内容和思想是否产生了一定的提升作用,并基于此向文章作者主张财产权。至此,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即读者对微信公众平台赞赏属于何种民事法律行为?赞赏所得是读者基于文章对作者的赠与,还是公众对其阅读文章后带来美好体验而向作者支付的报酬或对价?上述不同认识说明,虽然我们对于自媒体平台原创作品赞赏已经习以为常,但对赞赏功能的基本性质及定位仍不清楚,而这恰恰是解决文章作者是否应当向视频素材提供者支付报酬的关键。
一、微信公众平台赞赏功能赠与属性说
(一)赠与属性说的由来
微信公众平台赞赏功能自2015年3月内测上线以来,我们已经对其习以为常。依据《微信公众平台赞赏功能使用条款》1.1微信公众平台赞赏功能:指腾讯向微信公众账号用户和微信赞赏用户提供的,允许微信用户自愿通过公众账号用户发布的文章内容向微信赞赏用户赠与款项以示鼓励的功能[2]。2016年6月13日,苹果开发者协议更新,认为微信公众平台打赏是购买行为,而微信方面则认为这是读者对公众号作者的赠与,而非购买行为[3]。2017年10月19日,苹果公司在其《App Store审核指南》增加3.2.1(vii),App可允许个人用户使用非App内购买项目机制向另一位个人送赠货币式礼物,前提为:(1)送赠方拥有决定是否进行送赠的完全自主权;(2)获赠方收取100%的礼物金额。然而,礼物若在任何时间点对应或包含接收任何数字内容或服务,则必须使用App内购买项目[4]。苹果认可微信赞赏为附条件的送赠货币式礼物。2018年微信公开课PRO版上,腾讯集团高级执行副总裁、微信事业群总裁张小龙称红包和赞赏这样的一些行为是比较有中国特色的,赞赏是针对作者进行赞赏,而不是针对一个公众号进行赞赏,似乎更加确认了赞赏功能的赠与属性。因此,腾讯公司认为微信公众平台赞赏功能具有赠与属性,体现了对作者的鼓励,这是目前微信公众平台赞赏功能性质的通说。
(二)微信公众平台赞赏功能赠与属性说形式上符合赠与合同的性质
1.赠与属性说为微信公众平台赞赏所得提供了财产转让的法律依据
微信公众平台赞赏功能符合赠与合同的相关规定。我国《民法典》第六百五十七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因此,作为微信公众平台原创文章的作者,其有权利取得文章赞赏所得,同时赠与属性说也否定了赞赏所得为作者发布原创文章的稿酬或者劳务报酬。
2.赠与合同的法定撤销权为赞赏资金的退还提供了法律依据
我国《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一条规定,赠与合同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第六百六十三条第一款(三)规定,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第六百六十五条规定,撤销权人撤销赠与的,可以向受赠人请求返还赠与的财产。
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发布原创作品应当遵守《微信公众平台原创声明及相关功能使用条款》,该条款为作者增设了其发布的原创作品不得存在抄袭等侵犯他人权益的行为和风险的附加义务。如违反前述附加义务,且申诉期内未进行申诉或者申诉经审核未通过的,腾讯公司可将未结算资金将退还微信用户。
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者开启原创作品赞赏功能即表示其具有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微信公众平台的赞赏功能是赠与人与受赠人达成赠与合意的同时即转移财产权利。虽然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但不影响赞赏所得的流转与分配。同时,将微信“赞赏”定义为赠与,不仅符合微信赞赏设立之初衷,也能够为微信赞赏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式各样的问题提供法律解决的依据和途径[5]。因此,微信公众平台赞赏功能赠与属性说形式上符合赠与合同的法律性质,也为赞赏所得的转让与分配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
据此,微信公众平台赞赏系读者为了鼓励作者创作而向作者赠与的款项,因此文章作者不应当向视频素材提供者支付一定的“报酬”。
二、微信公众平台赞赏功能赠与属性说的不足
(一)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看,赞赏并不具有赠与的典型属性
如张小龙所说,红包和赞赏这样的一些行为是比较有中国特色的,但仔细分析,赞赏与红包虽然都具有一定的主动性和自愿性,但二者的性质明显不同。在中国乃至亚洲地区,熟人之间在重大节日相互赠送红包确实具有中国特色。如果说赞赏也具有中国特色,赞赏更可能源于中国社会中观赏杂技曲艺等表演人员后对其表演认可而做出表示的传统,赞赏所得是杂技曲艺等表演人员为生的一种手段。同时,赞赏功能更加类似于现代的体验式消费,消费对象并非是有形商品,而是观看表演之后得到的一种精神体验和满足,红包明显不具有这种性质。因此,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看,赞赏并不具有赠与的典型属性。
(二)赠与的无偿性与微信公众平台赞赏功能的性质不相符
微信公众平台赞赏功能赠与属性说虽然从形式上解决了微信公众平台赞赏所得财产的转让与分配,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微信公众平台赞赏所得并不具有无偿性。读者是阅读文章后进行的赞赏,而阅读与载体无关,仅与阅读主体有关[6]。因此,赞赏是读者阅读微信公众平台发布的原创作品后得到精神满足与体验后向原创作者的赞赏,该以体验为前提,以得到良好的阅读服务为对价,如上文所述,其更加类似于对阅读服务的体验式消费。阅读服务是一种基于数字技术媒介,以用户行为及需求为驱动,提供优质的知识服务及知识衍生产品,塑造阅读价值链的,融合数字出版服务产业[7]。因此,读者基于微信公众平台发布的原创作品体验到良好的阅读服务得到精神满足与体验,并不具有典型的无偿性。一方面,运营者选择开通和使用赞赏功能表明其有获得收入的需求意愿;另一方面,读者给予赞赏具有主动性,赞赏人在阅读了公众号作品之后,以货币的形式传达了对文章的赞同,某种程度上属于知识付费的形式[8]。
(三)微信公众平台赞赏功能赠与属性说对赞赏者保护不足
虽然赠与合同赋予赞赏者任意撤销权和法定撤销权,由于网络技术原因赞赏无法撤回,因此,赞赏者无法通过行使任意撤销权撤回微信赞赏行为。同时法定撤销权看似为赞赏资金的退还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其实现比较困难,同时,仅仅退还赞赏资金对赞赏者保护略显不足。如李律平与厦门喂格鲁特科技有限公司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中,李律平阅读厦门喂格鲁特科技有限公司公众号发布的《请拖凑数、推APP、关联交易、中国平安和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真会玩》后打赏66元,后发现其所打赏文章内容不实,以构成欺诈为由要求退还打赏费用。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李律平与厦门喂格鲁特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的赠与合同为无偿、单务合同,厦门喂格鲁特科技有限公司并不因此负担对待给付义务,故李律平将66元款项给付厦门喂格鲁特科技有限公司后,相应的财产权利已经转移,因此,李律平不得任意撤销赠与并要求受赠人返还打赏款项。同时,在向相关部门及人员了解之后,厦门喂格鲁特科技有限公司及时发布后续文章进行更正和说明,并不存在虚构事实的情形,故李律平主张厦门喂格鲁特科技有限公司发布文章的行为构成欺诈,亦缺乏事实佐证为由驳回李律平诉讼请求。二审法院以李律平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厦门喂格鲁特科技有限公司不履行合同约定义务为由维持原判②。因此,虽然赠与合同的法定撤销权为赞赏资金的退还提供了理论上的法律依据,但实际操作中,除了腾讯公司发现文章被投诉或处罚而将打赏资金退还微信用户外,赞赏者通常无法提取并保存相关证据,很难通过自己努力实现打赏财产的返还,甚至还要承担诉讼费及产生的律师费用。
(四)微信公众平台赞赏功能赠与属性说难以实现其鼓励功能
腾讯公司认为微信公众平台赞赏功能具有赠与属性,是针对作者进行的赞赏,从而体现对作者的鼓励。赞赏功能一方面是对文章版权的尊重,同时也让作者有充裕的资金创作更多原创作品,形成用户与运营者双赢的局面[9]。同时,赞赏模式中读者付费的主动性、非强制性,说明这种赞赏付费完全是读者出于对作品抑或作者个人的认可[10]。但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赞赏所得是否能实现让所有作者得到充裕的资金创作更多原创作品尚待考证。
首先,原创作品大部分是微信公众号的订阅读者阅读,其订阅读者的数量多少不一,而赞赏多少与文章阅读量有关。因此,订阅量很小的公众平台发布的原创作品得到的赞赏很难保证为其创作提供足够资金。其次,赞赏具有非强制性和主动性,当前自媒体作品读者尚未建立起付费赞赏的习惯。因此,并非每一个原创作品均能得到赞赏,同一原创作品在不同微信公众平台发布,面对不同的读者得到但赞赏也不相同。因此,仅仅依靠读者自主的赞赏很难实现对作者的鼓励和支持。最后,作者与赞赏取得者的分离导致赞赏对作者的鼓励功能难以实现。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接受赞赏的用户并不一定为原创文章的作者,可能是原创作者授权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者发布。微信公众号上线至今,不同微信公众号订阅者数量差别极大,很少有公众平台能持续达到10万+的阅读量。赞赏所得与阅读量及读者对公众号的粘性成正比,而原创作品的持续创作并非一人能够完成。因此,一些作者与公众平台约定通过投稿的方式在其平台发布作品,赞赏所得由原创作者与平台经营者分成,或者平台经营者事先通过一次性向作者支付报酬的方式转让作品财产权利而获得所有的赞赏所得。此时,赠与属性说难以实现对作者的鼓励功能。
三、微信公众平台赞赏功能交易属性说
在微信公众平台赞赏模式推出后,2015年11月6日“付费阅读”相关字段出现在微信文章页面的代码中,说明微信开始着手推广付费阅读模式,这也预示着微信付费阅读的开始,87.06%的被调查者认为打赏行为预示内容付费时代即将到来[11]。但是,2016年6月微信与苹果支付争端的出现,使得微信重新重视赞赏功能的赠与属性,苹果公司认可其赠与属性而妥协,这也导致微信付费阅读项目停滞不前。
不论是按时间顺序分析,还是按微信与苹果博弈的结果来看,赞赏功能无疑是微信培养用户支付习惯的重要途径[12]。打赏实质上是消费者为良好的阅读体验买单,消费者打赏的自愿性和打赏的便捷性,预示着付费时代的到来[13]。2020年1月,微信公众平台重新推出付费阅读功能,同时赞赏功能并未取消,二者同时存在于微信公众平台,供不同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者选择。
2015年11月到2020年1月,付费阅读的推出一波三折,二者具有一定的共通性,赞赏功能表现出的消费和交易属性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有学者认为打赏具有先消费后付款以及自愿付款的特点,是免费思维与收费思维的融合,与粉丝经济和体验经济结合产生的一个变体[14]。通过免费知识补贴用户,借以占领市场、换取未来收入的手段,但内容长期免费会带来质量下降、进而引发市场的回调和分化,付费方式就会应运而生[15]。也有学者在研究国外媒体付费阅读模式后,提出微信公众号从打赏公众号文章开始,用户可以给喜欢的文章支付一笔“小费”,这是微信在付费订阅前尝试的一种非强制性的付费方式[16]。因此,微信公众平台赞赏功能本身蕴含阅读体验与付费的交易的属性,与当前推出的付费阅读无异。
如上所述,赞赏功能看似为粉丝基于良好体验之下的一种自愿消费,实则是其为内容买单的行为,可以潜移默化地培养用户为内容付费的习惯,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新媒体内容付费使用的进程[8]。微信公众平台赞赏功能使读者在满足受众学习知识和获取资讯的需求之外,也有利于培育用户付费阅读习惯的养成。因此,将微信公众平台赞赏功能视为一种消费和为阅读服务付费也符合市场交易的规则。
微信赞赏行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单务行为,在公众号发布文章时作者对文章的原创性负有保证义务。如果认为微信公众平台赞赏功能具有赠与属性,即认可赞赏实际为一种单务行为,赠与人无对价而支付利益,受赠人不负担任何对待给付义务即可获得利益,双方地位严重违反均衡正义[17]。有学者认为作者以提供文章作为对价,不符合赠与行为构成要件,是用户阅读获取知识后,对优质内容输出者的付费[18]。因此,公众号运营者不仅仅享有接受赞赏所得的权利,同时负有提供作品并保证作品原创性的义务。如果认可微信公众平台赞赏功能的交易属性,则双方权利平等,读者的合法权益会得到相关法律的保护。
我国《著作权法》制定的目的不仅保护作者著作权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更重要的功能是鼓励作品的创作与传播。微信公众平台赞赏功能仅考虑对作者创作的鼓励,却忽略了作品的传播。同时,消费代表了一种期待,认可微信公众平台赞赏功能的消费和交易属性,深化和用户的关系,吸引用户付费、用户愿意付费最终形成一种与用户的强关系,免费阅读虽然带来大量的用户,但是这种关系是非常浅层次的[12]。读者与微信公众平台的这种深层次的强关系,同时明确了读者作为付费用户的权利,免去读者分享文章又担心侵犯作者著作权等相关权益的后顾之忧,同时使那些尊重版权的读者思想上无搭便车之虞,有助于读者对文章的传播。
因此,根据微信公众平台赞赏交易属性说,赞赏系读者基于作品良好的阅读体验之下的一种自愿消费,是一种为内容买单的行为,那么文章作者应当按照视频对文章内容和思想提升的程度向视频素材提供者支付一定的“报酬”。
四、微信公众平台赞赏功能交易属性的制度分析
(一)《电子商务法》为交易属性说提供制度支持
有学者认为自媒体打赏行为是一种特殊的电子商务活动,是网民通过观看直播节目、阅读网络文章等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之后再贡献打赏,即获得精神满足之后为之付费[19],这也是微信公众平台赞赏功能的交易属性应有之义。我国《电子商务法》第二条第三款后段规定,金融类产品和服务,利用信息网络提供新闻信息、音视频节目、出版以及文化产品等内容方面的服务,不适用本法。这并不意味着《电子商务法》对微信公众平台赞赏功能的交易属性的不认可和对利用信息网络提供文化产品或服务交易的排除适用。我国《电子商务法》关于内容服务中“内容生产或者产生”的规制,有特殊管理的必要性,但内容生产后的交易环节,如电子书、数字音乐、数字电影的买卖或者在线播放,设计合同的成立以及数字产品的在线交付、电子支付等行为,仍适用《电子商务法》。
通过社交平台等方式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行为,因为其符合“利用网络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本质属性,所以应纳入电子商务法的调整范围[20]。对于以利用信息网络提供新闻信息、音视频节目、出版以及文化产品等内容为交易标的的电子商务合同行为,仍应当适用《电子商务法》第五十一条等关于采用在线传输方式交付合同标的的规定[21]。
(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保护阅读服务交易理论上的适用性
读者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赞赏功能的交易属性而阅读微信公众平台发布的文章接受服务,属于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应当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微信公众平台读者享有消费者的相关权利,显然比作为赠与者权益保护更加全面。虽然实践中尚没有出现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维护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其他自媒体平台交易的案例,但这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三)有助于目前征税管理制度实施
我国对“微信赞赏”所得的法律性质没有形成统一观点,理论界以赠与所得说、劳务报酬所得说和稿酬所得说三种为主流。若微信赞赏功能所获赞赏收入定性为读者对原创作者自发无偿的赠与行为,赞赏收入属于受赠收入,不应征税。若将“打赏”所得定性为“稿酬所得”[12],并且结合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提出具体的征管建议,以期在实践中可以更好得以运用,从而平衡经营者、自媒体平台和国家三方利益,推动我国自媒体行业税收制度发展,最终实现税收福利社会共享[16]。也有学者赞成将赞赏收入定性为经营收入,个人微信公众号赞赏行为是基于打赏人对公众号运营者发表文章的价值认同而给予的对等支付。一方面,运营者选择开通和使用赞赏功能表明其有获得收入的需求意愿,另一方面,读者给予赞赏具有主动性,赞赏人在阅读了公众号作品之后,以货币的形式传达了对文章的赞同,某种程度上属于知识付费的形式,因此本质上赞赏收入是一种经营收入[8]。
从征税管理的角度看,无论稿酬所得还是经营性收入,都摈弃了赠与所得说。交易属性也涵盖了稿酬所得与经营性收入,因此,确认微信公众平台赞赏功能的交易属性,将其认定为作者或者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者通过交易得到的报酬,无疑对我国目前税收管理制度的实施提供了更好的理论支持。
结语
澳大利亚学者彼得·德霍斯教授在《知识财产法哲学》中采取财产工具论的立场同样有助于我们分析微信公众平台赞赏的性质并得出其交易属性。在科学哲学范畴,工具论是组织观察结果以获得先见与结论的实用手段[22]221-228。工具论属于实用主义哲学,更多关注财产行为方面,同时还借鉴了法律的经济学方法,支持计算知识财产保护的社会成本。其认为知识财产权是抑制自由的特权,建立在工具论基础上的特权伴随着特权拥有者的义务,该义务以不损害特权最初被授予的目的的方式行使特权。实现最初设立该特权的目的的可能性是最大化赋予知识财产所有者一定的义务。同时,有权利必然有义务,但这些义务独立于权利而存在,该义务基于人类基本价值的共识而产生[22]221-228。
每个国家不同时代制定的法律必然有其内在的价值,其中蕴含法律体系中公平正义的原则和理念。基于此,我们分析微信公众平台的交易属性也离不开我国当前法律中蕴含的价值。我国《著作权法》制定的目的不仅保护作者著作权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而且鼓励作品的创作与传播。微信公众平台赞赏功能的赠与属性说表面上解决了赠与财产的取得与分配,但其与我国相关法律制度难以衔接,也未全面保护作者和读者合法权益,对作品的创作与传播起到的鼓励作用有限。因此,站在知识财产工具论立场,我们认为,微信公众平台赞赏功能的交易属性说比赠与属性说更有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注释:
① 参见新浪微博投票https://vote.weibo.com/h5/index/index?vote_id=2019_347554_-_86109e;网易新闻投票http://vote.news.163.com/vote2/showVote.do?voteId=70869。
② 参见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2民终4106号民事判决书,http://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3831010c07ba48e3990aaaf70091023e,最后一次访问2021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