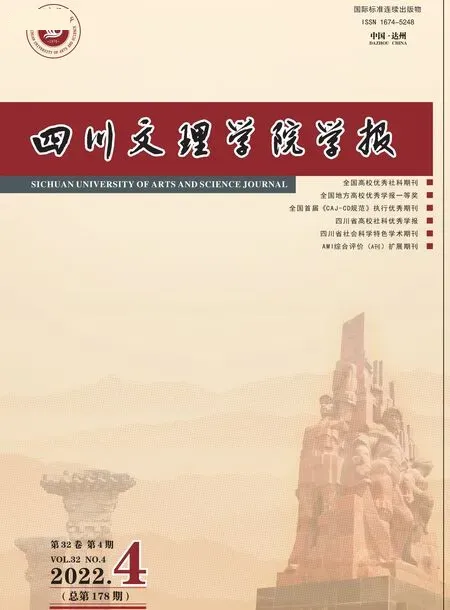《修辞学发凡》的术语修辞实践
张春泉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北碚 400715)
术语修辞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机制。术语修辞,简单地说,是术语的有效生成或适用(适当使用)。概括地说,术语修辞,包括消极术语修辞和积极术语修辞。消极术语修辞,是指术语的合常规适用;也指术语的一般生成(常规造语)。积极术语修辞,是指术语的超常规适用;亦指术语的临时生成或其他形式与方式的修辞造语。术语修辞是利用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有效生成、建构、调整、传播术语。[1]文学话语建构需要术语修辞,学术话语建构同样也需要术语修辞。近现代以来,不少学术大家积极建构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者陈望道即属此列。修辞学家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的术语修辞实践即为范例。学界对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修辞学史方面,较少关注《修辞学发凡》的学术话语实践。
在我们看来,陈望道不仅有卓越的术语学思想,[2]还有丰富的术语修辞实践,《修辞学发凡》即可作为其术语修辞实践的代表作。《修辞学发凡》首次出版于1932年,由大江书铺出版,其后有多个版本。我们以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大江书铺1932年版为主要语料来源,探究《修辞学发凡》术语修辞的基本动因、运作机制、领域生态、风格要素。
一、认知与审美:术语修辞的基本动因
术语是表征和传播科学知识的基本单元。一般认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术语学著作是1987年问世的《现代术语学引论》。[3]饶有意味的是,虽然未及系统研究术语学,《修辞学发凡》早已直接论及“术语”。“如语言上有术语、俚语、方言、古语……种种,辞的背景情味也就随着而有术语的、俚语的、方言的、古语的等多种不同的情趣。见用术语时,对于那语的背景就会有专门人物或专门知识等联想;看了或者会有庄严深奥等感杂然并呈,形成以其语为烧点的一团情趣。使其语所要表现的思想,因此更其不悬空,不单弱。”[4]231这里关于术语功用的描述“不悬空”,十分贴切。
《修辞学发凡》术语修辞的基本动因(或曰理据)是认知和审美。认识人自身、社会和自然界,获取各类信息,都是认知。认知主要是理性活动,除了理性活动,人还有感性活动。审美就是诉诸感性的常常以认知为基础的让人感动、让人感兴趣的活动。修辞的美是言语活动的美,是言语活动的“尽职”。“我们以为,文章在传达意思的职务上能够尽职就是‘美’。能够尽职的属性,就是美质。这个美质,也并不一定要显现在文章上,如显现在言语上也未始不可能;单就显现在文章上的而说,就是‘文章的美质’。”[5]55正是这个意义上的美质,“我们可以将彼分别为三:第一要别人看了就明白,第二要别人看了会感动,第三要别人看了有兴趣。”[5]55陈望道先生说的“美”包括“文章”的美和“言语”的“美”,一定意义上可以包括术语修辞的审美。认知和审美促使术语修辞的发生。例如陈望道先生关于“文法”这个术语的定名即较为充分地考虑到了认知和审美因素。“文法”定名、正名后多次使用于《修辞学发凡》。例如:“文法组织,无论是词的组织,还是句的组织,都是比之某些词汇较难变动的,但在汉语文中也已经有了不少的变动、改进。”[4]37-38修辞学著作中使用“文法”首先可看作是一种术语的跨领域传播,尽管“文法”和“修辞”是十分相邻相近的领域。
再就“文法”本身而言,《修辞学发凡》中使用的术语“文法”的定名,无疑是一种修辞活动,是一种术语修辞。陈望道先生曾经谈到“文法”这个术语的定名理据(修辞动因,也是定名的心路历程)。术语修辞动因与效果是统一的。可以通过术语解释统一起来。一定意义上,术语解释也是一种术语修辞。陈望道内省式地谈到了自己为何使用“文法”,而不用“语法”等。“‘文法’一词修辞的功能也比较强,可以作种种的譬喻用法用,‘语法’却没有这种能力。……此外我们还可以说某人研究音乐文法,某人学习戏剧文法,以及某校擅长排球文法,某校擅长足球文法等等。”[6]597以上是陈望道主张采用“文法”这个术语作为文法学科的定名或正名诸理由的第三条,这条理由直接与修辞相关,是基于修辞功能上的考量。文中共四条理由,第四条理由是:“作为语言的组成部分共有三个要素:语音、词汇、文法。用‘文法’这个名称和语音、词汇配合,也比用‘语法’的名称更为整齐些匀称些,如果采用‘语法’一个名称,那与语音词汇配合起来就有一个‘语’字重复。”[6]598其中“整齐”和“匀称”主要是就审美而言的;“如果采用‘语法’一个名称,那与语音词汇配合起来就有一个‘语’字重复”似乎是兼有认知和审美上的考虑。可见第四条理由也是与认知和审美直接相关。此外,第一条理由:“‘文法’这个术语的历史比较长,流行也比较广,早已有约定俗成之势。采用这个术语为文法学科的定名或正名,最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也最便于说明文法学科的历史发展。”[6]597不难理解,“喜闻乐见”和“便于说明”是着眼于审美和认知的。再看第二条理由:“‘文法’这个名称的含义也比较明确、简括。《释名·释言语》:‘文者会集众采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也。’‘文’字的本身就有语文组织的意义,‘语’字本身没有组织的意义。”[6]597这一条从语源上的形象观照文法“组织”,有一定的说服力。虽然“文法”在今天因为种种原因还是为“语法”所替代,但陈望道关于“文法”的定名、正名却是很好地阐明了术语修辞的认知和审美理据。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修辞动因,认知和审美也是相关的。事实上认知与审美常常可以通过术语修辞融通起来。《修辞学发凡》有言:“我们前面所谓记述的境界和表现的境界,便是假定有这两种体式的纯粹境界说的。但纯粹的境界实际上是少见的。例如最尚平淡的科学的语文,现在也常有所谓肺管肺叶,所谓车手车肩等等,用了好些隐喻。而最尚绚烂的诗词,又不见得句句都用辞藻。”[4]270其中的“肺管肺叶”“车手车肩”等术语的修辞造语,具有鲜明的形象性,更便于接受者认知,正说明了术语修辞的存在及其在认知和审美上的融通。
二、规范与变异:术语修辞的运作机制
规范与变异不是泾渭分明的,二者互有关联,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对应类似于认知与审美的关系。就变异而言,有个体变异和社会变异。这里所说的变异以规范为基础,乃有序变异,是一种分析扬弃,是语词的调整适用。规范是对无序变异的规范。术语定名、正名、解释往往伴随着规范与变异的互动。
或可说术语几乎与生俱来地需要规范,但在领域交叉和融通之后,可能发生变异,具体可体现为语体义和指称义及其他义素的变异。“语言单位发生义素变异,扩大了其组合功能……语言单位之间由于义位组合等条件的限制,在构建言语结构体时,往往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功能上的特殊性,诸如能与什么组合、不能与什么组合、与什么组合好、与什么组合不好等等,义素变异后的语言单位从某种程度上克服了这种不足,使原来‘不能’的组合形式变为‘可能’,于是富有创造性的言语表达方式便产生了。”[7]用陈望道先生的话说,规范是“零度”,与之相对的变异是“零度以下”。就意义而言,“语言文字的固有意义,原是概念的、抽象的,倘若只要传达概念的抽象的意义,此外全任情境来补衬,那大抵只要平实的运用它就是,偶然有概念上不大明白分明的,也只要消极地加以限定或说明,便可以奏效。故那努力,完全是消极的。只是零度对于零度以下的努力。”[4]70这里的“零度”颇为耐人寻味,它自身即是从其他领域(譬如数学)借用而来的。王希杰先生在谈及“词语附加意义的偏离”时似有对照性的表述,“修辞学的任务就是词语附加意义的负偏离的零度化,或者是正偏离化。”[8]
一定意义上,“规范”与消极术语修辞相对应。例如:
(1)析字是构成所谓廋辞的重要方法。廋辞一名,始见于《国语》……这条解释就是说:廋辞便是隐语,便是隐伏谲诡的话。但秦客当时的话,已不可考,我们无从确知它的内容。只从后世修辞情形倒推起来,我们大致可以推定它不外乎析字。这种廋辞,有时也称隐语。……重在斗知,而廋语隐语却重在斗趣或暗示,中间略有分别;我们或许可以说谜语是从廋语‘化’出来的,但不能把廋语谜语混看作为一件东西。(《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58-159页)
以上是关于术语“析字”的定名,其与“廋辞”“隐语”“廋语”“谜语”等术语的辨析,是规范的视角。
变异,则与积极术语修辞在一定意义上相对应。积极术语修辞尤能体现异质性存在。例如:
(2)可以说,语言是我们用来进行宣传的工具,或武器。我们倘若用武器来做譬喻,便也可说修辞是放射力、爆炸力的制造,即普通所谓有力性动人性的调整,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同立言的意旨无关的。(《修辞学发凡》,第11页)
上例使用了作为喻体的术语“放射力”“爆炸力”。
(3)学问越是社会实践直接所要求的,越能给人生命,使亲近它的人得到了实际的学力。对于那种学力的浅深和广狭,也就象对于社会实践经验的浅深和广狭一样,将要无可隐藏地反映在写说上。(《修辞学发凡》,第41页)
上例的“生命”也是作为喻体。以上是共时层面的变异。
(4)这类转类用法,一向叫做实字虚用,虚字实用。有时也简称虚实。一向所谓虚实,或实字虚用,虚字实用,多不过是名词和动词的转类。……以上所谓实字虚用,虚字实用,都把名词叫作实字,把动词叫作虚字;所谓实字虚用,虚字实用,都就是名词用作动词,动词用作名词,也都就是名词和动词的转类。实际转类并不限于名词和动词。又转类,也不止是文言中可以用,语体文及口头语上也是可以用的。(《修辞学发凡》,第192-193页)
上例是关于“转类”历时变异的描述。
(5)本格第一类错综,以前称为‘互文’或‘互辞’。如刘知几著《史通》……又如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四《互辞》……第二类的错综,名称和议论更多,其议论大都为卫护错综辞格而发。如沈括(存中)所谓‘相错成文’……陈善所谓‘错综其语’……严有翼所谓‘蹉对’……此外如陈绎曾《文说》所谓‘拗语’之类,内容也是大同小异,无非议论侧重错综,例证偏乎对偶,我们可以不必多引了。第三第四类的错综,在我国书中我还不曾发见谁曾谈到过它们。(《修辞学发凡》,第214-216页)
上例是关于“错综”历时变异的描述。
(6)陈骙在《文则》卷上丙节也里曾说到隐喻。但他所谓隐喻,适当我们下文说的借喻,同此刻说的隐喻不同。(《修辞学发凡》,第78页)
上例是关于“隐喻”与“借喻”历时变异的描述。
(7)俞樾在《古书疑义举例》里,曾经批评过从前注释家对这一组对代的误解。……他的所谓‘以大名代小名’,就是我们所谓用全体代部分;他的所谓‘以小名代大名’,就是我们所谓用部分代全体。(《修辞学发凡》,第86-87页)
上例是关于“大名”和“全体”以及“小名”和“部分”历时变异的描述。
以上是不同修辞主体(术语的创立者)使用术语的历时变异,是一定意义上以规范为旨归的历时变异。这种变异也是必然的。诚如陈望道所言:“我又以为一切科学都不能不是时代的,至少也要受时代所要求所注重,及所鄙弃所忽视的影响。何况修辞学,它的成事成例原本是日在进展的。成事成例的自身既已进展,则归纳成事成例而成的修辞学说,自然也不能不随着进展。”[4]283还需注意的是,《修辞学发凡》关于术语历时变异的描述是对相关学术史的“讲述”,这种讲述似乎可看作是一种元话语修辞。
除了语义,术语修辞的规范与变异的运作还可以直接表现在语形上。除了共时变异、多主体历时变异,术语语形同样也还有同一修辞主体的历时变异。前文已述及,《修辞学发凡》首次出版后,不断修订,有多个版本行世。后出版本修订了一些术语的名称,术语的语形发生了变化,同一作者同名著作这种历时版本的“改笔”也是一种修辞。这里用初版(1932年版)和1976年版(陈望道先生在世时的最后一版)的某些术语做简单对比:首版“铺张”,1976年版为“夸张”;“微婉”后改为“婉转”;“讳饰”后改为“避讳”;“精警”后改为“警策”;“周折”后改为“折绕”;“转品”后改为“转类”;“辞的声调”改为“辞的音调”;“语文的体类”改为“文体或辞体”。
三、适应与和谐:术语修辞的领域生态
一般而言,术语终究是特定学科专业领域的术语,特定情形下术语会跨领域使用和传播。在“本色当行”的领域生成或建构术语时,术语需适应特定的题旨情境(含认知语境等)。跨领域传播术语时,和谐则应是术语修辞的重要领域生态。有意思的是,我们所提出的“术语修辞”这个术语本身即跨术语学和修辞学这两个领域,这个术语自身就是专业方向领域交叉的结果,其交叉是可能的。术语,是用来说明科学规律的;修辞,也可用来说明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术语”和“修辞”的交叉融合是必然的,也是契合的和谐的。这正类似于我们对应提出的“认知与审美”“规范与变异”“适应与和谐”三对概念,每对概念内部的两个概念在术语修辞意义上可以契合。就术语的领域生态而言,在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中,已然形成了适应与和谐的领域生态。这种领域生态在一定意义上是术语跨语域使用传播的结果,是语域交叉融合的体现。
领域交叉和融通,是积极术语修辞(或曰典型术语修辞)的重要领域特质。即不同学科领域的术语在语篇中和谐运用。例如:
(1)最明显的,如佛教输入,文学输入,以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输入时期,都曾有过这样的现象。(《修辞学发凡》,第40页)
上例“佛教”“文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术语跨学科领域和谐共用。
(2)而一度试用有效的,又并不能永久保存作为永久灵验的处方笺,所以也决不能借为獭祭的方便。(《修辞学发凡》,第18页)
上例使用了“处方”这个医学术语,语言学与医学领域有了交叉。
(3)表情的态势虽然似乎多是反射作用,未经反省的,但刺激旁人的功用却颇大。(《修辞学发凡》,第22页)
上例恰当使用了“反射作用”这个药学术语。
(4)至于所谓四法六法等等刻板定数,在东方是有一个公用绰号,叫做‘杓子定规’,而学诚却也替它起了一个绰号,叫做‘井底天文’。(《修辞学发凡》,第243页)
上例使用了“天文”这个天文学术语。
(5)语言中的声音也是一种音。凡是略略翻过物理学的,大约都知道音是由于物体的振动而成。这振动从空气中或从别种物体中传达到我们的耳朵,刺激了我们的听神经,我们就发生了音的感觉。我们知道音有音别、音色等音质。音质是由于许多振动复合所成的色彩。又有强有弱,有高有低。强弱是由于振幅的大小,高低是由于振动的快慢。又有长有短。长短是由于振动延续的久暂。(《修辞学发凡》,第29页)
上例较为密集地使用了“振动”“听神经”“感觉”“音色”“音质”“振幅”等物理学、生理学术语。
(6)故同单表意义的图影,单表意义的数学记号等类标记不同,也同单表声音的音标不同。(《修辞学发凡》,第31页)
上例使用了“数学”“音标”等数学和语言学术语。
(7)意义也有具体抽象的区别。这同心理学或逻辑学上所谓概念观念相当。平常出没在我们知觉、记忆、想象中间的,常是事物的观念。(《修辞学发凡》,第32页)
上例“概念”“知觉”“记忆”“想象”等逻辑学、心理学术语恰当适用于《修辞学发凡》中。
需要说明的是,领域生态的交叉并不是要取消“学术界限”,事实上陈望道是反对学术界限不清的。如陈望道曾指出并评论道:“这样内容杂乱的情况,直到一八九八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出版,才被改进了一点。《马氏文通》是一部严格讲述文法的书,同修辞学本来没有多大关系,但因影响很大,从《马氏文通》出版以后,便有一些学术界限不清的人,从故纸堆里搬出以前那些修辞古说来附和或混充文法,成了一个拿修辞论的材料混充文法的时期。”[4]278“内容杂乱”“附和”“混充”恰恰是“和谐”的反面。
四、简括与平易:术语修辞的风格要素
一定领域生态中的术语,在较大篇幅的语篇(学术专著)或篇幅相对较小的系列语篇里可以形成特定话语风格。术语修辞的风格要素包括但不限于简括和平易,它还可能有诸如新奇、疏放等要素。就《修辞学发凡》而言,其术语修辞的主要风格要素似乎是简括与平易。平易,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和谐。“就象选词,我们现在是以平易做标准。”[4]244如果说术语修辞有一定的标准,则“标准”也是效果。因为通常情况下达到标准了,效果也就生成了。
或者可以说,风格是持久的效果。术语定名一般不宜草率,往往颇费踌躇,从这个意义上说定名似乎又能体现术语修辞风格。譬如关于辞格的定名,也是一种“选词”,《修辞学发凡》坚持定名的简括与平易。“这种分类,或许也有不大自然的地方,但实际,经过十几次的修改。对于名称,也很慎重,大抵都曾经过仔细的考量,又曾经过精密的调查,凡是本国原来有名称可用的都用原来的名称,不另立新名。”[4]71关于辞格的定名之谨慎,陈望道后来还有相关说明:“许多学生不会写文章,问我文章怎么做,许多翻译文章翻得很生硬,于是逼着我研究修辞。我是从调查修辞格入手的,调查每一格最早的形式是什么。格前面的‘说明’不知修改了多少次,就这样搞了十几年。”[9]
再如《修辞学发凡》关于“修辞学”这个核心术语的说解也是简括和平易的。“修辞学原是‘勒托列克’(Rhetoric)的对译语,是从‘五四’以后才从西方东方盛行传入的。”[4]15类似地,“明喻”“借喻”的定名也是基于简括与平易。“日本人所著的修辞书中,历来都是根据这一条,把我们所谓明喻叫做直喻,中国也有人用这个名称,但我以为还不如明喻这一个名称显明。”[4]77这里所说的“这一条”,是指“唐彪以前,曾由宋人陈骙称它为‘直喻’”。[4]76此外,“‘借喻’这名,系沿用元人范德机的定名(见《木天禁语》‘借喻’条)。此外所有的名称,如‘隐语’(见元人陈绎曾所著《文说》论‘造语法’条),如‘譬况’(见明人杨慎所著《丹铅总录》卷十三‘订讹’类‘譬况’条,又卷十八‘诗话’类‘双鲤’条),如‘暗比’(见清人唐彪所著《读书作文谱》卷八《暗比》条)等,或太浮泛,或同别的譬喻名称不很连贯,都觉得不大适用。”[4]80此外,有意思的是,《修辞学发凡》中诸多示意图里的语言文字也主要是术语,这大概也是出于简明的考虑。
需要指出的是,术语修辞可以形成风格,有其风格要素,而风格是相对特殊(与“普遍”相对而言)的,表现的是差异性,但这决不是说术语修辞没有共同性可言,不是说术语修辞学没有办法归纳和演绎术语修辞的共同规律。毕竟,风格的形成和表现受规律支配。再者,“术语修辞学”在一定意义上是“修辞学”这个“属概念”的一个“种概念”。“修辞学的任务就是探求修辞现象的规律,缩小所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境地。过去有一个人说某首词好,我问他好在那里,这个老先生是专讲究读的,他说有几种读法,那里该重读,那里该轻读。再问他,他还是叫你读。他认为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只能以心传心。我们则主张科学,凡是可以意会的一定可以言传。研究修辞,就是要缩小和消灭‘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境域。”[10]修辞学探求规律,术语修辞风格有其规律,探究术语修辞风格,也是不断走近科学。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的术语修辞实践表明,术语修辞的话语符号建构有其认知和审美动因。在此基础上,往往形成种种适应与和谐的领域生态。领域生态的适应与和谐,常常诉诸规范和变异的运作。运作的结果符号化并成熟稳定后形成特定的言语风格,陈望道《修辞学发凡》术语修辞的风格要素主要为简括与平易。陈望道的术语修辞实践契合于其修辞学和术语学思想,并可作为后世术语修辞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