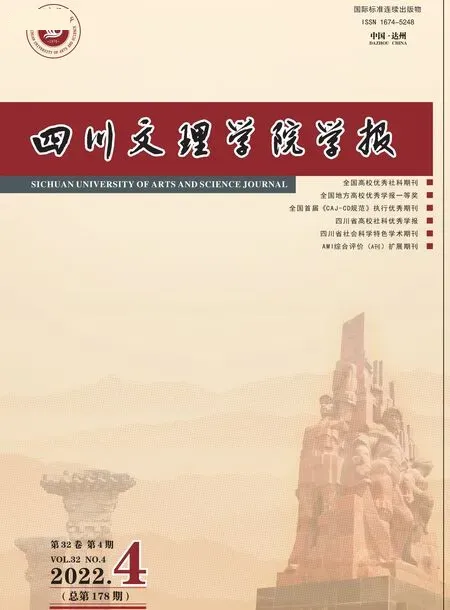发凡以垂法 继往而开来
——学习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的心得体会
高万云
(山东大学 文化传播学院,山东 威海 264209)
1932年4月和8月,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下册由大江书铺刊行,同年9月,《修辞学发凡》合订本由大江书铺出版。与之前唐钺《修辞格》、王易《修辞学》、董鲁安《修辞学讲义》、张弓《中国修辞学》和薛祥绥《修辞学》相比,《修辞学发凡》不仅“是中国有系统的兼顾古话文和今话文的修辞学书的第一部”,[1]289而且是“批判地继承古今中外修辞学遗产,立足于汉语修辞现象实际,建立了一个中国化的科学的修辞学体系。”[2]160《发凡》的问世,标志着中国作为科学的修辞学的建立,也确立了它在中国修辞学史上无可替代的学术地位。因为它对中国修辞学的贡献是全方位的,我们曾在《汉语修辞学方法论研究》中指出《发凡》的三大贡献,一是“在修辞学与相邻学科的交汇处认识修辞学的多边性”,对修辞现象与修辞行为进行哲学、美学、逻辑学、心理学、语言学、文艺学、文章学等学科的互文式观照;二是建立了一个以古今修辞现象为基础、以“修辞所可利用的是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修辞要讲究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三大命题为支柱、以“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分野为主构的修辞学体系;三是科学的研究方法:现象描写与规律阐释互补、逻辑推演与价值认定互证、辩证分析与系统建构互释。[3]152-175可以说,《修辞学发凡》不仅开创了中国修辞学的新纪元,而且引领了这一领域的新征程。九十年来,《发凡》滋养了四代修辞学人,这种滋养,不仅仅是泽被陈望道先生的亲传弟子和再传弟子,而且惠及所有的修辞学人。
我不敢说是陈望道先生的传人,因为我只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跟随胡裕树先生和宗廷虎先生学习修辞学,先是在助教进修班听宗廷虎先生讲授修辞学和修辞学史,后又做二位先生的访问学者,主攻修辞学。在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我系统地学习了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作文法讲义》《美学概论》和《陈望道修辞论集》等著作。虽然我天资愚钝,灵性不足,但还是有不少心得体会。对此,宗廷虎先生评价说:“万云作为一位中年修辞学家,为何能慧眼独具,捧出如此多的创新性成果?其中奥秘何在?据我所知,首先要归功于陈望道修辞学思想的培养和熏陶。”[3]4所谓创新,乃先生谬赞,愧不敢当,但我在继承并延续陈望道修辞学思想方面确实下了不少功夫。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 继承为了创新,继往方可开来
《修辞学发凡》是一座宝库,修辞理论的阐释,修辞现象的描写,科学方法的运用,学术简史的勾勒,学科体系的建构,无不对后世的修辞学研究有着重要影响。然而,正如望老所言:“一切科学都不能不是时代的,……归纳成事成例而成的修辞学说,自然也不能不随着进展。……所以修辞学的述说,即使切实到了极点,美备到了极点,也不过从空前的大例,抽出空前的条理来,作诸多后来居上者的参考。要超越它所述说,并没有什么不可能,只要能够提出新例证,指出新条理,能够开拓新境界。”[1]283可以看出,陈望道先生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为中国的修辞学奠定了基础,而且更为后世学人指明了研究方向:“我们生在现代,固然没有墨守陈例旧说的义务,可是我们实有采取古今所有成就来作我们新事业的始基的权利。”[1]283这就告诉我们,要有所创新,必须打好继承性的基础。正是遵循了以上教导,我首先尝试继承性研究。
第一,系统研究《修辞学发凡》,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开掘。《修辞学发凡》不仅以语言为本位,而且强调修辞的多边性,对此,我在《钱钟书修辞学思想演绎》和《汉语修辞学方法论研究》中都有详细阐述,并且在多篇论文中都有所生发。如在《跨学科与跨世纪——汉语修辞学的个性与出路》中,对陈望道“修辞学介于语言、文学之间,它与许多学科关系密切,它是一门边缘学科”[4]的论述进行进一步明确化,认为“跨学科”是中国修辞学的学科个性,是由交叉学科“移植组合”“交叉融合”和“多元综合”中的第三条形成途径建构而成的,即“多学科的基本要素相互渗透、交叉综合而产生的学科。”[5]指出“修辞学必须研究修辞的逻辑基础问题”“修辞学必须研究修辞的社会制约问题”“修辞学必须研究修辞的心理机制问题”“修辞学必须研究修辞的审美追求问题”,“另外,修辞学研究还必须从文艺学、文章学、交际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中吸取理论营养。”[5]以上说的是修辞学与相邻学科的交叉关系,就修辞而言,也与其他学科互相交织,我们在《钱钟书修辞学思想演绎》中描述钱钟书的文学修辞,也总结出五个方面,即文学修辞具有审美韵味、语法程度、逻辑理据、心理机制和游戏趣味。[6]69-80也正是继承了这一思想,我在《文学语言的多维视野》中探讨了文学修辞的语言本质和多边属性,胡裕树和宗廷虎二位先生给予很高评价:“该书最鲜明的特点是高屋建瓴,视野宏阔,多角度透视,多方位观照。它打通了文学和语言学的界限,借鉴中国传统的文学、美学、哲学、修辞学理论和西方人文科学尤其是20世纪的文艺学、文化学、符号学、心理学、逻辑学、语言哲学等理论,既从宏观上变换视角,对文学语言的逻辑理据、民族特质、心理机制、审美追求、修辞意识、个性特征、游戏旨趣、变异规律等进行科学分析,又从微观上深入文本,对诗歌语言、小说语言、散文语言等进行细读审视,最后通过科学整合和哲学升华,建立起一个以规范问题、艺术问题为研究起点,以交叉扫描、逻辑推演为基本方法,以揭示规律、指导实践为主要目的的新的学科体系。这一体系的建立,拓展了文学语言研究的认知空间,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多项空白。”[7]胡、宗二位先生多有溢美之辞,其实这不过是对陈望道修辞学思想的继承与延展而已。
第二,继承《发凡》辩证动态地考察修辞学发展历史的传统,响应望老攻克“汉语修辞学史”这一薄弱环节的号召,对以宗廷虎、陈光磊、李熙宗、李金苓等复旦修辞学家为主体的修辞学史研究略有突破。一是撰写了20世纪最后20余年的修辞学史《20世纪中国修辞学》(下卷),宗廷虎先生认为:“迄今为止,将改革开放后二十余年的当代修辞学研究写成史著,此书还是第一部。”[3]3而且专门开辟了“相邻学科的修辞学研究”专章,对语言学家黎锦熙、王力、吕叔湘、胡裕树等,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汪曾祺、王蒙、鲁枢元、高行健等,以及其他各科专家费孝通、启功、陈宗明、龚文庠等的修辞论述进行了系统梳理,这是以前的修辞学史中很少见的,为中国修辞学的理论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和启示。二是撰写了“我国第一本系统探索钱钟书先生对我国修辞学重要贡献的专著”[3]3《钱钟书修辞学思想演绎》,对非修辞名家钱钟书散落且隐匿在《管锥编》《谈艺录》和《宋诗选注》等著作中的关于修辞和修辞学的“精辟见解”连缀起来,演绎成一个显在的体系。对钱钟书的语言观和修辞观、文学修辞论、理解修辞论、辞格论、文体论、语言风格论、修辞批评、修辞史研究和修辞研究方法等都做了较为细密的研究,这也可说是对中国修辞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三是撰写了专门研究我国修辞学研究重镇复旦大学的修辞学研究史《复旦百年修辞学史论》,从“中国修辞学从这里起步”“中国修辞学在这里诞生”“中国修辞学在这里坚守”“中国修辞学在这里繁荣”“中国修辞学从这里延伸”五个方面,系统描述了复旦大学对中国修辞学的重要贡献。特别剖析了复旦大学“各届领导重视修辞学”“各种形式宏扬修辞学”“各门学科介入修辞学”“各代后学传承修辞学”的深层逻辑动因。[8]对马相伯、严复、李登辉、夏敬观、陈望道、苏步青、谢希德等各届校领导,张世禄、胡裕树、严修、范晓、申小龙、戴耀晶等语言学家,严复、刘大白、周谷城、吴文祺、赵景深、王运熙等非修辞学家,陈望道、郭绍虞、倪海曙、陈光磊、李熙宗、宗廷虎、李金苓、邓明以、吴礼权、祝克懿、霍四通等修辞学家等都做了详细描写,可以说这也是中国修辞学史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二、修辞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探索
前面提及,《修辞学发凡》整体上运用的是辩证的研究方法,如二元对待、动态考察等,但在对具体修辞现象、特别是修辞格进行考察的时候,基本上采用的是归纳的方法,所谓“从空前的大例,抽出空前的条理来”。我在继承归纳法的同时,也尝试运用演绎法研究修辞现象,如发表在《修辞学习》2000年5、6合刊的《辞格的演绎研究》,就是根据“辞格的本质是对语言单位进行变形使用”[9]这个大前提进行逻辑推演,语言单位分为四个层次:语形、语义、语法和语理,变形使用分为五个方面:复叠、增损、颠倒、转移和比并,然后根据语言层面和变形方式结合的可能性,得出20种基本修辞方式。最后建立模型,得出结论:“运用演绎模式,我们不仅可以找出辞格的理据,而且还可以‘生产’出大量的新格以及新的细类,同时还可以探索修辞学研究的新的文体。”[9]再如,古代“炼字”讲究“诗眼”“句眼”等,并认为五言诗多以第三字为句眼,七言诗多以第五字为句眼。钱钟书不以为然,认为只要“得力”与“得所”统一,句眼可在诗的其他位置,他举了以“借”为句眼的四句诗,证明句眼可以在一、二、四、五字上:
征文北山外,借月南楼中。(孟郊《夜集汝州郡斋听陆僧辩弹琴》)
故来不是求他事,暂借南亭一望山。(白居易《过郑处士》)
池月幸闲无用处,主人能借客游无。(白居易《集贤池答侍中问》)
坐中更得江南客,开尽南窗借月看。
(黄庭坚《次韵向和卿与邹天锡夜语南极亭》之二)
钱钟书没有找到“借”在三、六、七字位置上做句眼的例子,我们则根据演绎法规则推演出“借”可出现在任一位置:
俗夫不堪赏夜景,池月借与美人看。
静心亭边羞借月,闹春树下怯听蝉。
赏月常与镜湖借,只缘玉人在湖边。[6]113-114
这虽然是自己“造”出来的句子,但它符合诗歌规则和演绎推理规则。我们在《并重双关》《简说复加修辞格——以〈西游记〉为例》《简说辞格“因声附义”》《浅谈汉语的变性增义》等论文中都有推演出的例子,我们认为这是演绎法的自觉运用,其结论是可靠的。
另外,我们还尝试运用了其他研究方法,如在《修辞学研究与运筹学方法》中用了“运筹学方法”,在《混沌理论对汉语修辞学的启示》中用到了“概率推理”,在《汉语修辞学方法论研究》中用到了实验方法等等。都对修辞学研究方法做了尝试性探索。
在运用新方法研究修辞现象的同时,我还自觉探讨修辞学方法论问题。1986年郑子瑜在《修辞学习》发起“语法修辞结合论”大讨论,1992年《语文建设》发起“文学语言规范问题”大讨论,我觉得两场讨论存在一个很大的方法论问题,就是没有在同一概念上讨论问题。前者我发表了《语法修辞不能结合》(《修辞学习》1987年第4期)系统批评郭绍虞先生的“语法修辞结合论”,认为作者把语法修辞结合与语法研究与修辞研究结合混为一谈了。后者我发表了《我对文学语言规范的理解》(《语文建设》1993年第11期) 于根元在《中国现代应用语言学史纲》中指出“不少文章对规范涵义的认识就不清楚。对此高文分析得相当清楚。”[10]于先生所指是拙文中这样一段话:“我们发现,人们之所以争论不休,主要是因为把语言的逻辑功能和艺术功能割裂开来了。主张规范的往往把逻辑功能作为衡量文学语言的唯一标准,拿非文学语体中的语言现象套文学语言;主张‘反规范’的也把语言的诗歌功能从语言中分离出来,从而得出文学语言反规范或者有时反规范的结论。正是由于这种前提的片面和缺漏,才导致结论的以偏概全。”[11]这里说的是学术研究起码的逻辑方法。此后,我一直在思考汉语修辞学的方法论问题,至今已在《当代修辞学》《学术月刊》《天津社会科学》《山东大学学报》《福建师范大学学报》《首都师范大学学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报刊发表此类文章30余篇,于2012年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语修辞学方法论研究》(项目批准号:12BYY102),并出版同名学术著作。宗廷虎先生认为:这“既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汉语修辞学方法论的专著,是我国修辞学理论研究史上的一次重要突破,也是第一个有关汉语修辞学方法论的国家社科项目。”[3]1“该书最主要的贡献是为中国修辞学界提供了第一部既具理论性也具实用性的修辞学方法论研究专著。它在融合古今中外名家理论基础上,提出的修辞行为理论、修辞主体间性理论、修辞与思维关系的理论、修辞方法的目的性层次性契合性理论等,都对中国修辞学的理论建设有重要意义,而这些理论对指导修辞学研究和教学也有重要的应用价值。该书为扭转我国修辞学理论研究多年以来一贯存在的薄弱状态,贡献了重要力量!”[3]3可以说,这也是我对望老《修辞学发凡》有关方法和方法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三、科学的修辞批评
我国的修辞批评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修辞批评的论述出现,如春秋三传。《左传》之“《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已见修辞批评之雏形,而《公羊》《谷梁》对《春秋》“微词”“内词”“讳词”之探讨,几乎可说是细读式批评,到了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再到后来的诗话词话小说评点等,那就是典型的修辞批评了。不过,中国的修辞批评模式多是修辞效果感悟式,修辞技巧鉴赏式,既不成体系,也无固定标准。所谓“着一‘闹’字境界全出”,而为什么“闹”出了境界则再无下文。发展到现在,基本定型为三种类型,即点评式、鉴赏式和比较式,《修辞学发凡》中对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的分析多涉及这三个类型。而到了1935年陈望道发表《语言学和修辞学对于文学批评的关系》,则已经有了科学的修辞批评的认知,他认为:“语言学和修辞学的知识差不多就是文学批评的原理,而文学批评差不多就是语言学和修辞学的特殊应用。”[12]正是学习和借鉴了望老的研究成果,我对修辞批评做了如下三个方面的探索:
第一, 关于修辞批评理论。我曾在论文《中国文学的修辞批评》(《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4.5)、《文学修辞批评之中西比较》(《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5.1)、《郭保林散文的修辞批评》(《聊城大学学报》2009.2)和论著《钱钟书修辞学思想演绎》(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20世纪中国修辞学》(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都对修辞批评有所界定,指出“当今文学的修辞批评,不再仅仅是诗话词话中炼字炼句法门的评点, 也不再是不同作家、不同作品、不同版本之间的修辞优劣评判,而是接纳了西方从修辞意图、修辞策略、修辞方式到修辞读解和修辞评价整个修辞过程的新的批评范式。这无疑对文学的修辞性言说和修辞性阐释提供了科学的视角。”[13]在修辞批评的理论方面,我们提出了科学的修辞批评的基本内涵:一是修辞批评必须建立在科学的修辞观的基础之上;二是修辞批评对象“必须对文学的修辞运作做全程跟踪”[13]“作家的修辞运作:修辞目的与修辞策略”;“作品的修辞评价:修辞环境和修辞技巧”;“作品的修辞解读:修辞接受与修辞意义”。[14]三是修辞批评行为,主要是理清各种修辞关系,如修辞主体间性、文体间性、文本间性等。《文学语言的可变性规律初探》(《文学评论》1990.5)、《文学语言的可变性规律再探》(《当代文坛》1992.5)则是对各种修辞关系的尝试性分析。这自然扩大了传统修辞批评的空间,也增加了修辞批评的科学性。
第二,我们也尝试用新的修辞批评理论对作家作品进行批评,主要包括选择具有特定修辞观的修辞理论、选择特定的作家和作品、选择特定的分析方法或工具、分析文体或文本。这方面我们在文学理论刊物和修辞学刊物都发表了文章,如《中国文学的修辞意识》(《东方丛刊》2003.1)、《也谈小说语言之“超常”》(《文学评论》1989.2)《汉语诗歌的语法学研究》(《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93.2)、《当代小说的修辞学论析》(《小说评论》90.1)、《郭保林散文的修辞批评》(《聊城大学学报》2009.2)《美文的弹性——郭保林散文的整体评价》(《聊城大学学报》2004.5)前四篇以陈望道修辞学理论为评价标准,对文学和文学中的小说、诗歌进行修辞分析,后两篇则是对散文家郭保林的散文从修辞意识、修辞策略和修辞技法三方面进行全面评析,这种修辞批评模式,比简单的感悟式评价、纯技法鉴赏要深入和科学一些。
第三,当然我们也有一些纯粹的鉴赏式、细读式批评,如《鲁迅作品中省略号的修辞作用》《老舍小说的用词艺术》《朱自清散文的叠词美》《论王蒙小说的辩证施句》等,都是按照传统的修辞批评方式展开的,这算是纯粹的继承式研究。
以上是我研读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的心得体会和继承性研究成果,偶尔也有一些自认为有所突破的创新性研究。不揣浅陋,以就教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