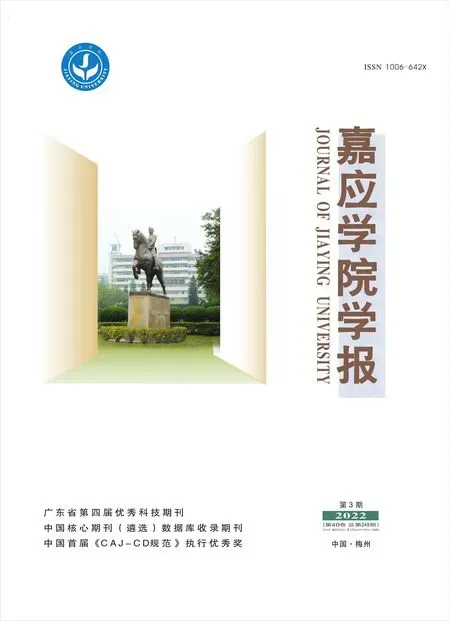动形养生的文化要义与当代价值
李 雪,李文鸿,王 敬
(1.山东体育学院 研究生教育学院,济南 250102;2.嘉应学院 体育学院,广东 梅州 514015)
动形养生在社会变迁中传承,为社会带来秩序和意义,成为“世代相传的行为方式和对社会行为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1].不同于西方将身体视为客观之物的身心二分的观点,动形养生“通过导引行气等锻炼方式来畅达经络、疏通气血和调理脏腑”[2],是在阴阳、天地、身心、形神等对立统一中对生命的独特理解与实践.例如,从西方舶来的“运动健身”理念将静止的久坐视为不良习惯之时,动形养生主张“动静之练”,在看似不健康生活方式处谋取健康的伟大抱负,既有“动练其形、静练其神”的精细化也有“调姿、调息、调心”的立体化的伟大创造.当前,对动形养生的探讨主要集中于中医学和体育学两个学科,范式主要包括重思辨的历史文化研究和重实验的科学实证研究两类.实验研究主要目的在于证明功法的习练效果,本质上是在西方医学指导下对东方文化科学性的验证,一方面对变量难以控制,另一方面几乎无法触及习练效果的心理层面,传统养生身心一元的整体性被人为割裂.历史文化研究梳理动形养生的历史源流,概括其文化特征,但本质的、深层的阐释不足,尤其是在跨越“传统-当代”的文化穿透性和中西健康文化比较方面缺乏深入探讨.因此,重新认识动形养生之“道”,发现其不同于西方运动健身的独特魅力,既是文化自觉的需要,也是丰富世界健康文化的需要.
1 动形养生的文化要义
“一种文明的生存之道就是一种文明的生长方式和维持存在的方法论”,[3]从万物一气到阴阳调谐,中国哲学的宇宙论以“生成论”从本源上决定了动形养生区别于西方健身话语“构成论”的哲学基础.“考其阴阳者,察其动静也.”(卢辩注:《大戴礼记·文王官人》)中国哲学是在身体力行的过程中追求理想境界实践的“功夫”[4],在与身体、心灵、天地万物和谐对话中,动静结合的养生形态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实践体现.
1.1 阴阳调谐的文化理念
“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庄子·知北游》)此“气化天道系统”被诠释为“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素问·宝命全形论》),“气散则分之,生化息矣”(《六微旨大论》).气既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又是人体的生命动力,体现着人类生命的时间性特征.如果宇宙万象都能返回到“万物一气”的混沌统一中,那么以超验之义理解人类生命形式的终极起源,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活动具体的、实际的状态.气的动力学为我们构建了一个生命存在的具有连贯性和偶然性的时空纹理,以及生命不可化约的多样性和必然的物质形式.由此,人在天地“德流气薄”(《灵枢·本神》)中产生的生命,都能在不同的时间和角度看到纷繁的意义.从传统的宇宙生成论出发,可以更加深刻理解“生”
之奥义.“生,进也.象草木生出土上.”(《说文解字》)故甲骨文“生”字形作“”,刘巘《易义》中说:“自无出有曰生.”生命从无到有,开启万物之始,故《周易·系辞传》赞叹道:“天地之大德曰生.”在“养生”一词中,“生”主要指生命,与生长、生活、生态紧密联系.《周易》说“生生之谓易”,“生生”彰显出让一切存在都能够继续存在,让一切生命都繁衍生息的自然之本意,“共在”成为万物得以存在的最重要条件,隐含着中国古典生命智慧的现代色彩.“天地和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荀子·礼记》),《易传》曰:“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二炁交感,化生万物”(周敦颐:《太极图说》),万物的化生源于阴阳之间的相互作用.在人与天地万物的汇通中,着眼于生命的养生以“万物一气”确立了抽象之“道”和阴阳和谐的辩证之义,进而,动形养生以动静相宜、身心共养为方法和目的搭建起沟通养生文化理念与身体实践的桥梁.
1.2 动静相宜的身体实践
中国文化的实践理性精神是养生穿越阶级、时空传承至今的文化动力.李泽厚指出,儒家仁学思想以血缘、心理、人道、人格构建了一个以实践(用)理性为特征的思想模式的有机整体,并为其它诸家(孟、荀、庄、韩)所保存和承续,构成了一种具有实践性格而不待外求的民族性的文化—心理结构.[5]这一文化—心理结构的实践理性精神决定了与养生紧密相关的中国哲学范畴(阴阳、五行、气、道、神、理、心),大都是功能性而非实体性的概念,重视的是事物的性质、功能、作用和关系,强调人世现实,偏重与实用结合.所以,动形养生镶嵌于中国文化的总体背景中,其阴阳之道、动静之法穿越历史时空,至今仍为国人所实践和遵循.
动形养生是一个动静辩证统一的身体实践系统.首先,静是对精气神的持守,指向心理之“和”.“夫精神气志者,静而日充者以壮,躁而日耗者以老.”(刘安:《淮南子·原道训》)所以,“欲延生者,心神宜恬静而无躁扰.”(《医述·医学溯源》)尽管儒释道对养生之义各有所重,但均强调对精神的保养,所谓“害道无如徇爱嗔,养生犹要啬精神.”(陆游:《次韵李季章参政哭其夫人》)静之追求在动形养生实践中表现为“导气”,目的在于“导气令和”,即旨在谋求心理的平和.王逸讲“栖神藏情,治心术也”(《楚辞章句·卷五》),“导气”的根本目的即在于生命内在的精神层面的治理.其次,动是对形体气血畅通的追求,指向身体之“柔”.“得神者昌,失神者亡”,但“善养生者,无不先养此形,以为神明之宅.”“心常凝不动,形要小劳之”(陆游:《秋怀》),动形以“小劳”为原则.所谓“小劳”,即华佗所谓“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陈寿:《三国志·魏书·华佗传》)动形养生实践的身体之动表现为“引体”,目的在于“引体令柔”,因为“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陈寿:《三国志·魏书·华佗传》)此时,形体之动则关照“通则不痛”的生理医学意义,成为对心神之静的有益补充.最后,动形养生是动与静的辩证统一.传统动形养生功法(如五禽戏等)虽有动功、静功之分,但内外皆有动静,实为 “静中求动”“动中求静”的功夫.正如清代养生家曹廷栋所说,养生“心不可无所用,非必如槁木,为死灰,方为养生之道.静时固戒动,动而不妄动,亦静也.”(《老老恒言·卷二·燕居》)动形养生中的“气”与“体”、“导”与“引”、“和”与“柔”分别对应健康身体的一体两面、营卫之法和理想状态,其实践要求体现于调身、调心、调息的创造之中,即“调整身形,使之端正”“调伏妄念,正心诚意”“调整呼吸,使之深匀”.此“三调”最终落实于“血脉流通”的根本目的,从而达致“百病不生”之效.总之,动形养生关照动静两种炼养方式,且动静均不使极,正如司马迁所言:“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动形养生将中和之道贯穿始终,以达致形神共养的目的.
2 动形养生的当代价值
动形养生讲求“中和之道”,形成了对西方以“动”为主的健康观的补充,以对国家政治话语的响应承续“身国同一”的文化传统,以个人身体的自我管理隐喻着“阴阳和谐”的社会秩序.
2.1 “中和之道”的健康理念讲求
18 世纪以后,西方基于基础医学的发展,将身体锻炼与健康紧密关联.[6]西学东渐,“中国数千年来哲学的医学,一变而为科学的医学”,[7]追求身心和谐的动形养生传统逐渐让位于西方科学话语主导的身体运动,中国以固有传统构建养生方法论或者养生知识生产的能力和动力被弱化,换言之,以动为主的西式健身之法使动静结合的中国养生黯然失色.
作为以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和动静和谐的辩证观为指导的摄生实践,动形养生文化早已成为人们须臾不可离身的生活方式.所谓“孤阴不生,孤阳不长”,从阴阳调谐的中国健康文化理念看,仅以“身体运动”保养生命失之一隅,由此凸显了动形养生动静结合、辩证中和的特殊意义.其一,中国古代的养生之道以“阴阳调谐”为精神底蕴,既是对“天行健”之刚毅坚卓的默契,也是对“地势坤”之厚实和顺的持守.以此观之,“刚柔并济”的生命态度从根本上决定了国人的身体运动并不刻意追求超乎自然常态的体能 .“静则生慧,动则成昏”,动形养生更重视通过对极端化身体运动的克制体验身心和谐的愉悦.其二,养生对“静”的强调因关注内心体验而更具普适性.在动不使极的身体运动之外,动形养生以“静”维度的开发强调对“精气神”的保养从而指向心理的平和,老少强弱皆可身体力行.如新编健身气功功法在进入肢体动作前均有静心凝神之环节,导引养生功更是有功前调息凝神的准备过程,并配合默念口诀“夜阑人静万虑抛,意守丹田封七窍.呼吸徐缓搭鹊桥,身轻如燕飘云霄.”如此,以导引为主要形态的传统动形养生更重视身心的渗透、互补(阴阳)和自行调节,以保持整个机体、结构的动态平衡,反倒有可能更接近西方自古希腊以来追求至善人生和人的健全发展的“体育之真义”.其三,动形养生对阴阳、动静等平衡关系的把控,使其在根本上规避了遭受“异化”的可能.动形养生重视心神虚静的“内视”而非来自他者眼光的评判,“所以比较不容易从‘为己’的健体活动异化为‘为人’的商业行为,以至于引得大多数人放弃了积极参与运动的锻炼时间,去观赏甚至逼迫少数人在竞争中把身体拼坏.”[8]
2.2 “身国同一”的文化传统承续
“一人之身,一国之象也.”(葛洪:《抱朴子内篇·地真》)健康问题本质上是社会问题,应该通过改进社会关系、构建和谐社会的方式来促进健康.[9]《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明确要求“加强非医疗健康干预,塑造自主自律的健康行为”,国民健康长寿成为新时代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动形养生的动静相宜之道充分表现于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和谐关系之中.
在追求“全面小康”的新时代,古人所谓的“全身”凸显着对“健康中国”行动的特殊意义.首先,养生之道因关乎万物而成为创造美好生活、追寻生命意义的行动,将生活、健康、常识交织为一个有机统一体,为“健康中国”行动构建了实践的框架和基础.其次,“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健康中国”行动在个人、家庭、社会和政府联动中展开,养生以身体锻炼之“动”和心态调适之“静”的有机结合调和生活之甘苦,使人们在个人身心平和中获得家庭和谐.养生所建立的以丰富生命形态、提升生命质量为鹄的的健康空间和和谐人际关系厚植着 健康中国的社会根基,直接呼应了政府对国民身心健康的期待.最后,在国家医疗资源相对短缺(看病难)的现状下,积极主动的养生是应对医疗市场化带来的“望医却步”问题的自我身体管理之法,也是对国家推动的“全民健身,全民保健”政策的主动贡献.正如人们所常说:“养生可以少得病,减轻子女负担,对家庭、社会都有好处.”当代大众养生的“身国同一”意象,从美国人类学家冯珠娣(Judith Farquhar)对北京人养生活动参与观察的描述中清晰可见.[10]换句话说,如果说动形养生“身国同一”之传统在古代是传统文化“大小宇宙和谐共鸣”之认识向现实世界的个人与国家关系延伸,那么,当代普通社会大众养生的这种“身国同一”则转变为个人对国家共建健康中国的责任意识和认同感.
2.3 “阴阳和谐”的社会秩序隐喻
人们将讲求阴阳和谐的身体养护延展至家国社会,在进/退、顺/逆等关系的平衡中展现着对和谐秩序的追求.阴阳和谐是动形养生的根本法则,身体的动静相宜之养是阴阳和谐的具体展现.改革开放以来,在所有人目视一物“向钱看”的浮躁中,“清静为天下正”的传统思想重新唤起大众的共鸣,人们以传统养生“心神宜恬静而无躁扰”的坚持使身心归于平和,以“吾心养吾浩然之气”的宠辱不惊塑造了个人生命的方法、体系、理念,维持着身心的和谐与平衡.从古代传统和社会分层角度看,养生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文人雅士以养生之举展示避世隐逸的生活状态,以个体的“反社会化”实现对社会的另类融入,意在心理调适;而下层民众则以实用为原则,将养生作为物质和医药短缺时代的替代,意在谋求生存.[11]在当下繁荣和谐社会中,养生尽管仍有古代遗风,但人们更多的是以“静”之智慧勾画出与“躁”之世界两不相干的健康生活轮廓,以身心健康的幸福和愉悦呈现出新时代的健康形象.动形养生的动静之“术”融于阴阳之“理”,以文化传统之力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将大小宇宙和谐共鸣的“天人合一”理想延伸至人际合和与社会秩序的安定.作为一门生活的艺术,养生之阴阳、动静思想以生存技艺、经验法则与日常惯习的形式流传于市井,以朴素的强调中庸之道的常识观念使大众身体与丰富的传统遗产连接起来.具有健康指导意义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之说既是中医的经典理论,也在代代相传中成为坊间人尽皆知的养生法则.在此指导下,“导引行气”的动形养生行动既是“治未病”的健康管理,同时隐喻着积极向上、有条不紊的生活秩序.总之,动形养生具有显著的自制伦理特征,这种“‘自我技术’视‘快感的肉体养生法及其节制是整个自我艺术的一部分’”[12],在当代大众朴素的“莫生气”“找乐”的心理调适(“静”)以及规律的身体锻炼(“动”)之中获得了自我管理的意义,维系了和谐的社会关系.
3 结语
近代以来,中国固有的养生之道逐渐被西方话语所遮蔽,但健康作为一种观念,理应在对本土性的强调中呈现文化的多样性.动形养生不仅是近代以来被西方健康话语统摄的“动以养形”之法,也是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静以修身”的精神调适;不仅是吸收外来西方医学理念的卫生之法,也是源于历史深处的摄生之术;不仅是谋求个人健康幸福的身体实践,也是助力“健康中国”的社会力量和文化媒介.由此,动形养生在“身国同一”中彰显出约翰·费斯克所强调的“文化的政治意义”[13].万物一气的身体想象与动静不使极的摄生实践,以及由此派生的健康理念和“导气令和,引体令柔”的养生方法(太极、健身气功等)具有强大的时空穿透力,至今仍是中国健康文化难以被攻破的堡垒和中国人因循的身心护养之“道”.因此,在“生命在于运动”的动健康理念之外,应重新发现动形养生动静相宜的本土智慧,服务于人类保持身体长久身心健康的美好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