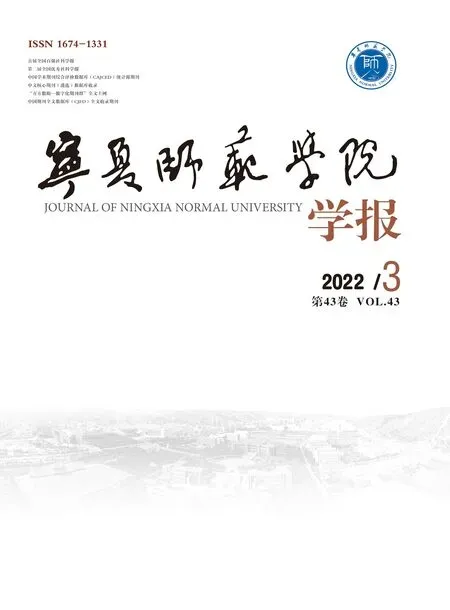《史记》人物传记中的戏剧化色彩管窥
孙宏亮,王甜甜
(延安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戏剧起源于古希腊的民间歌舞,它从诞生伊始,便与舞台密不可分,世界戏剧艺术最早出现在距今约两千四百多年以前爱琴海边的古希腊。从古希腊时期戏剧理论的出现,到莎士比亚戏剧理论的成熟,戏剧经过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在这个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西方的戏剧理论也更加完备。西方戏剧的主要元素是演员、故事、舞台和观众,是以对话、歌唱、动作等表现出来的艺术,它按不同的内容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其中戏剧人物和戏剧冲突,是戏剧中最不可缺少的两个重要因素。虽然戏剧以舞台表演的形式为主,依托舞台为载体传达给观众,但是戏剧在构成因素中其实与文学作品密不可分,二者都需要以人物和故事情节为核心,戏剧的表演需要用戏剧冲突来取得戏剧效果,增强舞台的感染力。文学作品的写作,同样需要戏剧因素来增强表现力。
虽然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初衷是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为他的写作目标,但《史记》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一部重要的史学著作,并不只是总结历史、编撰史实。由于司马迁本人是具有文学家浪漫的气质和感情强烈的特质,因此,《史记》中具有强烈的抒情发意的色彩,它的核心部分是本纪、世家、列传。为了让这些人物传记更加丰富,生动的贴近这些人物自身的意识、再现当时的场景,司马迁运用了大量的写作手法。由此,本文以《史记》为例,研读《史记》创作中对戏剧化手法的运用,来探讨《史记》中的戏剧化色彩,对增强《史记》人物传记中的人物形象和情节结构的表现力和艺术旨趣产生的积极意义。
一、冲突戏剧化的情节结构
根据《辞海》的定义:“叙事文学作品或戏剧演出中情节发展的基本单位,是人物同人物在一定时间和环境中相互发生关系而构成的生活的画面。”[1]情节关系实质上就是矛盾冲突,戏剧主要是通过建构矛盾冲突来展开故事的情节结构的,矛盾冲突是戏剧的灵魂所在,没有矛盾冲突就没有戏剧。而《史记》的人物传记中,同样需要矛盾冲突来深化文本。因为人物传记并不是平铺直白的叙事文本,而是需要人物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因此矛盾冲突不断加剧的过程,才是整个故事最精彩的部分,只有冲突集中化的故事情节,才能达到故事的精彩性和人物形象的完整性,才能实现戏剧的场景重塑,引领观众去感受当时的人物气氛和人物性格。司马迁在《史记》中以主要人物的主要事件为主,情节高度集中,直陈其人其事,无过多琐事和人物介绍的赘述,在叙述描写时高度集中于一人一事或一人几事,以其最具代表人物性格的事件为主,突出人物的特点,这种集中密集、直切主题的人物表现手法使得《史记》中的每个人物都色彩鲜明,在《史记·项羽本纪》“鸿门宴”中:
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2]
在这个片段中,首先对鸿门宴的人物位次进行了交代:“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真切的展示了宴会的场景和座次的主客尊卑,古代的室内座次尊卑有别,十分严格,位高者尊于上位,即主位,位低者卑于下位,即次位。同位者尚右边,以右为尊,室内尊卑顺序分别为:“东为主、南次之、北又次之、西为末”,而项羽把刘邦安排于北位,位次甚至都低于刘邦的谋士,说明项羽醉翁之意不在酒,根本没有把刘邦放在眼里,意在羞辱刘邦。司马迁交代这句,也意在说明项羽和刘邦的此时实力相差悬殊。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也有类似的位次情节的介绍:“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3]这种情节结构的设置让读者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
接着直入“鸿门宴”的冲突,范增多次用“数目”“举玉玦”等行动以提醒项羽,在屡次得不到回应时,范增让项庄舞剑助兴借机诛杀刘邦。项庄随即“入为寿——寿毕——请以剑舞——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以身翼蔽沛公”,这一连串的人物动作,在叙述中娓娓道来,把人物与人物之间隐藏着的微妙、隐秘、猜忌、敌对等种种复杂因素表现出来,两方对峙,每一方的一举一动的最终走向都如同“谜”一般尚待揭晓,读者无法预测到最后的事件发展线索和发展脉络。这种场景重塑、矛盾突出的情节建构的方式,如同戏剧放映式一般,把最真实、直观的场面摆在读者眼前,时刻犹如吸铁上的磁石,紧抓读者的视野。这种直观的感受,正如日本近代学者斋藤正谦所说过的一句话:“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事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4]
为了增加故事情节的生动性、趣味性和集中爆发性,司马迁在描写人物传记中,往往运用时空裁剪法,高度浓缩时空,常常截取几段重要的事件,加以渲染,使故事情节的矛盾高度集中,一触即发,比如在《史记·刺客列传》中荆轲刺秦王片段:
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绝袖。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恐急,剑坚,故不可立拔。
荆轲逐秦王,秦王还柱而走。群臣惊愕。[5]
这样矛盾冲突剧烈的场面依靠秦王和荆轲两人的尖锐对立的人物动作和情节表现出来,当面临荆轲行刺,秦王展示出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所折射出来的生与死的争斗,群臣临危时的惊恐呆滞,兵卒徒手与荆轲搏斗的张惶失措,矛盾在这一刻爆发到高潮,在你追我赶的交锋中,人物间敌对的立场交织成错综复杂的戏剧矛盾冲突。在这一既定的时间、空间和事件中,整个事件的冲突、人物与人物的冲突,全都放在朝堂中进行,情节、矛盾可谓是波澜起伏、高度集中。
这样的手法贯穿在《史记》中大部的人物传记里。司马迁高超的建构故事情节矛盾的才能,用场景重塑的方式构建冲突戏剧化的情节结构,不仅赋予整个事件以波澜,更使整个故事张弛有度,绝无平直浅显之感。
二、戏剧性的故事色彩
《电影艺术词典》曾将戏剧性定义为:“在剧作中,由人物自身的矛盾,人与人的性格或意志之间、人与自然环境或社会环境之间发生的抵触或矛盾冲突所造成的悬念或激变。”[6]但是随着社会的更替,戏剧性具有了更加广阔的内涵,一些高潮起伏、离奇荒诞、出人意料的情节也称作戏剧性。清代袁枚曾在《随园诗话》中说过“文似看山不喜平”,[7]就是指读者在阅读时有产生戏剧性的心理期待,因此作文应该奇势迭出,司马迁所作的《史记》就具有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戏剧性故事色彩。
(一)戏剧性的神话渲染
在《史记·高祖本纪》中,刘邦的出生就带着浓厚的戏剧化色彩,开篇把汉高祖刘邦的出生归纳为其母亲做梦的产物,极具荒诞性。在《史记·高祖本纪》的开篇描写道:
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常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8]
高祖出生之前,他的母亲曾在大泽的岸边休息,梦到与神交合,他的父亲太公正好去看,看到有蛟龙缠在她的身上,不久,他的母亲就有了身孕,生下了高祖。刘邦的出生极具戏剧化色彩,从开篇的出场就被赋予了一种帝王的神性,这看似荒诞、极其不可信的神性故事,或许是一开始汉王朝对刘邦天赋神权的舆论宣传,又或是为了让底层群众对刘邦称帝的臣服,抑或是对刘邦白手起家初登帝位的这种不可思议、反常规现象的解释。无论是出于何目的,司马迁并没有对这种民间传说弃而不用,反而引用这一戏剧性的离奇神话,从《高祖本纪》一开始就对刘邦称帝进行神秘的故事渲染,加强了文本的神秘色彩和奇异内涵,为后面构建汉高祖刘邦这一生非凡的经历和人物形象进行铺排,激起了读者对汉高祖刘邦的这一传奇经历的心理预设和期待,紧抓读者的阅读心理。
在《史记·项羽本纪》这段中,范增对项羽说:“沛公居山东时,贪於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9]范增劝说项羽的对话中,为了增加规劝的效果,用奇异的现象增加语言的说服力,明显也带有戏剧性的色彩。
(二)戏剧性的故事变化
戏剧因素能够增强文学性,故事变化能够增强戏剧性,戏剧化的文学作品,会对提升和充实双方的艺术品质有很强的功用性。戏剧虽然具有强烈的时空限制,与文学作品的表现形式也完全不同,但戏剧与文学作品在人物、冲突、对白、情景结构中有很大程度的共通之处,他们的受众都是观众或者读者,因此作家在创作时会不自觉地运用到戏剧创作原理,使文学作品也自然的具有戏剧化的色彩。司马迁在塑造刘邦这一人物形象时,开头即大力渲染刘邦的神性色彩,说刘邦的出生是神的产物,长着一副龙的容貌,喝醉了身上常有龙出现,他每次去哪家买酒那家店买酒的人就会增加,司马迁描述的这几种怪现象,给读者营造出一种刘邦异于常人的神人之感,但又在其中穿插着故事性的变化:“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把刘邦拉下神坛,以酒醉者的形象化为浑身带有市井无赖习气的常人,使刘邦的形象游走在神性与人性之间,人物形象也变得更加丰满立体、有血有肉。他以这种神性和人性共有的特质,使刘邦游离在神、人之间,这种来回切换的书写方式对刘邦从底层的市井无赖到成长为创下功业的一代帝王的传奇生命历程作出了富有戏剧性、阐释性的文本描绘。
三、人物语言的戏剧性
在戏剧作品中,人物的语言可以分为三大类型,即对白、独白与旁白。对白就是指人物与人物的对话,对白是戏剧中重要的叙事方式,很多基本的人物信息都是靠人物之间的对白来进行传达的,高尔基曾在《文学论文选》中说道:“剧中人物的形象是由演员的台词给观众的印象形成的,也就是依靠单纯的口头语言,而不是依赖故事的叙述性语言。”[10]由此可见,对白是人物形象的构建和人物性格刻画的重要方式。司马迁在《史记》中大量运用人物对白,独白和旁白,从人物的语言交流中创造出言语的交锋,以此凸显人物的个性特点,从而推动故事中的叙事进程的发展,加强故事的张力。
(一)人物语言的性格化
《史记》中有大量的语言运用,这些语言具有很强的个性化特征,从这些人物的语言中可以清晰的了解到人物的性格特点,在语言的对话中透视人物的心理活动,起到刻画人物的作用。司马迁笔下塑造的人物都性格鲜明,类型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每一个人物形象都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在《史记·项羽本纪》中描写到:
沛公军霸上,未得与项羽相见。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於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项羽大怒,曰:“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11]
人物的语言昭示人物的性格,人物的性格奠定人物的最终结局。在这简短的对话中,明显可以窥探出项羽和范增的人物性格特征,刘邦的左思马曹无伤派人对项羽说刘邦打算在关中称王,要任命子婴为国相,所有的珍宝全部都要据为己有。项羽一听此事,立马大怒道,明天要犒劳士兵,给我去打刘邦的军队。言语虽短,但显然能看出项羽的刚愎自用、缺少谋略和暴躁易怒的性格,在听到来人短暂的上报后,不经查实和缜密的布战计划就宣布要攻打沛军,这致命的性格缺陷也为他最后的失败奠定伏笔。而范增劝说项王之言,则展现出范增的远见卓识和衷心耿耿,是一个有勇有谋的谋士。二人的性格特征和社会地位都通过对话语言交代清楚。
司马迁运用人物的说话方式和心理语言展示其性格,在《史记》中大量运用这样的笔法,其中《陈涉世家》中记载道:
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勿相忘。”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12]
从这一对话中,明显可以看出陈涉的性格,他自命不凡,野心勃勃,他看不起佣者浅陋的眼见,觉得自己虽然身处底层,但志向远大,仍非池中之物。
司马迁在塑造人物性格的时候,是从人物的出场就开始的,让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用这些极具人物性格的对话来推动事件的发展,从而塑造出一个完整的人物故事。老舍也曾在文章《戏剧语言》中说道:“对话乃是一个人的性格发出的声音,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对话,作者必须对塑造的人物形象进行认真勾勒思考,这个人应该说什么样的话,相同的话这个人应该怎么样说。”[13]司马迁这种建构人物性格的手法,让整个人物的形象立了起来,和老舍所说的戏剧的创作手法有异曲同工之处。
(二)人物语言的类型化
戏剧在人物语言的构造中具有三种表现手法,分别是对白、独白和旁白,这三种表现手法在《史记》中都被大量的运用,人物语言的对白推动事件进程的发展;独白则倾向于对人物此刻的心理状态与心理活动进行披露和补充;旁白,简言之就是画外音,是对人物或者是整个故事作一个解释性的说明或评论,提升文本的叙事功能。这三大类型相互结合,可以使文本的表达内容更加丰富,让故事的艺术形象达到最佳的呈现。
在《史记·李斯列传》中,秦始皇在巡游途中病逝之后赵高和李斯密谋篡改诏书时有这样一段对话:
高乃谓丞相斯曰:“上崩……善者因祸为福,君何处焉?”斯乃仰天而叹,垂泪太息曰:“嗟乎!独遭乱世,既不能死,安托命哉!”[14]
司马迁在构建人物对白的时候,并不是全篇进行人物语言的对白描写,而是选取最能代表人物关系和人物命运转折的交界点来着重刻画,在语言对白中对语言的塑造详略得当,重点突出。《李斯列传》里赵高和李斯的这段对话,寥寥几句,就交代清楚人物的目的和关系,赵高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威逼和利诱共存,使得李斯不得不就范,这也为李斯后来不得善终的结局埋下伏笔。这样类似于戏剧手法的人物语言刻画,让整个文本活了起来,使我们读其言则知其人。
独白、旁白则是对文本的又一种有力的补充,任何人物都是具有内心活动的,人物内心的活动也往往是最隐蔽和不为人知的,而文学语言可以通过人物的独白来展示人物最隐秘的内心世界,把人物的内心世界毫无隐蔽地表现在读者的眼前,能够让读者从灵魂层面去把握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感情。同样在《李斯列传》中,赵高忌惮李斯位高权重,诬陷李斯想要裂地为王,李斯被捕入狱后有这样一段独白:
仰天而叹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为计哉!昔者桀杀关龙逄,纣杀王子比干,吴王夫差杀伍子胥。此三臣者,岂不忠哉!然而不免于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无道过于桀、纣、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岂不乱哉!”[15]
李斯的这段独白美化了他的忠臣形象,却掩盖了秦王去世时伙同赵高篡改遗诏、背叛国家的人生污点。他把秦二世的暴虐无道堪比夏桀、商纣、夫差,认为关龙逄被夏桀所杀,比干被商纣所杀,伍子胥被吴王夫差所杀,他们都是尽忠而死,虽然他的智慧赶不上这三个人,可是他也是尽忠而死的。事实上,李斯的死主要还是归咎于他执着富贵,贪恋权位,嫉妒贤臣,不愿放手权力,最后中了赵高的奸计。他的独白,让读者更能直达人物的心灵深处,准确把握李斯的人物形象定位,阴谋的制造者最终被阴谋所累。
旁白,作为人物语言中的一部分,能让文本主题更加突出,叙事更为完整,表达更为细腻。司马迁在撰写人物传记的时候,在每篇之后都有一段名为“太史公曰”的评论性文字,他以一种上帝的视角,不仅是对传记的主要人物和事件作出见解性的看法,更是对文本内涵的一种深层解读,能够让读者更为清楚地提炼文本的意蕴,具有画龙点睛的妙用。
运用人物语言类型化使人物形象个性更具典型性,对白、独白和旁白三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作用于人物语言的表达。事实上,这三种人物语言类型的本质都是“对话”,对白是人物与人物的对话、独白是人物与世界或者自我的对话,旁白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对话,这些“对话”使每个人物传记中的人物不仅仅是司马迁笔下被描写的客体,而是一个个完整的、区别于他人的、独立存在的人物个体,这些鲜活的人物个体让整个文本更具生命力。
(三)人物语言的潜在化
司马迁往往在《史记》人物传记的对白中设置人物语言的潜台词——在这里我们姑且把它解释为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人物语言作为文本的需要,有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文本信息,但人物语言的对话并不总是直接传达文本信息的,内含着一定的潜在性的意味,而文本中语言对白的潜台词运用,能加强观众对文本内涵的思考,真正意义上理解事件发展的节奏和把握文章的真实情感。《史记·项羽本纪》鸿门宴这一片段中:
沛公大惊,曰:“为之奈何?”张良曰:“谁为大王为此计者?”曰:“鲰生说我曰:‘距关,毋内诸侯,秦地可尽王也。’故听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为之奈何?”[16]
在张良把项伯之言告诉刘邦,说项羽准备攻打沛军,让他早日离开刘邦,投靠项军。刘邦大惊,说:“为之奈何?”在这里并没有表明刘邦的发问是针对刘邦攻打沛军一事的“为之奈何?”还是意指担心张良被劝服改投项羽门下的“为之奈何?”问话中包含着两层言外之意,引起读者的疑问,促使读者继续带着问题阅读下去。张良在面对刘邦的疑问,也并没有正面回答直视刘邦的问题,而是提出“是谁替大王提出这个计谋呢?”先不急于回答刘邦之问,借此问题来寻找自己作为谋臣在刘邦面前的存在感,以此巩固自己的谋士地位。在中国古代,为了达到一方领导者势力的最大化,阵营中往往招贤纳士,有较多谋士猛将的足迹。因此,谋士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张良的反问,一是间接的告诉刘邦之前谋士提出的让他提早进入关中的策略是错误的,暗含刘邦当时没有寻求他的意见便鲁莽入关;二是潜在表明只有自己才可以为刘邦建言献策,解决眼前的困境。刘邦随后又回答他:“小人告诉我说把守住函谷关,不要让诸侯的军队进来,我就可以占据整个秦国的地盘了。”刘邦的这句回答一语双关,既向张良表明了入关是误信谗言,又用“鲰生”一语略过之前张良询问进言入关的谋士之名,这句话不仅带有刘邦潜在的内心活动,还表明了刘邦的人物性格和人物背景,出身底层,言语粗鄙,城府极深。不似项羽那般直来直往,在鸿门宴中为了增加双方的信任,毫不避讳告密者的姓名。在刘邦和张良的这段简短的对话中,双方都步步为营,言语间带有强烈的潜在动机,以此来探寻对方的真实意图,言语间的交锋和心理对抗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史记·张仪列传》中,张仪在楚国游说中被误认为偷了碧玉,遭到了毒打,再回去时和妻子进行了这样一段对话:“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17]张仪遭受毒打受到妻子的嘲讽,反而问妻子的是看我的舌头还在吗?这句话表面是问舌头是否尚在,实际上是告诉他的妻子,舌头尚在,本事就还在,就能继续游说诸侯,就能一雪前耻,谋得官位。这句张仪受辱之后自嘲的话,实际上表明了他落魄不落志,坚信自己有朝一日能成就大业。从张仪与其妻的对话中充分展示出了人物语言的魅力所在,我们从人物语言的潜在意味可以窥探出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由此可见,司马迁对人物语言的塑造功底可见一斑,这样的对话在《史记》中不可胜道,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张大可先生曾称《史记》为:“一部熔史学、文学、哲学于一炉的旷世大典。”[18]总的来说,《史记》不仅兼具史学、哲学与文学三方面的含义,还兼有戏剧化的色彩,虽然在汉代时期并没有戏剧这一概念,但在文学的创作中却内陈着戏剧中的高度集中的情节结构、性格化的人物对白、潜在化的人物语言和荒诞的故事色彩,这种多种含义兼备的创作手法,使得《史记》既有了史学可信性、可参考性的特点和哲学的可思辨性特点,又有了文学可读性和可鉴赏性的特点,还不失戏剧的趣味性和扣人心弦、丝丝入扣、层层递进的紧张感,在这样的基础前提之下,《史记》在前人的叙事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把中国传统文学中塑造人物形象和建构情节结构的艺术手法,提高到了一个相当完备的高度,直到现在,仍旧是我们研究史实与文本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