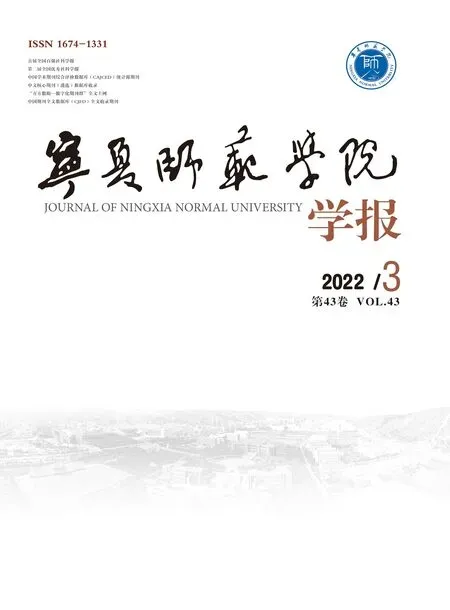杜甫陇右诗的盛唐西北边郡印象①
陈江英,蒲向明
(1.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甘肃 成县 742500;2.西北民族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部,甘肃 兰州 730030)
杜甫陇右诗,指的是杜甫去华客秦、寄寓同谷、度陇入蜀过程中所作的一百一十多首诗作。杜甫的陇右诗作,可以说是杜甫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因此冯至先生说:“在杜甫的一生,759年是他最艰苦的一年,可是他这一年的创作,尤其是‘三吏’‘三别’以及陇右的一部分诗,却达到了最高的成就。”[1]这些诗歌,在登临怀古、忧国忧民、感时伤乱、抒发忧愤、山光水色等描写之外,还包含着民族交融、多元文化共同繁荣的内容,由此毗连一体,构成了其陇右诗的盛唐西北边郡民族文化交融印象。
唐代秦州是丝绸之路重镇,它由西北经兰州连接河西走廊,南经陇南徽县、文县通巴蜀天险,自古就是胡汉交融、多民族杂居、聚居之地。唐王朝在文化上提倡兼容开放的政策,安史之乱后,作为边塞要地的秦州,鼓角阵阵,胡笳声声,胡舞蹁跹,民风民俗相互融汇,使这里成为胡汉文化交融的大舞台。正如杜甫陇右诗所抒写:“马骄朱汉落,胡舞白题斜。”(《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三)“羌女轻烽燧,胡儿制骆驼。”(《寓目》)在诗境里也是胡汉杂居共处,民风民俗相互融通。透过杜甫笔下的边陲风光,更多的是民族文化交融的见证和盛唐西北边郡印象。目前学界对杜甫陇右诗的研究,多在其陇右诗的纪行特质和诗史属性方面,但对其描摹盛唐西北边郡民族文化交融的印象多有疏漏。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此展开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边郡风光
陇右边郡地理位置独特,扼陕甘川要道,既是战略要地和商贸中心,同时还是少数民族文化交汇之地。《唐六典》卷3载:“(陇右)辖境‘东接秦州,西逾流沙,南连蜀及吐蕃,北界朔漠’”。[2]《元和郡县图志》说得更为具体:“陇右道辖境秦州、武州、兰州、河州……”[3]特殊的地理位置无疑给多民族杂居共处创造了条件。而奇险的山川、广袤的风光亦成为诗人心中歌咏的对象。杜甫辞官离开华州,西行流寓陇右,创作了大量诗篇。这些奇妙精巧的诗篇,在描写边塞风光、忧时伤乱、寄寓象征的同时,更多反映出多元文化交融的西北边郡风光。诗人“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秦州杂诗》其一),离开华州,历经坎坷抵达陇山(陇坂),扑面而来的便是“迟回度陇怯,浩荡及关愁”陇山的险峻(《秦州杂诗》其一)。紧接着感受到的是“莽莽万重山,孤城山谷间。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的辽阔苍莽(《秦州杂诗》其七),还有层峦叠嶂间孤城难眠的漫漫长夜。而这一切的“奇险”“孤寂”绝非只是边塞之地应有的景色,更多的缘由来自于“西征问烽火,心折此淹留”的西北边郡感受(《秦州杂诗》其一)。目及“降虏兼千帐,居人有万家”的多民族环境(《秦州杂诗》其三),诗人这种陇右地域风光的抒写,由胡汉杂居的独特地理位置铺展出独有的写作背景。
多元文化的交融,使得陇右山川具有更为宽广、包容的情怀,杜甫陇右诗也因此具有了辽阔的意境和广袤的胸襟。“鼓角缘边郡,川原欲夜时”,鼓角阵阵,日暮黄昏,诗人“咏鼓角以见世乱之极”(《杜诗五言补注》卷一),秦州城中甚至于天地之间,戎马鼓角随处可见可闻。来自西域的行旅商贾,在乱世边陲的秦州驿站自由出入。弥漫在悲伤雄壮鼓角声中的边郡之地,时刻受到吐蕃的威胁,《秦州杂诗》之七在雄奇阔大的境界中寓含着时代的悲凉。“烟尘一长望,衰飒正摧颜”既呈现出悲壮的艺术美,也表现出诗人对整个西北边境胡汉杂居共处的担忧。正是笔触所至,广袤辽阔的边郡风光得以生动再现。烟火纷飞中,“羌童看渭月,使节向河源”“萧萧古塞冷,漠漠秋云低。不意书生耳,临衰听鼓鞞”。尽管战乱不断,烽烟四起,而少年不知愁滋味的牧童,依然在月下轻快地吹着羌笛。“羌女轻烽燧”,少年曼妙、能歌善舞的羌女们避开烽烟,还在丝竹声里欢快地轻歌慢舞。“胡儿掣骆驼”,牵着骆驼的西域人,依然平静随意自由地出入在陇右之地上。我们仿佛看到一个个驼队缓缓行走在街头巷尾、田间地头,似乎听到胡人狂歌笑闹和随风远去的声声驼铃。
同时,杜甫陇右诗用更多笔墨,于苍莽雄奇的自然风光中深刻抒写西北边郡民族文化气息之交融。“安史之乱”后“羌童看渭月,使节向河源”“马骄朱汗落,胡舞白题斜”的多民族交融共存的景观随处可见。安史叛乱平定,外患却在加剧。“乱起后,吐蕃趁国内用兵,边庭空虚……广德元年入大震关,尽占陇右之地,后又不断蚕食西北边州,对唐朝构成极大的威胁……朝廷值‘多事之后,姑欲安人’,既无心思也无实力解决藩镇割据问题,只能任其盘结自固。”[4]
诗人目之所及胡人熙熙攘攘,身影遍地;亲耳所闻胡人杂语、鼓角边声,此情此景,诗人难免忧国伤己。因而杜甫笔下的边陲重镇秦州、同谷平添了几分悲凉色彩。“下马古战场,四顾但茫然。风悲浮云去,黄叶坠我前。朽骨穴蝼蚁,又为蔓草缠”(《遣兴三首》之一)。“万里流沙道,西征过北门。但添新战骨,不返旧征魂”(《东楼》)。残酷的现实和对陇上前途的担忧无不充溢在字里行间。安史乱起,西北党项、吐蕃等少数民族乘机入侵,不时掠夺边地,乘机夺取陇右、河西之地。《旧唐书.吐蕃传》载:“乾元之后,吐蕃乘我间隙,日蹙边城,或为掠劫伤杀,或转死沟壑。数年之后,凤翔之西,邠州之北,尽蕃戎之境,淹没者数十州。”[5]安史乱后,吐蕃攻占兰(甘肃皋兰)、河(甘肃临夏)、廓、鄯、临(甘肃临洮)、岷(甘肃岷县)、秦(甘肃天水)、成(甘肃成县)、渭(甘肃陇西)等陇右之地,……至此陇西、河西等陇右大片土地沦为吐蕃的天下。
张籍的《横吹曲辞·陇头》诗形象地描绘了当时凉州(今甘肃武威市)城的惨状:“陇头已断人不行,胡骑夜入凉州城。汉家处处格斗死,一朝尽没陇西地。驱我边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黍。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谁能更使李轻车,收取凉州入汉家?”[6]占据良田、畜禽,甚至和当地居民通婚,陇右重镇的秦州成了多民族聚居杂居之处。而疲于应对的唐王朝无力对抗只能默许,众多的胡人、氐羌族在陇右重镇秦州等地安身。杜牧诗《河湟》讥刺唐朝流治者的昏庸无能:“元载相公曾借著,宪宗皇帝亦留神。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遗弓剑不西巡。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杂诗第六首句又写到另一种边声“城上胡笳奏,山边汉节归”,圆润、哀怨的悠悠胡笳,既言用兵之事和对戍卒之苦的慨叹,又烘托出边地军民融合和边陲风光的凄凉。“天宝乱后,回鹘留长安者常千人,九姓商胡冒回鹘名杂居者又倍之……”[7]此时的秦州,无论语言、风俗、音乐都已经胡汉杂糅、交相映辉。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战争烽火气息的边城中,于平常景物中敏感到其中蕴含着不平常气息的同时,也感受出羌、氐、胡、汉、吐蕃少数民族融合的文化气息。“属国归何晚?楼兰斩未还”,诗人虽是对出使吐蕃的使臣迟迟未归、吐蕃侵扰的威胁未能解除的忧患,也从侧面刻画出多民族杂居共处的边郡风光。
民族杂居共处的现状,无不昭示着西北边郡辽阔而烟火纷飞的事实。极目远望,辽阔无垠的大地满身疮痍。原本奇险广袤的自然风光也因战乱而呈现出深深的忧伤。然而,在诗人着眼陇右之地的忧国忧民情感深处,可以看到唐代社会的对外交流、民族融合并未因战争的缘故而停止。正如尹海江所说:“战争是残酷的,但它也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和文明的交流。”[8]战乱带来灾难的同时,也促进了民族文化的融合与繁荣。因此,杜甫陇右诗作再现的不仅仅是边郡苍莽浩渺、奇险突兀的山川风光,更多展现了安史乱后陇右地区多民族杂居共处、融合发展的雄奇景色。正是在艰辛的跋涉和苍莽奇崛的西北边郡风光中,促成杜诗边郡风光诗境的生成。杜甫陇右诗自辛苦得之,主要源自生活的艰辛和道路的艰难,这种外在的因素直接作用到了诗歌创作的风格变化和诗境生成。[9]杜诗陇右雄奇景色带给杜甫的感受,聂大受先生有很好的阐释“独特的地理环境所造就的民族浑融和文化多元的情境与不时出现的边烽警急情势,让第一次走进陇右的杜甫感到新奇和惊异,同时也新增了一层忧虑。这样的社会氛围无疑影响了杜甫的思想,也影响了他的创作,他把在中原地区难以见到的文化景观一一写进了诗篇之中。[10]
二、民俗风情
杜甫陇右诗中异彩纷呈的民族风情,如服饰、歌舞、乐器、饮食等,与人物一起烘托出多元文化的共同发展和繁荣。
杜甫入秦之前的作品,几乎鲜见少数民族称谓出现。但在其陇右诗作中,有关少数民族及其服饰、民族歌舞、民族乐器等民族风物,却屡见不鲜。“华夷相混杂,宇宙一腥膻”(《秦州见敕目》),“西戎外甥国,何得迕天威”。西戎华夷,多民族共存,华夏文明和少数民族文化交相辉映,异彩纷呈。《秦州杂诗》其三对此最具代表性,既有对少数民族殊异习俗的写照,又有对民族服饰的生动描绘:“州图领同谷,驿道出流沙。降虏兼千帐,居人有万家。马骄朱汗落,胡舞白题斜。年少临洮子,西来亦自夸。”虽然李唐王朝平息了“安史之乱”,但地处陇右要地的秦州、同谷二郡,由于中原战火正炽,西北边境依然烽烟迭起,旧时归降唐朝的“降虏”,即氐羌等少数民族,在秦州城中居住的人口越来越多。放眼望去,秦州城外搭满胡人的帐篷。“马骄朱汗落,胡舞白题斜”,这里的“白题”有二层意思:一是指古代匈奴部族名。由于他们的风俗以白色涂额,故名。裴骃集解引服虔曰:“胡名也。”二是指古代少数民族的一种毡帽。用白毡制成,三角形、高顶,顶虚空,有边,卷檐。汉魏时期经由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传入内地,隋唐时广为流传,为行役之人所常戴。杜甫这里的“白题”,应该指的是第二种说法,即西北少数民族常戴的一种毡帽。北宋张邦基认为“白题乃胡人谓毡笠也。胡人多为旋舞,子美所谓‘胡舞白题斜’,笠之斜似乎谓此也”。胡人即西北少数民族的通称。海滨说:“西域服饰文化景观。胡服以毡裘为主……西域服饰多华丽繁富,尤其见于乐舞表演,反映这种情况的诗歌为数不少,但服饰主要是乐舞文化的附属。”[11]胡人善歌舞,舞到情深时,舞姿癫狂,所戴白题随着情绪的高涨也歪歪斜斜。正所谓能歌善舞是少数民族的特色,华丽的民族服饰是舞者最好的陪衬和装点。一时间边塞秦州,马骄、胡舞、白题胡族竟成盛况。杜甫眼中看到的不光是战争,还有其背后多民族杂居的民俗风情。聂大受先生说:“弃官后的杜甫,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对社会的深刻认识,对人生的重新思考,使他的精神追求与以前有了不同。”[12]
描述呈现于笔端,杜甫陇右诗中展现民俗风情的盛况随处可见。“闻道花门破,和亲事却非”(《即事》),这里的“花门”是回纥的别称。乾元元年(758),唐肃宗为了换取回纥的援兵,不惜把幼女宁国公主嫁给回纥可汗。不想回纥援军被安史叛军打败。对于这种由来已久的和亲安国的妥协政策,杜甫大胆予以直接的否定和披露。《杜臆》评价“和亲作俑于汉,而历代遵为御戎之策。公却非之,盖验诸己事也,结语正发其意”。陇右不仅胡汉共存,也聚集了众多的回纥族民。处于中原文明边缘地带的秦州、同谷(成州),自古是多民族聚居杂居之处。这里既是西北民族争疆夺土之所,又是民族文化荟萃之地。陇右独特的地域物事与文化,极大激发了杜甫的创作灵感。西出流沙的驿道、兵戈不息的凤林、接通西域的栈道、淳朴多彩的民风习俗,一一倾注在杜甫笔端。刘克庄《后村诗话》赞曰:“山川城郭之异,土地风气所宜,开卷一览,尽在是矣。”[13]
杜甫在秦州府,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感受着陇右与长安风光的迥异。少数民族向来擅歌舞、喜乐器。“羌妇语还笑,胡儿行且歌”(《日暮》)“城上胡笳奏,山边汉节归”(《秦州杂诗》其六),“胡笳楼上发,一雁入高空”(《雨晴》),“汉虏互胜负,封疆不常全”(《遣兴三首》其一),“修德使其来,羁縻固不绝”(《留花门》),“马骄朱汗落,胡舞白题斜”(《秦州杂诗》其三),“东征健儿尽,羌笛暮吹哀”(《秦州杂诗》其八),“羌童看渭月,使节向河源” (《秦州杂诗》其十),“朔风吹胡雁……高楼夜吹笛” (《遣兴五首》其一),“羌女轻烽燧,胡儿制骆驼”(《寓目》)等诗句造就的陇右诗边地艺境,使羌妇、胡笳、羌笛、胡歌,鼓角、天马、戍卒、使臣、羌歌、胡舞等意象,犹如一幅琳琅满目的民俗风情画卷,展现给读者乱后陇右边地特有的军民真实生活写照。安史乱后,吐蕃虎视眈眈,觊觎河西、陇右的大片土地。直至广德元年(763)七月,吐蕃入侵,尽取河西、秦、渭、洮等9州,陇右大片地区沦陷吐蕃手中。《新唐书》载:“虏六万骑侵灵州,败民稼,进寇泾、邠,浑瑊与战不利,副将死,略数千户。”[14]占据陇右边郡的吐蕃族歌舞升平,肆意妄为。胡儿马上且行且歌的轻狂、羌妇言谈间的浪笑、城上胡笳的绵延,胡舞的蹁跹、羌笛的悠长,羌女烽火间轻盈的舞姿、胡儿驼峰上的吟唱……都在杜甫陇右诗的笔端展开,而烽燧、骆驼,吐蕃、胡儿、羌妇、胡女往来穿梭于陇右大地,又是一番怎样的景象。《隋书·地理志》描述秦州多民族交融的盛况说“人物混淆,华戎杂错”。元稹《法曲》诗则不乏胡汉多民族共处的精彩描绘:“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15]几乎陇右大部分地域都成为胡汉共处之所。
事实上,胡汉共处现象由来已久,原因不外乎两点,其一陇右地区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其二陇右地区是中原与西域商贸往来的重要枢纽。“唐代丝路贸易的活跃及唐朝对西域的有效治理,对增进汉族人民和西域各族人民间的友谊和相互了解起了积极的作用,有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融合,以致在唐代出现了“汉人胡化”和“胡人汉化”的历史现象。”[16]汉人胡化、胡人汉化现象在陇右之地非常典型。向达先生对汉人胡化做了进一步解释:“此种胡化大率为西域风之好尚: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竞事纷泊,其极社会各方面,隐约皆有所化,好之者盖不仅帝王及一二贵戚达官已也。”[17]民族的融合促进了文化的交融和发展,文化的交融促进了民俗风情的繁荣。汉族从西域各族人民那里学到了许多宝贵的东西,并使之融合发展,共同构成我国灿烂文化的一部分。“安史之乱”后,中原与西域各民族文化的交融进一步加强,胡汉文化融为一体,成为杜甫陇右诗未了的篇章。就是胡人在集市的叫嚣贩卖,或许在街头的旋歌起舞,延续着“华夷一家”民俗风情盛况的独特展现。
三、特有物产
杜甫陇右诗作当中有不少西域物产的描述,具有别致独特的民族特点。其中不乏西域的葡萄、核桃、胡萝卜、胡椒、胡豆,还有胡人的皮毛、奔驰的骏马、高大的骆驼,回纥鲜美的牛羊,精美的饰品,熙熙攘攘的各色族民,以及五颜六色的民族服饰,数不清的胡马牛羊,说不清的各色语言……五味杂陈,交织一起。当然,最典型的当属《寓目》诗:初秋时节的秦州,“羌女”“烽燧”“胡儿”“骆驼”都定格在漫山遍野郁郁葱葱的苜蓿和硕果累累的葡萄里。这一景色,在初到秦州的诗人眼中别具一番韵致。于是诗人挥笔直抒胸臆:“一县蒲萄熟,秋山苜蓿多。关云常带雨,塞水不成河。羌女轻烽燧,胡儿制骆驼。自伤迟暮眼,丧乱饱经过。”这里既写了不同的物产,也写了地域的物象之异,更重要的是,这种观察是放在边郡离乱的动荡和对民生多艰的感慨——这一独特视域下展开。所以仇兆鳌深叹:“寓目,动边愁也……渐说到边塞可忧处。故有丧乱经过之慨,谓不堪再逢乱离也。《永徽图经》:蒲萄生陇西、五原、敦煌山谷,今处处有之,其实有紫白二种。《西京杂记》:乐游苑多苜蓿,一名怀风。关塞无阻,羌胡杂居,乃世变之深可虑者,公故感而叹之。未几,秦陇果为吐蕃所陷。”[18]仇兆鳌固然喟叹于杜甫对西域别致物产的描述,尤其重视由此引起的诗人对乱离世事的感受,但更深一层是慨叹诗人对陇右之地关塞无阻、羌胡杂居的深切忧患。此后不久,陇右果然被吐蕃侵占,杜甫忧国忧民之虑,不幸言中。
诗作所表达的陇右边地物产及历史文化意义,远非上述所能完全涵盖。《寓目》前六句,乃诗人“目之所寓,而末伤丧乱之未已也。”“羌女喜乱,胡儿贾勇,皆乱象也,故触目而伤心”(《杜臆》)。后两句慨叹战乱带给人们的灾难。“关塞无阻,羌胡杂居,乃世变之深可虑者,公故感而叹之”(《唐宋诗醇》)。“一县蒲萄熟,秋山苜蓿多”主要写的是物产之异,“关云常带雨,塞水不成河”写地域之殊,“羌女轻烽燧,胡儿制骆驼”写人性之悍,反映出胡汉杂居、和谐相处的情景。莫砺锋说:“满眼是成熟的葡萄,山野里长满了苜蓿。羌族姑娘对烽火台上传来的平安火毫不在意,胡族少年牵着骆驼来来往往。”[19]据史载,葡萄、苜蓿的产地本在西域,汉张骞出使返回才引入到了秦陇、中原地区。《史记》卷123《大宛列传》载:“宛左右以蒲桃为酒,富人藏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之高官别馆。”[20]此说“汉使”即指张骞。“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者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21]原产于西域的葡萄、苜蓿因汉使(张骞)引种至秦陇、中原。可见,葡萄、苜蓿在秦州的生根发芽,以致杜甫陇右诗描摹这些物产在盛唐的广泛种植,实即成为多民族交融传统、贸易往来的直接见证和资料留存。
同时,杜甫陇右诗中出现的特有物产还有胡人、骏马、骆驼、百草等西北民族独特物事。“北门天骄子,饱肉气勇决”(《留花门》)中的“骄子”,这里的“骄子”借指胡人。《汉书·匈奴传》:“胡者,天之骄子也。”言胡人的粗犷和强悍。“地用莫如马,无良复谁记”中的骏马(《遣兴二首》其二),“牵牛去几许,宛马至今来”中大宛国的名马“宛马”(《秦州杂诗》其八),“南使宜天马,由来万匹强”中的“天马”(《秦州杂诗》其五),据《汉书·张骞传》“神马当从西北来”载,应该是西域骏马的称谓。马是古代最为重要的交通工具,秦州是丝路的必经之地,这些大多来自西域少数民族的马随着民族贸易的往来也逐渐出现在秦州土地上。据史料载,安史之乱后以秦州为主线的陇右道茶马贸易极为盛行,西域马匹经丝绸之路到秦州,而产自陕南、川西的茶叶经陇右道抵达秦州完成交易,其中不乏众多胡人携家经商贩运的盛况。
杜甫陇右诗写西域特有物产与多民族传统的互映,深层的意义不离忧国忧民的基调。“胡儿制骆驼”中的胡儿驾乘威武的“骆驼”,而“朔风飘胡雁,惨淡带砂砾”(《 遣兴五首 》之一),劲风中不能自主的大雁、昏暗中的飞沙走石,使惨淡的景物更加蒙上一层萧瑟、凄惨的色彩。“日落风亦起,城头乌尾讹”(《日暮》),城头乌鸦尾巴上下掀摆、蠢蠢欲动,暗示出战争的一触即发。“云气接昆仑,涔涔塞雨繁,羌童看渭月,使节向河源。烟火军中幕,牛羊岭上村。所居秋草静,正闭小蓬门”(《秦州杂诗》其十)。仇兆鳌谓“咏秦州雨景也”。[22]《杜甫陇右诗注析》却认为“诗中隐藏着不安的种子,透露出诗人心中无边无际的忧愁。羌童和使客同一画面,军营和山村互相混杂。正因为有了这一切,就可以使人体会到,蓬门内的诗人绝不是悠悠然在听雨、打秋草。而是为国家的前途牵肠挂肚”。[23]也正是在诗人这种牵肠挂肚的忧愁中,使人感受到烟火、山村、羌童、使客的混杂相处和各民族之间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而忧国忧民的含义挥之不去。
透过诗人眼中深深的忧国伤怀不难看出,“安史之乱”后,西北边郡秦州多民族的杂居共处和民族文化传统的交融与繁荣。“边郡秦州文化构成多元,一方面多民族杂居带来了多民族的文化结构,另一方面也使得这座边城时时遭到吐蕃的骚扰。”[24]正如李济阻先生所论:“诗人杜甫所见,却只有‘葡萄’‘苜蓿’‘骆驼’,这些‘舶来品’,再有就是骁勇的‘胡儿’、得意的‘羌妇’、匆忙的‘使者’、不眠的‘将军’;这些人和物交织成一片浓密的战争阴云,重压在秦州上空。”[25]杜甫的陇右诗反映出边郡秦州“安史之乱”的战争阴云,也见证了唐代陇右一线,多元文化的并存:回汉、胡汉、戎狄平民之间的杂居共处和文化交融。有论者称:“将元稹之诗歌和向达之论述互相补充印证,我们可以概括唐代西域民俗文化盛行的总体情形:从宫廷王室、达官贵族到民间市井,西域民俗都受到欢迎和追捧;从唐朝的饮食、宫室等物质民俗,到节庆、娱乐等行为民俗,以至于审美性比较强烈的服饰妆扮民俗等,都有西域民俗流行的天地。”[26]这些西域民俗和文化在中原地区的盛行情形,几乎都能在杜甫的这些陇右诗作中找到影子。正如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砺锋先生诗曰:“少陵诗里识秦州,苜蓿葡萄塞上秋。三月寓居留胜迹,千年诗笔壮山丘。前临蜀道重重险,却顾中原处处愁。遥想诸公凭吊处,滔滔清渭自东流。”[27]
杜甫的陇右诗,有对时局的思考,有对战争的关注,有对边陲风光的描绘,或登临怀古,或借古喻今。不仅写出了特有的异域风情,而且真实再现了特定时期西北边郡的民族关系。杜甫的陇右诗可以说是民族融合、多元文化交融的见证。
——以清代与民国“秦州志”编纂为例
——评《产品包装设计( 第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