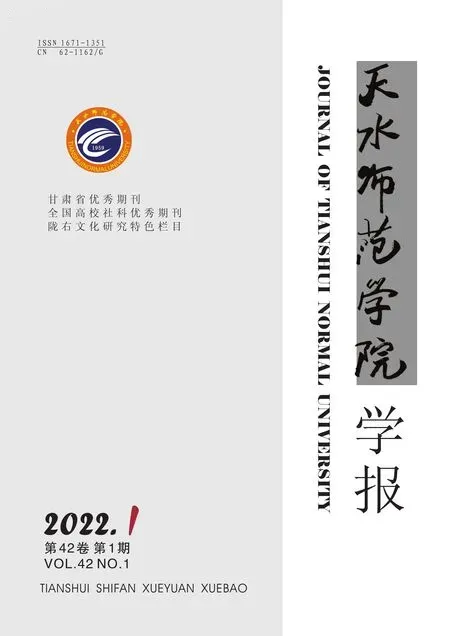论古代敦煌人的道德社会化
——以敦煌碑铭赞为例
买小英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古代敦煌以河西走廊为纽带,向东连接中原腹地,自西通达西域和中亚。在古丝绸之路沿线经济、贸易、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下,敦煌地区逐渐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社会结构,由此形成地域性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构建起了古代敦煌社会成员实现社会互动、学习道德规范、内化道德价值和培养道德情操的内在机制,以此推动人们道德行为的养成和确立。这种演变过程或发展轨迹既是一个社会群体道德社会化的发展过程,也是社会化过程中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它实现的是社会道德规范的内化以及社会角色的形成。[1]102
本文以敦煌碑铭赞为例,从认同道德规范、明晰道德关系和形成道德人格等方面来阐释古代敦煌人道德行为的养成和确立过程,以及他们在社会道德教育和个体道德修养的共同作用下道德社会化的实现路径。
一、认同道德规范
道德规范古已有之,19世纪英国历史法学派代表人物亨利·梅因曾在《古代法》里讲过一句颇具方法论意义的话:“现在控制着我们的行动以及塑造着我们行为的道德规范的每一种形式,都是由古代社会胚胎发展而来的。”[2]69
自汉代伊始,敦煌就与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公元8世纪,吐蕃先后占领河西陇右后,敦煌便与中原地区隔绝。张议潮大中二年于敦煌起事,赶走了吐蕃统治者节儿,收复瓜沙二州,结束了吐蕃在敦煌的统治。大中三年收复甘州、肃州,大中四年收复伊州,咸通二年收复凉州,形成东起灵武,西至伊吾的辖区。[3]16纵观敦煌自汉立郡以来的社会历史发展脉络,其间虽然经历了吐蕃长达百年的占领与统治,但自古传承与延续而来的中原人文思想与文化传统依然存在。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在特定的社会必然性中,这些规范是历史形成的”。[4]317敦煌社会中人与人以及人与群体之间的道德规范、道德标准、道德价值同样根深蒂固。
如S.6537《社条》中记载:
“敦煌胜境,凭三宝以为基,风化人伦,藉明贤而共佐。君臣道洽,四海来宾,五谷丰登,坚牢之本,人民安泰,恩义大行,家家不失于尊卑,坊巷礼传于孝宜。”[3]20-21
可见,当时敦煌社会以佛教信仰为基础,全社会均呈现出一派和谐繁荣的景象:君臣关系融洽,人们礼尚往来,家家粮仓丰盈,户户安居乐业,邻里之间和谐共处、尊礼守法。
再如P.3451《张淮深变文》中记载:
“又见甘凉瓜肃,雉堞彫残,居人与蕃丑为肩,衣着岂忘于左衽;独有沙州一郡,人物风化,一同内地。”[3]21
这里是说,晚唐五代时期河西走廊地区的甘州(张掖)、凉州(武威)、瓜州、肃州(酒泉)等当地人的着装大都受到吐蕃人的影响,风格已发生改变,唯独沙州(敦煌)一地的人们依然保持着中原的道德规范和民风习俗。
与此同时,这种承袭了中原传统的道德规范还为敦煌人有效参与社会生活提供了所必需的知识、态度、价值观和行为标准。
如P.2641《莫高窟再修功德记》中写道:
“人贤地杰,物产珍奇,乡闾只务于谦恭,士庶各怀于佛道。”[3]21
P.4640《沙州释门索法律窟铭》中记载:
“人驯俭约,风俗儒流,性恶工商,好生恶煞,耽修十善,笃信三乘。”[3]21
从上述这些记载来看,晚唐五代时期敦煌社会的道德规范是被普遍认同的,整个社会群体既信仰佛教,又推崇儒风。
至此,道德社会学的研究者也许会质疑:古代敦煌人普遍接受的价值观、思想和行为方式,这种认同及道德规范的遵守是否与实现个人自由达到了内在的统一,抑或这些群体依然只是一些被动的墨守成规者?实际上,从现存文献资料来看,古代敦煌人认同及遵守道德规范与实现个人的自由是内在统一的。
如P.2385《释门应用文范》是为父母写经的发愿文,其中写道:
“(前略)伏惟先考工部尚书荆州大都督上柱国周忠孝公赠太尉、太子太师、太原王,风云诞秀,岳渎毓英,赞纲地之宏图,翊经天之景运。先妣忠烈夫人太原王妃,蹈礼居谦,韫七诫而乘裕;依仁践义,总四德以申规;柔训溢于丹闱,芳徽映乎彤宫;资忠奉国,尽孝承家;媛范光于九区,母仪冠于千古……”[3]7
这段范文说明,古代敦煌人将为父母追福祈愿作为其行孝、尽孝的重要途径之一。
再如P.3608《大唐陇西李氏莫高窟修功德记》(因该碑立于大历十一年,故简称《大历碑》)中写道:
“时有住信士朝散大夫郑王府咨议参军陇西李大宾,其先指树命氏,紫气度流沙之西;刺山腾芳,鸿名感悬泉之下。时高射虎,人望登龙。开土西凉,称藩东晋。咨议即兴圣皇帝十三代孙。远沠天分,世济其美,灵根地植,代不乏贤。六代祖宝,随使持节侍中西陲诸军事镇西大将军领护西戎校尉开府仪同三司沙州牧敦煌公玉门西封邑三千户。曾王父达,皇敦煌司马,其后因家焉。王父操,皇大黄府车骑将军。烈考奉国,皇照(昭)武校尉、甘州和平镇将。早逢昌运,得展雄材。一命是凌云之姿,百龄怀捧日下之庆。垂条布颖,业继弓裘。筑室连闳,里成冠盖。难兄令弟,卓然履道之贤;翼子谋孙,宛尔保家之主。咨议天授淳粹,神假正直;交游仰其信,乡党称其仁。”[5]19
此碑文刻于敦煌莫高窟148窟前室南厢碑之北向,其内容例数了李氏家族的渊源及其历代祖上的功德及品行,说明此种世代相传的家风、门风是一脉相承的。
由此可见,古代敦煌人是将个体的家族传承、家庭幸福、人生追求、功德成就等与国家、民族的兴衰和命运,以及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已经厚植在敦煌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之中。据现存敦煌文献可知,这些大量撰写或抄录下来的碑铭赞、邈真赞或斋文、愿文中都饱含着浓厚的家国情怀和乡土情愫,其中充分表达出古代敦煌人对自我文化身份的选择与认同,以及内心深处难以割舍的文化孺慕和历史归属感。这都说明他们是作为积极自由的个体与社会整体实现并存。历史也充分证明,他们能够也确实创造和改变了敦煌本土文化与社会的结构。
二、明晰道德关系
道德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在人们的道德活动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依赖关系和各种联系的总和”。[6]272根据主体和客体的不同,可以把道德关系简化为“个人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个人同个人之间的关系”。[7]48古代敦煌人在处理个体与个体之间和个体与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时,是在继承中国传统儒家道德关系的社会角色及其道德规范的基础上,糅合佛教义理与佛教思想元素,形成了具有敦煌地域特点的儒释道德关系。
(一)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往往是通过特定的社会角色及其规范表现出来的。社会角色是“与人们的特定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是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它构成社会群体或组织的基础”。[1]107古代敦煌人正是在家庭关系中实践着父母、夫妻、子女等角色,在社会关系中实践着臣子、师徒、朋友等社会角色。
1.家庭关系中的角色
如北图冈字44《佛说阎罗王授记经》中写道:“四月五日,五七斋,写此经,以阿娘马氏追福,阎罗之子,以作证明,领受经功德,生于乐处者也。”[4]59《佛说护诸童子经》中写道:“四月十二日,是六七斋,追福写此经,马氏一一领受写经功德,愿生于善处,一心供养。”[4]59《般若心经》中写道:“四月十九日是收七斋,写此经一卷,以马氏追福,生于好处,遇善知识,长逢善和誊属,永充供养。”[4]59-60P.2055《佛说盂兰盆经》中写道:“六月十一日是百日斋,写此经一卷,为亡母马氏追福,愿神游净土,勿落三途。”[4]60《大般涅槃摩耶夫人品经后题作佛母经》中写道:“为亡过家母写此经一卷,周年追福,愿影游好处,勿落三途之载,佛弟子马氏一心供养。”[4]60
以上文本是子女为亡母马氏在五七斋、六七斋、七七斋、百日斋以及周年斋时所抄写的用于祈福发愿的经文,体现出子女同父母之间的孝亲关系。
再如P.4640《张潜建和尚修龛功德记》中所表达的就是兄妹之间的关系:
“妹尼妙施,习莲花之行,慕爱道之风;遮性皎而无瑕,寂照悬而颖悟。兄唱妹顺,罄舍房资。妹说兄随,贸工兴役。既专心而透石,誓志感而随通。不逾数稔,良工斯就,内素并毕。”[4]83
2.社会关系中的角色
如P.4640《沙州释门索法律窟铭》中记载:
“和尚俗〔姓索〕,香号〔义辩〕。其先商王帝甲之后,封子丹于京索间,因而氏焉。远祖前汉太中大夫抚,直谏飞龙,既犯逆鳞之势,赵周下狱,抚恐被诛,以元鼎六年,自钜鹿南和徙居于流沙,子孙因家焉,遂为敦煌人也。”[4]72
在这篇文本中提到,沙州释门索法律的远祖因逆天子之意而下狱,其子孙被迫迁徙至敦煌的故事,体现出王权至高无上,社会尊卑有序的君臣关系。
如P.4640《住三窟禅师伯沙门法心赞》中写道:
“从事随旆兮东征,凌霾霰兮万里扬旌。复河湟之故地,运鹤烈之雄足。美军中之赳赳,实武幕之将星。东收神武(乌),西接二庭。军屯偃月,拔帜柳营。子能顿悟,弃俗悛名。寻师落发,割爱家城。潢(湟)源受具,飞锡翱形。归于宕谷,亚果精研。有无都泯,浊流本清。红莲拔淤,俱可有情。同镌此窟,雕碑刻铭。”[4]80
文本的末尾无撰写人署名及撰写题记,但依据内容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篇为禅师伯沙门法心所做的赞文,体现出撰写者对禅师伯沙门法心的敬仰与赞誉。
再如P.4640《先代小吴和尚赞》中写道:
“希哉我师,戒行标奇。处中(众)有异,当代白眉。量含江海,广运慈悲。戒珠圆洁,历落芳菲。一方法主,万国仍希。禅杖恤茷,性海澄淤。帝王崇重,节相钦推。都权僧秉,八岁蒙施。示疾方丈,世药难治。阎浮化毕,净土加滋。声闻不悟,忧苦生悲。菩萨辽达,生死如知。灵神证果,留像威仪。名传万代,劫石难移。”[4]89
这篇文本是窦良骥为吐蕃统治敦煌时曾出任都教授的吴洪辩所写的赞文,表现的是师徒关系。
(二)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
由于群体又可以作更细致的划分,致使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也会因群体范围和等次的不同而表现出多种形式:比如,个体与作为初级群体的家庭之间的关系、个人与作为正式组织的职业群体之间的关系、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个人与民族、国家的关系等。
1.个体与家庭之间的关系
如P.4660《敦煌阴处士邈真赞并序》中写道:
“风云秀士,望重始平。孤高卓荦,独擅其名。游心物外,守志英灵。训严众子,肃穆家庭。门臻余庆,终洽遐龄。克俭克让,高揖辞荣。”[4]154
这里提到了敦煌阴嘉政同家人之间的关系。
再如P.4638《曹夫人宋氏邈真赞并序》中提道:
“妇道俱明,轨范恒彰于五郡。温恭立性,高名传九族之中。愕节清贞,美响透六亲之内。……母仪婉顺,妇礼寻常。冰姿皎洁,桃李争芳。操越秋妇,德亚恭姜。谋孙育子,训习忠良。方保受荫,岳石延长。”[4]225
此处提到了曹议金夫人宋氏在家族六亲中的声名地位,以及为母、为妇时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2.个体与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
如P.4660《张禄邈真赞》中写道:
“龙沙豪族,塞表英儒。忠义独立,声播豆卢。仁风早扇,横亮江湖。有德有行,不谓不殊。闺门孝感,朋友言孚。家塾文议,子孙徇德。事君竭节,志守荣枯。洞归(赜)政法,安然不徂。夜泉忽奄,悲云四颫。神剑溺海,过隙潜驹。千秋美誉,应同玉壶。”[4]166
文中提到张禄的事迹及其德行与仁义,反映出他同家族、朋友、同僚之间的关系。
再如P.4660《译经三藏吴和尚邈真赞》中写道:
“大哉辩士,为国鼎师。了达玄妙,峭然天机。博览犹一,定四威仪。就(鹫)峰秘密,阐于今时。西天轨则,师谓深知。八万既晓,三藏内持。桧叶教化,传译汉书。孰能可测,人皆仰归。圣神赞普,虔奉真如。诏临和尚,愿为国师。”[4]188
这里记载了吴法成和尚的事迹,体现出吴和尚同信众之间的关系。
3.个体与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
前文提到,古代敦煌人始终将个体的家庭幸福、家族传承、人生追求、功绩成就等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以及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在敦煌文献中常常能看到这样的记载,如P.4660《康通信邈真赞》中写道:
“懿哉哲人,与众不群。刚柔相伴,文质彬彬。尽忠奉上,尽孝安亲。叶和众事,进退俱真。助开河陇,效职辕门。横戈阵面,骁勇虎贲。番禾镇将,删丹治人。先公后私,长在军门。天庭奏事,荐以高勋。姑臧守职,不行遭窀。他乡殒殁,孤捐子孙。”[4]114
再如P.4660《令狐公邈真赞》中也写道:
“温良恭俭,信义资身。治官清恪,爱富怜贫。勉修农战,息马养人。心坚铁石,志烈情存。助收河陇,效职辕门。行中选将,节下选陈。前矛直进,后殿虎贲。三场勇战,克捷成勋。”[4]144
这两篇文献中记述和赞颂了敦煌人康通信、令狐公等为官时期爱国为民、尽忠职守、骁勇善战、保家卫国的英勇事迹。
由此可见,古代敦煌人在处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体与社会群体之间关系的过程中,积极地实践着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他们的努力实践及在角色规范之间所产生的互相关联,不仅形成了敦煌社会的“差序格局”(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5]25,而且也构成了敦煌地区特定的社会人伦关系。可以说,古代敦煌人在不同的社会角色中,不仅实践着个体与不同群体的道德关系,而且在社会实践中积极地处理各种关系,在不同的社会角色和规范中更好地实现着他们的人生价值。
三、形成道德人格
道德人格与人格的含义紧密相连。人格指的是“特殊的思想、感觉和自我观照的模式,它们构成了特殊个体的一系列鲜明的品质特征”。[8]147道德人格强调的是个体人格的道德规定性,“是一个人做人的尊严、价值和品格的总和”。[7]183
中国传统的道德人格注重个人修养,特别强调个人的修养境界,注重培养理想人格,追求个人道德价值的彰显;同时对理想人格、道德价值、至善的追求也是对人生幸福的追求。古代敦煌人的道德人格处处渗透着中国传统的人格论,同时还充分利用了佛教等非中国传统哲学的人格思想。
如P.4638《曹良才邈真赞并序》中写道:
“秉心洁己,清名久播于人伦;端直守忠,奉上贞心而廉慎。……威权将略,恩广义深。遂乃别选携持,重迁大务,荣加五州都将,委任一道指挥。更乃恪节当官,不犯清闾之道;差科赋役,无称偏傥之音。断割军州,例叹均平之好。遂使八方赞美,声传于凤阙之中,四道扬名,德播于丹墀之内。”[4]255
这里提到的曹良才很有可能是敦煌莫高窟第108窟甬道北壁西向第四身“故兄归义军节度应管内二州六镇马步军诸司都管将使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谯郡曹□□一心供养”中的“曹□□”。[9]文本中写出了曹良才为人忠诚刚直、克礼守节,其高尚的德行声名远扬、备受赞许。
再如P.3720《都毗尼藏主阴律伯真仪赞》中写道:
“大哉物望,可赞可扬。戒圆白月,郁郁桂香。天资纯善,生惧探汤。门传积庆,花萼流芳。禅枝异秀,律纲奇(足罔)。群氓导首,苦海舟航。学业无倦,修文有郎。富不奢泰,贵不优倡。尊礼重乐,靡损于常。斯人鲜矣,难测难量。代传法印,家盛人康。始平起义,随官敦煌。清廉众许,令誉独彰。”[4]266
这里记载的是前敦煌都毗尼藏主阴律伯的生平事迹,反映出阴律伯天性纯善、聪慧好学、尊礼重教、清廉节俭的品格。
又如P.2991《张灵俊和尚写真赞并序》中写道:
“和尚早岁出家,童祯(真)学业。心灵似皎月,明利性而宿同。自得情怀金石,恳慕真空。龄当弱冠之初。道亚生融之迹。业资惠海,德爽智山。证三教而精通,修四禅而凝空。……石基案上,亲传孔父之文。师子座前,广扇真风之理。故得三场演教,指极相应之宗,窍尽不思议之际。芳兰之义,恒播布于人伦。异类程凝,追机缘而辫化。千千释众,举郡皆嗟。万万法徒,刚柔同叹。”[4]323
序中记载的是敦煌灵图寺僧张灵俊的生平事迹,反映出张和尚自幼聪颖好学,成人后明镜高尚,深谙佛教义理,广授弟子,其为人与学识深得众徒敬仰和赞许。
通过以上文献中所记载的内容,反映出古代敦煌人的道德规范、行为举止、道德品质、道德修养不单单是社会规范、道德关系所施加的规定与要求。就其个体而言,这些规范和行为已然成为他们日常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当然,从文本产生的历史渊源来看,邈真赞本身即是对主人翁功德业绩的赞颂,其内容自然要以赞颂、褒奖为主。此类文本能作为敦煌寺学学生们学习时的范文传抄下来并流传后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古代敦煌人是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认同、提倡并以此为典范的,进而承袭和推崇这种由做人的尊严、崇尚的价值和践行的品格等聚合在一起的道德人格。
黑格尔说:“道德的意志是他人所不能过问的。”[10]111所以说,那些合乎道德的行为举止,光靠认同社会的道德规范、遵守群体纪律、明晰道德关系从而实现对群体的效忠显然是不够的。除此之外,还必须对个体的行为有理性的认识和理解,进而将其升华为道德自觉,也正是“这种自觉意识为我们的行为赋予了自主性,从此时起,公共良知要求所有真正的、完整的道德存在都具备这种自主性。”[11]118
从上述例文中可以看出,道德人格其实就是强调人所特有的道德规定性,它构成了一个人比较稳定的内在精神结构,并由此产生出前后相继、首尾一贯的行为倾向和生活态度,在面对好与坏、善与恶、高尚与卑下的情境时,能够做出合理的道德选择,体现出稳定的立场和态度。这正是个体道德人格的集中体现。古代敦煌人的道德人格在某种程度上也具备了“自我”“自主性”“自觉”,以及“主体完整性”,并相互联系、彼此作用,从而形成了社会整体的人格。
四、实践道德社会化
按照道德社会学的观点,道德社会化的实现途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道德教育,二是个体的道德修养。社会化的过程涉及一系列广泛的个人、群体和机构。古代敦煌人的道德教育同样经历了社会和个体两个方面。
(一)社会的道德教育
据现存敦煌文献可知,敦煌地区最迟在汉平帝元始年间就已建立较为完备的地方官学教育机构。[10]30至唐代,沙州地方官学已设有州学、医学,州学内建有孔庙。敦煌县、寿昌县设有县学,县学内也建有孔庙。除州县官学之外,还有乡村学校(义学或私学)的存在。[12]164-165由此可见,唐代时,敦煌地区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州(郡)学、县学、医学,以及乡村义学(私学),且在州县学内均建有孔庙。[13]不仅如此,敦煌还设有道学和寺院教育。
虽然敦煌的社会教育有官学、私学之分,但其教授和学习的教材大都以儒家经典为主,内容都以文、行、忠、信为主,侧重为人处世、德行礼乐及修身立行的道德教育。如针对儿童的蒙学教育,所教授的内容就包括《开蒙要训》《古贤集》《太公家教》《辩才家教》《崔氏夫人训女文》等道德类书籍,通过思想道德教育,培养儿童的孝悌观,注重习性以及意志品质的塑造;针对普通民众的寺院教育,学习的内容有《孝经》(如P.3396《孝经一卷》等)、《论语》(如P.3433《论语集解》、P.2716《论语卷第七》等)以及五经等,还有《释奠文》《祭社文》《祭雨师文》等规范吉礼祭祀文书,以及《大目键变文》《忏悔文》等佛教道德类文本等,通过这些教育使人们树立忠君观,树立家庭伦理观,关注个人品行修养等。
可见,古代敦煌人所接受的社会教育,主要是地方政府承担主要职责,同时充分调动寺院等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其教育的内容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道德行为准则上推崇忠、孝、节、义、仁、礼、智、信等。
(二)个体的道德修养
个体的道德修养主要是指“人们在道德品质、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习惯等方面进行的自觉的自我改造、自我陶冶、自我锻炼和自我培养功夫。”[14]456古代敦煌人深受中国儒家传统道德思想的熏陶,同时又吸收佛教思想的精髓,对个体的道德修养有着更深层次的追求与向往。
佛教重视心性的修行,在宗教实践上重视内心的自证自悟,在道德修养上重视内心的行善积德。如敦煌文献中的《施入疏》就充分体现出敦煌人行善积德的种种善举。
如S.3565《河西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浔阳郡夫人等供养具疏》中写道:
“弟子敕河西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太保曹元忠以浔阳郡夫人及姑姊妹娘子等造供养具疏。造五色锦绣经中壹条,杂彩幡额壹条,银泥幡施入法门寺,永充供养。右件功德今并圆就,请忏念。赐紫沙门闻。”[15]98
如S.5973《宋开宝八年(975)二月归义军节度使曹延恭施入回向疏》中写道:
“布叁疋充大众,布壹疋充大像,绯锦紬壹疋充法事。右件讲畅舍施所申意者,伏以有碍家国,要凭无上胜因。今车取舍之少财,投如来之大道,虔诚法会,求乞福圆……”[15]103
以上两篇《施入疏》都是供养者为寺院布施各类物品的记载。实际上,古代敦煌人布施的行为十分普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一种常态。他们相信,勤于布施的人不但可以在现世得到福报,而且此福德还能“次第传生,至后世身”。[16]223
与此同时,个体的道德修养离不开家庭的教育。在家族传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各自家庭特点的道德规范,而后世子孙正是通过家庭教育的方式使其道德规范世代相传,构建起本家族的家风传承。[17]
如P.2625《敦煌名族志》中记载了索氏家族成员累世为官的盛况:
“后汉有索頵,明帝永平中为西域代戊己校尉,居高昌城。頵子堪,字伯高,才明,举孝廉、明经,对策高弟(第),拜尚书郎,后迁幽州刺史。其抚玄孙诩,字厚山,有文武才,明兵法,汉安帝永初六年拜行西域长史。弟华除为郎。华之后衾,字文长,师事太尉杨赐展。孙翰,字子曾,师事司徒,即咸致仕官。宗人德,字孟济。祖毅,太尉椽。父桓,杜陵令。德举孝廉,拜驸马都尉,桓帝延熹元年,拜东平太守。子韶,西部长史。祖子降,子祖,其父宜,清灵洁静,好黄老,沉渗笃学,事继母以孝闻。族父靖,字幼[安],与乡人张彪、索珍、治衷、索馆等五人俱游太学,号称‘敦煌五龙’。四人早亡,唯靖该博经史,兼通内纬。”[18]103
由此可知,从两汉到魏晋时期,索氏家族累世仕宦,且个个才德兼备。其家族成员文化修养较高,大多出身于孝廉、明经等科,为索氏家族“礼乐传家”的优良家学教育传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索氏家族之所以能在敦煌的历史舞台上经久不衰,与此家学传统是密不可分的。[19]
P.4660《索公邈真赞》中对索公的记载:
“间生英杰,颖拔恢然。阀阅贵泒,毅勇军前。松筠秉节,铁石心坚。文武双美,荣望崇迁。横铺八阵,操比苏单。韬黔莅职,忠孝骈联。奇眸卓荦,㑺异貂蝉。功庸阜绩,名播九天。”[4]168
这里是说,索奉珍和索公等索氏后代子孙与他们的先祖索靖、索琳一样忠于君国。
P.4638《大番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公修功德记》中记载:
“江边乱踏于楚歌,陇上痛闻于豺叫。袅声未歼,路绝河西。燕向幕巢,人倾海外。羁维板籍,已负蕃朝献血盟书,义存好舅。熊黑爱子,拆掇袱以文身鹤鸯夫妻,解鬓锢而辫发。岂图恩移旧日,长辞万代之君事遇此年,屈膝两朝之主。”[4]239
该文认为,包括阴氏在内的敦煌大族之所以投降吐蕃,并不是对忠义家风的摒弃,而是在当时特殊环境下,秉承儒家大忠的内涵而采取的大义之举,这也是对传统忠君忠国所作出的适时调整。[19]
再如S.530《大唐沙州释门索法律义辩和尚修功德记碑》中记载,吐蕃时期索氏家族的索清政被时人誉为“礼乐名家,温恭素质”。这里的礼乐文化是中原传统教化伦理道德的重要形式。还有唐代敦煌高僧、释门都法律索智岳虽“早明梦幻,喜预真诊,投绪割爱,顿息攀缘”“真乘洞晓”,但是他对于中原传统文化也能做到“儒墨兼宣”,在道德规范上也坚持儒家所提倡的“门传孝悌”。[4]170
总之,敦煌的大族、高僧等在唐、蕃交替统治敦煌时期,个体及家庭成员都能以“居敬”“穷理”“内省”“慎独”“省察克治”“积善成德”等规范自我,维持着以“忠”“义”等为代表的礼法、道德与家风。
综上所述,古代敦煌人将个体与群体的兴衰、命运同社会历史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传承和延续着中原内地的道德规范、道德标准、道德价值等。他们在处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时,合理地实践着家庭关系中的不同角色和社会关系中的社会角色;同时,在处理个体与社会群体之间关系时,平衡着个体与家庭、个体与群体以及个体与社会、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并在规范中积极地实践各类关系所产生的相互关联,在敦煌地区社会道德教育和个体道德修养的共同作用下实现着道德的社会化。
由此可见,道德社会化对于社会个体和社会共同体来说都是必需的。对社会个体而言,道德社会化是个人融入社会的基本途径,在这个过程中“自我”得以确立、个人的德性品质得以形成和完善,实现了从生物人向社会人的转变;对社会而言,“只有当一个社会的成员一起行动共同支持、维护这个社会的时候,这个社会才会生存下去,所以每个社会都会塑造成员的行为来达此目的”。[8]142即通过道德社会化的过程,培养出一定社会所需要的社会成员,同时民族的道德传统才能得以积累和延续,社会的道德秩序才能得以维持和发展。[20]敦煌亦如此。